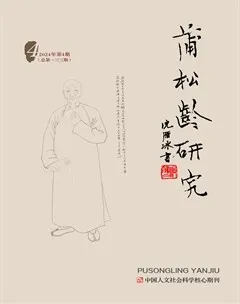清代聊齋戲對《聊齋志異》的接受、改編與誤讀
摘要:錢維喬創作的傳奇《鸚鵡媒》是目前可考最早的一部聊齋戲,也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從選材來看,聊齋戲是一類特殊的戲曲,體現著文壇、曲壇對《聊齋志異》的接受與理解。以《鸚鵡媒》為個案,分析其對《聊齋志異》的接受、改編與誤讀,發現:錢維喬一方面對《阿寶》的人物、情節、主旨和藝術特色進行了符合傳奇體式的接受與改編,兼采《牡丹亭》等前代傳奇的營養,宣揚符合綱常名教的才子佳人式至情;引入“互夢”與“對鏡寫真”兩大敘事母題并與《牡丹亭》形成互文,是《鸚鵡媒》的亮點所在。另一方面,劇作改編后人物形象的異化、庸俗化及情節的蕪雜也偏離、降低了《阿寶》原作的格調和詩意風韻,存在一定誤讀。
關鍵詞:聊齋戲;《聊齋志異》;《鸚鵡媒》;接受;誤讀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聊齋志異》一經問世便在文壇引發震動。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聊齋志異》第一個刊本(青柯亭本)刊行不久,即有“聊齋戲”問世。至清末,已知的聊齋故事被改編為雜劇、傳奇的約有二十種;到了近代,京劇和各種地方戲曲中改編、上演的聊齋戲估計在一百五十種以上。[1]1《聊齋志異》為戲曲作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他們對《聊齋志異》中的一篇或多篇經典故事進行情節、人物等方面的剪裁、改編和重構,度之以曲譜,形成了蔚為大觀的聊齋戲戲曲系統。經研究者確認,錢維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創作的傳奇《鸚鵡媒》是目前已知最早具有完整劇本的聊齋戲 [2]27,該作以《聊齋志異·阿寶》為藍本,兼采《牡丹亭》《西廂記》等前代才子佳人戲之養料,在清代聊齋戲中屬于上乘之作,其與《聊齋志異》及其他戲曲乃至乾嘉文壇、曲壇傳統間的關系值得認真審視。本文立足于傳奇《鸚鵡媒》文本并側重于將其視為《聊齋志異》的一種接受形式,通過其與《阿寶》及《牡丹亭》等傳奇的對照比較,分析聊齋戲《鸚鵡媒》對《聊齋志異》的接受、改編與誤讀。
一、《鸚鵡媒》對《聊齋志異·阿寶》的接受
傳奇《鸚鵡媒》分上下兩卷,共四十出,劇作的主體情節對《聊齋志異·阿寶》幾乎沒有改動。全劇圍繞孫子楚和王寶娘的生死情緣展開,牢牢抓住小說中主要人物孫子楚的最重要特質——“癡”,并側重于愛情表現方面,塑造出宜于才子佳人戲的志誠情癡孫子楚形象。《斷指》《社晤》《神遘》《酬詠》《韻感》等出在男女相思、戀愛方面寫心尤其細致入微。如《斷指》中,孫子楚偶見寶娘春容而傾心,乃至茶飯不思,托媒人說親,在書齋坐立難安:“窗兒曉,恁遲延辜人懇托。巫媽媽說今早便回音,怎不見來?敢則丈人行絮的忒裝喬,早難道女冰人忘了?” [1]27媒人終于上門告知求親失敗,孫子楚先是懊惱:“只是小姐,你但得個才郎,便小生多了個指兒,有甚爭差也?” [1]28后又自言自語,自慚形穢:“我也休如此說,想小姐何等俊容?我這指兒實在也有些可憎。天那!你何苦偏在我孫子楚身上多生這一個指兒?” [1]28-29進而生出割指念頭,只愿打動佳人芳心:“我形慚穢,魂待銷,一指拼教和淚拋。只是好不痛人,如何下手?……我孫子楚若得小姐見憐,就死也何惜!情真敢惜惺惺報,霜鋒欲引心撲跳。小姐,小姐!我命鴻毛,只這血痕一縷,滲著您心苗。” [1]29孫子楚斫指前的畏痛猶疑,下決心時的心理斗爭和對寶娘的癡戀情深都十分生動而真實。《阿寶》對孫子楚的斷指僅以簡單敘述“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一言帶過,《鸚鵡媒》對其作了符合傳奇體式的詳盡細膩描寫,是一次成功的跨文體接受與再創造。
《阿寶》云:“性癡,則其志癡,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 [3]243贊揚心性純凈、專一,對鐘愛事物矢志不渝的“癡人”。在劇作思想上,《鸚鵡媒》將孫生之“性癡”演繹為“除俗慧,剛養得如愚之氣”“小生有一癖性,最恨那輕浮面目,才非嵇阮,徒貌狂蹤;更厭的機械心腸,志乏儀秦,漫夸辯舌” [1]3的清高狷介、不流時俗,并對“情癡”部分加以突出,既符合才子佳人戲的題材需要,也較好地貼合了《阿寶》乃至《聊齋志異》全書的精髓。
值得注意的是,《鸚鵡媒》在搬演才子佳人婚戀的主線劇情之外,亦花費不少筆墨描寫人生不得志與命運不如意。劇中有失意士子孫、李兩生困頓于場屋的窘迫和懷才不遇的壓抑:“都則為儒冠輕惹,受了磨折,兩般兒才命難協。漭長虹向螢案羈紲,便教你阿堵神通作論嗟,注就這書生囊篋。枉擔著五車賣弄,趕不上一貫傳呼,算將來吾道非耶!” [1]112有忠貞之臣于謙生前因君主不明、奸佞誣害而屈死的一腔悲憤:“一班兒怨著俺堂堂正正舊時攔縱。下的個惡惡狠狠的擠,密密切切的慫,磕磕磣磣、牢牢逼逼天柱催崩。苦的俺悠悠浩浩。昏昏慘慘丹心一夢,只落得半腔兒郁郁騰騰化作長虹碧血中。” [1]146有寶娘失卻愛侶,生死別離陰陽兩隔的摧折心肝:“恁教人昏沉黑漆,生隔著疼熱噯夫妻。他那里颭寒燈敢見的人單只,俺這里對廬帷抓不到影兒隨。說甚么魚和水,轉眼里幽棺一閉,真和你即世見無期。” [1]140在《鸚鵡媒》的世界里,不論癡男怨女還是孝子賢臣都往往時乖命蹇,可謂“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全劇始終籠罩著揮之不去的哀傷氛圍。即使是在劇作的結尾,孫子楚與寶娘、李含輝與倩奴兩相完婚各成眷屬,且金榜高中,團圓合聚之際,作者安排他們天竺進香,合唱:“算即空是色是空名,法喜勘無憑。……看破這一枕琉璃大地幾人醒。莽因緣,難折證,死生夢幻總因情,除則蕭寺晨鐘和著這殘拍聲。” [1]170佛家勘破世事、空無寂滅的消極情緒沖淡了言情的纏綿和團圓之歡樂,讓《鸚鵡媒》成為一出帶有悲情色彩,“不完滿”的喜劇。
梁溪楊芳燦蓉裳氏撰《鸚鵡媒傳奇序》有言:“真珠密字,和淚點以俱圓;疊雪輕綃,寫愁絲而不斷。人之情也,能無嘆乎!所以辭緣苦而彌工,言因悲而轉幻。” [1]172點明了《鸚鵡媒》的悲劇性及成因。錢維喬出身書香門第,學貫古今,詩文皆精,尤擅書畫,兼通音律,自號竹初,“予性頗愛竹,謂其致蕭疏” [4]99,追求高尚的人格,身為一位難得的藝術全才卻一生經歷坎坷。竹初少年早慧,二十三歲(乾隆二十六年)得中舉人后卻六次會試不第,早歲起相繼失去父母、幼子幼侄、兩位妻子和兄姐,長期困頓場屋,一生沉淪下僚。乾隆三十三年,十七歲便嫁與竹初的結發夫人汪氏早逝。錢維喬倍感喪妻之痛和人生艱難,取《孔雀東南飛》劉蘭芝故事譜成《碧落緣》傳奇二卷,又作《鸚鵡媒》傳奇寄托哀思。《鸚鵡媒》中癡心耿介、不愿流俗的孫子楚和超越生與死、人與物的夫婦至情正是錢維喬本人心照。可以想見錢維喬在讀到《聊齋志異》時,兩位“塵世傷心人”相逢于筆墨,劇作家的心靈定然與一生苦行、孤憤著書的蒲松齡碰撞出共鳴。
伊瑟爾指出,文學作品是一種交流形式,在文本和讀者之間存在一個雙向交互但不對稱的交流結構。[5]163文學作品本身既不同于閱讀前的文本,也不同于在閱讀中的文本的具體實現,而是在文本和閱讀之間,兩者在交流的過程中相互作用的結果。換而言之,讀者的閱讀行為本質是與作者的交流與合作以及對文本意義的再創造,文本在歷代讀者的閱讀與接受中也得以煥發新的生機。蒲松齡曾經感嘆:“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渴望以文字召喚知己。從接受美學角度來看,竹初居士和他的《鸚鵡媒》可算得上異史氏的翰墨知音了。可以說,《鸚鵡媒》是錢維喬對《聊齋志異》在人生、心靈共鳴基礎上的接受。縈繞全劇的蕭散抑郁之氣也與蒲松齡寫作《聊齋志異》“發憤之作”的動機相合。
二、《鸚鵡媒》對《聊齋志異·阿寶》的改編
《聊齋志異·阿寶》篇幅短小,全文不足兩千字,將其敷演成長達四十出的傳奇劇目,必然需要對原作進行擴充和改編。《鸚鵡媒》對《阿寶》的改編主要體現在戲劇情節的極大豐富、人物形象的重構與濃縮、母題的提煉與鋪陳,以及對《牡丹亭》等前代傳奇作品精華的吸收上。
(一)《鸚鵡媒》對《聊齋志異·阿寶》情節、人物、母題的改編與重構
《鸚鵡媒》在尊重《聊齋志異·阿寶》原貌的同時,極大豐富了戲劇情節。小說《阿寶》中,阿寶與孫子楚的姻緣源自一句戲言和清明出游的偶然邂逅,阿寶“夢與人交”和孫子楚心有所念,“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去,直達寶所”的經歷具有很強的神秘性和奇異浪漫色彩。可以說,《阿寶》中孫、寶兩人的生死姻緣更像不可知力量支配的產物。蒲松齡有意在文本中保留的某些空白和懸念增添了小說的張力和詩意,但對于敘事性顯著增強,且需要考慮劇本舞臺演出效果的戲曲文體而言,情節的完整性與豐富性要求顯然更高。是故,《鸚鵡媒》開篇即借夢神之口將孫生、寶娘二人的婚戀設定為觀音大士指明的“姻緣夙定”,并安排孫子楚夢游王家后園,在粉壁上讀到藏有寶娘閨名、預言兩人愛情波折的詩:“欲識人間美,全憑物外身。寶山應不遠,須結再生因。”鸚鵡與畫像的傳情,春社的初遇到互夢的定情,背后都有一條觀音大師的法旨為線索,牽引著孫生寶娘二人演繹出一幕人可以物、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宿命姻緣故事,全劇的情節和波瀾較之《阿寶》明顯增強,但是線索清晰,脈絡完整,繁而不亂。
道具的巧妙安排也增添了劇情的波瀾,二人在第十一出《社晤》清明春社初遇之前已以鸚鵡為媒產生了千絲萬縷的關聯。《阿寶》中地位和作用并不十分突出的鸚鵡,被《鸚鵡媒》賦予了情節和結構的多方面功能。觀音大士將“良緣在上”的鸚鵡在寶娘夢中相贈,后果在市上購得鸚鵡,寶娘十分愛惜,朝夕調弄,自繪春容的契機正是丫鬟所說:“何不自己畫一幅調鸚的行樂消遣情懷?”由此,鸚鵡與寶娘一起入畫,后又被孫子楚偶然見到,一段相思由此種下。這只擁有神性的鸚鵡在寶娘、孫子楚的夢中,猶喚“孫郎”。作者多次用“共命迦陵”等佛教神鳥代指鸚鵡,渲染其靈性和姻緣信使的身份。相思最濃時,孫子楚的靈魂更附在鸚鵡身上,得以親近寶娘傾吐衷腸,終于打動其以身相許,道具的功能得以最大化體現。傳奇發展至乾嘉時期理論已臻成熟,眾多劇作家、理論家在創作與經驗總結時都格外重視道具的作用。舉凡《紫釵記》《風箏誤》《燕子箋》《桃花扇》《梅花簪》等,以道具直接作為篇名的明清傳奇作品數不勝數,《鸚鵡媒》亦然。作家將鸚鵡和寶娘春容兩種道具結合在一起,構建了一條“鸚鵡—畫像—姻緣”的情節鏈條,核心道具鸚鵡既推動情節、緊密針線,又富有詩意和象征意蘊,是道具的一次成功運用。
《鸚鵡媒》情節的豐富還體現在戲劇沖突的增加及典型人物塑造上,二者相輔相成。《阿寶》中取笑、捉弄孫子楚的“諸少年”被濃縮成一個類型化、臉譜化和頗具喜劇色彩的小丑式反派胡俊,并安排其介入寶娘、孫生姻緣之中,既增加了全劇的波瀾,又頗似《西廂記》中的鄭恒和《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馬文才,從而暗合了觀眾、讀者欣賞才子佳人戲的審美期待。寶娘之母亦被塑造成一位貪圖財帛的“糊涂家長”,與寶娘之父——克己復禮、以才貌品行擇婿的王員外形成沖突和鮮明對照,兩人的對話給全劇增加了不少看點和喜劇笑料。如孫生婚后僅二十日便猝逝,員外嘆曰:“這也是你我命運不濟,所以如此。”老安人反唇相譏:“員外,你好眼力,揀得好快婿,真個一快百快!” [1]135-136不由令人捧腹。
《鸚鵡媒》喜劇色彩也是劇作情節改編的亮點之一,該劇的笑料包袱恰似幾點星辰點綴夜空,雖不密集卻閃爍著文人式的機智幽默,殊少市井氣和俚俗氣,給人印象深刻。如第三十二出《危訣》孫生病篤,家人為之延醫診治,丑扮醫官上場,唱了一支【趙皮靴】,巧用中藥名雙關活畫出庸醫混世之態,“論起我心地密蒙,便行業原無遠志。偶檢著本草內幾張故紙,學得個人面前滿口柴胡” [1]129,既生動有趣,又于幽默中刺世。喜劇情節的加入也使劇情更加熱鬧豐富。《社晤》是全劇“笑果”最為集中的一出,于熱鬧的排場戲中既寫男女戀愛風情,又為作者寫心,極顯竹初之筆力。在“春社奔忙”的氛圍中,生、小生、凈、末、外、副凈、老旦、丑、雜、旦、貼依次登場,穿插丑角掉鞋,老旦和副凈科諢的笑料。就在這熱鬧歡樂的氣氛中孫子楚初遇寶娘,一如張生遇鶯鶯般“正撞著五百年前風流業冤”,凝神癡立。此時眾雜扮【游佛殿】齊唱:“普救寺佳人到,張解元著了魔,俏鶯鶯嚇得含羞躲,小紅娘廝趕得輕狂播,法聰僧也惹的蒼蠅餓。普天下佛殿有奇逢,三教堂多少的風流座。” [1]46熟悉《西廂記》的觀眾當會心一笑。《社晤》既有才子佳人愛情喜劇的溫馨歡樂,宜于案頭亦適合場上,更暗合奔放熱烈的原始婚戀:春暖花開之際,青年男女在原野的祭祀儀式上自由結合,為整出《鸚鵡媒》增添了莊嚴華妙的儀式感。值得注意的還有生與小生的一段科白:“太白一代軼才,可惜逃名詩酒;若不是傳奇搬演,這些庸夫俗子那知天上謫仙!(小生)正是,戲劇一端,流傳甚于史冊。這些里閭觀誦,倒得個姓名不朽。我輩若得演入戲場,怕異日不人人知為才子。……只怕長安沒有賀季真,就是青蓮復生,不免寂寞酒肆。” [1]44-45作者在借劇中人之口寫心抒情,傳達對戲曲一道的思考和懷才不遇之感的同時,讀者、觀眾的審美視野也超越了人物和劇情,與作家的心靈實現了一對一的直接對話,無意中實現了“打破第四堵墻”的間離效果,可謂戲曲“寫心”藝術的別樣收獲。
《鸚鵡媒》的成功改編還體現為人物形象的提煉重構,集中于劇作核心人物孫子楚身上。《阿寶》中的孫子楚是一個賈寶玉式的“癡兒”,一個詩性的人物。蒲松齡善于以作詩之法寫小說,將前代詩文掌故不著痕跡地化用,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莊子·駢拇》有言:“駢拇枝指,出乎性哉!”天生六指,后竟因阿寶一句戲言而斬去枝指的孫子楚,其行為全是源于天性,因而自然淳樸、誠實可親,與《莊子》所提倡的天然本真,發自性情之生命理想狀態暗合。其“癡”也具有《莊子》之灑脫詩意。《鸚鵡媒》將孫子楚之癡提煉為情癡,成為一個憤懣于世道不公,知世俗而不世俗的癡情書生,較之《阿寶》中孫子楚的詩性特質有所弱化,而強化了其人生經歷的傳奇性:孫子楚的愛情故事可歸納為“夢中見女—托媒聘女—斷指求女—簾幕窺女—生死得女”,整個歷程奇情異彩。早在鐘嗣成《錄鬼簿》中就常以“奇”“新奇”品評雜劇。到了明清,“戲曲尚奇”已經成為自覺的藝術追求。《聊齋志異》本身就是一部談狐說鬼、講論奇聞異事的“尚奇”之作,《鸚鵡媒》的改編是恰如其分的。
《鸚鵡媒》敏銳地抓住了《阿寶》中最具奇幻色彩的“離魂”母題,秉承“戲曲尚奇”理念將其鋪陳得搖曳生姿。中國古代小說中最為著名的離魂故事當屬陳玄佑《離魂記》,而早在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已有離魂故事出現,《搜神后記》中“匹夫匹婦”故事和《甄異傳》中“王肇”故事均屬此類。《阿寶》是中國古代小說離魂故事的集大成者。傳統的離魂故事中離魂主體往往為思婦,《阿寶》則以男性為離魂主體。孫子楚三次離魂,而三次又各不相同,囊括了中國古代的所有離魂模式。[6]154而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在于孫子楚魂魄離體托為鸚鵡,馮鎮巒評曰:“若仍前離魂隨之去,便少趣,忽附一鸚鵡,又開異境,文情之妙,不可名狀。” [7]235錢維喬一方面注意到鸚鵡與離魂母題之間的關聯并極力發揮鸚鵡之道具功能,另一方面吸收《牡丹亭》等前代傳奇營養,將《阿寶》的離魂母題延伸為“互夢—離魂”的雙重母題。孫子楚因畫種下情根,一見寶娘即魂不守舍,終于在第十二出《神遘》中進入小姐夢中。孫生夢魂讀到小姐題詩,魂歸原體之后將和詩托媒人寄予寶娘。寶娘驚異“那生真個夢中到此”,更感念其“乍丹青偶見,便是入骨疼憐”的深情,一對才子佳人終于心心相印。夢中離魂成就姻緣,可謂奇巧之至。
(二)《鸚鵡媒》與《牡丹亭》等前代傳奇的互文
在《鸚鵡媒》對《阿寶》的改編與再創造中,明顯可以發現《牡丹亭》等前代傳奇的影響。《鸚鵡媒》深受臨川“至情觀”啟發;劇作文辭與《牡丹亭》相映成趣;劇中的“互夢”與“對鏡寫真”兩大敘事母題也與以《牡丹亭》為主的前代傳奇形成了異代互文。
《鸚鵡媒傳奇·自序》談道:
是故情之至也,可以生而死之,可以死而生之;可以人而物之,可以物而人之,此《鸚鵡媒》一劇所以捉管而續吟也。《鸚鵡媒》者,其事本諸般陽生《聊齋志異》,而益以渲染成之,或有疑其幻者,則夫蜀魄楚魂,至今不絕,又況千年化鶴,七日為虎,漆園蝶栩,槐安蟻封,天下境之屬于幻者多矣!何不可作如是觀耶?臨川曰: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信已![1]174
讀者不難發現其與湯顯祖《牡丹亭·題詞》的互文。錢維喬從《阿寶》的情節出發,將《牡丹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情進一步發展為“可以人而物之,可以物而人之”。《鸚鵡媒》的至情觀遠承莊周夢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的物我交融、物我合一,乃至物我兩忘的“物化”哲學思想,具備一定理趣。或受傳奇敘事文體所限,《鸚鵡媒》本身并沒有圍繞孫生魂附鸚鵡的劇情,在“物化”方面進行更多的解釋,但作者的自序已經注意到了“至情”與“物化”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系,可以說這也是湯顯祖“至情觀”在哲學思想方面的深化。
《鸚鵡媒》曲詞婉轉優美,從情節安排、思想主旨到行文遣句,乃至曲詞、科白,處處體現《牡丹亭》傳統。以孫子楚觀畫的心理活動描寫為例,其情節與曲文明顯借鑒了《牡丹亭·玩真》一出。
《鸚鵡媒》在高舉至情旗幟的同時又試圖以綱常名教之理對之加以調和。這一方面與《牡丹亭》的深遠影響及乾嘉文壇、曲壇之風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錢維喬本人人生經歷的寫照。《牡丹亭》自誕生始便光耀文壇,“書初出時,文人學士,案頭無不置一本”“閨人筐篋中物。蓋閨人必有石榴新樣,即無不用一書為夾袋者,剪樣之余,即無不愿看《牡丹亭》者” [8]312。據郭英德統計,《牡丹亭》現存版本不下五十種,“其中明單刻本有十八種,明合刻本六種,清單刻本、石印本十九種,清合刻本五種,另有清抄本三種等” [9]18-39。很多戲曲作家毫不諱言自己的作品接受了《牡丹亭》的影響,如沈璟《墜釵記》、吳炳《畫中人》、洪昇《長生殿》,作品中偶一運用《牡丹亭》典故的劇目更數不勝數。乾嘉時代的戲曲觀較之前代已發生了極大改變,士人間盛行與倡優交往的風氣,“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之相狎” [10]33,曲家明確標舉“以曲為史”,不再以此為小道。乾嘉文人學養深厚,作品考據化、學術化與內省傾向明顯,劇壇誕生出一大批寫心、閑適,旨在譜寫個人心曲“借他人之酒杯,澆胸中之塊壘”的作品。此外,錢維喬作為乾嘉常州詩派的中堅力量,與袁枚是筆墨好友,深受其“一生心性愛疏狂”的影響。錢詩中有“子才吾友亦吾師,別來三載夢見之” [4]142之句。袁枚強調詩歌抒寫真情,對男女之情和艷情文學頗為包容。在乾嘉曲壇時風和作者文學交往的共同影響下,《鸚鵡媒》用清辭麗藻描繪青年男女戀愛的真情,既是對《牡丹亭》傳統的繼承,也是對袁枚性靈詩學的回應。而錢維喬一生沉淪下僚,身世波折,喪妻之痛和莼鱸之思是縈繞其心頭的兩大主題。作者在《鸚鵡媒》中時有憤激、惆悵乃至悲酸之語,這使得全劇具有較為明顯的內向、內斂、自省以及悒郁氣質,較之《聊齋志異》的淳樸天然顯得循規蹈矩而拘束,較之《牡丹亭》的熱烈浪漫則顯得內斂而難以擺脫時人常有的道學氣和頭巾氣。
在對《阿寶》的戲曲化改編上,《鸚鵡媒》引入了“互夢”和“對鏡寫真”兩個經典的、經《牡丹亭》發揚光大的敘事母題。“互夢”母題在筆記小說中時有出現,常表現為友人、夫妻、親人之間做相同的夢。《牡丹亭》將“互夢”母題引入明清傳奇領域,并創造性地將“互夢”發展到陌生的男女二人之間,兩者因情而生夢,同時入夢,為夢中之情“生生死死隨人愿”。《牡丹亭》中,柳夢梅因夢中美人改名,杜麗娘為夢中情緣一病而死、死而復生。柳夢梅的名字源于夢境,而杜麗娘重生的生命也源于夢中之情,名字與生命都是身份的基本前提。可以說,杜、柳二人不僅因夢結緣,更因夢中的彼此而獲得了立足于現實世界的身份,看似虛幻之夢卻照應并影響了現實。《牡丹亭》之互夢母題徹底打破了戀愛題材中夢與醒、真與假、現實與虛幻的界限。《鸚鵡媒》中孫子楚與寶娘雖不是因夢相識,但二人的相知、剖白乃至兩相情動都以互夢為重要媒介。特別是對寶娘來說,現實中的她對孫子楚這個因戲言而斷指的“冒失書生”并無太多好感,甚至不太熟悉。但在第十二出《神遘》中,寶娘在夢中遇見孫子楚夜入閨閣,傾吐“我為你春容眼兒盼花,我為你夢芳姿心兒悶加,我為你透骨髓波查,則這一指相思,險些痛煞” [1]51,感其癡情,復慕其才貌,“看他言詞舉止,殊覺可人。奴家雖未涉解佩之嫌,未免動聞琴之好” [1]64。可見,如果沒有“互夢”為媒,深居閨中、謹守男女大防的寶娘和單相思的孫子楚很難兩心相悅。《鸚鵡媒》中的“互夢”母題,既繼承了《牡丹亭》打破虛幻與現實,大力張揚“至情”的思想主旨,在推動情節發展的同時,又貼合了《阿寶》自身的亦真亦幻和浪漫離奇的藝術氛圍,是對《牡丹亭》傳統的合理移植。
“對鏡寫真”母題在中國古代繪畫中多以唐代才女薛媛的臨鏡自照,寫真寄夫故事為藍本。今存典型作品是現藏于大英博物館的宋代銀鏡奩蓋面上的圖像,以及明代的《千秋絕艷圖》。此外即《牡丹亭》現存的最早刻本版畫插圖:明萬歷四十五年(1617)石林居士序刻本《牡丹亭還魂記》中第十四出《寫真》插圖頁,畫面中同時出現了杜麗娘本人、鏡中人杜麗娘和畫中人杜麗娘三張面孔。[11]86-95出現“對鏡寫真”的戲曲則多屬受《牡丹亭》影響的劇本系統,如《療妒羹》《畫中人》《夢花酣》《桃花影》等。《牡丹亭》中,麗娘因病重而形容憔悴,為了定格青春生命的美麗燦爛,她自行寫真,借丹青以傳真容于世。吳吳山三婦評曰:“麗娘千古情癡,惟在‘留真’一節。若無此后無可衍也。”杜麗娘的畫像成為她病危之際生命的延續,“有美人自家寫照,寄與情人。似我杜麗娘寄誰呵”的感嘆也在期待、召喚著潛在的知音。圖像是身體缺席的在場,后來柳夢梅果然拾得畫像,它代替麗娘本人成為柳夢梅的“畫中情人”,引來麗娘魂魄團圓。《牡丹亭》“對鏡寫真”的母題寓意著女性對自我的審視、自我價值的發現、生命存在的確認和生命孤獨性的表達,其哲學和美學意涵遠遠超越了戲曲中畫像單純的道具與情節功用。與大多數簡單模仿《牡丹亭》寫真情節的傳奇不同,《鸚鵡媒》在充分發揮畫像道具功能的同時,注意到“對鏡寫真”母題中暗含的一個疑問:鏡中人、畫中人與現實中的繪畫人三者之間的身份差異與認知上的微妙錯位。先看《牡丹亭》中杜麗娘寫真的過程:
輕綃,把鏡兒擘掠,筆花尖淡掃輕描。影兒呵,和你細評度:你腮斗兒恁喜謔,則待注櫻桃,染柳條,渲云鬟煙靄飄蕭;眉梢青未了,個中人全在秋波妙,可可的淡春山鈿翠小。宜笑,淡東風立細腰,又似被春愁著。謝半點江山,三分門戶,一種人才,小小行樂,捻青梅閑廝調。倚湖山夢曉,對垂楊風裊。忒苗條,斜添他幾葉翠芭蕉。[12]77
《牡丹亭》對杜麗娘作畫的過程采用了間接描寫的策略。櫻桃、柳條、煙靄、春風、青梅、湖山、垂楊、芭蕉等意象的重重疊加讓這幅自畫像顯得云遮霧繞。對鏡中、畫中、病中和昔日杜麗娘的處理也具有相當程度上的模糊性,作畫的杜麗娘已經病重消瘦,容顏殘損“十分容貌怕不上九分瞧”,她在繪畫過程中有意識地表現自己記憶和想象中昔日的“艷冶輕盈”之態,最終定格在畫卷上的杜麗娘是否真的像她本人(無論是病中的她、夢中的她還是昔日健康的她)是值得懷疑的。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春香對她“可廝像也”這一疑問的回答:“丹青女易描,真色人難學。似空花水月,影兒相照。”而后來柳夢梅拾得畫像,呼喚畫中美人引來麗娘魂魄之時,他也并沒有立即認出她就是畫中人。呂立亭(Tina Lu)精準地指出:“在好幾出戲中,柳夢梅都是凝視著畫像為之心醉神迷,但他還是沒有把他幽靈般的戀人與畫像中的女孩等同起來。只是當這個女鬼(失去耐心,我猜)最終提示他,他才突然想到把二者聯系在一起。我們沒有證據證明這個女鬼與自畫像的作者完全相像。……我們所認為的自己的形象與別人眼中的我們的形象這二者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13]41
無獨有偶,當孫子楚在骨董店偶見春容即害相思時,朋友李含輝勸道:“畫圖容貌不足為憑。”孫子楚也自忖:“畫圖難信一說,小弟也疑。天下豈有如此美色?”至此,畫中人與真實人物身份與認知的錯位問題再度出現。顯然,《鸚鵡媒》注意到了《牡丹亭》開創的“對鏡寫真”戲曲母題中的身份錯位問題。錢維喬的處理策略是:極力彌合畫中人與真實人物身份之間的裂隙,通過劇情上的反復強調和確認,將二者合而為一。試看《鸚鵡媒》對寶娘的自繪描述:
常則是一泓波嬌對整,不爭的撤菱花難自省。掠鬟痕再得消詳,分笑靨相看不另。(作畫介)注秋波自把盈盈定,略則挪顏偏換影。(貼持鏡旁照介)靠這一些些評度分明,怕筆尖兒溜來欠領。略描成,早認是鏡里卿卿。……亭亭,天然秀整。(作看鏡再看畫介)小姐你玉容顏化作三星,點將腮斗紅微剩,掃眉尖暈淺青。我生來本色淡妝成,白描呵恰稱。只借他翠羽把羅衫映,落得個買胭脂多半省。[1]8
與《牡丹亭》相比,《鸚鵡媒》將寶娘的對鏡寫真過程表現得相當細致而具體。寶娘作為一位繪畫者,始終把注意力放在畫中之人是否像自己,是否還原了被畫者自身的容色、神態上。作為評畫者的倩奴說:“小姐,真個怪煞你的才思,你又不是畫師,怎寫得這般活現呵。” [1]9又在《跋真》一回中再次確認:“不是小姐,天下那里還有這樣個標致人兒像他!” [1]40極力強調畫中人、鏡中人和真實的寶娘三者的一致性。與柳夢梅對畫像的反應不同,孫子楚輕易就認出了畫中人就是寶娘本人。在《社晤》一出,孫子楚偶遇寶娘出游,一見便知眼前的小姐就是畫中的美人:“我只道降天仙云靄飄香,原來是意中人畫里明珰。”《神遘》一出安排孫子楚魂入小姐閨房,與寶娘互夢,先是在閨中再次見到小姐春容,而后見到小姐本人,“愛他殘妝一抹,半啟犀牙,颭的來嬌如畫” [1]51。至此,畫卷中的寶娘與真實的寶娘二者合為一體,眼前的寶娘就是孫子楚朝思暮想的畫中人,無可置疑。
對“對鏡寫真”母題的重視和反復推敲,當與錢維喬本人的畫家身份和自覺的畫家意識有關。錢維喬生于文人世家,不但擅長詩文,而且工書善畫,與乃兄錢維城并稱“常州二錢”。有《南山積翠圖》《林亭遠岫圖》《疏水平泉圖》《云山桑苧圖》等丹青傳世。通覽全劇,《鸚鵡媒》中寶娘的畫像更多地作為其自娛的產物和定情道具而存在,思想深度較之《牡丹亭》仍相形見絀。不過,《鸚鵡媒》畢竟注意到了“對鏡寫真”母題中存在的身份認知錯位并在情節安排上努力調和,雖仍有生硬和作者直接介入之嫌,但在受《牡丹亭》影響的才子佳人傳奇中已屬難得的嘗試。
三、《鸚鵡媒》對《聊齋志異·阿寶》的誤讀
從人物形象的異化和思想的庸俗化傾向,以及劇情中蕪雜成分的羼入來看,《鸚鵡媒》對《聊齋志異·阿寶》的某些改編降低了原作的格調,存在明顯的誤讀,側面透露出作者本身及乾嘉社會對《聊齋志異》及才子佳人戲的接受態度。
首先是人物形象在某些方面的異化及思想的庸俗化。劇中的孫子楚和寶娘與《阿寶》原作相比都失去了不少天真淳樸的特質。原著的孫子楚不僅情癡,而且性癡,“人誆之,輒信為真”,有著對人不設防,天然無雕琢的赤子之心。孫子楚的“癡”不僅體現在對愛情的執著上,更體現在為人處世的方方面面。如原著孫子楚在全未見到阿寶,不知其才貌之前,因阿寶一句戲言就愿斷指求婚;受到妓女的戲弄時竟“赪顏徹頸,汗珠珠下滴” [3]236;一遇阿寶則一見傾心,癡性發作,“癡立故所,呼之不應”“至家,直床上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喚之不醒” [3]238。這些表現都讓人聯想到《紅樓夢》中亦有癡公子之稱,受多姑娘戲弄而“心內早突突的跳起來了,急得滿面紅脹,又羞又怕” [14]1018,紫鵑一試則“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吃茶” [14]734的寶玉。而《鸚鵡媒》中的孫生除了癡心于愛情和待人一片至誠之外,其他方面較之《阿寶》中的孫生都有所異化。孫子楚始終懷著“馬蹄一日看花易”的功名之心,對寶娘的傾慕也是因為看到了美人的自畫像而慕其才色。在諸少年拿來假擬的題目,意圖愚弄時,《阿寶》中的孫生信以為真,晝夜揣摩;《鸚鵡媒》中的孫生則一眼看破其詭計:“好笑老胡,將這般假題也來哄我!休說場中怎出如此險僻之題,若果是真的,又焉肯輕自付我?” [1]155與阿寶相比,劇中的寶娘也丟失了許多天真單純的性格,代之以閨閣淑女的端方持重、貞潔自守。斫指的戲言本出自阿寶之口,在《鸚鵡媒》中則換成了倩奴。得知孫生為情斷指之后,阿寶的反應是“女亦奇之,戲言再去其癡” [14]237,其天真活潑、心直口快的本性躍然紙上。而《鸚鵡媒》中,媒婆巫媽媽將斷指之事講給寶娘聽,她卻說道:“媽媽好笑,這也干我甚事?”言語間頗為冷淡。直到與孫生互夢,明明已“動聞琴之好”的寶娘仍然擺出嚴肅的淑女面孔:“秀才,你便自多情,須知大禮嫌疑之際,怎只管逗留在此?……須省道鉆穴踰墻,是甚生涯?奴是個守香閨含真棲托,休猜做琴挑求鳳,門迎待月,枉責閑牙。” [1]51寶娘和孫子楚形象的異化與乾嘉曲壇的風氣有關。乾嘉曲家試圖調和情理,一如李調元所說,傳奇要能“發人深省”“入人心脾”,即所謂“曲之為道,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15]366。在處理才子佳人的愛情題材時也強調“情不失其正”,如蔣士銓言“情包羅天地”“情順”“情正” [16]363即為美,逆情則不美。《鸚鵡媒》亦不能免俗,而這種“不失其正”的情與《阿寶》所追求的淳樸真情相比,多了不少羽翼名教的教化文字,難免顯得庸俗而道學氣。
其二是劇情中蕪雜成分的羼入。《鸚鵡媒》中存在不少與劇情主線無關、信筆漫衍的文字,它們或宣揚名教,或憤激于世事,或借詠史懷古以自傷,純為寫心而存在。尤其是在下卷第二十九回《初諧》孫生寶娘完婚之后,劇情更顯蕪雜,與《阿寶》原作的簡潔凝練相悖,有剪裁失當之嫌,更不利于場上演出。《阿寶》中,孫子楚死后在冥間的經歷僅以其本人的敘述幾句帶過,文字簡練但富于神秘性和想象空間。而《鸚鵡媒》第三十五出《冥釋》用了接近一出的筆墨敘述“天下都城隍”于謙生前忠心體國卻遭奸人讒害而枉死的故事,形式上則以外扮于謙,丑扮鬼卒,二人一唱一和一問一答,缺乏情節沖突和波瀾,幾近一篇懷古之文。明代以降,傳奇中出現大量“鬼戲”回目,它們往往是一出戲中出彩、熱鬧的“戲眼”,在實際表演中,舞臺上的武打表演成分遠遠多于曲文演唱。而《冥釋》一出,將大量筆墨花費在外、丑二人的對話唱和上,可以想見實際舞臺表演中勢必成為近乎“抱肚子唱”的枯燥無聊場次。究其緣由,與乾嘉時代文人戲日益案頭化、書齋化的傾向,傳奇、雜劇等古典劇種的蛻變衰亡不無關系。
結語
聊齋戲的藝術成就雖不能與《聊齋志異》小說文本相提并論,但仍然擁有獨特的價值。錢維喬的《鸚鵡媒》作為清代聊齋戲中較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在將小說《阿寶》文本內容和藝術內涵轉換為戲曲的過程中既有合理的接受,更有改編的亮色,也有明顯的誤讀。以現代人眼光觀之,其誤讀是可以原諒的,仍不失為一部優秀的傳奇劇作。
參考文獻:
[1]關德棟,車錫倫,編.聊齋志異戲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鄭秀琴.奇情異彩《鸚鵡媒》[J].四川戲劇,2015,(3).
[3][清]蒲松齡.聊齋志異鑄雪齋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清]錢維喬.竹初詩鈔[M]//《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6.
[5]金元浦.接受反應文論[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6]熊明.中國古代小說離魂故事范型的文化觀照[J].蒲松齡研究,2008,(3).
[7][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8]中國戲曲研究院,編.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清代編(第三集)[G].合
肥:黃山書社,2008.
[9]郭英德.《牡丹亭》傳奇現存明清版本敘錄[J].戲曲研究,2006,(3).
[10][清]趙翼.檐曝雜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1]唐宏峰,程思煜.對鏡寫真:從《牡丹亭》插圖看圖像的生成與觀讀機制[J].藝術廣角,
2022,(1).
[12][明]湯顯祖,著.牡丹亭[M].徐朔方,楊笑梅,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13][美]呂立亭,著.人物、角色與心靈——《牡丹亭》與《桃花扇》中的身份認同[M].白華山,
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
[14][清]曹雪芹,著.紅樓夢脂評匯校本[M].脂硯齋,評,吳銘恩,匯校.沈陽:北方聯合出版集
團,2013.
[15]隗芾,吳毓華.古典戲曲美學資料集[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
[16][清]蔣士銓.蔣士銓戲曲集[M].北京:中華書局,1993.
The Acceptance,Adaptation,and Misreading of
Liaozhai Zhiyi in Qing Dynasty Liaozhai Opera Ying Wumei
Wang Yuning
(School of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opera Ying Wumei created by Qian Weiqiao is currently the earliest Liaozhai opera that can be tested,and it is also a representative work among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 selection,Liaozhai opera is a special type of opera that reflects the 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Liaozhai Zhiyi by the literary and musical circles. This article takes Yingwu Mei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its acceptance,adaptation,and misreading of Liaozhai Zhiyi. It is found that Qian Weiqiao,on the one hand,accepted and adapted the characters,plot,and artistic features of A bao in an opera style,while also drawing on the nutririon of previous operas such as Peony Pavilion to promote the scholar and beauty style of love that conforms to the teachings of the moral obligations and preachings. Introducing the two main narrative themes of “mutual dreams” and “drawing a self portrait in front of a mirror” and forming intertextuality with Peony Pavilion is the highlight of Yingwu Mei. On the other hand,the alienation and vulgarization of the character images,as well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plot after the adaptation of the play,have deviated from the style and aesthetic of the original story A Bao,and there are certain misunderstandings.
Key words: Liaozhai Opera;Liaozhai Zhiyi;Ying Wumei;acceptance;misreading
(責任編輯:景曉璇)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4?0096?15
收稿日期:2023-09-05
基金項目: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聊齋學’文獻整理、研究與數據庫建設”(編號:21RWZD08)
作者簡介:王譽凝(1994- ),女,遼寧朝陽人。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在讀,主要從事明清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