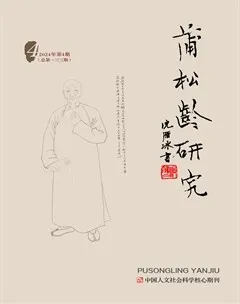物性 情性 智性 善性
摘要:《省身語錄(殘稿)》并非蒲松齡勞作園地的主打產品,但接承及傳輸中華文化優質內容,對中華智慧的精義匯聚、精準悟解及精確表達,的確不應該被忽視。物性、情性、智性及善性多角度的探析路徑,作為邏輯推演的方法有序展開,全在于這多個層面本就是《語錄》的事實存在。《語錄》中有物,蘊物性,聚合物的多樣、整體意蘊,言物不受物限,而是緣物而擴/拓時空,見思想際域之廣闊。《語錄》情意融通,和風細雨,微風拂面似地以情展性、顯性、明性,緣情而明理,通情而充智。《語錄》的智性品質隨詩性展露,知天地交合、萬物生動,且理趣相融、辨思精細,疏通文脈。《語錄》基于物、情、知、智而融通的德性與善性,智慧滿滿、情意無間,映現“聊齋先生”的仁與智,鏡攝融情與和善的策略及方式。《語錄》智慧性、全形態的自省性,“發世德之祥”的表達之勢,展示了中華智慧傳承的基本脈絡及重要載體的獨有魅力。
關鍵詞:《省身語錄(殘稿)》;智慧性;中華智慧;詩性;德與善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較之《聊齋志異》的鬼狐神魅,幻境異趣,情意涌動,變動不居,蒲松齡的詩詞、雜著或更有接地之勢,實在、智慧且具知行和合,儼然是身體力行的生活截取、直錄及鏡像。此時的“生活”,可謂蒲松齡全身心參與,是根性、地力堅實的生長,是智慧性凝練;其身體、心力及靈境的全方位踐行,有助境界性提升;儼然全形態展示“聊齋先生”作為一個立體、完全,能夠洞見“天文”與“人文”化通之魅的生命活動體。本文所勘探、體認、闡釋,乃至給予哲性辯證的《省身語錄(殘稿)》(以下簡稱《語錄》) ① 更像一面鏡子,映現“聊齋先生”的仁與智,鏡攝其融情與和善的策略及方式,是展示其“全人”形象的重要一隅。作為中華文化的接續、接承,《語錄》既是文類/體式、詩性/哲思、教義/啟示作用的延伸,又合理合情發揮著知行、愛意及自省精神。《語錄·序》有言:“余半生落魄,碌碌無所短長,自念遺行或多,故不足以發世德之祥,敬書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 [1]總2071《語錄》全形態的自省性、智慧性含蘊及表達,展示了中華智慧傳承的基本脈絡及重要載體的獨有魅力。
一、關于導入《語錄》智慧探析的方法問題
語錄體自導、自制、自省、自警、自喻,有記錄自身思想精神、身心動勢、所做所求,展示教義、能解惑、重啟悟的多重作用。作為一種文類、體式,語錄體具有短精、洗練、傳神及詩性的特點,能夠沁人心脾,撼動心靈,具有牽情理脈之勢。以如此之譽,評價《省身語錄(殘稿)》也是頗為恰切的。《語錄》的確是從己、從心、從思、從身及從體驗、體悟而發,但又需向外,是發散、輻射的,是施教及育化的。
(一)版本依據
本文所敘《省身語錄(殘稿)》為盛偉先生所編《蒲松齡全集》第三卷“雜著”的一部分。關于版本來源,盛偉在“校勘記”中寫道:“該輯校本所收錄的《省身語錄》(殘稿),其抄本為藏于日本慶大的題名為《聊齋編處事格言百全》(殘稿)。此稿本封面與正文前皆殘缺,至于失去多少,不得而知。” [1]總2111-2112該輯校共計347條,格式多有變化,大都以詩、楹聯、韻語及相對應的長短句構成,尚有4條詩及韻語,因存疑,故收于“附錄”中。
(二)智慧性
本文之所以對《語錄》給予“智慧性”界定,起碼基于三重含義:其一,人生智慧。《語錄》的展示、生發滿含人生智慧,有別于《聊齋志異》、蒲松齡的詩詞、俚曲,作為一部優質作品,無疑是人生體驗的綜合性匯聚,也集中展出“聊齋先生”的知識視野、人生悟解及價值觀。其二,生命智慧。《語錄》中并未暢論何謂“生生”“生命”,但其豐富蘊含無疑是寄望生命的恢弘,“聊齋先生”的命運歷程不乏矛盾、坎坷、跌宕,但生命智慧卻是輝光閃耀的。其三,中華智慧。《語錄》深蘊中華智慧,是中華文化精義及濃縮,對于天地和合、倫理善性、人性守則、寬闊視域等等,都能辨理清晰明確,適宜于平民化、知識化、情理性、全面性的傳輸,儼然一部充知明理的智慧性教科書。
(三)一般性
我們循物性、情性、智性、善性來層次性探進,從概念辯證的一般性體認《語錄》的精深、精到。對《語錄》的一般性把握,包括人類性整體共通共同的一般性,中華文化、中華智慧的一般性,“聊齋先生”人文風貌的一般性。《語錄》不只深蘊“聊齋先生”的人文情懷及個性,也經由物、情、智、善的合理路徑綜合體現他的人生過程及精神生產的一般性。從《語錄》中,我們的確可以深層讀解著中華文化及中華智慧精義,并能知曉人類共同共通的命運征程應該如何行進。
(四)文化自信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2]37-38堅守與提煉,需要我們精心挖掘,精準把握中國文化傳統的優質內容,創新性研究屬于人類共同財富的中國文化的智慧性內容。同時,人文學術還應基于中國特色話語及學術體系的建設,繼而哲性辯證、學理性梳理,面向世界、面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面、系統地完善中華智慧及中國形象,“傳播好中國聲音”。
二、物性:根性實在、接地堅實
世界是物的存在。人也是物的存在,更是精神性存在。人與萬物交合、能量互通、信息傳遞,生生化育,沖氣以為“和”。人為事、行文不離物的支撐,欲知其所以然,必尋源明理,精神調控及提升是必須。這里言及“物性”,并非簡單地評價《語錄》中暢言了哪種物,是動物還是植物,是天地、日月,還是山川、河流,而是探析物與生命的“生生”合成,如何成就整體和諧的視野、氣象、氛圍,如何凸顯“聊齋先生”的知識視野、人生智慧、融情方式及命運征程。從這種意義上論,《語錄》所論之物,既顯物形,也呈物生及物蘊;既示物內,更啟思物外;既借力于單個物的特性,更在合成同類物的整體意蘊;言物不被物限,緣物旨在擴/拓時空,以見思想際域之廣闊。
《語錄》對物的合成及詩性表達展示了中華智慧的特質。“名山大川”“花繁柳密”“風狂雨驟”“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崇德效山,藏器學海”“青天白日的節義自暗室屋漏中培來;旋轉乾坤的經綸自臨深履薄處得力”“心地上無波濤,隨在皆風恬浪靜;性天中有化育,觸處見魚躍鳶飛”“龍吟虎嘯,鳳翥鸞翔,大丈夫之氣象;蠶繭蛛絲,蟻封蚓結,兒女子之經營”“石火光中爭長競短,幾何光陰?蝸牛角內較雌論雄,許大世界”“昂藏老鶴雖饑而飲啄猶閑,肯似雞鶩之營營而逐食?偃蹇寒松縱老而豐標自在,豈效桃李之灼灼而爭妍”。自然萬物的多樣性合成,與人的生生動勢攜程,詩性韻化,創生警句,生成氣氛,成就意象,明辨道理,升華境界,這是中華文化中行文、馳思的致法,也可為一種“審美經驗”。這種“合成”不限空間性,更為時空交合,或更依“生”與“時”的動態及流程性,生生不息、生生永續。中華智慧的一種致法,是在乾坤、天地、陰陽、氤氳、剛柔,甚至動與靜轉換中氣脈運行、生生而動,成就時空交合。我們說形成氣氛,彰顯氣象,成就意象,這是生生的,是轉換轉化的,是氣韻生動的氣象、氣氛,顯然不同于西學視域中所言的“氣氛”。格諾特·波默在《氣氛美學》中討論“氣氛”,強調那種場景化“氣氛的營造”。波默說:“一件音樂作品或藝術品、一個日常對象,一棟建筑物或某種空間態勢,散發的都是氣氛,是那種對在場的人具有情感作用的氣氛。” [3]中文版前言6波默這里的“氣氛”起碼有兩個關鍵項,即在場性及所指性,顯然這是以空間性為主的義項。在中華文化中,即便是這種在場,或基于某部作品的所指,都不限定獨立空間,也不靜止于空間,而是在生生及時序的流程中成就空間的動靜轉換,不拘于在場的局限、靜態及特定所指的狹義,而在生生之動及轉換中形成“沖氣以為和”之勢,實際在詩意性展示宇宙、世界、生命之脈的動勢及循環。
《語錄》的詩性表達多為兩兩相應、相和,互補相融的,成警句、格言,既呈韻體,行格律,或五言七言,或楹聯、律絕,也合理運用長短句式,有效推進,用節奏成動律,同時也將比興、設喻相間,相互支持,互通轉換。對詩性呈現的物,其詩性合成除了氛圍、氣象的營造,多為起興及作比、設喻。“立品定須成白璧;讀書何止到青云”“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是腳根”“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秋在清涼臺上;窮豈能遣,而窮愁能遣,春生安樂窩中”“世事讓三分,天空地闊;心田培一點,子種孫收”“觀天地生物氣象;學圣賢克己工夫”“花逞春光,一番風一番雨,催歸塵土;竹堅雅操,幾朝雪幾朝霜,傲就瑯玕”。《語錄》中的物性表達是通“化”及“化”通的,其“化”層層推進,有物的實體、實在、實存的狀態,緣物的動態而轉化融通,直至推演及化成精神、善性、德性及人格構型,以彰明知行、品性,成就為人之道、之策。《周易》曾言天文及人文之化,自然之天與人的生生化通,必然成就人之化,以其文之化而匯聚人之性。顯然,這種詩性表達策略不惟“聊齋先生”所獨有,而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精義,是中華智慧的精致。我們如能至深且精細探究,也可見這重體驗策略在《語錄》中亦能具體、實在,其路數清晰,作比設喻精準。這并不排除中華文化演進至明清,其言語構成漸趨通俗,思想表達或許更直白,但在筆者看來,“聊齋先生”作為平民化文人,其語言及詩性表達風格的合理彰顯更為不可或缺的因素。
“聊齋先生”的詩歌、俚曲及雜著等其他種類,根性實在、接地堅實及平民化、通俗化的風格呈現,助推他能夠自如地走入“兒女子之經營”“子種孫收”的境域。我們將“化”繼續推進、細化及人化,或許可稱為化入民間、鄉間、親情間,化為民眾可接受的際遇,化為修身及守持人格的表征。
三、情性:融情入理、詠吟辨性
言情性,不限于“言情”,不論詩情、藝情、文情,或者說喜怒哀樂的日常情感表達,當情與性合體并稱,此時的情更在于表達“性”,凸顯“性”,疏通“性”的理義。情性和性情不只是互為轉換,互證詞性、概念,更在于指稱闡釋對象,由情的疏通而明確品質、性質及特性。
古代先哲曾不同程度地論述過“性—情”的結構性本質。《論語·陽貨》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先天相近的,人存在的差異性,為后天習得。《孟子·盡心上》有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4]2764《荀子·正名》云:“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 [5]428如此看來,先哲們認定,“性”多指原本的存在,或者直接指稱為“天”。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情,人之陰氣。” [6]217在后世的詩學及行文闡釋中出現“吟詠情性”“心統性情”等命題。本文在此使用“情性”并非僅僅將其作為結構性的“情—性”,而是作為一種概念性稱謂。這基于三重含義:其一,作為物性之基礎存在的必然延伸及推演過程;其二,作為情及情意表達的方式、品質及性質;其三,創造者如何通過情的暢舒,或者融情抒意,傳達思想,明晰理義,而思與理必然以先哲所論的性之天及天之性為基礎。筆者曾有文章討論,認為“性情”“情性”通聯詩性及藝術,“它是人類對自身存在的外—內、陽—陰、天—人等結構的價值性認同和藝術性展示,它構筑了由對人的本質存在的社會—哲學認識到藝術—審美認識和體驗的邏輯過程” [7]20-28。
《語錄》本就是詩性和藝術的一種文類、體式,由物性推演到情性闡釋,理應為事實存在,邏輯上也是可行的。《毛詩序》、鐘嶸《詩品》中都有“吟詠情性”之說,唐代司空圖《詩品·實境》云:“情性所至,妙不自尋。” [8]43宋代嚴羽也闡明:“詩者,吟詠情性也。” [9]26《語錄》多為詩體,運詩性,其中不乏情意、情蘊,并通于詩歌創生而韻“情”,故沿此而探析《語錄》的情性表達必然是可行路徑。應該肯定,《語錄》中的融情并非激情躍動,汪洋恣肆,更多呈現和風細雨,微風拂面似的情意融通。融情之路旨在通“性”,或者以情展性、顯性、明性,緣情而明理,通情而至善。這個詩性表達路徑必然由物性,由“生”為基礎和前提,人的身心及精神活動,藝術審美活動,感物必然融情,若覺知、品鑒,且人化物性,無法脫離情性的串接及浸染。《語錄》言:“一念慈祥,足醞釀兩間和氣;寸心潔白,可昭垂百代清芬。”“好惡之良萌于夜氣,息之于靜也;惻隱之心發于乍見,感之于動也。”《語錄》中詩性表達的這種情,不張揚,不夸飾,不雕琢,是自然而然的,是浸染、浸透性的,是娓娓暢舒的。《聊齋志異》的激憤及幻境生成中的男女施愛之情,蒲詩立地堅實抒發農情、鄉情,詩詞、俚曲中藝術性盤活的民風、鄉俗的情意表達,可以與之共情,能夠共展情性。當《語錄》以浸染方式將“情”緩緩融通,必然會細細溶解萬物,活化天地人和,交合思、理、善,成條理,成對應,繼而形成“心性”“質性”“理性”,聚合“善性”,或者說,是以融情推詩意,以詩性充知、明理、至性,也可謂疏情理而理情,故在此將其稱之為“情性”。
情性不離生,韻生生,也必然深蘊惜生、愛生之意。惜生且愛生疏通、明辨“性”之理,既展天地人和之性,運/韻/蘊生生化育、融情入境之性,更鑄固美、崇善之性。《語錄》言:“愛惜精神,留他日擔當宇宙;蹉跎歲月,問何時報答君親。”“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度量;臨喜臨怒得涵養,群行群止得識見。”“作踐五谷,非有奇禍,必受奇窮;愛惜只字,不但顯榮,亦當延壽。”“鳥驚心,花濺淚,具此熱心腸,如何領取得冷風月;山寫照,水傳神,識吾真面目,方可擺脫得幻乾坤。”《語錄》中詩性抒“情”,以物托情,以生融情,總是物物相牽,生生相惜。物物相會,時時顯現,有物、有情必有生,生生無處不在,無所不有,因生命之實永在。
四、智性:理趣相融、文脈疏通
物性、情性推智慧,既是實在,也是邏輯。物性的生生化育,情性的生生融通必然以“智”的方法、策略及路徑成就《語錄》。盡管《語錄》并非恢弘大論,不呈鴻篇巨制,卻能論天、論地、論人;論情、論愛、論理;論善、論德、論意;論天機、論精神、論積福;論“知多世事胸襟闊;識盡人情眼界寬”;論“花開花謝春如許,得意時休對人言;水暖水寒魚自知,會心處還期獨賞”;論“完名美節不宜獨任,分些與人可以遠害全身;辱名污行卻欲全推,引些歸己可以韜光養德”。《語錄》的智性品質循詩性展露:天地交合,萬物生動,理趣相融,辨思精細,文脈疏通,比興協同,適度中節,環環緊扣,層層推進,互補交通,如此娓娓道來。
言智性,需明確幾條通路:一是知識的習得,二是知識的運用,三是辯知的方法,四是明知的路徑。知與智相通、接承,智更在于知識的運用。“知”的累積成就基礎和條件,故《語錄》先期明確:“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充知識,必讀書,但還需“用”;如何用,用在何處,用之法何在,能否最大化升值;如何轉換、交叉、融通,生成新知;其法、其策、其徑,甚至其情的發抒及節度,則為智,或為智慧。緣此,“智”更在成“法”,在“化”機,在于優化、優質而“用”。《語錄》并不冗長的篇幅卻容量頗強,其知識性累積可謂面面俱到;盡管沒有大談先人、古人、經傳、典論,也未專論儒道何謂,理學、禮教何法,但其文脈承傳線路明晰、厚重,指涉精準,設喻真誠,類比得當,可謂能量充足。《語錄》并未暢論自然何謂,自然萬物何在,天文人文何“化”,但卻能駕輕就熟地將“自然而然”入化入木,將萬物與人之生生有機合奏,明晰地號準天文人文之化的脈象。
《語錄》言:“花繁柳密處撥得開方見手段;風狂雨驟時立得定才是腳根。”以生生協同的自然物性存在,以萬千變化的自然現象起興、牽引,動態性合成,旨在明晰做人的道理,個中也不乏為學、為證的精義。其中“手段”“腳根”兩個詞作為結論表述頗為恰切,行事的策略、方法及手段,為事、為證、為人的定力何在,“風狂雨驟”、撥云見日、穩健如泰山者為上。
《語錄》言:“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事務內巧機括,獨智士能看得透。”“有作用者,器宇定是不凡;懷智慧人,才情決然不露。”此二句暢言一種內守、內省,臨危不亂,參透塵世,表達人的智慧及堅守智慧之人的養成方式,不論是“智士”,還是“懷智慧人”皆具洞透力。這種能力的成就,除了“知”“知識”的豐厚,有動靜掌控及把握“度”的能力更為重要。
《語錄》言:“盈池拳石間便居然見萬里山川之勢;片言只語內又宛爾見千古圣賢之心。”“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過寒潭,雁去而潭未存影。”如何能有掌控力,練就洞透力,以小見大,于細微處見諸天地萬物,于言語警示中彰顯胸懷博大;世界之大,萬事之繁復,皆于小處而見。這就如同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這一切,如“無知”便不可能,而“無智”則更不可能。
《語錄》言:“滿室清風滿幾月,坐中物物見天心;一溪流水一山云,行處時時觀妙道。”“得意處論地談天,俱是水底撈月;拂心時吞冰咬雪,才為火內生蓮。”“坐”中見天,而非坐井觀天,“坐”亦如莊子的“心齋”“坐忘”。所謂見天,更為見心,為“心中一片天”。這是在識心見性,循心逐本,從心立根;見物見人,見天見心,是為絕妙之道。天地日月,萬物生生,與人與物或為同行同程,能夠參悟“妙道”,識“蓮”之形,悟“蓮”之色者,亦能見心、見性、見天。“見天心”“內生蓮”“觀妙道”,著實是非智者、非得其智性而不能為。
我們言智性,體認中華文化的智慧及精深,無法繞開中、節、和,這似是開門之鑰匙。我們探析《語錄》的物性、情性,掌智性,施善性,其多重互通、互補及生生關聯是為必須,于此,明“智”的方法和意義甚為重要。中與節是過程、是方法、是手段,和是起因,更是結果,事實上,三者不可分離,天地人之和的不同表現,是“生生”的過程性存在。老子“道生”論的邏輯推演即為“道生一”的原初之和,而生生轉換、遞進,必達“沖氣以為和”。中也好,節也好,皆不可偏離生生及陰陽轉換的過程。《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4]1625《周易》有“節以制度”之論,中、節、度相輔相成,如何有效把控,同樣是非智及非智者所不能為。如此可見,《語錄》之詩性表達,“智性”的駕馭,不只深諳其理,更能駕輕就熟其用。《語錄》言:“涵養沖虛便是身世學問;省除煩惱何等心性安和。”“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學道者須要努力;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得道者一任天機。”得道識得天機,并非一蹴而就,既需涵養修身,見學問,又需識性、心安,而努力、執著、堅韌是必須的,行進中、節,以求適度之法、之策則為不可失卻的路徑。
五、善性:辨理明德、樂與人善
“善”是中國文化傳統的核心區域,調協善的標準,掌控“至善”的方法和路徑,中華智慧有獨特的方法及策略。《禮記·大學》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宋代朱熹集注云:“言明明德,親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10]3明代王陽明云:“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11]6故我們言“善性”,其意有三:一是接續、推演的過程,二是作為一般性的學理范式,三是回歸中華智慧的核心區域。由感物、充知、融情、明智性到通疏善性,這既是邏輯的,也是中華智慧的明理、為人,乃至為政的必然。
《語錄》出自“余半生落魄,碌碌無所短長”的平民化的“聊齋先生”,盡管自稱“不足以發世德之祥”,只能“敬書格言,用以自省,用以示后”,就其地位而言,也著實無法與朱、王比肩,但我們還要認同“聊齋先生”的全面性,作為“全人”形象而創造《語錄》的獨有魅力,似體現了一種超越性。《語錄》在平實、守正、誠身中所“發世德”的格言及警示,其教義、教化而至“自省”力的確是“價值不菲”的,其物、情、知、智而融通的德性與善性,儼然智慧滿滿、情意無間的人生“教科書”。《語錄》不以繁復出現德與善的字面為上,也不專注于繁復論證何謂德,何謂善,但其詩性韻律,字里行間,德與善的意與義、態與勢卻不只通篇灌注,并且理與識、理與智、理與意可全本通透;既不纏,也不繞,而是直通心意、心靈;直接入情、入理、入境,似為親歷、親行。關于“德”,全本出現32處,與多詞相連而拓展含義,如積德、樹德、修德、天德、德量、德進、崇德、美德、養德、感德、頌德、報德、廣德、德器、謙德、道德等。關于“善”,全本出現19處,同樣與多詞相連以豐富其含義,如為善、行善、福善、公善、善事、樂與人善、善為至寶、善體黎庶情、責善切戒盡言等等。盡管是“自省”“示后”,但《語錄》中德與善的語義及其延展的范圍,思與理的辯證方式,關涉、覆蓋面的寬廣度,教義、踐行的動態性,則遠超于自體性表達,似已入通向遠、登高、和合之境。
首先,“德與善”理應從心及和親。德與善不離教、導、育,但這需從心而發,需要“和”,需要和親及親和。從這重意義上論,“和”不只對己,對他人,對民,對物,更需對萬物生生。宋代張載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12]62“民胞物與”,認同民與物皆為親,如無親,不從心,不能正己,便無以“和”。《語錄》言:“善為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良田,百世耕之有余。”“潔己方能不失己;愛民所重在親民。”心、潔、愛、親幾個關鍵性詞語使用頗為得當、準確,集中表述了“善”的內核,教導人要盡其一生去守持,為政者理應依此為準則。
其次,“德與善”融闊胸懷及眼界。德與善必然是自守、自省、自警的,但如無寬闊胸懷,無廣博的眼界,這種“自”也無以純正,如不純正,正己也難而之難。《語錄》言:“眼界要闊,遍歷名山大川;度量要宏,熟讀五經諸史。”“明星朗月,何處不可翱翔,而飛蛾獨趨燈焰;嘉卉清泉,甚物堪能飲啄,而蠅蚋爭嗜腥膻。”“聊齋先生”不止于平民化的教,能有如此高遠之境,的確值得敬佩。他能夠借力天地萬物之生、之和,憧遠境,辨精細,厘清明,其理據明晰、精準,也實實在在擴大了“德與善”境界。
再次,“德與善”助推修身及養性。智慧性繪就的德與善是剛柔相濟、動靜相融的,需要百般錘煉,需要知行和合,而修德、修身是必須的,修而養、養而修是相輔相成的。修與養的方式多之又多,靜修、勤儉、篤行,控因果、崇高雅是理應選擇的。《語錄》言:“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不因果報方修德;豈為功名始讀書。”“讀書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修德不期獲報,自然夢穩心安。”修而養,練而堅,知而行,由因求善果,“因”必須清晰、清凈,這不僅要從心而就,更需要千錘百煉。故《語錄》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
第四,“德與善”需要堅實及謙遜。堅實與謙遜是中華文化的優質內容,在《語錄》中被準確且形象化地表述著,無論何事,立足當下,腳踏實地,不只是“修德”,更為人的基本素養。《語錄》言:“立業建功,事事要以實處著腳,若稍慕虛名便成偽果;講道修德,念念要從虛處立基,若稍計功效便落塵俗。”
第五,“德與善”頤養氣性及生機。悟性、崇生不離自然萬物之生生而動,“善養浩然正氣”并非限于人的氣性養成,更要與萬物生生,化生化育中同行和氣,方可“沖氣以為和”,方可悟天機,充宇宙萬物之“精氣”。《語錄》言:“秋蟲春鳥共暢天機,何必浪生悲喜;老樹新花同含生意,胡為妄別妍媸。”“霜天聞鶴唳,雪夜聽雞鳴,得乾坤清淑之氣;晴空看鳥飛,活水觀魚戲,識宇宙活潑之機。”與萬物生生同行和氣,實際超越了“德與善”的人倫特性。人與自然萬物必要生態共生共榮,命運同程不可悖、不可違,這是必然且永續的。
第六,“德與善”植生愛意及溫厚。德與善必然是施愛的,不論仁愛,還是人愛/愛人,愛己、愛家、愛國是層次的遞升,也是品質的層級體現。《語錄》言:“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以保爵位之心保國家。”“半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哪有不慈愛的圣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量福田,試看哪有不容忍的君子。”《語錄》將愛提升至積德、積福的高度,將慈愛、容忍作為德器,生產福田,是為“君子”的準則,在“聊齋先生”這里的確難能可貴。
第七,“德與善”通曉福樂及眾樂。善也好,福也好,能使人快樂為上。樂,不止于自樂,更在眾樂。孟子曾與梁惠王討論:“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結論是“不若與人”“不若與眾” [4]2673。于是,與人為樂,“眾樂樂”成為評價何謂“樂”的一種標尺。《語錄》言:“憫濟人窮,雖分文升合亦是福田;樂與人善,即只字片言皆為良藥。”“圣人斂福,君子考祥;作德日休,為善最樂。”《語錄》中將德善、福樂同論,將“樂與人善”“為善最樂”與“憫濟人窮”及君子之態同程考量,明證且豐富了這種智慧性的快樂原則。
第八,“德與善”裁量美意及適度。我們曾論及中、節、度,在現實人生活動中如何把控,如何定尺度,以致如何裁量,甚為重要。《語錄》言:“儉,美德也,過則為吝慳,為鄙嗇,反傷雅道;讓,懿行也,過則為足恭,為曲謹,多出機心。”“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從烈火中煅來;思立揭地掀天的事功,須向薄冰上履過。”識美德、美玉,必須知節度,需要修身養性,需要錘煉、歷練,充知識、掌智性、修品性需要練,識度、不過、不失的“中節”更不可忽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既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腳下這塊生于斯、長于斯的土地,文藝才能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 [2]539習近平創造性地提出了“第二個結合”的思想,作為又一次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 [13]我們從學理性層面讀解《語錄》,也是在自覺地挖掘、整理中國文化傳統的優質內容,既是執守文化自信,也是在探求“中華文明發展規律”,聚合中華智慧,為“傳播好中國聲音”所進行的有效探究。這既是探究、嘗試,也是責任;是接地氣、底氣,灌生氣,也在灌齊魯文明之生氣。這個路子還很長,我們要更加精細、精準,需要不斷拓展寬闊的視野;既“入乎其內”,更“出乎其外”;既循歷史及文脈探進,也需明確如何接軌當代性、世界性;既需創新,也要借力多種理論和方法而不斷激活。
參考文獻:
[1]盛偉,編.蒲松齡全集(第三卷)[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2]習近平.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德]格諾特·波默.氣氛美學[M].賈紅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
[4][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0.
[5][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M].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6][漢]許慎.說文解字(附檢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7]蓋光.孟荀的“性—情”結構論及藝術本體性[J].孔子研究,2003,(5).
[8][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G].北京:中華書局,2004.
[9][宋]嚴羽.滄浪詩話[M].郭紹虞,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10][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1][明]王守仁,撰.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2][宋]張載.張載集[M].章錫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78.
[13]習近平.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N].人民日報,2023-6-3(1).
Physicality,Emotionality,Intellectuality,Goodness:
An Examination of Chinese Wisdom Embodied in Pu Songling′s
Quotations of Self-Reliance(Fragments)
Gai" Gu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255000,China)
Abstract: Quotations of Self-Reliance(Fragments) is not the main product of Pu Songling′s labor garden,but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mission of high-quality content of Chinese culture,the essence of the convergence of Chinese wisdom, accurate understanding and accurate expression,should not be ignored. The multifaceted path of inquiry into nature,psychology,intelligence,and goodness is ordered as a method of logical deduction,because these multiple facets are the facts of the Quote. In the Quote,there are things,substance,the variety and the holistic meaning of polymers. Words are not limited by things,but extend/expand space and time by things,seeing the vastness of the boundaries of thought. Quote:Emotions are connected,and the wind and the rain are gentle,and the breeze brushes upon the face with emotion,revealing,and understanding,because of the circumstances and reason,and full of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The intellectual qualities of the Quotations are manifested with poetic character,knowing that the earth and the earth meet,and all things are vivid,and they are compatible with reason and interest,and the reflection is refined,and the writing is clear. The quotes are based on the virtues and goodness of nature,love,knowledge and wisdom,and are wise and loving,reflecting the kindness and wisdom of “Mr.Chatham House” and reflecting the strategies and ways of reconciling love and kindness. The wisdom,the self-examination in all forms,and the tendency to express the detailed nature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heritage demonstrate the unique charm of the basic lines and important carriers of Chinese wisdom.
Key words: Quotations of Self-Reliance(Fragments);wisdom;Chinese wisdom;poetry;virtue and goodnss
(責任編輯:景曉璇)
①本文所釋《省身語錄(殘稿)》依據盛偉編《蒲松齡全集》第三卷“雜著”,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總第2071—2112頁。以下引述《語錄》中的話語,不再注釋。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4?0069?13
收稿日期:2023-02-22
作者簡介:蓋光(1956- ),男,山東煙臺人。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文藝學、美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