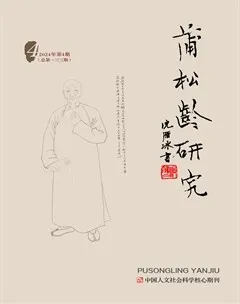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聊齋志異》能簡稱為《聊齋》嗎?
摘要:本文旨在糾正聊齋學研究領(lǐng)域及文藝作品創(chuàng)作中,將《聊齋志異》書名簡化臆改稱《聊齋》的不規(guī)范理解。該現(xiàn)象從300多年前遺傳至今,大有約定俗成的趨勢,而從未見有人論及。其實,聊齋乃蒲松齡居室名,也是其代稱,時人亦稱其聊齋先生。當年他在著作名前皆冠以聊齋,謂之《聊齋詩集》《聊齋詞集》《聊齋文集》《聊齋志異》《聊齋通俗俚曲》等,以顯示這些作品都是聊齋所著。《聊齋志異》書名是全稱,若需簡化只能稱《志異》,而不能稱《聊齋》。筆者從文獻史料入手,認真考證,得出上述結(jié)論。文字無小事,學術(shù)研究為求是,容不得臆斷和杜撰。聊齋學領(lǐng)域應(yīng)當規(guī)范的問題,不能留給后人去解決。
關(guān)鍵詞:《聊齋志異》;蒲松齡;學術(shù)研究;求是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假如有人提問:“《聊齋志異》能簡稱為《聊齋》嗎?”我會肯定地答曰:“不能!”為什么?因為“聊齋”是蒲松齡的室名,亦即代稱。其生前自稱“聊齋”,時人稱其“聊齋先生”。故其著作名前皆冠以“聊齋”,謂之《聊齋志異》《聊齋詩集》《聊齋詞集》《聊齋文集》《聊齋俚曲》等。以此可見,單把《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顯然有違蒲松齡的初衷,也不符合文法常理。
然而,聊齋學研究論著中將《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的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大有約定俗成的趨勢。讀者亦聽之任之,無人質(zhì)疑。為此,筆者不揣簡陋,首倡商榷,力求尋根溯源,找到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徹底解決之。
一、問題由來
本文題目,開篇即有了答案。可能有人認為過于簡單和武斷,這需要進一步說明論證,應(yīng)以蒲松齡的初心原意與歷史的發(fā)展過程為依據(jù),分析這一現(xiàn)象的成因和理由,讓讀者明白并且能達成共識。
綜觀聊齋學研究文獻中,將《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者,形式不一,有的在書名中,有的在文章題目中,還有在文章的表述中,都用《聊齋》代替了《聊齋志異》。
由于這種現(xiàn)象太過普遍,筆者不可能面面俱到,現(xiàn)只舉幾個例子以作說明。如新中國成立后出版的影響較大的多種《白話聊齋》,就是將文言文版的《聊齋志異》改寫為白話文的《聊齋志異》版本,只是書名中用《聊齋》替代了《聊齋志異》。研究專著中,如《聊齋發(fā)微》《聊齋藝術(shù)談》《聊話聊齋》《聊齋藝術(shù)通論》《聊齋人物塑造藝術(shù)研究》《花妖鬼狐話聊齋》《聊齋藝術(shù)的魅力》等,也都是將《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論文題目中,如《從〈聊齋〉略知時序的篇目試窺蒲松齡創(chuàng)作發(fā)展之一斑》《欲望交響曲——〈聊齋〉狐妖故事的心理學探索》《〈聊齋〉中的商人意識》《論佛家思想對〈聊齋〉創(chuàng)作的影響》《美丑的轉(zhuǎn)換與包含——談〈聊齋〉中的辯證法》《狐崇拜淵源與〈聊齋〉狐典型的高度藝術(shù)成就》《變出意外 幻在意中——論〈聊齋〉高潮的組織》等篇中的《聊齋》都是《聊齋志異》的簡稱。而有些論文的分段標題也用《聊齋》替代《聊齋志異》,行文表述中這種現(xiàn)象就更多了。另外有的雜志如《新聊齋》的刊名也屬于這種情況。
以上所舉數(shù)例是僅從聊齋學研究著述方面選擇的,而這種現(xiàn)象也蔓延到詩詞創(chuàng)作甚至文藝作品領(lǐng)域。如蒲松齡紀念館藏書畫作品中社會名流題贈的詩詞聯(lián)句,也有這種現(xiàn)象。葉圣陶的題聯(lián):“幼年頗讀聊齋垂老猶能不怕鬼;譯本遍傳異域奇文共賞固亦然。”陳叔亮書陽翰笙詩:“鬼非鬼怪狐非狐,畫盡人間世俗圖。蒲翁倘使生當代,聊齋能不寫工農(nóng)?”臧克家題詩:“從小聽聊齋故事,聽得入了神。長大讀聊齋,一遍兩遍永遠不過癮……多少枕上的不眠之夜,聊齋像好友伴我寂岑……感謝聊齋的主人,你歷盡了人間的酸辛……借著狐仙鬼怪的口,說出了人間的是非和寒溫。不可一日無聊齋,貴人們從中尋找開心。聊齋不厭百回讀,它使千萬人發(fā)笑也淚涔涔。”陳恒安題詩:“記取聊齋黔本無,朱批猶有但云湖。柳泉若當茅臺酒,灑向南天字字珠。”余修題詩(之二):“綽然堂前寫聊齋,草屋三楹稱留仙。為抒孤憤喜談鬼,風流一代傳文彩。”啟功題詩:“聊齋數(shù)仞郁崔巍,千古雄文日月輝。弄斧題詩吾豈敢,且隨曾點詠而歸。”關(guān)天相題句:“搔癢不著贊何益,入骨三分罵亦精。余舊有板橋眉批聊齋殘卷三冊,中多精譬之見且綴有詩,更多佳句。大荒先生欲錄未遑,而此書竟毀于十年動亂。今蒞蒲氏故居,憶此二語,書之志念,以奉蒲松齡故居存正。”胡繩題詩:“故居幸未罹文劫,依舊青山繞柳泉。一帙聊齋傳百代,求真刺惡說狐仙。”賀敬之題詩:“柳泉跡存留仙在,有限山川無限才。向燈父老閃淚眼,猶記兒時聽聊齋。”馮其庸書王漁洋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yīng)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后綴詩題“漁洋先生題聊齋詩”)李希凡題詩:“聊齋紅樓,一短一長。千古絕唱,萬世流芳。”高占祥題句:“短篇巨著世稀才,狐諧鬼唱入聊齋。”倫杰賢題聯(lián):“聊齋箴世;柳泉洗心。”李樺為蒲松齡紀念館作畫并題詩:“牛鬼蛇神登舞臺,狐仙妖怪不為災(zāi)。只緣留翁抒孤憤,青林黑塞托聊齋。”閻麗川畫牡丹圖并題句:“夜觀葛巾聊齋劇,晨起意摹洛陽花。”李燕畫狐貍圖并題句:“聊齋之中多有之,今戲作此可乎?”霍春陽畫牡丹圖并題句:“讀聊齋葛巾篇有感。”柳倩詩題《讀聊齋胭脂篇并觀越劇》。以上作品中所涉及的“聊齋”,皆為《聊齋志異》無疑。
上世紀80年代后期,為《聊齋志異》電視劇創(chuàng)作的主題曲《說聊齋》(喬羽作詞,王立平作曲),一經(jīng)傳唱即風靡全國。歌詞內(nèi)容如下:
你也說聊齋,我也說聊齋,喜怒哀樂一起那個都到那心頭來。鬼也不是那鬼,怪也不是那怪,牛鬼蛇神它倒比正人君子更可愛……笑中也有淚,樂中也有哀,幾分莊嚴,幾分詼諧,幾分玩笑,幾分那個感慨。此中滋味,誰能解得開……
不說大家也明白,歌詞中的“聊齋”即指《聊齋志異》。“你也說聊齋,我也說聊齋”,可都把那《志異》書名撇到了一邊!① 前面列舉的例子,皆有關(guān)學術(shù)研究領(lǐng)域,影響面小,可經(jīng)過《說聊齋》歌曲這一普及,全國各地乃至海外觀眾都知道了故事內(nèi)容是來自《聊齋》這部書,而《志異》書名卻好像無所謂了!這連其作者蒲老先生也未料到后人會擅改他的書名!
其實,將《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并非今人的創(chuàng)新,早在數(shù)百年前的古人就已開了先河。此事需要從頭說起。
二、前人誤導
蒲松齡生前,其著作無力梓行,只靠民間傳抄流傳,影響有限。至其逝后半個多世紀的乾隆三十年,才有時任睦州(嚴陵)太守的山東萊陽人趙起杲出資刻印《聊齋志異》。前后歷時半年多,其靠自己俸祿不足,便典質(zhì)家藏以繼之。書未刻完,他竟暴卒于主考童試的嚴郡試院任上。后由其弟與余集和鮑廷博印成,謂之青柯亭版《聊齋志異》,首創(chuàng)了該書印刷的先河。從此,諸多評注序跋題詠相繼出現(xiàn),而將《聊齋志異》簡稱為《聊齋》的現(xiàn)象亦隨之而至。
如劉瀛珍《〈聊齋志異〉遺稿序》云:“將欲區(qū)文章之善否,不必以理法繩也,但取而讀之……《聊齋》正編行世已久,……今乃得其遺稿若干首,奇情異采,矯然若生,而亡是公烏有先生又于于然來矣。黎陽段君雪亭,毅然以付梓自任,斯豈獨《聊齋》之知己,抑亦眾讀《聊齋》者所郁郁于中,而今甫得一伸者也。故樂為編次而序之。” [1]2360
陳廷機《序》云:“諸小說正編既出,必有續(xù)作隨其后,雖不能媲美前人,亦襲貌而竊其似。而蒲聊齋之《志異》獨無。……維時雪亭段君,踴躍付梓,快人快事,其有古人不見我之思乎?抑念兩美必合,《聊齋》之后復有《聊齋》,此亦天地間不可無之佳話,以視他書之贅而續(xù)之者何如也?……仆亦登記數(shù)則。非敢?guī)住读凝S》萬一,抑以事有不可沒者,爰率爾為之,以詳其顛末云爾。” [1]2363
段雪亭撰《例言》中有“所見《聊齋》刊本不一,有截其序者,有去其題詞、例言、小傳者,有刪其短篇者,有分門別類……” [1]2364等語。
喻焜為其所刻《聊齋志異馮但合評》撰序云:“《聊齋》評本,前有王漁洋、何體正兩家,及云湖但氏新評出,披隙導竅,當頭棒喝,讀者無不俯首皈依,幾于家有其書矣。然竊觀《聊齋》筆墨淵古,寄托遙深……” [1]2367
光緒十二年古越高昌寒食生為《詳注〈聊齋志異〉圖詠》本作序云:“《聊齋志異》一書,《齊諧》志怪之作也……《聊齋》所志,其事非盡為刑天舞戚,其人非盡屬牛鬼蛇神,則其圖之也……此廣百宋齋主人《〈聊齋志異〉圖詠》之所由作也……書成,丐序于余,余曰:‘是于《山海》《爾雅》之外,別開生面者也。以余襪線才,得以附《聊齋》驥尾,何快如之!’遂援筆而為之序。” [1]2369
道光五年蔡培為呂湛恩《〈聊齋志異〉注》作序云:“乙酉春,偶從博庵王少府案頭,見有《聊齋志異注》十六卷,詢知為呂子叔清所輯……因慨然曰:‘異哉!呂子之為是注也……若《聊齋》一書,乃柳泉不遇于時者之所為……毋乃膠柱鼓瑟乎?’” [1]2374
嘉慶二十三年馮鎮(zhèn)巒《讀〈聊齋〉雜說》云:
柳泉《志異》一書,風行天下,萬口傳誦……柳崖遂謂聊齋后身,青林黑塞間倘別有其人乎?吾將遇之。
平生喜讀《史》《漢》,消悶則惟《聊齋》……
《聊齋》非獨文筆之佳,獨有千古……
吾閑中偶然設(shè)想,柳泉一老貢士耳,同時王侯卿相,湮沒不知姓名者不知凡幾,聊齋獨以此一書傳,海澨山陬,雅俗共賞。即聊齋其他詩古文詞,亦不似此書流傳之遠……
此書多敘山左右及淄川縣事……聊齋家世交游,亦隱約可見。獨柳泉別種詩文,不可得聞。予于《雨村詩話》中見古作一首,實非凡筆。
詞令之妙,首推《左》《國》……聊齋吐屬,錦心繡口,佳處難盡言,如《邵女》……不能一一詳也。
往予評《聊齋》,有五大例:一論文,二論事,三考據(jù),四旁證,五游戲……
是書傳后,效顰者紛如牛毛,真不自分量矣。無聊齋本領(lǐng),而但說鬼說狐,侈陳怪異,筆墨既無可觀,命意不解所謂……比似《聊齋》,豈不相懸萬哉!……
文有設(shè)身處地法。昔趙松雪好畫馬,晚更入妙……聊齋處處以此會之。
讀《聊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漢……
《聊齋》之妙,同于化工賦物,人各面目……
昔人謂:“莫易于說鬼,莫難于說虎。”鬼無倫次,虎有性情也……試觀聊齋說鬼狐,即以人事之倫次,百物之性情說之……
或疑聊齋那有許多閑工夫,捏造許多閑話。予曰:“以文不以事也……何獨于《聊齋》而疑之。取其文可也。”
俗手作文,如小兒舞鮑老,只有一副面具……《左》《史》之文,無所不有,《聊齋》仿佛遇之。
作文有前暗后明之法……聊齋亦往往用之。
此書即史家列傳體也,以班、馬之筆,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說。可惜《聊齋》不當一代之制作……
沈確士曰:“文章一道,通于兵法……”聊齋用筆跳脫超妙,往往與中一二突接之處,仿佛遇之,惟會心人能格外領(lǐng)取也。
《水經(jīng)注》形容水之清澈,曰:“分沙漏石。”又曰……皆極造語之妙。聊齋中間用字法,不過一二字,偶露句中,遂已絕妙,形容惟妙惟肖,仿佛《水經(jīng)注》造語。
小說,宋不如唐,唐不如漢……故讀古書不多,不知《聊齋》之妙。
昔鐘退谷先生坐秦淮水榭,作《史懷》一書,……予批《聊齋》,自信獨具冷眼。倘遇竟陵,定要把臂入林。
友人曰:“漁洋評太略,遠村評太詳……然《聊齋》得遠村批評一番,另長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
紀曉嵐曰:“《聊齋》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留仙之才,予誠莫逮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遠村曰:“《聊齋》以傳記體敘小說之事,仿《史》《漢》遺法,一書兼二體,弊實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愛之,俗人亦愛之,竟傳矣。雖有乖體例可也。紀公《閱微草堂》四種,頗無二者之病……其生趣不逮矣。”
文之參錯,莫如《左傳》……左氏篇篇變,句句變,字字變。上三條,讀《聊齋》者亦以此意參之,消息甚微,非深于古者不解。
《聊齋》短篇文字不如大篇出色,然其敘事簡凈,用筆明雅,譬諸游山者,才過一山,又問一山……晚涼新浴,豆花棚下,搖蕉尾,說曲折,興復不淺也。
趙清曜謂:“先生書成,就正于漁洋,漁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不與,因加評騭而還之。”予思漁洋一代偉人,文章總持,主騷壇者數(shù)十年,天下翕然宗之,何必與聊齋爭之。且此書評語亦只循常,未甚騷著痛癢處,《聊齋》固不以漁洋重也。或謂漁洋跋,含蓄有味……漁洋實有不足聊齋處,故以率筆應(yīng)酬之,原非見地不高。公是公非,何能為古人諱。
予讀《李義山集》,集前有一條云:“詩人刻露天地間山川、草木、人物、百怪,幾于毫不留余矣。故少達多窮,以其鑿破混茫,發(fā)泄太盡,犯造物之忌也。”《聊齋》雖小說,描寫盡致,實犯此忌。故文名傳世,遇合蹇澀,以貢士終。壬戌在京師,與會理州嚴鶴堂爾讠惠同館。嚴曰:“聞聊齋犯雷劫。”予大怒曰:“此口孽也!聊齋圣賢路上人,觀其議論平允,心術(shù)純正,即以程、朱語錄比對觀之,亦未見其有異也。慧業(yè)文人如聊齋者,歿后不向圣賢位中去,定向仙佛位中來也。可以妄語污蔑也哉!”
先秦之文,段落渾于無形。唐、宋八家,第一段落要緊。蓋段落分,而篇法作意出矣。予于《聊齋》,鉤清段落,明如指掌。
近來說部,往往好以詞勝,搬衍麗藻,以表風華,涂繪古事,以炫博雅。《聊齋》于粗服亂頭中,略入一二古句,略裝一二古字……斑剝陸離,蒼翠欲滴,彌見大方,無一點小家子強作貧兒賣富丑態(tài),所以可貴。
《聊齋》說鬼說狐,層見疊出,各極變化……
讀法四則:
一、是書當以讀 《左傳》之法讀之。《左傳》闊大,《聊齋》工細。其敘事變化,無法不備;其刻畫盡致,無妙不臻。工細亦闊大也。
一、是書當以讀《莊子》之法讀之。《莊子》惝恍,《聊齋》綿密。雖說鬼說狐,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xiàn);如未央宮闕,實地造成。綿密實惝恍也。
一、是書當以讀《史記》之法讀之。《史記》氣盛,《聊齋》氣幽。從夜火篝燈入,從白日青天出。排山倒海,一筆數(shù)行;福地洞天,別開世界。亦幽亦盛。
一、是書當以讀程、朱語錄之法讀之。語錄理精,《聊齋》情當。凡事境奇怪,實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與先正不背在情理中也。[1]2385
以上舉例皆選自《聊齋志異》版本序跋中。另外,其版本題詠也有這方面內(nèi)容,一并選擇錄下:
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載朱緗七言詩末首云:
捃摭成編載一車,詼諧玩世意何如?
山精野鬼紛紛是,不見先生志異書![1]2387
青柯亭本《聊齋志異》載高鳳翰題詩云:
庭梧葉老秋聲干,庭花月黑秋陰寒。
《聊齋》一卷破岑寂,燈光變綠秋窗前…… [1]2387
余集題詩,前有小引云:
丙戌之冬,《志異》刻成,距荷邨歿又五匝月矣。以文索余賦詩殿諸君之后;余不解詩,其何能作?雖然,題《聊齋》可不作,而悲荷邨不容已也…… [1]2388
《聊齋志異》遺稿本載胡泉調(diào)寄[貂裘換酒]詞云:
留仙傳久矣,怎又把斷雨零云,從頭說起?觸目琳瑯沉吟卻,不似蘇豪柳膩。憶當年,抨彈紅紫隨時戲,也無心軒翥文林地。因此上,有遺志。" " 神仙富貴都虛耳,藉星星妖狐厲鬼,猶存忠義。暗惜年華如逝水,何苦勞勞不已?喜仙子蘭心蕙質(zhì),風流一洗寒酸氣。清酒一壺歌一曲,味詩書此外無他嗜。刊《聊齋》,有深意…… [1]2392
王廷華題[惜分釵]詞云:
聊齋筆,狐鬼跡,真真假假空耶色?墨痕干,夜光寒,經(jīng)營慘淡,淚燭成斑,難,難!nbsp; " 江上客,哦松室,小楷蠅頭消永日。一回刪,一回攢,鐫梨刬棗,成就今番,看,看![1]2397
從以上所舉多例中可見,無論是版本序跋或是題詠詩詞內(nèi)容,凡涉及到《聊齋志異》的書名時,會出現(xiàn)一種混亂概念,既有全稱《聊齋志異》者,也有簡稱《志異》者,更多的則臆稱《聊齋》者。同一篇內(nèi)容竟將幾種稱謂交替使用,還有的用《聊齋》既當書名,又當“聊齋先生”,再加上“留仙、柳泉”稱謂混雜其間,便形成了一種亂象,以至于流傳至今。
三、最終結(jié)論
分析以上問題的癥結(jié)所在,是其未能正確理解《聊齋志異》書名的結(jié)構(gòu)原意,簡單地認為《聊齋》可以替代整個書名,忽略了《志異》才是書名的主體,而“聊齋”只是作者的代稱而已。
青柯亭本《聊齋志異》,載有蒲立德乾隆五年《跋》稱:“《志異》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先大父諱松齡,字留仙,別號柳泉。聊齋,其齋名也……” [1]2357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載有殿春亭主人雍正癸卯秋七月《跋》稱:“余家舊有蒲聊齋先生《志異》抄本,亦不知其何從得……” [1]2358該本同時載有雍正癸卯秋七月南邨題跋稱:“余讀《聊齋志異》竟,不禁推案起立……聊齋少負艷才,牢落名場無所遇……向使聊齋早脫耩去,奮筆石渠、天祿間,為一代史局大作手……” [1]2359以上三《跋》可證,“聊齋”既是蒲松齡的齋名,又是其代稱,時人尊稱謂“聊齋先生”。蒲松齡亦自稱“聊齋”,如《聊齋志異》自序,就稱《聊齋自志》。
書中卷四有《狐夢》一篇,敘其友與狐女交往故事云:“余友畢怡庵,倜儻不群,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yè),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于樓上,攝想凝思……”后果然有狐女來,交往年余,臨別問畢怡庵:“君視我孰如青鳳?”畢怡庵答曰:“殆過之。”狐女曰:“我自慚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怡庵曰:“夙有此志……”篇末記云:“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墨有光榮矣。’遂志之。” [2]622
以此可證,不僅時人稱其“聊齋”,其亦自稱“聊齋”。且有自志的文字記載。
《聊齋詩集·庚寅·斗室》云:
聊齋有屋僅容膝,積土編茅面舊壁。
叢柏覆陰晝冥冥,六月森寒類窟室……" [3]629
《聊齋詩集·續(xù)錄(戊寅)·聊齋》七律一首云:
聊齋野叟近城居,歸日東籬自把鋤。
枯蠹只應(yīng)書卷老,空囊不合斗升余……" [3]683
兩詩中不僅都自稱謂“聊齋”,且其二詩題亦稱《聊齋》。
《聊齋詩集·己巳·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云:
志異書成共笑之,布袍蕭索鬢如絲。
十年頗得黃州意,冷雨寒燈夜話時。[3]543
詩中所稱“志異”即《聊齋志異》。
雍正三年二月,張元撰《柳泉蒲先生墓表》稱:“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 [3]1814
蒲箬撰《清故顯考歲進士、候選儒學訓導柳泉公行述》稱:“……先父諱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居士……一時名公鉅卿,日以文事相煩……如《志異》八卷,漁搜聞見,抒寫襟懷,積數(shù)年而成……” [3]1818
《蒲箬等祭父文》稱:“……我父少有才名,為海內(nèi)所推重,而淪落不偶,僅托諸悲歌慷慨之間。故詩賦詞章,集而帙者凡千余首;序表婚啟壽屏祭幛等文,計四百余篇;暮年著《聊齋志異》八卷,每卷各數(shù)萬言,高司寇、唐太史兩先生序傳于首,漁洋先生評跋于后……” [3]1821
以上史料中皆有《聊齋志異》八卷之記載,而未見有簡稱《聊齋》之書名,反倒是聊齋先生自己詩中稱其書名為《志異》。
可以肯定地說,聊齋即蒲松齡,蒲松齡即聊齋。這是其生前自己命名的齋稱,因而亦作為本人代稱。而時人也稱其“聊齋”,更尊稱其“聊齋先生”,如楊萬春與其信函稱《致聊齋》;《狐夢》中狐女與畢怡庵對話,稱“聊齋與君文字交”;《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載殿春亭主人《跋》稱:“余家舊有蒲聊齋先生《志異》抄本。”皆可證實(當然,聊齋作為其居室而言,是有專指性的,如蒲松齡故居院中的“聊齋正房”遺址,則另當別論)。
對于《聊齋志異》的書名而言,可以全稱,如各種抄本與刻本,皆用全稱。也能簡稱為《志異》,如聊齋詩《次韻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見贈》所云“志異書成共笑之”句,蒲箬《柳泉公行述》所云“如《志異》八卷”,以及前面所舉例中稱謂《志異》者,皆可證實。但絕不能用《聊齋》代稱之,因為書名是《志異》,“聊齋”只是作者書齋名或自稱,是不能混為一體的兩個概念。當年柳泉公自命齋稱為“聊齋”,并作為本人的代稱,還將其冠于自己的著作名前,謂之《聊齋志異》《聊齋詩集》《聊齋詞集》《聊齋文集》《聊齋俚曲》等,可能意在說明,這些作品的著作權(quán)統(tǒng)歸聊齋所有。以此而論,這些作品的簡稱,都不能用《聊齋》替代之。
那么,為什么古人今人都想將《聊齋志異》書名簡化臆改為《聊齋》呢?估計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嫌書名字多,想簡化之;二是未弄清書名結(jié)構(gòu)原意,隨便臆改;三是無人規(guī)范糾正,任意蔓延;四是口語習慣使然。難于真正說清。
總之,以往都成歷史,無法更改。目前應(yīng)當通過商榷達成共識,以利后來者。
參考文獻:
[1][清]蒲松齡,著.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M].任篤行,輯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2][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張友鶴,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清]蒲松齡,著.蒲松齡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Can Liaozhai Zhiyi be abbreviated as Liaozhai
Yang" Hairu
(Pu Songling memorial hall,zibo 25512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correct the nonstandard understanding that the title of Liaozhai Zhiyi was simplified and renamed as Liaozhai in the field of Liaozhaiology and the creation of literary works. This phenomenon has been inherited from 300 years ago,and it has a tendency of convention,but no one has ever talked about it. In fact,Liaozhai is the name of Pu Songling's habitable room,and it is also its pronoun. At that time,people also called him Mr. Liao Zhai,his works were all preceded by Liaozhai,which was called Liaozhai Poetry Collection,Liaozhai Ci Collection,Liaozhai Anthology,Liaozhai Zhiyi and Liaozhai Folk Songs,etc.,to show that these works were all written by Liaozhai. The title of Liaozhai Zhiyi is the full name. If it needs to be simplified,it can only be called Zhiyi,not Liaozhai. The author starts with the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carefully researches and draws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re is no trivial matter in writing,and academic research seeks truth,and it is not allowed to assume and fabricate. The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standardized in the field of Liaozhaiology cannot be left to future generations to solve.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Pu Songling;academic research;seeking truth
(責任編輯:朱" 峰)
①淄川方言,邊的發(fā)音為biai。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4?0026?11
收稿日期:2024-08-06
作者簡介:楊海儒(1944- ),男,山東淄博人。蒲松齡紀念館研究館員,《蒲松齡研究》學術(shù)顧問,蒲松齡紀念館學術(shù)委員會委員,中國聊齋學會(籌)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