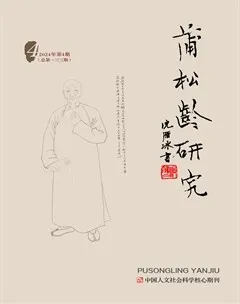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聊齋志異》對新城王氏家族的形象塑造
摘要:《聊齋志異》中,《四十千》《龁石》《廟鬼》《王司馬》這4篇小說的主人公都來自新城王氏家族。本文從新城王氏族人和家中仆人兩方面分析《聊齋志異》對新城王氏家族人物的形象塑造,追溯這些人物形象的原型,并通過分析《聊齋志異》其他篇目,補充、完善了《聊齋志異》對新城王氏家族的整體形象塑造。
關(guān)鍵詞:《聊齋志異》;新城王氏家族;形象塑造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biāo)志碼:A
《聊齋志異》是清代文學(xué)家蒲松齡創(chuàng)作的文言短篇小說集,成稿于清康熙年間。同時期,在孝婦河下游有一個世家大族——新城王氏。這個家族已興盛一百余年,被尊為“喬木世家” [1]1“江北青箱” [2],清代詩人、文學(xué)家、詩詞理論家王漁洋是這個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聊齋志異》中有許多故事取材于民間奇聞異事,其中就有關(guān)于新城王氏家族的故事。
一、《聊齋志異》對新城王氏家族人物的形象塑造
《聊齋志異》中有4篇小說的主人公來自新城王氏家族,這4篇分別是《廟鬼》《王司馬》《四十千》《龁石》。其中,《廟鬼》和《王司馬》的主人公是新城王氏族人,《四十千》和《龁石》的主人公是新城王家的仆人。
(一)對新城王氏族人形象的塑造
《廟鬼》的主人公是新城王氏第九世王啟后,文中描述他對引誘他的婦人“意堅定,終不搖” [3]45,是一個意志堅定、能禁得住誘惑的人。后借武士之口說:“樸誠者汝何敢擾。” [3]45夸贊他樸實忠厚。《王司馬》的主人公是新城王氏第六世祖王象乾,文中用舞動真假大刀震懾敵兵、蘆葦籬笆化身長城、坦臥營帳嚇退敵軍這三個情節(jié)刻畫了王象乾足智多謀、沉著冷靜的形象。
這兩則故事塑造的新城王氏族人形象都是正面的。其中原因,筆者認為有四個方面。首先,新城王氏家族在民間有口皆碑、婦孺皆知,家族成員勤勞質(zhì)樸、樂善好施。二世祖王伍舍粥行善,救濟貧苦百姓,被稱作“善行公”“王菩薩”,救災(zāi)民于水火之中,為家族后世留下了在災(zāi)荒年份賑災(zāi)救災(zāi)的好傳統(tǒng)。王氏家訓(xùn)稱“終身為善不足,一日為惡有余” [4]11“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5]15,要求族人多做善事,積累德行和善舉。其次,王啟后和王象乾都不是名聲不好之人,《聊齋志異》對二人形象的塑造基本符合人物原型。蒲松齡在創(chuàng)作時也注重作品的紀(jì)實性,“蒲松齡小說在創(chuàng)作動機上自覺依傍主流文化、‘羽翼信史’的特點,即重視記事寫實和強化勸懲的功能” [6]4。第三,蒲松齡坐館的東家畢氏與王氏家族是姻親之好。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開始在西鋪村畢際有家坐館,一直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撤帳歸里 [7]80。畢際有是王漁洋的從姑父,他的夫人是王象乾的堂侄女。畢際有對蒲松齡關(guān)懷備至、以禮相待,賓主之間相處融洽。康熙二十六年(1687),王漁洋在畢家見到了蒲松齡 [7]78,二人把酒論詩,相談甚歡,自此二十余年一直惺惺相惜,互通書信。這樣,不管蒲松齡是從畢家那里還是王漁洋那里聽到了王氏家族的故事,或是從其他渠道獲取了王家故事的素材,因著蒲松齡與畢際有、王漁洋的關(guān)系,《聊齋志異》都不太可能出現(xiàn)王氏族人負面的形象。最后,蒲松齡對王漁洋非常敬重。王漁洋不僅為《聊齋志異》題詩,還寫了30多則批語點評《聊齋志異》,蒲松齡在懷才不遇之際,得到了王漁洋這樣一位高官重臣、文壇名流的贊賞和鼓勵,自然對王漁洋十分欽敬,如此,《聊齋志異》中王氏族人的形象必然是正面積極的。
(二)對新城王家仆人形象的塑造
《四十千》的主人公是新城王氏第六世祖王象乾家中掌管錢糧收支的仆人,相當(dāng)于是管家。這位管家相信因果報應(yīng),他認為自己的兒子是夙孽,是來向自己討要四十千錢的債務(wù)。根據(jù)蒲松齡描述,管家家中非常富裕,富裕到什么程度呢?一是家中養(yǎng)有乳母,二是被人稱作“素封”,即雖無官爵封邑,卻富比封君的人。《龁石》的主人公是新城王氏第七世族人王與敕家一個養(yǎng)馬的仆人,但他自幼在嶗山學(xué)道,不吃熟食,只吃松子和白石頭,渾身長滿了毛。后來念及母親年邁,就返回故里住了一段時間,雖然漸漸恢復(fù)了吃熟食的習(xí)慣,但還是喜歡吃石頭。母親去世后,他又回到了嶗山,來去瀟灑自由,輕松自在。
《四十千》中的“素封”和《龁石》中的“道士”,都不像我們平常認知里的“仆人”,他們或是在物質(zhì)上、或是在精神上都十分“自由”。雖然明清時期富裕的奴仆并不少見,他們的財產(chǎn)權(quán)受法律保護,而且奴仆在法律上是有生存權(quán)和一定的自主權(quán)利,但“明清時期的賤民不僅要忍受來自官府和社會成員的歧視,而且還常會遭遇肉體上的痛苦” [8]202。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新城王家的仆人確實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研究解讀新城王氏家訓(xùn),可找到這種家仆形象的合理性。新城王氏家族一方面堅持尊卑原則,對奴仆嚴(yán)加管束;另一方面也要求族人子孫善待下人奴仆。王漁洋在《手鏡》中寫道:“馭胥役輩要嚴(yán),亦要體恤人情,勿近刻薄。” [9]32胥役包括胥吏,胥吏與奴婢、倡優(yōu)共同構(gòu)成了明清時期的賤民階層,胥吏主要由衙役、長隨和官員家人構(gòu)成,而官員家人就是官員家中的奴仆。[8]91王漁洋還教育兒子“下人衣食,亦須照管,令其無缺” [9]2。除了關(guān)心體恤奴仆之外,王氏族人還盡量在人格上平等地對待奴仆及其子女,如王漁洋祖父王象晉在《清寤齋心賞編》中說:“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 [5]19積極鼓勵奴仆們不要甘于貧窮和身份低賤,要樹立遠大志向,增強自身才能。
二、《聊齋志異》中新城王氏家族人物的現(xiàn)實原型
(一)王啟后
在明代名臣葉向高所撰的《處士王公傳》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
有被酒者,過城隍廟,侮神。忽身舉去地若懸,困苦甚,呼號于眾,言其故。眾為禱,不解。則曰:“若無為,須王菩薩乃可耳。”眾共請公。公謙讓:“神誕若乎?乃公何當(dāng)焉?”眾請益堅。公不得已,為一往,禱辭未畢,酒人已無恙矣。匍匐泣謝:“微公,我何逃于神罰?”公曰:“此神德也,誰敢貪之?”人以是愈益敬公。[10]492
將此故事與《廟鬼》進行對比,有許多相似之處。故事都是講城隍廟中的鬼神作怪,《處士王公傳》中喝醉酒的人是“身舉去地若懸”;《廟鬼》中的王啟后在患瘋癲病之前則是“足離地,挺然立當(dāng)中” [3]45。二人都被鬼神懸在了半空,都因王氏族人的德行化解了危機,《處士王公傳》是因為王伍德高望重救下了醉酒的人;《廟鬼》中的武士因為王啟后樸實忠厚才選擇營救他,最后打敗了城隍廟中的泥鬼。據(jù)此,筆者推測,《廟鬼》中王啟后的形象或許借用了新城王氏第二世祖王伍的形象。
(二)王象乾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號霽宇,明隆慶五年(1571)進士,歷仕隆慶、萬歷、泰昌、天啟、崇禎五朝,官至兵部尚書,累加太子太師。他安邊卻敵,威震九邊,為保衛(wèi)明王朝立下了汗馬功勞。
《王司馬》中關(guān)于王象乾的三個故事都發(fā)生在王象乾鎮(zhèn)守北方邊關(guān)時。在蒲松齡筆下,王象乾是個有膽有謀、善于騎射之人。現(xiàn)實中的王象乾也確實如此,《明史稿》載:“象乾機警有膽略,善騎射,熟外蕃故事、一切土俗及種落家世。” [11]1《聊齋志異》里的王司馬頗有威望,北邊的各個部落對他敬若神明。這一文學(xué)形象在《明史稿》中也能找到依據(jù):“諸部長皆懾不敢動……諸部長素懾象乾,愿獻馬、牛、羊、駱駝贖罪,通貢如故。” [11]3萬歷四十七年(1619),萬歷皇帝恩準(zhǔn)王象乾建造四世宮保坊(現(xiàn)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追封其曾祖王麟、祖父王重光、父親王之垣同為“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崇禎元年(1628),83歲的王象乾重被啟用,總督宣、大、山西軍務(wù)。崇禎皇帝詢問王象乾軍事方略,都對答如流。崇禎二年(1629),王象乾乞歸致仕,次年病逝。
(三)王家仆人
關(guān)于《龁石》中馬夫的人物原型,王漁洋在《池北偶談·談異一·啖石》 [12]3337中給出了答案,該馬夫是自家的傭人王嘉祿。《四十千》中的管家原型,目前還沒有相關(guān)資料確認其人物原型。
在明清時期,奴仆允許擁有個人財產(chǎn),包括擁有自己的奴仆,所以《四十千》中的管家養(yǎng)有乳母而且積蓄了大量的錢財,這種現(xiàn)象是確可存在的。他們雖然累積了巨大的財富,但社會地位仍低于庶民。如此富有的管家為何會欠別人四十千錢呢?明清時期的一些奴仆會利用被服務(wù)對象賦予的權(quán)利,對“吏民百姓上下其手,勒索納賄,所以能夠積蓄不少錢財” [8]119,這種現(xiàn)象在被服務(wù)對象是官宦人家的情況下表現(xiàn)得更加明顯。管家可能是通過非法途徑獲取了別人的錢財,又想賴賬,心中有鬼才會夢見討債的人。蒲松齡雖然沒有批判新城王家族人,卻在《四十千》這篇短文中批判了王家仆人,揭露了現(xiàn)實生活中世家豪奴仗勢欺人、欠債不還的現(xiàn)象,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認識價值。
三、《聊齋志異》中其他篇目對新城王氏家族形象的塑造
《聊齋志異》中還有一些篇目的主人公是新城王氏親族的族人,他們從另一個側(cè)面補充、完善了《聊齋志異》對新城王氏家族的整體形象塑造。對于這些篇目的主人公,蒲松齡或贊頌、或批判、或無情感傾向,只是單純引出所敘述的故事。
(一)借人物講述故事
《龍取水》的主人公徐夜(1612—1684),原名元善,字長工,號小巒,由明入清后,改名為夜,字東癡,號嵇庵,他的外祖父是王漁洋的叔祖王象春。徐夜三歲時父親去世,因此他幼時一直跟隨母親住在外祖父家,與王漁洋關(guān)系極為親密。蒲松齡通過徐夜南游的經(jīng)歷,描述了“龍取水”這一怪奇自然現(xiàn)象。《狐夢》的主人公是畢際有的族人畢怡庵,蒲松齡借其夢境描寫了一個人狐相戀的傳奇故事。《安期島》的主人公劉鴻訓(xùn)(1565—1634),字默承,號青岳,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進士,曾出訪朝鮮,官至內(nèi)閣首輔,授太子太保銜,升文淵閣大學(xué)士。新城王氏第六世祖王象咸的夫人出自劉鴻訓(xùn)家族,而王漁洋的孫女嫁給了劉家的劉宗璐。劉鴻訓(xùn)在出使朝鮮的歸途中的確遇到過海難,最后幸免于難,蒲松齡在這一真實事件的基礎(chǔ)上進行了夸張和虛構(gòu)。以上三篇故事中人物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借人物講述故事。
(二)對人物的贊頌和批判
《楊千總》的故事取自畢際有的父親畢自嚴(yán)的親身經(jīng)歷。故事夸贊了楊千總的高超箭法,批判了封建時期官員出行時要求百姓避讓這一惡習(xí),并通過畢自嚴(yán)喝止楊千總?cè)我馍錃傩者@個情節(jié),贊頌了畢自嚴(yán)持正公允、愛護百姓的品德操守。《放蝶》中,第二個故事的主人公于重寅,清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他的祖父于永清是明代的監(jiān)察御史,于家與新城王氏也有姻親關(guān)系,王漁洋族叔王與胤的夫人便出自于永清家族。蒲松齡評價于重寅“性放誕”,之后通過描述“火驢”這件荒唐事,表達了對于重寅的貶斥和憎惡。這里可以看出,蒲松齡并不會因為主人公是官僚世家就回避或一味褒揚,而是實事求是地刻畫人物形象。蒲松齡在他的故事里贊頌新城王氏族人的品德和功績,是對新城王氏族人人品的肯定,也進一步鞏固了新城王氏在士民心中的正面形象。
(三)對某種社會現(xiàn)象的批判
《鴿異》《庫官》的主人公都是鄒平張延登家族族人。張延登(1566—1641),字濟美,號華東,明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官至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延登家族和王漁洋家族世代聯(lián)姻,王漁洋娶張延登孫女為妻,他的大哥王士祿亦娶張家之女,王漁洋的一個姑姑也嫁入了張家。兩個世家望族通過聯(lián)姻,維系家族地位和門第不墜。關(guān)于《鴿異》的主人公,趙伯陶在《〈聊齋〉叢脞錄——說〈鴿異〉》中認為,并非《鴿經(jīng)》的作者張萬鐘,而是張萬鐘的弟弟張萬斛。[13]33《鴿經(jīng)》之所以能夠流傳后世,得益于張萬鐘的女婿王漁洋,正是王漁洋將《鴿經(jīng)》收錄在《檀幾叢書》中,才使得此書能夠面世,成為我國目前已知最早記載鴿子的專著。蒲松齡在《鴿異》中借張公子贈送珍貴白鴿給貴官一事和異史氏之語,批判諷刺了官場中討好上官、獻媚權(quán)貴的社會現(xiàn)象。《庫官》的主人公是張延登,故事表面是敘述了頒白叟庫官驛站作怪的故事,感慨命中收入皆有定數(shù)。故事之外,卻是蒲松齡借張延登從奉旨祭告南岳之行獲利二萬三千五百金之事,揭露批判封建政府的腐敗。王漁洋在看過《聊齋志異》后,對這些故事沒有提出異議,有兩種可能:一是對官場上的這些現(xiàn)象習(xí)以為常,思想上觸動不大;二是王漁洋本人也對這些現(xiàn)象深惡痛絕,希望借蒲松齡之筆,伐官場黑暗。清朝大學(xué)士王掞評價王漁洋為官:“曰知人之明,曰持身之潔,曰恤民之慈,曰用刑之慎。” [14]5111王漁洋一生為官清身潔己,不媚權(quán)貴,也曾拒絕給權(quán)相明珠寫金箋祝壽,因此,筆者更傾向于第二種可能。
參考文獻:
[1][明]陳繼儒.群芳譜序[M]//[明]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天啟元年刊本.1621.
[2][明]于慎行.王氏瑯琊公傳[Z].王士禛紀(jì)念館館藏石刻.
[3][清]蒲松齡.聊齋志異[M].長沙:岳麓書社,2019.
[4][明]王之垣.炳燭編[M]//[明]王之垣.炳燭編·攝生編.香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9.
[5][明]王象晉.清寤齋心賞編[G]//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編.新編新城王氏家箴.揚州:
廣陵書社,2016.
[6]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
[7]袁世碩.蒲松齡志[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8]蘇奇.明清賤民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xué),2022.
[9][清]王士禛.手鏡[G]//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編.新編新城王氏家箴.揚州:廣陵書社,
2016.
[10][明]葉向高.處士王公傳[M]//魏恒遠,編著.新城《王氏世譜》整理研究.濟南:齊魯書社,
2023.
[11][清]王鴻緒.明史稿·列傳·卷一百二十三[M].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
[12][清]王士禛.池北偶談·談異一·啖石[M]//[清]王士禛.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
2007.
[13]趙伯陶.《聊齋》叢脞錄——說《鴿異》[J].蒲松齡研究,2014,(1).
[14][清]王掞.傳記·皇清誥授資政大夫經(jīng)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M]//[清]王士禛.王
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
The Image-building of Xincheng Wang Family in Liaozhai Zhiyi
Chen Yanhua" Meng Zhu
(Wang Yuyang Culture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Center,Zibo 256403,China)
Abstract: The protagonists of the four novels in Liaozhai Zhiyi,namely Sishi Qian,He Shi,Miao Gui,Wang Sima,come from the Xincheng Wang Famil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ortrayal of the characters of the Xincheng Wang Family in Liaozhai Zhiyi from two aspects: the members of the Wang family and their servants. It traces the prototypes of these character images and supplements and improves the overall image-building of the Xincheng Wang Family in Liaozhai Zhiyi by analyzing other sections of the book.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Xincheng Wang Family;Image-building
(責(zé)任編輯:朱" 峰)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4?0037?07
收稿日期:2024-01-05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科聯(lián)2023年度人文社會科學(xué)課題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兩創(chuàng)”研究專項課題《“兩創(chuàng)”視域下的齊魯望族文化研究——以新城王氏家族為例》(編號:2023-WHLC-114)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陳艷華(1975- ),女,山東淄博人。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副主任,主要從事王漁洋文化研究和創(chuàng)意開發(fā)、古籍文獻研究;孟竹(1989- ),女,山東淄博人。王漁洋文化研究保護中心館員,主要從事文物博物和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