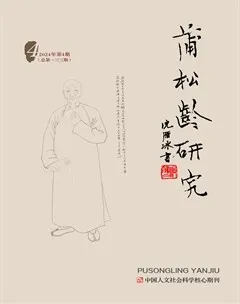《聊齋志異·采薇翁》人物本事與創作寓意考辨
摘要:本文厘清了《聊齋志異·采薇翁》中“芝生”是劉孔和的字及其生卒年份;劉孔和被劉澤清殺害的根本原因,是兩人對“國事”的不同態度;蒲松齡以“采薇翁”來命名人物及小說,應是出自《詩經·小雅·采薇》;蒲松齡的創作寓意主要體現在采薇翁的含義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表達了對劉孔和失敗教訓的深刻總結及其悲劇人生的深沉感喟。
關鍵詞:《聊齋志異》;劉芝生;采薇翁;創作寓意
中圖分類號:I207.419" " 文獻標志碼:A
《采薇翁》是《聊齋志異》中反映明清易代之際社會狀況的時事短篇,目前學界對于劉芝生其人本事、采薇翁的含義以及作者的創作寓意等問題還有著一些不同的認識。不揣淺陋,撰寫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關于書中人物“劉芝生”,《聊齋志異》諸多注本大都付之闕如,同時對其生卒年以及被劉澤清殺害的原因,有的觀點也多有可研討商榷之處。如有的著作對“劉芝生”的解釋:
劉芝生:當即劉孔和(1614—1644),字節之,長山(今屬山東省)人,明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劉鴻訓子。工詩,文章豪邁,好談兵。明崇禎十七年(1644)四月,清兵入關,劉孔和毀家紓難,起兵長白山中,聚眾三千,南下投劉澤清,旋因于廣座中有侮澤清,于同年十月間被害,年僅三十一歲。清王士禛《漁洋文集》卷五有《劉孔和王遵坦傳》。嘉慶六年(1801)《長山縣志》卷八《人物志·義烈》有傳,內容取自《劉孔和王遵坦傳》。[1]2026
筆者認為,這段話中有三處需要訂正或補充。
一是“芝生”未作解釋,這也是許多注本的缺憾。任篤行先生在《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中猜測“芝生或即節之之別號” [2]1580,但無文獻可征。據長山太和莊《劉氏家譜》卷二《世表》載:“孔和,字芝生,號節之,行二,邑廩生。” ① 可知“芝生”是劉孔和的字。劉孔和兄長劉孔中“字藥生”、弟弟劉孔武“字直生”,可見他們取字的方式是一致的。而王士禛《劉孔和王遵坦傳》、嘉慶《長山縣志》、道光《濟南府志》卷五十六《人物六》、陳鼎《留溪外傳》卷二《忠烈部下》等書中皆作“字節之”,或許是將劉孔和的字、號弄混,或許是劉孔和字“節之”與“芝生”兩者并用。因此,趙伯陶先生“簡評”中說蒲松齡“或許迫于當時形勢,不宜書寫其真名,只好以‘劉芝生’代之” [1]2029,就不夠準確了。更有甚者,王詠賦先生在其所編的《聊齋志異精裝分類全評本·神仙集》“老王感言”中寫道:“劉芝生‘自壞長城’(清朝評論家但明倫語),注定了他成不了氣候。果然,老王查了半天史料,也沒查到‘劉芝生’其人,說明他只是一個小毛賊。” [3]323-324因為不知道“芝生”是劉孔和的字,老王先生愣是把劉孔和這樣一個文武全才的抗清豪杰,當成了“小毛賊”,豈不可笑而又可嘆!
二是劉孔和的生卒年。關于劉孔和的生年,主要有三種說法,如:(1)約1613年,見王忠修等主編《鄒平歷史人物》;(2)1614年,見趙伯陶注評的《聊齋志異詳注新評》;(3)1615年,見盧興國主編的《鄒平名門望族》。余以第三種說法1615年為是,依據就是長山太和莊《劉氏家譜》卷二《世表》載:“公生于萬歷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巳時,卒于順治元年十月初一日,享年三十一歲。”其生年當以萬歷四十三年(1615)為準。對于劉孔和的享年,王士禛《劉孔和王遵坦傳》、嘉慶《長山縣志》、道光《濟南府志》以及太和莊《劉氏家譜》等都記載“年三十一歲”,清人徐釚撰《本事詩》說卒時“年才二十九” ① ,與諸書有異。劉孔和卒于順治元年(1644),《劉氏家譜》記作“順治元年十月初一日”,而清彭孫貽撰《蕩寇志》卷十三作“十月乙丑十一”(即順治元年十月初十一日),清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劉澤清》記載:“《甲乙史》云:甲申十月初九癸亥事。” [4]31則為順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九日,兩書所記與《劉氏家譜》相差幾天。
三是劉孔和被害原因。趙伯陶先生認為劉孔和被害的原因是“于廣座中有侮澤清” [1]2026,因為大庭廣眾之下侮辱了劉澤清而招致被殺,這個說法似未抓住根本,也與眾多史書的記載抵牾。《劉氏家譜》卷二記載:“值明末,闖逆犯順,乃散財結客,棰牛饗士,聚忠義數千人,起兵長白,樹義聯云:‘十七王德澤在人敢卜中興于再造,三百載臣節掃地愿抒下士之孤忠。’傳檄遠近,執禽偽縣令數人戮之。及闖逆陷京師,公率眾抵淮,駐軍黃河。時某以東平伯開藩淮上,憚公強,且以才名不相下,陰欲圖之,遂被害。”陳鼎《劉孔和傳》記載如下:
崇禎末,流賊熾中原。孔和忿之,投筆講武備,散家財結納海內豪俊,矢志滅賊。甲申闖逆犯京師,孔和倡義兵三千人,殺偽令霍某。趨救甫抵畿內,而京城陷矣。聞莊烈皇帝殉社稷,遂被白鎧,舉白旗,大書于幟上曰:“十六帝德澤在人可卜中興于再造,三百年臣節掃地愿抒下士之孤忠。”與賊血戰數十陣,而賊勢益熾,中原竟不可問,乃帥眾南奔渡淮,謁福王于南邸。以不能迎合馬、阮,故還軍駐桃源,希北窺中原復故土。忿劉澤清懷二志,誓欲誅之。事洩,澤清遣其下賊孔和于桃源之東關。及除命下授前協總兵官,而孔和已死三日矣。②
可見,復興大明、再造中興是劉孔和起兵及南下的動力和目的。“希北窺中原復故土,忿劉澤清懷二志,誓欲誅之”這才是他被劉澤清殺害的根本原因,而“于廣座中有侮澤清” [1]2026只不過是導火索而已。王士禛在《劉孔和王遵坦傳》中寫道:
(劉澤清)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即工,何益國事?況不必工耶?” [5]
劉孔和怒斥劉澤清身為藩鎮,肩負守土重責,卻不發一矢,不遣一卒,沾沾言詩,“何益國事”。正是這“何益國事”的嚴厲斥責,徹底戳中了劉澤清的命門,使其喪失顏面而“大恚”,才派人殺害了劉孔和。劉孔和之被害、劉澤清之“大恚”的根源就在于對“國事”的不同態度上。因此歸咎為劉孔和“于廣座中有侮澤清” [1]2026,既弄錯了事件的責任方,也弄錯了事件的主要原因,顯屬不當。
二
“采薇翁”的含義,也是該篇小說研究的一個重點。對于蒲松齡以“采薇翁”來命名人物及小說,是源于伯夷、叔齊采薇于首陽山,還是取自于《詩經·小雅·采薇》,是分歧的焦點。筆者認為,武王伐紂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是反對武王“父死不葬”“以臣弒君”的不孝不仁;武王已平殷亂之后,伯夷、叔齊采薇于首陽山、義不食周粟,是認為武王“以暴易暴”,而這些都與蒲松齡筆下采薇翁的思想及小說主旨沒有關聯。更何況采薇翁聞知劉孔和聚眾起義、南渡勤王之時,主動“請見”,積極獻策,嚴懲悍將,這又哪是“隱士”之作為呢?因此,蒲松齡以“采薇翁”來作為人物名字及小說題目,當與伯夷、叔齊的故事無關,應該是取自《詩經·小雅·采薇》。但有的學者說:“蒲松齡以《采薇翁》作為這篇小說的題目,除了跟‘部隊征戰’有些關聯,其他方面的意義,就難說了。” [6]279而筆者認為,蒲松齡以《采薇翁》作為小說題目,除了跟《采薇》所反映的與“部隊征戰”有關之外,最為重要的還有三層意思:
一是蒲松齡含蓄地暗示了采薇翁積極從軍的原因。《采薇》詩中的士兵歷盡艱辛戍守邊關,原因在于“靡室靡家,獫狁之故。不遑啟居,獫狁之故” ①,即因為外敵“獫狁”(我國古代的一個北方民族)的入侵,使得人們無家可歸。蒲松齡《采薇翁》開筆就點明故事背景是“明鼎革,干戈蜂起” ②,劉孔和“聚眾數萬”將要南渡勤王,從宏大的視角寫出了當時外敵入侵所造成的烽煙遍地、江山不寧、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接著聚焦于“於陵劉芝生”。“於陵”即長山,濟南府的一個小縣,劉芝生是已故相國之子、邑廩生,毀家紓難,高舉義旗,南渡勤王,眼前的社會景象與《采薇》詩中所描繪的“靡室靡家”“不遑啟居”何其相似。雖然人們對《采薇》的創作時期有宣王、夷王、懿王等不同的看法,但都認為這首詩表現了戍邊將士為抵御外辱而歷盡勤苦的主旨。因此,當采薇翁說出“自號采薇翁”之后,與蒲松齡同時代的那些飽讀詩書的讀者自會想起《采薇》詩中所寫語句,領悟人物字號的微妙含義了。
二是蒲松齡含蓄地表明了采薇翁被迫離去的原因。《采薇》第五章曰:“駕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意思是說,主帥乘坐的戰車那么高大,駕車的四匹公馬雄武強壯。將軍(“君子”)依車而立,士兵們(“小人”)憑借兵車遮蔽矢石。“君子”“小人”在詩中指的是將領和士兵,這是從地位的高低來區分人群。同時,“君子”與“小人”還可從品行的角度來指代那些品行高尚與卑鄙之人。我們認為,蒲松齡在構思本文時則使用了后一種詞義,意指劉孔和長白起義之后,投奔而來的人員既有如采薇翁一樣的君子,也有一些如悍將驕卒那樣的奸邪小人。王士禛《劉孔和王遵坦傳》記載:“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 [5]1588“死士”“輕俠”之語,也寫出了投奔而來的人員成分之復雜。因為采薇翁強調“兵貴紀律”,嚴懲悍將驕卒,危及了諸部領的利益與地位,于是他們對采薇翁惡意中傷,挑撥離間,最后劉孔和被小人所蒙蔽(“小人所腓”),竟然“從其言,謀俟其寢誅之”。
三是蒲松齡含蓄地揭示了全文的主旨及感情基調。《采薇》詩的最后一章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表達了士卒們戍守邊關的無盡鄉愁以及歸來時對家鄉親人茫無所知的傷悲痛苦,復雜的情感,無盡的思緒,一般人實在不好猜解,所以詩人才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深沉感慨。小說《采薇翁》中的人物與作者也有著與之相似的境況:采薇翁身懷絕技、治軍有道,但因損害了驕將悍卒、各位部領的個人利益而遭受誣陷,慘遭殺害,被迫逃走;劉孔和毀家紓難,俠肝義膽,但被心懷私利的眾部領挑撥離間,“信青蠅而誅之”,終致“自壞長城”(但明倫語);而蒲松齡對生前毀家紓難英勇抗清、死后化為“大王”護佑桑梓的鄉邦先賢劉孔和懷有崇敬景仰之情,但為他聽信譖言、痛失賢良及其悲劇命運而感慨萬千,難以言喻。或許唯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最能表達出他們共同的心聲與情感。
三
蒲松齡除了在采薇翁的含義上寄托寓意之外,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是頗具匠心。善于在眾多而復雜的人物關系與矛盾中塑造人物性格,是《采薇翁》鮮明的藝術特色。劉孔和與采薇翁之間、采薇翁與部領之間、部領與劉孔和之間,都有著復雜而微妙的矛盾關系。劉孔和對于采薇翁,從最初的相互交談而“說(悅)之”,觀其滿腹兵器而“神之”,聽其嚴飭之策而“善之”,乃至到后來對采薇翁的“疑之”“圖之”“誅之”,其巨大變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誤信了諸部領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譖言。因此,認真剖析部領的進諂之術,既有助于我們看清其詭辯之道,深入理解劉孔和的性格特征,也有助于我們理解蒲松齡對人性的深刻透視和深沉寓意。
諸部領譖于劉曰:“采薇翁,妖術也。自古名將,止聞以智,不聞以術。浮云、白雀之徒,終致滅亡。今無辜將士,往往自失其首,人情洶懼;將軍與處,亦危道也。不如圖之。”
這段話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說妖術亡軍。首先他們將采薇翁的殺敵神技說成“妖術”。如果單看采薇翁腹藏刀槍劍戟、兵將“首自墮地”,這都是非常人所能為,的確是有些“妖術”。但是,非常人所能為,具有超現實的本領,既可稱之為“妖術”,也可稱之為“仙術”“神術”,現在不也有評論家贊美采薇翁是“仙俠”嗎?部領們故意將采薇翁視為“妖術”,則列入了旁門左道,非君子所齒,其目的在于引導著劉孔和的思維走向一個錯誤的方向。接著談古代名將的治軍之道,并列舉浮云、白雀之徒的事例加以佐證。“好談兵” [5]1588“自喜以知兵稱” ① ,恰好是詩人兼將領劉孔和性格的一大特點。劉孔和在知兵為將上很是自負,他自然知道《孫子兵法》“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之類的道理,既然古人沒有將“術”列為治兵之要,那他自然也就只得默從。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要知道采薇翁嚴懲的是那些“掠取婦女財物”的“悍將驕卒”,是在以嚴治軍,是在為劉孔和剔除害群之馬,又何“妖”之有呢?部領們在此利用劉孔和的自負心理,悄悄地偷換概念,引其入彀。第二層次說“無辜將士”惶恐不安。那些違反軍紀、肆行剽掠者感到惶恐不安,本應是以嚴治軍所要達到的效果,部領們卻冠以“無辜”之名,顛倒黑白,而身為主帥的劉孔和沒有真正了解被懲處將士的死亡原因,因而認為人情洶懼,軍心不穩,隊伍損兵折將,長此下去自己的兵主身份就會名存實亡,于是引發了他對自己軍隊存亡的憂慮。第三層次是說劉孔和身處危境。他與采薇翁“同寢處”,如果采薇翁稍動邪念,劉孔和必定性命難保。這里部領們又利用了劉孔和對自己性命安危的擔憂心理進一步挑撥離間。就這樣,詭計多端、巧舌如簧的部領們層層鋪墊,最后使得劉孔和心紊智亂,竟稀里糊涂地中了他們“不如圖之”的圈套,也為自己此后的悲劇人生埋下了禍根。清代評論家但明倫對此評點道:“兵貴紀律數言,實行軍之要道。悍將驕卒,暗誅之以補糾察所不及,亦足多矣。信青蠅而誅之,毋乃自壞汝長城乎?” [2]1580實在是切中肯綮,不易之論。而另一位清代評論家何守奇則眼力大有不及,認為“諸部領之言雖出于譖,而所言實當,自古未聞以術定天下者也” [2]1580,實在是沒有讀懂蒲翁的良苦用心!
作者雖對劉孔和著墨不多,但善于巧用精當的細節來表現人物,將人物寫得性情活現。劉孔和對于采薇翁,初次交談而“大說(悅)之”,贈以寶刀;觀其滿腹兵器而“神之”,“敬禮甚備”;“時營中號令雖嚴”一語,意在突出劉孔和以嚴治軍,反對禍害百姓,因此,聽到采薇翁進諫嚴飭之道而“善之”,當即實施。這一連串的細節寫出了劉孔和的灑脫耿直、敬賢禮士、從諫如流,與《劉氏家譜》“性倜儻磊落”的記載相符合,表達了作者對劉孔和的景仰之情。在描寫劉孔和后來聽信讒言、圖謀采薇翁一事的表現時,蒲松齡也用筆謹慎,沒有讓劉孔和參與到殺害采薇翁的過程,表現出他的善良仁慈。聽部下說到采薇翁斷頭而能復合、鐵弩射中數人的神奇舉動后,劉孔和“急詣之”,急忙趕赴現場,表現出了他的關切、驚嘆、內疚、悔悟等復雜的情感,但采薇翁“已杳矣”的結尾,頗有“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的空寥孤寂之感,更有著“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深沉慨嘆,含蓄蘊藉,余味無窮。
《采薇翁》是一篇描寫真人傳事的時事短篇,而真人傳事,常常是借虛幻荒誕的傳聞之事來寫真實歷史人物的思想性格,寄寓作者的情感態度。在《采薇翁》中,作者既有對起義隊伍“剽掠婦女”的曲筆實錄,也有對悍將驕卒禍國害民的痛恨憎惡;既有對劉孔和敬賢禮士的崇敬贊頌,也有對其聽信讒言、“自壞長城”的惋惜痛心。可以說,《采薇翁》是蒲松齡對劉孔和起義歷史教訓的一次沉痛總結,也是對其悲劇人生的一曲深沉的挽歌。
參考文獻:
[1][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詳注新評(第三冊)[M].趙伯陶,注評.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2][清]蒲松齡,著.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第三冊)[M].任篤行,輯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3][清]蒲松齡,著.聊齋志異精裝分類全評本·神仙集[M].王詠賦,編.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
[4][清]計六奇,著.明季南略[M].任道斌,魏得良,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4.
[5][清]王士禛.劉孔和王遵坦傳[M]//王士禛全集(第三冊).濟南:齊魯書社,2007.
[6]劉鑫全,周容良,[日]岡井禮子.十年書簡話《聊齋》——探尋鬼狐故事里的中國文化[M].天
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8.
On Story Study and Creative Meaning of
“Caiwei Weng”in the Liaozhai Zhiyi
Nie Tingsheng1" Wang Dong2
(1.Zibo Sixth Middle School,Zibo 255300,China;
2.Zibo Zichuan District Lingzi Town High School,Zibo 255154,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Zhisheng”in“Liaozhai Zhiyi·Caiwei Weng” is Liu Konghe's words and his birth and death year;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Liu Konghe's murder by Liu Zeqing was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state affairs”;Pu Songling named the characters and novels with“Caiwei Weng”,which should be from“Book of Songs·Xiaoya·Cai Wei”;Pu Songling's creative meaning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meaning of Caiwei Weng and the shaping of characters,which expresses a profound summary of Liu Konghe's failure lessons and a deep sigh for his tragic life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Liu Zhisheng;Caiwei Weng;creative meaning
(責任編輯:陳麗華)
收稿日期:2023-11-23
作者簡介:聶廷生(1963- ),男,山東淄博人。淄博第六中學高級教師、山東省語文特級教師,主要從事語文教學與地方文化研究;王東(1984- ),男,山東淄博人。淄博市淄川區嶺子鎮中學一級教師。
文章編號:1002?3712(2024)03?0044?08
①長山太和莊《劉氏家譜》,民國八年(1919)四修印本,后引《劉氏家譜》皆出自該本。
①[清]徐釚撰《本事詩》前集卷六,第32頁,清光緒徐氏自刻邵武徐氏叢書本。
②[清]陳鼎撰《留溪外傳》卷二《忠義部下·劉孔和》,清康熙三十七年自刻本。
①本文所引《詩經·小雅·采薇》詩歌出自高亨注《詩經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后文不再注明。
②原文出自蒲松齡著,朱其鎧主編《全本新注聊齋志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后文不再注明。
①[清]李瑤纂輯《繹史摭遺卷》卷十一《勛戚世祿諸臣列傳》,第八頁,清道光十年活字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