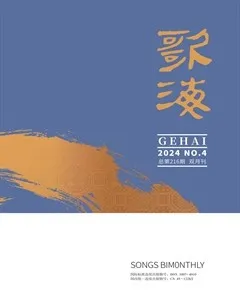符號·儀式·互動·認同:電視劇《繁花》集體記憶的建構
[摘 要]電視劇具有運用視聽語言喚起觀眾集體記憶使觀眾內心情感得到回溯并產生共鳴的文化功能。年代商業劇《繁花》在開播之初就頻頻引起觀眾熱議,引發受眾追憶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風云。《繁花》在新媒介環境下通過選取象征性符號、建立媒介儀式及與觀眾聯動的方式構建集體記憶,以此折射出歷史變革對個體和區域的影響。與此同時該劇集傳播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發揮了建構觀眾的文化認同的功能。
[關鍵詞]集體記憶;《繁花》;象征符號;媒介儀式;文化認同
1925年,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其導師涂爾干所提出的“集體意識”的概念之上,于《記憶的社會框架》一文中首次提出“集體記憶”的概念,稱“集體記憶”是社會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1即使不是親歷者,成員之間通過互動交往便可獲取記憶,所謂的集體記憶不過是某些群體根據自身的利益訴求,對過去的意象進行挑選、重塑,然后為全體成員營造出所謂的“共同記憶”,以此來操縱人的情感和態度2。集體記憶的本質是立足于現代對過去進行重構,年代劇與其本質不謀而合。年代劇是中國電視劇中頗具特色的一種類型,它立足于時代特色、地域文化及傳統道德等,通過特定的事件和人物形象展現一個年代的本質,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觀眾對某個地域某個年代的集體記憶。2023年底陪伴觀眾辭舊迎新的年代商業劇《繁花》,通過選取特定的象征符號,采用與媒體聯手、與受眾互動的方式,喚醒了一代人關于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集體記憶,并在潛移默化中向觀眾傳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價值取向,引發電視觀眾的情感共鳴。
一、象征性符號喚醒集體記憶
可以被反復使用、重現的象征符號是構成集體記憶的關鍵要素之一,1集體記憶的構建需要依賴視聽結合的表意符號系統。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論集體記憶》中表明:當主體在回憶往昔時,事件、一頁書、幾行字等象征性的符號,雖無法還原所有事件中的所有細節,但它可以讓某個場景或形象逐漸清晰,喚醒人內心深處的模糊記憶,象征性符號對構建集體記憶至關重要。2《繁花》是一部講述改革開放初期上海時代變遷的電視劇,創作者通過建構一系列具有象征意義的地理空間、事件及音樂等符號重現了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風云,喚醒電視觀眾的集體記憶,引發觀眾的情感共鳴。
(一)象征性空間:呈現上海地域文化
地理坐標具有客觀實在性,能遠離時空關系的張力作用,是進行文化回憶不可缺少的敘事手段,記憶術較早地使用以地理坐標為“文本”參與記憶建構的媒介方法。3電視劇《繁花》力圖充分還原上海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特征及地域特色。在自然地理空間的塑造上,從黃河路到和平飯店,從弄堂到菜場,《繁花》都致力于再現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都市面貌。“黃河路”是劇集里的重中之重,影片中大量人物的出場都和黃河路上的“至真園”有關。電視劇在海量考據的基礎上復原了當時200米的黃河路,影片中的“至真園”也是借鑒了現實生活中在黃河路開業的苔圣園。除此之外,和平飯店里作為劇中寶總和爺叔叱咤商場“根據地”的72號房間,繁花官微@繁花BlossomsShanghai稱該房間1∶1還原了英國套房的布景陳設,為了完整呈現屋頂上的刺繡,主創團隊選擇封閉屋頂拍攝及搭景當作實景拍,突破狹小空間調度的挑戰。除了城市空間建筑,電視劇《繁花》還重點刻畫了上海的獨特氣候。上海地處東南沿海,受季風的影響會形成梅雨季節,電視劇多次出現下雨天氣,如黃河路路面上坑坑洼洼的水坑,汪小姐在港口時常常遇到下雨,寶總和玲子開股東大會時下雨,寶總送李李回家和李李吃飯等眾多場景中均伴隨著下雨的天氣。導演通過城市建筑及氣候因素向觀眾展現了上海獨特的地理空間。
在人文空間的呈現上,電視劇《繁花》也力圖還原上海的地域特點,其中最鮮明的表現莫過于劇集運用了大量的方言對白,用上海話作為演員表演的主要語言(普通話版本是演員后期配音)。方言是具有鮮明地域文化特征的語言符號,使用方言能更加原汁原味地表現特定地域文化,1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地方則具有一方方言。方言是每個人最習慣、最熟悉的帶有地域文化特點的語言形態,要想表現某塊土地上真實生活著的人和文化,就離不開方言。影視劇對方言的使用不僅使敘事更強有力、更微妙,同時也成為被講述而非被書寫的故事的文化基礎,當普通話被作為主要的語言媒介時,總是會與劇作里的地方性主題存在程度不一的偏離,使用方言才能準確地把握住地方文化的靈魂,因為一種文化需要借助其本土語才能保持鮮活。2電視劇《繁花》用上海方言,真實地再現了上海人說話的特點,如小亭子姑娘說話的軟糯,汪小姐說話時的風風火火,生動再現了上海人說話的腔調,使得劇中人物更加鮮活。
除了語言之外,《繁花》劇組在人物造型、穿搭及物件上也力圖還原上海當年的情景。如汪小姐在初期“一身絲絨套裝加上小皮高跟鞋”的搭配是20世紀90年代女白領的標準職業裝。寶總送汪小姐博士倫牌隱形眼鏡,不同于現在在市場里流通的眾多隱形眼鏡品牌,博士倫在那個時代是隱形眼鏡的代名詞。寶總送給汪小姐的“凱迪拉克”更是20世紀90年代豪車的代表。在道具選擇上,繁花官微從2020年8月5日便在微博上征集上海老物件,并稱會從這些物件中篩選道具,以求真實還原20世紀90年代景象,如在劇集里由杜鵑扮演的雪芝系在身上的紅圍巾,就是由胡歌捐贈的媽媽生前留下的絨線所編織。
(二)象征性事件:刻畫時代符號
記憶建構的核心是對過去事件的敘述,集體記憶的建構必須依賴于群體所共同經歷的歷史事件和普遍認識。《繁花》作為一部反映改革開放時代上海風云的電視劇,它通過再現歷史圖景,喚起人們關于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記憶。
首先,《繁花》通過呈現上海知名地標“東方明珠”的剪影來暗示故事時間。《繁花》第1集中出現了正在建設的東方明珠,第25集呈現了將要建成的明珠塔,而在第30集中東方明珠正式建成,并且電視劇以1994年國慶節在東方明珠燃放煙花的場景落幕。“東方明珠”作為以浦東開放為鮮明標志的上海景觀,它建成和投入使用的日期正好是1994年10月1日。
其次,電視劇采用了“家國同構”的敘事模式,將劇中人物的命運與國家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通過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物故事來展演時代環境。在劇集一開始,導演便借助“寶總”這一人物的獨白交代了故事發生的時代背景:“1992年的上海,霓虹養眼,萬花如海,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南方講話,加快了中國股份制改革的步伐,舉世矚目……”隨著劇集的層層推進,男主人公阿寶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憑借三十元一張的股票認購券從“阿寶”搖身一變為寶總,汪小姐借助國家外匯制度的改革,用沃爾瑪牛仔褲一單一舉成名,范總憑借民族企業復興的浪潮在黃河路上贏得席位……電視劇《繁花》將國家發展、社會變遷與個體的命運緊密聯系起來,通過個體的發展來表現時代的風云。
(三)象征性音樂:彰顯時代坐標
正如王家衛本人所言,音樂是聲音的一部分,也是一種能提示你身處在什么環境什么年代里的提示音,在電影拍攝時他會事先了解環境是怎樣的以及這個地方會有什么樣的聲音,音樂對他來說往往是環境的一部分。1電視劇《繁花》復刻了王家衛的電影美學,將音樂的作用發揮到極致,它通過一系列音樂將觀眾拉回到20世紀90年代的風潮里。在《繁花》30集的容量里,王家衛選取了57首配樂,如《我的未來不是夢》《冬天里的一把火》《光輝歲月》《執迷不悔》《偷心》《再回首》《我是一只小小鳥》《路邊的野花不要采》等。《繁花》采用了許多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或渲染事件氛圍或暗示人物內心、故事走向。這些歌曲緊踩著故事推進的節奏,時代氣息濃厚。
二、媒介儀式營造集體記憶
除去象征符號,《繁花》還借助媒體報道塑造集體事件,進而建構集體記憶。集體儀式是構建集體記憶的關鍵要素。在過去,集體記憶的塑造是以儀式為主導,但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儀式作為權力運行方式的意義被不斷削減和弱化,而在網絡上引起公眾熱議的話題,則會在達到某個閾值時轉化成集體記憶,因此在社交媒體時代構造儀式最直接的方法是制造媒介事件,媒介事件可以充當集體記憶形成的標志。2丹尼爾·戴揚稱“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即是關于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即為“媒介事件”3。在技術發展致使媒介環境及傳播形態產生巨大變化的當下,媒介事件的內涵理應更具有包容性——任何重大的、能引起全社會群體共同關注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都應該被涵蓋在媒介事件的范圍內。4電視劇《繁花》聯合媒體策劃媒介事件,構建媒介儀式引發觀眾對改革開放初期上海的想象,喚醒觀眾的集體記憶。
在影視制作和開播前期,媒體就開始對與《繁花》有關的一系列話題進行集中報道,喚醒觀眾的集體記憶。2020年8月,《繁花》官方媒體開通微博賬號,率先在網絡上進行預熱,在微博上發布尋物啟示,向全社會征集與20世紀90年代上海有關的老物件,并將所尋物進行編號,介紹物件的生產信息及物件背后所隱藏的故事,以此引發受眾關注,營造集體回憶的儀式感。在劇集播出后,媒體進行話題引導,通過熱門話題來制造媒介事件,營造集體關注《繁花》的氛圍。在主流媒體中,《繁花》得到了諸如《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及“人民文娛”等媒體的報道。《光明日報》聚焦于《繁花》拍出了怎樣的上海意境,稱王家衛的《繁花》拍的是20世紀90年代上海的文化表象,是人們“記憶中的上海”,電視劇較小說有大幅度的改編,但城市的氣質被還原得恰到好處。《人民日報》稱該劇制作精良,導演在原作的框架下書寫了新的故事,彰顯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飛速發展、人民奮力向前的時代精神。“人民文娛”稱小說的魅力,來自那1000多個“不響”,來自歷史洪流中蕓蕓眾生的狂歡與悲涼。而王家衛則是在金宇澄留下的“不響”里,大開大合地填充進時代的黃鐘大呂。在平行世界里,它們演繹著各自的響和不響,是彼此呼應的復調,是合二為一的上海。根據媒介間議程設置研究可知,主流媒體相對于另類媒體而言具有更大的議程設置的影響。1改編不是亂編,戲說不是胡說,任何再次創作的作品,都要平衡好自我創作與故事本源,2主流媒體通過大量的報道,讓有關《繁花》的議題進入受眾視野,為電視觀眾設置議程,引導觀眾思考電視劇對原小說做出了怎樣的改編及改革開放之初上海的真實模樣等問題,從而喚醒觀眾的集體記憶。
除此之外,電視劇《繁花》還通過社交媒體平臺持續推出各種話題喚醒觀眾集體記憶。在社交媒體時代,信息傳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輿論陣地轉向微博、微信、抖音等社交媒體平臺,3社交媒體擁有強大的傳播功能,能夠實現信息的高效傳播,《繁花》聯手社會媒體,擴大內容傳播范圍。根據繁花官微2024年1月13日發布的收官戰報可知,《繁花》在播出前后微博熱搜熱榜總計上榜2922+次、相關話題閱讀量破102.84億,抖音霸榜熱點總計949次,主話題熱榜量突破103億。總之,媒體通過熱門話題制造媒介事件,助力電視劇《繁花》構建集體記憶。
三、線上線下互動呈現集體記憶
哈布瓦赫認為社會交往是保證集體記憶傳承的條件,“人們通常是在社會之中獲得他們的記憶的,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1,沒有參與就無法建構出真正的記憶,集體記憶的實踐離不開個人實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繁花》之所以能夠喚起廣大受眾的群體記憶,在于受眾自主地參與到對共同回憶的理解、加工和表達之中,從而使得電視劇對集體記憶的建構從劇中延續到劇外,使得“想象共同體”得以建構。
在劇集播出前繁花官微就登報尋上海舊物,劇集播出時舉辦繁花劇評、繁花留影二創大賽等活動,調動受眾積極性,號召大家共同參與到這場構建記憶的狂歡中。與此同時,受眾與受眾之間還組建了對話交流空間,讓電視劇對集體記憶的建構從劇中轉到劇外。《繁花》熱播期間,受眾對《繁花》自發進行二次創作、模仿等行為使得集體記憶在濃厚的氛圍中不斷加強。如在B站等社交媒體平臺上,許多博主分享自己關于20世紀90年代的記憶,在美妝領域,抖音、小紅書等平臺出現了大量有關《繁花》的仿妝,在情感領域出現了對《繁花》人物的情感解析,在財經領域有“《繁花》商戰大師班”,跟著寶總爺叔學炒股,在美食領域大量博主復刻劇中美食如排骨年糕等,在旅游領域有跟著《繁花》在上海citywalk,甚至出現大批的游客到上海黃河路打卡,入住寶總的和平飯店等。受眾的這些自發行為,讓交流空間從官方傳到民間,從線上延伸到線下,這些均為形塑集體記憶提供了新的“養料”,《繁花》和受眾共同形成了一部又一部《繁花》番外篇。
四、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
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體記憶是指特定群體立足現在和未來群體安全和發展的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質載體和交往形式對于共同歷史經歷的精神重構,集體記憶是具有現實功能的,其主要功能就是實現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而所謂的文化認同是指人們對于本民族文化模式的歸屬感,它是人們精神活動的根本追求,在靈魂深處形成精神支撐,賦予生命高層次的意義結構。2中國價值是中華文化認同的核心,中華優秀傳統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價值的歷史形態和現實形態,3兩者是當代中國普遍的價值遵循。電視劇《繁花》以象征性符號為表征,通過媒介事件聯動受眾,整合建構出改革開放時段上海風云變幻的集體記憶并將中華文化與具有感染力的影像畫面結合,以一種契合受眾心理的方式傳遞中華文化的價值,進而喚醒受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
(一)根植傳統文化,宣傳中國優秀傳統價值觀
電視劇《繁花》在價值認同方面,緊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觀,它通過具體人物的言行傳承和弘揚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國文化是倫理本位的文化,1何謂倫理本位?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指出:“人一生下來,便有與他相關系之人(父母、兄弟等)且將始終在與人相關系中而生活(不能離社會),此種種關系皆是倫理,倫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可無限向外圍擴展。而所謂的倫理本位是指以情誼為核心的倫理關系在人們各方面的社會關系中起主導和決定作用。”2《繁花》以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大眾生活,通過展現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的情節,彰顯了和諧的人倫情感,這種倫理本位的敘述能讓受眾在感動與敬佩的情感互動中實現對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認同。
倫理情感以親情、愛情、友情為本,3電視劇《繁花》對三者進行闡釋,凸顯了中國傳統中和諧的人倫情感。父子之間的倫理關系系統結構是構成家庭倫理的核心之一,正如《禮記》中所記載的“為人子,立于孝;為人父,止于慈”,傳統父子倫理的基本內容就是“父慈子孝”4。《繁花》雖沒有著重刻畫家庭環境里的“父與子”的感情,但刻畫了“阿寶”與“爺叔”這對不是父子勝似父子的師徒情。在阿寶變成寶總的路上,爺叔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教阿寶如何打造自己,如何炒股票做外貿,在阿寶需要時調動自己的人脈解救阿寶,全心全意為阿寶考慮,為阿寶的事業“兜底”。阿寶也扮演著爺叔“兒子”的角色,陪爺叔一家跨年,逢年過節給老人包紅包等。
除了對親情的刻畫,朋友情誼也在電視劇中得到溫情呈現。無論是在東京還是在上海,玲子對菱紅都照顧有加,陶陶無條件拿家底支持阿寶創業,阿寶在陶陶受到傷害時挺身而出說他的意見就是我的意見,汪小姐與阿寶的“革命友情”,潘總和小江西在李李受困時的支持,范總在汪小姐落魄時對汪小姐的支持等,這些人與人之間的“義”都彰顯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講究的“道義”。
在對愛情的刻畫上,玲子尋求的是和阿寶組建婚姻家庭,汪小姐要的是和寶總“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而李李和寶總之間則是“發乎情止于禮”的克制。《繁花》沒有加入大量復雜繁瑣的情感糾結,也沒有設置圓滿的結局,而是以一種含蓄朦朧的方式道出了“人生若只如初見”的惋惜,給觀眾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間。正如金宇澄在《繁花》小說中所描寫的:“男女之事,源自天時地利。差一分一厘,就是空門。”
(二)緊扣時代脈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電視劇《繁花》將著力點集中在平凡人物身上,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觀眾的情感認知、思想感情緊密結合,從而引導觀眾更容易接受和內化其所傳遞的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代表,甚至決定著其文化性質和發展方向,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影視藝術創作始終遵循以思想為引導、以藝術為標準的創作原則,利用影視藝術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實質就是把二十四字價值觀隱藏在作品的人物、故事和視聽語言之中,讓觀眾自行理解和提煉這些蘊藏其中的觀念,從而調動觀眾更深層次的情感共鳴和審美體驗,提高其踐行的自覺性。2
《繁花》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著影像敘事。在國家層面上,建構了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形象。《繁花》以改革開放為敘事背景,書寫在國家大政策背景下,各層次市民抓住改革開放的機遇,實現個人的成功,營造出“國家富強民眾才能幸福”的整體氛圍。在社會層面上,影像敘事承載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價值觀追求,強總和李李因為違反了國家法律法規,最終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外貿大樓里的金科長、汪小姐對待來外貿大樓辦事的人始終秉持公平原則,做事光明磊落。在個人層面上,《繁花》全篇始終貫穿著每一個公民自覺踐行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劇中的男女主人公寶總、汪小姐、李李及玲子,他們在事業中均堅持誠信敬業原則。總之,電視劇《繁花》以核心價值觀引導敘事,影片從不同人物、不同視角展現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應有內涵,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體化形象化,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觀眾,進而真正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要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生活情景和社會氛圍,使核心價值觀的影響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在”3的要求。
結語
集體記憶的形成分成兩種機制:第一種是自上而下的,即社會精英通過各種途徑對記憶進行解釋、包裝和重塑,然后傳遞給普通大眾,如政府通過主流媒體報道、組織大型的紀念活動等方式發出官方聲音主導記憶的建構;第二種是自下而上的,即國家以下層面的主體通過自發敘事來構建“非官方”記憶,在集體記憶的建構中發揮著自身的主動性。電視劇《繁花》正是通過上下聯動的方式營造集體記憶構建的場域,引導電視觀眾融入到集體記憶之中,最終構建出觀眾對20世紀90年代上海歷史的集體記憶并在這個過程中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要“承擔記錄新時代、書寫新時代、謳歌新時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時代課題,從當代中國的偉大創造中發現創作的主題、捕捉創新的靈感,深刻反映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為時代立傳、為時代明德”1。電視劇《繁花》通過結合當下現實生活對嚴肅文學進行改編獲得成功的案例,可給未來中國影視作品更好地講好“中國故事”提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