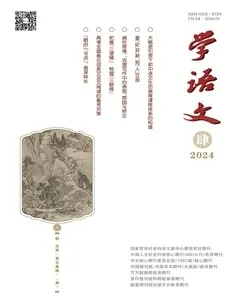《背影》的“四維”之美
摘要:《背影》是一篇抒情真切的寫人敘事散文,文章以質樸的文字記敘了作者回徐州奔喪,與父親浦口車站分別的事,通過聚焦父親的“背影”,把父愛寫得質樸、含蓄、深沉。作者在有層次的敘事中,又采用靈動的描寫,兼以樸實飽滿的抒情,再輔之以平實、典雅和干凈的語言,使全文呈現出“四維”之美。
關鍵詞:《背影》;敘事;描寫;抒情;語言
宗白華說:“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中。”[1]朱自清的《背影》就是以和諧的形式寫出至深的父愛,跨越時空,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背影》是采用什么樣和諧的形式呢?下面我將從敘事藝術、描寫藝術、抒情藝術和語言藝術四個維度來談其之美。
一、敘事藝術之美
《背影》涉及的事件很多,而且都是平常的生活小事,但經作者藝術化的處理,就線索清晰,詳略得當,鋪墊充分,側重點突出。具體如下:
首先是敘事線索的形象化之美。全文用“背影”作為線索串聯全篇。從標題開始,就在顯豁的位置提及“背影”,然后用“背影”串聯起四個片段,分別是:惦記背影→刻畫背影→惜別背影→回憶背影。有概述,有詳寫;有實寫,有虛寫。一線串珠,使文章結構緊湊,條理清晰。
最精彩之筆是“背影”不是作為一個抽象的詞語存在著的。作者通過外貌描寫和動作描寫賦予“背影”以具體的形象。其中外貌描寫的句子:“肥胖的,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其中動作描寫的句子:“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本來“背影”是一個抽象而寬泛的詞,作者通過以上外貌和動作的描寫,賦予這個詞以最動情而具體的瞬間形象,從此成了一幅經典圖像。在文中“背影”是作者感激父愛的切入點,是父親關愛兒子的象征點,是父子之情的交匯點,也是作者不能忘記父愛的觸發點。這條線索不僅形象,而且動情,是事實與藝術的融合,簡約而又富有深刻的象征意義。
其次是疊加與鋪墊的交織之美。通過事件的疊加,詳略的鋪排,推動情感一步一步走向高潮,讓后文自己的流淚趨于自然。作者在主體事件之前先寫祖母去世了,父親的差使交卸了,父親貧窮得要靠變賣典質來還虧空,要靠借錢來辦祖母的喪事……都是為寫車站與父親告別的傷感作鋪墊。父親穿鐵道、爬月臺的背影只是“我”流淚的觸發點。只有在前文充分鋪墊的基礎上,目睹了父親在艱難的處境中還如此細微地關心“我”,經這樣鋪墊后車站離別的流淚才合情合理,自然而然。葉圣陶在《讀〈背影〉》中曾說:“這篇文章把父親的背影作為主腦。……那么,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看見那一個背影……先要敘明父親和作者回到南京,父親親自送作者到火車上,就是為此。”[2]主體事件的出現,作者先進行鋪墊,讓人物的感情得到充分的醞釀,然后用自己的流淚襯托父親的背影給自己的感動。
再次是延宕與跳躍的節奏之美。《背影》在敘事上詳寫的是車站送別時父親買橘子的背影,在此之前,在敘事節奏上作者充分采用延宕的手法。如在主體事件“車站送別”之前,先寫“祖母去世”“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父親變賣典質還虧空”“借錢辦祖母的喪事”“我和父親同行到南京”“到南京有朋友約去游逛”“父親再三囑咐茶房”“終于決定還是自己送我”等等。這些零零碎碎的日常生活小事,作者是一筆一畫,慢慢交代,正因為這些點點滴滴事件交代時的延宕,把父愛給充分而真實地凸顯出來,讓讀者在作者質樸親切的文字的流動中不斷受到感動,為后文“我”看到父親買橘子時的背影因而流淚作了蓄勢,在情節設計上可謂水到渠成,這就是延宕的妙處。
父親攀爬月臺去買橘子和父親抱著朱紅的橘子回來,這兩個片段之間是“跳躍”的,省去了父親選購橘子、討價還價等事,而用“我流淚、拭淚”來巧妙過渡,既用情感來烘托父親的背影,又在敘事上巧妙跳躍,詳略有致,可謂一舉兩得,敘事上巧妙至極。
二、描寫藝術之美
為了把父愛展現得更為飽滿,作者還采用了一些獨到的描寫。
首先是描寫視角獨特的詩意美。本文通過聚焦父親的背影來贊美父愛。在車站送別之前父子倆的感情并不融洽,但當父親轉身離去時的“背影”卻為父子倆之間提供了情感調和的契機。過去,由于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父親在兒子面前總是表現出絕對的權力和威嚴,兒子與父親有了隔膜。但當父親轉過身去,把“背影”留給兒子時,因為即將離別,將與父親有了空間上的距離,所以父親所有缺點都暫時消失了,剩下的只是無法斬斷的父子之情。當父親轉身去買橘子時,或轉身混入來來往往的人流中時,之前覺得自己比父親“聰明”很多的兒子此時也不想再去尋找那種內心的優勢感。此時,父子之情又回到了父子關系的人性位置上,回到父子之間的血脈真情上來。正由于這種血脈之情的回歸,父親對親情的珍惜,兒子就容易被父親的關愛所感動,這是人之常情,也是距離產生美。可見,選擇“背影”這個視角來寫父親,角度獨特而又巧妙。
其次是描寫對象切換的靈動美。本文把描寫的對象在“我”和父親之間不斷的切換。如到徐州時,看到滿院狼藉,“我”流淚了,接著寫父親對我的安慰。在父愛的框架下把描寫的對象由“我”很自然地切換到父親,簡潔而又自然。又如寫父親攀爬月臺,接著用“我”流淚、拭淚來巧妙過渡,隨后又寫父親抱著橘子往回走。把描寫的對象在“父親—我—父親”之間自然地切換,構成一種“橫云斷山”之美。又如:“我望著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來看見我。”描寫的對象在“我—他—我”之間切換,語言簡潔,靈動而又充滿深情。諸如此類的句子有很多,使行文在描寫對象的不斷切換中跌宕起伏。描寫對象除了在人與人之間切換,還在外在客觀世界與內在主觀世界之間切換。如:“父親與腳夫們談價錢,但我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又如:“父親囑托茶房好好照應我,但我心里暗笑他的迂。”在這些客觀與主觀的切換中,事與情交融,讓行文流暢而又情趣盎然。
再次是繁筆與簡筆結合的交錯美。繁寫父親車站買橘子的背影。在此過程中,濃墨重彩,添加了外貌描寫和動作描寫。把父親的背影定格為一幅圖畫,讓讀者親切可感。繁寫父親對“我”關愛的言和行。如在徐州時,父親安慰“我”不必難過,天無絕人之路。這是怕兒子過分難過,強撐著自己,安慰兒子。又如南京車站送別,本來是讓茶房伴“我”同去,但在再三躊躇之后,最終決定親自送“我”。包括后來在車站,父親忙著與腳夫講價錢,幫“我”挑座位,囑咐“我”夜里警醒些……這些繁筆都體現出父愛的細膩。然而,起初“我”對父愛是抗拒的,不接受的。這既有時代的因素,又有父親個人私生活上過錯的因素[3]。但對這些,作者沒有過多交代,只是簡單一提:“總覺得他說話不大漂亮”“我心里暗笑他的迂”。簡單的話語中藏著很多難以啟齒的內容,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下,自己親生父親的形象是不能過多揭露的。像這樣,繁筆與簡筆相結合,讓行文詳略有致,中心突出。
三、抒情藝術之美
《背影》所贊頌的父愛是含蓄的、深沉的、細微的,作者通過很多細節的處理來達到這樣的表達效果。
首先是情感表露的自然與巧妙。表露情感收束一件事,同時又能巧妙地過渡到另外一件事。這樣做的好處是什么呢?既能構成敘事上的隔斷,避免平鋪直敘,又能在敘事的基礎上讓“我”對父親的情感不斷沉淀。如:“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此時作者“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至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此句的流淚既是對“我”到徐州見到父親、想起過世的祖母之事的收束,又引出下文父親對“我”的安慰和關心。讓行文形成“事—情—事”的模式,又是一種“橫云斷山”之法。又如在車站,父親非得親自給“我”買橘子,當“我”看到父親艱難攀爬月臺時,文中寫到:“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流下來。”這句話既轉換了描寫對象,由寫父親轉到寫“我”的表現,又讓敘事在此處巧妙地跳躍,跳躍到父親抱著朱紅的橘子往回走。這樣,既節約了敘事的篇幅,又突出了父愛的深沉和不易,幾年后,當時父親買橘的場景“我”仍歷歷在目。可見,巧用抒情句,能增加敘事的層次美和靈動感。
其次是情感呈現的樸實與飽滿。祖母去世,父親的差使交卸了,父親的生活境況江河日下,此時他的內心應該傷心至極。但當父親看到簌簌流淚的“我”時,又強掩藏住自己的悲傷并安慰“我”:“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短短的一句安慰的話里包含著多少深沉的父愛。本來父親想在南京找工作,事忙,不送“我”了,讓茶房陪“我”同去車站,躊躇之后還是決定自己送“我”。在這行文頓挫之間,把父親內心的矛盾糾結書寫得淋漓盡致。年齡再大的兒子,在父親的眼里都還是個孩子,只有親自送上車才放心。到了車站,父親忙著“照看行李“”講價錢“”揀座位”“囑咐我”“買橘子”,買完橘子還在車廂里,在兒子身邊站了一會兒,這是牽掛,是不舍,是偉大的父愛。作者采用小中見大的手法,把偉大的父愛通過細小的言行來呈現,寫得很落地,很樸素,很飽滿。李廣田說:“《背影》之所以能夠歷久傳誦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而只是憑了它的老實,憑了其中所表達的真情。”[4]細想想,在過往的日子里,我們的父親對我們或多或少都有過這樣關愛的言和行,只不過,當初我們沒有醒覺,在本篇中,一經朱自清先生點撥,就勾起我們對往事的回憶,產生了情感上的強烈共鳴。讀者和作者之間有了感情的共鳴,就能產生恒久的感動。
再次是情感抒發的典型與集中。父親少年時就出外闖蕩,做了不少大事。他自己沒有想到,到老了卻如此頹唐。當看到父親在徐州的住處滿院狼藉,又想起剛去世的祖母,“我”忍不住的流淚。此時此刻,“我”在為父親和家庭境遇的江河日下而憂傷。撫今追昔,天上人間。從過去的輝煌燦爛,到如今的頹唐衰敗;從過去的待“我”漸漸不同往日,到現在老邁時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父親,是許許多多小資產階級左翼人群的典型代表,他的人生浮沉,也是小資產階級左翼人群共同的時代遭遇。他的情感表現形式具有他所在群體的共同特質,具有典型性。
本文中的父愛,因祖母去世、父親差使交卸、“我”奔喪回家和奔喪完后要返回北京讀書這四種情境的共同作用而讓父愛的呈現尤為集中。或許是父親已到了老年,又身處在逆境中,在外工作處處不順利,巨大的外在壓力讓父親把情感和精力投向了家庭,投向了親人,更加重視家庭、親情。此次,回家奔喪,父親對“我”的愛細微而深切。這體現在父親給“我”訂做了紫毛大衣,給“我”揀座位,親自爬月臺給“我”買了橘子等等。作者在有限的字里行間,利用情境的綜合作用,把父愛進行了集中的呈現。
四、語言藝術之美
《背影》的語言平實,飽含深情,看似平淡,其實淡而不淺,淡而有味。正如蘇軾所言:“質而實綺,癯而實腴。”[5]
首先是語言的平實之美。如“不要緊,他們去不好”“我買幾個橘子去”“進去吧,里邊沒人。”自己對兒子的愛必須自己親自表達,才能表達自己作為父親的心情,別人是不能代替的。臨別,不給兒子買幾個橘子,就感覺有件事沒有完成,心里老是感覺不踏實。出門在外,叮囑兒子看管好自己的東西,避免不必要的損失。這些語句樸素,簡凈,又溫暖。在短短的字里行間,把父愛的深沉和細膩充分又自然地呈現出來。
其次是語言的典雅之美。《背影》的語言在平實中還多了份古文的典雅。如:“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文白夾雜,言簡意賅。使全文的語言在平實中增添了幾分典雅的風韻。又如最后一節引用父親來信的原文:“我身體平安,唯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投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信中有“唯”“舉箸”“諸多”和“大去之期”等文言詞語,語言具有個性化,符合父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身份,又豐富了本文的語言形式。這些話語為后文自己的再次流淚張本。
再次是語言的干凈之美。葉圣陶在《文章例話》中說:“這篇文章通體干凈,沒有多余的字眼。”如:“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先說“祖母的情況”,再說“父親的情況”,然后用一個“禍不單行”的詞語來概括。先列舉理由,后提出自己的觀點,語言干凈,思路清晰,言簡意明。再如:“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在父親心中,兒子再大也是孩子,時時不忘叮囑一句:不要亂走,防止丟東西,防止我找不到你……還有:“我走了,到那邊來信。”只說到那邊來信,省去了你的來信要向我報一聲平安,免得我為你擔心等內容。雖然文中沒有交代,但讀者都能理解,因為作者和我們的文化背景相同。既然大家都能理解,那么,作者就不需要交代得過于詳細,留給讀者一些審美想象的空間會更美。這樣,就形成了本文語言的干凈之美。
總之,《背影》這篇經典散文,正是通過敘事、描寫、抒情和語言這四個維度的完美融合,展現出“感人至深的力量”[6],可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參考文獻:
[1]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36.
[2]葉圣陶.文章例話[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177-178.
[3]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123.
[4]李廣田.李廣田全集:第5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86.
[5]張志烈,等.蘇軾全集校注[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763-782.
[6]吳晗.吳晗文集:第3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305.
(作者:許良兵,安徽省合肥市五十中學東校教師)
[責編:張應中;校對:尹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