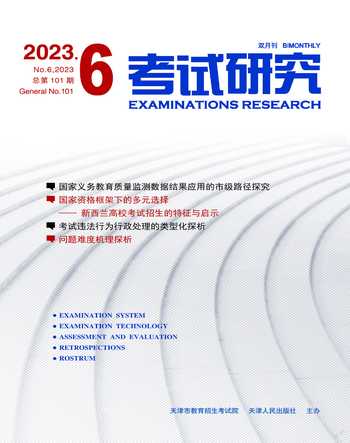考試違法行為行政處理的類型化探析
李祥 孟月桐
[摘要]考試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理形式多樣。司法實務的認定存在不統一、不準確的問題,學術研究亦存在明顯短板。明確其法律屬性是準確適用法律、推進依法治考、維護法治統一、保障考生權利的現實需要。取消成績因適用的情形不同分別屬于行政處罰和行政確認;撤銷考試授益性處理是行政行為的自我糾正;限制報考、延遲畢業屬于行政處罰中的行為罰;終止參加考試應視為“保安處分”;取消本次考試資格分別具有行政許可的撤銷和保安處分的屬性;考試失信約束懲戒措施不是行政處罰,宜定義為一種新型行政監管方式。
[關鍵詞]取消成績;限制報考;終止參加考試;取消考試資格;考試失信約束懲戒
[中圖分類號]G424.7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654(2023)06—044—011
中國是一個考試大國,目前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實施的各類考試多達200余種[1],每年考生多達上億人[2]。其中僅“國家考試”的種類就近20種,每年參加國家考試的人數超過4000萬[3]。有學者統計,我國與考試有關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等規范性文件多達3000余部[4]。考試執法涉及面廣、涉及人數眾多,是我國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和不容忽視的領域。對于考試中的違法違規行為,現行法律法規體系設置了復雜多元的處理方式(以下簡稱“考試違規處理”)。行政行為的模式,即行政行為的形式、范疇、類型、屬性,是指某類行政行為典型特征的理論化和固定化[5]。行政行為的類型化,即行政行為的模式化,就是將紛繁復雜的行政行為抽象為若干典型的行政行為類型,從而為法律對行政行為的控制及司法審查對行政行為的監督提供明確的形式連結點。考試違規處理大部分不是典型的行政行為類型,而且屬性復雜,從外在形式上難以對其屬性作出直接、準確的判斷。在司法實務中,法律屬性判斷的不準確可能影響審判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準確適用;在執法實踐中,克減程序、侵犯考生權利的現象亦時有發生。學界雖然對此也展開了相關探討,但是研究的視野狹窄,觀點片面,結論莫衷一是。本文以“國家考試”為藍本,在全面厘清考試違規處理的基礎上,對其屬性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對其中的焦點性、爭議性、癥結性問題予以回答,以期回應理論界的爭議、廓清實務界的迷霧,為更好地推進法律統一適用和依法治考進程提供參考。
一、理論研究和司法實務認定的現狀
(一)理論研究的現狀
考試違規處理屬性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和焦點之一,近年來產生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有學者對國家教育考試中違規行為行政處理的屬性進行了全面研究,認為取消考試資格、取消各科成績、停考這三類屬于行政處罰;取消報考資格、取消錄取資格、取消入學資格屬于行政許可的撤銷或拒絕;宣布作弊科目成績無效、取消學籍、拒絕授予學位、宣布學歷學位證書無效屬于行政確認以及行政確認的拒絕和撤銷[6]。有學者認為,國家教育考試中對考生實施的行政處罰有3種,分別是:取消相關考試資格、取消相關考試成績、停止參加相關國家教育考試[7]。有學者認為“宣布國家教育考試成績無效”具有懲戒性、處分性、不利性的特征,應當屬于行政處罰[8]。還有學者認為,取消成績根據其適用的情形不同,分別屬于行政確認和推定、行政處罰,綜合來看,應當定性為“不利行政處理”[9]。
現有的研究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研究的視野過窄,不夠系統全面。我國各類考試多達200余種,涉及到的考試違規處理方式多達幾十種,而當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考試領域,對“取消成績”“終止參加考試”等少數幾類較為常見、適用較廣的行政行為進行研究,對于其他考試中其他行政處理的研究鮮有涉足。二是對某一類處理考量不夠全面和細致。對某一類行政處理進行研究時沒有充分和全面地考察行政處理所適用的全部情形,而只是討論了其中的部分情形,“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存在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問題,進而導致研究結論陷入片面。如針對取消考試資格這類行為,研究者只是考慮到了它的制裁性和懲戒性,沒有結合該處理所適用的不同情形分別探討其屬性,從而忽視了它所具有的行政確認、糾正違法等其他屬性。三是對個別行政處理屬性的判斷不夠準確和周延。如將“取消錄取資格、取消入學資格”視為行政許可的撤銷,但是院校錄取的行為是否為行政許可有待商榷。
(二)司法實務認定的現狀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案件名稱”欄目輸入關鍵詞“考試”,“案由”欄目選擇“行政案由”進行檢索,共顯示264份判決書,分別涉及國家教育考試、公務員考試、注冊會計師考試、醫師資格考試等各類國家考試,其中絕大多數的訴訟都需要對取消成績、停考、終身禁考等考試違規處理進行定性。逐一審視這些判決書可以看出,當前司法實務中對考試違規處理屬性的認定存在如下問題:
一是認定不統一。當前司法實務中認定存在的最為突出的問題就是對同類處理認定不統一,其中以“取消成績”最為明顯。如“李某不服江蘇省教育委員會考試作弊處罰案”中,法院認為考試違規處理屬于行政處罰[8]。而在“劉某不服武漢某大學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案”中,法院認為宣布成績無效的行為屬于行政處理而非行政處罰[9]。在“馬某某訴內蒙古自治區教育招生考試中心”案中,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當次考試各階段、各科成績無效”不屬于行政處罰,而是教育行政管理行為[10]。在“劉某訴河北省人事考試局”一案中,原告對被告依雷同卷檢測報告作出的“取消考試成績”的處理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將案由確定為“教育行政管理”[11]。
二是認定不細致。如上述“劉某不服武漢某大學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案”,法院認為宣布成績無效的行為屬于“行政處理”;“吳志剛訴河南省人事考試中心案”一案中,針對“2年內不得參加各類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的處理,法院將案由確定為“其他行政行為”[12]。但是究竟屬于哪一類“行政處理”、哪一種行政行為,沒有作出具體認定,不能滿足審判實踐的需求。
三是認定不準確。例如“馬某某訴內蒙古自治區教育招生考試中心”案中,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當次考試各階段、各科成績無效,不屬于《行政處罰法》第8條規定的行政處罰種類,不屬于行政處罰,而是教育行政管理行為。”而在“羅某訴廣東省人社廳”一案中,廣東省人社廳認為,“對考生作出的5年內不得報考公務員的處理,是對相對人的考試資格在一定時間內予以限制的一種處理決定,不應理解為一種行政處罰”[13]。上述案件判決書反映出,審判機關并沒有抓住行政處罰的內涵和本質,進而得出了有失準確的判斷。“王某訴咸寧市教育招生考試院”[14]一案中,判決書顯示:原告因攜帶考試資料進入考場而被考試執法機關作出“當次考試成績無效”的處理。后原告提出陳述申辯,被告行政機關在原行政處理基礎上追加了“記入誠信檔案”的處理。本案中由于行政機關未能準確認識到“記入誠信檔案”是一種對當事人可能產生不利影響的行政處理,故而在當事人提出陳述申辯后增加了這一處理,侵犯了考生合法權益。在“陳某訴陜西省人事考試中心”和“王某訴陜西省人事考試中心”兩起案件中,原告對被告作出的考試科目成績“按零分處理”的行政行為不服而提起行政訴訟,法院認為“按零分處理”不屬于《行政訴訟法》第12條所規定的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15-16]。正是由于法院對“按零分處理”的屬性認定不準確從而致使原告訴權無法得到保障。
二、研究對象的選定及其復雜性表現
(一)研究對象的選定
考試違規處理本身不是一個確定的法律概念,也沒有清晰的范疇。為了確定研究對象,首先需要準確、全面地厘清其具體范圍。我國考試類多面廣,范圍不容易把握。其中“國家考試”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其違規處理方式也最具有代表性,而且也幾乎涵蓋了當前考試執法實踐中全部的行政處理方式。因此本文選擇“國家考試”為研究的藍本。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組織考試作弊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9〕13號),“國家考試”是指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所規定的考試。經梳理,目前我國共有19部法律規定了18種不同的國家考試,包括教育考試4種、資格類考試13種,以及國家公務員招錄考試①。進而,找到與18種國家考試相關的違規處理的規范性文件。除了國家考試的19部法律之外,其他規范性文件幾乎全部為國家考試主管部門制定的部門規章②。“行政處理”是指行政主體依法處理涉及相對人特定權利義務事項的行政行為,體現為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命令、行政確認、行政強制等一系列行政措施和決定。根據行政處理的定義,逐一對上述規范性文件進行梳理排查。在此基礎上剔除“內部行政行為”——建立在具有內部行政管理關系基礎上的行政行為,如政府機關對公務員的處理、高校對老師和學生的處理等,包括:開除(公職)、解聘、開除學籍、撤銷考點資格、停止參加考試工作。經過篩選和梳理,本文所界定的考試違法行為行政處理的范圍為:警告、罰款、行政拘留、沒收違法所得、取消成績、宣布成績無效、按零分處理、停考、取消報考資格、限制報考、終身禁考、延遲畢業、取消本次考試資格、取消本次報考資格、終止錄用程序、終止繼續參加考試、責令離開考場、取消錄取資格或學籍、取消錄用、宣布證書無效、責令收回證書或者予以沒收、撤銷職業資格、記入考試誠信檔案、考試失信約束懲戒措施。在這些處理方式中,警告、罰款、行政拘留、沒收違法所得屬于典型的行政處罰,本文不再探討。另需交代兩個問題,一是為了便于開展研究,本文將作用機理類似、具有同種處理效果,或者具有同種屬性的行政處理歸為一類進行分析;二是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采用的是“實質主義”立場而不是“形式主義”立場。
(二)考試行政處理的復雜性表現
一是“非典型性”“非模式化”。考試違規處理絕大多數都是由中央一級的考試主管部門所制定的部門規章針對不同的考試違規違紀行為而“量身定做”,這些處理為考試行政執法所特有,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其中除了警告、罰款等少數屬于典型的行政處罰外,其他絕大多數都不具有典型性。我國行政法的三部主要法律《行政處罰法》《行政強制法》《行政許可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的相關司法解釋、意見均沒有對這些處理作出明確的列舉。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印發〈關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暫行規定〉通知》(以下簡稱“《暫行規定》”)列舉了20種二級案由、140種三級案由,也均未將其囊括其中。這些行政處理無法從現有的成文法中找到其坐標,因此需要學界進行觀察、分析、提煉后加以歸納和認定。
二是屬性的多重性。同一種處理在不同的條件中、不同的情形下分別具有不同的屬性。考試違法違規行為可以分為考試違規違紀和考試作弊行為,同一種行政處理適用于不同的違法違規行為時分別具有不同的屬性。如“取消成績”這類處理,當適用于考試違紀和考試作弊時,分別具有不同的屬性;適用于取消作弊科目的成績和取消非作弊科目的成績時,也分別具有不同的屬性。“取消考試資格”適用于考試違規和考試作弊時,也分別具有不同的屬性。“限制報考”“終身禁考”這類處理,當作為一種對考試違規違紀的處理方式時,具有明顯的懲戒性和制裁性,屬于行政處罰;而當作為一種信用監管方式時,又不屬于行政處罰。因此在定性過程中需要結合其所適用的情景、情形分門別類地展開探討,而不宜一概而論。
三是表達方式的多元化。不同的行政處理名稱或法律表述不同,但是內涵和本質上可能屬于同一類行政處理。如取消成績在不同的規范性文件中有時也表述為“記為零分”“按零分處理”“宣布成績無效”等,其實際效果和法律屬性是一致的。如取消考試資格在公務員考試的違法違規處理中表述為“終止錄用程序”,在事業單位招聘考試中表述為“終止聘用程序”,實則是同一類處理。又如取消學籍、取消錄用、宣布證書無效、撤銷職業資格、責令收回證書等一系列處理,從外在形式上看分別屬于不同的行政處理,但實際上其本質相同,是同一類處理。
四是身份的迷惑性。有的行政處理以“改頭換面”“改名換姓”的方式冠其他處理之名行處罰之實,或以“瞞天過海”的方式從行政處罰向一般性行政行為“逃逸”。有些行政處理從外在表征上看符合行政處罰或行政強制措施的要素和特征,但是實則不屬于這一類行政行為。如取消考試資格、終止參加考試、責令離開考場等具有行政處罰的外在特征,撤銷學位、撤銷職業資格、取消學籍也具有行政處罰的外在特征,公務員考試錄用中“不得確定為擬錄用人員”的處理也符合“限制從業”處罰的外在特征,但究其本質都不屬于行政處罰。盡管《行政處罰法》已經對行政處罰作出了定義并且列舉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和形式,然而僅通過其定義和形式尚不足以對制裁性作出判斷,還需要結合行政處罰的內涵、特征、本質、學說理論,從行政行為的立法本意、實施目的等多個角度進行判斷,透過現象看本質。
三、研究的重要性和現實意義
(一)統一司法尺度、準確適用法律的現實需要
近年來司法實務中出現越來越多的“涉考類”行政訴訟案件,面對這類案件法院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判斷行政行為的屬性。作為行政法重要原則的“平等原則”要求,相同的事件應當得到相同處理,不得為差別對待,除非有合理、正當的理由[17]。如果不能準確地識別行政行為的屬性,準確適用法律、實現同案同判、維護司法公正就無從談起。由于司法實務中對考試違規處理的認識尺度不統一,屬性認定不準確,影響了法律的準確適用,產生了“同案異判”和“類案不同判”的現象,極大地挫傷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此外,準確判定行政行為的屬性是確定訴訟案件“案由”的基礎,而明確案件的案由是審理一起行政訴訟案件的關鍵環節。《暫行規定》深刻闡明了確定行政案由的重要意義:“案由是行政案件名稱的核心組成部分,起到明確被訴對象、區分案件性質、提示法律適用、引導當事人正確行使訴訟權利等作用。準確確定行政案件案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行政立案、審判中準確確定被訴行政行為、正確適用法律……”《暫行規定》將行政案件的案由劃分為三級,并規定依次優先適用三級、二級、一級案由。然而由于考試違規處理沒有對應的三級案由,司法實務中一時無法準確確定其屬性,進而繞過“三級案由”逃向“二級案由”或“一級案由”,將其統歸為“其他行政處理”。個別案件還存在案由認定錯誤的問題。
(二)推進依法行政和依法治考、維護法治統一的現實需要
《行政處罰法》是行政處罰領域的基本法律、通用規范,是行政處罰體系的“總綱”“總則”[18]。2021年修改后的《行政處罰法》明確了行政處罰的定義,厘清了行政處罰的種類,并對行政處罰的設定權進行了重新分配,分別賦予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以不同種類行政處罰設定權。2021年12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通知》中提出,“……要依法設定行政處罰,不得以其他行政管理措施的名義變相設定,規避行政處罰設定的要求。”“要加強行政規范性文件合法性審核,行政規范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處罰;違法規定行政處罰的,相關規定一律無效,不得作為行政處罰依據。”考試是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一項重要制度,考試執法作為行政執法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板塊,“依法治考”是國家實施考試活動、進行考試執法的基本遵循,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路徑。“依法治考”是指遵循法治的核心精神、依照法律的基本要求對考試行為進行治理,蘊含著“權力法定”“程序法定”“越權無效”“權利保障”等內涵要素[19]。近年來考試種類不斷擴張,考試中的違法行為不斷變型升級,迫切需要使用多種行政規制工具。然而我國考試法治體系建設卻明顯滯后,目前仍然缺乏一部統一的“考試法”或者考試行政法規。針對考試中的違法違紀行為,考試主管部門在無上位法依據的情況下以部門規章的形式設定了多種多樣的行政處理,進而產生了“越權”和“抵觸”現象。例如,《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違紀行為處理辦法》第8條設定了“終身禁考”的處理,但是遍覽上位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都找不到“終身禁考”的依據;《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對自學考試中的作弊行為設定了“延遲畢業1-3年”的處理,而《教育法》對考試作弊僅設定了“停考1-3年”的處理。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有學者曾專門撰文指出和批判這一現象和問題[20]。正是由于其屬性的不明確,進而掩蓋了其違法性。明確行政處理的屬性,對于明確其設定權限、依法設定行政處罰,規范考試相關規范性文件的“立改廢釋”工作,更好地推進依法治考和依法行政,更好地維護國家行政處罰法治的統一,都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三)明確實施程序、保障考生權利的現實需要
“考生”是考試執法活動的相對人和主要參與者,而且也是一類較為特殊和敏感的群體。每一類考試違規處理的設定、每一次執法活動,都涉及到考生權利的減損,都密切關系到考生的切身利益。嚴格履行相關的程序、切實保護相對人權利是“依法行政”“依法治考”的重要內涵。程序公正聯結著實體公正和當事人權利保障。然而現實中考試違規處理以“其他行政處理”之名行處罰之實,或者從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向一般行政行為逃逸,簡省或違反了相關程序,又或者在實施主體上做了變通,由監考人員實施本應由執法人員實施的措施等,這些現象都讓考試執法主體逃避了“程序性義務”,進而剝奪了考生的知情權、陳述申辯權、獲得救濟權等“程序性權利”。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對行政處理的屬性判斷不準確,致使對本應當予以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剝奪了考生的訴權和救濟權,或者使得具體行政行為逃避了司法審查的監督。因此,明確不同行政處理的類型,對于保障實施程序、明確法律救濟、保障考生權利、更好推進“依法治考”都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四、“取消成績”“撤銷授益性處理”的認定
(一)“取消成績”的認定
取消成績是指考試執法機關對于違反考試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宣布考生當次一門或多門考試科目的成績無效,包括已經取得的考試成績和尚未取得的考試成績。“取消成績”在有些法律法規和文件中也表述為“宣布成績無效”“記為零分”或者“按零分處理”,它們表述方式不同但是法律效果和實質含義相同。“取消成績”是考試行政執法中所特有的一類處理,同時也是適用最廣泛、最普遍的處理方式,無論是考試違紀還是考試作弊,取消成績都是首要的處理方式。這類處理是審判實踐中引起行政訴訟最多的行政行為,也是理論界爭議最大、實務界認定最不統一的處理。爭議的焦點在于是否屬于行政處罰。新《行政處罰法》第2條開宗明義地對行政處罰作出了定義:“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依法對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以減損權益或者增加義務的方式予以懲戒的行為。”并列舉了6類、13種處罰。新《行政處罰法》既揭示了行政處罰行為的內涵,提供了抽象的實質性判別標準,也廓清了行政處罰的外延,提供了直觀的外在識別標準。有學者將行政處罰的特征抽象為三個要素,分別是“不利益性”“違法性”和“報應性”[21],取消成績符合前兩項要素,其是否屬于行政處罰,關鍵就在于判斷是否具備“制裁性”和“報應性”。
以“取消成績和違規行為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作為分類標準,取消成績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為取消成績與違規行為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在具體的規范中包括兩種情形,分別是考生存在作弊行為而被取消作弊科目的成績,不具備考試資格的考生以偽造相關證明、填報虛假信息等方式參加考試而被取消成績。在這一類型中,考生的違規行為直接導致了成績無效的后果,取消成績只是考生對其違法行為所承擔的“等價性”不利后果而沒有付出額外的“代價”。第二種類型是指取消成績與違規行為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這一類型也包括兩種情形,一是考生因擾亂考場秩序、破壞報名秩序等考試作弊之外的其他違規行為而被取消考試成績;二是考生因在某一科目考試中作弊而被取消其他未實施作弊科目的成績。這一類型中,考生的行為從事實上并不必然會導致“成績無效”的后果,取消成績是考生在其違法行為之外付出的額外代價。行政處罰本質特征的“制裁”可以理解為“報應”。所謂“報應”是指讓違法者承擔違法行為之外額外的付出和代價,是“侵害的侵害”“惡行的惡報”,是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邏輯對當事人實施的報復。因此第一種類型中僅承擔等價性的不利后果不具有“報應性”,不是處罰,只有第二種類型的取消成績才是行政處罰。第一種類型的取消成績是對客觀事實狀態的認定、確認和宣告,因此可以視為“行政確認”。因此,“在某一科目的考試中作弊而被取消當次考試所有科目的成績”這一行政行為,具有行政確認和行政處罰的雙重屬性。在新《行政處罰法》法關于行政處罰五分法的分類中,“行為罰”是指限制或剝奪當事人“行為能力”的處罰,包括責令作為和責令不作為[22]。取消成績剝奪了當事人“獲得考試成績”這一行為能力,是一種宣布“行為無效”的處理,應當視為“行為罰”。
(二)“撤銷授益性處理”的認定
考生參加考試后,相關部門根據考生取得的成績予以錄取、錄用、學籍登記、授予資格、頒發證書等行為,均屬于“授益性行政行為”。如果在授益性行為作出后相關部門發現考生在考試過程中存在作弊、弄虛作假等違法行為或事實,就會撤銷已經作出的行政授益性行為,這類處理可以統稱為“撤銷考試授益性處理”,在各類法律規范中具體體現為:撤銷學位、取消錄取資格或學籍、取消錄用、取消聘用、宣布證書無效、責令收回證書或者予以沒收、撤銷職業資格等。這類處理明顯地減損了考生的權利,很容易被誤認為是行政處罰。也有學者將其認定為行政處罰[23]。然而這類處理的共同特征是,其所減損的是考生所不應當取得的“非法利益”,是否屬于行政處罰取決于行政處罰所減損的利益是否包括“合法利益”。只有在其違法行為之外或者課予的負價值超出其應有義務范圍的,才具備制裁性的特征[24]。換言之,只有讓當事人的狀況惡化到比違法之前更不利的狀況才具有制裁性。因此行政處罰所減損的權益只能是當事人合法、正當的權益。根據“任何人不得因為違法行為而獲利”這一法理,剝奪非法權益是行政機關通過糾正違法的方式使相對人的狀況恢復到違法之前的狀態,是一種“恢復原狀”的處理[25],不具有制裁性,不是處罰。這類處理是因考試作弊而導致原授益性行為所依據的基本事實不真實或者不能成立,因而行政機關撤銷了已經作出的授益性行政行為,其本質是對已經作出的行政行為的糾正。在學理上一般將這類行為稱為行政機關的“自我糾正”行為[26]。
五、限制報考、延遲畢業的認定
對于較為嚴重的考試違紀和考試作弊行為,在作出取消成績基礎上會增加“禁考”類的處理,具體體現為停考、限制報考、取消報考資格、終身禁考等。這類處理在一定時期內或終身性地剝奪了考生今后參加考試的權利和資格。考試是國家選拔人才、分配教育資源、授予資格的重要制度和方式,國家舉辦或組織的各類考試面向全體公民開放,公民通過參加各類考試獲得教育資源、資格準入、職位等。在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考試幾乎是考生升學、服公職、獲得特定職業資格的唯一渠道。因此“考試權”是符合條件的公民本應享有的一項重要的法定權利、正當性權利。限制報考剝奪了考生的“考試權”,同時也相當于在一定時期內或終身性地剝奪了考生升學、就業、獲得職業資格的權利。這一處理具有明顯的“制裁性”,應當屬于行政處罰。在國家自學考試中還有一類特殊的處理即“延遲畢業”。《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第9條規定,“參加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的考生有前款嚴重作弊行為的,也可以給予延遲畢業時間1至3年的處理,延遲期間考試成績無效。”延遲畢業對當事人產生了兩個方面的法律效果:一是延遲畢業期間內不予受理考生的畢業申請,二是延遲畢業期間內考生取得的考試成績無效。這種處理在一定時期內剝奪了考生申請畢業和獲得考試成績的權利,是對考生在其違法行為之外所施加的“報應”,目的在于對考生施加制裁,因此也應當屬于行政處罰。
限制報考和延遲畢業既是對考生資格的剝奪,同時也是對行為的限制。新《行政處罰法》在處罰種類上區分了行為罰和資格罰,而行為罰和資格罰往往難以區分。從某種意義上看,“行為”和“資格”是不可分的,資格罰脫胎于行為罰,二者具有共通性。行為以資格為前提,任何資格的剝奪或限制均意味著基于資格所從事的行為被禁止,資格的剝奪最終也體現為對行為的限制。但是二者的運行機制有著根本的區別。當事人的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基于行政許可所從事的行為,當事人沒有取得許可就不得從事該行為;另一類是不實施行政許可的行為,當事人無須取得許可證就可實施該行為。行政處罰禁止前一類行為的,就是資格罰;禁止后一類行為的,就是行為罰[23]。換言之,對于事先無須取得資格的行為,只能處以行為罰。限制報考限制的是“報名參加考試”這一行為,該行為不是基于行政許可的行為,也不是必須基于某種資格才能實施的行為,因此限考類處理是行為罰而不是資格罰。從另一個角度上看,考生報名參加考試,考試主管部門經審核后發放準考證的行為可以看做是一種“行政許可”。限考類處理相當于“不得申請行政許可”,其制裁機制和作用機理與作為行為罰的“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相似,應當視為行為罰。而延遲畢業限制了考生申請畢業的行為,并且剝奪了考生獲得考試成績的“行為能力”,是一種“責令不作為”的處理,也可以看做是判定“行為無效”的處理。申請畢業這一行為也不需要以獲得行政許可為前提,因此也應當視為行為罰。
六、終止參加考試、取消本次考試資格的認定
(一)“終止參加考試”的認定
終止(繼續)參加考試是對于現場發現的“正在發生”的考試違紀或作弊行為而“當場”作出的一種處理,通常與“責令離開考場”配套使用。這類處理的法律效果是終止考生參加本場考試,具有當場性、緊急性、暫時性、立即執行的特征。“責令性”行為常常陷入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命令三者之間的泥淖。
有學者認為,“終止參加考試”和“責令離開考場”屬于行政強制措施[7]。這種理解看似合理但實則難以站得住腳。這類處理雖然具有行政強制措施的服從性、防范性、即時性的特征,但是缺乏行政強制措施所必備的特征之“物理性”。“物理性”是指直接作用于當事人的人身或財產并具有改變其物理狀態的效果,是發生可見動作的有形行為和實力行為[27]。終止參加考試是“意思性”“決意性”行為,而責令離開考場則是“命令性”行為,二者都不是物理性、動作性和實力性行為,因此不宜認定為行政強制措施。這類處理應當區別于“驅逐考生離開考場”“強制帶離考場”,后二者才具有物理性和動作性。
另外一種理解是將其視為行政處罰。考生報名經審核通過后享有了參加考試的權利,而終止參加考試是基于考生的違法行為而剝奪了其繼續參加考試的權利,是對考生“繼續參加考試”這一行為作出的處分,具備“行為罰”的特征。而且“責令離開考場”是“責令停止行為”的一種形式,而“責令停止行為”在《行政處罰法》一審稿中曾經被列為行政處罰的種類之一。不僅如此,“責令離開考場”與作為行政處罰的“限期出境”在實施方式和作用機理上具有相似性,因此有理由認為其屬于行政處罰。
決定其是否屬于行政處罰關鍵在于是否具備“制裁性”,這需要回歸到行政行為目的上。正如德國法學家魯道夫·馮·耶林曾經說過的:“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于一種目的,即一種實際的動機。”[28]“終止參加考試”分別適用于現場發現的考試違紀和考試作弊。對于擾亂考場秩序、不遵守考場規則等考試違紀行為,終止參加考試的目的在于制止違法行為,維護考場秩序并保障考試順利進行。正在進行的考試作弊行為對考試的公平公正和考試安全構成了現實的威脅,如果允許考生繼續考試就可能導致試題答案泄露等危險的進一步擴大,因此對于現場發現的作弊行為作出終止參加考試的目的在于制止違法行為,排除危險因素,維護考試安全。同時考試作弊絕大多數都會使用一定的器具或資料,終止參加考試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對作弊考生進行調查,及時固定證據,防止證據毀損滅失。綜合來看,終止參加考試的目的可以概括為“制止違法行為,保障考試安全”。
“終止參加考試”與行政處罰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區別。首先,制裁是對過去所犯錯誤的“報應”,是“回顧性”的而不是“預防性”的。而“終止參加考試”主要著眼于對未來可能發生危險的預防,是預防性的而不是回顧性的。行政處罰雖然也具有預防性,但是其預防性是通過制裁實現“一般預防”。而終止參加考試是特殊預防,著眼于從個體上預防危險發生。其次,制裁是以“責任”為前提條件,而終止參加考試以“行為”或“危險”的存在為實施根據。如果考生欠缺行政責任能力要件,如法定年齡、精神狀態等,則不能實施行政處罰。但是只要考生實施了特定的行為,具有人身危險性或造成了一定的危險,無論其是否具有行政責任能力,都可以終止其繼續參加考試。第三,行政處罰是終局性行為,而終止參加考試是一種中間性、過程性、階段性行為。
綜上所述,“終止參加考試”既不屬于行政處罰,也不屬于行政強制措施。但是這類處理客觀上對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作出了實際的處分,因而有學者將這類行為描述為“預防性不利處分”[29]。本文認為更宜將其定位為“保安處分”。所謂“保安處分”,是指以個別預防為目的,基于當事人的人身危險性而采取的使其改善或不能再犯的預防性處置措施[30]。
(二)“取消本次考試資格”的認定
“取消本次考試資格”(終止錄用程序、終止聘用程序)是一種較為少見的行政處理,僅存在于公務員錄用考試和海關報關員資格考試的違規處理規定中。“取消本次考試資格”的效果在于宣告考生失去本次考試資格,并無權繼續參加其后的幾場考試。公務員招錄考試中的“終止錄用程序”和事業單位招聘考試中的“取消本次應聘資格”在考試階段與之具有相同的含義和法律效果,只不過它們適用的范圍延伸至了體檢、考察等環節。對于該行政行為的屬性,應當結合其所適用的情形分別予以探討。取消本次考試資格的適用情形總體上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報考者所提交的報考材料、信息不真實。這種情形下,考生自始就不具備考試的條件和資格。考生報名參加考試,考試執法部門經審核后準予參加考試的行為是一種行政許可行為。由于考生本身不具備考試的資格和條件,取消本次考試資格是行政機關對已經作出的行政行為的自我糾正,是行政許可的撤銷。第二類是考生在考試過程中存在舞弊、弄虛作假等違法違規行為,以及有擾亂考場秩序、不服從考試管理等考試違紀行為。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考生的違法違紀行為已經威脅到了考試安全,影響了考試的順利進行,取消考試資格是為了保障考試的安全,保障考試順利進行,其屬性與“終止參加考試”相同,應當視為“保安處分”。
七、記入考試誠信檔案和考試失信懲戒約束措施的認定
隨著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和信用監管機制的構建,考試誠信檔案以及各地市建立的信用地方性法規、規章逐步將考試失信信息予以記錄、歸集。在這個過程中涉及到兩類具體行政行為,分別是記入考試誠信檔案和考試失信約束懲戒措施。“記入考試誠信檔案”是信用信息歸集的過程,它雖然不產生外部法律關系,也不會對失信人產生立即的權利義務影響,但是檔案內容會在將來被用于設定新的法律關系,從而間接影響考生的權利義務,因此記入誠信檔案可以被定義為“準行政處理”[31]。
失信懲戒是指公共管理部門在對信用信息分類分級評價的基礎上,對失信人施加的一系列限制、制裁和管理措施。《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將這一系列的失信懲戒措施綜合概括為“行政監管性懲戒約束”。對于失信約束懲戒措施的屬性,學界形成了多種不同的學說,其中“行政處罰說”支持者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對于考試失信約束懲戒措施是否屬于行政處罰,應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前考試失信約束懲戒措施主要有三類。一是高等院校拒絕授予學位,體現為部分高等院校在其自治章程中規定考試期間有作弊記錄的不予授予學位③。“學位獲得權”是法律賦予受教育者的一項權利,其本源是《憲法》《教育法》中的公民受教育權[32]。《教育法》第43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權利。這類處理從外表上看減損了考生“學位獲得權”。根據《高等教育法》《學位條例》的規定,高等院校有權自主設定學位授予條件。部分高等院校認為學位授予包含道德水平的要求,不授予學位是高等院校認為考試作弊的學生不符合學校培養目標和學位授予條件而作出的一種處理。它不具有懲戒性,不應認定為行政處罰。二是高等院校的不予錄取。部分高等院校在其自治章程中規定有考試作弊行為記錄的考生不予錄取④。這類處理也是高等院校基于《高等教育法》《學位條例》自主設定招生條件、自主選擇招生對象的行為,不具有懲戒性,也不應認定為行政處罰。三是公務員、警察等招錄程序中對于存在考試舞弊或者嚴重舞弊行為的人員認定為考察不合格⑤。考試作弊行為反映了一個人具有投機取巧、弄虛作假、隱瞞欺騙的品行,是一個人道德品行不佳的表現。而公務員是履行國家公職、行使公權力的人員,需要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行。《公務員法》也規定公務員應當具備良好的道德品性。不予錄用的行為實際上是將道德不佳的人排除在公務員隊伍之外,是一種人力資源優化配置的行為。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錄用應當遵循“擇優錄取”的原則。因此這類行為也可以視為國家公務員招錄的“選優”行為[33]。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類行為都不具有制裁性和懲戒性,不應當被評價為行政處罰。
綜合來看,考試失信的信用約束懲戒措施從某個角度上看雖然減損了當事人的某種權利,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對失信人進行制裁和懲戒,而是在對失信人進行信用分級、評價基礎上的風險規避措施和資源優化配置措施,不具有制裁性,因而不宜認定為行政處罰。實際上,失信約束懲戒措施與行政處罰在行政任務、行政目的、理論基礎、運行規律、責任屬性等多個方面均不同,不是一類行政行為[34]。同時,這類行為與傳統的行政行為也存在著區隔,應當被定義為“新型行政監管方式”。
八、結語:現實困境的積極應對
考試違規處理的多變性、復雜性極大地增加了判斷的難度,也帶來了實務中司法尺度不統一、執法程序不完善、權利保障不足等一系列問題。面對這一現實困境,司法、執法、立法層面都應當作出積極應對。司法層面,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加強典型案例的發布,通過案例指導的方式塑造統一的司法標尺;同時應及時修訂《暫行規定》,將考試違規處理吸納入其中,明確考試違規處理的案由,以便更好地規范和指引司法實踐。執法層面,應當借《行政處罰法》修改之機,對考試相關的規范性文件進行系統性檢視、評估,加強法律的立改廢釋,及時清理其中沒有法律依據、與上位法相抵觸的行為;同時根據行政行為的屬性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行政行為的實施程序。立法層面,可以考慮適時出臺統一的國家考試法或者考試行政法規,以規范違規處理的統一適用。
注釋:
①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規定,機動車駕駛證考試也屬于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但是由于其考試形式、實施方式、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理與其他國家考試有著較大差異,因此本文并未將其納入研究范疇。
②其中,行政法規僅有《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地方性法規僅有《重慶市國家教育考試條例》。此外,《資產評估師資格考試違規行為處理辦法》制定主體為中國資產評估協會,屬于行業的全國性自律組織,不屬于國務院部門,不是部門規章。
③例如《吉林師范大學學士學位授予工作細則》第四條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授予學士學位:2、考試違紀舞弊者”;《山東大學高等學歷繼續教育本科畢業生學位授予實施辦法》)(山大教字[2021]39號)第7條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不得授予學士學位:(二)有作弊…等情形的,不授予學位。”
④例如:《中國人民公安大學2023年碩士研究生招生章程》規定:“報考我校碩士研究生的考生,應當符合下列條件:(六)無國家法定考試違規作弊記錄。”參見網址:https:// yzb.ppsuc.edu.cn/info/1009/2846.htm
⑤如中組部印發的《公務員錄用考察辦法(試行)》第9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確定為擬錄用人員:(九)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中被認定有嚴重舞弊行為的。”又如《公安機關錄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辦法》(公通字〔2020〕11號)第8條規定,存在以下情形的不得被錄用為人民警察:“(十六)在國家法定考試中被認定有舞弊等嚴重違紀違規行為或者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以外的其他考試中被認定為組織作弊的。”
參考文獻:
[1]李化德.論國家考試立法[J].現代法學,2008,30(5):29-37.
[2]陳啟新.我國考試法立法研究綜述[J].教育與考試,2014,(1):11-17.
[3]張兆安代表:制定國家考試法提升依法治考水平[EB/OL].(2022 - 09 - 04). www. npc. gov. cn / npc / c202 / 200903 / 537473d2815c431b849ce33d7e123af3.shtml..
[4]李化德,李亦成.關于國家考試執法的幾個問題[J].中國考試,2012,(6):48-54.
[5]姜明安.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154.
[6]陳韶峰,朱衛國.論國家教育考試舞弊行為的行政處理[J].江蘇高教,2013,(4):32-35.
[7]陳韶峰.論國家教育考試作弊行為的行政處罰[J].上海教育科研,2016,(9):50-54.
[8]孫才華.論宣布國家教育考試成績無效的法律屬性——兼論不利行政決定的合理性審查[J].中國教育法制評論,2015,13(00):120-133.
[9]湛中樂.國家教育考試中考生考試作弊行為的認定、處理及其法律救濟——2003年全國碩士學位聯考中的三個案例分析[J].中國教育法制評論,2004,(0):276-300.
[10]馬震發訴內蒙古自治區招生教育考生中心教育行政處理糾紛二審行政判決書:呼行終字第00049號[EB/OL].(2015-11-06)[2022-08-10].https://wenshu.court.gov.cn.
[11]劉建明、河北省人事考試局教育行政管理(教育)二審行政判決書: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2019)冀01行終187號[A/OL].(2015-11-06)[2022-08-10].https://wenshu.court. gov.cn.
[12]吳志剛與河南省人事考試中心行政處理決定一案一審行政判決書:金行初字(2014)第177號[A/OL].(2015-11-06)[2022-08-10].https://wenshu.court.gov.cn.
[13]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與羅軍其他二審行政判決書:粵高法行終字第432號[EB/OL].(2015-11-06)[2022-08-10]. https://wenshu.court.gov.cn.
[14]王權、咸寧市教育招生考試院教育行政管理(教育)二審行政判決書:(2019)鄂12行終26號[EB/OL].(2015-11-06)[2022-08-10].https://wenshu.court.gov.cn.
[15]陳佳訴陜西省人事考試中心教育其他行政行為一審行政裁定書:(2016)陜7102行初387號[EB/OL].(2015-11-06)[2022-08-10].https://wenshu.court.gov.cn.
[16]王艷與陜西省人事考試中心教育其他行政行為一審行政裁定書:(2016)陜7102行初386號[EB/OL].(2015-11-06)[2022-08-10].https://wenshu.court.gov.cn.
[17]林騰鷂.行政法總論[M].臺灣:三民書局,1999:81.
[18]章志遠.作為行政處罰總則的《行政處罰法》[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0,28(5):19-31.
[19]彭宇文,姜杰文.依法治考核心要素探析[J].中國考試,2021,(11):73-79.
[20]胡建淼.設定行政處罰要注意法律位階——從“司法考試作弊終身禁考”談起[J].人民法治,2016,(11):87.
[21]熊樟林.行政處罰的概念構造新《行政處罰法》第2條解釋[J].中外法學,2021,33(5):1286-1302.
[22]黃海華.行政處罰的重新定義與分類配置[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0,23(4):31-43.
[23]胡建淼.論行政處罰的手段及其法治邏輯[J].法治現代化研究,2022,(1):17-31.
[24]王貴松.論行政處罰的制裁性[J].法商研究,2020,37(6):19-32.
[25]王紅建.新《行政處罰法》疑難條款的解讀與適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31.
[26]高鴻.行政行為自我糾正的制度構建[J].中國法律評論,2021,39(3):62-68.
[27]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釋義與案例[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41-43.
[28][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122.
[29]袁雪石.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釋義[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94.
[30]葉良芳,苗一路.兩岸保安處分制度構建之比較[J].浙江工業大學學報,2016,(4):404-411.
[31]何海波.行政訴訟法(第三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144-146.
[32]龔向和,魏文松.學位獲得權的內涵界定、現實困境及其制度完善[J].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20,(7):13-23.
[33]譚波,劉昭辰.失信懲戒資格罰與限制從業的銜接——以《行政處罰法》修訂為背景[J].行政科學論壇,2021,8(10):26-32.
[34]劉文凱.信用行政懲戒不宜定性為行政處罰[J].政法論壇,2023,41(3):55-67.
The Typification Research about Administrative Treatment on Exam Illegal Acts
Li Xiang1Meng Yuetong2
1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038
2 Jinan Engineering Polytechnic, Jinan, Shandong, 250200
Abstract:The administrative treatment of the illegal acts of examination has various forms and changes. The identification on judicial practice is not uniform and inaccurate,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s obvious shortcomings. Clarifying its legal attributes is the realistic need of accurately applying the law,promoting exam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maintaining the unity of the rule of law,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examinees. Score cancelling respectively belongs to 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administrative confirmation according to its applicable situation. The revocation of beneficial administrativ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dministrative selfcorrection act. Examination attending limit and graduation dela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onduct administrative penalty. Termination of attending examination should be regarded as security guarantee measures. Cancell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examination respectively belongs to revo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icensing and security guarantee measures. Exam credit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is not an administrative penalty. It can be defined as a new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act.
Key Words:Score Cancelling,Examination Attending Limit,Termination of Continuing Attending the Examination,Cancelling the Qualification of this Examination,Exam Dishonesty Administrative Discipline
(責任編輯:吳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