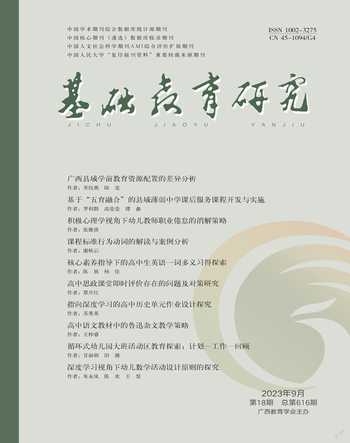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的啟示
王華婷 王登峰
【摘 要】課程實(shí)施直接關(guān)乎課程質(zhì)量,其實(shí)質(zhì)是協(xié)調(diào)處理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的關(guān)系。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以處理結(jié)構(gòu)與行動關(guān)系聞名,其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具有啟示,即要思想上確立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之間的二重性關(guān)系,努力挖掘、梳理課程實(shí)施中的結(jié)構(gòu)性特征以指導(dǎo)課程實(shí)踐,充分發(fā)揮課程實(shí)施中課程行動的主觀能動性以建構(gòu)更加適宜的課程結(jié)構(gòu),以此形成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的良性互動來保證課程質(zhì)量和立德樹人效果。
【關(guān)鍵詞】幼兒園 課程實(shí)施 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
【中圖分類號】G6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275(2023)18-97-03
課程問題是教育的核心問題,提升教育質(zhì)量的關(guān)鍵在于改革和完善課程。園本課程的建設(shè)是一個(gè)系統(tǒng)工程,涉及課程理念、課程目標(biāo)、課程內(nèi)容、課程實(shí)施、課程評價(jià)、課程資源等多種要素,所有的這些要素共同組建起整體的課程結(jié)構(gòu)。課程結(jié)構(gòu)化的程度有高有低,根據(jù)其結(jié)構(gòu)化程度高低的不同構(gòu)成一個(gè)連續(xù)體,所有活動都能在連續(xù)體上找到其位置。[1]一個(gè)活動結(jié)構(gòu)化程度的高低主要在于是強(qiáng)調(diào)教師預(yù)設(shè)還是強(qiáng)調(diào)兒童生成,實(shí)質(zhì)涉及的是課程實(shí)施取向[2]的問題。更進(jìn)一步說,課程實(shí)施中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之間應(yīng)該是一個(gè)什么關(guān)系,是課程實(shí)施實(shí)際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專注于社會結(jié)構(gòu)與社會行動的關(guān)系問題,所以本文從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出發(fā),探討其對課程實(shí)施即處理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之間關(guān)系的一些有益啟示。
一、結(jié)構(gòu)化理論與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
(一)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
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作為當(dāng)今最具影響力的社會理論之一,其試圖克服結(jié)構(gòu)與行動的二元對立,系統(tǒng)闡釋了結(jié)構(gòu)及其二重性。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所研究的基本領(lǐng)域“既不是個(gè)體行動者的經(jīng)驗(yàn),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shí)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shí)踐”[3]。結(jié)構(gòu)化理論中的“結(jié)構(gòu)”,指的是“社會的制度化特征(結(jié)構(gòu)性特征)”[4]。而“結(jié)構(gòu)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制度中反復(fù)采用的規(guī)則與資源”[5]。其中,“規(guī)則”是指“在社會實(shí)踐的實(shí)施及再生產(chǎn)活動中運(yùn)用的技術(shù)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6];“資源”是指“這樣一些模式,轉(zhuǎn)換關(guān)系可以借助它們真正地融入社會實(shí)踐的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7]。吉登斯也特別強(qiáng)調(diào),結(jié)構(gòu)具有二重性,即“社會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性特征對于它們反復(fù)組織起來的實(shí)踐來說,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結(jié)果”[8]。
(二)結(jié)構(gòu)化理論適用于課程實(shí)施
教育作為社會的有機(jī)組成部分,教育活動也必然是社會實(shí)踐活動的一部分。所以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也被一些研究者用于教育領(lǐng)域的理論研究與實(shí)踐指導(dǎo)。幼兒園教育活動的開展就是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的行動展開,所以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也是一種社會實(shí)踐活動。更進(jìn)一步說,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正是有序安排幼兒一日生活的社會實(shí)踐,跟其他社會實(shí)踐活動一樣也是在一定的規(guī)范和制度下進(jìn)行的,其中也蘊(yùn)含著結(jié)構(gòu)性特性。因此,作為關(guān)注時(shí)空向度上有序安排的社會實(shí)踐的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應(yīng)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jià)值。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結(jié)構(gòu)性的理解與把握,將會為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的行動提供實(shí)踐邏輯的支撐,促進(jìn)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的質(zhì)量提升。
(三)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面臨結(jié)構(gòu)化轉(zhuǎn)型
課程實(shí)施是教育質(zhì)量的關(guān)鍵所在。對于幼兒園來說,“課程實(shí)施是幼兒園課程目標(biāo)實(shí)現(xiàn)的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是將計(jì)劃形態(tài)的課程經(jīng)過教師的理解與轉(zhuǎn)換,與兒童發(fā)生直接聯(lián)系、真正對兒童產(chǎn)生教育影響的過程”[9]。因此,深入研究、分析、理解課程實(shí)施成為一項(xiàng)不得不面對的任務(wù),也是最終促進(jìn)教育目標(biāo)達(dá)成的實(shí)質(zhì)性行動。隨著課程改革的推進(jìn),“舊的課堂教學(xué)結(jié)構(gòu)正在被改變,新型課堂教學(xué)結(jié)構(gòu)正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10],主要表現(xiàn)為向“‘以學(xué)習(xí)者為中心的課堂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11]。對于學(xué)前教育來說,變革又何嘗不在發(fā)生。隨著幼兒教育不斷對兒童地位的強(qiáng)調(diào),幼兒園也面臨著師幼關(guān)系變革的課程實(shí)施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這將十分考驗(yàn)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者。在此背景下,可以借鑒結(jié)構(gòu)化理論的合理資源來促進(jìn)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的理解與踐行。
二、結(jié)構(gòu)化理論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的啟示
(一)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具有二重性
根據(jù)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有研究者指出,“學(xué)校的各種行為規(guī)范和制度最能體現(xiàn)教育結(jié)構(gòu)的二重性特征”[12]。幼兒園的課程實(shí)施也不例外,其也是在各種規(guī)范和制度下,師幼通過行動來對各種規(guī)范和制度進(jìn)行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的過程。各種規(guī)范和制度組成了總體課程結(jié)構(gòu),而“課程結(jié)構(gòu)是課程行動所必須依賴的規(guī)則與資源,是課程行動的媒介”[13],即課程行動是在課程結(jié)構(gòu)的框架下得以發(fā)生,是依據(jù)課程結(jié)構(gòu)來進(jìn)行的。同時(shí),“從課程結(jié)構(gòu)是人造事實(shí)這種意義上來說,課程結(jié)構(gòu)是課程行動者展開課程行動的結(jié)果”[14],即課程結(jié)構(gòu)是通過課程行動所體現(xiàn)出來,而且是在課程行動中得以維持乃至建構(gòu)的。所以,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遵循課程結(jié)構(gòu)和課程行動的“二重性”原理,是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相互作用的實(shí)踐過程。
基于此,要認(rèn)識到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不是二元對立的,在課程實(shí)施中要努力梳理并把握其二重性關(guān)系。在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中,人們往往容易認(rèn)識到課程結(jié)構(gòu)即各種規(guī)范和制度對課程行動的作用,總覺得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就是貫徹執(zhí)行幼兒教育政策文本的精神、幼兒園教育大綱、一日活動安排等,而忽視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的作用。殊不知,課程行動并不是完全被動的執(zhí)行過程、要素,它也會表現(xiàn)出一定的建構(gòu)性、變革性。例如有覺悟的教師意識到新時(shí)代幼兒應(yīng)該更具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那么在教育教學(xué)行動中就會給予幼兒更多的自主空間,所開展的課程就會更多地基于生成,其行動就會對舊有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xué)大綱”形成沖擊、挑戰(zhàn)。隨著這種新行動的增加,逐漸就會“撼動”舊有的“教學(xué)大綱”,從而推動課程結(jié)構(gòu)的制度性變革。所以努力梳理并把握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的二重性,應(yīng)認(rèn)識到課程結(jié)構(gòu)對課程行動的作用,更應(yīng)認(rèn)識到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的作用,從而形成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相互作用的完整認(rèn)識,即二重性認(rèn)識。
(二)努力挖掘、梳理課程實(shí)施中的結(jié)構(gòu)性特征
在明確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具有二重性之后,理解課程實(shí)施結(jié)構(gòu)就需要把握課程實(shí)施實(shí)踐活動中的結(jié)構(gòu)性特性,最主要的是厘清課程實(shí)施實(shí)踐活動中的規(guī)則、資源,以及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課程實(shí)施在比較明確的規(guī)范制度下進(jìn)行,同時(shí)又在習(xí)之而不察的“慣習(xí)”中悄然展開。于是在課程實(shí)施中,教師需要將顯性的規(guī)范制度進(jìn)行梳理,也需要對隱性的行動“慣習(xí)”進(jìn)行洞察,把握課程行動展開的實(shí)際邏輯和蘊(yùn)含其中的“轉(zhuǎn)換關(guān)系”。基于此才能厘清課程實(shí)施中的結(jié)構(gòu)性特性,對課程實(shí)施具有主動的意識,從而能夠發(fā)現(xiàn)課程實(shí)施賴以展開的規(guī)則和資源,進(jìn)而能夠?qū)φn程實(shí)施進(jìn)行理解和反思。
具體來講,幼兒園課程的總體結(jié)構(gòu)比較清晰,即由課程理念、課程目標(biāo)、課程內(nèi)容、課程實(shí)施、課程評價(jià)等構(gòu)成,這些相對容易把握和梳理,也是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中經(jīng)常做的和容易做的。難點(diǎn)在于把握和梳理課程實(shí)施中的“實(shí)踐慣習(xí)”——進(jìn)一步厘清幼兒一日生活中各類活動開展的一般性技術(shù)和流程及其中的“轉(zhuǎn)換關(guān)系”。雖然從顯性上看,課程行動都是在課程結(jié)構(gòu)的支架下進(jìn)行,但是由于個(gè)體對課程結(jié)構(gòu)相關(guān)要素理解認(rèn)知的差異及實(shí)踐中情境要素的影響,個(gè)體課程行動的真正展現(xiàn)很大程度上又是體現(xiàn)為具有一定“實(shí)踐慣習(xí)”的。所謂課程行動的“實(shí)踐慣習(xí)”,就是通常所說的“大家都是這么做的”,有一種習(xí)之而不察的特點(diǎn),是一種無明確意識的課程實(shí)踐,或者說是一種完全內(nèi)化的課程實(shí)踐。這種出于“實(shí)踐慣習(xí)”的課程行動才是課程實(shí)踐中更需要好好把握和梳理的,只有將這種課程實(shí)施中隱性的結(jié)構(gòu)性要素挖掘出來,才能更好地為理解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結(jié)構(gòu)和采取課程實(shí)施行動提供理論支撐和行動邏輯。
(三)充分發(fā)揮課程實(shí)施中課程行動的主觀能動性
明確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具有二重性,并且把握課程實(shí)施中的結(jié)構(gòu)性特性,以此為課程行動提供實(shí)踐意識與行動邏輯支撐。正如“二重性”所強(qiáng)調(diào)的結(jié)構(gòu)對行動具有促動性也具有制動性,雖然課程結(jié)構(gòu)一方面有利于課程行動的展開,但是課程結(jié)構(gòu)對課程行動也具有制約作用,尤其是當(dāng)原有的課程結(jié)構(gòu)已不適用新的課程行動時(shí)。另一方面“二重性”強(qiáng)調(diào)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既有延續(xù)作用,又有建構(gòu)作用,所以當(dāng)舊有的課程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不能滿足新的課程行動時(shí),行動需要發(fā)揮其建構(gòu)的主觀能動作用。也就是說,課程結(jié)構(gòu)化不僅是關(guān)于課程各要素之間比例是否適當(dāng)、結(jié)構(gòu)是否合理、邏輯是否有序等課程結(jié)構(gòu)問題,而且是包含課程行動在內(nèi)的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互構(gòu)的問題,尤其是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的生產(chǎn)與再生產(chǎn)。
現(xiàn)階段幼兒教育面臨新時(shí)代新任務(wù),要培育一代新人,就需要教育結(jié)構(gòu)、課程結(jié)構(gòu)的變革,要轉(zhuǎn)變以往的“教師中心”“教材中心”“課堂中心”,要凸顯兒童、經(jīng)驗(yàn)、活動,建構(gòu)一種“主體間指導(dǎo)學(xué)習(xí)”[15]的關(guān)系型教育結(jié)構(gòu)、課程結(jié)構(gòu)。于是在課程實(shí)施中就需要發(fā)揮課程行動的主觀能動作用,去踐行主體間的師幼關(guān)系、教學(xué)關(guān)系、活動關(guān)系,通過這種課程行動在時(shí)空向度上穩(wěn)定下來從而形成制度化的課程實(shí)踐,進(jìn)而建構(gòu)出與之適宜的課程結(jié)構(gòu),去規(guī)范后續(xù)的課程實(shí)踐。這樣循環(huán)往復(fù),實(shí)現(xiàn)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之間的辯證統(tǒng)一,確保課程實(shí)施在新時(shí)代背景下得以有序展開。
同時(shí),發(fā)揮課程行動的主觀能動性才是園本課程在地化、中國化的關(guān)鍵。如果只是一味講究、追求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的延續(xù)性,那么幼兒園的課程實(shí)施就會出現(xiàn)“一刀切”的同質(zhì)化現(xiàn)象。同質(zhì)化是指課程實(shí)施不顧地域、文化、園所實(shí)際的差異而按課程結(jié)構(gòu)模板刻畫課程行動,這樣會導(dǎo)致課程行動的亦步亦趨。還有一些幼兒園課程照搬國外等優(yōu)秀幼兒教育模式、案例來開展課程行動,出現(xiàn)課程行動的“依葫蘆畫瓢”現(xiàn)象。這都不符合具體幼兒園的實(shí)際,不符合實(shí)事求是的精神。只有充分認(rèn)識到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具有建構(gòu)作用,充分發(fā)揮課程行動的主觀能動性,才能克服幼兒園課程行動中的同質(zhì)化,實(shí)現(xiàn)園本課程的在地化,即課程行動遵循幼兒園的實(shí)際。同時(shí)應(yīng)避免幼兒園課程行動中的“依葫蘆畫瓢”行為,實(shí)現(xiàn)幼兒園課程的中國化,即扎根中國大地辦幼兒教育。這樣才能形成在地化的、中國化的園本課程,促進(jìn)立德樹人根本任務(wù)的實(shí)現(xiàn)。
課程實(shí)施就是課程行動在課程結(jié)構(gòu)下綿延展開的實(shí)踐過程。借鑒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明晰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具有二重性關(guān)系,即課程結(jié)構(gòu)對于課程行動既有促動性也有制動性,課程行動對課程結(jié)構(gòu)既有延續(xù)性又有建構(gòu)性。所以在課程實(shí)施中一方面要梳理課程結(jié)構(gòu)中的結(jié)構(gòu)性特性,這既包括課程總體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也包括具體課程實(shí)施的技術(shù)流程、“實(shí)踐慣習(xí)”等,從而理解、支撐課程行動的有效展開。另一方面要發(fā)揮課程行動的主觀能動作用,在課程結(jié)構(gòu)的新時(shí)代變革中積極通過課程行動建構(gòu)適宜的課程結(jié)構(gòu),從而推動課程實(shí)施的結(jié)構(gòu)化、時(shí)代化、在地化、中國化。
課程實(shí)施的結(jié)構(gòu)化就是課程結(jié)構(gòu)與課程行動不斷互構(gòu)的過程,也是課程結(jié)構(gòu)的普遍性與課程行動的具體性相結(jié)合的過程,還是課程結(jié)構(gòu)的歷史性與課程行動的現(xiàn)實(shí)性辯證統(tǒng)一的過程。正是在不斷互構(gòu)、結(jié)合、辯證統(tǒng)一的過程中使得課程既具有普遍性、歷史延續(xù)性,又貼合新時(shí)代發(fā)展的特殊性和幼兒成長的現(xiàn)實(shí)需要,由此才更可能實(shí)現(xiàn)課程高質(zhì)量發(fā)展和真正落實(shí)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wù)。
【參考文獻(xiàn)】
[1]朱家雄.從教學(xué)活動的結(jié)構(gòu)化程度談幼兒園課程的設(shè)計(jì)和實(shí)施[J].學(xué)前教育研究,2003(10):5-6.
[2]張華.論課程實(shí)施的涵義與基本取向[J].外國教育資料,1999(2):28-33.
[3]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gòu)成:結(jié)構(gòu)化理論大綱[M].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61.
[4]同[3]290.
[5]同[3]87.
[6]同[3]85.
[7]同[3]80.
[8]同[3]89.
[9]王萍.幼兒園課程實(shí)施現(xiàn)狀與特征的個(gè)案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xué),2010:摘要Ⅰ.
[10]王鑒,王文麗.結(jié)構(gòu)化理論視角下的課堂教學(xué)變革研究[J].山西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9,42(3):91.
[11]同[10].
[12]李慧敏,張潔.走向教育的“二重性”:探求安東尼·吉登斯結(jié)構(gòu)化理論的教育意義[J].河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5(5):102.
[13]楊道宇.課程效能生成的原理研究:基于結(jié)構(gòu)化理論的視角[D].哈爾濱: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2010:171.
[14]同[13]172.
[15]郝文武.現(xiàn)代中國教育本質(zhì)觀的合理性建構(gòu)[J].高等教育研究,2022,43(1):9.
王華婷 / 西安文理學(xué)院學(xué)前教育學(xué)院,教師,博士,從事學(xué)前教育基本理論研究(西安 710065);王登峰 / 西北工業(yè)大學(xué)幼兒園,高級教師,從事幼兒教育工作(西安 710072);*通訊作者,E-mail:wdf19870409@sina.com
【基金項(xiàng)目】陜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學(xué)規(guī)劃課題“基于童心保育的幼兒園師幼互動質(zhì)量提升路徑研究”(SGH22Q202);陜西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研究專項(xiàng)青年項(xiàng)目“陜西省公辦幼兒園教師專業(yè)成長動力現(xiàn)狀及提升路徑研究”(2023QN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