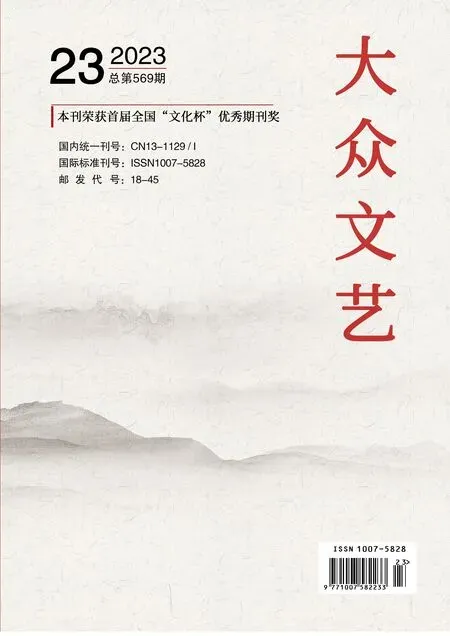跨文化視域下的《列王紀》細密畫
汪雅彤
(陜西師范大學,陜西西安 710000)
一、古代中國與波斯的交流
(一)中國與波斯的早期經濟來往
中國與伊朗最早的交流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時期就有共同的邊界,最早以民間交流居多,古代游牧民族的遷徙很可能就是歐亞大陸之間最早期的交流,《史記·大宛列傳》中提到:“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表明在漢武帝統治時期,中國和波斯就已建立了較為緊密的關系。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絲綢之路后,漢朝建立了與西域多國的外交關系,中國和波斯官方層面的交流逐漸增加,貿易往來頻繁。[1]中國最早流入西亞的商品是絲綢和瓷器,被當時的波斯貴族所喜愛收藏,波斯的金銀器、玻璃器和織錦等傳入中國。在山東青州西辛戰國末至西漢初期墓以及廣東廣州西漢南越王墓等墓葬中都曾出土過一種水滴紋凸瓣銀盒,這種工藝品很可能從當時的安息王朝傳入,器物上所采用的錘揲工藝可追溯至阿契美尼德王朝[2]。薩珊王朝時波斯經濟文化發展到巔峰,中國和波斯的交流日益頻繁,薩珊銀幣作為一種國際貨幣在中亞、東歐以及中國西部等地區流通,據考古發現,中國多地如新疆、青海、山西、河南以及河北都出土過薩珊銀幣,[3]學者夏鼐認為在河西地區薩珊銀幣是作為流通貨幣使用的,這些出土的錢幣是當時中國和波斯密切交流的最好見證。
(二)中國科學技術對波斯文化的推動
中國的造紙術曾對波斯文化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據推測751年怛邏斯之戰中唐軍戰敗,被俘將士中相當一部分是造紙工匠,阿布·穆斯林便讓他們集中到撒馬爾罕開展造紙業,不久,撒馬爾罕成為全國的造紙中心,制作出了大量便宜好用的紙張,為后期的“百年翻譯運動”以及細密畫的繁榮與發展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阿拔斯王朝時期書籍裝幀的主要流程是謄抄和裝訂,不重視繪圖,只是在一些科學著作上面會有簡單圖解,可以說是細密畫的雛形。1252年,旭烈兀出征波斯,消滅木刺夷及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1256年建立伊爾汗王朝,伊爾汗王朝的統治者十分重視文化建設,此時插圖與文學的聯系逐漸緊密,書籍的精致程度也越來越高,流程相較之前更加煩瑣細致,包括:制紙、書法家謄抄、藝術家裝飾、裝訂、裝幀等流程。其中,裝飾是最工作量最復雜的一項,需要設計邊框、描繪題匾、插圖、鍍金、上光等。一部完整書籍的制作流程之復雜超乎常人的想象,制作插圖本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波斯細密畫的整個制作流程要大量紙張的支撐,可以說波斯細密畫的成熟與中國造紙術的傳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②
(三)中國畫院體制的傳入
伊爾汗在蒙古語中意為“臣屬汗”,即蒙古大汗的附庸,體現了伊爾汗王朝是元朝的附屬國,無論是君主冊封還是官員任命,都必須得到元朝政府的承認,因此伊爾汗國政治上與中國元朝保持著密切聯系。蒙古人建立伊爾汗王朝后,把中國的畫院體制帶入波斯,波斯細密畫屬于宮廷繪畫,為統治者服務,風格華麗細膩,雙方又以官方層面的交流為主,筆者認為波斯細密畫受到中國宮廷工筆畫的影響更為明顯,雖然宋元時期文人畫達到一個至高境界,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波斯人對文人畫的興致不高,學界很少把細密畫與文人畫作并論,因此不做討論。前文提到過伊爾汗王朝統治者——合贊汗(1271-1304年)非常尊重知識分子,重視文化建設,鼓勵發展科學文化,在位時期授意宰相拉施特建立一座藝術城,包括圖書館、畫院等等,招募國內外的文人名士、能工巧匠集中于此,進行文藝創作,培養了一大批職業畫家,當時很多中國居住在大不里士城當中,為波斯學習中國繪畫提供了極大可能。[4]到了帖木兒王朝沙哈魯在位時期,波斯文學藝術發展到新的高度,統治者大力扶植書法、繪畫、文學,在撒爾馬罕聚集了大量的藝術家,增進了中伊之間的文化交流,據史料記載:1387年拜松格曾向中國派出一個由文藝和科技人員組成的使團,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波斯宮廷對中國文化的重視。
畫匠們接觸到中國工筆畫后,把中國工筆畫山水、花鳥以及人物的暈染方法運用在波斯細密畫中,波斯細密畫因為融合了東方藝術而更具觀賞性,增加了其欣賞價值。波斯著名的民族史詩《列王紀》就是在該畫院繪制的(繪制于1330—1336年),多幅繪畫中都有中國宋元時期繪畫的影子。但中國元素的引入并沒有破壞波斯細密畫原有的特色和韻味,波斯的能工巧匠在保留波斯的民族風格的同時廣泛吸收外來文化,為我所用,成就了波斯細密畫在世界美術當中的獨特地位。
二、《列王紀》細密畫的藝術特色
(一)波斯細密畫與中國繪畫的區別
兩種繪畫的區別首先表現在空間意識上。雖然波斯細密畫與中國細密畫都不受焦點透視法的限制,但是二者還是存在很大的差異。公元651年阿拉伯消滅薩珊波斯帝國后,在波斯強行推行伊斯蘭教,隨著時間的推移,波斯人對于伊斯蘭教的態度由抗拒轉變為接受,波斯的文學藝術與宗教關系極為密切,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文學藝術是為宗教服務的。在波斯細密畫中為了體現宗教和世俗王權至高無上的地位,采用了45度的俯視視角,即真主阿拉的視角,波斯人認為真主阿拉是神通廣大無所不能的,可以不受時空的限制洞悉一切,即是一種全知性的視角,畫中所有事物都處于同一平面,沒有近大遠小,也無里外之分,一覽無余,極具裝飾性。③中國繪畫運用散點透視,即有多個焦點,視點流動,可以表現出萬里山河氣勢雄強之感,中國繪畫有近大遠小之分,運用墨色的濃淡來區分,且不是以全知視角描繪,更多的是畫家心靈情感的表達。
波斯細密畫的色彩極為艷麗豐富,首先波斯細密畫作為宮廷繪畫,由宮廷畫師所繪制,運用華麗的色彩彰顯統治者的權力、地位和財富。第二,細密畫在色彩上也遵循“崇高”之感,細密畫喜用藍色,藍色是由一種稀有礦石——天青石磨制得來的,色澤亮麗華貴,受到貴族的喜愛,藍色常被用于圣母以及一些神圣人物的衣袍上,以突出他們身份地位的尊貴,與西方油畫的精密刻畫不同,波斯細密畫多使用平涂的技法,在描繪花卉、樹葉、山巒時會用到漸變和過渡的手法,但不會給人以立體之感,總體上呈現平面性的裝飾效果。中國院體工筆花鳥畫致力于“真”,造型精密不茍,色彩細膩艷麗,運用極細致的線條和細膩的暈染,創造出生動逼真的藝術形象。
由于兩種繪畫都不是由寫生得來的,中國畫和波斯細密畫都很少表現“影子”,畫面當中沒有特定的光源,幾乎不表現黑夜,波斯細密畫即使是刻畫黑夜的場景也僅僅是用深藍色的天空和一彎明月等意象表示,整個場景看上去依然是明如白晝。波斯人把真主看成光,真主眼中的世界是不會有陰影的。
(二)《列王紀》細密畫中的中國元素
1.龍紋
龍在中國繪畫和波斯細密畫中所扮演的形象完全不同,在中國,龍是吉祥、權力的象征,而在波斯藝術中的龍卻總是以邪惡、兇狠的形象出現。中國龍的頻繁出現在波斯的建筑、繪畫和工藝品當中,巴格達城驅邪門的門拱上方以及波斯拉法朋大清真寺門上都有中國龍的形象。《列王紀》成書于波斯人民愛國情緒高漲的時期,書中故事多表現民族英雄的赫赫戰功,其中生動地描寫了皇帝巴赫拉姆·古爾的事跡,在細密畫中巴赫拉姆·古爾常以屠龍者的身份出現,現存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巴赫拉姆·古爾屠龍》當中(如圖1),這頭形似獅子的巨龍,身形肥碩,頭頂的角似鹿、四爪,身上有零散細碎的鱗片,龍嘴較長,巴赫拉姆左手持弓,右手拉弦,身騎戰馬,利劍刺進龍的脊背當中,這張畫中的龍形象更接近于中國唐宋時期龍的形象,尤其類似于應龍,蟠行狀,龍爪粗短,宋代的龍由唐朝的三爪演變為四爪,體態雖與中國龍接近,但氣質神情截然相反。波斯文學當中的龍一般充當反面形象,龍豐腴的體態是為了表現其貪婪殘暴的性情。

圖1 《巴赫拉姆·古爾屠龍》
類似于龍鳳的神獸意象在早期波斯文學中就已經存在,但由于古代伊朗宗教中的神靈形象都是抽象的,人們在描繪它們的時候需要從東方藝術范例中尋找合適的圖像,這時中國龍形象的傳入,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④波斯龍的形象可能是受到中國絲織物和瓷器等藝術形式的影響,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元代青花云龍紋梅瓶上的龍身修長蜿蜒,四肢較之前也更細長,全身遍布像魚一樣細密的鱗片,有鬃毛,《“野驢”巴赫拉姆五世殺龍》(如圖2)中的龍與元青花上的龍十分相近,由于頻繁的貿易往來,波斯工匠有非常多的機會能接觸到中國藝術,借鑒中國龍紋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圖2 《“野驢”巴赫拉姆五世殺龍》
2.云紋
云紋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紋樣之一,歷史悠久,文化內涵豐富,常被用在青銅器、瓷器、玉器上,一般作為輔助紋樣,與龍鳳、神仙等象征祥瑞的事物組合。其發展過程經歷了從夏商周時期的云雷紋、春秋戰國時期的卷云紋、漢代的云氣紋、魏晉南北朝的流云紋,唐宋時期的朵云紋,一直到元明清時期的如意云紋。在細密畫中云紋經常被作為填補空白的次要紋樣居于繪畫的邊角,沒有任何的象征意義。在《列王紀》細密畫中使用最多的是如意云紋,在《吉夫通過殺死塔扎夫為巴赫拉姆報仇》(如圖3)中畫面的左上角和右上角都使用了云紋,云頭呈如意形,云尾自然飄逸,勾線和暈染有明顯的裝飾意味[5]。
3.中國工筆畫技法
在蒙古伊利汗國統治時期,細密畫對中國工筆畫風是被動接受的,畫風和筆觸略顯生硬,隨著帖木兒帝國的建立及崛起,與中國的來往更加密切,宮廷甚至專門派遣使團來到中國,學習中國的宮廷繪畫,據文獻記載:蓋耶速丁率領使團回國之時,帶回了一些中國繪畫作品,據說波斯美術史上最偉大的畫家之一——畢扎德曾深受這批作品的影響。赫拉特畫派應運而生,此時波斯畫家對中國畫法的接受從被動逐漸轉為主動,更靈活地運用從中國畫師或中國繪畫作品當中學習來的技法,鄧惠伯在《中國繪畫橫向關系史——絲綢之路與東方繪畫》中寫道:“在赫拉特派的波斯細密畫作品中,有相當數量的與中國水墨畫風格類似的畫幅。其中用毛筆畫的完全是中國式的,畫家可能就是中國人,或是已經熟練掌握了中國水墨技法的波斯畫家”。⑤在這幅《塔赫穆拉斯擊敗了迪夫》(如圖4)當中馬的形象有宋元繪畫的影子,形象樸素自然,體態肥碩,馬頭細長,背景是中國式的,對山石的描繪明顯具有中國院體工筆畫的特征,陰凹處色彩濃重,陽凸處色彩較亮,與郭熙、李成等人的表現凹凸之感的手法相近,波斯畫家對中國山水畫技法的理解還停留在一個淺顯的層面,沒有中國畫多變的線條和皴法,僅僅在表現山石的凹凸方面有所借鑒。花卉、葉子和樹木也融入了中國繪畫的暈染技法,用極細的線條勾勒,填以重彩,如圖中的花卉,越靠近花蕊的地方顏色越深,到了邊緣處為白色,改變了過去呆板的畫風,中國技法的加入豐富了波斯繪畫的畫面風格。
三、結語
波斯在歷史上頻繁地改朝換代,但古代波斯并沒有被外來的文化所替代,而是有選擇地借鑒,奉行“拿來主義”,取其他文化之長處為我所用,與本土文化完美結合。波斯地處絲綢之路的要道,各種文化在這里交流交融交鋒,加上中國與波斯自古以來就有密切的交往,波斯細密畫受到中國繪畫的影響可以說是必然的,中國元素在波斯細密畫中被吸收、轉化為波斯本土化的形式,使波斯細密畫增加了自身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兩國文化在這一藝術形式當中都實現了突破和升華,形成了跨文化語境下各國文化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局面。
注釋:
①《列王紀》:伊朗文學巨著,從伊朗人的起源寫到651年薩珊王朝的滅亡,內容包括波斯始祖的早期神話傳說、波斯民族創造輝煌古文明的歷史以及波斯歷朝的功過得失,涉及內政外交、軍事征戰、宗教文化、民族關系和社會習俗等各個方面。
②穆宏燕.波斯古代的書籍制作與圖書館[J].讀書,2021(04),第118頁.
③孟昭毅.中古波斯細密畫與中國文化[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0(06),第59頁.
④弗拉基米爾·盧科寧、阿納托利·伊萬諾夫.波斯藝術[M],第18頁.
⑤鄧惠伯.中國繪畫橫向關系史——絲綢之路與東方繪畫[M]北京:商務印書館,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