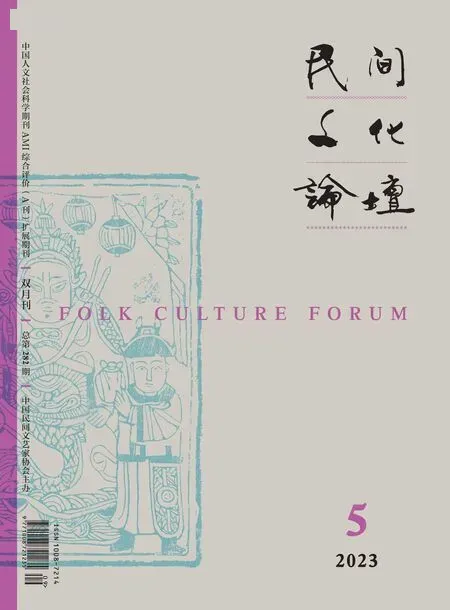從傳統(tǒng)到現代:建構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民間文學理論
呂 微 戶曉輝 黃永林 陳泳超 黃景春 毛巧暉
白話:日常生活的自由權利—— 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概念的先驗邏輯“正位論”
呂 微
我想結合李小玲先生的新著《二十世紀初民間文學研究及當代意義——以胡適民間文學理論為例》①李小玲:《二十世紀初中國白話文學研究及當代意義》,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進入我的討論。李小玲先生的新著受美國電影評論家漢森(Miriam Bratu Hansen)的啟發(fā),用Vernacular 這個詞翻譯胡適的“白話”,并承認漢森等人基于后現代性文化多樣性-相對主義立場將Vernacular 用作白話現象的直觀-描述性概念的正當性。我不知道當年胡適自己是否曾把“白話”譯作Vernacular,因此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李小玲先生,李小玲先生回信告訴我:胡適本人好像沒有過這樣的譯法。
胡適指稱“白話”用的最多的英文詞或詞組是spoken language,還有vulgate Chinese,也用過plain language,最后這個詞,他還在后面注明“白話”二字。胡適在《文藝復興》《中國文學革命》等文中頻繁使用vulgar language,vulgar tongue,vulgar dialect 等概念。別人介紹胡適的白話文學運動時會用到vernacular 這個詞,有文章就直接把胡適的白話明確指稱為vernacular……②李小玲2020 年10 月10 日給呂微的來信。
之所以援引李小玲先生的新著進入討論,是因為悥出Vernacular,的確反映了民間文學家們轉換“研究范式”以應對“學科的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的學術努力。將Vernacular 概念,作為直觀的描述性概念,用作電影評論、文學評論,進而引進民間文學研究中,英語學者發(fā)明于前,日語學者踵繼于后。陸薇薇《日本民俗學的vernacular 研究》一文“摘要”云:
將vernacular 這一概念導入民俗學研究是日本民俗學界的最新嘗試,以示與傳統(tǒng)民俗學研究的區(qū)別。vernacular一詞近年在西方的人文社科領域被廣泛運用,內涵得以拓展,已成為當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術語。日本民俗學對vernacular 概念的援引和闡發(fā),與其日常生活研究、公共民俗學研究、對抗霸權的民俗學研究等研究趨向密切相關,旨在拓展當下日本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并凝練出作為方法的vernacular。但與此同時,卻也存在對vernacular 中隱含的權力問題的忽略、與既有概念之間的調和[用“調節(jié)”這個詞更好,詳見下文——呂微注]等問題,需要我們更加深入且自反地加以探討。我們還需要重返中國民俗學的原點,重審白話文(vernacular)運動與中國民俗學生成的關聯,構建屬于中國民俗學的vernacular 論。③陸薇薇:《日本民俗學的vernacular 研究》,《民俗研究》,2022 年第3 期。
而李小玲先生新著的重點正在于通過胡適“重返中國民俗學的原點”,以“構建屬于中國民俗學[現代性普遍主義,而非后現代性文化多樣性相對主義]的vernacular 論”,這是李小玲先生新著的重要學術貢獻。
近二十年來,中國民間文學界重新“激活”學科傳統(tǒng)、經典的理論概念即“古典新用”的做法不乏其例——“激活”“古典新用”出自高丙中的提倡——“白話”即其中之一。我本人在與學界同人的對話中,也先后討論過“母題”“類型”“形態(tài)”“體裁”“過渡禮儀”“禮俗互動”“拉家”“家鄉(xiāng)”等原本就是學界耳熟能詳的理論概念或命題。所謂“理論”,在這里是沿用康德的用法,指經驗性認識論。而“實踐民俗學”的先驗范式提出之后,實踐論學者對于“激活”傳統(tǒng)經典,以“古典新用”的關切,可以表達如下:
傳統(tǒng)、經典的民間文學理論(經驗性認識論)概念、命題,是否(應該)以及能否(可以)轉換為實踐(先驗倫理學)概念、命題?
或者換個具體的說法:
如果實踐民俗學的目的是為學科前提重新做倫理學的先驗奠基,那么,在重新確立了民間文學的倫理學前提的先驗學術語境條件下,像vernacular 這樣的傳統(tǒng)、經典性概念、命題,是否或者能否被繼續(xù)正當(合理、合法)、有效地用作有先驗根據的、直觀地描述民間文學現象的經驗性概念或命題?
回答應該(應當)也能夠(可以)是肯定的。
我在《“過渡禮儀”理論概念與實踐模型的描述與建構——對話張舉文:民俗學經典理論概念的實踐使用》①呂微:《“過渡禮儀”理論概念與實踐模型的描述與建構——對話張舉文:民俗學經典理論概念的實踐使用》,《民間文化論壇》,2016 年第1 期。一文中,通過改造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只有規(guī)定性邏輯序列沒有反思性邏輯序列)“正位論”和康德的先驗邏輯(只有時間邏輯序列沒有價值邏輯序列)“正位論”,排列了一個先驗邏輯(既有規(guī)定性也有反思性的時間-價值雙重邏輯序列)正位論“生活-實踐模型”圖式,用以直觀地闡明我的上述想法。所謂概念的“正位論”,就是把概念置于諸概念間的邏輯關系中,以確定概念在不同的(時間或價值的)邏輯關系中所可能發(fā)揮的不同功能(通過邏輯定位而為概念定性)。

在上面這個圖式中,有兩條邏輯軸線。一條是橫線的時間邏輯軸,站在時間邏輯軸線中看,“婚禮中的某儀式”是“婚禮日”儀式在時間中的原因(工具、手段)即經驗性條件,“婚禮日”儀式是整個“婚禮進程”“結婚禮儀”的經驗性原因條件,而整個“婚禮進程”“結婚禮儀”又是全部“人生禮儀”的經驗性原因條件;反過來說,后者是前者的經驗性結果。換句話說,惟當你在時間中依次走完了“婚禮中的某儀式”、“婚禮日”儀式、整個“婚禮進程”“結婚禮儀”(例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全部過程,抵達了時間終點,你才可能依次(從前往后地)“手段(工具)性”地成全全部“人生禮儀”的經驗性時間結果。在時間中看,生活的具體目標與人生的總體目標之間的手段(工具)-目的性關系是:從局部(經驗性的過去和現在)到整體(經驗性的未來)。
另一條是縱線的價值邏輯軸,從價值邏輯軸線上看,原因和結果的關系恰恰相反,全部“人生禮儀”是整個“婚禮進程”“結婚禮儀”在價值上的原因(理由)即先驗條件,整個“婚禮進程”“結婚禮儀”是“婚禮日”儀式的經驗-準先驗原因條件,而“婚禮日”儀式又是“婚禮中的某儀式”的經驗-準先驗原因條件。換句話說,唯當你在價值上反思地還原到全部“人生禮儀”的價值邏輯起點,你才能逐層(自上而下地)達成整個“婚禮進程”“結婚禮儀”“婚禮日”儀式、“婚禮中的某儀式”的先驗價值結果。從價值上看,人生的總體目標與生活的具體目標之間的關系是:從整體(先驗的未來)到局部(經驗性的現在和過去)。
這樣,我們就通過雙重邏輯軸線——時間邏輯軸線、價值邏輯軸線——將全部“人生禮儀”中的“婚禮中的某儀式”“婚禮日”“婚禮進程”“結婚禮儀”,安排進一個雙重的整體或總體性邏輯關系當中,并且為人生、生活的每一步驟、每一層次安排了具體的時間與價值邏輯的坐標位置。這就是民間文學理論概念(命題)與實踐理念(命題)的先驗邏輯正位論,這樣一個(改造了亞里士多德式、康德式邏輯正位論)的雙重先驗邏輯正位論,將為民間文學理論概念、命題的理論和實踐的正確、準確使用提供一個先驗反思的直觀闡明,以助力于“防止純粹知性受到欺騙及由此產生的錯覺”即理論和實踐概念、命題的理性誤用,“因為[理性]它任何時候都要分辨出這些概念真正屬于何種認識能力[理論認識能力或實踐認識能力]”。①[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41—242 頁。
人生的全部(整體、總體)生活過程——包括在時間中從經驗性原因(工具或手段)到經驗性結果(目的)的生活,以及在價值上從先驗原因(理由)到經驗性結果(存在)的實踐——就如“過渡禮儀的經驗性目的-手段論生活與先驗理由-存在論實踐模型”所顯示的,可類比為一部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推論(“類比”是因為前者已不同于后者)。不同的是,正如以上已指出的,在先驗邏輯的“三段論”推論中,不僅有從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結論的規(guī)定,而且有從結論到小前提再到大前提的反思——在“生活-實踐模型”圖式中,每條軸線的端點都有一個箭頭,分別代表“順推”的規(guī)定性和“逆推”的反思性——后者是傳統(tǒng)的、經典的形式邏輯所不具備的。
這就是說,站在先驗邏輯的立場上看,無論對于時間邏輯軸線,還是對于價值邏輯軸線來說,推論都首先(邏輯上的“首先”)從結論還原到小前提再還原到大前提,然后(邏輯上的“然后”),再用大前提規(guī)定小前提進而規(guī)定結論。借用康德的話說,前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從后往前的“逆推”和從前往后的“順推”;后者,我們可以稱之為自下而上(“上升”)的“逆推”和自上而下(“下降”)的“順推”。在形式邏輯中,只有單向的規(guī)定性“順推”沒有反思性的“逆推”(例如亞里士多德式的邏輯正位論),而在先驗邏輯(無論時間邏輯還是價值邏輯)中,推論是雙向的,“順推”在邏輯上依賴于“逆推”。而后現代性的邏輯正位論(如果有的話),在極大程度上(同于亞里士多德式的邏輯正位論),淡化并且取消了邏輯正位論的先驗反思維度,甚至剔除了價值邏輯序列而僅僅保留時間邏輯序列),從而拒絕了價值邏輯序列的自由第一因——作為“普遍規(guī)則”(康德)——對時間邏輯序列的價值規(guī)定。
在時間邏輯序列的自然因果性推論中,一部具體的三段論中的大前提已經是一個普遍性真理,從這個普遍性真理(“普遍規(guī)則”)出發(fā),我們才有可能“順推”地規(guī)定(構成、建構)小前提和結論的普遍真理性。但是,這部三段論的大前提又是在它之前的一部三段論“順推”的結論,而那部三段論推論的大前提更是在它之前的一部三段論“順推”的結論……以至無窮。所以在時間邏輯序列的自然因果性推論中,只有相對的經驗性大前提,如果我們要還原出自然因果性推論中絕對的先驗大前提,即自然因果性的自由第一因,那我們只能訴諸于“無窮”“無限”這樣的整體性、總體性理念(沒有經驗性對象的概念),或者,就設定作為自由創(chuàng)始者或創(chuàng)世者的上帝;在設定了這樣自然因果性時間邏輯序列的整體性、總體性理念之后,我們才可以假定,在時間邏輯的上升序列中的所有環(huán)節(jié)都已經被給予,因而各個環(huán)節(jié)(無論作為大前提還是作為小前提)都具有完成的真理性(這決定了每一次邏輯推論的大前提的普遍真理性)。當然,在時間中的經驗性“順推”中,“無限”“無窮”“上帝”等整體性、總體性理念并不在諸“下降”序列中直接參與規(guī)定的構成性或建構性推論,只是作為反思的理念發(fā)揮調節(jié)性或引導性(范導性)作用。就像一些自然科學家那樣,他們一方面從事著經驗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又堅持著超驗的宗教信仰;而他們對上帝的信仰,雖然并不參與具體的科學研究,卻能夠為科學地研究具體的自然——這本“上帝之書”——提供了調節(jié)性或引導性(范導性)的超驗推動力。
與時間邏輯序列中的自然因果性推論不同,在價值邏輯序列上的自由因果性推論中,自由第一因并不需要訴諸“無窮”“無限”“上帝”等總體性、整體性理念,即,到人之外去尋找自由第一因,而是在人自身之內,就可以找到這樣的自由第一因。而人之內的自由第一因,就是人自身先天地擁有的自由意志及其自我立法的道德法則,而道德法則正構成了人生價值的總體性、整體性實踐目標。在人生禮儀的整體性、總體性價值實踐中,自由、道德盡管都是超驗的理念,對人生價值的具體實踐來說,卻不僅僅是間接的調節(jié)性、引導性(范導性)理念,而往往就是直接構成、建構的規(guī)定性概念。換句話說,人生禮儀的每一步驟、每一層次的價值實踐,都被人生價值的終極目標的道德法則所直接地規(guī)定——“規(guī)定”有兩個意思,一是對應該(應當)合于(甚至出于)道德的強制規(guī)定,二是對“并非不道德”的“允許”規(guī)定——只有在時間邏輯序列的準自然-社會因果性生活中,體現總體性、整體性人生價值的終極目的的道德法則,才好像僅僅是間接(隱蔽)地發(fā)揮著引導性(范導性)、調節(jié)性的作用,就像我們在“生活-實踐模型”中直觀地看到的那樣,只要我們把生活的時間邏輯序列與實踐的價值邏輯序列合縱連橫。但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在社會因果性的時間邏輯序列中,同樣,在對社會因果性的經驗性研究中,價值邏輯序列的總體性、整體性的自由理念,盡管沒有直接地發(fā)揮著規(guī)定性(構成性、建構性)作用,但仍然有間接地發(fā)揮的反思性(調節(jié)性、引導性或范導性)作用。
我曾援引高丙中對文化遺留物經驗性研究的先后不同評價,闡明非道德、非價值的經驗性研究隱秘的道德、價值基礎。文化遺留物研究,是一種經驗性研究,作為社會科學研究,自身在客觀上并不一定就帶有多少正、反面的價值判斷、道德評估;盡管“遺留物”作為社會因果性時間邏輯序列中的存在物,在主觀上還是可能多少帶有一點負面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評估的意思。這就是說,社會科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一個道德因果性的自由第一因,或者在社會批判、文化批判的實踐論研究中,直接地發(fā)揮著規(guī)定性的構成、建構作用,或者在看似價值中立、道德無涉的認識論研究中,通過反思而間接地發(fā)揮著引導(范導)性、調節(jié)性作用,就像顧頡剛對孟姜女故事的歷史系統(tǒng)、地理系統(tǒng)梳理,以及袁珂對中國神話的體系復原,看似道德中立、價值無涉,其實前者關乎反抗傳統(tǒng)社會、建設現代共同體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后者關乎建設現代共同體的文化意識形態(tài)。白話也是一樣,當年胡適提出的“八不主義”并不僅僅是為白話本身(作為自然因果性邏輯序列的一環(huán))而吶喊;胡適為白話吶喊,也就是為老百姓、普通人盡管凡俗卻也是由自由第一因(道德法則)所規(guī)定的口語表達的自由權利吶喊,進而也就是為我們每一個人或所有的人爭取、捍衛(wèi)自由、平等、安全(不受脅迫)地過正常的“小日子”的日常生活的普遍權利。所以,白話不僅僅是自然手段,更是自由價值的目的本身。
我的“八不主義”,是單從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著想的。……把這“八不主義”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氣,又總結作四條,如下: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
二,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么時代的人,說什么時代的話。①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第40—41 頁。
這就是說,道德法則作為價值邏輯序列的整體性、總體性自由第一因,始終引導(范導)、調節(jié)著研究者研究成果的價值、道德取向。激進地說,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服務于某種意識形態(tài),那種認為存在著價值中立、道德無涉的社會科學研究(更遑論人文科學研究),只是經驗論者思想中的認識論“錯覺”(見上引康德文),就像我們構擬的“生活-實踐模型”,必然(不僅應然而且實然地)是雙重的時間-價值邏輯軸線,而不可能僅僅是單重的時間邏輯軸線。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諸如“母題”“類型”“形態(tài)”“體裁”“過渡禮儀”“禮俗互動”“拉家”“白話”“家鄉(xiāng)”等等民間文學理論研究傳統(tǒng)的、經典的經驗性概念、命題,在面對“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的學術語境條件下,或者作為認識論研究或者作為實踐論研究的“中層”或“中間”概念予以應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盡管在某一項具體研究中,這些概念、命題可以被臨時地用作總體性、整體性直觀描述的概念、命題——就像英語、日語學者的做法——但借助上文“生活-實踐模型”的提示,即便不是受實踐研究先驗理念的直接規(guī)定,也實際上受實踐研究的先驗理念的間接規(guī)定,即實踐理念的調節(jié)、引導(范導)下的“中層”或“中間”概念或命題,因為它們不僅在社會因果性時間邏輯序列的經驗性研究中處于中間階段,在自由因果性價值邏輯序列的先驗研究中也處在中層位置,作為尚未被總體性、整體性自由因果性的普遍性條件所規(guī)定(構成、建構)的對象——無論作為大前提還是作為小前提——都需要自由第一因的道德法則反思性規(guī)定,即便不是直接的規(guī)定,也應該是間接的規(guī)定即接受自由第一因道德法則的引導(范導)性調節(jié)。而這就是我們民間文學在面臨“發(fā)展機遇與挑戰(zhàn)”的時候,無論是經驗認識論范式流派的理論研究者,還是先驗價值論范式流派的實踐研究者,都應該是——至少就學科整體而言——自覺地牢記于心、操作于手的必修課。以此,我們與其被動地、不自覺地服務于未經反思性、批判性檢驗的意識形態(tài),不如主動地、自覺地服務于已經受了反思性、批判性檢驗的意識形態(tài),以提升我們學科的總體或整體以及我們每一位學者、學人具體的研究方向與研究方式的正當性(合理性與合法性)與有效性。因為前車之鑒,實為后事之師。
民間文學:為自由而生的文學形式
戶曉輝
首先祝賀李小玲教授新著《二十世紀初白話文學研究及當代意義》順利問世!該書的獨到研究指出,既然胡適的“白話文學這一概念從提出伊始就是兼顧語言和文學、價值主體和學術主體的雙重考慮的”,那么,“我們對胡適有關民間文學的理解就不能僅局限于文學的范疇,還應該將其納入到哲學的考辨當中,而關于哲學的問題首先是解決人的問題”。①李小玲:《二十世紀初白話文學研究及當代意義》,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12 頁、第86 頁。此項研究和我自己的一點研究②戶曉輝:《發(fā)端于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研究——以胡適與康德、杜威的僑易關系為例》,《民間文化論壇》,2022 年第1 期。都可以表明,從胡適當年的留學經歷、選課內容以及受到康德、杜威思想影響的事實來看,胡適絕非只是“技術男”。
進而言之,胡適以及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研究從一開始就是有理念、有理想的,不是單純追求實用技術。現代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源于一個大覺醒、大覺悟,源于一個驚鴻一瞥,這種大覺醒、大覺悟和驚鴻一瞥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民間文學自由屬性的猛然覺悟。1924 年,北京大學歌謠研究會出版了董作賓編的《看見她》,其中匯集全國各地以“去丈人家看見未婚妻”為主題的45 首歌謠。有人說,在《看見她》中,看見的不僅僅是“隔著門簾的她”,也不僅僅是“非她不娶的他”,更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他——董作賓先生。我要說,《看見她》中的“她”又何嘗不是民間文學或白話文學的象征呢?中國現代學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驀然回首,由此在歷史和現實的燈火闌珊處看到并發(fā)現白話文學或民間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家隱隱約約、有先有后、不約而同地覺識到:民間文學是一種為自由而生的文學形式。可以說,由胡適擴展開去,還有周作人、劉半農、顧頡剛、董作賓等一批現代民間文學研究者。他們之所以能夠看見民間文學或白話文學這個“她”,甚至不僅僅是看見,更是重新發(fā)現、重新開辟出嶄新的、前所未有的甚至開天辟地的這個“她”,恰恰因為他們看出民間文學或白話文學這個“她”負載著自由的理念。盡管這種理念在經驗現象上時隱時現,尤其在理論上不夠明確、不夠清晰、不夠深刻,但這恰恰是需要我們后人不斷回首并深入開掘的根本問題。
對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朝戈金先生和徐新建先生在發(fā)言中都提到“民間”的自我邊緣化問題以及是否還要繼續(xù)使用這種非官方、底層社會意義上的“民間文學”概念問題。雖然現代民間文學學者已經為“民眾說了算”做出自己的貢獻,但我們仍需繼續(xù)努力。正因如此,我在《民間文學的自由敘事》一書中指出:
盡管有人會認為,“民間文學”概念在中國的繼續(xù)使用表明我們落后于世界學術潮流,但我認為,這并非問題的根本所在。因為真正的問題意識并不取決于是否趕得上時髦的風潮,也不表現為中外優(yōu)劣之爭,而是來自問題本身。“民間文學”這個概念在中國沒有過時,恰恰表明它的內涵還沒有被耗盡,它在中國還有未了的心愿(假如真有“了”的那么一天的話),它仍然是現代精神的一個未完成的方案。既然中國仍在使用“民間文學”這個概念,仍然需要“民間文學”的理論,這就表明,“民間文學”的深層含義和內在目的仍然沒有被搞清楚,甚至可能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開掘和深入的領會。③戶曉輝:《民間文學的自由敘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第9—10 頁。
呂微先生在給拙書寫的“序”中也進一步指出:
所以,不僅不拋棄、不放棄“民間文學”的說法,而且還延續(xù)傳統(tǒng)的、經典的“民間文學”的用法,這首先是一個中國問題,當然,也是一個世界問題,只是我們的國外同行們還不曾站在folklore 自身內在的實踐目的及承載了folklore 的內在目的的民間文學的純粹實踐形式的立場上,思考folklore 的客觀價值;而只是根據其外在目的,僅僅考慮了其主觀的使用價值(曾服務于政治角色認同的實用功能),于是才導致了folklore 的使用價值(實用功能)即外在目的(主觀性內涵)已被耗盡(以此才應該通過更名而服務于文化身份認同等新的外在目的、使用價值或實用功能)的理論認識。其實,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各國,folklore-民間文學的價值(純粹意義),即其內在目的(客觀性內涵)都還遠遠沒有被耗盡,也永遠不會被耗盡,不僅在中國,民間文學的內在目的,仍然是“現代精神的一個未完成的方案”; 而且在世界上,也永遠是人類精神的一個“將來完成時”的指南,因為民間文學的內在目的,實在就是人作為自由主體而存在、實踐或生活的根本原則或“邏輯前提”。①呂微:《接續(xù)民間文學的偉大傳統(tǒng)——從實踐民俗學的內容目的論到形式目的論》,載戶曉輝《民間文學的自由敘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序”第3—4 頁。
回到現代民間文學研究的發(fā)端時期,如果沒有內在能力與潛在的可能性,現代歌謠、白話文學或民間文學能夠被委以重任呢?在我看來,民間文學之所以能夠擔起重任,恰恰因為這個重任并非從外在方面強加的外在價值,而是民間文學自身先天就具有并且能夠具有的內在價值。相比而言,當年民間文學的重任可能主要是拓展經驗認識,現在民間文學的重任則是開辟新的先驗實踐。實踐民俗學試圖推進的是從先驗的存在論層面證明:民間文學本來就是由自由而生、為“我們”的自由聽說而生的文學形式,這就從根本上突破了民間與官方、雅與俗、口頭與書面等一系列經驗對立和現實對立,由此論證民間文學是與人類普遍的自由存在方式密切相關的文學形式。也可以說,作為人類自由存在形式的民間文學為民間與官方、雅與俗、口頭與書面等一系列經驗對立和現實對立確立了普遍前提、超越維度、先驗基礎和根本原則。這樣一來,民間與官方、雅與俗、口頭與書面等一系列經驗對立和現實對立就不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而且才有了實踐上所必須的理性目的與普遍尺度。謝林的神話哲學②F. W. J. Schelling, 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 Nachschrift der letzten Münchener Vorlesungen 1841, Stuttgart-Bad Cannstatt:fromann-holzboog, 1996;[德]《神話哲學之歷史批判導論》,吳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戶曉輝:《謝林神話哲學的先驗人類學主場》,《廣西民族大學版》(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4 期。、卡西爾的象征形式哲學③Ernst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Zweiter Teil.Das mythische Denken,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GmbH,2010;戶曉輝:《卡西爾與神話的批判現象學》,《民族文學研究》,2009 年第3 期;戶曉輝:《神話的象征形式及其精神限度》,《民族文學研究》,2023 年第4 期。、葉舒憲的玉教神話信仰研究④葉舒憲:《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 年;戶曉輝:《玉教的理想類型及其合理化問題——對葉舒憲〈玉石神話信仰與華夏精神〉的韋伯式解讀》,《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 年第6 期;戶曉輝:《四重證據法的文化科學方法論基礎》,《社會科學家》,2022 年第3 期。、呂微的實踐神話學研究⑤呂微:《回到神話本身的神話學——神話學的民俗學現象學—先驗論革命》,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 年;戶曉輝:《神話原型結構的實踐民俗學闡釋》,《民俗研究》,2023 年第4 期。以及呂蒂的童話研究⑥[瑞士]麥克斯·呂蒂:《歐洲民間童話:形式與本質》,戶曉輝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8 年。都是這方面的重要貢獻。我在《民間文學的自由敘事》一書中做了一點闡述工作⑦戶曉輝:《民間文學的自由敘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年。,剛剛完成的一本小書《神話形式的還原之路》,也希望以神話為例來表明:民間文學在存在本原上、在先驗根子上就內在地是為自由而生的文學形式,它并非人為地、外在地被委以重任,而是內在地就是為自由而生的文學形式,只不過這種重任需要我們從哲學上、從理論上去深挖、細描和實踐。
由此可以看出,不是我們搞啥啥重要,而是啥重要我們搞啥。我們不能僅僅以其他學科的價值為價值,因為它們的價值也往往是相對的、特殊的價值,因為所有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都需要以普遍的人性價值為共同價值和共同前提。在缺乏共同價值和共同前提的情況下把學科價值問題相對化、主觀化、后現代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普遍的價值標準而自說自話甚至自娛自樂,這是中國許多學科產生無效討論、虛假討論和浪費討論的根本原因。在這方面,中國民間文學或民俗學絕非做得最差的學科。多年前,在一次會議發(fā)言中,有一位所謂的大咖質疑說:人文科學為什么要研究人?當時差點讓我驚掉下巴。人文學科如果不研究人,那豈非咄咄怪事?邏輯上講得通嗎?而要研究人,那就必然涉及人觀以及三觀(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也就必然需要價值判斷。我們尤其需要警惕學界把馬克斯·韋伯的“wertfrei”(字面意思相當于英語value free)誤解為“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所帶來的危害。正如顧忠華先生所指出:
由20 世紀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來看,一直存在著對于韋伯“價值自由命題”(Postulat der Wertfreiheit)的重大誤解,基于翻譯及詮釋上的問題,此一命題常被“簡略化”、“庸俗化”與“極端化”,譬如Wertfreiheit 或wertfrei 由德文直譯成英文乃value free,因此中譯原本就應為“價值自由”,但或許考慮到主詞指涉不清楚,所以通常被譯成“價值中立”,只是這樣一來,經常讓人理解為科學的“去價值化”,好像科學家一定要對任何公共議題“保持中立”,甚至流弊所及,似乎在鼓勵一種“鄉(xiāng)愿”的態(tài)度。至于譯作“價值無涉”,則更強化社會科學必須與任何價值切割關系,才能維持知識上的“純潔”“客觀”。事實上,這兩種主張皆限縮了社會科學研究應該爭取更大自由條件的意義。①顧忠華:《韋伯學說的當代詮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年,第186 頁、第189 頁、第196 頁。
因此,“價值自由”恰恰說的是,我們做學術研究需要探尋研究對象自身的客觀價值和人文學術自身的內在學理,需要知曉人類的普遍價值尺度并且把各種特殊價值放在人類普遍價值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以此做出客觀的價值判斷,盡可能減少主觀臆測式的價值判斷。正如邏輯、數學、物理、化學是全人類通用的和普遍的一樣,人之為人和人之做人也有通用的和普遍的價值尺度。只有先了解普遍尺度,才能判斷某個研究對象或問題是否特殊以及如何特殊,因而在學理上普遍性優(yōu)先于特殊性。同樣,要對研究對象或問題做出價值判斷,那就不能僅僅依據學科標準、地方標準和各種各樣的特殊標準,而是需要以內在的、客觀的價值標準和普遍的學術通則來衡量所有學科的特殊價值。韋伯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基本區(qū)分,大致對應于康德對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區(qū)分。在中國,不缺對工具理性的引進和討論,但對價值理性的理解、接受和傳播不是多了,而是非常不夠,這是常常被我們視而不見的一頭“房間里的大象”。正因如此,有不少中國學者在反思和反對工具理性的無限膨脹時沒有看到價值理性的存在及其必要性,而是一味地反理性。“這正是當代中國啟蒙者的歷史錯位。我們還沒有進入到啟蒙的歷史過程,就已經‘超越’啟蒙了。……后現代反理性的理性精神是我們這些根本還未建立起理性法則來的‘反思啟蒙’的人所不具備的,我們不敢于懷疑一切,不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性,卻裝出不屑于運用理性的樣子,這是典型的阿Q。”②鄧曉芒:《啟蒙的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 年,第39 頁。結果是在一個本來就缺乏價值理性的地方反而加重了對價值理性的無知無畏程度,甚至延續(xù)并助長了生活現實中混亂不堪的非理性局面。實踐民俗學恰恰試圖在這方面做一點補救工作。
剛才,安德明先生和江帆先生提到了講故事的本原性,林繼富先生提出作為本體的民間文學,還有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從一開始就關注到的民間歌謠,都可以從人類存在的本原層次來加以理解和證明。當然,這種理解和證明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長期的研究和實踐,并且首先需要方法論上的根本轉變。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曾引用哲學家梅洛·龐蒂的觀點說,每當人類學家回到他的知識的活的源頭之時,就會自發(fā)地進行哲學思考。列維—斯特勞斯不僅贊同這個看法,而且認為這是人類學家應做之事。①參見Sebastian Luft, “The A Priori of Culture:Philosophy of Culture Between Rationalism and Relativism.The Example of Lévi-Strauss'Structural Anthropology,”J. Tyler Friedman and Sebastian Luft eds.,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A Novel Assessment, 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5, pp.393-395。在我看來,這又何嘗不是民間文學、民俗學研究者的分內之事呢?這不是由個人愛好決定的,而是由問題性質的客觀需要決定的。因為人的存在及其意義問題以及包括民間文學在內的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需要思考和面對的許多問題,都不僅僅是形式邏輯就能解決,而是需要先驗邏輯才能對路和勝任。我們不僅要眼光向下,還要眼光向上,因為民間文學關涉的問題本來就不僅僅在形而下層次,還有形而上層面,正如我們不能一直回避和忽視由糟糕的三觀所導致的社會苦難和學科災難一樣,我們還需要重新思考學科的三觀問題,當此之時,只有民間文學的學科知識就不夠用了。為了思考這樣的問題,我們需要采用先驗邏輯的演繹法。謝林、卡西爾、葉舒憲、呂微研究神話以及呂蒂研究童話所采用的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經驗歸納法,而主要是演繹推論法,因而具有邏輯上的可辯駁性與可證偽性。正如謝林所說,“不先有先驗思維方法,就會感到無法理解先驗哲學。因此人們一開始就自由地置身于掌握先驗思維方法,這是很必要的。”②[德]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梁志學、石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第39 頁。單純從認識方式上來看,如果說我們通常習慣的經驗思維方式是以小見大、見微知著,那么,以理智直觀為代表的先驗思維方法則恰好相反,也就是以大見小、知著見微,是由普遍性、一般性推論出特殊性與個別性。用呂微先生發(fā)言的話來說就是,從先驗的未來看經驗的現在和過去,從經驗中看不到的絕對起點和絕對前提出發(fā)。我們知道,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中見到的許多論述和觀點都具有主觀性和偶然性,大多依靠悟性,甚至可以耍小聰明和抖機靈,即便我們有不同看法,也難以反駁和證偽,容易自說自話。但演繹推論法卻能夠清晰地向我們展示出論證的前提和步驟,讓我們能夠隨時隨地檢查其邏輯前提和論證步驟是否成立、是否有問題。在我看來,這種邏輯論證和先驗推論是我們中國學者所不習慣、不擅長的思維方式,只不過這種思維方式并非可有可無,而是進行哲學思辨和理論研究所必須的思維方式,因而值得年輕學子下功夫去學習。
正因為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研究在發(fā)端時肩負著文藝的和學術的雙重使命,所以從一開始才能吸引一批優(yōu)秀學者入行研究。中國現代學者能夠成功地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讓白話文學或民間文學成為國語文學,這種由觀念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可謂中國現實的“山鄉(xiāng)巨變”,也是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在中國歷史上的華麗轉身、在中國現實中的閃亮登場。當代以及未來的中國民間文學研究能否吸引優(yōu)秀學者參與研究并且能否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有所貢獻,取決于我們能否證明:民間文學堪當重任,而不是社會生活可有可無的點綴或犄角旮旯里的邊角料。也可以說,民間文學能夠在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生存中發(fā)揮怎樣的大任,取決于我們作為研究者能夠從民間文學身上看出怎樣的大任,能夠讓這種大任發(fā)揮到什么程度。民間文學學科的未來從內在方面取決于我們如何理解、如何實踐民間文學自身的自由潛力。
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機遇、挑戰(zhàn)與未來
黃永林*
民間文學是人民群眾自己創(chuàng)作、傳承和享受的文學,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活動形式,具有區(qū)別于作家文學的獨特文學性與審美性。民間文學既是一種文藝現象,更是一種文化生活,深深植根于人民群眾生活土壤。作為一門學科,民間文學主要是研究民間文學的范圍、特質、價值及其流傳、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探討作品的思想內容、藝術形式與社會功能等的學問。近年來,國家大力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積極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構建,這為新時期民間文學的保護和學科發(fā)展帶來了機遇與挑戰(zhàn)。本文在分析這種機遇與挑戰(zhàn)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未來走向。
一、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的機遇與挑戰(zhàn)
近些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更加重視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大力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積極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這為中國民間文學學科提供了難得的發(fā)展機遇。
(一)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提升了民間文學保護意識
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各級黨委和政府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開展了一系列富有創(chuàng)新、很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增強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凝聚力、影響力、創(chuàng)造力。
2021 年12 月14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提出,“要重視發(fā)展民族化的藝術內容和形式,繼承發(fā)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tǒng),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①習近平:《展示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交出版社,2022 年,第326 頁。2022 年10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17、45—46 頁。這為全社會提高對民間文學的認識提供了思想武器,為民間文學學科的發(fā)展指明了根本方向。
2017 年1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燦爛輝煌。在5000 多年文明發(fā)展中孕育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豐厚滋養(yǎng),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是當代中國發(fā)展的突出優(yōu)勢,對延續(xù)和發(fā)展中華文明、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發(fā)揮著重要作用。”①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2017 年第6 號國務院公報),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7/content_5171322.htm?eqid=a73b38a9000b351500000004645608b6, 2017 年1月25 日;瀏覽日期:2023 年2 月6 日。由此提出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2022 年8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十四五”文化發(fā)展規(guī)劃》提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持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深入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扶持民族民間文化整理研究。”②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十四五”文化發(fā)展規(guī)劃》,中國政府網,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eqid=98f194c400000c7b00000002646b1a8a,發(fā)布日期:2022 年8 月16 日;瀏覽日期:2022 年10 月5 日。這些文件為民間文學的保護傳承提供了政策依據和行動指南。
我國各民族民間文學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和基石。在上述背景下,我國啟動了“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出版工程”和“中國民間工藝傳承傳播工程”,這兩大工程“文”“藝”并舉,相輔相成,旨在為中華民族保留彌足珍貴的文化記憶。與此同時,民間文藝進校園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民間文學數字化工程進展迅速,民間文藝數字化博物館建設成效顯著,民間藝術家得到大力扶持,民間文藝之鄉(xiāng)成為地方文化繁榮的亮點,這些民間文藝的實踐活動和成果洋溢著新時代的濃郁氣息,全面而又生動地呈現出新時代的嶄新面貌。③邱運華:《民間文藝繁榮發(fā)展 譜寫新篇開創(chuàng)未來——中國民間文藝十年》,《中國藝術報》,2022 年10 月18 日。這些工程和活動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提供了動力,為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和實踐基礎。
(二)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促進了民間文學保護工作的開展
2004 年,中國政府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在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下,我國下發(fā)了《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等文件,明確了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目標、任務和要求。201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頒布實施,為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奠定了堅實法律基礎。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又相繼印發(fā)了《“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guī)劃》和《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等文件,為做好新時代非遺保護工作指明了目標方向。與此同時,文化和旅游部印發(fā)了一系列文件,如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認定和管理辦法、國家級文化生態(tài)保護區(qū)管理辦法,聯合中宣部、財政部印發(fā)非遺傳承發(fā)展工程實施方案,聯合財政部出臺非遺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等等,逐步健全配套政策,搭建起非遺保護傳承法規(guī)體系的主體框架,有力推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截至2022年底,我國認定各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十萬余項、各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九萬多人,其中包括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5 批1557 項、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5 批3068 人(現為3057 人)。共有昆曲、中醫(yī)針灸、太極拳等43 個項目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名冊,總量居世界第一。新世紀,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推動下,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在中國非遺名錄中,民間文學被列為第一類,成為非遺重點保護的對象。在已公布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民間文學類有 251 個項目;在已公布的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錄中,民間文學類有123 人。在非遺活態(tài)化保護的大背景下,民間文學回到生活中活態(tài)傳承,為民間文學提供了最理想的保護方式。這些對助推中國民間文學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客觀上也促進了民間文學學科的建設。
(三)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推動了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放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2016 年5 月17 日,習近平總書記專門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他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①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6 年5 月17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15 頁。2017 年5 月,中共中央印發(fā)了《關于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對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作出全面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深入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培育壯大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②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43—44 頁。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文學, 在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背景下,在學術研究和學科發(fā)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民間文學理論研究方面,發(fā)表了一大批影響較大的理論著作和論文,在民間文學史、神話學、故事學、史詩學、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等領域,涌現了一批原創(chuàng)性成果;創(chuàng)辦了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術雜志。在研究生學位點建設方面,不少學校堅守民間文學學科,在不同的大學科下,自主設立了民間文學碩士、博士研究生點,培養(yǎng)了一大批民間文學研究生。部分學校的民間文學學科還成為國家級和省部級重點學科和重點研究基地。在民間文學學術隊伍建設方面,初步形成了一批老中青結合的學術團隊。在民間文學課程設置方面,形成了從本科生到研究生的比較完備的民間文學課程體系,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民間文學教材。
二、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的危機與出路
(一)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的兩次沖擊
第一次沖擊發(fā)生在20 世紀末,我國學科專業(yè)目錄的調整導致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陷入困境。“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原本是“文學”門類“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的二級學科,但1997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發(fā)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yǎng)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將“中國民間文學”調整到“民俗學(含中國民間文學)”中,歸入“法學”門類“社會學”一級學科中,與社會學、人口學、人類學并列為二級學科。一方面,由于“中國民間文學”調出“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體系,當時不少原已在文學院(系)設置的“民間文學”學科及相關隊伍被迫調整到社會學的“民俗學”中,盡管少數學校因對民間“文學性”的堅守勉強將“民間文學”專業(yè)留在文學院(系),由于在現行的學科、專業(yè)目錄中,中國文學已有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課程體系,民間文學被視為特殊專業(yè)而成為被“照顧”的對象,實際上是被邊緣化了。而轉到“民俗學”后的“中國民間文學”專業(yè),由于研究的主體內容和學科研究范式的差異和非主流“小學科”,也淪為依附的地位。這是民間文學學科發(fā)展面臨的第一次危機。
第二次沖擊源自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開展。如前所述,從21 世紀初開始,由于我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在政府強力推動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日益深入人心,保護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民間文學學科也因此發(fā)生了一些變化,一些高校的民間文學教學和研究機構隨之改名,有的民間文學碩士點和博士點也向“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轉向,國家也在本科專業(yè)中設置“非物質文化遺產”專業(yè),研究生學科目錄也通過自主增列設立了“非物質文化遺學”專業(yè)。這也導致了原本屬于“小學科”的民間文學專業(y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語境下的弱化。①萬建中:《十四五時期民間文藝學學科建設的愿景》,《文藝報》,2020 年12 月25 日第8 版。
(二)中國民間文學學科歸屬的三種路徑
學科建構有助于進一步厘定相關知識譜系,并將研究事象提升到原理層面,建構起相應的方法論體系,這對于學術和學科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為促進民間文學學科的發(fā)展,從不同學科背景和學術立場出發(fā),根據新的形勢,在現體制下,提出民間文學學科歸屬新構想,主要建議有三種。
1. 在“文學”門類“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設“中國民間文學”二級學科
在國家學科目錄中將“中國民間文學”回歸“文學”門類,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設“民間文學”二級學科。其理由是中國民間文學一直是在中國語言文學大的學科框架下發(fā)展起來的,與中國語言文學有直接的關聯性,從學科本質來說中國民間文學屬于人文科學。這是大多數民間文學學者所期盼的。
2. 在“藝術學”門類下設立“民間文藝學”一級學科,“民間文學”為其二級學科
在“藝術學”門類下新設立“民間文藝學”一級學科,其下設“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學”“民間文藝學理論”等二級學科。其理由是民間文學與民間藝術的關系十分密切,現行的學科設置將兩者歸屬于不同學科,割裂了關系的整體性。民間文藝不只是民間文學、美術、工藝等橫向類別的構成,更是“藝術學”意義上一種縱向的、基礎性的存在。這是許多民間藝術學者們所希望的。
3. 在“交叉學科”門類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一級學科,“民間文學”為其二級學科
在“交叉學科”門類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一級學科,下設民間文學、民間藝術學……二級學科。其理由是民間文學本質上是一種民間生活文化,對其研究涉及諸多學科理論和方法,加強各學科之間的合作、交叉、融合是這一學科建設的內在要求。這是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者的設想。
以上三種關于“民間文學”學科歸屬的新設想,從各自學科立場上來說都有自己的依據和合理性,筆者希望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重視以上建議,并在修訂學科目錄時予以采納。各學校應根據本校民間文學的研究特點和優(yōu)勢選擇其中【包括現行的“民俗學(含中國民間文學)”】的某一種作為未來學科發(fā)展的方向,各安其道,自主發(fā)展。
三、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未來關注的重點問題
無論民間文學學科未來歸屬如何,必須以問題為導向,堅持“問題性學術”的學術取向,其研究對象和方法應是學科發(fā)展關注的重點,在當今社會背景下,以下應成為民間文學研究重點關注的問題。
(一)人民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19 頁。人民創(chuàng)作、人民傳播和人民享受是民間文學人民性的具體表現。對民間文學人民性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共產黨文藝思想的歷史來源,把握民間文學學科的本質特征。
堅持民間文學研究的人民性立場,牢固樹立人民群眾是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唯物史觀。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②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人民日報》2015 年10 月15 日第2 版。我國民間文學是千百年來人民大眾的文化創(chuàng)造、智慧結晶、生活反映,對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所產生的潛移默化影響十分深遠,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和基石。我們要通過深化對中國民間文學內在精神和生命力的認識,發(fā)現人民群眾在文化傳統(tǒng)和歷史創(chuàng)造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增強中國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加強民間文學人民性的研究,必須“朝向當下”更加關注人民群眾的現實生活。民眾生活是民間文學得以傳承發(fā)展延續(xù)的土壤,民間文學本身也構成了民眾生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生活屬性是民間文學人民性的直接體現。民間文學研究必須“朝向當下”,關注民眾的現實生活。世世代代傳承下來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小戲、說唱文學等都是人民群眾不可缺少的生活樣式,沒有哪一種文學形式擁有如此廣泛的人民性。加強對民間文學的人民性的研究,就是要讓這些傳統(tǒng)的民間文學在現代人的生活世界中持續(xù)釋放出強大的精神能量,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賦能。
(二)應用性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這為我國民間文學的應用性研究指明了方向。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學院化”,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通過人才培養(yǎng)和科學研究更好地保護傳承利用發(fā)展民間文學,為國家的文化建設和社會經濟發(fā)展服務。
推動民間文學資源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是中國民間文學學科建設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提出,“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內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產生活各方面。”隨著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的快速發(fā)展,民間文學的獨特價值被重新發(fā)現,民間文學的現代應用應被納入學界視野。發(fā)揮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民間文學學科優(yōu)勢,對民間文學資源的搶救保護、傳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轉化等開展針對性、前瞻性、應用性的研究,既是民間文學學科的職責所在,更是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開展民間文學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研究是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當代價值的體現。新形勢下,民間文學學科必須適應不斷更新的民眾生活,關注現實發(fā)展需求,深入探討傳統(tǒng)民間文學樣式與老百姓日常生活和文化精神的關系,深刻理解民間文學民族性的深刻內涵,把握傳統(tǒng)與當代、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在保持民間文學特點基礎上,大力推動民間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開展應用性研究中實現民間文學學科的使命與價值。
(三)交叉性
近年來,在“新科技”和“新文科”背景下,學科發(fā)展呈現出不斷交叉、融合、滲透的趨勢,跨學科研究對傳統(tǒng)民間文學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
民間文學研究要樹立大文學觀,加快建構和完善跨學科體系。新時期民間文學研究要以兼容并包的開放姿態(tài),保持對不同形式不同類型文學與文化及其相關理論方法的主動觀照與借鑒,樹立跨界融合、跨學科交流意識,走多學科交叉之路,加快建構和完善跨學科、跨領域的民間文學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
民間文學研究要確立自主地位,堅持人民立場,強化問題導向。在推動民間文學跨學科發(fā)展時,要準確把握本學科建設規(guī)律,堅守民間文學學術品格,堅守民間文學學科自主地位,防止在學科交叉中成為其他學科的附庸。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堅持人民立場,強化實踐與問題導向,重點關注回應社會與時代對民間文學發(fā)展要求的核心議題,使其能夠實現與未來時代發(fā)展的無縫銜接。
(四)田野性
在習近平總書記把學問寫在大地上,讓科學理論能夠“飛入尋常百姓家”思想的指導下,許多民間文學學者積極走向中國大地,致力于在田野中理解中國民間社會,用心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
田野作業(yè)是現實地打開“人的實踐”的方式。不論是社會科學抑或人文學科,都是以研究“人”為中心的學問,田野作業(yè)作為一種了解和探究“人”及其活動的有效手段和方法,提倡學者走出書齋,走向社會,深入民眾日常生活,以具體的人和事為研究對象,發(fā)現其背后的“人情世故”和文化傳統(tǒng),從而更好地理解民眾社會形成的歷史過程。田野作業(yè)體現了對民眾生活的學術關切。
田野作業(yè)最佳狀態(tài)是形成“有溫度的田野”。民間文學田野作業(yè)就是深入民眾、扎根生活的田野,發(fā)掘、搜集、記錄與整理活態(tài)民間文學,把握民間文學的生態(tài)現狀。在田野作業(yè)的過程,必須以平等心態(tài)去學習、去欣賞民眾所創(chuàng)造和傳承的民間文學,以深厚的情感形成“有溫度的田野”。民間文學田野作業(yè)可以獲得真實可靠的第一手民間文學資料,既是搶救保護民間文學的有效手段,又是高質量民間文學科學研究的資料基礎。
(五)共同體
學術共同體是以某一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紐帶,聚集同一學科或不同領域的學者和團隊,發(fā)揮不同學科優(yōu)質資源和集體攻關優(yōu)勢,共同開展研究的學術組織形態(tài)。民間文學學術共同體除了傳統(tǒng)的師門和行政性研究機構之外,主要還有兩種形態(tài):
一種是在民間文學領域內圍繞民間文學同一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形成的學術共同體。如我國改革開放初民間文學學者自發(fā)成立的神話學會、傳說學會、故事學會、新故事學會、史詩研究會、歌謠研究會等等以民間文學體裁為研究主體的學術組織,以及“四大傳說”研究會、孟姜女研究會、故事家研究會等以某一重要研究內容為對象的學術組織,這類學術共同體的優(yōu)勢是參與者都是本領域或相關問題的重要研究者,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有著自己獨特的深入研究,能群策群力、集思廣益,深入推進這一問題的研究。如圍繞“中國民間文藝理論體系”課題,整合民間文藝學的歷史、原理、評論及方法等不同研究方向的學者開展系統(tǒng)化研究,通過這一學術共同體可以為構建中國特色的民間文藝學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做貢獻。
另一種是不同學術領域學者圍繞民間文學某些重大問題形成的集體攻關學術共同體。在這個學術共同體中,打破傳統(tǒng)學科壁壘,充分尊重不同學科特點,加強不同學科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借鑒,從多領域多角度開展研究。比如開展利用民間文學資源發(fā)展影視文化產業(yè)重大項目研究,就必須組成有民間文學資源研究的學者、藝術創(chuàng)意的設計者、新媒體的研究者以及工程技術專家等共同參加的研究團隊,才有可能最終實現民間文化資源的產業(yè)轉化,而任何單一學科都不可能完成這一復雜的綜合性強的課題。這種跨學科研究共同體是實現學術和學科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重要組織保障。
在新時代,加強中國民間文學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必須從本土、本民族的歷史以及民眾文化生活出發(fā),把握民間文學的本質和規(guī)律,以相應的概念、范疇、命題等加以闡釋,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和方法,使之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組成部分。
民間文學研究的守正與開新
陳泳超
守正與開新,是任何一門成熟的學科都需要不斷面對的話題。這里就民間文學的研究現狀做一些針對性的反思,主要談三點個人感想:
第一,認清家底,守住根脈。一門學科要自立于浩繁的學術之林,必須有自己獨特的對象和方法,否則只能趨于末流乃至最終被無情淘汰。民間文學研究有其光榮傳統(tǒng),產生過許多經典命題和研究范式,像神話的意義闡釋、傳說的歷史演變、故事類型學與形態(tài)學、歌謠與文藝的關系、史詩的口頭展演及其族群功能……這些都是別的學科不能取代的,也是本學科的立身之本。不能因為它具有較長的歷史就輕易認為已經過時,不顧傳統(tǒng)的一味求新很容易迷失自我。真正成熟的學科無不有自己不斷經營的學術根脈。比如考據學可算是老掉牙的方法了,可在古典學領域中卻是無可爭議的基本法則,你的觀點和方法再怎么更新換代,都跳不過考據的基本功夫,否則即被視為無根游談。再比如考古學,其現代學術史與民間文學學科差不多同步,它看上去似乎日新月異,但地層學、年代學、類型學等等始終是其基本方法,它們的類型學與民間文學的類型學其實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靠一些可直接辨識的外部特征來觀察不同文化現象之間的復雜關系。所以,我們必須盤清自己學科的家底,予以充分的敬畏和重視,不要踩著前輩留下的金礦去羨慕別人的鐵礦,而是要在持續(xù)研究中不斷精深化,從而產生更多更深入的新知,影響到本學科之外的學術研究,才能維系本學科的活力和獨特的存在價值。
我們當然非常鼓勵學術研究要關注現實文化的最新動態(tài),尤其是青年學子,他們對于現實的敏感度遠遠超過老師輩。像都市傳說、謠言、段子、網絡文學、動漫、線上游戲、各種直播節(jié)目等等,已經得到了民間文學研究界越來越多的關注,近年來研究生選擇這方面話題的論文逐漸增多。我們原則上都積極支持,但也會提醒他們:這些現象其他很多學科也在關注,你的研究到底有怎樣的特色能脫穎而出呢?客觀地說,當代流行文化研究早已是一個熱門學科,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理論和方法,他們觀察、跟蹤流行文化動態(tài)的速率高于我們,因為這就是他們的本行。我們投身進去,則需要考慮如何與本學科的傳統(tǒng)優(yōu)勢結合起來。像施愛東用故事形態(tài)學的原理去解析謠言,便是出色的范例。所以練好本門內功是行走江湖的必要前提,否則很容易目迷五色,失去自家面目。
另外,田野調查當然是我們的看家本領之一,但作為民間文學學科的基本方法,我個人認為恐怕應該是文本與田野之間無間斷的平等互動與生發(fā)。單個的學者盡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性做純文本或者純田野研究,只是各自不要忘了另外一個維度的存在:文本研究時要從貌似無語境的文本(比如古代典籍中對民間文學的簡單記錄)中看到可能的語境信息,田野調查則要經常與書面記錄產生恰當的聯想和印證。這兩方面要做好都不容易,但都是我們學科的支柱,兩者總體上應該持續(xù)發(fā)生良性互動,不要各據一端,更不必厚此薄彼。比較來說,個人覺得目前對于傳統(tǒng)典籍的輕視似乎更嚴重一點,不少研究缺乏歷時性的文獻維度,甚至連這樣的意識都很淡薄,能想到去古籍庫里摘抄幾條古文已不容易,至于引文、段落、標點、版本等方面的錯亂更不在話下,這些基礎技能的衰減,是需要警惕的。
第二,努力拓殖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關聯領域。如前所說,我們非常鼓勵青年學子關注現實文化建設中的各種新近動態(tài),不過,這里要說的是,開新并不是單線的越新越好,有時候離身邊不遠之處,就有值得開拓的廣闊原野。比如傳統(tǒng)的戲曲和說唱文藝。
我們都學過民間文學概論,知道民間文學一般分為四大塊領域:民間散文類敘事(廣義的民間故事),即神話、傳說和狹義的故事;歌謠、敘事歌和史詩等民間韻文;民間說唱;民間戲曲。可是我們學界絕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在前兩類,后兩類除了個別人有所經營之外,基本處于“有目無詞”狀態(tài),很多時候甚至已經被民間文學從業(yè)者屏蔽于學科意識之外,這就等于丟掉了理論上的半壁江山。或許有人會說,說唱已經有曲藝學,戲曲更有戲曲學,它們各自發(fā)展成了獨立學科,不勞民間文學去置喙了。如果這么說,那么我們的民間文學概論為什么還要保留這兩部分呢?直接去掉不好嗎?去掉之后的民間文學的學科體系會不會受到損傷?回顧學術史,當初在建設民間文學體系時,這方面的工作就沒有得到充分重視,有些概念設定得不甚科學。比如為了區(qū)別于戲曲學這一新興而龐大的學科,前輩提出了一個“民間小戲”的概念,似乎為自己的體系留下了一個合法性管道。問題是民間只有二小戲、三小戲嗎?比如目連戲,經常能連續(xù)演出幾天幾夜,是十足的大戲,而它基本都是由草臺班子甚至大量群眾來充當演員的,我們看一下魯迅筆下的《女吊》《無常》《社戲》即可知其概貌,它難道不應該被視為民間文學的天然成員嗎?它不僅是戲曲,更是社區(qū)普渡施食鎮(zhèn)魂祭祀的法事活動,以之求得集體凈化的儀式效用。這就凸顯出民間文學研究與一般曲藝、戲曲文藝研究的主要差別了:曲藝學、戲曲學盡可更多關注其藝術面向,將之視為可以抽離出現實生活而進入特殊場所表演的綜合藝術;而民間文學則更多關注其與信仰儀式的相互紐結,儀式與文藝合二為一,共同組成了民眾日常生活實踐的有機部分。
因此,我們與曲藝學、戲曲學等相關學科的區(qū)別主要不在于藝術形式,而在于不同的理解視域,相對于文本與表演而言,我們更關注它們在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功能。事實上,類似目連戲這樣的民間戲曲還很多,像各地儺戲之類的儀式劇就琳瑯滿目,大小不一,我們?yōu)槭裁匆谩懊耖g小戲”來自我矮化呢?而民間說唱領域的類似現象就更多了,寶卷、贊神歌、香火書、打待尸、圣諭宣講……比比皆是。它們的歷史、現狀參差不齊,但總體蘊藏量極其豐富,只要隨便翻一下各地的非遺代表作名錄即可知曉,而民間文學界目前對這方面的關注嚴重不足。近年來我們團隊努力提倡的“儀式文藝”研究,就是想以這樣一個概念來將上述那些零落散存的藝術形式攏合起來,重新帶入民間文學的研究視野。這與其說是拓殖新領域,或許還不如說是收復失地更加合適,它不僅可以豐富民間文學的研究對象,而且更便于跟其他學科發(fā)生碰撞,這就牽涉到下面要說的話題了。
第三,主動與強勢學科開展有效對話。民間文學學科在整體學術格局中長期處于弱勢地位,這是誰也掩蓋不了的事實。對此,我們慣常的做法是不斷論證本學科的重要性,呼吁各界予以關注和重視。這些努力當然有其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你得做出實際的學術成績來,才能真正讓其他學科重視你而不是同情你。有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們不敢小覷了神話研究;有了普羅普的故事形態(tài)學,民間敘事研究的正當性和輻射力更是無可置疑;同樣,顧頡剛的孟姜女研究直接跟向來強勢的歷史學發(fā)生了強烈碰撞,才會得到那么多的贊許,奠定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的現代基點。所以,我個人一向主張,民間文學界有能力的學者,應該盡量將自己的優(yōu)秀成果發(fā)表到本學科之外的陣地上去,不要老守著本學科的一畝三分地,滿足于關起門來自己喊好。早些年葉濤就在《文史哲》上發(fā)表過關于泰山石敢當的民俗考據文章,戶曉輝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fā)表過民間文學的理論文章,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除了發(fā)文之外,主動參與甚至發(fā)起主持一些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學術話題,也是彰顯民間文學學科魅力的一項措施。事實上,許多強勢學科的前沿話題,民間文學非但應該參與,有時甚至是本學科的優(yōu)勢所在,我們不要妄自菲薄。最近我個人因緣際會分別參加了由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組織的學術活動,兩次討論的主題非常接近,都是從物質層面轉向重新審視文學史的文獻學及其價值取向,其核心意旨是反撥以經史為最高典范的傳統(tǒng)文獻學,希望充分重視不同學術門類中多樣化的文本存在方式,尤其關注文本借重的物質手段,從而對文學史過于固化的本質主義研究發(fā)出挑戰(zhàn)。他們討論的諸多面向,比如文本的多介質性、不穩(wěn)定性、無定本性、副文本(paratext)等等,其實在我們民間文學里體現得尤為典型,并且已經積累了相當成熟的業(yè)績。因為那些強勢學科,基本限定于從文字范疇來討論文學,其物質性也大多著眼于文字的載體。而我們民間文學學科還有悠久而廣闊的口頭傳統(tǒng),只有加入了這一維度,五光十色、豐富多樣的文學文本譜系才是完整的。更重要的是,從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史來看,口頭傳統(tǒng)居于整個文學譜系的開端,它不僅哺育了后來的復雜形態(tài),而且本身也在與文字世界發(fā)生著或平行或相交的各種聯系。從這一端點投射出去,可以映照出許多別開生面的景觀,至少從口頭到文字的飛躍,就不可避免地呈現出物質的和非物質的種種因素與機制,可以為其他文學研究提供某種積極的參照。最近,朝戈金在《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等頂級刊物上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重要成果,不僅是對口頭傳統(tǒng)的全面闡發(fā),更始終在與現行的文藝理論進行著或明或暗的對話,無形中也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有效的回應,顯示出民間文學學科與各強勢學科平等對話的勃勃生機。
當代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新路徑
黃景春
田野調查既是民間文學的資料來源,也是問題意識的源泉,還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民間文學新問題的發(fā)現和解決,都應在田野調查中完成。當代民間文學出現了新形態(tài),傳統(tǒng)的走向鄉(xiāng)村的田野調查之路,應通向大城市、旅游景區(qū)、網絡空間。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關注重點要及時調整,調查方法也要及時更新。
一、民間文學的新面貌
截至2020 年底,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過60%,農村人口不到40%,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以不可逆轉之勢快速推進。城市人口不僅占據數量優(yōu)勢,還在經濟、文化方面更加活躍。城市化、網絡化時代的民間文學呈現出的是前人未曾設想的新面貌。城市居民創(chuàng)作和傳播的民間文學在城市、鄉(xiāng)村流行開來,像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超大城市,都孕育出豐富的都市傳說(Urban Legend)。譬如,北京有375 路公交車傳說、北新橋傳說、京城81 號傳說,上海有九龍柱傳說、恒隆廣場傳說、太平洋百貨商場傳說、漕寶路地鐵站傳說。其他大城市也不乏此類傳說。由于城市的繁榮,城市人口對旅游消閑的需求大幅增長,旅游景區(qū)也會對神話、傳說、歌謠、史詩加以改造,從而帶動民間文學以舞臺表演的形式呈現出來。繁華的城市催生出民間文學的新樣態(tài)。
口頭性一向被認為是民間文學第一位的最具根本性的特征,現在我們發(fā)現很多故事、歌謠不是口頭演唱出來的,而是撰寫出來的。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國文盲率下降到2.67%,也就是說,識字率上升到97.33%;每10 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15467 人,高中15088 人,初中34507 人,折合成百分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達到65.16%。這個比例換算成人數,就是9.18 億人。他們都具有一定讀寫能力。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具備讀寫能力的人還在不斷增多。長期的學校教育隔斷年輕人跟地方傳統(tǒng)的緊密關聯,講故事、唱山歌的口頭表演能力萎縮,很多民間故事、歌謠的文本不是依照口頭講唱寫下的,而是作者在了解某方面知識后編創(chuàng)出來的。另外,文人還會像作家一樣創(chuàng)作“新故事”“新兒歌”,這些作品跟口頭表演沒有關系,而是作者出于闡釋地方歷史或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以書面形式寫出來,借助于報刊發(fā)表,它們具有民間文學的外表,其實并非口頭創(chuàng)作,也不借助于口頭傳播。
特別是最近20 年,不少民間故事、歌謠是在電腦上編寫出來,在網絡上傳播的。某個人編寫的故事、歌謠,發(fā)布到互聯網上,別人可以直接轉發(fā),也可以做一定的改編再發(fā)布,從而形成電腦寫作、網上傳播的新模式。在傳播過程中,不斷有人加入到對文本再加工的行列。這樣的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和傳播迥異于過去的口頭形態(tài)。實際上,城市民間文學的口頭性特征已經淡化,而集體創(chuàng)作、集體傳播的特征依然如故。過去的傳播借助于口語講唱,現在借助于網絡空間的反復轉發(fā)或發(fā)布。智能手機大量投入使用,讓更多人有機會利用手機介入民間文學的創(chuàng)作和傳播。電腦寫作、互聯網傳播讓民間文學生存方式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二、田野調查遇到的新問題
傳統(tǒng)的田野調查,不管是格林兄弟到德國鄉(xiāng)村,馬林諾夫斯基到遙遠的西南太平洋島嶼,還是顧頡剛等人到妙峰山趕廟會,當代民俗學家到河北耿村搜集民間故事,都是學者來到傳統(tǒng)社區(qū)開展調查。這些社區(qū)一般都有古老的村落、廟宇,流傳著某種神話、傳說或信仰、儀式。到傳統(tǒng)社區(qū)尋找知情人觀察、采訪、座談,聞別人所未聞,見別人所未見,通過記錄、拍照、錄音、錄像等方式獲得第一手材料,發(fā)現學科新問題,探討解決問題的新方法。這種田野調查今天仍然存在,對民間口頭傳統(tǒng)的研究仍然有效,但它無法滿足城市化、網絡化時代的新需要。
今天民間文學研究者進行田野調查遇到的新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城市化乃至都市化創(chuàng)生出新的民間文學。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是農民,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tài),男耕女織的生活方式,都決定了鄉(xiāng)村是文化生產的主要場地。有些城市文化、上層文化也會流布到鄉(xiāng)村,城市里已經失傳的,鄉(xiāng)村仍有存留,形成“禮失而求諸野”的現象。過去做田野調查總是走向鄉(xiāng)村,走向少數民族地區(qū),就是因為那里有古老的文化遺存。當代城市化的結果是小城鎮(zhèn)變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變成大城市,大城市變成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乃至國際化大都市。城市人口不但在數量上占多數,在文化創(chuàng)造上也顯示出更大的活力。城市成為文化生產的主要場地。大量的民間文學誕生于城市,流布到鄉(xiāng)村。在此情形下,田野調查必然走向城市。做都市傳說研究的人,只能前往上海、北京、深圳等大都市做調查。
其二,旅游景區(qū)對民間文學的舞臺化、影視化改編。利用神話、傳說、歌謠創(chuàng)建旅游景區(qū)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新型文化產業(yè)。為了符合游客的觀光、娛樂、休閑需要,歌謠在景區(qū)做舞臺化表演,神話、史詩做影視化展示,景點也做傳奇化解說,從而形成對民間文學的持續(xù)加工和利用。旅游公司動用自身的人力、財力支持對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有的經過改編后拍攝成影視劇,制作成動畫片。它們的目的是借此宣傳景區(qū),實現廣告效應,提升景區(qū)的經濟效益,但也為民間文學的改編、創(chuàng)新和傳播開辟了新道路,并一定程度上激發(fā)民間文學的生命力。但是,我們需要關注其間發(fā)生的新變化,通過田野調查掌握產業(yè)資本對神話情節(jié)、歌謠音韻等做了哪些改造,注入了哪些情感和觀念,推動民間文學朝向怎樣的方向轉變。
其三,電腦寫作、網絡傳播下的民間文學多媒體化。當代文人書寫的民間故事、歌謠需要經過公開發(fā)表才能為大眾廣泛接受,發(fā)表的藝術和政策門檻比較高。進入電腦、互聯網時代,改編故事、歌謠更加便捷,發(fā)表作品幾乎沒有門檻。手機短信、微信的廣泛使用讓眾人參與故事、歌謠創(chuàng)作的途徑更加廣闊。有人在轉發(fā)過程中插入圖片,有人把講故事、唱民歌拍成視頻,集體創(chuàng)作和傳播的過程,也是多媒體化的過程。集體創(chuàng)作跟新媒體結合起來,民間文學的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粘貼、轉發(fā)實現了民間文學的快速傳播。這種新的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傳播機制如何運作,各類人群如何介入網絡民間文學的改編,它跟口頭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傳播有哪些相同與不同之處?這些都還沒有人做深入調查研究。
其四,電子游戲、網絡游戲對民間文學的改編和利用。電子游戲、網絡游戲經常利用神話、傳說(包括都市傳說)、故事的詭異元素營造奇幻背景、恐怖情節(jié),在對抗、闖關、升級的過程中激發(fā)游戲玩家的興趣。這類游戲對民間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改造有其內在邏輯,玩家從中可以體驗到某種場景真實和情感共鳴。由于電子游戲、網絡游戲大量存在,不斷迭代翻新,對民間文學的利用越來越多,受眾面也越來越大。然而,民間文學研究者對這一改編和利用過程同樣不太了解,它對民間文學將會造成怎樣的影響,我們也不甚了了。田野調查需要關注這個問題。
這些都是傳統(tǒng)的田野調查未曾遇到的新情況。如何研究這些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
三、田野調查的新路徑
城市民間文學、網絡民間文學的田野調查跟過去有很大不同。我們要對田野調查方法加以革新,探討調查的新路徑。
首先,我們的田野調查要來到城市,包括大都市,要以中青年人為主要調查對象。城市里的職場笑話、黃色段子、時政歌謠都在中青年人中間流傳;都市傳說在企事業(yè)單位職員、政府公務員、出租車司機、大學師生那里講述更多。中青年人是這類民間文學的主要創(chuàng)造者和傳播者。如果我們到城市里仍然找老年人訪談,他們提供的很可能是比較傳統(tǒng)的故事和歌謠,而對新東西所知甚少。對于城市新故事來說,口頭講述只是一種次要方式,文本書寫、電腦編創(chuàng)和網絡傳播才是主要方式。有些網絡文本已經發(fā)表在報刊上,對報刊的查閱,對文章作者的采訪也是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都市傳說經常依托于特定建筑物及其雕塑作品,尋訪設計師、工程師或雕塑家,對于弄清一些傳說的來龍去脈很有幫助。
其次,我們的田野調查必須借助于電腦和手機,利用各種檢索手段,實現網絡田野。做網絡田野,調查方法不僅是觀察、訪談,查閱報刊書籍,還要利用百度、谷歌等檢索平臺搜集信息,還要訪問百家號、頭條、抖音、快手等自媒體平臺,大量瀏覽微信群和朋友圈。城市居民發(fā)表想法,獲取各種信息,主要依靠電腦和手機,我們做調查也要到網頁、博客上去,不僅要瀏覽互聯網上的文章、博主的主帖,還要查看留言和跟帖,甚至對留言、跟帖做分類統(tǒng)計,匯總數據,也要關注跟帖提供的某些補充信息和細節(jié)。微信群和朋友圈是這十多年最便捷高效的交流手段,各種個人見解、非官方消息借助于微信群轉發(fā)快速流傳,其中不乏謠言、傳說、故事和歌謠。為了更好地進行網絡田野,多加相關人士的微信,多瀏覽朋友圈,然后對我們感興趣的話題展開追蹤,是一種有效的調查手段。
第三,調查電子游戲、網絡游戲對民間文學的改造和利用,需先去玩這些游戲,體驗和熟悉游戲中的人物、情節(jié)和規(guī)則。沉浸在電子游戲中,或在網絡游戲中打通關,并非學者所樂意,也非我們的精力、能力所能及。但是,要調查電子游戲、網絡游戲中的民間文學元素,梳理游戲設計中故事情節(jié)的改編邏輯,了解游戲利用神話傳說的效果,研究者必須親自體驗這些游戲,才能把握其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游戲公司依據什么故事版本,加入哪些人物角色、工具武器、打斗情節(jié)和對抗性動作,參照了哪些國家的哪些游戲,設計了怎樣的等級和關卡,打通關過程中人物的形象和命運如何,與民間故事中的人物特點是否一致,都需要我們深入考察。為此,我們還需要訪談游戲腳本編寫者、角色設計人員、技術開發(fā)人員,請他們介紹游戲開發(fā)的思路和設想;也要訪談資深的游戲玩家,聽取他們的感受和見解。當然,我們最終要考察的是這些游戲對于民間文學發(fā)生了哪些改造作用,對玩家認知特定神話傳說產生了什么影響。
至于到旅游景區(qū)調查舞臺化、影視化的民間文學,上節(jié)已經有所涉及,這里就不再討論了。
新時代民間文學的田野調查,需要我們搜集的資料更多,我們不僅要做記錄、錄音,拍照片、錄像,還要下載網上文本、圖片和視頻,保留較多的手機截屏,并及時對這些文件命名,分類保管,建立數據庫。通過文字記錄可以把握田野調查的整體結構和過程,通過拍攝和下載圖片也能印證這個過程,而錄音、錄像及網絡視頻則可以生動展現調查對象的活動細節(jié)。
總之,城市田野、網絡田野并不意味著比到鄉(xiāng)村做田野調查輕松一些,恰好相反,我們面對的調查對象更復雜,調查資料更豐富,調查過程也更艱辛。我們必須迎接民間文學田野調查的新挑戰(zhàn),才能在研究方法上與時俱進,成為當代民間文學的合格研究者。
作為學科的民間文學—— 多元取向與學科本位的抵牾
毛巧暉
1996 年美國民俗學年會專門討論了民俗學的“名稱意味著什么”(What’s in a Name),會上很多學者提出了“folklore”是否還能有效概括他們當下的民俗學研究。①[日]菅豐:《民俗學的悲劇——學院派民俗學的世界史縱覽》,陸薇薇譯,《民俗研究》,2022 年第3 期。近年來,國內對于民間文學的學科名稱也引發(fā)了類似的思考,包括民間文學這一名稱是否還能涵括當下學界研究中關注的口頭傳統(tǒng)、網絡民間文藝、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等;注重文字傳統(tǒng)的“文學”概念,是否能囊括當下變化和更新了的民間文學文本概念等。其實對于民間文學學科合法性的討論并非只是當下才出現,可以說從現代民間文學興起之時,這一問題就一直伴隨著民間文學的發(fā)展。筆者想通過對民間文學發(fā)展脈絡的簡單勾勒,呈現民間文學在不同時代所面臨的問題,或可對民間文學的當下情境有一定鏡鑒意義。
一、作為經世之學興起之初的多學科參與底色
現代民間文學的興起與現代中國的轉型直接相關。19 世紀末,受西方浪漫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及對現代性的思考等的影響,中國知識階層掀起了對民眾、民族與國家關系的討論;他們意識到中國要想進入現代國家行列,就要構建民眾與國家的聯系。在這一過程中,民間文學引起了知識人的注意,他們看到民間文學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的文人創(chuàng)作。他們一方面將民間文學作為重構現代民族文化的“資源”與“工具”,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民間文學“形式”與“內容”的利用和改造,使其擢升至“公共文化層面”。在這一發(fā)展脈絡中,民間文學的社會功能受到極大關注,無論是知識人還是政治精英,都希冀通過對民間形式的利用和改造,最大限度發(fā)揮其所包蘊的“革命”性。洪長泰在對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民間文學研究進行了比較全面的闡述:
中國民俗學者的民粹主義還停留在“理解”民眾的階段。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認為,民俗學者對民間文化只有純粹的學術興趣。事實上,大多數民俗學者都把研究民間文學堪稱是在追求一個更大的理想。……這場運動的重要性也就在于它本身沒有停留在文學的或學術性的層面。②[美]洪長泰:《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新譯本),董曉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年,第212—213 頁。
之所以將這一段反復被學者引用過的話語放到這兒,更多是想強調民間文學在“到民間去”的運動或知識分子重構與民眾關系中,它的“經世”之用。這其實也延續(xù)了儒家學以致用的傳統(tǒng),我們當下對民間文學的學科思考不能忽略這一學術興起之時的情境。正因為知識分子是奔著“理想”而去,他們參與民間文學的“學術思考”似乎處于第二位,他們并沒有糾結于“白話文學”“民間文學”“平民文學”“民眾文藝”“農民文藝”“通俗文藝”等不同的表達,也使用著民俗學、民間文學研究話語,如《陜北民歌選》的“關于編輯‘陜北民歌選’的幾點說明”中,何其芳就說得很清楚,這次編選的目的“不是單純?yōu)榱颂峁┮环N民俗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資料,而且希望它可以作為一種文藝上的輔助讀物。因此,入選的民歌,便要求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有可取之處”。①魯迅文藝學院編:《陜北民歌選》“關于編輯‘陜北民歌選’的幾點說明”,哈爾濱:光華書店,1948 年,第1 頁。但并未有人專門去辨析。可見對于使用者而言,并未將其視為問題,而更多是為了戰(zhàn)時需要或者前文所言“理想”訴求。文學、學術及社會價值被視為一個整體。這一理念延續(xù)至今,只是不同時代的變現不同而已。
在論及民間文學學科范式不定及發(fā)展薄弱問題中,中外很多學人都提到過民間文學興起之時參與群體大多為“兼職”,后來很多人都離開了民間文學領域。如周作人、顧頡剛、董作賓,他們的重心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翻譯、史學、考古學,參與西北科考團進行地質考察的袁復禮最早搜集發(fā)表了花兒,等等。但是在學術史梳理中,我們能看到民間文學從北京大學發(fā)起的歌謠運動到三四十年代逐步擴大到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童話等研究的脈絡,也可以隱隱看到當時對民間文藝學建設思考的歷程。只是研究者并未進行名、實之辨,而更多是質疑民間文學或民俗學(當時兩者合為一體)系統(tǒng)研究不夠,或者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關注不足。如傅彥長、朱應鵬、張若谷撰寫了《藝術三家言》,鐘敬文在對此書的評介中感慨道:“其實,他們的文章,是關于民間文藝的占多數”,這些應該是“民俗學者專門工作的園地”,但卻未有人涉足,而是其他行業(yè)的人完成的。正因為這樣的態(tài)度,民俗學也只能是取得一些“雞零狗碎的成績”。②敬文(鐘敬文):《藝術三家言》,《民俗》第8 期,1928 年5 月9 日。這樣的理論憂郁似乎一直伴隨著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發(fā)展。另外,隨著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轉向,民俗學、民間文學在中山大學遇到困境,全國的研究局面也因國民政府反對迷信及新生活運動等發(fā)展而衰落,當然在很多學者的討論中將其歸結于“統(tǒng)一化和標準化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民俗學因為關注地方性而被抑制。其實從當時民族學的興起及被重視來看,這一論點難以成立,只是民族學暗合了當時民族主義意識的轉向而已。③袁先欣《設想“民族”的前提——楊成志云南調查與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載《開放時代》,2022 年第3 期)一文有詳細論述。民族學及同時興起的人類學調查及研究中,很多人關注到民間文藝,比如楊成志、凌純聲、芮逸夫等都涉及民間文藝的搜集,當下我們的民間文學學術史回顧中也兼及這一部分。所以從民間文學興起之初,研究受到時代情境與政治文化的影響,同時其一直處于多學科交融或說多元取向中,學人有理論系統(tǒng)發(fā)展之憂,但并無學科固守之見。
二、納入國家文學體制及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民間文藝學
新中國成立后,延續(xù)了從“到民間去”運動到延安時期的民間文學理念,民間文學超越了學術,或許可以將其歸納為作為學術研究的民間文學及納入國家文化建設的民間文學工作,當然兩者并非截然分開的,而是合為一個整體。
1949 年7 月,召開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一次文代會”),會上通過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以下簡稱“《章程》”)。第一次文代會與新中國初期的文學體制形成有著緊密關系,在《章程》中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民間文學,但提到“積極幫助并指導全國各地區(qū)群眾文藝活動,使新的文學藝術在工廠、農村、部隊中更普遍更深入地開展,并培養(yǎng)群眾中的新的文藝力量”。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宣傳處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集》,北京:新華書店,1950 年,第573 頁。關于群眾文藝的論述與1949—1966 年間民間文學的發(fā)展基本一致。之后,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以下簡稱“民研會”),并將民間文學的發(fā)展納入“第一個五年計劃”及“1956—1967 年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等,同時民間文學文本納入中小學課本及北京師范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復旦大學、蘭州大學等諸多高校的課程設置。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由于受到蘇聯民間文學研究的影響,名稱也出現諸多變化,如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文學等名稱,其中也出現了民間文學是否能涵括迅速發(fā)展的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如新民歌、新故事等,并引發(fā)過一系列有關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概念、范圍的討論。 1961 年4 月和11 月,民研會的研究部與《民間文學》聯合召開了兩次 “社會主義時期民間文學范圍界限問題討論會”,高校教師許鈺、段寶林、朱澤吉、義龍、吳開晉和李文煥等參會并發(fā)言,賈芝、天鷹(姜彬)、巫瑞書、陳子艾、王仿等發(fā)表文章,他們主要圍繞社會主義時期民間文學的特征、社會主義時期民間文學的范圍界限與合流問題、新民歌新故事問題展開討論。②《民間文學》1957 年5 月號曾發(fā)表克冰(連樹聲)《關于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這也算當時圍繞民間文學概念發(fā)表的一篇較為全面的文章。但連樹聲并未加入后來的討論。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和《民間文學》雜志社召開的討論會上的發(fā)言及相關學者發(fā)表的文章均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研究部編《民間文學參考資料》第二輯,內部資料,1962 年。這可以說是民間文學學術史上一次較為集中的有關民間文學概念的討論,其結果就是民間文學的研究范疇中納入了一些新事物(新民歌、新故事、革命故事、革命歌謠等),但何其芳等在“民間文學主流論”盛行之時,都反對民間文學研究范圍的無限制擴大,即當下所言的開始彰顯出固守學科本位的意識。③1959 年7 月26 日起何其芳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連續(xù)3 期發(fā)表了《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當然這些討論也因為民間文學已經納入新中國文學體制及學科體系(這在哲學社會科學十二年規(guī)劃中可以看到)。民間文學興起之初的多學科參與逐步開始規(guī)范到文學范式,但這一時期的民間文學研究對象、特征顯然與民間文學興起之初有了一定的差異,這也是民間文學適應時代、社會需求的學術調適,其實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之時,鐘敬文在民間文學講義中就意識到過去研究的概念、觀點與方法的不適用④“民間文學方面的參考材料還是感到相當缺乏,特別是理論方面。(過去出版的一些成本頭的書,大都在觀點方法上是陳舊的,不很適宜于現在同學們的研習。)”見鐘敬文:《民間文藝新論集(初編)》“付印題記”,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 年。。當然也不像當下的很多推斷,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的發(fā)展只有文學研究,其實在民族識別中,民間文學的搜集與整理得以迅速推進,正如賈芝在1959年所撰寫的《民間文學十年的新發(fā)展》中所言,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的搜集與整理取得重大成就,這與民族識別及民族學的發(fā)展有著直接關系,當時民研會、國家民委、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共同推進這一工作,從民族學視域也有大量對民間文學的研究。當然無論是文學還是民族學視域的民間文學研究,都須將其置于社會主義國家文化建設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也才能在學術史長河中理解20 世紀60 年代初期民間文學范圍、界限討論的意義及價值,這次討論與當下有著民間文學學科名稱、研究范疇思考的內在勾連。
三、新時期以來民間文學的理論建設與學科范式討論
新時期首要的任務就是恢復民間文學的學術研究,同時重新審視1949 年以后的民間文藝學。這一時期民間文學的發(fā)展主要圍繞民間文學的基本特征、民間文學的分類、民間文學搜集與資料保存等基本問題展開。
隨著民俗學的恢復與發(fā)展,民間文學的研究也逐漸開始接續(xù)20 世紀初期至30 年代的研究傳統(tǒng),民俗學傳統(tǒng)與延安文藝傳統(tǒng)在民間文學領域并行發(fā)展,這在1988 年3 月23 日至25 日召開的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學術研討會上是一次集中呈現。在這次會議上,就“民間文學(化)在21 世紀的走向,建設中國民間文藝學體系,民間文學的理論、觀念、方法以及流派”等問題展開討論,不僅提出了民間文學—民間文化的內部研究視野,還談到了民間文學研究學派的三種層次問題:單一民間文學派(文學角度);復合派(人類學、文藝學方法的結合);綜合派(以民間文學為對象,無論用何方法,宗旨在民間文學)。“民間文學研究的科學化”也在學術研究過度功利化的現實問題與世界學術對話的現實需求的矛盾中被凸顯,學者們提出“要加強田野作業(yè),特別是參與研究,對活的民間文學形態(tài)進行實地考察的方法對于建設民間文藝學的重要性”或“從西方批評學派中借鑒研究方法(系統(tǒng)論、接受美學、二重組合原理以及比較研究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等。①蘭葉:《新的觀點——全國民間文學基本理論學術研討會側記》,《民間文學論壇》,1988 年第4 期。同時,會議還就深圳特區(qū)出現的新的民間文藝現象“廣場文化”“大家樂”舞臺等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在學術史上提及的并不多,但其影響還是很大的,包括對少數民族民間文學領域的波及。這次討論中,新穎的研究理論及開闊的研究視野確實為民間文學研究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但也應該看到,多元理論的“注入”并未使民間文學形成清晰的理論脈絡。
90 年代中后期開始,民間文學領域逐步引入故事形態(tài)學、口頭程式理論、表演理論、民族志詩學等,從文本到語境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民間文學的困境似乎并未解除,這在學術史回顧中已經進行了大量討論,在此不再贅述。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民間文學的存在樣態(tài)、傳播方式、傳播群體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與共享研究對象的相鄰學科交流亦出現新境況,這與新中國初期、新時期所面臨的情境不同,但其有著內在的一脈相承。從新中國初期就曾質疑民間文學對其對象的涵括性問題,到了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再次出現這樣的問題,但最后在學術長河中,民間文學還是比較穩(wěn)定地保留了下來,但其特征、研究范疇卻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同樣,多元取向與學科本位在不同時代都曾出現在民間文學研究的基本問題中,但民間文學似乎是在兩者抵牾中逐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