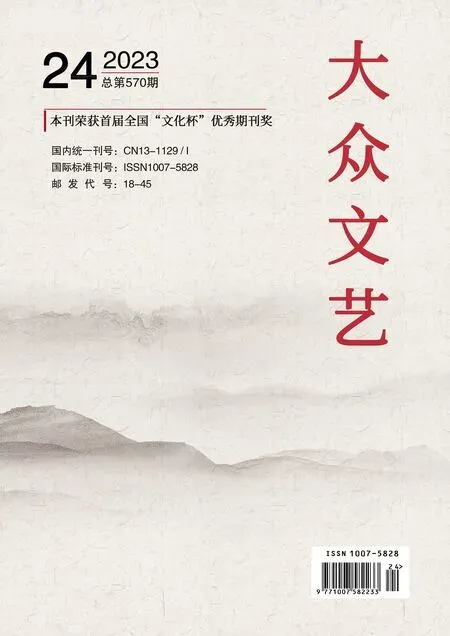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的音樂教師教育研究動態與趨勢*
周迪雅
(上海音樂學院、華東師范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松江分校,上海市 200031)
在“全球化”趨勢下,國際視野中的音樂教師教育成為世界各國的研究焦點,越來越多的國家關注于教師教育質量與教育公平等問題[1]。為培養高質量未來音樂教師并支持教師專業終身可持續發展,ISME學校音樂與教師教育委員會(MISTEC)舉行第24屆國際音樂教育大會會前研討會,該研討會以“讓音樂教育面向所有人”為主題,征集了來自全球各國的音樂教師教育論文、海報、工作坊等內容,旨在發展音樂教師教育領域專業知識與實踐方法,促進世界不同區域的國際合作與聯合項目研究,共享多元文化資源與各國政策經驗。
2022年學校音樂與教師教育研討會突出強調了國際藝術教育的合作以及音樂教師教育的崇高信仰,以此促進藝術教育者與研究者實現系統化的跨國界、跨語境、跨文化、跨社區合作。墨爾本大學奈里爾?讓內特副教授(Neryl Jeanneret)指出非殖民化、文化彈性、包容性與幸福感、后數字時代將成為當下國際音樂教師教育四大研究問題[2],在教師教育國際化進程中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幫助各國發揚本土化教育理念,促進數字化轉型,消除長期以來的種族、性別等偏見,保證音樂教師團隊的多樣性發展。內布拉斯加州大學林肯分校的格林?尼爾曼教授(Glenn Nierrman)認為音樂教師應有終身奉行的使命與哲學信仰,他們能正確認識音樂本體與非本體意義,例如賦予人責任感與正義感的社會意義、文化傳播意義、審美感知意義、表演實踐意義、社會情感學習意義等。
本次研討會大致可分為音樂教師教育課程、音樂教師素養與教師角色、音樂教學方法研究、政策對音樂教師教育的影響四大主要議題,通過Nvivo軟件對34篇文獻進行內容分析,獲得詞頻列表(表1)。

表1 詞頻列表
一、音樂教師教育課程變革:數字化轉型與創造力提升
信息化技術改變傳統音樂教育理念的同時,也推動了音樂教師教育課程變革。多年來,音樂教師教育尚未形成鮮明的現代特性,傳統教學常按照專業音樂家的培養模式培訓音樂師資,重視音樂技能而忽視音樂教育理論、音樂教學、學習方法和學校實習等師范技能,迫切需要全面改革。澳門理工的代百生教授認為音樂教師教育課程的變革包括調整人才培養目標、轉變入學考試方式、采用基于結果的教學(OBTL)評估方法、建立PDCA(計劃-執行-檢查-行動)質量自我管理體系等多個方面[3]。
音樂教師教育課程研究中創造力與數字化是近年來兩個高頻出現的關鍵詞,澳大利亞維多利亞政府頒布的《優質音樂教育框架》中“創造力和活動性”是其特色之一,其中音樂制作是所有音樂學習的核心,有效的教師強調發展強大的聽覺技能,給予聽眾、表演者、作曲家和即興演奏者積極參與的廣泛機會,幫助學生在所有音樂制作中建立音樂反應能力,并能引導、促進學生的創造性體驗[4]。許多音樂學院將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放在其機構價值觀和教育目標的突出位置,以便音樂學院畢業生“具有高度專業素養和個人深度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個人”[5]。那么如何促進創造性教學?引導創造性體驗?首先,研究者提出支持課堂創造性過程的框架以及課堂創造性過程實踐的模型,其中框架下包含培養兒童的創造性過程、激發想象力和經驗、促進課堂上的創造性過程、最大限度地發揮創造性過程的成果和培養自主學習五大策略[6];其次,開設“音樂的創造力”課程,該課程包括構圖、小組歌曲創作、即興創作、參與音樂聆聽四大任務,整個教學過程都通過電子“數字化”檔案袋記錄[7];此外,還有研究者應用現代化技術輔助音樂創造性實踐,比如使用Ableton Live、Soundtrap for Education、協作式數字白板等數字媒體工具共同創作音樂,或是編寫計算機程序和探索計算思維輔助音樂理論學習[8]。
二、音樂教師成長的影響因素:教師動機、素養與自我效能感
教師的成長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職業生涯階段,包括職前、入職、能力建設、熱情和成長、職業挫折、職業穩定、職業放松和退休,處于不同職業生涯階段的音樂教師在動機、價值觀、挑戰、壓力、課程實施、專業發展和職業預測等方面都各有差異,研究者認為挑戰、個人滿意度和領導力都是資深音樂教師的積極動機,激勵教師教學與自身發展,也有助于職前教師與入職教師更清晰地了解教師成長軌跡及其重要影響因素[9]。
此外,教師自我效能感與教師素養的培養也是教師成長的重要影響因素。部分高等師范院校欠缺對在職教師自我效能感的關注,造成新手教師的持續流失以及教師隊伍的雙峰化趨勢。教育部門組織的音樂教師講習班能提高教師在創造性藝術教學中的自我效能,影響決策效能感、自我教學效能感、紀律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評價[10]。在教師素養方面,研究者認為音樂教師的核心素養應該包括人文和藝術美學、音樂知識和分析評論能力、音樂表演能力、教育教學技能、學術研究能力、創造性引用技能,以滿足新課標下“培養具有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復合型人才”的教育目標[11]。澳大利亞《艾麗斯?斯普林斯(馬班圖阿)教育宣言》指出教師應輔助學生“發現、探索、游戲、創造和表達自己”,但普通中小學教師缺乏對學生音樂體驗教學的信心,學校可以通過社區、藝術家和學校的合作,來培養教師的藝術技能和信心[12]。
三、音樂教育實踐與教學方法
埃利奧特等實踐主義哲學家認為音樂不僅僅是“沉思的對象”或生活經驗的象征性表達,“Praxial”強調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實際音樂制作和音樂聆聽,通過證明意義和價值來理解音樂。音樂教育實踐是音樂教師教育的重要基礎,不少音樂學院以及師范類院校呼吁本科生體驗音樂表演以外的各種參與性音樂角色和行為[13],能幫助職前音樂教師熟悉未來工作并促進就業。
在音樂教育實踐過程中多種方法能促進教學有效性,比如青少年嗓音研究與語種研究能促進多種語種背景下的合唱團訓練與合唱歌曲創作[14];服務性學習(Service Learning,SL)等創新的教學方法有利于實現教師、學習者、社區和高等教育機構等實踐參與者共贏互惠[15];實踐共同體(CoP)的理論框架有助于豐富教育環境中的音樂體驗,為未來音樂教師教育的強化和教育改革提供了必要信息[16];教師支架和同伴支架能培養學生的個人和音樂能動性[17]。除此之外,柯達伊教學法與奧爾夫教學法作為音樂教育實踐的實用教學方法仍持續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
四、國際政策與觀念影響下的音樂教師教育
近二十年來,通過參與式和協商式方法進行教育治理仍然是一種新現象,“與學生共同構建音樂教育政策”的呼聲日益明顯,歐洲各國逐漸讓教育相關者與音樂教育的公共機構參與教育決策任務,通過國際和國家協議以及改變對兒童的態度來加強兒童的社會地位和權利,推動音樂教育以兒童為核心的民主化進程。[18]“芬蘭活動理論學派”的代表人物伊戈斯托姆(Engestr?m)認為“學習者集體”與“高級學習網絡”能形成交互性與開放性更強的活動系統,活動中的共同體分工與合作,通過規則的協商與調節發揮共同體最大效益[19]。
除教育民主化進程外,全球范圍的多元主義同樣也引發非殖民化進程,在高等音樂和音樂教師教育中,公平、多樣性和非殖民化的努力往往局限在個體層面。因此,如何通過政策與機制將意識轉化為可以實施的結構性任務,依然是當今高等音樂和教師音樂教育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研究者認為使用政策變革的間斷均衡模型,理解與引導改革,然后設計、協商、妥協以及部分實施[20]。
五、音樂教師教育研究啟示與未來趨勢
音樂教師教育仍是我國師資培訓的薄弱環節,作為教育主體的音樂教師似乎失去了發言權,高等音樂教育與普通學校教育實踐脫節的現象數見不鮮,我們既未傾聽一線教師真實的訴求,也未傾聽學生的需要。當下,我們需要思考怎樣的音樂教師教育才能幫助教師更好地實踐,學生更好地成長。
首先,學校、教師、學生是教與學過程中的協商者與合作者,教學要為學生服務,即教師能夠聽到不同學生的“聲音”,提供有效學習的基本條件,并將其納入教學和課程建設中。同時教師承擔著讓年輕人充分參與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的責任,這意味著教學必然是情境化的,且能為學生提供所需的適應社會的基本技能。當然,協商與合作也存在于教師之間、教師與教育機構之間,以促進教學問題的共同探討和教學技能的提升。
其次,全球化與信息化背景下,學習者群體的多樣性促進多元文化互動的環境,開辟了跨文化音樂學習道路。為促進多元文化的交流,音樂教師教育的“虛擬化”趨向將有助于各國教師通過互聯網線上分享教育教學經驗,例如2022年國際音樂教育大會給來自亞洲、歐洲、北美洲等各國教育學者提供教育經驗和前沿信息分享平臺,有利于及時應對后疫情時期的教育危機和教育公平問題。此外,多元文化語境之下催生的對世界音樂教育學(WMP)的研究也有利于多文化音樂語言的融合以及新的音樂形式產生。世界音樂教育學者認為音樂是一種文化依賴性的人類表達形式,它通過專注聆聽、參與式聆聽、表演性聆聽、創造世界音樂、整合世界音樂五個階段,支持多種方式的音樂聆聽、探索和體驗,發揮音樂的創造力和情感表達價值[21]。
最后,為建立一支知識更豐富、技能更高的專業教師隊伍,音樂教師教學實踐與專業知識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新手教師需要習得未來教師的經驗,要求他們轉變學生時期的教育理解與心理狀態。為此,許多高等音樂院校及師范院校重新設計實踐課程,組織職前音樂教師學習教學法,并采用“觀察學徒制”使課程更廣泛地與未來教學實踐相聯系,通過大量的案例、行動研究、績效評估,將理論與實際結合[22],其中專業發展學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簡稱PDS)的引入將推動職前教師培訓與在職教師進修。另一方面,教師教育理論研究也是加強教師專業的關鍵。格里菲斯大學的卡羅爾?埃文斯(Carol Evans)教授等研究者認為“有效地應用和發展研究是教學不可分割的能力”。因此,音樂教師應將教學視為一項探究的活動,包括基于探究的學習和反思性專業實踐[23]。本次學校音樂與教師教育研討會(MISTEC)的開展將持續開拓我國音樂教師教學實踐與理論研究視野,且作為國際音樂教育大會線上會議的嘗試,也將帶給各國音樂教育者提供更便捷的知識獲取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