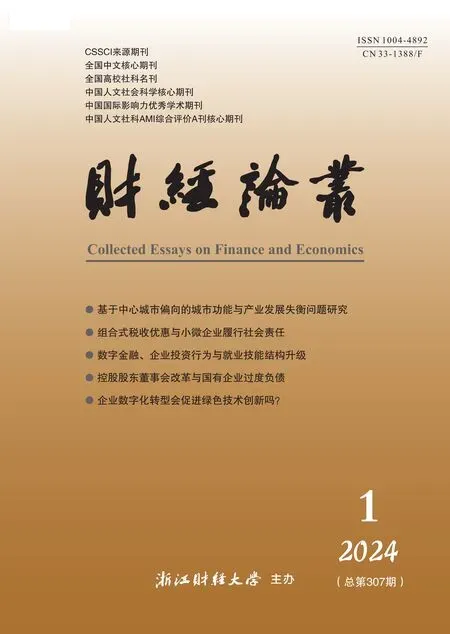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地區差異、動態演變及時空收斂性
劉高秀,劉菖山,孫 婧
(云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一、引 言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在綠色發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國經濟增長迫切需要實現綠色效率變革,而摒棄傳統的“資源掠奪式”發展理念、實現資源消耗型經濟增長向環境友好型經濟增長轉變顯得尤為重要[1]。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完善支持綠色發展的財稅、金融、投資、價格政策和標準體系,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在推動經濟綠色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實質性地改善環境,不僅要加強末端治理,還要通過政府使用財稅手段來改變資源配置的激勵機制[2],推動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讓經濟和能源結構變得更加綠色。近年來,隨著財政對重點行業領域綠色低碳轉型升級的支持力度逐漸加大,我國財政發展“綠色化”特征逐步凸顯[3]。通過推行綠色債券稅收優惠、綠色貸款財政貼息、國家綠色發展基金等多元財政政策工具[4],我國引導更多資金投向綠色低碳產業領域,快速滿足了發展綠色產業的資本需求。
綠色財政政策的實施能否有效助力“雙碳”目標的達成,已成為學者以及相關政策制定者迫切關心的話題。然而,盡管部分學者測算了區域和行業層面綠色創新效率以及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但鮮有學者從現實層面關注地方政府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話題。我國地方政府的綠色財政產出是否有效?各省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其效率損失的來源是什么?隨著時間推移,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是否會出現動態轉移,并最終趨向于同一個最優穩態水平?科學、嚴謹地回答這些問題對相關部門加強財政資源統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以及提高綠色財政政策的精準性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與本文研究主題相關的文獻可以大致分為以下三類。第一,綠色財稅政策理論與實證研究。從理論內涵上看,綠色財政一般是指中央和地方財政部門通過財政支出、稅收激勵、政府采購等政策協同發力,在保持經濟宏觀調控功能的同時發揮財政政策在污染治理、節能減排、生態保護等方面的管理作用[5]。從其表現外延上看,綠色財政主要包括綠色財政收入、綠色財政支出、綠色稅收優惠和綠色財政管理等環節。綠色財政相關理論研究大多側重于對其理論內涵、內在邏輯、政策效果等相關問題進行學理闡述,依托不同理論、不同分析方法對綠色低碳發展的財稅政策體系進行探索性分析。在實證層面,現有文獻主要使用“節能減排財政政策綜合示范城市”試點等政策沖擊評估綠色財政政策效果[6][7]。此外,也有學者通過構建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綠色財政金融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以及環境保護稅和綠色財政政策的耦合機制[8][9]。第二,綠色創新效率以及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研究。此類研究的測算方法可大致分為以隨機前沿分析法(SFA)為主的參數法[10]、以數據包絡分析法(DEA)為主的非參數法[11],以及改進的DEA、SFA 方法[12][13]。然而,以上方法在效率測算過程中并未將所有數據單元放在同一個前沿面進行比較,可能會忽略各數據單元之間存在的技術差異,導致測算出來的綠色效率數值存在偏差。O’Donnell等(2008)[14]提出的共同前沿理論有效彌補了上述兩種方法存在的缺陷,被國內外學者廣泛運用于區域和行業層面創新效率以及環境效率測算[15][16]。第三,效率測算以及區域差異、動態演變及收斂性研究。此類研究又可以細分為綠色效率相關和非綠色效率相關兩類研究[17][18][19]。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1)從地方財政視角切入,根據財政發展水平差異將省份劃分為不同群組,之后從多維度構建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評價指標,以測算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2)嘗試對綠色財政產出無效率數值進行分解,探究各省效率損失來源并梳理未來效率提升的重點;(3)拓展分析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存在的區域差異現狀、動態演變趨勢以及時空收斂特征,為各省科學制定綠色財政政策、系統編制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提升方針提供量化支持。
三、研究方法、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一)研究方法
參考O’Donnell等(2008)[14]、錢麗等(2021)[15]、Choi等(2015)[16]及Chiu等(2012)[20]的處理方法,運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共同前沿SBM-DEA模型,測算共同前沿和群組前沿下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MF和GFτ,進而計算得到共同技術比率MTR、綠色財政產出無效率GFIE、技術差距無效率TGI和管理無效率GMI。
(二)變量選取
1.共同前沿SBM-DEA模型變量選取。由于我國不同省份在經濟發展水平、財政收支均衡、債務可持續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如果將所有省份的指標變量放入同一個技術前沿面進行比較,測算得到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可能會偏離實際效率值,進而使得研究結論出現偏差,難以真實反映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
現有文獻大多根據省份所在區域,把所有省份劃分為東、中、西三個群組進行測算[21]。這種劃分標準忽視了各省財政發展的異質性,難以將財政發展水平相似的省份置于同一群組進行比較。基于群組劃分標準的科學性與嚴謹性,本文參考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中國各地區財政發展指數報告2022》中的指標體系,測算2007—2020年我國各省財政發展總指數,并根據指數測算結果的均值進行排序,將省份劃分為財政發展高水平地區、中水平地區和低水平地區三個群組(1)根據指數測算結果的均值從高到低排序,財政發展高水平地區包括上海、北京、浙江、廣東、山西、山東、江蘇、內蒙古、遼寧、寧夏在內的10個省份;財政發展中水平地區包括天津、吉林、福建、河北、黑龍江、陜西、甘肅、河南、湖北、江西、安徽在內的11個省份;財政發展低水平地區包含海南、湖南、西藏、云南、廣西、四川、新疆、貴州、青海、重慶在內的10個省份。。在劃分群組之后,本文參考錢麗等(2021)[15]、楊冕等(2022)[22]以及孫虹玉和劉澤杰(2023)[23],多維度綜合選擇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指標體系,詳細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評價指標
2.控制變量選取。在進行空間條件β收斂檢驗時,本文將下列影響因素作為控制變量納入空間杜賓模型:政府財政規模(Gov),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占實際GDP比重衡量;城鎮化程度(Urb),用年末城鎮人口比重衡量;教育水平(Edu),用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衡量;基礎設施水平(Infra),用人均城市道路面積衡量;城市人口密度(Pop),用常住人口與城市面積比值衡量;環境規制強度(Regu),用工業污染治理投資額來衡量;對外開放程度(Open),用進出口總額與實際GDP比值衡量;地方金融杠桿(Finan),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值衡量;公共醫療服務水平(Med),用每萬人擁有衛生技術人員數來衡量;民生必要消費水平(Consu),通過計算恩格爾系數進行衡量(2)限于篇幅,控制變量的描述性分析結果未列出,作者備索。。
(三)數據說明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地區)面板數據,使用共同前沿SBM-DEA模型、Dagum基尼系數、馬爾科夫模型和時空收斂模型測算我國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分析效率變化趨勢及損失來源,并對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區域差異、動態演變和時空收斂性進行研究。本文數據來源于各省統計年鑒、政府工作報告、《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網站,部分缺失數據通過查詢Wind 數據庫或者使用插值法補齊。
四、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測算及分析
(一)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測算
根據測算,共同前沿和群組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分別為0.674和0.772,表明從全國來看,我國各省的綠色財政產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損失。兩種前沿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還有32.6%和22.8%的提升空間,未來應堅持新發展理念,堅定不移走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通過統籌謀劃、協調推動全國不同區域綠色低碳技術產業布局,降低單位產出效率損失。
由表2可知,分群組來看,共同前沿下我國財政發展高中低水平地區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分別為0.709、0.632、0.686,高水平地區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顯著高于中、低地區,中、低地區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分別有36.8%和31.4%的提升空間。總體而言,財政發展高水平地區往往能夠通過不斷強化政府引導作用構建有利于低碳綠色發展的財政制度標準體系,提升綠色財政產出效率。

表2 我國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3)限于篇幅,表2—表4未列示所有年份結果,作者備索。
分省份來看,共同前沿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最高的省份為廣東,效率值高達0.989;海南、四川和江蘇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均大于0.9,依次位于全國第2至4位,表明這些省份能夠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提高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此外,共有13個省份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低于全國均值,其中山西、云南、甘肅和青海效率年平均值均低于0.5,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二)共同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變化趨勢
根據表2,共同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呈現波動上漲趨勢,全國均值從2007年的0.613上升到2020年的0.656。分群組來看,財政發展高水平和中水平地區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變化趨勢與全國變化趨勢保持一致,地區均值整體呈現波動上升趨勢,且2020年之后,這兩個地區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增長慣性較為明顯。此外,所有地區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在2017年均出現了明顯下降,使得2017年前后各地區效率出現明顯波動。究其原因,根據生態環境部公布的《2017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以及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發布的信息可知,2017年我國全國臭氧超標率明顯增加,峰值濃度出現明顯抬升。在此背景下,國務院在2017年開展第二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各地區持續開展污染防治行動,并加大財政對生態環境保護的支持力度,短期內對相關產業造成沖擊,這在一定程度上對該年度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產生抑制影響。但從長期來看,各地區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均有所提升。
(三)共同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無效率分解與提升重點
上述分析表明我國各省的綠色財政產出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效率損失。為了更好探究各省效率損失來源并梳理未來效率提升的重點,本文對綠色財政產出無效率數值進行分解。首先,使用表2共同前沿下我國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依次計算GFIE、TGI以及GMI,進而分析各省效率損失來源。其次,分別計算TGI和GMI與GFIE的比值,其中TGI/GFIE為技術差距無效率占比,GMI/GFIE為管理無效率占比。最后,根據測算的比值大小,本文梳理各省未來效率提升的重點。
根據測算結果可知(4)限于篇幅,具體測算與分解結果未列出,作者備索。,共同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無效率的全國均值為0.326,其中,技術差距無效率占比為30.1%,管理無效率占比為69.9%。這表明從全國層面來看,綠色財政政策在綠色低碳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優化升級等方面的管理上存在產出效率損失。
分群組來看,財政發展高中低水平地區的技術差距無效率占比分別為34.6%、46.6%、4.8%,管理無效率占比分別為65.4%、53.4%、95.2%。這表明財政發展高、中水平省份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會受到技術差距無效率和管理無效率的雙重影響,而財政發展低水平地區省份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損失主要由于管理無效率引起。
分省份來看,四川、福建、北京、黑龍江的技術差距無效率占比均超過60%,而管理無效率占比較低。未來這些省份應大力推動綠色低碳技術研發、示范和應用,發揮技術、管理和工程的協同作用,為提升本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提供重要科技支撐。江蘇、山東、海南、云南、西藏、青海的管理無效率占比均達到100%,這些省份應進一步優化能耗雙控政策,完善保障方案及配套制度,推動本省相關領域改革,加快構建綠色低碳技術和產業創新體系,提升本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
五、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地區差異、動態演變和時空收斂性
(一)地區差異
為了分析不同地區效率的差異,本文參考Dagum(1977)[24]的分解方法,運用Dagum基尼系數對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差異進行測算與分解,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2007—2020年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總體基尼系數整體呈現波動下降趨勢,總體基尼系數從2007年的0.239降至2020年的0.169,降幅達到29.29%。這表明在觀測期內,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地區差異逐漸縮小,均衡化水平不斷提升。具體來看,2007—2016年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總體基尼系數呈現穩定下降趨勢,2016—2020年份呈現小幅波動上升趨勢,這與前文結論保持一致。超變密度差異與總體基尼系數的波動趨勢保持一致,且超變密度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均值達到51.512%,表明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總體差異變化主要源于不同財政發展水平地區之間的交叉重疊影響。此外,地區內和地區間差異整體呈現平緩下降趨勢,且地區間差異對總體基尼系數的貢獻率均值僅為17.713%,表明地區內和地區間差異并不是影響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總體差異變化的核心因素。

表3 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Dagum總體基尼系數及其分解
從表4地區間差異變動數值來看,財政發展高中低水平地區間差異系數呈現下降趨勢。從2007到2020年,高—中、高—低、中—低水平地區間基尼系數降幅分別達到32.61%、27.49%、25.34%,這表明財政發展高中低水平地區間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差異在樣本期內有所降低。此外,根據表4,從地區內差異變動數值來看,財政發展高中低水平地區內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基尼系數年平均值分別為0.159、0.130、0.209,表明財政發展低水平地區內各省份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差異化最大。具體來看,處于財政發展低水平地區的省份產出效率差距較為明顯,例如共同前沿下海南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年平均值高達0.946,而同群組內的青海僅為0.169。此外,財政發展高水平地區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組內差異大于中水平地區,可能的原因是財政發展高水平地區內部所包含的省份在財政管理體系成熟度以及綠色科技創新能力上存在一定差距,導致組內差異大于中水平地區。

表4 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Dagum分地區基尼系數
(二)動態演變分析
為了更好反映我國各省份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值變動的可能性及其內部動態轉移趨勢,本文引入馬爾科夫模型及空間馬爾科夫模型進行分析。參考Sergio和Brett(1999)[25],本文將樣本期內各省按照共同前沿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由低到高排序,并使用經典的四分位劃分法,將各省劃分為綠色財政產出低效率(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下分位數)、中低效率(下分位數≤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中位數)、中高效率(中位數<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上分位數)、高效率(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上分位數)四種不同類型,之后運用馬爾科夫模型測算不同產出效率類型的轉移概率矩陣。
1.馬爾科夫模型。由傳統的馬爾科夫模型測算結果可知(5)限于篇幅,具體的測算結果未列出,作者備索。,轉移概率矩陣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遠大于非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綠色財政產出低效率、中低效率、中高效率和高效率類型的省份在下一年度仍維持在原等級的概率分別為69%、46.08%、47.47%和72.55%,表明在樣本期內,不同產出效率類型的省份具有相對穩定性,存在“俱樂部趨同”現象。低效率、中低效率和中高效率類型的省份在下一年度實現效率提升的概率分別為25%、29.41%和21.21%;中低效率、中高效率和高效率類型的省份在下一年度出現效率降級的概率分別為18.63%、24.24%和20.59%。這表明各省能夠通過強化綠色發展低碳技術創新、推動產業結構深度優化等途徑,綜合提升本省勞動生產率和綠色產業附加值,進而推動本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進入更高等級。此外,低效率類型的省份在下一年度有6%的概率提升至中高效率等級,中低效率類型的省份在下一年度有5.88%的概率提升至高效率等級,這表明我國可能會出現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跨級跳躍式”現象,但“跨級跳躍式”轉移的概率相對較低。
2.空間馬爾科夫模型分析。在現實情況下,各省份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等級的提升或下降并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具有廣泛的空間相關性。因此,本文將空間鄰接矩陣(6)由于海南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參考已有研究成果,在空間權重矩陣設置中,設置廣東作為海南的相鄰省份。引入馬爾科夫模型,分析在空間滯后影響下,我國不同類型省份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轉移概率矩陣。
由表5可知,考慮空間鄰接因素(7)穩健性檢驗嘗試更換權重矩陣,使用空間經濟距離矩陣、空間地理距離矩陣和空間經濟地理嵌套矩陣重新進行測算,測算分析結果與正文所得結論保持一致。的影響之后,不同滯后類型下,t年財政產出效率屬于低效率類型的省份在下一年度提升至中低效率等級的概率從傳統馬爾科夫模型測算的25%變為38.46%、19.44%、28.89%和0%,這表明各省之間存在的空間相關性會對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四種不同類型之間的動態轉移產生顯著影響。此外,在部分空間滯后類型下,轉移概率矩陣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出現小于非對角線上的轉移概率的情況,表明在考慮空間溢出效應時,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類型鎖定”概率有所降低。此時,不同產出效率類型省份的“俱樂部趨同”現象會有所減弱,相對穩定性下降,這一現象在產出低效率和高效率滯后類型條件下更為明顯。

表5 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空間馬爾科夫轉移概率矩陣
此外,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等級較高的省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相鄰省份起到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提高相鄰省份在下一年度效率類型向上轉移的概率。以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中低效率類型為例,隨著空間滯后類型的提升,中低效率省份在下一年度提升至中高效率等級的概率為23.08%、27.91%和36.84%。這表明綠色財政產出效率較高的省份能夠有效發揮財政政策的協同作用,通過逐步推行綠色要素市場建設,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在當地形成可操作、可復制、可推廣的綠色發展產出高效率模式,給鄰近省份提供模式參考與制度借鑒,進而產生正向溢出效應。
(三)時空收斂性
馬爾科夫模型的測算結果表明,不同產出效率類型省份之間存在動態轉移的可能性。那么,在具備動態轉移可能性的情況下,隨著時間的推移,擁有不同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省份最終是否會趨向于同一個最優穩態水平?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本文參考Barro和Sala-i-Martin(1992)[26]的處理方法,使用σ收斂和β收斂模型檢驗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時空收斂特征(8)限于篇幅,σ收斂分析結果未列示,作者備索。。
1.σ收斂分析。本文使用變異系數法對2007—2020年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σ系數進行測算。結果顯示,共同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σ系數在2007—2014年呈現曲折下降趨勢,2014—2016年趨于平穩,2016年之后σ系數出現波動上升趨勢。群組前沿下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σ系數的變動趨勢和共同前沿變動趨勢基本保持一致,并未呈現σ系數隨年份的增長而穩定下降的趨勢。總體來看,在樣本期內,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未出現明顯的σ收斂態勢。
2.β收斂分析。β收斂理論認為綠色財政產出低效率省份會對高效率省份進行“追趕”,最終各省份產出效率會趨近于一個相同的穩態水平,實現效率趨同。上文空間馬爾科夫模型的分析結果表明,各省之間存在的空間相關性會對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動態轉移產生顯著影響。基于此,參考Elhorst(2014)[27]的處理方法,本文使用包含固定效應的空間杜賓模型(SDM),引入空間鄰接矩陣、空間經濟距離矩陣、空間地理距離矩陣和空間經濟地理嵌套矩陣進行空間β收斂檢驗(9)在研究過程中,本文還使用面板固定效應和面板隨機效應模型對兩種普通β收斂類型進行回歸,所得結果與空間β收斂結果保持一致,均符合β收斂特征。此外,本文還使用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使用SYS-GMM和FD-GMM模型進行內生性處理,結果依舊符合β收斂特征。,檢驗結果見表6。表6絕對收斂下的列(1)—(4)(條件收斂下的列(5)—(8))分別對應使用上述四種權重矩陣的檢驗結果。

表6 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空間β收斂檢驗結果
由表6可知,不論是否考慮各省存在的現實差異,使用四種空間權重矩陣測算的空間β絕對收斂和空間β條件收斂模型的系數Beta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存在明顯的空間β絕對收斂和空間β條件收斂特征,不同省份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最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收斂于同一個穩態水平。絕對收斂回歸結果表明,若在模型測算中不加入控制變量,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收斂速度分別為4.6364%、4.6360%、4.4112%和4.4718%,半程收斂周期分別為14.9501年、14.9514年、15.7135年和15.5006年。條件收斂回歸結果表明,在考慮各省在政府財政規模、城鎮化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上存在的差異之后,收斂速度顯著提升為6.3573%、6.0402%、6.0556%和8.4324%,并且半程收斂周期也相應縮短為10.9031年、11.4755年、11.4463年和8.2200年。空間β條件收斂速度顯著快于空間β絕對收斂速度,表明各省存在的經濟社會差異會顯著影響本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收斂特征,這也從側面說明本文控制變量的選取具備一定的合理性。此外,不論是絕對收斂還是條件收斂,模型的空間自回歸系數rho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各省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存在明顯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這也從側面證明前文結論的可靠性。
六、結論與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對不同財政發展水平省份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差異和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并探究了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可能存在的區域差異現狀、動態演變趨勢以及時空收斂特征。本文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地區差異逐漸縮小、均衡化水平不斷提升,且效率總體差異變化主要源于財政發展不同水平地區之間的交叉重疊影響;第二,不同產出效率類型省份之間存在效率等級的動態轉移現象和正向空間溢出效應;第三,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不存在σ收斂,但存在明顯的空間β收斂特征,各省的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最終會趨向于同一個最優穩態水平。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對策建議:第一,要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財政政策執行的全過程,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加大綠色低碳技術應用力度,降低綠色財政產出效率損耗;第二,進一步加強對綠色環保的關注度,充分發揮區域差異規劃、政策工具與綠色財政預算之間的聯動效應,提升財政政策效能,逐步縮小我國綠色財政產出效率的總體地區差異;第三,要重視綠色財政產出效率不同類型省份之間存在的空間溢出效應以及收斂性特征,根據各省存在的經濟資源稟賦差異制定適用于當地的綠色財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