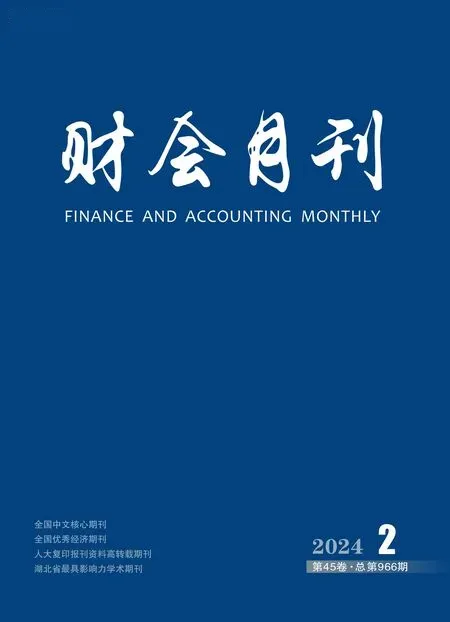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能有效破解“和諧共生”難題嗎
蔡禮輝(博士),孫凌宇(教授),李董林(博士),楊厚玉
一、問題提出
目前,各經濟體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面臨著環境變化帶來的諸多挑戰,環境問題逐步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由此,尋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途徑成為全球性重點問題(解學梅和朱琪瑋,2021)。我國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是遵循綠色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更彰顯了積極應對環境挑戰的大國擔當。雖然“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已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和行動指南,但如何在改善環境效益的同時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仍是我國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國際能源署(IEA)統計數據顯示,2021 年全球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363 億噸,其中,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119 億噸,占全球總量的33%。
全球價值鏈(GVC)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高級形態,標志著經濟全球化進入資源深度整合時代,是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源動力(陳勁,2018)。我國憑借資源要素稟賦優勢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在獲得巨大經濟收益的同時,成為全球價值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蔡禮輝等,2020)。因此,在當前全球價值鏈重構和低碳經濟發展背景下,深入探究我國如何從促進全球價值鏈深化的角度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成為當前亟待研究的重要問題。
綜觀已有研究,有關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文獻主要聚焦于衡量指標測度和影響因素分析上。關于可持續發展績效,部分學者采用環境績效(Fare 和Grosskopf,2010;涂正革和劉磊珂,2011;高贏,2019;孫振清等,2021)和污染排放(Machado 等,2001;Antweiler 等,2001;López 等,2018;楊莉莎等,2019)來刻畫,也有學者使用碳生產率作為代理指標(Kortelainen,2008;王勇和趙晗,2019;楊慶等,2021)。然而,經濟效應和環境效應的協同發展更能有效衡量經濟體是否滿足可持續發展要求,一方面它詮釋了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它詮釋了在保護環境、資源永續利用的前提下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能力。目前,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面臨著兩大緊迫性任務,一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二是保持經濟穩步增長。兼顧碳減排和經濟穩增長的唯一途徑在于提高碳生產率(Beinhocker 等,2008;Sun 等,2018)。因此,本文采用兼顧環境績效和經濟效率的碳生產率指數全面衡量可持續發展績效。
本文關心的另一個問題是探討全球價值鏈地位通過何種內在機制影響工業可持續發展績效。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基于技術視角探討全球價值鏈地位或參與度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王玉燕等(2014)認為,全球價值鏈通過綠色環保、高質量標準為發展中國家企業提供技術支持,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積累不斷增長,獲得更大的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空間,從而降低碳排放量。同時,一些研究指出,技術進步可以顯著提升經濟體可持續發展績效(李平,2017;陶俊等,2017)。由此可見,技術進步可以作為鏈接全球價值鏈與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橋梁。已有研究要么從某一個角度對全球價值鏈作用機制進行分析,要么對作用機制缺乏實證檢驗。因此,本文擬從技術進步、環境規制和結構優化的理論視角探討全球價值鏈地位與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的作用機理,并對其進行實證檢驗。
綜上,本文立足于當前全球價值鏈分工和綠色經濟轉型背景,以我國工業細分行業為研究對象,從理論視角探討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工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作用機理,并通過實證研究驗證其合理性。本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①不僅對全球價值鏈地位與工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關系進行分析,還通過聚焦行業異質性揭示不同行業性質下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差異,豐富了全球價值鏈與可持續發展績效關系的研究,深化了現有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②通過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的中介機制進行檢驗,拓展了全球價值鏈地位發揮作用的渠道,揭開了全球價值鏈和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的“理論黑箱”;③在計算可持續發展績效指標時,充分考慮了化石燃料氧化率的行業異質性并對17種化石燃料和14種工業過程的碳排放數據進行測算,更為準確地衡量了可持續發展績效指標。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技術進步效應
發展中國家企業主要通過技術轉移、學習、吸收、模仿和二次創新等參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實現對現有技術的整合和水平提升,從而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技術進步效應首先體現在技術的有效轉移上。一方面,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將產品生產的某一環節外包給發展中國家企業,為生產出符合環境標準的高質量產品,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會積極向發展中國家企業轉移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中國家企業在生產出符合條件產品的同時,享受到技術溢出紅利,從而不僅能獲取更多的貿易利益還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提升;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時,為節約成本或樹立良好品牌形象,會積極引進母國先進生產技術,甚至有的發達國家企業直接在承接國設立研發中心,以便能生產出更具競爭優勢的高質量產品,這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承接國企業的生產技術水平,進而影響經濟體可持續發展績效。
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技術進步效應還體現在學習、吸收、模仿和二次創新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企業主要以進口發達國家中間產品進行再生產后,將最終消費品出口到其他發達國家的方式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進口高技術含量的中間品不僅可以提升生產效率,還可以通過模仿中間品生產技術逐步提升本國附加值創造能力和能源使用效率。發達國家企業通過不同的方式為發展中國家企業提供“主動溢出”,發展中國家企業積極發揮“干中學”效應,不斷學習、模仿和二次創新,以較低的投入成本實現技術水平的較快增長,進而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此外,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過程中,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將價值鏈質量、環保及安全等標準傳遞給發展中國家企業,會倒逼企業進行技術、管理等革新以提升國際競爭力,減少環境污染,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
(二)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環境規制效應
伴隨著全球經濟和全球價值鏈的不斷發展,世界范圍內的環境規制標準日益提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經濟體為順應經濟發展形勢及應對國際環境壓力,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創新補償效應論認為,合理的環境規制對可持續發展績效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根據波特假說,環境規制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在于科學合理的環境規制能夠倒逼企業進行技術和管理革新,技術革新引致的經濟利益遠遠大于投資成本,從而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產生促進作用。一方面,隨著經濟體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不斷提升,其在全球價值鏈中將更多地參與高附加值綠色生產環節,對產品生產的環境管制也會隨之趨嚴,便會將高耗能、高污染的低附加值生產環節通過外包的方式轉移到更具要素稟賦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承接更具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需要滿足更加嚴格的環保標準,促使企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綠色科技水平,進而提升本國的可持續發展績效。
同時,綠色悖論假說認為,企業一旦產生環境規制越來越嚴的預期,將會預計更多的化石能源消耗量,從而加劇化石能源的開采,能源需求隨之提升,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績效提升。加之,短期內環境規制會通過短期成本的增加從而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即環境規制帶來短期內企業生產成本的增長,企業生產規模和利潤都會受到影響,進而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環境規制效應因區域、規制工具和作用時間的不同而不同。
(三)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結構優化效應
早期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低下,主要以財政和稅收優惠、廉價勞動力和土地低成本優勢吸引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投資設廠,由于中國企業主要利用廉價勞動力成本優勢從發達國家進口來料進行加工、組裝,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長期的價值鏈參與活動使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用于研發的投入也隨之增加,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提升,產業結構也不斷升級,發展方向逐步由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相對勞動密集型行業而言,能源利用率高、消耗量較小,且單位產品獲得的附加值利潤較高,使得可持續發展績效提升。此外,全球價值鏈引致的產業結構升級會帶來生產要素投入結構的變化,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對清潔能源的需求量相對較大,對煤炭等傳統能源的需求量相對較小,而要素投入結構又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關鍵因素(彭星,2012)。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產生積極影響。
綜上,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會產生顯著影響,其核心機制在于經濟體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會提升參與國的技術水平、環境規制水平和優化其產業結構,進而影響附加值創造能力和能源消耗量,最終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這種影響方向和大小由技術進步、環境規制和結構優化三個方面綜合決定,具體有待進一步檢驗。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在充分考慮前人研究成果及前文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本文構建檢驗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影響的面板模型如下:
式中,i 代表行業,t 代表時間。spit為被解釋變量可持續發展績效;ɑ0為常數項;gvcit為解釋變量全球價值鏈地位。本文控制變量包括:技術創新(inv),以專利發明數量衡量;能源強度(ei),以單位產值能源消耗量的自然對數值衡量;外商直接投資(fdi),以外商資本占實收資本的比重衡量;對外開放度(open),以行業貿易額占行業產值的比重衡量;能源結構(es),以煤炭消耗量占能源消耗總量比重的自然對數值衡量;人均產出(pp),以行業產出與行業從業人數比值的自然對數值衡量。θi、μt和ξit分別表示行業的個體效應、時間效應和其他擾動項。
(二)變量測度
1.全球價值鏈地位測度。考慮到即使兩國參與國際分工的程度相同,也會在全球價值鏈地位上存在差異,因此本文參考盛斌和景光正(2019)的做法,采用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來綜合反映中國工業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本文借鑒Koopman 等(2010)的測算方法,基于全球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GMRIO),從增加值貿易視角對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進行測算。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IVir為r 國i 產業中間產品出口所獲得的增加值,FVir為r 國i 產業增加值出口中所包含的國外增加值,Eir為r 國i 產業出口總額。IVir與Eir的比值為前向參與度,FVir與Eir的比值為后向參與度。
2.可持續發展績效測度。根據前文的分析,考慮到單要素碳生產率的核算體現了經濟可持續發展最本質的內涵,即經濟持續發展和污染不斷減少,本文使用單要素碳生產率作為可持續發展績效的代理變量。在計算碳生產率時,參考Shan 等(2018)的測算方法,在充分考慮17種化石能源和水泥工業生產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基礎上,對可持續發展績效進行更為準確的測算。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GDPit為t 時期i 行業的產值,ADij是i 部門j 類化石燃料的使用量,NCVj為凈熱值,CCj為j類化石燃料單位凈熱值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Oij為i 部門j 類化石燃料的氧化率,ADt為水泥數量,EFt為水泥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因子。spit取值越大,說明行業可持續發展績效越高,反之則越低。
(三)樣本與數據說明
鑒于部分指標統計數據始于2000 年以后,本文以2000~2018 年中國工業為研究對象,根據國際行業分類標準(ISIC Rev.4)和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 4754-2017),將多個數據庫的數據進行匹配,最終得到17 個行業的數據,具體如表1所示。
各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與可持續發展績效數據根據上文公式計算而得,數據來源于OECD-TiVA 數據庫和CEADS 數據庫。技術創新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企業科技活動統計年鑒》和《中國科技統計年鑒》,能源結構及能源強度數據來源于CEADs 數據庫,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工業統計年鑒》,貿易開放度數據來源于OECD-TiVA 數據庫,人均產出數據源自WIOD 數據庫中投入產出表(input-output tables)和社會經濟賬戶(socio-economic accounts)。為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對與價格相關的數據進行了平減處理,統一折算為1990年不變價格,并對部分變量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基準回歸
在進行基準回歸前,首先對模型進行了F 檢驗和豪斯曼檢驗。結果顯示,選用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理。表2中第(1)列為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可以看出,全球價值鏈地位與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提升。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經濟體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通過模仿、吸收和二次創新提升生產技術水平,在增加產出的同時降低了碳排放水平,進而提升了可持續發展績效。二是發展中國家參與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跨國公司和國際大買家將全球價值鏈質量、環保及安全等標準傳遞給參與國企業,倒逼企業進行技術、管理等革新以提升國際競爭力,進而促進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提升。表2 中第(2)~(6)列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實證結果。可見,在加入行業特征因素時,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

表2 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
(二)內生性及穩健性檢驗
在沒有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估計結果將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為解決內生性問題對實證結果產生的系列影響,本文參考李鍇和齊紹洲(2011)的處理方法,將被解釋變量的滯后期作為當期值的工具變量,并選取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廣義矩估計(GMM)對內生性問題進行處理。利用工具變量進行估計的結果如表3 所示。從表3中可以看出,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和廣義矩估計方法下,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仍然顯著為正,這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說明在考慮內生性的情況下本文研究結論依然成立。

表3 內生性檢驗
為進一步保證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三種方法對研究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改變估計方法,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回歸分析;二是改變函數形式,將被解釋變量可持續發展績效不作對數化處理;三是替換關鍵變量,借鑒Wang 等(2017)的測算方法對全球價值鏈地位進行測算,利用新的測算結果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和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三種方法下的實證結果都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這說明本文的核心結論是穩健的。
(三)異質性分析
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可能會因為行業性質的不同而存在差異,本文進一步對行業異質性進行分析。具體地,參考《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報告》的行業分類方法,依據耗能量將樣本劃分為高耗能行業和低耗能行業;同時,參考WIOD 行業分類法,依據技術所屬類別將行業劃分為高技術行業和低技術行業。表4 中第(1)~(4)列報告了不同樣本組下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結果。進一步地,本文參考Sandkamp(2020)的研究方法,考察樣本組間差異性,結果見第(5)列和第(6)列。檢驗結果同樣顯示出顯著的差異性。高耗能行業中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較低耗能行業大且顯著,低技術行業中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較高技術行業大且更加顯著。

表4 異質性分析
在高耗能行業中,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有利于高耗能行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提升;而在低耗能行業中,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并不顯著。產生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高耗能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更容易受全球價值鏈低碳、環保、綠色標準限制,倒逼企業進行大力度的技術創新,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進而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二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一般會將高耗能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當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提升時,會減少對其他國家高耗能行業的承接,甚至會將本國高耗能行業生產轉移到其他國家。在低技術行業中,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而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在高技術行業中顯著性較低。可能的原因在于:低技術行業以勞動密集型行業為主,這些行業主要依賴進口中間產品進行加工組裝,參與全球價值鏈會使這些行業學習、模仿國外先進技術,享受技術溢出紅利,進而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而高技術行業容易遭受價值鏈主導者的低端鎖定,不利于全球價值鏈地位效應的發揮。
五、進一步研究:作用機制檢驗
本文進一步對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的作用機制進行檢驗,借鑒呂越等(2020)的檢驗方法,構建機制檢驗模型如下:
式中,pathwayit為影響渠道,包括技術進步(techit)、環境規制(enviit)和結構優化(strucit)。本文使用研發投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作為技術進步的代理變量,使用工業污染治理運行費用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作為環境規制的代理變量,使用各行業產值與總產值之比作為結構優化的代理變量。其中,技術進步相關數據來源于《中國企業科技活動統計年鑒》《科技統計年鑒》,環境規制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數據庫》,結構優化數據來源于OECDTiVA 數據庫。
表5 列示了作用機制的檢驗結果。第(1)~(3)列為全球價值鏈地位對技術進步、環境規制和結構優化的影響,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對三者的影響至少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有利于技術水平、環境規制水平的提升和產業結構的優化。第(4)~(6)列為加入核心解釋變量和渠道變量后的實證結果。第(4)列為加入技術進步變量后的結果,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可以通過提升行業技術水平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第(5)列為加入環境規制變量后的結果,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有利于環境規制水平的提升,進而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環境收益假說認為,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企業會更加熟悉國際環境標準及國外消費者的環境偏好(蔡禮輝等,2020),全球價值鏈地位越高的經濟體,越會不斷提升自身環境管理水平和遵守及制定高環境標準,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示范者和指導者角色,從而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第(6)列為加入結構優化變量后的結果,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進而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有利于經濟體在精細化供給的同時向高端化產品和服務邁進,從而形成優質高端的供給體系,最終有利于產業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提升。總體來看,全球價值鏈地位主要通過三種渠道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并且呈現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

表5 作用機制檢驗
六、結論與啟示
經濟全球化和社會經濟轉型背景下,我國工業經濟發展面臨“雙重悖論”:一方面,經濟發展面臨日趨嚴格的環境規制;另一方面,礙于生產技術水平限制,我國工業主要位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履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的能力亟待提升。而悖論的根源在于忽略了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需要嵌入本土的“和諧共生”理念。據此,本文基于全球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GMRIO),構建“全球價值鏈地位—技術進步、環境規制、結構優化—可持續發展績效”的邏輯框架,深入探究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內在機理,實證檢驗二者之間的內在關系,采用多種內生性和穩健性檢驗策略提高模型的無偏性和一致性。研究發現:全球價值鏈地位與可持續發展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績效的改善,主要通過技術進步、環境規制和結構優化等三種渠道來實現;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存在顯著的行業異質性,這種異質性體現為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可持續發展績效的影響在高耗能行業和低技術行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啟示:第一,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強化經濟發展的內源性和可持續性。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這就要求經濟增長方式要更加強調內源性和可持續性,企業在生產過程中要注重技術創新,積極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的全過程,從而保證在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同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價值鏈上下游布局。從源頭上調整優化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低碳化。根據行業不同特征,采取差異化的環境規制政策,嚴防高污染、高排放行業向國內轉移,同時延長價值鏈,將附加值含量低下的環節轉移到更具要素稟賦的經濟體進行生產,從而提升我國可持續發展績效。第三,推進全球價值鏈升級,深度參與國際合作。實施國家區域價值鏈戰略,在關鍵領域和環節構建中國主導的低碳價值鏈體系,加強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國家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合作,在全球價值鏈重構中掌握主動權。
【 主要參考文獻】
解學梅,朱琪瑋.企業綠色創新實踐如何破解“和諧共生”難題?[J].管理世界,2021(1):128~149+9.
蔡禮輝,張朕,朱磊.全球價值鏈嵌入與二氧化碳排放——來自中國工業面板數據的經驗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20(4):86~104.
高贏.中國八大綜合經濟區綠色發展績效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9(9):3~23.
楊莉莎,朱俊鵬,賈智杰.中國碳減排實現的影響因素和當前挑戰——基于技術進步的視角[J].經濟研究,2019(11):118~132.
王勇,趙晗.中國碳交易市場啟動對地區碳排放效率的影響[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1):50~58.
盛斌,景光正.金融結構、契約環境與全球價值鏈地位[J].世界經濟,2019(4):29~52.
Kortelainen M..Dynamic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alysis:A Malmquist index approach[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4):701~715.
Beinhocker E.,Oppenheim J.,Irons B..The carbon productivity challenge:Curbing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ing economic growth[R].Mc 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08.
Shan Y.,Guan D.,Zheng H.,et al..China CO2 emission accounts 1997-2015[J].Scientific Data,2018(1):17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