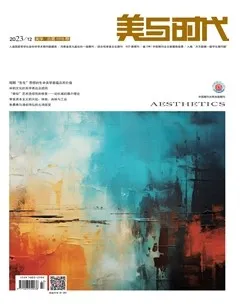文圖關系:文學與拉斐爾前派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摘? 要:圖像的本質(zhì)仍是敘事。拉斐爾前派受到文學影響,圖像富有詩歌性,具有文學研究意義。他們的繪畫技法承襲古典準則,詩學和法學的內(nèi)在精神蘊含其中,自然場景和人物形象營造愛與秩序的沖突對抗,由此生成美感,并促生語言流變。“青春、力量和熱情”的年輕畫派富有活力,而他們內(nèi)在的秩序感使其在美術(shù)史上留名。本文通過研究文學與拉斐爾前派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闡明藝術(shù)圖像內(nèi)部的語言流動,論證圖像敘事對圖像表現(xiàn)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拉斐爾前派;圖像;敘事
一、拉斐爾前派的美學價值:改變和創(chuàng)造
討論拉斐爾前派的潮流起源于藝術(shù)和科學的爭辯,這也是羅斯金發(fā)起的一場藝術(shù)工藝運動的開始。羅斯金的《建筑的七盞明燈》幾乎在維多利亞風格之后開啟了整個美國自然建筑風格的潮流。維多利亞風格和傳統(tǒng)的古典風格被認為矯揉造作,樸素簡單的自然風格成為整個藝術(shù)工藝的核心。拉斐爾前派的藝術(shù)風格和羅斯金的藝術(shù)理念不謀而合,因此,拉斐爾前派自然成為工藝美術(shù)運動的核心力量。盡管他們的繪畫技巧仍然講究精細,反對平庸和瑣碎,但是他們提倡回歸自然真性情的主旨被推到藝術(shù)高潮。繪畫風格里內(nèi)在的詩歌性被解讀為藝術(shù)的生命,因而這一畫派也被歸納為古典美學之后的自然美學典范。他們“認為文藝復興的錯誤在于,文藝復興的藝術(shù)家們認為藝術(shù)和科學是一樣的,他們沒有意識到,科學證明已經(jīng)知道的事情,而藝術(shù)是在改變、產(chǎn)生、創(chuàng)造和影響人類的感官和人類的靈魂。”[1]自然藝術(shù)維系了本土風格的神話,詩人和詩歌的存在避免了物質(zhì)和精神生活的不平衡發(fā)展。自然美學傳遞了自然圖像中尋找每一部分的象征和整體的象征意義,將心靈寄托在自然生長的事物之中,“詩人直觀地閱讀和翻譯所有自然和人造的東西作為神圣心靈的符號。”[2]43-68在建筑中增加植物圖像的浮雕圖像,增強建筑的生命力,成為1860到1870年間美國重要的建筑風格[2]48。植物顯現(xiàn)出的簡單流暢的線條最終被用在拉斐爾前派的繪畫中,表現(xiàn)出歷史、當下和向未來生長的藝術(shù)生命。
植物生長的繪畫過程被認為是具有少女生命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風格。將植物的特性和少女的性格貼切地合二為一,是自然畫派神化女性的巔峰。盡管這種繪畫風格看起來清新樸素,但是,只有具備很高藝術(shù)天分的藝術(shù)家才能通過流暢線條創(chuàng)作出自然畫派的典型風格——生命力。拉斐爾前派顯然也在建筑上顯現(xiàn)了才華,這一創(chuàng)作風格已經(jīng)擴張到任何一種接受自然美學的藝術(shù)家手上,他們在建筑浮雕上用植物替代了古希臘的女神圖像,增添了大自然的氣息和神話美學的神秘感。
二、語言流變:喬叟和拉斐爾前派
圖像敘事風格對畫家格外重要。畫家通過虛構(gòu)真實表現(xiàn)美,通過描繪經(jīng)驗敘述真實,通過多人物場景展現(xiàn)多重敘事,增加繪畫的層次感。拉斐爾前派深受文學家的影響,其圖像敘事帶著大文學家的印記。莎士比亞、喬叟、達芬奇和歌德都為他們提供了創(chuàng)作靈感。以喬叟為例,我們可以初步理解文學對這一畫派的潛在影響。作為一個世紀語言流變的促發(fā)者,喬叟“愛與美”的自然主義風格十分明顯地體現(xiàn)在拉斐爾前派的作品之中。
喬叟的一生具有傳奇色彩,富有騎士精神。他改變了拉丁語和法語寫作的傳統(tǒng),被譽為“英國文學之父”。喬叟筆下的文學故事,真實與虛構(gòu)相互交織,夢幻與現(xiàn)實交錯,背靠廣闊的歷史環(huán)境,文化交混,上下階層流動,美與錯愕碰撞出火花,以英語文學的方式開啟了新的時空。喬叟有極高的文學素養(yǎng),受過專業(yè)的法律訓練。他的作品中展現(xiàn)了其詩學與雄辯術(shù)的造詣,同時也體現(xiàn)了中世紀基督教美學和文藝復興風格。在喬叟生活的年代,英格蘭民間文學少能登上大雅之堂,但喬叟結(jié)合了法國宮廷文學的傳統(tǒng)和古羅馬文學的崇高精神,其詩學既有宮廷色彩,又有神學之神秘性,同時對民間生活的自然風尚的描繪也栩栩如生。“經(jīng)驗性”的表達是喬叟的典型風格[3],他有與“天才般的靈感”完全不同的生活氣息,“超驗的”神學思想較少是作品的中心。喬叟在1385年被指派為肯特郡的治安法官,次年選為下議院議員。1387年,喬叟的妻子過世,他的精神受到重大打擊,加之上層政局變動[4]5-6,他在創(chuàng)作《坎特伯雷故事》的時候文學風格自然而然偏向朝圣文本。朝圣文本蘊含柏拉圖精神,結(jié)構(gòu)主義難以闡明。傳奇式的情感美學依靠靈感頓悟,中間夾雜著美與痛苦。相較傳統(tǒng)的理性美學,喬叟的文學風格自然奔放,富有神性的騎士精神影響了整個拉斐爾前派的畫風。
到14世紀末,英國社會對喬叟偏愛有加[5]。上層社會的拉丁語風格使下層百姓脫離良好教育,拉丁語的文書風格措辭嚴謹復雜,語言封閉,缺乏靈活性和生命力,仿佛古老的印記。而喬叟通過簡單的英語語言將法律和道德知識融入詩學故事之中,文風樸素自然,使整個社會逐漸發(fā)生語言轉(zhuǎn)向。以《公爵夫人之書》為例,這首詩歌是喬叟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甜蜜的愛情環(huán)境和悼亡傷痛合二為一,字句的比喻開放而跳躍,具有音樂性和運動性,在當時帶來較大的影響。在《聲譽之堂》的創(chuàng)作中,神學色彩已十分明顯。阿波羅太陽神引導詩人進入神思,聲譽女神在眾人的懇請下賜予“美好的聲譽”,喬叟和所有詩人一樣,重視自己的名譽。后期《坎特伯雷故事》現(xiàn)實與夢幻交織的文學風格已經(jīng)展現(xiàn)出美學的新高度——美不再停留在詞匯的表達,而是擴展到真實的器物、人文與社會風尚。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風采已油然而生,審美思維從下至上發(fā)生轉(zhuǎn)變,美學的信徒不再局限于上層民眾,普通大眾也獲得了審美和審美批評的權(quán)利[6]。“愛與律法”是喬叟的常見主題,在《眾鳥之會》開篇,喬叟談及刑律、書法,又談及星辰、地獄,他說愛情的時候稱“我逐漸地見有一抹微乎其微的光線”。高貴的品性以比喻的方式留在詩篇之中,符合所有詩學的共同之處。“五月是良辰之始,這時殘冬凍死的花卉怒發(fā),鮮麗的藍、白、紅,各色相稱著,田野中吹著花香;費白斯的陽光照耀,從白牛宮中放出光芒……”[4]133神學的隱秘知識在真實的四季更替中顯得優(yōu)雅自然。喬叟的語言不再是宗教精神的復制轉(zhuǎn)述,而是真實生活的再創(chuàng)作,使藝術(shù)有了生命力。這種風格帶來的想象力直接影響了拉斐爾前派的繪畫主題:自然景物增加夢幻色彩,人物的線條與草木融為一體,別具一格。
福特·馬多克斯·布朗創(chuàng)作的《喬叟在愛德華三世的法院》[7]17是拉斐爾前派受到喬叟影響的佐證。
這幅藝術(shù)作品是典型的意大利古典主義的風格,線條封閉,人物表情清晰,雖然心理刻畫不如喬托風格鮮明,但是細微之處還是體現(xiàn)了人物的內(nèi)在情感。圖像中不再全是宗教式的人物形象,各個階級的人物均有體現(xiàn),莎士比亞、斯賓塞和但丁都置身其中。基督教的符號隱藏在人物服飾和自然背景之中,騎士形象十分鮮明,《玫瑰傳奇》的意象巧妙地置于畫面中心,依然保持了“圣物”的色彩。喬叟幾乎將“玫瑰”符號化為“愛情”的象征,連接著舉止優(yōu)雅得體的宮廷貴族。這種“自在之物”的美感脫離了神學,進入文學領域。符號有了“詩性”與“正義”的交織。“騎韻”是喬叟的創(chuàng)新風格,開放與封閉交疊的英雄對句“符合新古典主義的藝術(shù)原則”[8],這是古典主義詩歌的發(fā)展,增加了語言的開放性和想象力。這種詩歌風格,也影響到了拉斐爾前派的繪畫風格。騎士文學內(nèi)在的正義與反叛是拉斐爾前派與喬叟最具親緣性之處。其中,布朗尤其喜歡將與法律相關的元素放于繪畫作品之中,相較于其他畫家,他個人的政治色彩十分鮮明[9]。他對“體面和責任”的關注遠高于其他畫家,喜歡將報紙上刊登的法律問題放在繪畫作品中,增加作品的社會關注度。
喬叟在法院任職時尚未受到職業(yè)挫折,因此這副繪畫作品中的人物表情幾乎看不到痛苦。這一時期喬叟的文學風格還具有法語文風,后期才日漸出現(xiàn)叛逆風格。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喬叟已經(jīng)同時出現(xiàn)自然粗糙與優(yōu)美靈動的詞語,個人內(nèi)在的裂痕通過“朝圣”文本逐漸化解,恰如其分的“得體”文風穿插了生活氣息。15世紀,喬叟的美譽使他與薄伽丘和彼特拉克齊名。到16世紀,英國開始清理一些不適宜社會發(fā)展的文學文本,喬叟的作品轉(zhuǎn)而成為為數(shù)不多還能夠被閱讀的文學,他作品中展現(xiàn)的民族性團結(jié)了社會更廣泛的群體力量。實際上,考慮到《圣經(jīng)》長久以來對普通民眾有太多束縛,喬叟的自然風格的確帶來了社會變革的曙光。這種文學流派對繪畫風格的形成至關重要。
喬叟的敘事風格推動大眾審美的轉(zhuǎn)變,影響了后來拉斐爾前派的創(chuàng)作風格。語言變革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必然產(chǎn)生影響,繪畫內(nèi)在的圖像精神因此存在明顯差異。拉斐爾前派是典型的具有柏拉圖精神和斯賓塞“愛神”精神的畫家流派,他們的繪畫風格承襲古典主義,但圖像缺少宗教束縛,喜好從文學和詩學中尋找靈感。因為沒有受過法律訓練,他們不具有喬叟的騎士精神,但風格因貼近自然神性,需要批判性的欣賞。他們在畫風中展現(xiàn)出反叛的一面,雖然缺少美感,但更加真實,能夠通過藝術(shù)的手法展現(xiàn)出普通大眾的精神風貌,將現(xiàn)實主義與夢幻交織在一起,從而在藝術(shù)史上留下痕跡。
三、唯美主義:拉斐爾前派的內(nèi)在詩性
拉斐爾前派遵循意大利的古典技法和圖像情感的內(nèi)在統(tǒng)一,主題性“反叛”具有政治隱喻和情感宣泄的作用。長久以來,宗教藝術(shù)是西方古典繪畫的中心,保持傳統(tǒng)是首要選擇,但是,繪畫主題的創(chuàng)新必不可少,宗教只會束縛藝術(shù)家的想象力,所以,從文學中尋找繪畫靈感是年輕藝術(shù)家的必然選擇。古典主義的主題越來越稀有,浪漫主義文學作品成為拉斐爾前派創(chuàng)作靈感的首選。中世紀神秘主義和文藝復興的欣欣向榮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符號成為文學與神話的連接點。喬叟的騎士精神和英雄主義引導了拉斐爾前派的創(chuàng)作情感,“忠于自然”是他們的行動準則。
帶有文學色彩的自然描繪脫離了現(xiàn)實主義,為大自然增加了一些奇幻色彩,這種圖像敘事的本質(zhì)仍然是詞匯和符號的延異。以米萊最出名的《奧菲利婭》[7]49為例,女性主義文學色彩在《奧菲利婭》的圖像中顯現(xiàn)出魅力。拉斐爾前派打破傳統(tǒng)將女性囿于封閉空間的古典畫風,將她在自然之中,與開放的世界合二為一。這幅繪畫作品的人物、場景和畫面源于《哈姆雷特》“奧菲利婭之死”的場面。繪畫場景哀怨矛盾,主角躺在綠草叢生的河床之中,色彩斑斕的痛苦令人感覺到悲劇的最高藝術(shù)。隱喻在圖像中通過植物、色彩和姿勢表現(xiàn)出來。她手中的彩色花卉是五彩斑斕的生命力的象征,而兩岸的白色花卉則是死亡和蒼白的表征,這種色彩沖突對立,是典型的深層次圖像隱喻。綠植的生命性又與人物的死亡融為一體,生死主題表現(xiàn)明顯,心理色彩更貼近自然人性,產(chǎn)生獨特美感。
這種美學性意象成為圖像敘事的“外觀”,內(nèi)在的品質(zhì)仍然是繼承了唯美主義的純粹美學色彩。難以否認,圖像敘事因為有了喬叟和斯賓塞的影子增加了古典高雅,將詩歌的敘事風格與繪畫融為一體,把符號的情感敘事發(fā)揮到極致。但是,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色彩仍然保留在這幅畫中。一個世紀的漫長壓抑,致使藝術(shù)作品中仍然“揭示了一個高度自我意識的時代所存在的一些隱藏的神經(jīng)癥。”[10]當然,盡管拉斐爾前派以唯美主義著稱,他們的政治性仍然體現(xiàn)在圖像、尤其是對女性的繪畫之中——一種對維多利亞時期婦女遵從的反抗。維多利亞時期以來對“婦女貞潔”的推崇,被拉斐爾前派認為是虛偽和欺騙,因為他們放棄了家庭場景的圖像描繪,而將所有非家庭以外的場景隱喻為“婦女的冒險”。“家庭被定義為道德和社會秩序的基礎。尤其是在商業(yè)和城市社會,家庭是作為危險地的比照,認為家庭是其他地方的價值觀和情感的源泉。象征家庭的最常見的圖像表現(xiàn)為是天堂或庇護所。”[11]
虛構(gòu)性敘事的風格使繪畫作品具有獨創(chuàng)性。神話和世俗世界在圖像內(nèi)部互動,圖像再現(xiàn)內(nèi)在隱藏的文本,這種文圖關系使藝術(shù)品獲得生命。如果圖像本身沒有詩學和文學為依托,圖像就會喪失敘事的生命力,因此,純粹的宗教繪畫死氣沉沉,而自然主義畫風則生機勃勃。拉斐爾前派始終保持著專業(yè)技法,沒有脫離傳統(tǒng)的古典英雄敘事流派。唯美主義昭告了興盛的理由——藝術(shù)的美感可以控制在理性的層面,諷喻的叛逆不會走到離經(jīng)叛道的地步。悲劇式的古典美德蘊藏在整個畫面中,內(nèi)在的文學文本使整個圖像敘事在閉合和開放之中游走。《奧菲利婭》將圖像封閉在一個場景中,而這個場景可以延伸到整個《哈姆雷特》,甚至是莎士比亞的整個悲劇精神。藝術(shù)必然是生死之表現(xiàn),甚至超越生死。人神同體的人物形象放置于大自然中,與自然之奧秘又結(jié)合在一起,自然景物使繪畫具有神性。
文學的敘事傳統(tǒng)在圖像中顯得更為重要,尤其是內(nèi)涵文化政治學的藝術(shù)作品在文學批評史上占據(jù)核心地位。文學藝術(shù)、社會政治與詩性主義的結(jié)合,是藝術(shù)作品能長久流傳的關鍵。無論“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唯美主義在一段時期如何受人追捧,最終受歷史檢驗的仍然是文化政治藝術(shù)作品。即使是較為邊緣的拉斐爾前派藝術(shù)風格,最受關注的也是具有莎士比亞詩學風格的《奧菲利婭》和法學藝術(shù)流派《喬叟在愛德華三世的法院》。這并非是一種偶然出現(xiàn)的藝術(shù)風格,是歷史之必然。哲學、政治學和美學理論進入藝術(shù)學界,會帶來新的學院藝術(shù)批評潮流,后現(xiàn)代和新批評派會漸漸失寵。在圖像藝術(shù)作品里,內(nèi)在文本的對立、張力、反諷、暗喻和悖論都需要文學分析一一闡明,這樣既有利于對圖像的深入了解,也有利于對圖像再創(chuàng)作的思想深化。顯然,在藝術(shù)圖像作品中存在獨立的文學話語和自主世界,深入挖掘圖像的內(nèi)在詩性是創(chuàng)建文學藝術(shù)獨立宇宙的重要方法。盡管,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理論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間,但是內(nèi)在的整合才是藝術(shù)作品真正尋求的結(jié)果。現(xiàn)實與虛構(gòu)能夠巧妙地合二為一,作品和作者的二元沖突可以逐步調(diào)和,混亂的藝術(shù)流派開始走向井然有序,最終藝術(shù)的文本向世界開放,而非封閉在圖像之中。
四、結(jié)語
文學與拉斐爾前派的聯(lián)系通過符號之隱喻實現(xiàn)。作為一種圖像敘事的藝術(shù)符號,可以生產(chǎn)哲學和詩學的意味。敘事隱藏于圖像之中,文學的生命性在符號之間流動[12]。這種圖像敘事既有直覺主義的神秘感,也有理性主義的思辨性。自然與秩序?qū)αf(xié)調(diào),在情感與理智的對立沖突中,畫家能集中表現(xiàn)情感,實在難能可貴。他們更多受到學院派的影響,宮廷式秩序束縛感較少,風格自由,情感充沛。他們順利地將使用古典技法的藝術(shù)作品普及到普通群眾,這也正是拉斐爾前派的意義之所在。符號的隱喻原本是流動的,固定的符號體系由經(jīng)驗帶來。文學在藝術(shù)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恰恰是在固定的文本中實現(xiàn)想象的張力。圖像敘事應力求達到文學流派中心靈“凈化”的效果,從騎士文學過渡到完美神性的心靈結(jié)構(gòu)。貼近大眾生活的繪畫風格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主義的生命力,描繪傳統(tǒng)的高尚品行也尊崇了古典美學的德性。無論如何,堅持真理的藝術(shù)風格可以站在美術(shù)史的頂端,藝術(shù)回到自然神性,得以體現(xiàn)藝術(shù)的真正價值。
參考文獻:
[1]Lawrence Wodehouse."New Path" and the American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J].Art Journal,1966(4):351-354.
[2]Lauren S. Weingarde.Naturalized Nationalism A Ruskinian Discourse on the Search for an American Style of Architecture[J].Winterthur Portfolio,1989,24(1).
[3]A. Blamires.Chaucer Manifesto[J].The Chaucer Review,1989(1):29-44.
[4]喬叟.眾鳥之會[M].方重,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
[5]Susan E.Phillips.Chaucer's Language Lessons[J].The Chaucer Review,2011(1-2):39-59.
[6]David Raybin and Susanna Fein.Chaucer and Aesthetics[J].The Chaucer Review,2005(3):225-233.
[7]斯哲哈吶.拉斐爾前派[M].鄭軍榮,唐娜,張雯靜,譯.南昌:江西美術(shù)出版社,2018.
[8]肖明翰.喬叟學術(shù)史[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2:62.
[9]羅斯.拉斐爾前派[M].北寺,譯.長沙: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2021:10.
[10]Jan Thompson.The Role of Woman in the Iconography of Art Nouveau[J].Art Journal,1971-1972(2):158-167.
[11]Lynn Nead.The Magdalen in Modern Times: The Mythology of the Fallen Woman in Pre-Raphaelite Painting[J].Oxford Art Journal,1984(1):26-37.
[12]牛宏寶.圖像隱喻及其運作[J].文藝研究,2022(6):5-22.
作者簡介:吳雨帆,浙江大學文藝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理論、藝術(sh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