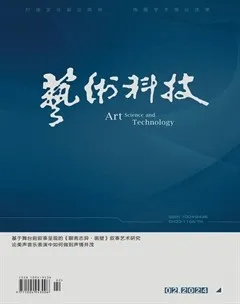災難文學中的英雄形象研究
李雅舟 陸王妤佳 張丁睿
基金項目:本論文為2023年度揚州大學大學生實踐創新訓練計劃項目“災難文學中的英雄形象”研究成果,項目編號:202311117159Y
摘要:目的:第一,梳理界定相關概念范圍,提供災難文學研究新視角。文章從“人”這一元素入手,提供了一個基于人的行為模式及心理機制的研究角度。第二,從更廣闊的社會心理學領域闡釋災難文學的內在邏輯。第三,災難文學將意識災害轉變為災害意識,將非理性的感知轉化為理性的思考與感性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啟發了讀者思考生命的意義,對青少年生命意識的塑造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第四,發掘災難下民族精神的閃現及災難文學的療愈作用。方法:通過明確災難文學的相關定義,梳理古今災難文學,并與其他題材作比較得出結論。結果:提高了災難中媒體與大眾對受難者的關注度,構建了受難者的英雄形象,完善了災難文學的敘事倫理與社會功能,提升了災難文學的審美價值。同時立足于當代青年的危機、生命意識淡薄,學校對災難文學不夠重視的現實情況,以災難文學的特殊性構建受難英雄的形象,加強生命教育,并拓寬災難文學的理解空間,增強其對讀者尤其是青少年的感染力,激發災難文學的活力。結論:文章以災難文學的英雄形象為研究對象,基于對災難文學的研究和反思,構建受難者英雄形象,提升災難文學審美價值,并據此開展生命教育,增強現代青少年的生命意識,災難下的民族精神及災難文學的療愈作用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
關鍵詞:災難文學;英雄形象;生命意識
中圖分類號:I10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2-00-03
頻繁的災難誕生了題材豐富、數量眾多的災難文學。災難發生之后,災難文學作品應聲而動,然而媒體報道的重點、群眾關注的焦點、文學表現的亮點逐漸呈現出從受難者向救難者轉移的趨勢,對承受災難的主體——受難者的關注度降低。這也反映出我國當代災難文學的不足,即數量眾多的災難文學作品呈現出淺表性特點。“許多作品只是一味地展覽災害中的苦難,歌頌各路救援英雄,書寫多難興邦的國家形象,這與古代的大禹治水、女媧補天等神話所形成的英雄救災模式沒有本質區別。災難文學除了書寫悲天憫人的情懷、英雄主義的頌歌以及國族的認同之外,好像就沒有什么可以去思考和表達的了。”[1]經過時間沉淀和深刻思考后形成的災難文學作品極少,這造成了災難文學災難意蘊與精神深度的欠缺。現階段災難文學還停留在紀實作品和直接抒情的階段,沒有進一步挖掘人類面對災難的精神世界及倫理思考。災難文學想要豐富作品意蘊,發掘更深刻的意義,必須突破對災難淺表層次的書寫,直面可怖的災難與面臨重重困難的受難者,不再將災難符號化、數字化,而是在展現真實災難情景的基礎上,不斷挖掘災難重壓下生命的價值與人性的力量。這也是建構受難者英雄形象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本文在整理劃分受難者和救難英雄形象的基礎上,著重建構災難文學中受難者的英雄形象。
1 災難文學中英雄的定義
英雄一直是文學書寫的主題,是敘事中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核心力量,而災難文學作品對英雄的歌頌往往集中在救難者身上。的確,舍己為人的救難者本身就擁有鮮明的英雄底色,凸顯他們無疑具有正面意義。但是,災難文學如果只停留在歌頌救難英雄上,就很難開發出更深廣的意義空間。災難中的受難者并不是只能處于被同情、被援助、被憐憫的位置上,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受難者中同樣存在英雄形象。盡管身處災難中的他們或許沒有力量去拯救他人和社會,但堅強樂觀地面對災難的態度與不輕言放棄的精神等同樣具有震撼人心的生命力。這種力量也很能感染人,具有鼓舞人心的積極作用。對受難者與災難本身的關注,能讓讀者充分感受到生命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下的頑強和堅韌,體會災難中受難者求生的本能,進而思考生命價值與自我存在。
2 災難文學中的英雄形象劃分
災難一旦發生,人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兩種身份,即受難者與救難者。可以說,災難之下沒有非受難者,一些人面對災難挺身而出,主動擔當,是災難中最容易被看見的正面力量。當代文學作品中出彩的救難者形象不勝枚舉,如遲子建的《白雪烏鴉》就塑造了一個勇于承擔責任、不懼權威的醫學家伍連德。而受難者作為災難的直接承受者,如地震廢墟里的災民等,面對災難,忍受折磨,掙扎求生。之所以要建構災難文學中受難者的英雄形象,就是因為受難者直面極端的災難情境,更能表現人在苦難重壓下的抗爭精神,并洞悉生命的奧秘。苦難是災難文學的基本底色,向寶云提出:“災難文學要完成對災難的超越而實現苦難敘事。”[2]也就是說,災難文學不能止步于救災敘事以及對災難情境的記錄,更要體現人在苦難中的抗爭、力圖掙脫災難帶來的消極影響的種種行動和嘗試,使災難文學作品打破時空限制達到更高的境界,體現人類生存的普遍意義。
受難者與救難者的界定是相對的,只是作為一種身份的表現,一個人可以具有多重身份,如兼具受難者與救難者的雙重身份并在某種情境中進行身份轉換。災難中的救難者同樣承擔著災難造成的破壞,可以說,災難下受難者就是最基本的底色。而在地震、洪水、疫病等災難發生后,我們還能看見許多志愿者穿梭在現場,這些受難者在自救之余,完成了從受難者向救難者的轉變。
3 受難者英雄形象建構
3.1 頑強的求生意志
“人類在未曾經歷滅頂災難之前,很難想到生存對于生命的含義,也很少意識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樣的堅韌與頑強。”災難和死亡是河流的上下游,沒有體驗過死亡威脅的人是無法想象自己生命的極限的,而死亡意識與生命意識緊密相連,正是產生了死亡無法避免的認知,人才意識到自己生命的存在與價值。許多以災難為背景的小說將目光聚焦于災難之外的因素,而報告文學注重真實記錄災難情境下受難者的生存樣貌。錢鋼的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渴生者”這一章節,展現了一連串突破生命極限的奇跡,彰顯了人類生命的堅韌。這些渴生者,讓讀者看到了人性中最頑強的一面。
3.2 強大的心理素質
生命既頑強、堅韌,又懦弱而脆弱,錢鋼感嘆:“常常,生命的消失不僅僅在于外在的災難,更在于虛弱的人類本身。”他在《唐山大地震》中寫道,“他們并不是死于建筑倒塌而導致的砸傷或者擠壓傷,他們完整的尸體上有著一道道的、指甲摳出的暗紅色的血痕,觸目驚心;那是他們絕望時瘋狂抓撓留下的印記”,這些遇難者在極度的恐懼中精神崩潰,自己“殺掉”了自己。人類想要與死亡抗爭,就必須具備強大的心理素質。在鋪天蓋地的災難面前,人無疑是渺小的,但總有人能以自身的智慧和能力鑿出一條生路,展現了人在苦難中的主動性和行動力。
3.3 向死而生的心態
遲子建在《白雪烏鴉》中建構了王春申這樣一個“平民式英雄”,其實這本小說就是以鼠疫下的平民為主角,描繪了瘟疫下廣大受難者的生存圖景。這些平凡甚至卑微的生命直面死亡,與瘟疫抗爭。鼠疫讓這座小城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但人們以向死而生的精神凝聚微薄的力量,用生的力量擊敗了對死的恐懼,用堅忍的意志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些隱沒在蕓蕓眾生中的普通人,在災難面前變得高大偉岸起來,他們被遮蔽的人性得以綻放。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對人無法避免的死亡給出了一個終極答案:生命意義上的倒計時法——“向死而生”。正如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把人逼上絕路,人在精神上是無法覺醒的,而《白雪烏鴉》中的災難情境就作為死亡的絕境,激發了小說人物的覺醒,他們的生命因內涵的豐富而延長。
3.4 齊心協力的團結精神
災難發生后,原本素不相識或關系冷淡的人們在災難中攜起手來,互相幫助渡過難關。《唐山大地震》也記錄了幾戶人家在震后相互扶持,互幫互助,甘苦同嘗。地震雖然導致地面嚴重開裂和拱起,卻彌合了人們心中的疏離。不少作品也關注到了自然災難下人心理的轉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人人都被思想變革所裹挾,部分人的價值觀逐漸被扭曲。歌兌的長篇小說《坼裂》就以四川大地震為背景,基于大地坼裂引發的種種現象去探尋當代社會和當代人潛在的心靈的坼裂,小說男女主人公林絮和卿爽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迷茫困惑尋找自我,卻在天崩地裂的災難里、出生入死救死扶傷的考驗中逐漸確認了自己生命的價值。“汶川大地震這樣的大自然的‘坼裂’災難非人力可以阻止,但是當代社會的人心的‘坼裂’卻并非不可救藥。”[3]在人力無法抵抗的災難中,人們明白了個體生命的脆弱,看清了自身價值取向的局限性,開始回歸社區與家庭,重新思考當下的生活。
4 災難文學中英雄形象的現實意義
4.1 英雄形象的建構
英雄作為崇高化的人的形象,承載著人民對理想化人格的想象,也蘊含著人民對民族倫理價值觀的取向。然而,在當代網絡語境下,崇高的傳統價值面臨嚴峻的挑戰,有關英雄形象的記憶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一方面,網絡碎片化的傳播模式難以構成完整且嚴謹的歷史記憶。某些自媒體在英雄事跡的傳播中簡化了英雄的行為動機,夸大了英雄的具體行為,讓本應偉大的英雄行為淪為刻奇心理的產物。另一方面,網絡的解構性對英雄形象造成了潛在的危害。在泛娛樂化的互聯網環境中,英雄的莊嚴性被世俗消解,甚至出現了丑化、矮化英雄的現象。這與其說是信息傳播,不如說是一種娛樂和消費。傳播者在否定英雄本人的同時,也否定了英雄所處的歷史與社會環境。因此,文學應當通過自己的方式重塑人們對英雄的認知。災難文學由于其歷史性與紀實性,能夠深化民眾對災難事件的認知,形成較為完整的災難記憶。同時,災難文學也贊頌災難中人的情感與精神的高貴。英雄與普通人并無地位上的高低和能力上的明顯差別,這使英雄的所作所為更易得到讀者的理解與尊重。此外,由于災難文學創作的全民性,英雄形象的建構將有望形成自下而上、共同參與的局面。在愛國主義教育中,英雄形象的建構多由官方主導,民眾自發的紀念活動較為少見。而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全民創作熱潮的涌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文字鏈接他人的記憶,依托災難文學,形成一座座救難英雄的紀念碑。
4.2 災害意識及生命意識的塑造
建構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塑造災害意識及生命意識,由于災難的偶發性,人們對災難的感知也是不連續的。通常而言,群眾對災難的感知是滯后的,且這種意識往往混雜著恐懼、痛苦等非理性因素,對人們將來面對類似災害并無正面價值。而災難文學將意識災害轉變為災害意識,將非理性的感知轉化為理性的思考與感性的認知。同時,災難文學對生死的描寫也在無形之中塑造著讀者的生命意識。災難面前,人的生命顯得無比脆弱。救難行為固然高尚,但也要準備周全,盲目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前去解救他人并非明智之舉。災難的描寫將讀者的思維從生活拉向生存,反復呈現生存的艱難處境,以告誡讀者生命的沉重可貴。
4.3 民族精神的閃現及災難文學的療愈作用
通過災難文學中的英雄形象發掘災難下民族精神的閃現以及災難文學的療愈作用對社會的影響是十分廣泛且深遠的。由于新聞媒體的發展,災難報道往往將整個民族置于災難情境之中。“地震災害被賦予了‘民族危亡’的歷史想象,地震文學創作成為一種‘民族救亡’的行動。”在此前提下,平民式英雄成為民族精神的最佳載體。首先,英雄的誕生需要強烈的矛盾沖突,以促使英雄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在災難中,每個人都面對著個人生死與民族危亡的抉擇,而能堅定選擇后者的人便成了英雄。其次,災難中的英雄時刻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這讓英雄行為的動機變得無可撼動,避免淪為說教式的利他主義式的扁平人物。
災難除了造成經濟損失,還造成了群體性的災后創傷。許多受難者在災后出現了人際交往、情感認知等方面的障礙,而文學也承擔著療愈受難者精神創傷的使命。災難文學作為一種群體性的創傷書寫,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汶川地震后,許多相關詩歌在網絡上發表,并在社交媒體上擁有極高的熱度。社群性的寫作增強了讀者的集體歸屬感,給予了讀者克服恐懼的力量。
5 結語
對受難者英雄形象的建構完善了對中國當代災難文學中英雄形象的整理分類,打破了對英雄形象的救難限定,展現了人類的精神力量,提升了災難文學的審美價值。基于此開展生命教育,有利于增強青少年的生命意識,進而產生更深遠的社會意義。
參考文獻:
[1] 張堂會.當代文學自然災害書寫的延續與新變[J].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4):31-37,42.
[2] 向寶云.災難文學的審美維度與美學意蘊[J].社會科學研究,2011(2):13-19.
[3] 丁臨一.穿越災難的成熟成長:評長篇小說《坼裂》[J].中國出版,2011(5):76.
作者簡介:李雅舟(2003—),女,江蘇無錫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
陸王妤佳(2003—),女,江蘇啟東人,本科在讀,研究方
向:現當代文學。
張丁睿(2002—),男,江蘇常熟人,本科在讀,研究方
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