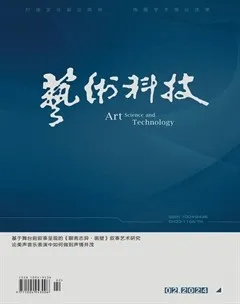基于舞臺劇敘事呈現的《聊齋志異·畫壁》敘事藝術研究
郭家慧 郭勇
摘要:目的:《聊齋志異》的491個短篇故事大多是把花妖狐魅由至幻之境引入凡俗人間,而《畫壁》卻與之相反,是將現實人物引入夢幻的壁間世界,向讀者呈現一場舞臺劇的表演。方法:文章從敘事角度出發,分三部分論述,認為蒲松齡讓《畫壁》中的凡俗之人進入幻境,和佛經中的散花天女一同上演了一場詭譎奇幻的舞臺劇表演。結果:文章第一部分從寺廟空間切入,分析蒲松齡采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帶領讀者觀看朱孝廉的進場;第二部分是文章的論述重點,蒲松齡將敘事焦點聚集在主角朱孝廉一個人身上,對敘事視角實現了如攝像鏡頭般的精準調度、操控和把握,為讀者呈現了一出精彩的壁上舞臺表演;在最后一部分,文章認為《聊齋志異·畫壁》在表現主角退場時,不單單是渲染人物的恐懼情緒,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種恐怖的情境,具體來說,這種恐怖情境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多重敘事視角與時空界限的打破,二是非對稱錯時性。結論:從寺廟到壁畫,《畫壁》橫跨了兩個空間,不同的人物活動由此對應三種人物狀態,展現出三種不同層次的境界。因此,主角朱孝廉從上場到退場,從入幻到出幻,其間的壁上表演也呈現出巨大的敘事空間,使得小說《聊齋志異·畫壁》產生了真幻難辨、虛實難分的敘事效果。
關鍵詞:? 《畫壁》;舞臺劇;觀看;進場;退場
中圖分類號:I207.4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2-00-03
0 引言
《聊齋志異·畫壁》只有短短915字,故事情節也很簡單,講述的是書生朱孝廉偶然進入畫壁世界,和拈花少女完成了一段人仙相通的魚水之歡。那么《畫壁》何以能在《聊齋志異》近500個故事中脫穎而出,在研究中不斷推陳出新,挖掘新內涵呢?原因之一在于作者蒲松齡采用了獨特的敘事手法,從獨特意象“壁”的設置到情節結構的巧妙構思,再到僧人展現的神秘佛教意味,研究角度也具有多樣性。現有研究多從夢境、鏡像、空間與越界等角度切入,闡釋“壁”的含義,指向《畫壁》在佛道思想下“幻”的主題。
從“誰在看壁畫”這一問題出發,《畫壁》的結構清晰明了。從寺廟進場時朱孝廉和他的同伴孟龍潭觀看壁畫,到朱孝廉進入壁畫后,他從觀眾變身為演員,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舞臺劇演出,被孟龍潭和僧人觀看,當朱孝廉退場之后又復看壁畫,整個故事首尾相合,結構完整,人物的空間位置也復歸如一。故事的魅力正在于此,在不變中發生了最大的變化,“共視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1]14。敘事視角的變化與非對稱錯時的運用將第三部分怖境的營造推向高潮,使得小說的整體敘事呈現出真幻莫辨、虛實難分的效果。
1 從寺廟進場
蒲松齡采用第三人稱的全知視角帶領讀者觀看朱孝廉的進場,他進入的是一個獨特的封閉空間——寺廟,其所具有的宗教意味將觀看空間和現實世界拉開一定距離,使得主角進入壁畫世界成為可能。在這一不甚宏闊的蘭若寺中,“惟一老僧掛褡其中”[1]13,這為后面朱孝廉神游入幻埋下伏筆,因為他稍后的登臺亮相亦是在“老僧說法”這種森嚴肅穆的殿宇之中。
《聊齋志異》中有多篇故事發生在寺廟空間,寺廟本是僧侶修行的威嚴清靜之處,但蒲松齡讓其間或有花妖鬼狐出沒,或有落魄書生暫住,二者的邂逅成為故事發生的起點,這一空間設置在一開始就暗示一切皆是佛門幻境。清代何守奇對《畫壁》作點評曰:“此篇多宗門語。至‘幻由人生’一語,提撕殆盡。志內諸幻境皆當作如是觀。”[1]14因此,寺廟空間的非現實指向為朱孝廉的進場提供了前提條件。
進場觀看壁畫只需要封閉的寺廟空間,然而并不是一般的游客皆能進入壁畫。蒲松齡此時悄悄變換視角,暗示讀者必須跟隨主角朱孝廉的視線,才能看到非常人所能及之景。他看到壁畫中的眾多散花天女中“內一垂髫者,拈花微笑,櫻唇欲動,眼波將流”[1]13。學者馮鎮巒將其解釋為“因思結想,因幻成真”[1]14,散花天女所蘊含的佛教意味以及蒲松齡鮮活生動的塑造手法使得主角神游其中。
具體來看,散花天女本是佛經中檢驗菩薩道心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行與佛教理性。然而蒲松齡向讀者展現的卻是一個具有世俗氣質的鮮活女子,作者選取的一連串動詞如“拈花”“微笑”,以及虛詞如“如生”“欲動”“將流”,無不是從朱孝廉一見傾心式的個人視角描繪了一位栩栩如生的拈花少女,她美得幾乎要從畫變為真人,走出壁畫。然而《畫壁》卻打破讀者的慣常預期,讓這位“神搖意奪,恍然凝思”之人步入畫中,而神意未被奪取的正常觀者孟龍潭卻沒有資格進入這一幻境。
2 壁上舞臺表演
中國的傳奇小說在選取敘事視角時,多繼承了歷史敘事中的全知全能視角,然而“志怪小說別出心裁,標新立異,其中的佳作較多地采用限制視角”[2]。和一般傳奇小說一樣,《畫壁》在第一部分選取全知視角敘述主角的進場并不新奇,然而蒲松齡在第二部分將敘事焦點聚集在朱孝廉一人身上,對敘事視角實現了如攝像鏡頭般的精準調度、操控和把握,為讀者呈現了一出精彩的壁上舞臺表演。
根據情節發展走向,朱孝廉舞臺劇表演的主體可分為兩部分。
2.1 視覺——其樂融融的世俗生活圖景
朱孝廉與散花天女相遇、相識的氣氛輕松愉悅,畫面美好而溫馨。這部分主要從視覺方面向觀眾展現神女是如何主動吸引朱孝廉而成歡愛之劇。“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髫兒囅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搖手中花遙遙作招狀,乃趨之。”[1]13蒲松齡讓觀眾隨著演員的視線移步換景,在“囅然”和“搖手中花遙遙作招狀”的誘惑中不知不覺進入和神女相好的親密狀態。
神女的女伴們發現二人的不當關系后,并未嚴厲指責二人的行為,反而對朱孝廉和散花天女的關系表示認可和支持,她們在一種輕松歡快的氣氛中為神女梳頭裝扮。蒲松齡用“生視女”“四顧無人”等視覺描寫的詞語逐步推進朱孝廉與散花天女的關系,使得觀眾在觀看時也處于一種安全、隱秘與舒適的狀態。
2.2 聽覺——險象迭起的榻下黑暗地帶
相較于視覺和觀看所具有的安全保障,隨之而來的演出則重點采用聽覺,烘托緊張和恐懼的氣氛。以“忽聞”二字宣告金甲使者的上場,使故事走向急轉直下。首先清晰地聽到金甲使者們所穿吉莫靴發出尖銳的“鏗鏗”聲,然后是他們雙手所提的緝拿犯人的刑具“縲鎖”發出的“鏘然”聲,最后眾聲喧嘩,紛囂騰辨,從清晰到混亂,用聲音渲染大禍即將臨頭的緊張感。當眾人聽到金甲使者大聲詢問這里是否有藏匿凡界之人,神女們紛紛回答沒有。本以為能化險為夷,觀眾可以稍稍松口氣,誰知金甲使者突然反身回頭,將緊張的氣氛烘托到極點。
朱孝廉在神女的指導下急忙藏匿于榻下,暫時得以脫險。此時舞臺燈光完全聚焦在朱孝廉一人身上,對其感知覺的關注被放大到極致。對于外界發生了什么,神女有沒有從金甲使者那里脫身,觀眾和主角一樣,一概不知,朱孝廉只能依靠外界聲響辨別自己是否安全。當喧鬧聲遠去,朱孝廉心緒稍微得以平靜,然而一旦有往來交談的聲音,就會令其耳中不斷蟬鳴,雙眼燥熱。朱孝廉只能依靠耳朵安靜聆聽,等待散花天女歸來,慢慢地竟然忘記自己是從哪里來的了。
正如學者指出,書生朱孝廉“現正被囚禁于壁畫內外兩個世界之間的黑暗地帶”[3],作為舞臺上的演員,朱孝廉身處這樣“非舞臺”的黑暗地帶,他既不屬于現實世界,又不屬于壁間舞臺世界,此時他似乎成為這場舞臺劇的被拋棄者,這為其稍后的退場埋下伏筆。
朱孝廉在壁間世界的舞臺表演張弛有度,從發生、發展、高潮到結尾,呈現出一條清晰完整的邏輯鏈條。蒲松齡通過對主角特定鏡頭的調度與轉換,一步步將壁畫中的奇幻世界引入現實空間,借奇幻以寫實,寓奇幻于日常,同時也與主角接下來驀然退場而產生的恐怖效果形成強烈的反差。
3 退場之怖境
蒲松齡筆鋒一轉,將視角切換至主角的同伴孟龍潭,“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1]14,演出結束之突然,主角退場之匆忙,暗示此時存在種種不和諧的恐怖因素。作為人的四種基本情緒之一,恐懼是“面對事物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料性,是驚恐反應的誘因”[4]。而《畫壁》在表現主角退場時,不單單是渲染人物的恐懼情緒,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種恐怖的情境。具體來說,這種恐怖情境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3.1 多重敘事視角與時空界限的打破
第一,從孟龍潭的視角來看整個奇幻的壁畫表演,他的同伴所經歷的長達三日的詭譎奇幻的壁畫之旅,在現實中不過轉瞬而已。同伴朱孝廉的退場和進場一樣,毫無防備,當老僧以指彈壁,聲音穿透壁畫,詢喚朱孝廉為何遲遲不歸,此時孟龍潭作為觀畫者才猛然間目擊到朱孝廉在畫壁上的客觀存在。他作為觀眾,驀然發覺觀看的表演主角竟是自己身邊人,時空的模糊錯位產生了恐怖的效果。
第二,從主角朱孝廉的視角來看,他進場時自以為身處看似隱秘的空間“舍內寂無人”,實則成為公開的表演舞臺,方才發生的一切秘境、一切褻境全然公開,更是使其心房潰散。最后,當三人共視拈花人,發現其“螺髻翹然,不復垂髫矣”,繪畫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永恒性,然而此刻拈花少女發髻的改變則證明時間與空間、現實與非現實的界限徹底被打破的事實。
第三,作為全知視角,小說結尾“異史氏”的出場拉開了敘事與故事的距離。讀者剛從觀畫者孟龍潭的視角意識到同伴的離奇退場和拈花少女“不復垂髫”的荒誕事實,此時又驟然驚覺這一切只是個被“異史氏”——一個干預敘事者講述的虛構故事。讀者從層層嵌套的敘事結構中脫離出來,由此產生虛實難分的錯愕感與驚惶感。
3.2 非對稱錯時性
《畫壁》所具有的非對稱錯時性也為朱孝廉的退場帶來反常的恐怖體驗。“非對稱錯時”的概念是由學者尚繼武提出的,它是指“所述事件或事件諸環節的次序不變,但是時間的尺度、節奏、頻率發生變化,使事件的延續過程在時間幅度上存在錯位”[5]。
一般小說是通過加快人間的時間節奏、放慢虛幻空間的時間節奏以達到非對稱錯時的效果,如“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就是讀者熟悉的模式。而蒲松齡在《畫壁》中卻另辟蹊徑,將壁間歡樂時間放慢、拉長,對朱孝廉在幻境中的敘述詳細而具體,延續三日,而在現實空間卻只是“少時”之間,蒲松齡將現實之境與幻化之境相交錯,給讀者帶來一種既真實又神秘的新鮮感。
這樣一場看似正常的萍水之愛,也并沒有如花妖鬼狐等驚悚駭人的意象般單純、直接地展示恐怖,為何能產生如此光怪陸離的神奇效果?
首先,從陌生化角度來看,這是蒲松齡有意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其根基依舊是現實世界里的生活經驗,小說結尾正是借異史氏之口,點出了《畫壁》幻由人生、色即是空的主旨,“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1]14。朱孝廉的淫心和色欲成為一切恐怖的根源。
其次,從美學角度來說,這種驚恐的審美體驗也可借由康德力學上的崇高來解釋,如其所言,“只要我們處身于安全之中,則它們的景象越是可畏懼,就將越是吸引人”[6]。無論是寺廟還是畫壁,這兩種空間本身都不具有正常的安全屬性,由此使得上演一出日常的、真幻難辨的舞臺表演成為可能。
4 結語
從寺廟到壁畫,《聊齋志異·畫壁》橫跨了兩個空間,不同的人物活動也由此對應三種人物狀態,展現出三種不同層次的境界。第一是孟龍潭和壁畫中的神女以及使者等人。孟龍潭只存在于現實世界,他以肉體凡胎見證了這場奇幻表演。而壁畫世界中的散花天女、散花女伴和金甲使者作為純粹的表演者,則只存在于藝術世界,和現實世界不產生連接。第二是主角朱孝廉,他被作者蒲松齡偶然賦予神力,有條件出入現實世界與藝術世界,打破了時空界限,成為連接二者的橋梁,在退場后壁畫少女發型的改變證明了朱孝廉是超出第一境界的不尋常人物。第三則是超脫于現實世界與藝術世界的老僧,只有他自始至終知曉主角行蹤,并能將其拉回現實,在結尾意味深長地點明“幻由人生”的主題,表明老僧早已參透一切。
在這三種境界中,摻雜了種種真實與虛幻的因素。一方面,朱孝廉的進場和退場雖然都是在現實中發生的,但卻毫無緣由,更無準備,且由于寺廟空間所具有的模糊時間的功能,所以敘事效果最不真實。另一方面,舞臺上的表演顯得極其真實,朱孝廉在壁間世界與散花仙女的相遇相識是真實的,天女雖是佛經中的非現實人物,但其行為舉止、性情特征都和世間女子別無二致。由此,《聊齋志異·畫壁》以舞臺劇的形式呈現了朱孝廉進場—舞臺(下轉第頁)(上接第頁)劇表演—退場的全過程,具有真幻難辨、虛實難分的敘事效果。
參考文獻:
[1] 蒲松齡,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3-14.
[2] 楊義.中國敘事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4.
[3] 任增強.《畫壁》與蒲松齡對界限的操控:美國漢學家蔡九迪《聊齋志異》研究·結語篇[J].蒲松齡研究,2018(4):70-83.
[4] 孟昭蘭.情緒心理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62.
[5] 尚繼武.《聊齋志異》敘事藝術研究[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76.
[6]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M].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271.
作者簡介:郭家慧(2000—),女,河南駐馬店人,碩士在讀,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中國語言文學文藝學。
郭勇(1978—),男,湖北麻城人,博士,教授,研究方
向:中國文論與美學、西方文論與美學、中西比較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