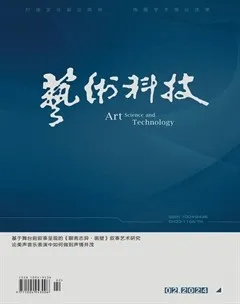人工智能作品的權利歸屬探析
夏心雨 沈世娟
摘要:目的:面對蓬勃發展的人工智能市場,以及伴隨而來的司法問題,文章旨在探究人工智能作品的權利歸屬與責任承擔,明確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以及什么樣的法律人格契合人工智能發展現狀,從而在人工智能發展的同時做好利益平衡,探索符合我國人工智能發展水平的相關法律制度。方法:通過分析人工智能概念,解析法律人格概念,查閱學術文本與資料,以強、弱兩種人工智能分類展開討論,并從倫理、社會影響、立法方向等角度構想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的情況。通過案例分析,探究之前的法律設計是否合理。結果:從倫理角度看,弱人工智能可作法律客體,強人工智能可作法律主體;從社會影響看,人工智能基礎上的算法法人需要從長計議,避免驟然顛覆過去的傳統組織形式;從立法角度看,否定直接套用舊有法人模式,以及具有缺陷的職務作品說。結論:人工智能可以獲得有限的法律人格,從而適配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可以自我深度學習的人工智能,并需要對不同水平的人工智能進行分別規定。人工智能開發者與使用者以協議的合意優先,在無協議的情況下,由創作主體獲得著作權,但人工智能使用者也可以獲得相應權益,這樣一方面能促使人工智能得到廣泛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使人工智能技術切實為公眾帶來好處。
關鍵詞: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權利歸屬
中圖分類號:D923.41;TP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02-0-03
1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法律人格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使人工智能愈加貼近人們的生活。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出的繪畫作品、文章,乃至專業的數據分析報告,應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繪畫方面有Stable Diffusion等,寫作有Notion等,辦公類的Tome則可以生成ppt來輔助工作。本文以人工智能作品稱呼人工智能生成的產物,并不是指產物的實際作者是人工智能,而是表示這些產物都基于人工智能而產生。
首先討論人工智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中是否享有著作權。《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創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主持,代表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意志創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承擔責任的作品,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視為作者。著作權是為了鼓勵人類創作而生,保護自然人的權利,這是毋庸置疑的。但為了商業經濟的發展,也產生了與自然人人格相對的法人人格。
目前,人工智能可分為弱人工智能與強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被認為缺乏自主意識,按照人類制定的規則行動。強人工智能則被認為本身具有自我意識,擁有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對于弱人工智能而言,從倫理角度看,馬開軒等學者將其看作物,起到工具的作用,并不需要具有法律人格[1]。葉娟麗等學者從社會層面出發,認為弱人工智能像算法法人,這種區塊鏈去中心化自治組織,會加劇社會的不平等[2]。從立法角度來說,徐慧麗等學者認為在政府支持人工智能的情況下,人工智能會得到迅速發展,產生更復雜的權責分配問題,迫切需要擬制法律人格去解決問題[3]。張力教授認為,法人本身就是帶有明確政策目的的篩選與重塑的組織體,出于促進算法發展、便于國家法律監管等原因,將其法律人格設定成法人人格是合適的[4]。學者王澤方則稱,應以自然人作者為原則,法人或非法人組織作者為例外,人工智能作品可被視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的職務作品[5]。張志堅教授認為,人工智能的本質是財產,具有財產性人格,但無人身性人格,應歸入法人范疇,成為電子法人[6]。學者唐云驄認為,不需要改動現有法律體系,可以用《著作權法》中的鄰接權予以保護[7]。針對強人工智能,有學者表示擔憂,一旦有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的例子,就會有更多“非人”要求法律人格,引起法律秩序崩壞。
2 人工智能應被賦予限制性法律人格
目前的人工智能存在算法黑箱,即人們可以根據輸入內容得出輸出結果,至于它是如何學習分析并得出這一結果的,人們并不知道。人類不能預測結果的工具是失控的工具,故將人工智能僅僅看作工具并不妥當,工具論僅適用于弱人工智能。
對于算法法人的提法,將顛覆之前的傳統法人體系,從社會和法律層面都是一種巨大的沖擊,盡管其似乎剔除了舊組織的獨斷徇私等弊端,但是學者們的擔心不無道理。算法法人的設立,需要衡量利弊與時機才能決定。法具有規范作用,面對飛速發展的人工智能,不宜操之過急,但也需要及時調整以適應社會現狀,具體可以從綱領到細則的逐步建立,及時補充。法人作品對人工智能作品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能以法人作品去套用。法人背后雖是自然人,但可完全獨立存在,且目前的人工智能雖超出弱人工智能水平,但仍達不到完全具有自我意識的強人工智能水平。對于職務作品說,當人工智能開發者并未提前約定作品的權利,而使用者又不是因為職務使用人工智能時,相關法律就無法適用,由此便產生了法律空白,故不支持。
對于鄰接權的提議,則不能忽視立法的整體性與系統性,而且要考量《著作權法》外的情況。
法律人格被認為是私法上權利和義務的歸屬主體。針對人工智能的法律人格,筆者支持有限人格說,并對智能程度不同的人工智能采取不同的對策。目前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不一,如果智能程度低下、運行結果完全由人類掌控的弱人工智能也被賦予法律人格,會使得其背后的自然人借此逃脫法律制裁。而像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自己深度學習,不全為人類掌控的人工智能則可以賦予有限的法律人格。另外,人工智能并沒有人類的喜悅、悲傷等情感,所以它的法律人格僅僅為財產性質。
在實際的法律運用中,若軟件開發者已經事先與軟件使用者協議確認了作品的權利歸屬和責任承擔,則依協議。若無協議,則按作品的創作主體來劃分權利,即人工智能創作占比高的,就由人工智能享有著作權歸屬,使用者也可獲取一定的利益;如果人類創作成分占比高,那么著作權歸屬于人類。之所以如此設計,是因為要考慮利益平衡原則與市場規律等因素,主要會面臨以下三種情況。第一,開發者如果在使用者使用前已收費,同時協議著作權歸開發者所有,使用者仍然選擇該人工智能,那么說明該產品比市場上其他產品的回報率高。第二,開發者在使用者使用時不收費,則可通過獲得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來獲取利益。第三,開發者已經收取使用者的費用,且協議著作權歸使用者所有,那么會促進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推廣與發展。在無協議的情況下,若人工智能作品由使用者提示方向,設定詞匯等簡單指令產生,作品的著作權歸屬于使用者并不妥當,而開發者雖設定了人工智能的核心程序,但其未參與此次創作,將著作權全部歸屬于程序開發者也不合理。因此,人工智能創作占比高的享有部分著作權權利,而創作主體為人類的,則享有相關的著作權才比較公平。總之,這對未來的文學和藝術發展都會是一項巨大的考驗,但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在舊的圖景上產出的,而美術和文學都是時代發展的折射與未來的展望,自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對文藝來說,既是挑戰,又是促進其躍進的推動力。
3 人工智能權利歸屬案例分析
以下三個案件,都存在值得分析討論的問題。如果最終法典采取有限人格說,那么在目前出現的國內三個案件中會得出相對明確的結論。
3.1 “人工智能陪伴”軟件侵害人格權案
被告運營的軟件中有一項人工智能陪伴功能,可以由用戶上傳圖文等信息塑造該人工智能的形象、性格等。原告何某并沒有授予該軟件權利,法院認定被告未經同意使用原告姓名、肖像,設定涉及原告人格自由和人格尊嚴的系統功能,構成對原告姓名權、肖像權、一般人格權的侵害[8]。
盡管數據是由用戶上傳的,但是開發該核心算法的公司實際上在設置算法中沒有規避對他人肖像權等的利用,而是鼓勵用戶用數據去塑造這樣的人工智能陪伴者,并不屬于人工智能的程序中立。筆者所設定的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為財產性人格,不具有人身性人格,因此,人工智能目前不享有對應的人格尊嚴等權利,也不能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故該案中,應由被告公司承擔侵權責任。
3.2 騰訊訴盈訊侵害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一案①
騰訊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開發了一款智能寫作輔助系統,并許可原告使用。許可范圍包括被許可方使用其創作作品的著作權歸被許可方,以及可以對侵犯授權軟件著作權的侵權行為采取相應法律措施。原告在網站上發表了《午評:滬指小幅上漲0.11%報2671.93點通信運營、石油開采等板塊領漲》(以下簡稱“涉案文章”)。原告對此表示,涉案文章系由原告主持,代表原告意志創作,原告應視為作者,涉案文章作品的著作權歸原告。而被告網貸之家發布的文章與騰訊在官網發布的完全一致。
法院首先判斷涉案文章是否符合獨創性要求,以此確定是否能享有著作權。隨后根據原告公司提供的創作過程數據,包括數據類型的輸入語料的設定等認為文章受主創團隊的控制,所以是由該團隊創作。最終認定該文章是法人作品,著作權歸原告所有,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在此案中,法院否定了人工智能的主體資格,認為該篇文章受主創團隊控制,盡管文章由人工智能生成,但是前期的準備工作,以及人工智能生成方向和結果檢驗由企業所控制。法院認為在這個作品的完成過程中,人起到了主要作用,所以著作權歸主創團隊所有。軟件開發方已經許可使用方的權利,并且文章由主創團隊控制,盡管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并不會完全受主創團隊控制,但是依案例來看,文章的主要創作者仍然是人類,所以該作品應當由原告公司享有著作權,人工智能參與文章的創作不影響原告公司對被告公司侵權的控訴。
3.3 菲林律師事務所訴百度案②
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是一款智能的數據庫,菲林律師事務所在數據庫報告基礎上,完成了《影視娛樂行業司法大數據分析報告——電影卷·北京篇》(以下簡稱涉案作品)。百家號在抹去事務所的署名、引言、檢索概況等內容的情況下,發表了與涉案作品基本一致的文章,并署名“點金圣手”。
事務所主張百家號侵犯其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及保護作品完整權。本案的焦點在于,第一,由事務所提供搜索詞而產生的分析報告是否具有獨創性;第二,如果分析報告認定有獨創性,那么該報告是否認定為《著作權法》上的作品;第三,如果能成為作品,那么誰能成為該報告的作者,享有其著作權。
一審法院認為,第一,基于分析數據而產生的柱狀圖等不符合《著作權法》中的圖形作品要求。第二,盡管使用數據庫設置搜索方向,并由其自動生成了分析報告,但自然人創作才是《著作權法》中作品的必要條件,所以分析報告不能成為作品。并且,一審法院認為,開發者與使用者都不能成為分析報告的作者,但同時支持使用者在傳播過程中表明自己的權益。
對于在分析報告基礎上創作的涉案作品,一審法院認定其為事務所主持創作的法人作品。二審法院只糾正了保護作品完整權的部分。
菲林律師事務所付費使用數據庫,并且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沒有事先協議分析報告的著作權歸屬。與第二案不同,雖設置了搜索詞去引導分析報告的生成方向,但其在分析報告中起到的作用很小,分析報告的著作權歸屬應當為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事務所雖然沒有取得分析報告的著作權,但是也在分析報告的基礎上,創作出了涉案作品,并取得了該作品的著作權。其在分析報告的基礎上,對當前的影視行業進行了大數據結果的分析,并將此結果呈現在公眾面前。
4 結語
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大推進了人工智能步入日常生活的進程,其商業價值不可估量,應盡早確定人工智能的限制性法律人格,明確人工智能作品權利歸屬,為其進入市場做好準備。同時,人工智能開發者與使用者也應在法律約束下,創作出更多人工智能作品,豐富人們的日常生活。
參考文獻:
[1] 馬開軒.人工智能法律主體地位的法哲學反思[J].學習論壇,2021(6):122-130.
[2] 葉娟麗,徐琴.去中心化與集中化:人工智能時代的權力悖論[J].上海大學學報,2019,36(6):1-12.
[3] 徐慧麗.人工智能法律人格探析[J].西北大學學報,2020,50(1):107-119.
[4] 張力.區塊鏈與人工智能組織體法人化理路探正[J].東方法學,2022(5):45-59.
[5] 王澤方.論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歸屬[D].海口:海南大學,2021.
[6] 張志堅.論人工智能的電子法人地位[J].現代法學,2019,41(5):75-88.
[7] 唐云驄.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保護的司法裁判基準研究[D].揚州:揚州大學,2021.
[8] 北京互聯網法院.“人工智能軟件侵害人格權案”入選民法典頒布后人格權司法保護典型民事案例[EB/OL].今
日法院-要聞動態,(2022-04-14)[2023-10-01]. https://
www.bjinternetcourt.gov.cn/cac/zw/1651208235008.html.
作者簡介:夏心雨(1998—),女,江蘇常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經濟法學。
沈世娟(1970—),女,江蘇南通人,碩士,教授,系本文通訊作者,研究方向:經濟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