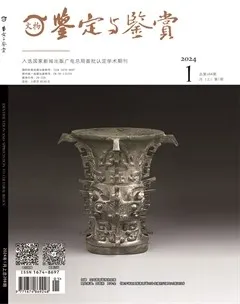影響中國書法的云南著名碑刻
羅旭崐



摘 要:云南書法歷史可以追溯到楚漢時期。在這個時期,云南地區已經有了一些石刻和墓葬中的書法藝術作品。尤其是東漢的《孟孝琚碑》,東晉、南北朝時期的《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不僅展示了古人書寫的藝術才華和雕刻技藝,更為后人提供了研究古代歷史、考古學和文字書體演變的重要依據。此外,這些碑刻也是國家珍貴的文物資源,承載著民族文化的記憶和傳承,具有極高的收藏、展覽和研究價值,是研究中國書法史和文字學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保護和傳承古代碑刻文化,既是對中華文明的尊重與傳承,也是推動文化繁榮與發展、增強民族自信的重要舉措。
關鍵詞:《孟孝琚碑》;《爨寶子碑》;《爨龍顏碑》;傳承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4.01.005
1 東漢《孟孝琚碑》
我國的書法藝術發展史是漢字的演化史,也是書體的演變史,歷經了篆、隸、楷、行、草的書體演變。書法藝術是一門獨特的藝術,是我國四大國粹之一,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縮影。我國書法藝術能夠流傳至今,傳承的本質上與碑刻有密切的關系。云南著名的碑刻有很多,年代最早并最有影響的當數東漢的《孟孝琚碑》(圖1)。該碑是刊刻于漢代的一方碑刻,碑文書體屬于隸書書法,歷史上又稱為《孟廣宗碑》《孟琁殘碑》。1901年9月出土于云南昭通城南的白泥井。時任直隸清河道的昭通人謝崇基返回故里時,對此碑的書體大為驚嘆,他撰寫跋文道:“其文辭古茂,字畫遒勁,方知滇中古刻,遠在兩爨諸碑之上,雖碑首斷,間有泐痕,年代無考,然以文字揆之,應在漢魏之間,非兩晉六朝之物。”該跋文另刊刻一石附嵌在原碑末行空隙處,現依然保存完好。該碑現位于云南昭通文淵小區內(現有碑亭保護)。碑高133厘米,寬96厘米,厚約30厘米,碑側有龍、虎紋,下有龜蛇紋。碑文共15行字,其中第5行3個字,第13行無字,第14行16個字,第15行10個字,其余每行21個字,合計殘存260個字,內容記述了漢代武陽令之子孟孝琚的生平事跡。內容文辭典雅,碑文書法系方筆隸書,取勢橫扁,左右舒展,筆畫瘦勁古樸。
陳榮昌(1860—1935),清代進士,字筱圃,先生在孟碑拓本上題簽曰:“云南第一古石。”《孟孝琚碑》的書法藝術風格,筱圃先生也推崇備至,他說:“《孟孝琚碑》用圓筆結體豐滿,確是西漢分書,與《郁閣頌》相近。”又說:“《廣藝舟雙楫》推爨龍顏碑為楷書第一碑,列諸神品之首,今吾亦推孟孝琚為分書第一碑。其書體筆力雄厚,體勢古雅,其磅礴氣象實足以壓倒一切也。”
《孟孝琚碑》與著名漢碑《禮器碑》立石屬同年,字體方正渾樸,就碑刻書法而言,能與《張遷碑》《衡方碑》《潘校官碑》《孔宙碑陰》媲美。兩漢佳碑較多,論其結體有方有扁,用筆有圓有方有肥有瘦。而《孟孝琚碑》是方體圓筆,力度在肥瘦之間,實為漢碑中不可多得的佳品。
此碑是目前云南唯一的一塊漢碑,其書法之中篆書、隸書、行書甚至楷書也夾雜其中。碑上的文字大、小、長、短、肥、瘦變化多端,但總體上的行氣、章法、布白十分整齊,甚是和諧。
2 正書古石第一的《爨寶子碑》
從出土的碑刻來看,云南書法藝術在兩漢、三國、兩晉以及南北朝時期發展的總體趨勢與中原內地是一致的。
東晉時期,一個叫爨琛的人在云南建立了爨氏政權,獨自稱霸南中。由于中原戰亂不斷,很多難民南遷云南,這些難民帶來的中原文化與當地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特色的爨文化,今天成了云南獨有的文化財富。如今我們見到的《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就是夷漢文化融合的見證。
《爨寶子碑》(圖2),全名為《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爨府君之墓》,東晉義熙元年(405)立石,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于云南省曲靖府城南35千米里揚旗田出土,咸豐二年(1852)移置于曲靖城內,今保存于曲靖第一中學爨碑亭內。碑高1.62米,寬0.63米,厚0.21米。碑文共13行字,每行30個字,碑額15個字,碑尾有題名共13行,每行4個字,全碑總計402個字。書體為隸楷之間,屬正書(楷書)范疇。《爨寶子碑》比《爨龍顏碑》早52年立石,至今已有1600余年的歷史。因碑體比《爨龍顏碑》小,故又稱《小爨碑》。
阮元(1764—1849),云貴總督,曾定《爨龍顏碑》為“云南第一古石”,而此時《孟孝琚碑》尚未出土,《爨寶子碑》雖已出土,但不為阮元所見,遂成憾事。
清代自乾嘉以后,一派書家為了矯正“館閣體”軟媚之流弊,曾力主推崇北朝碑版。阮元首倡“北碑南帖”論,為晚清尊碑風尚進行了強有力的推動。繼而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大力倡導碑學。當時出土于云南的《孟孝琚碑》《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等正好為研究碑刻提供了充分而有力的依據與資源,一時間談碑學碑之風日趨活躍,學碑者如桂未谷、鄧石如、趙之謙、伊秉綬、張廉卿等書家大顯于世。至清末,康南海又把尊碑之風推向了高潮。他激動地說:“道光之后,碑學中興,迄于咸同,碑學大播。”他見到《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的拓片后,更是異常興奮。在《廣藝舟雙楫》中,他對《爨寶子碑》推崇備至,他說:“寶子端樸若古佛之容,厚重古拙,體勢飛揚,用筆如長槍大戟,直來直往,沉著而痛快。”“當為正書古石第一本。”此后,《爨寶子碑》拓本廣為流傳,引起海內外一些金石學家、史學家、書法家極大的研究興趣,大范圍臨習。
《爨寶子碑》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由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典型實物,反映了漢字在演變過程中的一種字體風格。在晉碑中,無論南碑還是北碑并無與之相類的書體,可知此碑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寶貴程度。與《爨龍顏碑》相比,《爨寶子碑》更接近于隸書,且還有一些篆書風格。而《爨龍顏碑》由于晚立50多年,故楷書成分大大增加,由兩碑字體的差異可以明顯看出漢字書法藝術演進嬗變的痕跡。
《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出土后,梁啟超驚嘆曰:“天津橋上聞杜鵑,豈地氣寶鐘于南徼耶!”康有為說:“南碑今所見者,二爨出土于滇蠻,然其高美,已冠古今。”郭沫若認為東晉時期的書法應處于隸楷階段,依據是東晉所立《爨寶子碑》和1965年出土的東晉《王興之夫婦墓志》均屬隸楷書體。就東晉書法而言,有隸書,有帶隸意的楷隸,有行楷書,各種書體并存,相得益彰。以“二爨”代表晉代書體之一,這是云南書法史上的驕傲。
書法和文字的發展一樣,根據人們書寫的實用性要求兼具審美需求應運而生,是漸變而不是突變。從晉代眾多的碑刻來看,漢字的書體已逐漸楷書化,偶爾帶有一點隸書筆意的筆畫痕跡,前人稱之為“楷隸”,即《爨寶子碑》一類的漢字寫法。可以認為《小爨碑》是用篆隸筆法寫楷書,外方內圓,其最大的特點是用方筆起勢、收勢,用筆特殊,字體參差,拙中帶巧,同字異寫,寫點均呈三角形,有豎、有橫、有斜,變化無窮,姿態生動。李根源說它“下筆剛健如鐵,姿媚如神女”,康有為稱它“樸厚古茂,奇姿百出”,可見《爨寶子碑》的藝術價值之高。該碑上承兩漢隸分之遞變,下開隋唐正書之先河,實為楷法之鼻祖。
《爨寶子碑》碑文內容屬駢散結合而以駢為主,內容上文辭典雅,古意盎然,頗具六朝余韻。其書法藝術風格獨特,不愧為“南碑瑰寶”。
3 “神品第一”的《爨龍顏碑》
《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既有中原文化傳統,又有邊疆民族特色,文章典雅,書法得于漢晉正傳,令書法界人們景仰。
《爨龍顏碑》(圖3),即《宋故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邛都縣侯爨使君之碑》,又稱《大爨碑》。立于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九月,距今1560余年。現存于云南省陸良縣貞元堡(亦稱薛官堡)村,1986年3月,建亭移置加以保護。碑全高3.38米,寬1.46米,厚0.25米。上方呈半圓形,浮雕青龍、白虎和朱雀,半圓形高度為0.88米。半圓形與正文相接處有一孔洞,孔洞直徑為0.17米,在孔洞的左、右側分別刻有日紋(日中刻踆鳥)、月紋(月中刻蟾蜍),直徑各為0.16米。碑陽面之碑額共有24個字,碑正文共24行,每行45個字,全文共904個字,其中20余字分辨不清。碑陰面刻有官職題名共3段,上段15行,中段17行,下段16行,每行3至10字,共313個字,其中9個字分辨不清。其左邊還刻有清阮元、楊珮、邱均恩三人題跋以及知州張浩修建碑亭記述等內容的一行文字,外加監造以及作者署名的17個字,全碑共計1234個字。道光六年(1826),時任云貴總督的金石學家阮元在貞元堡(亦稱薛官堡)村外的一片荒丘上找到此碑,并在碑后作跋,盛贊《大爨碑》的書法藝術特點。他寫道:“此碑文體書法,皆漢晉正傳,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寶護之。”道光七年(1827),其令知州修建亭子對其加以保護。經阮元對碑學的極力提倡,諸多學者競相考釋研究,《爨龍顏碑》也從此在業界家喻戶曉。
《大爨碑》的書法藝術和價值,正由于阮元的極力推崇,在晚清書法界引起巨大的轟動。清阮福(阮元之子)在《滇南古金石錄》中亦大為贊揚:“可嘆劉宋、蕭齊八十年間,宇內竟無片石,偉哉此碑!遠立邊裔,至今巋然,為劉宋以來錄碑諸家所未見。”《大爨碑》和《小爨碑》的書法書寫特征在隸、楷之間,《大爨碑》的立碑時間比《小爨碑》晚了50余年,由隸變楷的演化又進了一步,《大爨碑》比《小爨碑》更接近楷書,這也完全符合漢字演變的規律。《爨龍顏碑》書法雄強茂美,筆力遒勁,布局等氣勢宏偉,方筆中兼帶圓筆、隸書筆意,隸楷極則。其圓筆比《鄭文公碑》(比《大爨碑》晚53年立石)鏗鏘挺拔,方圓得當,其方筆又比《張猛龍碑》(比《大爨碑》晚64年立石)凝重大方,樸拙天趣,結體古拙嚴謹。碑文書體中的點畫書寫蒼勁雄強,變化豐富,橫豎堅實,鉤提豐滿,撇捺明快潔凈,爽灑自然,橫彎轉角,方圓相濟,渾然天成,隸楷嬗變中既有創新又有突破。阮福評價道:“字體方正,在楷隸之間,畢肖北魏各碑,實為六朝碑版之冠。”
康南海在《廣藝舟雙楫》中把《爨寶子碑》列為“神品第一”,又說:“龍顏碑下畫如昆刀刻玉,但見渾美;布勢如精工畫人,各有意度,當為隸楷極則。”并作詩贊曰:“漢經以后音塵絕,惟有龍顏第一碑。”清范壽銘跋稱:“龍顏碑立于大明二年,與后魏太安二年《嵩高靈廟碑》同時而立,南北兩碑遙相聳峙。淳樸之氣則靈廟為勝,雋逸之姿則爨碑為長。蓋由分入隸之始,開六朝唐宋無數法門。魏晉以還,此兩碑實書法家之鼻祖矣。”此碑備受康有為推崇,其評價此碑道:“與靈廟碑同體,渾金璞玉,皆師元常(鐘繇)實承中朗之正統。”由此可知,《爨龍顏碑》的書法藝術無疑是研究中國漢字書體演變歷史和文字學珍貴的一手資料。
《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出自云南,從碑文的文學性和書法藝術性來研討,更充分地說明了滇文化的這一特點。中原文化與云南地區的長期融合與共同發展,產生了“二爨”這樣的書法豐碑,實為云南的驕傲。
4 結語
碑刻大都是民族藝術的結晶,有較高的文學藝術研究的價值,更重要的是碑刻記載了歷史上民族圣賢的功德,這些寶貴的記憶是鑄就民族之魂的重要源泉,它能帶給人們無窮的啟示和力量。
從書法藝術史角度來看,縱觀云南眾多的碑刻,最早并具有一定規模的還得首推東漢的《孟孝琚碑》,雖然它出土比《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晚,但它畢竟是云南僅存的一塊漢碑,是名副其實的“云南第一古石”。其次則是東晉、南北朝的《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的碑文書法極佳,是證明我國文字書體演變過程中由隸書過渡到楷書的典型實物,尤以《小爨碑》最為突出。考證和研究這些著名碑刻,無疑會對今天書法藝術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我們認識和學習這些碑刻,保護這些難得的碑刻資源,去見證歷史滄桑巨變,彰顯悠久的文明史與文化底蘊,弘揚碑刻書法藝術,有利于找尋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既是對民族文化遺產的尊重,又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參考文獻
[1]張誠.書法新論[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2.
[2]秦文錦.晉爨寶子碑集聯[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3]秦文錦.宋爨龍顏碑集聯[M].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4]朱天曙.中國書法史[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
[5]周康林.爨龍顏碑[M].北京:中國書畫家,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