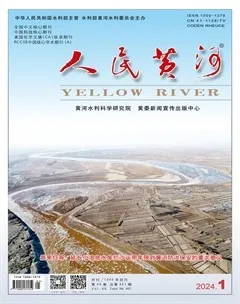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互動關系研究
劉建華 普凌宇



關鍵詞: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互動機制;黃河流域
中圖分類號:F124.5;TV882.1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 j.issn.1000-1379.2024.01.002
引用格式:劉建華,普凌宇.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互動關系研究[J].人民黃河,2024,46(1):5-11,18.
數字經濟已經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2022 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就發展數字經濟作了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一文中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黃河流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空間格局中的地位重要,但近年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凸顯,各省(區)產業倚能倚重、低質低效問題突出。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多次提及數字經濟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賦能作用。因此,厘清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現狀,探究二者的耦合協調與互動關系,有助于推進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
近年來,有關數字經濟發展的研究多以國家、省域或城市群等為研究對象[1-7] ,多數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有促進作用[8-10] ,也有學者認為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正向影響受區域資源稟賦等約束[11] 。自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上升為重大國家戰略,學術界圍繞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水平測度、驅動因素、實現路徑等進行了廣泛的理論分析及實證研究[12-18] ,關于數字經濟與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相互關系也有所研究[19-20] ,但實證研究鮮少,且已有研究多從黃河流域各省(區)、城市群等宏觀層面展開,少有從地級市(州)層面的探索。因此,本文以黃河流域64 個地級市(州)為研究對象,利用耦合協調度模型、PVAR 模型等探究2011—2020 年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及互動關系,以期為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實施提供參考。
1 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互動機制
數字經濟與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互動機制見圖1。
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后的新經濟形態,對高質量發展的賦能作用體現在以下4 個方面:1)數字產業化必將帶來技術創新,有助于降低通信成本,增強創新網絡的互聯互通,提升社會經濟活動效率,加速形成由數據驅動的新型數字產業體系,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夯實數字基礎;2)依托產業數字化、利用數字技術,再造黃河流域傳統產業全鏈條,促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產品及其服務深度融合,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21] ,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增添活力;3)依靠數字化治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推動黃河流域數字城市、智慧城市建設,可為市場主體營造良好營商環境,進而支撐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4)通過數據價值化加快培育數據要素市場,改變生產要素的獲取方式及投入結構,提升數據要素配置作用,有助于催生新技術、新業態,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力。
數字經濟發展需要依托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體現在經濟有序發展、人水和諧共生、生態環境健康、人民生活幸福、文旅融合發展5 個方面:1)經濟有序發展需要創新驅動,通過加強教育和科研投入為數字經濟提供科技支撐[22] ,進一步促進技術擴散和知識外溢,有效推動技術創新和人才積累,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2)人水和諧共生需要全面推進算據、算法、算力建設,構建具有預測、預警、預演、預案功能的智慧水利體系,進而有效預防水旱災害,合理管理和調配黃河流域水資源;3)綠色低碳是生態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利用數字技術革新工藝流程,可以提升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調整能源結構朝綠色化發展,從而減少碳排放量,助力生態環境保護;4)人民對美好生活的不斷追求要求進一步加強數字政府建設,通過“讓百姓少跑腿、讓數據多跑路”提升社會治理的智慧化水平,改善人民生活品質;5)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發源地,要加強黃河流域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與傳承,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黃河文化旅游帶,離不開數字經濟的賦能。
2 研究設計
2.1 指標體系設置及數據來源
基于科學性、系統性、適用性、可操作性等原則和黃河流域發展的現實基礎,參考傅為忠等[23] 、劉建華等[24] 的研究,構建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系統與高質量發展系統耦合協調量化評估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對于數字經濟系統,參考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2 個維度設置5 類共9 個指標;對于高質量發展系統,從經濟有序發展、人水和諧共生、生態環境健康、人民生活幸福、文旅融合發展5 個維度設置12本研究所用數據除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源自《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 年)》外,其他指標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地級市(州)統計年鑒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缺失數據通過線性插值法予以補充。
2.2研究范圍及區域劃分
基于“以自然黃河流域為基礎支撐、盡可能保持地級行政區劃單元的完整性、考慮地區經濟發展與黃河的直接關聯性”原則[25] ,按照黃河水利委員會劃定的黃河流域范圍,不考慮內蒙古蒙東地區及四川省,把研究范圍確定為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山西、陜西、河南、山東等8 個省(區)的64 個地級市(州),并將其劃分為上游、中游、下游3 個區域,見圖2。
3 實證分析
3.1 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測度結果
3.1.1 數字經濟測度結果分析
2011—2020 年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提升(數字經濟指數由2011 年的0.102 提升到2020年的0.258),仍有待繼續提高。以研究期各地級市(州)數字經濟指數均值表征各地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采用Kriging 插值法進行可視化處理(見圖3),從黃河流域整體上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東高西低的空間分布特征;從各省(區)局部來看,數字經濟發展呈現以省會城市為核心的圈層結構,形成了分別以濟南、太原、呼和浩特、鄭州、西安為核心的數字經濟指數高值區。
依據各地級市( 州) 的數字經濟指數均值,以0.149、0.199、0.249 為間斷點,可把64 個地級市(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由高到低分為4 個梯隊:第一梯隊有太原、西安、西寧、濟南;第二梯隊有鄭州、呼和浩特、晉中;第三、第四梯隊城市較多,占比分別為42.2%和46.9%(其中:第三梯隊城市多分布于黃河中下游地區,圍繞在第一、第二梯隊城市周圍;第四梯隊城市多分布于黃河中上游地區,集中于陜西和寧夏)。黃河流域中下游省會城市數字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較強,而位于黃河上游的省會城市西寧、蘭州、銀川自身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待提升、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暫不明顯。
2011—2020 年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提升,高質量發展指數從0.376 提高到了0.508。同樣以研究期內各地級市(州)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值反映各地高質量發展水平并進行可視化處理(見圖4),可以看出,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圈層結構,形成了分別以濟南、鄭州、太原、西安、蘭州等省會城市為核心的高質量發展指數高值區,同時存在周口、榆林、固原、定西等高質量發展指數低值區,且低值區多集中于黃河中上游地區,表明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問題顯著,存在兩極分化的情況。
依據各地級市(州) 的高質量發展指數均值,以0.199、0.249、0.349 為間斷點,可把64 個地級市(州)高質量發展水平由高到低分為4 個梯隊:第一梯隊城市有西安、太原、濟南、鄭州、蘭州、東營;第二梯隊城市占比為18.8%,緊挨第一梯隊城市分布;第三梯隊城市數量最多,占比為40.6%,抱團分布于第二梯隊城市周圍;第四梯隊城市占比為31.3%,分布于各城市群邊緣地區。總體來看,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第二、第三梯隊城市包圍第一梯隊城市的“眾星拱月”特征,高質量發展“高地”與“洼地”共存。
3.2 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測度結果分析
2011—2020 年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顯著提高。根據64 個地級市(州)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逐年耦合協調度及表2,可判定各地級市(州)逐年協調水平的等級,分別以2011 年、2015年、2020 年代表研究期期初、期中、期末,繪制不同時期各級協調水平分布圖(見圖5),可以看出:2011 年,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協調水平具有顯著的地區差異,太原、西安率先跨上勉強協調水平(耦合協調度分別達到0.528、0.519);濟南、鄭州、蘭州、銅川、銀川次之,屬瀕臨失調水平(耦合協調度在0.440 以上);其他市(州)處于輕度失調或瀕臨失調水平,二者占比分別為75.0%和21.9%。2015 年,跨上勉強協調水平的地級市增至6 個(均為省會城市),按照耦合協調度從高到低的順序依次為西安、太原、濟南、鄭州、蘭州、西寧,這6 個省會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與高質量發展均位于黃河流域前列,協調發展基礎較好,優勢明顯;輕度失調水平的城市大幅減少、瀕臨失調水平的城市明顯增加,二者占比分別達32. 81% 和57. 81%。2020 年,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水平實現跨越式提升,所有城市均在瀕臨失調及以上水平,其中西安、太原、晉中、鄭州、濟南、西寧已達到初級協調水平。
圖6 為黃河上、中、下游地區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變化情況,可以看出,黃河上、中、下游地區耦合協調度均呈逐年上升趨勢,2015 年之前黃河中游地區協調水平相對較低、上游和下游協調水平相當,2015 年之后黃河中游地區與下游地區協調水平逐漸持平且均高于上游地區的,至2020 年形成了下游>中游>上游的格局。研究期內,下游地區耦合協調度上升幅度最大,由2011 年的0.370 上升至2020 年的0.515,實現了從輕度失調到勉強協調的轉變;中游地區耦合協調度雖然前期上升緩慢,但2015 年之后快速上升;上游地區耦合協調度雖有所上升但比較緩慢,至2020 年仍處于瀕臨失調水平。
總體來看,研究期初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協調水平屬輕度失調,研究期末二者協調水平屬瀕臨失調和勉強協調并呈現進一步向初級協調轉變的趨勢。研究期內耦合協調度提升的同時,協調水平的區域差異逐步擴大,總體上呈現東高西低的趨勢,即黃河中下游地區耦合協調度高于上游地區的,其原因在于黃河中下游城市人口基數較大,高校及科研院所眾多,有豐碩的科研成果和充足的人才儲備,而黃河上游城市發展方式仍較粗放,科技力量較弱,經濟發展相對滯后。
3.3 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互動關系
運用PVAR 模型,基于2011—2020 年相關數據,進行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互動關系的實證分析。
3.3.1 序列平穩性檢驗
為避免“偽回歸”,在運用PVAR 模型之前,采用LLC 檢驗、ADF 檢驗、PP 檢驗分別對數字經濟指數與高質量發展指數的序列平穩性進行檢驗。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高質量發展指數未通過單位根檢驗,經一階差分后數字經濟指數與高質量發展指數均通過檢驗;進而進行協整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 可以構建PVAR 模型。根據赤池信息準則(AIC)、貝葉斯信息準則(BIC)和漢南-奎因信息準則(HQIC),確定模型的滯后階數為1 階。
3.3.2 脈沖響應分析
為探究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之間的響應機制,通過200 次Monte-Carlo 模擬,得到二者對彼此滯后10 期脈沖(1 個單位標準差)的響應(即相互影響)軌跡(見圖7,其中虛線表示置信區間上下限),可以看出,二者對彼此脈沖的響應均呈收斂趨勢,說明模型是可靠的。
由圖7 可知:1)數字經濟發展和高質量發展在對自身產生脈沖沖擊后,即期產生正向響應且響應程度較高,隨時間推移響應程度逐漸下降,最終趨向于0%,表明數字經濟和高質量發展均有相對的慣性,即對自身依賴性較強,其中數字經濟對自身的依賴程度高于高質量發展對自身的依賴程度;2)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當期影響程度為0%,第2 期影響程度迅速上升、之后逐漸下降,在第10 期趨于0%,說明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但其促進作用具有滯后性且逐漸減弱,原因是數字經濟賦能高質量發展需要經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數字技術應用、數字成果轉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等;3)高質量發展對數字經濟的影響程度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 形變化,影響程度當期為0%,在第2期迅速達到峰值后逐漸降低,在第10 期仍有正向響應(約0.5%),表明高質量發展對數字經濟的積極影響具有一定滯后性和長期性,原因是高質量發展對數字經濟的支撐機制尚未完全形成,相關基礎設施建設需要一定時間。
3.3.3 方差分解
在脈沖響應基礎上,對PVAR 模型進行方差分解,取滯后第5 期、第10 期和第20 期方差分解結果(見表3),分析高質量發展與數字經濟的相互影響:1)數字經濟對自身方差的貢獻率在第20 期仍高達98.2%,說明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發展具有一定慣性,因此各市應適當調整相關政策,除充分發揮數字經濟自身作用外,還要注重其他因素對數字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確保數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方差的貢獻率在第20 期僅為1.8%,即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有限、有待加強,表明黃河流域數字經濟基礎薄弱,未來應著力推動黃河流域數字化轉型,充分挖掘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的價值。2)高質量發展對自身方差的貢獻率保持在75%以上,即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也具有一定慣性,原因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在現階段仍主要依賴相關政策;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對數字經濟方差的貢獻率在逐漸上升,由第5 期的19.0%上升到第20 期的24.9%,說明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可有效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4 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在研究期有所提升,但仍普遍較低且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具有東高西低的特征,呈現分別以濟南、鄭州、西安、太原、呼和浩特為核心的圈層狀分布格局。
2)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不平衡問題突出,存在兩極分化的情況,也呈現明顯的圈層結構,形成了分別以濟南、鄭州、太原、西安、蘭州等省會城市為核心的高質量發展水平高值區。
3)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逐年上升,但協調水平整體上還較低,當前僅實現了由輕度失調水平向瀕臨失調水平的跨越,耦合協調度在空間上呈現下游>中游>上游的特點。
4)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均具有較強的自我依賴性,高質量發展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較為明顯,而數字經濟發展對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有待加強。
4.2 建議
1)提高黃河流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應把握全球數字化發展契機,推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提升黃河流域數字經濟水平。在濟南、鄭州建設國家超算中心等的基礎上,在西安等中心城市加快布局建設國家超算中心、互聯網數據中心等,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推動“智慧黃河”建設。
2)縮小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上游地區應搶抓實施“東數西算”工程的機遇,加快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中游地區應圍繞電子信息、裝備制造、交通運輸等優勢產業,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下游地區應保持良好發展勢頭并發揮引領作用,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
3)提高黃河流域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水平。一方面,各省會城市正處于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相互促進的發展階段,要注重數字經濟與傳統產業的結合,打造先進科技產業園區,形成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數字經濟與高質量發展協調度較低的地區應注重培育數字經濟市場,建立與省會城市之間的鏈接,促進數據要素流通,探索適合當地的數字經濟發展方式,為高質量發展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