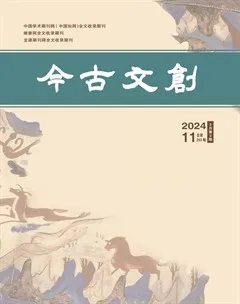民國時期妾之身份地位問題研究綜述
李嘉美
【摘要】目前,學術界關于近代妾的身份與地位的相關研究大都從法律的視角出發,然而妾的身份與地位在法律上的規定與實際生活存在差距,單從法律的視角無法全面、真實地體現近代妾之群體的生活全貌。隨著民主革命的發展,男女平等思想逐漸傳播,女性權利日益受到重視,有關反對蓄妾的言論中多見男子本位立場,難以純粹地表達女子訴求,探討妾之身份地位的轉變需多關注女性本身。歷史地分析妾的身份地位變化對于探究民國時期妾制問題,進而揭示其復雜性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關鍵詞】民國時期;妾之身份地位;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K258?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12-007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2.023
妾制作為中國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婚姻形態的產物,歷經漫長的發展過程將女性禁錮在傳統禮教之中,納妾逐漸成為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習俗。近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想文化傳入中國,人們對平等人權的訴求深入到各個領域。受女性主義影響,具有濃厚社會基礎的妾制受到輿論抵制,廢妾運動推動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身為邊緣群體的妾的身份與地位在動蕩局勢下發生微妙變化。
學術界有關妾的研究大多包含于婦女史研究之下,對妾的專題研究不多。近代社會學家、女權主義者、法學家、歷史學家等從不同視角拓展婦女史研究,研究范圍深入到社會邊緣群體,有關妾、婢女、娼妓等的研究逐漸增多,對于妾的研究涉及妾的來源、身份、地位、財產、婚姻等問題。以下將對有關妾之身份地位的研究成果進行簡單綜述:
大體來看,舊時妾的身份與地位是低下的。麥惠庭(1935)指出妾不論在法律上還是家庭中都是最卑賤的,法律上表現在名稱、喪服、刑律、離婚、為母等方面的規定上,妻與妾存在明顯的不平等。妾的來源大多是婢女、已婚的婦人、娼妓、平常女子很少,以上這幾種婦女都為一般人所賤視,她們嫁人做妾,也常被人看不起。陳東原(1928)認為女子淪為姬妾便與玩物無異,能夠留有性命已是幸事。近代以來,妾的身份地位有所變化,以下分法律和家庭兩方面做敘述。
一、民國法律中妾之身份地位的相關研究
民國妾制在法律規定中的變化是中國法律近代化過程中的重要內容之一。妾制法律變遷關注到妾的權利問題,法律上賦予妾家屬的身份。徐靜莉(2008)根據大理院的司法判決來界定妾的身份,妾的身份在正妻死后可能發生變化,通常必須經過特別聲明或某種特別的儀式將其改為正妻,該妾才可取得妻之身份。李淑婷(2019)認為妾的地位總體上是卑賤的,明清時期由于商業化和社會變動的加劇造成身份等級界限的松動,國家和社會對貞潔寡婦的崇拜使得守節寡妾的社會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李淑婷關于妾身份法律上的界定與徐靜莉的看法一致,并在此基礎上又補充了“平妻”這種不被法律認可的民間習慣,平妻在地位上沒有高低之分。與民間習慣不同,法律規定中的妻妾地位更為明確,梅杰(2009)提到民國時期妻妾地位的差異,妾的家屬地位的獲得需與家長同居,沒有同居就不能稱為家屬,也不可以要求扶養費,這樣的規定顯然將妻妾的地位嚴格區分開來。席悅(2016)指出民國時期大理院判例中妾身份的成立需要具備的條件:雙方達成合意;妾與家長是契約關系;夫妾關系不同于男女曖昧同居之關系,享有家屬之待遇。梅杰認為妾取得身份后在家族中的地位低于正妻,受正妻監督,妻與妾的身份并不是不可轉換,妾可扶正為妻。王若宇(2018)認為民國初期納妾并未被法律禁止,妾在形式上等同于妻,便可宣告其身份的確立,另外,判例中規定“妾為家屬之一員應與其他家屬受相同之待遇”,妾被正式確定為家屬中的一員。
南京國民政府試圖通過法律制度取消妾制。王昆(2009)運用女性主義法學的研究方法,以女性的視角和女性的思維方式在宏觀上關注法律制度對女性的壓迫,論述了南京政府婚姻法中的妻妾關系與地位。王昆認為南京婚姻法中沒有對妾問題做相關規定,表面上,妾制度消失于婚姻法典,事實上仍然存在。實務上或許將妾當作社會中的弱者,加以保護。妾可在妻亡后取得妻的地位,夫妾關系的解除條件較之夫妻關系解除條件更為寬松。李剛(2010)關于妾的法律地位與王昆的看法相同,他認為在司法實踐中,最高法院盡力支持妾的訴訟請求,保護婦女權益。王翔(2012)認為,到了近代,妾因其卑賤的出身被人所詬病,一個人只要沾染了妾的名號,就被當作揮之不去的污點。法律上,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大理院的不斷的判例釋法到《親屬篇》的頒布,妾逐步從按照“妻備用之”的家屬變為徹底不受任何婚姻法律限制的“家屬”。李剛最后得出結論,妾的身份在當時的法律規定中消失。
權利意識的增強使得妾在法律上的身份消失后依然能夠維護自己的權利甚至提高自身地位。程郁(2002)分析了北洋時期發布的《民律草案·親屬篇》及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民法《親屬編》相關條文,認為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十分微妙,由于家族制正在解體以及現代法律意識的引進,傳統的妻妾之間嚴格的階級差別已大大削弱,而隨著男女平等思想的傳入,妻在法律上的權力較前加強,于是妾隨之得以在某些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地位。社會變動的加劇及道德觀念的轉變促成妾地位的變遷。盧然(2021)指出近代以來,在子女地位與繼承權利方面,妾的地位得到顯著提升。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妾大多出身貧寒,在身份關系中受人宰制的可能性極大,因此傾斜性的保護并擴張妾的權利成為司法實踐中的突破點,這一突破的背后是女性平權的訴求,妾在法律上的地位變遷是道德觀念從傳統過渡到近現代的典型例證。黃夢蛟(2013)在論及妾的法律地位時認為從古代到民國初年,妾一直具有合法地位,南京民國政府時期,由于男女平等、廢止納妾等思想原則成為國民黨的黨義,必須照顧到眾多納妾者的利益。妾在法律上的規定特殊,雖然妾在事實上尚且存在,但其地位如何,無須以法典或者單行法的形式規定出來。
然而,妾權利的維護在司法實踐中面臨諸多困境。丁艷雅(2021)以民國新會何氏告夫妨害婚姻案為例展現女性維權的不易。整個訴訟過程始終圍繞何氏的身份是“妻”還是“妾”這一問題。是否為“妻”決定著何氏能否對其配偶提起告訴。“妾”由于法律上的身份消失,并不具有告奸資格。司法官對何氏身份的認定經歷了由妻到妾再到妻的反復過程,丁艷雅認為這背后是以夫權為中心的傳統婚姻觀與男女平等的新型婚姻觀的較量。由于民國時期女性的依附地位與知識的局限,民國法律對告奸權利設置的限制明顯偏向男性,只要男子納妾得到其妻子的同意或諒解,男子納妾就被變相保護。據此案例,丁艷雅指出何氏不懼一次次失敗,堅決依據民國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維護自己的權利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這充分表明何氏女性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堅強性格,另一方面何氏法律知識的局限,進一步加劇了本案的復雜性以及何氏在訴訟中失敗的可能性。
大體可以說,法律規定中妾的消失對于妾群體來說并不是一種消極打擊。一方面,妾擁有家屬身份可以享有與其他家屬相同的待遇。另一方面,取消妾制使得夫妾關系解除更為自由,這給了妾更大的自主權。男女平等意識及法律意識的加強為妾在實際生活中爭取自己的權利進而提升自己的地位提供了可能。
二、家宅之中妾之身份地位的相關研究
近代中國社會處于各方面趨向近代化的過渡階段,妾群體身處在動蕩局勢之下,其身份與地位與舊時相比也發生著變化。席悅(2016)從四個方面論述了妻妾之分:數量上,妻子只有一個,妾可以有多個;程序上,娶妻必須明媒正娶,納妾沒有要求;家族地位上,妾不被當作夫家的家族成員不可入宗廟,妾所生之子不可承繼宗嗣;日常吃穿住行上,妻妾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吳曉娟(2017)指出“中國婚姻之目的,在上以祭祖先,下以續后世。”納妾作為延續宗族血脈的重要手段得到家族勢力的支持,直到民國時期,納妾依然作為一種民間習慣在社會中普遍存在。作者認為,在西方女權主義思潮以及男女平等思想的影響下,“三從四德”“貞節烈女”的封建枷鎖被拋棄,婦女團體開始反抗舊家庭制度的束縛,妾群體也不例外。程郁(2007)認為民國時期妾的出身發生著復雜的變化,相對于明清時期宗譜中省略妾的出身,民國時期的宗譜部分有的稱“愛娶”,記有父名,還記有妾的故鄉,良家女兒為妾者更多了。名人之妾公然登上社交場面以及寵妾虐妻現象都表明妻妾關系發生微妙變化。程郁指出前清時妻打殺妾罪輕,而妾打殺妻罪重。民國時期,這種不平等條款被取消是妻妾關系中最為明顯的變化,由于丈夫寵妾多于妻,妻就容易淪為被凌虐的一方。
盡管妻妾之間尊卑不可逾越,但是近代以來妾的地位總體上是提升的。程郁(2005)認為民國時期妾的地位有所上升,民國時期,名流攜妾出入公共場所并非罕事,甚至出現妻守于內而妾出于外者。在稱呼及家儀上,妻與妾在一些場合已皆稱夫人或太太,僅冠姓以區別。妾地位的提升還體現在家譜中妾名字的記載以及妾財產權的保護上。蘇全有(2018)論述民國時期妻妾對于財產、名分、家務及傷人的爭斗,民國時期正常家庭中妻妾之爭呈現出多種形態,正室的強勢地位并沒有特別凸顯,存在妻居高位、妾居高位以及妻妾勢均力敵三種情況,妻妾之爭中妻妾的地位各有差異。蘇全有從妻妾之爭的復雜性中發現妾的地位處于一種動態變化中。朱穎(2014)依據資料認為在民國社會實際生活中,妾在家庭中的地位沒有傳統意義上認為的那樣低下,有經過親族同意后進門的“二夫人”,這些人地位比妾還要低。從遺產繼承上來看,妾所生子女與嫡出子女在家中的待遇幾乎是一樣的,在財產分割中亦沒有區別。有的妾自恃夫寵,地位甚至超過了妻。張靜(2018)論述了近代社會廢除妾制的曲折,民國初年,納妾成為一種風尚,很多軍閥官僚出入各種高級場合都帶著“如夫人”出席,從這個角度看,妾的地位還略高于妻。社會中擁有三妻四妾者不可勝數,許多人認為這樣才能維護中等人家的體面。溫文芳(2007)通過對《申報》中一些有關晚清“妾”之地位的典型案例的分析,闡述了作為近代婦女一部分的“妾”在當時婚姻家庭方面的地位。妾來源的獨特性決定了她們身份地位的奴役屬性,若丈夫寵愛,妾的境遇會好一點,甚至出現“權傾正室”的可能。
社會變革之際,近代的妾制徘徊在消亡與興盛之間,并且出現與舊式妾天差地別的新式妾。陳俊(2017)認為“新民法”采取放任不管的態度,不僅沒有遏制社會上的納妾之風,反倒助長了社會的不正之氣,使得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家庭矛盾也愈加激化。吳卓昱(2017)認為北洋時期妻妾的身份法律地位之不同體現在娶妻納妾的程序上,納妾已經更加注重雙方的意志自由,而非強迫被逼。娶妻的規定與納妾的規定相比,仍顯得更加規范、正式和嚴格。新式妾與傳統的妾相比地位有著天壤之別,有的甚至高于夫的原配和夫本人。武學茹(2019)從習俗方面體現家庭中妻妾身份地位之別。民國時期妻子對丈夫可以以“夫”相稱,而妾只可以“君”“家長”相稱。在為親者守孝的時間與喪服問題上,妻與妾的待遇截然不同,按照封建倫理,妻死妾有守孝的義務。在子女方面,妾的子女是庶出,妾無權置喙兒女的婚配問題。其次,納妾會影響夫妻關系,導致家宅不寧。妻妾共侍一夫,容易引發女子的妒忌心,爭風吃醋,嫡庶有別,容易帶來異母兄弟的明爭暗斗。趙雨薇(2018)認為民國當下因寵妾而冷落正妻的情形比比皆是,雖然妻對妾有監督權,但妻妾別居顯示妻對妾的監督弱化,這多出于維護社會和家庭穩定的考慮。
從以上研究成果可知,近代以來的妾的身份與地位較舊時的妾已經有了提升,法律上賦予妾家屬身份,司法實踐中保護妾的權利。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妾與妻的身份地位甚至可以互換,新式妾的出現顛覆了舊式妾被奴役被買賣的卑賤形象。不過,以上研究偏重法律視角,角度單一,難以體現近代社會妾制發展的動態變化及其復雜性。
三、研究不足與展望
從法律和家庭兩個角度看以上研究成果,學者對民國時期妾的身份地位變化的考察不斷深入,但仍有一些缺憾需要繼續補足。有一些亟待解決問題,如民國時期的妾與舊時的妾的身份地位有何發展?在妾的身份地位變化過程中,身為妾者是對自我的身份認知如何?這些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對近代婦女邊緣群體史料的深入挖掘與思索。
參考文獻:
[1]程郁.清至民國蓄妾習俗與社會變遷[D].復旦大學,
2005.
[2]程郁.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及其變遷[J].史林,
2002,(02).
[3]吳卓昱.北洋政府時期妻妾身份法律地位之比較[D].西南政法大學,2017.
[4]王若宇.民國時期東北地區納妾現象研究——以《盛京時報》刊載為中心[D].吉林大學,2018.
[5]朱穎.民國時期妾的法律地位研究[D].華東政法大學,2014.
[6]徐靜莉.民初女性權利變化研究——以大理院婚姻、繼承司法判解為中心[D].中國政法大學,2008.
[7]梅杰.從典型案例析民國婚姻法制演變[D].西南政法大學,2009.
[8]席悅.民初妾之民事法律地位研究(1912—1928)[D].西南政法大學,2016.
[9]王昆.南京政府婚姻法的女性主義法學分析[D].河南大學,2009.
[10]王翔.如夫人的煩惱——中國二十世紀早期有關納妾的記憶、敘事與現實[D].首都師范大學,2012.
[11]盧然.女性平權與法律革新[J].蘇州大學學報,2021,
(05).
[12]李剛.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妾”的法律地位與司法裁判[J].山東社會科學,2010,(04).
[13]李淑婷.民國時期妾之財產權研究(1912—1949)[D].天津財經大學,2019.
[14]黃夢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離婚制度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2013.
[15]丁艷雅.是妻抑妾:民國新會何氏告夫妨害婚姻之訴中的眾聲喧嘩[J].中山大學法學評論,2021,(01).
[16]蘇全有.論民國時期的妻妾之爭[J].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18,(02).
[17]吳曉娟.民國時期納妾現象的法社會學分析[D].南京師范大學,2017.
[18]溫文芳.晚清“妾”之地位及婚姻狀況——以《申報》1899年—1909年“妾”之典型案例為中心[J].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07,(03).
[19]陳俊.民國時期妾制的法律變遷[D].蘇州大學,
2017.
[20]張靜.批判與反思:中國近代廢除妾制的艱難歷程[D].西南政法大學,2018.
[21]程郁.中國蓄妾習俗反映的士大夫矛盾心態[J].河南大學學報,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