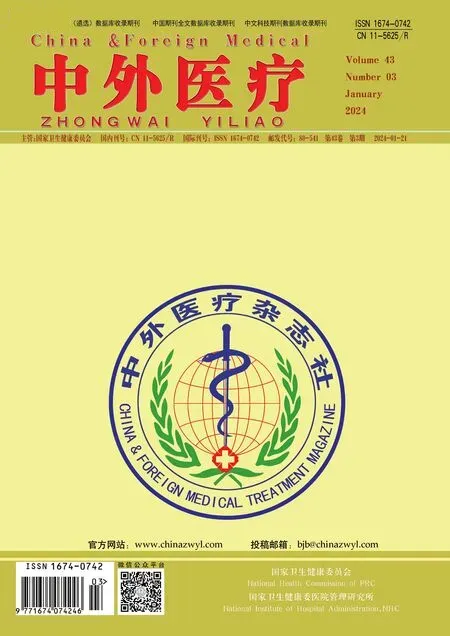糖尿病腎病診斷及治療新進展分析
張偉蘭
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醫院內分泌科,上海 201505
糖尿病腎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為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微血管并發癥之一,根據文獻報道約有35% 的DM 患者會發展為DKD[1]。由于近年我國DM 患病率上升顯著,最新數據顯示患者數量已超過1.4 億,改變了慢性腎臟病病因頻譜,DKD 已經取代腎小球腎炎成為我國慢性腎臟病的首要病因[2]。現階段,隨著對DKD 研究的深入,國內外更新了DKD 診治指南,同時大量關于DKD 的臨床證據涌現,為本病的臨床診斷和治療提供了新的依據和思路,現對此進行總結,具體如下。
1 DKD 診斷方法研究進展
研究發現,DKD 腎功能喪失可能發生在白蛋白尿之前,國內外指南推薦的尿白蛋白(Urinary Albumin, UALB)和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在DKD 早期臨床診斷中的應用存在一定局限性[3]。探尋DKD 早期診斷高度靈敏和特異的生物學標志物成為研究重點并取得一定成果,為本病早期診斷提供了靶點,現對近年發現的DKD 新型生物標志物進行綜述。
1.1 非對稱性二甲基精氨酸(Asymmetric Dimethylarginine, ADMA)
ADMA 為L-精氨酸(Arginine, Arg)二甲基化衍生物,是內皮祖細胞分化的一種內源性內皮型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 NOS)抑制劑。研究發現,血ADMA 水平增高會減少DM 患者一氧化氮(Nitric Oxide, NO)生成,造成腎臟血流減少,引起eGFR 下降及腎缺氧[4]。ADMA 還會選擇性抑制NOS 引起血管內皮功能障礙,抑制血管內皮細胞再生和分化,同時顯著提高細胞外基質蛋白表達水平,強化氧化應激與炎癥反應,促進組織纖維化,直接參與DKD 進展[5]。有學者在研究中證實,ADMA與eGFR 呈負相關,與糖化血紅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 HbA1c)、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rine Albumin-to-creatinine Ratio, UACR)和UALB 呈正相關,并正式對DKD 有評估價值[6]。另有一項列隊研究發現,ADMA 高水平的2 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T2DM)患者蛋白尿發生率與早期DKD 發生率均高于ADMA低水平者,認為ADMA 與DKD 獨立相關[7]。
1.2 可溶性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物受體(Soluble urokinas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ceptor, suPAR)
suPAR 為三級結構域蛋白,在內皮細胞、免疫細胞等多細胞中表達,被證實與包括DM、DKD 等在內的多系統疾病存在相關性。有研究發現,suPAR會改變腎小球通透性,影響尿白蛋白的排泄,是DKD 發生與進展的影響因素[8]。有橫斷面研究顯示,1 型糖尿病患者血suPAR 高表達,而且與患者尿蛋白量和DM 病程獨立相關。另有學者在研究中證實,健康人、T2DM 患者及DKD 患者的suPAR 呈遞增趨勢(P<0.05),suPAR 與DKD 患者的eGFR 呈負相關,認為可用于DKD 的早期識別,以及預測DM及DM 高危人群高蛋白尿風險[9]。
1.3 晚期糖基化終末產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AGEs)
AGEs 是過量的糖與蛋白質結合形成的高度異質化產物,可以同人體細胞組織上的AGEs 受體累積部位引起氧化應激,從而對細胞結構與功能造成破壞,被認為與多種退行性疾病的發生有關并且能夠加速衰老。有研究顯示,DM 患者機體代謝紊亂、血糖高,會增加AGEs 表達,激活AGEs-AGEs 受體(Receptor of AGEs,RAGE)軸,從而產生更多活性氧與細胞因子并增強炎癥反應,會引起腎臟結構改變與功能喪失,損害腎小球濾過屏障功能,最終引發DKD[10]。有學者基于腎活檢測定的腎小球基底膜寬度將DKD 患者分為快速進展和緩慢進展兩種,發現前者的AGE 顯著升高,經回歸模型分析AGEs 與DKD 快速進展呈正相關,可用于DKD 進展的早期評估。葉帥等[11]依據UACR 將105 例T2DM 患者分為3組,均行皮膚AGEs 檢測,結果顯示AGEs 與UACR 呈顯著正相關,AGEs 是UACR 獨立風險因子,AGEs 診斷DKD 的靈敏度為78.78%,特異度為76.92%,認為AGEs可作為DKD 預測因子。
1.4 蛋白質組學與代謝組學
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相關脂質載運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 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是一種脂質結合蛋白,能夠與中性粒細胞明膠酶結合并調節其活性。現代研究發現,NGAL 參與細胞分化凋亡與炎癥免疫應答,中性粒細胞在炎癥狀態下激活,釋放過量NGAL 進入周圍組織,會加重炎癥反應,造成組織損傷。NGAL 也被急性透析質量倡議工作組認為是腎損傷最具潛能標志物之一[12]。有研究中指出,人體器官組織代謝異常會引起NGAL 過量表達,DKD 患者血NGAL 水平升高明顯且表達速度比Scr、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等更快,以此診斷DKD 的敏感度優于傳統腎損傷標志物[13]。張馳等[14]人通過研究證實,大量UALB 的DKD 患者NGAL 高于UALB 正常及微量的患者,是DM 患者并發DKD 的獨立危險因素,診斷DKD 敏感度93.97%、特異度95.74%,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Curve, AUC)0.759,聯合血清胎球蛋白診斷效能更高。
代謝組學方面,有研究證實,DKD 患者血鞘磷脂、葡萄糖神經酰胺、鞘氨醇等鞘磷脂代謝產物水平均明顯高于單純DM 患者,且與DKD 患者UACR明顯相關[15]。另有學者分析DKD 患者腎臟結構與尿代謝產物相關性,發現DKD 患者腎臟內皮細胞破壞與尿液中的短鏈非酯化脂肪酸2-乙基-3 羥基丙酸有關,DKD 患者脂代謝紊亂,短鏈非酯化脂肪酸高表達,會加重腎間質細胞纖維化與尿蛋白,可能提示DKD 早期病變[16]。
2 DKD 治療藥物研究進展
近年,關于DKD 治療藥物的研究同樣取得一定突破,國內外指南也均對DKD 的治療做了更新,另有不少藥物正處于臨床研究階段。現對近年熱門研究及應用的藥物進行綜述。
2.1 鹽皮質激素受體拮抗劑(Mineralcorticoid Recept Antagonist, MRA)
鹽皮質激素受體(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MR)主要在包括腎臟和心血管在內的醛固酮(Aldosterone, ALD)靶器官中表達,腎素-血管緊張素-醛固酮系統(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興奮時,過量分泌的ALD 進入靶細胞與MR結合會介導靶器官病理損害。另外,DKD“高灌注、高過濾、高壓力”也會引發MR 過度活化,會增加患者腎心不良反應發生風險,同時加速DKD 進程。MRA 可以與MR 結合,從而阻斷MR 過度活化,抑制其生物效應,與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Angiotensio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 ACEI)、血管緊張素受體阻滯劑等DKD 傳統治療藥物聯合應用,被證實可以雙重阻斷RAAS,降低DKD 患者心腎損害。
非奈利酮為第三代MRA 的代表藥物,是近年DKD 治療領域研究的熱點藥物之一。本品是基于二氫吡啶結構研發的塊狀立體非甾體新結構藥物,對MR 的選擇性更高、結合力更強,效果優于螺內酯、依那普利等傳統MRA 藥物,可以更好地抑制腎臟炎癥與纖維化。有學者在標準RAAS 抑制劑治療基礎上,予以血鉀≤4.8 mmol/L 的T2DM-DKD 患者不同劑量的非奈利酮及安慰劑,結果顯示患者的UACR 呈劑量式降低。有研究在最大負荷劑量RAAS 抑制劑治療基礎上予以T2DM-DKD 患者非奈利酮治療,結果顯示患者eGFR 下降率超過40%,腎臟原因終點事件以及心衰住院、心肌梗死死亡等心血管事件發生率也明顯降低,效果優于安慰劑治療,并指出DKD患者病程早期應用非奈利酮可能獲益更多[17]。另有一項薈萃分析發現,DKD 標準治療基礎上加用非奈利酮,可以降低患者心血管復合風險14%、首次心力衰竭住院風險22%、腎臟復合終點23%[18]。
2.2 鈉-葡萄糖協同轉運蛋白2(Sodium-dependent Glucose Transporters 2, SGLT2)抑制劑
DKD 治療策略眾多,阻斷RAAS 目前仍是控制本病發展的關鍵,RAAS 抑制劑也因此成為DKD 標準用藥。不過研究發現,此類藥物對早期DKD 患者腎小球高過濾狀態改善效果不明顯。SGLT2 抑制劑為DKD 治療新藥,包括坎格列凈、達格列凈、恩格列凈等6 種,也是繼RAAS 抑制劑后第二個經循證醫學證明能夠延緩本病進展的藥物。此類藥物可以通過管球反饋機制雙重介導葡萄糖和鈉的重吸收,從而保護腎臟,提高腎小球濾過率,被認為適用于DKD 的早期治療。有研究予以T2DM 患者SGLT2 抑制劑,結果顯示患者UACR 升高的相對風險率降低,DKD 發生和進展的風險降低,腎臟替代治療減少[19]。相關學者在RAAS 抑制劑治療基礎上予以早期DKD 患者SGLT2 抑制劑24 周,結果顯示患者eGFR 較前明顯提高,血糖參數、Src、BUN、UACR 等較前明顯降低,血脂參數也得到改善,認為SGLT2 抑制劑可以緩解DKD 早期癥狀,延緩或抑制DKD 進程。另有研究證實,以SGLT2 抑制劑聯合二甲雙胍、RAAS 抑制劑治療T2DM 可以明顯降低患者eGFR,與本品可以降低血糖、改善腎臟血流動力學穩態、減少氧化應激水平、減輕腎小管間質損傷有關[20]。中華醫學會腎臟病學分會《糖尿病腎臟疾病臨床診療中國指南》(2021 版,以下簡稱CSN 指南)對DKD 治療做了更新,推薦合并DKD 且無禁忌證的T2DM 患者使用SGLT2 抑制劑。
2.3 胰高血糖素樣肽-1 受體激動劑(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 GLP-1RA)
GLP-1RA 作用靶點多樣,可以調節RAAS,改善氧化應激與內皮功能,減輕MRA損害與腎纖維化,是新近應用于臨床的DKD 治療藥物,可以降低血糖,發揮腎臟保護作用。GLP-1RA從結構上可以分為基于Exendin-4 結構和天然GLP 結構2 種,依據半衰期不同可以分為日制劑與周制劑2種。其中,日給制包括艾塞那肽、利斯那肽、利拉魯肽等,周制劑包括度拉糖肽、度拉糖肽、阿必魯肽等,為臨床用藥提供了更多選擇,利于DKD 患者個體化降糖管理的實現。有研究予以T2DM 患者利拉魯肽,結果顯示患者心腎危險因素與腎臟終點時間發生率均低于應用安慰劑的患者。另有研究顯示,艾塞那肽日劑與周劑的有效性與安全性相當,均可有效降低DKD 患者血糖水平與HbA1c,同時可以比格列美脲更好降低DK 患者的UALB,并且還具有抗腎臟纖維化的作用,可以減少腎臟復合終點事件與心血管結局事件的發生[21]。另有學者在甘精胰島素基礎上予以中晚期DKD 患者杜拉魯肽,雖降糖效果同對照組相當,但患者體質量與UACR下降水平明顯,eGFR持續下降也超過30%。另外,2021版CSN 指南對于存在禁忌證以及用藥后血糖控制不佳的T2DM-DKD 患者,推薦具有腎臟獲益證據的GLP-1RA以延緩病情進展。
3 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對新近DKD 診斷及治療方法進行了匯總分析,診斷方面以探究DKD 早期診斷高度靈敏和特異的生物學標志物為重點并取得一定成果,ADMA、suPAR、AGE 以及蛋白質組學和代謝組學相關指標,為DKD 的早期診斷提供了新靶點。治療方面,MRA、SGLT2 抑制劑、GLP-1RA 為DKD 新近治療藥物,在臨床得到應用并被認為有效,相關研究取得可喜進展,但在病機研究與藥物開發方面尚有巨大進步空間。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藥物進入臨床試驗,將為DKD 及相關疾病治療提供更加豐富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