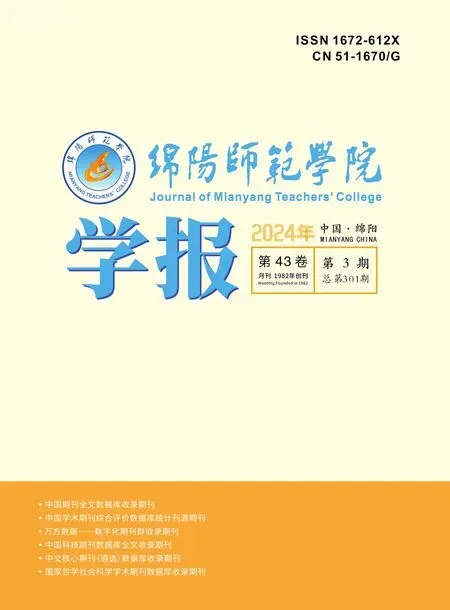元好問《東平府新學記》解析
楊萬里
(溫州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溫州 325035)
一
成吉思汗六年(金大安三年,1211)蒙古第一次攻金,揭開了蒙古人滅金的序幕。九年(金貞祐二年,1214)五月金宣宗從中都(今北京)向南遷都汴京(今開封)。十二年(金興定元年,1217)蒙古征金統帥木華黎聽取漢人謀士的建議,采取了武力征伐與政治招撫相結合的策略,重用金國降附過來的漢將,迅速攻取遼西、河北、山西、山東各地數十城。十五年(金興定四年,1220),金宣宗分封河北、山東、河東的地方長官或武裝首領王福等九人為公,總率本路兵馬以抵抗蒙軍,并可自設公府、任命官吏、征斂賦稅、賞罰號令。蒙古統帥木華黎及其子仿效金人作法,置漢軍萬戶(亦稱“世侯”)。到窩闊臺汗六年(金天興三年、1234)滅金時,十四年間河北、河南、山西、山東出現了數量眾多的世侯,其中真定史天澤、順天張柔、東平嚴實、益都李全、澤州段直皆其表表者。
據記載,在蒙金之戰中,“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汾、石、嵐、管無不屠滅”[1]卷二十八《廣威將軍郭君墓表》,15,“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2]乙集卷十九,592,“貞祐初,人爭南渡(即金宣宗南遷)而阨于河,河陽三城至于淮、泗,上下千余里,積流民數百萬,饑疫薦至,死者十七八”[3]卷134,448。李俊民《大陽資圣寺記》載,金朝盛時晉城縣境內有寺院二十一區,經貞祐甲戌至甲午(1214—1234)蒙金之戰,二十年間僅存十之三四。居民蕩析,鄉井荊棘[4]卷二十九,406。蒙古軍在滅金的23 年里,肆意蹂躪華北和中原,而這些漢族世侯為保存當地的農業文明和儒家文化,為保護廣大老百姓免遭涂炭起到了重要作用。
自蒙古滅金(1234)至忽必烈繼汗位(1260)的26 年間,蒙古統治者尚不能接受中原的政治文化傳統,整個北方的社會政治秩序處于混亂動蕩之中。這一時期,金朝遺留下來的士大夫主要受到漢族世侯的庇護,聚集于他們的幕府中。如《元史·張柔傳》:“(金國)其臣崔立以汴京降,柔于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實錄》并秘府圖書,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余家,衛送北歸。”王惲記載:“北渡(指金國滅亡,在京官員士人被押至河北、山東安置)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真定史天澤)好賢樂善,偕來游依。若王滹南(若虛)、元遺山(好問)、李敬齋(治)、白樞判(華)、曹南湖、劉房山、段繼昌、徒單颙軒,為料其生理,賓禮甚厚,暇則與之講究經史,推明治道,其張頤齋、陳之綱、楊西庵、張條山、孫議事,擢府薦達,至光顯云。”①劉因《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載∶“州人李俊民,在金時以明經為舉首,后國朝亦被累征,賜號‘莊靖先生’,蓋有道之士也。是時方避地河南,隱約自處,公(段直)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后已。故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②[3]卷466,436-437李謙《冠州廟學記》也提到:“一時名士夫,如遺山元公(好問)、紫陽楊公(奐)、左山商公(挺)諸人,皆流寓于此(東平冠縣)。”[3]卷287,85-86金亡后,在東平嚴實保護下的名士有宋子貞、王磐、康曄、李昶、劉肅、張特立、徐世隆、張昉、商挺、杜仁杰、元好問等。1238 年李世弼應孔元措之請而撰寫的《褒崇祖廟記》有云:“元措以太常卿寓于汴。歲癸巳(1234),當京城之變,被領中書耶律公(耶律楚材)奏稟,檄遷于博,再遷于鄆(即東平)。其衣食所須,舍館之安,皆行臺嚴相資給之。”這大概是當時世侯保護知名士人的一般情形。嚴實之子嚴忠濟嗣位后,沿續了其父在位時的統治做法,并于1252—1255年重修東平府學,元好問為此寫下了這篇《東平府新學記》。
二
元好問在學記中開篇就回顧了東平府學的歷史: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圣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徳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978—1038)罷相判州(1035 年前后),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牓》在焉。劉公摯領郡(1092),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眀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1130—1137)都大名,徙學于(東平)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為圣作者,不預焉。齊巳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1201—1208)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髙公霖同出于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按,指徙學府署西南以來),貞祐之兵(1213 年秋,元太祖率兵自紫荊關入,略河北、山東、河東而歸)始廢焉。
元好問這段對東平府學歷史的追溯文字,核心思想有三點:一是東平府學在唐宋金歷史上一脈相承;二是東平“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的風俗強大;三是東平在金國出了數位大人物,故府學最盛。
按,東平府學在宋代稱鄆州州學,始于王曾罷相判府之時(1038),早于慶歷興學的1044 年。皇祐五年(1053)龐籍降知鄆州,他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元豐八年(1085)轉運使井季能新建鄆州學。第二年元祐改元(1086),滕元發再知鄆州,增學田二千五百余畝,從此鄆學經費充裕,教師和學生得以安心問學。元祐朔黨領袖劉摯自小撫養于鄆州外家,結發就師即在此學讀書,從先生長老姜潛(石介弟子)、劉述、龔鼎臣(1009—1086)輩治經藝,習文辭,上下凡十余年。元祐五年(1090)劉摯回鄆州當知州,七年正月上書請頒經籍,詔可,十月自京師得書二千七百卷,事見劉氏《鄆州賜書閣記》③。北宋時知鄆州者大多卓有聲望,他們在鄆學應多留有文字,然元好問在重建后的東平府學中所見北宋舊物,僅僅陳堯佐(963—1044)的《府學題牓(記)》和富弼(1004—1083)的《新學記》,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概與黨爭有關,如偽齊時東平遷新學,舊學中徽宗撰稿、蔡京書寫的《大觀八行碑》就被拋棄不用。舊黨領袖劉摯的《鄆州賜書閣記》應有刻石在鄆州州學里,但也找不到了。
元好問強調東平府學在唐宋金歷史上一脈相承,與他持 “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的基本文化立場有關[1]卷三十九。這種思想出現的原因是:蒙古族入侵金國后,極大地激發了當時士人階層對金朝的認同感和責任感,以金朝為“中國”、為“正統”的意識得到空前的強化④。元好問在蒙古圍汴京城時,深感“獨有事系斯文為甚重”,便給蒙國統帥的重要參謀耶律楚材寫了一封信,即《癸巳歲寄中書耶律(楚材)公書》,信中元好問低聲下氣地向耶律楚材請求,希望后者能保護自己列在名單上的金國文化人:“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以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助閣下。”[1]卷三十九維系金國正統地位的力量當然不是種族,而是文化,直接說便是“中州文派”。東平府學實在是這個文派相承的重要載體。因為在元好問眼中,學校出好風俗,好風俗出人才。
元好問在本篇學記中特別提到東平“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的良好風俗,這與他一慣強調風俗的重要性有關。他在《令旨重修真定府廟學記》中說:“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并在《壽陽縣學記》一文中重復了這個觀點:“予謂二三君子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儀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風俗是國家元氣,風俗由學校而來。顯然,元好問所說的風俗是指知書達禮的社會習俗,一種有別于游牧文明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類似的意思,元好問還在《博州重修學記》中說道:“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將風俗提升到國家元氣的高度,這是元好問獨特的文化歷史觀。
“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眀復、徂來石守道配焉。”在學校里或旁邊建當地名人祠堂,以勵風俗,這種風氣起于北宋后期,盛于南宋中期以后。劉摯《閣記》并未提到此祠,應該是當時還沒有。元好問見到的東平府舊學門外的王曾祠,或許建于金國時,受南宋影響而建者。祠王曾而以孫復、石介配享,實屬不倫,或以位而不以德也。以學問和影響力而論,王曾不能與孫、石二人比。孫復(字明復)1034年起在泰山附近講學30年,范純仁等是其早年的學生。石介(字守道)天圣八年(1030)與歐陽修同榜中進士,出任鄆州觀察推官。后提舉應天府書院、任御史臺主簿、國子監直講,“太學之盛,自先生始”,慶歷五年去世。孫復與石介都是開宋代理學風氣的先驅。王曾只不過是一個官運亨通的太平副宰相罷了,其歷史地位無法與孫、石并論。
又,依劉摯《鄆州賜書閣記》所述,“鄆學興于景祐戊寅(1038),實在慶歷立學詔令前,歷年最久,盛冠東方”。東平府學鼎甲一方由來久矣!非盛于金國泰和以后。不過,金朝時,東平府學倒也沒有衰落,繼續保持著以前的榮耀,這是值得肯定的歷史功績。《金史》高霖本傳記載“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恒數百人”,規模不小。高霖授徒當是私人招生講學,官學不與,因為當時府學的官定規模不過六十人(詳下)。
三
先相崇進開府之日(1236),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蒞政(1240),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馀六十人,在東序,隸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隸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1251)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1255)六月。五十一代孫衍圣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1234)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1239)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懸),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元好問《東平府新學記》)
嚴實開府東平大約是1236 年前后,是時,他雖有復興學校之意,但恢復生產、安置流民尚是當前最迫切任務,加之他在1240 年就去世了,所以東平府學的復興并沒有走在當時世侯辦學的前列。澤州長官段直在1246 年前已修成澤州府學⑤。真定府史天澤與手下張德輝于海迷失后稱制元年(己酉,1249)建成真定府學。東平府學重建始于1251 年,竣工于1255 年,其時離金國滅亡已21 年。東平府學雖然不是世侯中復學最早的,但是建筑規模最大的,同時,地位也是最特別的。
新建的東平府學地位的特別之處第一個表現是:它既是州學,所謂“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馀六十人,在東序”是也,也是孔府家塾,所謂“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是也。新的東平府學在規模上一承金制。按《金史》卷五一《選舉志一》,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定制:東平府學定額是60 人,與大興府學、開封府學、平陽府學、真定府學的人數相同,均屬金代人數最多的學校。為什么孔氏家塾也在這里舉辦呢?自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南遷汴京,成吉思汗趁金國上下混亂,大掠河北、河南、山東,曲阜孔廟(祖庭)也在這次戰亂中被焚毀⑥。金國滅亡時,衍圣公孔元措(孔子五十一代孫)被俘,安置在博州、冠縣,后被嚴實接到東平。衍圣公孔元措是孔氏正脈所在,正統儒家的象征,嚴實禮遇孔元措,實際上是執士大夫之牛耳。在孔氏家族隨孔元措駐足東平的時候,嚴實為他們特地建家塾,自在情理之中。
東平府學地位特別之處的第二個表現是:東平府學暫時扮演了太常寺的功能。衍圣公孔元措在金國做過太常卿,他于元太宗十年(1238)上疏,請朝廷派員收錄金國散失的太常禮冊、樂器、樂官和樂工。朝廷同意由孔元措出面走訪收錄。但是,當時的蒙古國還在四處打仗,大本營又遠在漠北,且蒙古上層不熟悉、不理解這些東西。于是,朝廷在此年十一月詔管民官,“(徙亡金知禮樂舊人并其家眷赴東平,令元措領之于本路,稅課所給)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并其家屬赴東平,令元措領之,于本路稅課所給其食”[5]卷六十八,1691。最終孔元措訪得金朝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翟剛等92 人。這些金國的太常禮冊、樂器、樂官和樂工來到東平后,都被安置在了東平府學中。“備鐘磬之縣(懸),歲時閱習”,東平府學有了太常寺的味道。元憲宗二年(1252)三月五日,朝廷命東平萬戶嚴忠濟立局,制冠冕、法服、鐘磬、簡虞、儀物肄習⑦。據說習成之后,諸樂工被召至日月山試奏于皇帝面前,并獲準用于祭祀上天。可見,這里既是前朝亡國禮樂的集中地,又是元朝禮樂的重要發源地。元好問說“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其原因在此。
嚴實及其繼位者嚴忠濟控制和保護下的東平,因此成了當時的文化高地。隨著大批文人和藝人流落東平,此前的宋雜劇、話本、平話、澤州諸宮調等藝術形式在這里匯合,戲劇一度繁榮。一起在東平避難的元好問、商挺、杜仁杰等,都是知名元曲作家。杜仁杰的《莊家不識勾欄》寫東平戲劇表演:“前截兒院本《調風月》,背后幺末敷演劉耍和。”“院本”一般認為是金代戲劇的稱謂,“幺末”即宋雜劇的別稱,以插科打諢為特色。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的女主角王金榜是東平散樂。可見東平所產戲劇人才比較受南宋后期、元代前期人們的喜愛和肯定,故以之為招牌。水滸戲是當時戲劇創作的熱門題材,而水滸劇中好漢們棲身的梁山和梁山泊,就在東平府城的西面。高文秀、康進之都是當時寫李逵戲的高手,孫楷第《元曲家考略》“康進之”條曾詳考東平府學祭酒康曄(字顯之),推測康進之與康顯之為兄弟行,皆寓東平府者。
據元好問《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君神道之碑》記載:“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元好問此記中提到的東平府學諸人,如教官梁棟、王磐、祭酒康曄、提舉宋子貞、禮樂孔元措、名士張澄,他們是東平府學派的第一代人物。這些人只是嚴實父子招徠的學者群體之冰山一角,其他同時人還有李世弼、李昶(李世弼子)、張特立、劉肅、徐世隆、張昉、商挺、杜仁杰等。東平府學新造后,培養的學生很多成了元世祖朝的重要官員,閻復《鄉賢祠記》記載了康曄的9個優秀學生:“自復齋徐公接武始,國子祭酒、集賢學士周砥,翰林學士承旨李謙⑧,江西行省參政翰林學士承旨徐琰、翰林供奉淮東提刑按察使孟淇,禮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張孔孫,集賢學士劉賡,國子司業楊桓,吏部尚書、翰林直學士夾谷之奇,揚歷館陶者十余人,司風憲、握郡符及不求聞達者尚眾。”(《全元文》卷二九五))元好問在東平府學重建后,參加該校第一批人才的選拔,親選閻復⑨、李謙、徐琰、孟祺四人[5]卷一六〇,3772。以上諸人外,東平府學培養的著名學生還有申屠致遠、李之紹、吳衍、馬紹、王構、曹伯啟等(《宋元學案》“泰山學案”)。
東平府學培養了元朝第一批重要的文人官僚。虞集說:“方是時,士大夫各趨所依以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于東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啟祚,政事文學之科,彬彬然為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胡祇遹《泗水縣重建廟學記》中說:“即今(朝廷)內外要職之人才材,半出于東原(即東平)府學之生徒,豈非明效之大驗歟?”袁桷《送程士安官南康序》中說:“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以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十居六七。”(《清容居士集》卷二四)東平府學人才濟濟,培養的政事文學之才也占據元初半壁江山,很自然地會形成文化學術上的“東平學派”。日本學者安部健夫認為元初存在兩大知識分子集團:一是由耶律楚材、宋子貞興起,元好問、康曄、王鶚、王磐、李昶、李楨、閻復、李謙、孟祺、張孔孫、李之紹、曹伯啟等繼之,下之李治(冶)、徒單公履的一派;另一是由楊惟中、劉秉忠、趙復興起,竇默、姚樞、許衡、楊恭懿、王恂等繼之,下及耶律有尚、姚燧、劉因在內的一派。前一派叫作“文章派”,后一派叫作“德行派”。重浮華、喜宴游是文章派人們的共同特征,他們是華美的雜劇的愛好者,是優伶歌妓的捧場者,他們自己執筆寫一折雜劇也不為難⑩。顯然,文章派的絕大部分成員都是來自東平府的學者,而該文人團體重文藝的文化趣味,與元好問等人的“中州文派”“中州文氣”的文化自覺分不開,即與他們“以文存史”的文化理念分不開。至元年間(1264—1294),在大都為官的東平府學師生,形成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文人群體,他們的詩文唱和是此時大都文學活動最主要的內容之一?。當然,東平文人大量進入中央,也與元好問、張德輝等人的居間活動有一定的間接關系。
同時,東平府學培養的人才,還源源不斷地輻射到周邊,對北方儒學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南宋滅亡后,南北統一,但北人地位高于南人,南方新政權的主持者多由北方而來,如南方州縣的很多地方官就出自東平府學。劉岳申《吉水州修學記》載:“吉水鄉校,自至元中縣令丞多東魯儒生,凡致美于廟學者,靡不畢用其致。改州以來,東平曹侯珣始筑修堤甃夷道,濟南程侯又遷亭于學外,凡曹侯不及為者,畢具之……于是延祐科舉十有二年矣,吉州之士貢于鄉、擢于禮部者,常倍于他州。”翻開元代學記,其中標明州縣令或學官出自東平者,時時見之。可見東平府學在當時的重要影響。
四
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巳。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教以徳,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诐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元好問《東平府新學記》)
元好問主張學校的教育內容分為三項:德、行、藝。三者的具體內容見之于《令旨重修真定府學記》中:“德則異之以知、仁、圣、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卹,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诐行,凡不足以輔世無所容也。”[1]卷三十二類似的意思,元好問還在《博州重修學記》中重申過:“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1]卷三十二《趙州學記》中亦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興廢。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1]卷三十二
元好問的教育觀,比當時及稍后的元代文人的教育觀要開放。一言而蔽之,元好問主張正統儒家教育,不認同“百姓日用不知”的理學教育和宗教異端教育。元好問在教育觀上與元代其他文人多主張理學教育明顯有差異。正統儒家教育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培養經邦緯國之人才,教材是六經;南宋以及元代的理學教育以培養醇儒為目標,即培養進退揖讓有度、心性道德日新的君子,教材是朱熹《四書集注》。元世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正是理學教育。
另外,全真道在元朝統治者的庇護下,在當時北方的民眾中迅速擴散。1223 年73 歲高齡的丘處機于興都庫什山成功拜見成吉思汗,全真教道士得到了敕免差役賦稅的特權。1224 年丘處機返抵燕京,住大天長觀(后改名長春宮),“由是玄風大振,四方翕然,道俗景仰,學徒云集”。玄風大振的另一個原因是宋金戰爭導致的流民大增。正如平陽士人段成己稱:“自天兵南牧,大夫士衣冠之子孫陷于奴虜者,不知其幾千百人,一入于道,為之主者,皆莫之誰何,而道之教益重。既占道家之籍,租庸調舉不及其身,非有司所得拘,而道之教益盛。”?丘處機及其弟子們不失時機地大力發展全真教,大約經過三十余年的經營,全真道的宮觀、弟子遍布于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陜西、甘肅等廣大地區。《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稱:“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這就是元好問當時看到的社會現實——戰亂漫延和異端突起。
這樣的現實情況帶來了元好問無法忍受的兩種文化墮落:殺身之學橫行,異端雜學泛濫。什么是殺身之學?元好問在這篇學記文中有詳細的羅列:
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縱惡若崩。時則為揣摩、為捭闔、為鉤距、為牙角、為城府、為穽獲、為溪壑、為龍斷、為捷徑、為貪墨、為蓋蕆、為較固、為干沒、為面謾、為力詆、為貶駁、為譏彈、為姍笑、為陵轢、為瘢癜、為睚眥、為構作、為操縱、為麾斥、為劫制、為把持、為絞訐、為妾婦妬、為形聲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髙亢、為湛靜、為張互、為結納、為勢交、為死黨、為嚢槖、為淵藪、為陽擠、為陰害、為竊發、為公行、為毒螫、為蠱惑、為狐媚、為狙詐、為鬼幽、為怪魁、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巳,合謾疾而為圣癲,敢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怨仇薫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
亂世投機主義大行其道,仁義禮忠信蕩然無存,人的行為近乎禽獸,凡此種種行徑,元好問皆斥之為踐行“殺身之學”者。至于異端雜學泛濫的表現,元好問在本文中也有列舉:
今夫緩歩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后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縳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
如果說,殺身之學是儒家思想明面的敵人,那么,異端雜學就是儒家思想暗面的敵人,對讀書人更有欺騙性,比如主張儒釋道三教全流的全真教和標榜做君子的理學(假道學)。全真教的危害性比較好理解,但是道學家們的危害性比較難發現。其實后者的危害性更烈,是一種溫水煮青蛙般的慢性自殺。“緩歩闊視,以儒自名”者皆假道學也。元好問痛心疾首地指出:“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真正的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人才是這樣的:道德上以天下人民的福祉為己任的責任感;行為上是踐行知行合一的原則;能力上是具有詩、書、禮、射、御、數等多種技能。元好問此處還有暗示批評理學的意味,他在記文中接著怒斥道:“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巳乎!”當下這些小人所談論的主敬主誠的《中庸》,就像魏晉時期的《周易》多參虛無主義、崇寧大觀時期的《周禮》充斥假古董一樣,其后果就是破家亡國,不僅僅是殺一身而已。
面對金亡以后殺身之學橫行、異端雜學泛濫的社會現實,元好問奮身而起,積極游說地方世侯禮遇士人,興辦學校,推行儒家文化。據當時人的記載,元好問受多處世侯之禮遇:在冠氏,他與楊奐、商挺受到嚴實部下趙天錫的優待;在東平,他受到嚴實父子優待;在保定,他與王鶚、郝經一起聚于張柔門下;在真定,他與王若虛、李治、白華等投史天澤門下。其實,他周旋各地,曳裾世侯之門,既不是為了跑官要官,也不是蹭吃蹭喝,他這樣做的目的,就是堅持他曾低聲下氣地給耶律楚材寫信的初心:保護文化人,保存儒家文化。清人凌廷堪說: “(元好問)所以奔走間關,終身不受升斗之祿,不過欲以此身存百年之掌故而已。”“不受升斗之祿”是矣,但以身保存百年掌故不必要奔走侯門,而推廣儒家文化這件大事則非得如此不可。經過多年努力經營,1252 年元好問與張德輝覲見了忽必烈,他們開導皇帝要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擁立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使之免除儒戶兵賦。這大概是元好問在本學記文中盼望的發揚儒家文化的最好結局吧。
五
元好問《東平府新學記》一文是金國滅亡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世侯的保護下逐漸恢復的時代大背景下寫就的。在他的文化理念中,“金源文化幾及漢唐”,金國文化是漢唐(北)宋中原儒家文化的正統繼承者。因此,他在文章開篇即詳細介紹了東平府學的歷史,意在表明唐宋金三朝文化的一脈相承,并特別提出:尊師重道的風俗就是國家之元氣,而這元氣是由學校培養的(“教則學政而已矣”)。這是他在這篇學記中表達出來的對學校作用的基本定位。
新建的東平府學其地位特別,它既是州學,也是孔府家塾,同時兼具元朝禮樂制度的培訓機構的角色。元好問在本學記中提到了東平府學在培養人才方面的成就,但是他沒有想到,這些成就的影響力遠超他的設想:東平府學培養了元朝第一批重要的文人官僚,促進了東平學派的形成,帶來了元代戲劇文學的第一次繁榮,元朝文學創作的第一波高潮也是由在京東平學生們帶起的。如果元好問活得更久一點,看到東平府學的學生們在元朝至元年間(1264—1294)大放異彩,他的感慨會更深,他所殷憂的殺身之學的橫行和異端雜學的泛濫,畢竟沒有蓋過儒學正道的成長。
這篇《東平府新學記》符合一般學記文的寫作法,前半敘事,后半議論。但該文體制宏大,篇幅上超過他幾年前創作的另一篇重要的學記文《令旨重修真定府廟學記》。《東平府新學記》的敘事要旨和議論中心都在《令旨重修真定府廟學記》一文的基礎上有所發展。該文的敘事除了敘述建學經過之外,還側重敘述了東平府學的歷史傳承和風俗之美,則是其他學記文少有者。這大概與他經歷了喪國和戰亂有關。可議之處在于:敘建學之事中攬入“十一代孫衍圣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一段較為突兀,中斷了敘建學之事的完整性。后半的議論大段文字羅列殺身之學與異端雜學的種種表現,深刻體現了元好問的憂世之心。總之,這是一篇體現元好問文化立場的重要文章,值得認真研究。
注釋:
① 王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秋澗先生大全集》卷48,第19頁,《四部叢刊初編》本,第226冊。
② 李俊民《(澤州)重修廟學記》提到了元太宗十年(1238)的“戊戌選試”(科舉初試),澤州士人在段直的勸喻下積極響應,初試入選者一百二十二人(全國四千零三十人)。
③ 宋 劉摯《鄆州賜書閣記》,《忠肅集》卷九(《四庫全書》第109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56頁)。
④ 江湄《“國亡史作”新解——史學史與情感史視野下的元好問碑傳文》,《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5期。
⑤ 這兩個年代據榮國慶《劉因〈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考釋》一文。李俊民有《(澤州)重修廟學記》,不署作文年月。按,劉因《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載段直任萬戶后“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段直任澤州萬戶是1234年左右,“不五六年”就是1238年(古人記憶不一定精確,一年誤差可通)。
⑥ 孔元措《手植檜刻圣賢像記》,《孔氏祖庭廣記引》。
⑦ 《(乾隆)東平州志》卷十九王惟賢《重新雅樂記》。見郭云策《歷代東平州志集校》,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頁。
⑧ 按,此處的李謙,即下文元好問挑選的四個優秀學生之一(1255年),與當時真定府學的教官李謙不是同一個人。后者見元好問《令旨重修真定府廟學記》(己酉年作,1249。《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十二)。
⑨ 《元史》卷一六○《閻復傳》:“弱冠入東平學,師事名儒康曄(顯之)。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迎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復為首。”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772頁。
⑩ 安部健夫著、索介然譯《元代的知識分子和科舉》,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五卷,中華書局,1993年。
? 葉愛欣《元代東平府學文化活動考論》,《平頂山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第50頁。
? 段成己《創修樓(棲)云觀記》,《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