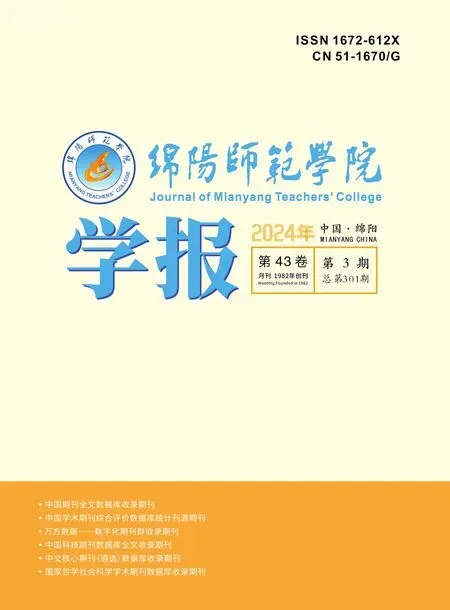論中國當代生態詩中的自然生態書寫
孔曉悅
(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青島 266071)
隨著現代化和工業化的飛速發展,人類在享受越來越方便、快捷的生活的同時也面臨重重危機。人類對自然界看似取得了節節勝利,但是危機早就潛伏在這些勝利背后。早在工業革命時代,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指出:“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78兩位哲學家在工業社會早期就以其前瞻性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生態詩的創作源于生態危機,在人與自然關系日益緊張的今天,中國當代詩壇出現了一批生態詩人,他們用生態意識去書寫自然,在詩歌中重新構建人類與自然界的關系,不再從人類中心主義的視角去看待自然,而是號召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體現了中國當代詩人的社會責任感。隨著生態危機的日益深入,對生態詩的研究也越來越多,本文就在當代生態詩人創作的基礎上,論述中國當代生態詩歌中的自然生態書寫。
一、復魅:書寫神性自然
遠古時期,人們對自然頗為依賴,因此人類尊重自然,甚至崇拜自然,把天地稱為“皇天后土”,部落首領更是宣稱自己“受命于天”,往往以天降異象作為鞏固自己統治的手段。部落中的圖騰也多為自然物,人與自然的關系非常密切,這是中國古代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自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成為萬物之靈長,人類中心主義思想面世,人與自然的關系發生巨大變化。人類從敬畏自然走向駕馭自然,科學思想統治了人類的思維,天地與自然萬物的神秘性不復存在。這種理性思維逐漸統治社會的思想軌跡被馬克斯·韋伯稱為“世界的祛魅”。祛魅在幫助人類的物質文化獲得飛速進展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帶來了許多危機。生態危機正是祛魅思想帶來的危機中的一種。在祛魅思想的影響下,自然不再作為可敬畏的存在,而是成為了被人類利用的工具,人類與自然的聯系減弱了。
面對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人提出了“復魅”,認為“復魅成為祛魅種種病癥的療救力量”[2]。當然,復魅并不是要求人類拋棄科學回到蒙昧的原始社會,也不是要求人類重新信仰天地鬼神,而是提倡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重新整合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從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待自然,而是把自然放到與人類血脈相通的位置,尋找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平衡點。這種對自然生態的復魅,體現在詩歌創作中,就是對自然生態的神性書寫。
生態學家眼中的自然是宇宙運行、地殼運動、生物進化等一系列有科學依據的行為導致的結果,但在生態詩人眼中,無論是自然地理還是植物、動物,都有其神性所在。在詩人們筆下,山川河湖等自然地貌都成為可被崇拜之物。如于堅,作為中國生態詩歌的先行人,他在許多詩中都賦予了自然地貌以神性。在《河流》中:“但你走到我故鄉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會聽見人們談論這些河/就像談到他們的上帝。”[3]11河流在中國傳統的認知里本來就有母親的含義。古代人逐水而居,有水才能農耕,才能生存,但是現代社會隨著技術的發展,人們不再依賴水源選擇居住地,河流在人們心中的神圣性逐漸降低,隨之而來的是人類對河流的瘋狂開采和利用。但在《河流》中,河流仿佛回歸了工業社會之前的狀態,河流的意義不再被現代社會詮釋。大河潛藏在高山之間,“有些地帶永遠沒有人會知道”[3]10,充滿神秘性。人類對河流重回崇拜,將之奉為“上帝”。山本是地殼擠壓后產生的自然地貌,但在于堅筆下,高山也具有了強大的力量,并且能賦予人力量。在《高山》中,他對山進行了神性書寫:“在高山中人必需誠實/人覺得他是在英雄們面前走過/他不講話/他怕失去力量。”[3]12盡管高山只是自然地貌,但是于堅將其比作英雄。它的高大會使人不由自主地沉靜下來,以敬畏和誠實之心對待高山,而這也正是詩人追求的生態倫理的價值訴求。再如華海的《天湖》:“這山頂天湖 赤腳穿過起伏的叢林/靠近它 怕弄臟它碧玉般的/肌膚 甚至 這樣的造訪/是否也構成了對神圣的褻瀆。”[4]5在詩人的筆下,天湖不僅僅是一種自然地貌,而且具有了一種自然神性。天湖是白鷺鳥的朝圣地,也正是因為白鷺鳥的獻祭,天湖才擁有如此沉靜、豐盈的靈魂。在這樣的天湖面前,人類也不自覺感到敬畏,甚至于收起了衣飾鞋履等不必要的身外之物,讓人赤著腳,以一種最原始的、與自然最親密的狀態與天湖接觸,表達人類對于天湖的敬畏、崇拜之情。
除自然地貌外,在生態詩人的詩中,動植物也充滿了神性。鷹是于堅作品中提到的比較多的一種動物。在他筆下,鷹是天空的領主,是高居于人類之上的:“呵 你這天之驕子/人類一想到你/就要仰起頭顱。”[5]210鷹的生存空間是高居于人類之上的,也是被人類仰望的。鷹對于人類而言,變成了某種誘惑和向往的化身。于堅以植物為主題的詩歌同樣含義深刻,在《蘋果的法則》中,他描寫了一個蘋果的一生:“一只蘋果 出生于云南南方/在太陽 泉水 和少女們的手中間長大/根據永恒的法則被種植 培育/它永恒地長成球體 充滿汁液/在紅色的光輝中熟睡/神的第一個水果/神的最后一個水果/當它被摘下 裝進籮筐/少女們再次陷入懷孕地期待與絕望中/她們和土地都無法預測/下一回 下一個秋天/墜落在籮筐中地果實/是否仍然來自 神賜。”[3]14所謂“永恒的法則”是指人類科技介入之前蘋果的正常生長過程:陽光、雨露、土壤、少女們的手,這樣生長出來的蘋果是健康的。自然的陽光雨露成了神的意志,蘋果成了神創造的水果,蘋果被于堅賦予了神性。而人類科技的運用已經改變了蘋果的正常生長軌跡,化肥、農藥的使用,種植環境的改變,人為的降水、光照的控制,少女們已經無法確定下次成熟的蘋果是否還是神賜。人類的意志已經影響了植物的生長軌跡,將自然的恩賜置之不顧。蘋果的自然生長軌跡使人感到神圣,對人類科技介入蘋果生長的懷疑又使人憂慮。作品隱含著于堅對人類濫用科技改變植物生長法則的聲討。與于堅相比,吉狄馬加筆下的植物未受現代科技的影響,仍然有著土地賦予的深沉與厚重。他在《苦蕎麥》中對“蕎麥”這一人類的糧食作物進行了真情歌頌:“只有通過你的祈禱/我們才能把祝愿之辭/送到神靈和先輩的身邊/蕎麥啊,你看不見的手臂/溫柔而修長,我們/渴望你的撫摸,我們歌唱你/就如同歌唱自己的母親一樣。”[6]51在吉狄馬加筆下,蕎麥吸收宇宙土地之精華,既是大地的容器,又是人與大地鏈接的媒介,借此傳達出人類對大地的敬畏。同時,蕎麥作為糧食作物,她對人的作用如同母親的乳汁對嬰孩的作用,所以蕎麥就像人類的母親一樣值得被人類歌頌。這首詩用第二人稱來完成,以一種想象的方式將苦蕎麥擬人化,將之與“母親”比擬。在這種擬人化的書寫中,更見苦蕎麥的神性之光,更顯詩人對于這一大地容器、人類之母的敬畏。
總之,在生態詩中,不論是自然地貌還是植物、動物,都被賦予了神性。這種神性,一是來源于自然萬物本身的雄偉;二是來自于其背后所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對人類的啟發。在科技手段越來越發達的今天,自然生態似乎越來越成為純粹客觀之物。在這種情況下,將自然萬物賦魅,對其進行一種神性書寫,有助于人類保持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有利于人與自然達成一種和諧共生的狀態。這既是對中國古代自然崇拜思想的某種復歸,也是人類找到的一條拯救生態危機的新路。
二、回歸:書寫詩性自然
詩性與神性有著密切的關系,二者都強調一個“感”字。神性感動的是天地,目的是讓人類心生敬畏;而詩性感動的是人心,它本來就是詩人在審美的心理訴求下展開的對于自然生態的描寫,它依賴于詩人豐富的精神世界,感動著讀者的心靈。詩歌是心靈的產物,詩人在感知自然時,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給各種自然現象披上神秘的面紗,表現在文本中,就不再是一個對自然現象純粹理性客觀的書寫,而是展現出一個富有詩性的情感世界。
詩人的心是纖細敏感的,面對現代社會的各種危機,許多詩人不愿直面,便將純凈的自然作為自己的精神家園。盧梭第一個打出了“遠離社會,回歸自然”的旗幟,以此反對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詩人們想要回歸的,是自然、田園、故鄉、廟宇這些和工業社會相反的元素。但是,人類已無法在現實中回歸,因為土地和人類早已改變。基于此,魯樞元先生提出了“回歸”的概念。回歸不是倒退,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詩人們可以在“回歸”中書寫詩性自然,尋找力量。
書寫詩性自然,首先體現為對生態自然的本真書寫,塑造澄澈明凈的理想生態境界。比如詩人華海,他的詩帶給人一種寧靜的氛圍,在這樣的寧靜中,帶來的是超脫于世俗的、對自然生態的審美。“如果你靜靜感受 也會傳染/一種醬紫色的情緒 如果/默默玄想 一只蝴蝶也會在血管/底部 掀起一場藍色風暴//在靜福山 用泉水洗目/任山風濯耳 讓蟲鳴清潔肌膚/你又走回兒時的童真 能與山雀嬉戲/與一只螞蟻演繹一條回家的路。”[7]19讀這首詩,仿佛跟隨華海回到了生命的童年時代,以最本真、最純凈之心看待世間萬物。這就是華海塑造的理想境界:擺脫物欲喧囂的社會,構建靜謐的、萬物和諧的生態世界。他的代表作《喊山》更是境界超脫:“山有時睡有時醒/醒的時候/想說話//山的聲音/灌進樵夫的血管/……花狐貍倏地閃過/山燦爛了一下/又黯了//許多聲音。”[4]4這是一首充滿靈性的小詩,山川草木、花鳥魚蟲皆成了華海詩歌的主體,而且一切都融合得那么完美,樵夫與山、樵夫與樵夫、花狐貍與山……一切都處于和諧的狀態,有種世外桃源之感。更為難得的是,詩人是真正地將自己融入了自然之中,回歸自然,視自己為自然的一員,所以才能有“花狐貍”這一境界超脫的神來之筆,才能有純粹的詩性自然之感。再如詩人韓作榮的《原始森林印象》:“可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森林內的潔凈/厚厚的死去的松針,褐紅的松針/以鐵銹般的顏色敷滿林地/蓬松卻并不柔軟/干凈得沒有一星灰塵,一絲雜蕪/只有蕨草從枯死的針葉中鉆出來/細弱,鮮綠而又輕盈。”[8]190詩人在高處俯瞰原始森林,給我們呈現出一幅理想化的原始森林圖景:浩瀚、潔凈、有生命力。整個世界仿佛回到了原始的生存狀態,森林里的一切都各得其所,死去的松針化為營養,鮮嫩新生的蕨草就從這些枯死的樹葉中汲取著生命的力量。森林生命的倫理融匯在這首小詩中,這也是一種天然的、不經世俗侵擾的理想生態境界。
除了對生態自然的本真書寫外,詩性自然還體現在對自然生態中本真人性的發掘。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環境不同,人的心緒不同,體現出的人性也就不同。長期生活在欲望都市,人的心境自然就會被都市社會的物質欲望浸染。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人的靈魂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響,比如于堅在《那人站在河岸》中重敘了傳統的河邊戀愛主題,但是環境的改變不可避免地作用于人。“那人沉默不語/他不愿對他的姑娘說/你像一堆泡沫/河上沒有海鷗/河上沒有白帆/他想起中學時代讀過的情詩/十九世紀的愛情也在這河上流過/河上有鴛鴦 天上有白云/生活之舟棲息在樹蔭下/那古老的愛情不知漂到海了沒有/那些情歌卻變得虛偽。”[3]21所以“那人”無法借物喻人,無法在河岸邊重拾古老的浪漫愛情,他所能做的,只有沉默。生態環境的惡化讓人的精神世界趨于沉默,而在對美好的自然生態的描寫中,對自然生態的回歸使人的本真人性得到發掘與拯救。華海的一些詩有中國古代田園詩的意境,他在詩歌中將自己置于一個遠離都市社會的鄉村環境中,在這樣一個自然環境中書寫健康本真的人性。比如他的《鄉居生活》:“鄉野寧靜的生活/不會讓人產生偏狹心理/一人獨處看看星空/三五成群談談桑麻/在凡夫俗子中間/也能自然地活出一種風度。”[4]77這首詩以新詩的體式繪出了唐人“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之詩酒田園風景圖。鄉村一直都是詩人想要回歸的遠方,古代厭惡官場的士人如此,今日厭惡都市文明的詩人也是如此。在華海的筆下,詩人在鄉村中找到了最本真的自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單純而友好,毫無偏狹;詩人找到了本真的生存狀態,在星空與凡夫俗子間找到了安置自身的位置。華海在對田園的回歸中找到了力量,在對生態自然的書寫中體現了生態之美與人性本真。鄉村生活幫助華海找到本真人性,而雷平陽想要回歸的是廟宇。在《建廟記》中,他描寫了一幅廟宇隱居的場面:“他在山中建了一座小廟/光頭,袈裟,一個人/興致勃勃地守著/功德箱很大,很沉,晚上/他就用它抵住廟門/酒多的時候,門外松濤虎狼奔突/他就摟著一尊泥菩薩/天人合一,睡得如癡如醉/沒有晨鐘暮鼓,也/無早課和靜修。”[9]90現代人在都市中產生的焦慮不安的心情就在這樣遠離俗世的廟宇中得到了治愈。在這樣的環境中,人放棄了虛偽的面具,裸露出自身的真實人性,以一種純粹的心靈去享受自然,在自然中修煉自己的本真人性。
總之,中國文人對自然的詩性書寫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雖然社會存在已經改變,人類已經無法回歸到工業社會之前人與自然“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中,但是面對日益喧囂的都市社會,不妨在“回歸”中尋找力量。不論是對生態自然的本真書寫,還是理想生態環境的塑造,抑或是本真自然中本真人性的發掘,都在表現詩性自然的同時,將詩人們的自然生態理想做了完整的呈現。詩人們以詩性的語言構筑詩性自然,為現代人洗滌塵世污濁、凈化內心、重返大自然提供了有力的范本。
三、共生:人與自然萬物的和諧相處
不論是對自然的神性書寫還是詩性書寫,最終都指向一個終點,那就是達到人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狀態。自然與人類應該是有機統一的,一方面人改變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作用于人。如果妄圖強行以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統治自然,最終危及的只會是人類自身。長期以來,人類以自然的主人自居,殊不知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關于人類與其他生命的關系,史懷澤在《敬畏自然》中提出了對道德的基本原則的闡釋,即“善是保存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的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10]7-8。尊重自然生命就是尊重我們自身,自然萬物與人類享有同等的道德地位。人類應當敬畏生命,學會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中國當代詩人在進行生態詩創作時,將動物、植物等多重元素融入詩歌中,描寫它們和諧共生的場面,體現著詩人們的生態良知和對構建和諧的自然生態的價值訴求。
在書寫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時,詩人們常從整體觀的角度出發,往往以一個地域為載體,書寫其中的植物、動物與人類的共生關系。如李少君的《鸚哥嶺》:“鸚哥嶺上,芭蕉蘭花是尋常小景/鳥啼蛙鳴儼然背景音樂/每天清晨,松鼠和野雞會來敲你的門/如鄰里間的相互訪問//作為一名熱衷田野調查的地方志工作者/我經常會查閱鸚哥嶺的花名冊/植物譜系在蒲桃、粗榧、黃花梨名單上/最近又增添了美秋葉海棠和展毛野牡丹/動物家族則在桃花水母、巨蜥、云豹之外/發現了樹蛙和綠翅短腳鴨。”[11]45短短一首詩中涉及了七種植物與九種動物,凸顯出了本地動植物數量之豐富,并且還發現了許多新物種,體現著當地生態系統的開放性和流動性,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設置了一個人類作為地方志工作者。這個工作者與當地的自然環境處于完全和諧的狀態。從立場上講,他熱衷于田野調查;從行為上講,他致力于調查當地的動植物物種,并給它們提供更多保護。在這首詩中,人類與自然不是對立的關系,人類成為自然的保護者和觀察者,二者關系分外和諧。華海更是強調生態詩歌創作中地域感建立的重要性,“我們只有回到殘存的自然中,回到原點,重新建立起與自然的關系——生生不息的生態整體關系”[7]3,才能探索一種對和諧未來的構想。多年以來,華海的創作依托于筆架山、靜福山,以這兩個地域為載體,探索現實中喪失的人與萬物詩意“棲居”的狀態。在《靜福山系列》中,他寫道:“你要聽懂靜福山的語言,就得坐到蛐蛐和鳥雀的/鳴叫聲中 伏在大葉榕樹根浮動的氣息場里//還得閉上嘴巴 靜下心來//這時候,一種聲音里有無數的聲音/千百種動植物的方言土語卻是一種語言/在一瞬間 仿佛已經歷所有的時間/甚至前世今生的生死循環。”[7]5很顯然,在靜福山這個生態場中,整個生態系統都是一個互相聯系的整體。自然作為一個整體具有不可被冒犯的尊嚴。人類在這個生態場中毫無特殊之處,只有將自己融入山野間的植物、動物之中,才能真正地被當地的生態系統所接納,實現一種和諧的相處狀態。李少君和華海都站在生態整體觀的立場,以一個地域為載體,書寫其中萬物共生的和諧關系,而于堅則將自己融入動物之中,讓自己以動物的姿態生存,以期實現自己和其他動物的和諧相處。他的《在馬群之間》將自己同化為馬,以馬的姿態生存:“就在這開闊的草地上/我擺動著四肢/不斷地調整動作 把身子舒展/我要完全進入一匹馬的狀態……我要跑得更加優美/我要在它們合攏過來之前/從它們中間穿過。”[3]81人類與馬的外在形態自然是不一樣的,但是在這首詩中,于堅通過對馬的觀察,將馬的一切細節銘記于心,所以能不斷調整自己,讓自己進入馬的狀態。這種狀態不僅僅是形體上的相似,更是氣場上與馬的融合。當人類從馬群中穿過而不致驚擾到馬的時候,人真正地和馬融為一體,人類和馬真正達到了一種和諧的狀態。
除整體描寫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的關系外,詩人們還經常在詩中為其它生靈立言,以一種寶貴的生命格調將生物本應該享有的生命權力回歸它們自身,體現著詩人們萬物平等的思想、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以及構建和諧共生的生態家園的美好理想。在這些詩歌中,詩人不再視自己為自然界的主人,而是以一種平等的姿態對待世間萬物。比如沈葦的《達浪坎的一頭小毛驢》,詩人采用一種對比的手法,小毛驢無憂無慮地生活在草原上,與人類保持著親近的關系,“達浪坎的一頭小毛驢/有一雙調皮孩子的大眼睛/在塵土中滾來滾去/制造一股股好玩的鄉村硝煙”[12]127,正當讀者沉浸在這個和諧的氛圍中時,作者卻筆鋒一轉,“在鐵掌釘住自由的驢蹄之前/太陽照在它/暖洋洋的肚皮上”[12]127,給整首詩溫暖的基調蒙上了一層陰暗的氣氛。兩相對比之下,以小毛驢的無憂無慮反襯出人類的自私和殘忍,表現出人類與動物本該有的平等關系,以及人類對動物的傷害造成的惡果,體現了沈葦為小毛驢立言的生態責任感。在《開都河畔與一只螞蟻共度一個下午》中,沈葦更是將目光投向了螞蟻這個人世間微不足道的動物。他寫出了這種動物的卑微,它的生與死于任何其他生物都無礙。然而,詩人卻給予了螞蟻足夠的尊重,他對螞蟻作為生態系統的一份子的身份給予正名,拋棄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姿態,以平等、尊重的態度對待螞蟻,與之交談。“我俯下身,與螞蟻交談/并且傾聽它對世界的看法/這是開都河畔我與螞蟻共度的一個下午/太陽向每個生靈公正地分配陽光。”[12]5詩人通過詩歌創作,反駁世俗社會中人類對于毛驢、螞蟻的看法,展現它們作為自然一份子與人類平等的姿態,體現出一種建設平等、公正生態家園的理想。同時,為其它生靈正名,也是為了喚醒人類的生態良知,促進人類與自然萬物的和諧共生。詩人張二棍更是把這種對萬物的關照延伸到植物上。在《俯身》中,他從容地俯身,看見自己和萬物之間的聯結,“俯下身來,和一支斷折的草莖交換名姓”,“俯下身來吧,在這磅礴暮色里,成全自己的小/與軟弱。讓一個人忘記自己吧,這一刻/把每個瞬間都當成遺址/像個去國的君王,無端淚涌”[13]121。俯下身來,詩人才能看到萬物,也才能看到自己的渺小與生命的短暫。這是一種瞬間的頓悟,也只有明白自己的渺小,才能看見萬物的偉大。在這種頓悟中,人類與草木形成了一種平等的和諧關系。
在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生命意識覺醒后,生態詩人們自覺地對世間萬物產生了憐惜之情,放棄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采取一種虔誠、卑微的態度與萬物平等相交,進而融入整個生態系統,將自己作為與動物、植物平等的一份子,這就是生態詩人生態智慧的體現。總之,不論是從整體觀的角度描寫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狀態,還是關照其他渺小的生物,發現其獨特價值,抑或是將自己置于其他生靈的立場,為其立言,表現對個體生命價值的尊重,都體現著詩人與其他自然生靈的親近、和諧,從而反映出詩人為構建和諧共生的理想生態自然而作的努力。
四、結語
中國當代生態詩歌中對于自然生態的書寫體現著詩人們強烈的生態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對自然生態的復魅傳達出“萬物有靈”的生態思想,引導人們重新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回歸自然的神性狀態;對自然的詩性書寫則從審美的角度帶領詩人“回歸”,在生態詩中體驗自然的本真,回歸人性的原初狀態;而對于人類和其他自然生靈和諧相處的共生狀態的書寫,則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美好愿景的呈現,其中不論是人類與動植物友好關系的呈現,還是人類代其他生靈立言,都體現著一種萬物平等的生態思想。生態詩是貼近現實的創作,中國當代生態詩歌創作對于喚醒民眾的生態意識,呼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警醒人類面對即將來臨的生態危機,都有極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