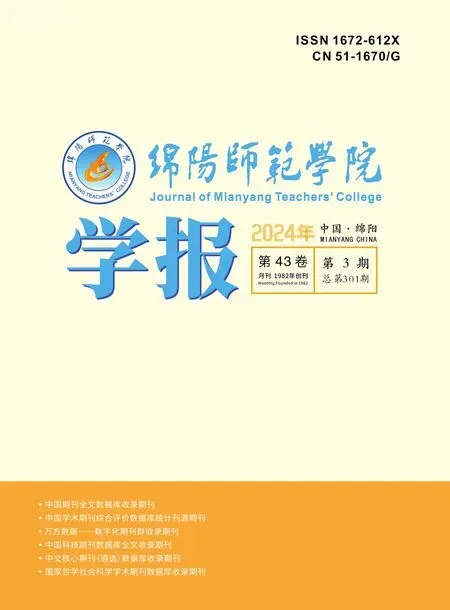“空間轉向”的本土化以及網絡文學空間敘事研究趨向
陳海燕
(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四川成都 611700)
一、引言
中國的敘事學研究在接受國外研究理論框架的同時,又對國外敘事學研究作出獨立思考,致力于在本土敘事資源和最新的敘事創作中尋求新路徑、探索新模式,使得敘事學逐漸成長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然而,長期以來國內學界關注的重點更多地聚焦在時間上,空間敘事并不受重視。這與中國傳統小說往往以時間順序為線索、以季節更替為框架來敘事有關。互聯網與數字媒介的興起帶來虛擬空間的崛起,使得空間研究成為文藝理論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而受到關注。其中,網絡文學作為當代中國“四大文化奇跡”之一,作為當代最具互聯網特征的文藝類型,其極具時代氣息的空間屬性和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屬性,引發了學界的關注與探討。
二、國外空間敘事理論的興起與發展
空間,作為一個與時間相提并論的概念,在人類漫長的認知過程中被長久忽視,直至在康德那里才獲得了在理論層面與時間并置的地位,從傳統意義上“沒有內容的容器”,演變成為“一種‘先驗的’范疇:一種組織感性現象的方式”,“一種主體的、內在的、觀念的、先驗的、本質的結構”[1]2。
空間敘事理論興起的背景與工業革命浪潮帶來的社會變革直接相關。馬克思認為時空壓縮與資本主義的崛起和擴張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伴隨著火箭技術與航天技術的發展,空間毫無疑問地‘流行’起來了。”[1]3本雅明借用保羅·瓦雷里的觀點提出:“二十年來,不論材料、空間還是時間都和往昔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應期待的是如此重要的新局面必會使一切藝術技術改頭換面,從而推動發明,甚至可以巧妙地改變藝術本身的觀念。”[2]283工業革命帶來時空壓縮的加速,引發了現代主義藝術對時空的高度敏感,表現為對空間的重視以及時空藝術的變革,新的空間概念源源不斷地被藝術家們生產、表現出來,全面推動了空間敘事研究的演進。
約瑟夫·弗蘭克的《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作為空間敘事學的濫觴,首度提出了“并置”的概念,他從語言的空間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間和讀者的心理空間三個層次來分析小說中的空間形式[3]。其后,時間的序列性和事件的因果律被大多數現代小說家拋棄,代之而起的是空間的同時性和事件的“偶合律”。從這種空間布局的大變革中,現代小說體現出超越故事敘述本身的象征意義和哲學意義。
備受矚目的“空間轉向”興起于20 世紀70 年代,亨利·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提出“社會空間”的概念,并將此分為“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間”[1]40。戴維?哈維繼承了馬克思的觀點,他的觀點被閻嘉總結為“在后現代小說中,分裂的空間戰勝了傳統小說敘事的連續性”,“粉碎了時間維度,把過去的體驗壓縮到現在之中”[4]。
福柯等人將空間視為社會關系的進一步開拓,將其與現代都市、現代文化聯系在一起,成為文化研究的重要論題。W.J.T.米切爾將文學中的空間形式劃分為物理空間、虛構世界、間序列和主題意義空間四個類型[5]。米克·巴爾(Mieke Bal)認為空間夾雜在聚焦與地點之間,區分為內部與外部空間,同時提出靜態空間和動態空間、否定空間和肯定空間等對立的范疇[6]134-143。魯思·羅儂則區分了“框架的空間”和“架構的空間”。加布里爾·佐倫(Gabriel Zoran)的《走向敘事空間理論》根據空間形式建構的空間理論模型,提出了敘事空間的三個層次,即地志的空間、時空體空間和文本的空間[7]。
三、國內空間敘事理論研究
“空間轉向”在國內的興起相對較晚,其理論的本土化甚至在當下也并未完全實現,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兩方面:一是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小說)對于時間的高度依賴;二是現當代小說對于鄉土敘事的單一關注,而鄉土本身長期靜態的穩定結構使其空間特征因缺少變化而乏善可陳。這兩個原因共同導致空間相關研究被忽視,國內敘事學一度僅將空間敘事視為時間敘事的一種變形。如趙毅衡曾經提出:“獨立地談被敘述事件的空間關系,是意義不大的事。”他認為加斯東?巴歇拉(Gaston Bacherlard)所謂“空間詩學”指的是文學作品的空間象征性,而象征問題與敘述學無關。“為什么這種關系是敘述的‘空間形式’呢?看來這些文論家只是對‘非時間性’這個否定性的范疇感到不安,一心想找出一個更可捉摸的名稱而已。”[8]215
龍迪勇對空間敘事學在國內的興起具有開創之功。自2003 年開始他發表系列論著,其中《論現代小說的空間敘事》分析了現代小說的空間敘事特征[9]。《空間形式:現代小說的敘事結構》[10]、《敘事學研究的空間轉向》[11]分別從不同視角切入空間敘事。《空間敘事學》對空間敘事理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12],論述了空間轉向以及空間敘事的重要意義,同時提出了現代小說的“套盒式、圓圈式、鏈條式、桔瓣式”等空間形式。其后他進一步拓展了空間理論,《空間敘事研究》[13]、《空間敘事學》[14]等陸續面世,對空間敘事轉向、理論發展脈絡、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開展了深入探討。方英出版了多部空間敘事相關論著,她在界定“敘事空間”概念的基礎上探索小說“空間敘事”的規律與特點,聚焦其模式特征、時空關系、意義言說等問題,試圖對小說空間敘事作出系統的理論探討[15]。她進一步指出,空間是由作者、讀者、文本共同建構的想象性、藝術化空間,既是表達層面的空間形式,又是內容層面的具象空間[16]。
此后,空間敘事逐漸被納入國內學界的關注視野,“空間轉向”理論逐漸“本土化”。程錫麟對空間敘事理論的主要論著進行了述評[17]。周和軍梳理了從弗蘭克、列斐伏爾再到蘇賈等學者的觀點,指出其在空間敘事理論發展上的重要意義[18]。余新明提出加強對空間敘事外圍問題如形態、視點、節奏等方面的研究[19]。陳德志對空間概念進行了辨析[20]。鄒波提出需要在傳統文學研究與經典敘事學等研究譜系中清理空間的身體性、當下性等內涵[21]。卓拉·加百利提出文本中具有地形層、時空層、文本層三個不同的空間建構等級[22]。王愛松翻譯了多琳·馬西的《保衛空間》,他提出需要借助空間的多樣性、“關系的空間”等[23]2。
國內空間敘事相關研究開始涉及戲劇、電影、電視、建筑等多個方面,空間敘事學在國內的關注已經逐漸從最開始的哲學范疇,發展至文學范疇,進而延伸、跨界到多個領域。
四、古典及現當代文學的空間敘事研究
20 世紀國內空間敘事學較多被運用于對古典小說的關注之中。浦安迪等國外學者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敘事學進行解讀,尤其是其頗具影響的《中國敘事學》[24],對《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多部古典名著展開敘事學分析,其中不乏對空間敘事的關注。張世君在《紅樓夢的空間敘事》[25]、《論〈紅樓夢〉的空間敘事藝術》[26]等系列論作中,對《紅樓夢》的空間敘事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此后不斷有學者探討中國古典小說的空間敘事特征,如李艷蕾的《〈三國演義〉的空間敘事》、解立紅的《〈水滸傳〉的空間敘事研究》等。
此后學界關注開始轉向現當代小說,運用空間敘事理論展開研究,如程錫麟的《論〈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空間敘事》、方英的《小說空間敘事論》、顏水生等的《新時期小說空間敘事研究》、王安的《空間敘事理論視閾中的納博科夫小說研究》、余新明的《〈吶喊〉〈彷徨〉的空間敘事》等。
五、網絡文學的空間敘事研究
作為數字信息革命的“長子”、最具創新精神和時代氣息的網絡應用類型,網絡文學以其海量的文本和強大的創新精神成為當代文藝最具代表性的典范。國內文藝創作的“空間轉向”首先集中爆發于網絡文學創作領域,在數字媒介與信息革命雙重加持的“故事變身”背景下,一場持續的“空間轉向”正在從網絡文學創作領域,蔓延到網絡文學閱讀、評價等產業全鏈條上,最終推動網絡文學研究的“空間轉向”。網絡文學的空間書寫日益成為國內敘事學理論關注的重點領域,研究網絡文學的“空間轉向”不僅成為必然趨勢,同樣還將成為切入當下時代理論話語的最好錨點,成為構建中國文藝批評話語的最佳突破口。總體來看,學界對網絡文學的空間屬性、空間特征多有論述,但直接關涉空間敘事的論著成果并不多見,較早涉及這一領域的主要有周冰、韓模永、許苗苗、黎楊全、禹建湘、單小曦、王金芝等。
周冰發表了系列網絡文學空間敘事的論文。他提出:“如果網絡小說太過于迎合‘超級注意力’,空間營構上缺少深度價值的支撐,那么空間敘事只會演變為以空間結構敘事的便利,走向空間式的情景消費,導致敘事的膚淺化、同質化,降低其審美性與意識形態效能。”[27]他進一步提出,空間充滿了敘事動能,是小說總體構架、人物刻畫、情節節奏等的關鍵手段,而地圖的展開則是各類空間的敘事演繹。“網絡小說的敘事是一種旅行敘事,以空間來結構情節,以旅行來串聯情節。”[28]而在如何敘述上,《網絡小說敘事的圖像化傾向》認為,它通過對位置、空間、場景的強調和安排,以空間繪圖的方式將空間時間化,在蒙太奇式的“換地圖”中完成對事件的結構,本質上是空間流動性生產中的位置經營[29]。韓模永提出:“在結構形態上,網絡文學大多走向一種帶有非線性、多向性和碎片化色彩的空間結構,即超文本和數據庫結構;在表現媒介上,視覺化圖像成為文學表現的形式符號,即便是純粹的文字文本,其文字表現的時間性被弱化,直觀性得以加強;在文學境界上,靈境和場景取代了傳統的意境,沉浸性和鏡頭感都大大增強,這也正是網絡圖像時代的一個必然轉向。”[30]他提出,國內網絡原創小說的空間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文本自身的空間性;另一方面是文本動態轉換的空間性[31]。同時指出:“在外在的審美特質上,文學則從時間藝術進入空間轉向。網絡文學場景書寫突出文學的視覺形象、創造并置的空間結構并建構移動的位置場所。”[32]
許苗苗梳理了現代空間研究的理論發展脈絡,對北京都市空間展開研究[33]。她在《網絡文學中的空間變遷與時代癥候》一文提出,網絡文學中的空間經歷了從現實城市空間向神話異世和跨次元、超維度空間的轉變。網絡文學中的空間濃縮了時代癥候,它如同一面多棱鏡,透過變形、離奇的碎片影像,實時反映出網絡社會的現實[34]。黎楊全在《中國網絡文學與虛擬生存體驗》中對“架空寫作”、“隨身”小說、重生小說、穿越小說等展開了深入詳盡的分析,強調網絡文學呈現了網絡新青年的數碼浪漫主義與個人奮斗體驗[35]。同時提出:“中國網絡文學從現代人與連線世界的日常互動,網絡的界面穿越、‘線上’與‘線下’世界的時空區分,以及虛擬性與交互性中獲得想象靈感,并隱喻性呈現出現代人與網絡的共生與伴隨關系、虛擬主體的間性、網絡生活的‘重置’體驗及其精神癥候。”[36]他強調:“在元宇宙中,與敘事時間的衰落相比,敘事空間的重要性表現了出來。用戶穿過空間的運動本身成為情節線索。”[37]
黎保榮開設了“網絡文學的空間敘事”的專欄,他認為:“有什么樣的空間類型,人物在空間里做什么,有什么樣的空間敘事手法。”[38]專欄中,四位作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網絡文學的虛擬、現實空間展開分析。陳紅旗分析了“云南蟲谷”這樣一個虛構空間所發生的種種奇詭事件以及其中的人物、故事[39];王少瑜關注《甄嬛傳》在獨特的后宮空間中所形成的非正義的詭謀文化[40];張麗鳳等剖析了“空間弱化與城市個體的浮夸與束縛”[41];陳宛頤關注《華胥引》在“沉溺于夢境”的虛構空間中的欲望表達與抒發[42]。王金芝在《網絡文學:媒介·文本和敘事》一書中專章論述“文本與空間”,借用弗吉利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討論女性網絡文學空間的意義和局限[43]。李星儒提出:“包括網絡劇在內的多媒介版本可通過對同一個文本的講述形成多層異構的互文空間,共同構造起復調式的故事世界。”[44]其中列舉了《魔道祖師》《司藤》《隱秘的角落》等網絡小說作為案例。耿文婷指出:“對‘單一物理空間’的突破,是中國網絡幻想文學的空間魅力所在。”[45]李志艷、鄒建軍從文學地理學的角度切入網絡文學研究,認為:“網絡文學生產機制中,文學文本封閉性的消解、讀者對文學生產的參與、文學生產的循環等問題都產生了系列新變,并在空間的角度上得以集中顯現。”[46]俞汶宜、單小曦等分析了《牧神記》獨特的“東方玄幻”世界中所運用的“蓮花地圖”“千層餅式歷史敘事”等空間結構[47]。胡影怡關注網絡玄幻小說中的空間建構,認為“玄幻小說構建了相當數量的虛擬空間,隨著主人公的活動,空間不斷位移,成為虛擬地圖上有意義的點,并且故事中的空間起著指向和導引的作用”[48]。李衛華對網絡玄幻小說的空間類型進行了詳細的區分,分為物質空間、社會空間和游戲空間三種類型,提出這些空間建構具有想象性、奇觀性和游戲性的特征[49]。同時他認為,網絡玄幻小說的奇幻地理景觀,正是福柯的“異托邦”,它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穩定結構,并對網絡時代的快節奏、偶然性與物質化生活提出了反思與質疑[50]。姜云峰提出網絡小說敘事是一種旅行敘事,通過旅行敘事中的移步換景和地圖轉換,推動情節的發展,實現空間的增量與故事的擴容[51]。杜麗娟認為網絡小說借互聯網建構起的空間景觀,既展現了網絡空間的無限延展性,又彰顯了網絡小說自身的自然客觀空間和精神主觀空間的多重復雜性[52]。王翌霖、易禮霜將“場域觀將空間及其力量”納入網絡文學的讀寫行為中,分析網絡文學邁進數字符號介入的“虛實交融疊加場域”所構建的網絡文學特有的自身認知空間[53]。
不少學者關注到網絡文學的空間特征,禹建湘提出,“空間轉向”作為網絡文學批評的新范式,批評的主體是“個人化的大眾批評”,批評的方法是“跨語境的文化批評”,批評價值觀是“開放性的多元批評”[54]。邵燕君借用福柯“異托邦”的理論,進一步分析了網絡文學的“幻想空間”[55]。王玉玊借鑒東浩紀“游戲性寫實主義”來分析網絡文學的游戲化特征,挖掘其中的“數據庫美學”傾向[56]。王金芝強調早期的網絡文學除了題材拓展,更為重要的是“開啟了中國文學網絡書寫的新篇章,這是相較于題材拓展更加重要的向虛擬空間的拓展”[57]。韓偉認為,超文本文學作為一種形式層面的空間狂歡,實現了文學空間的縱向拓展。類型文學作為一種總體性文學現象,實現了對文學空間的橫向拓展[58]。李雪、陳海燕提出:“游戲、愛情虛擬中的交往又反過來促進現實虛擬世界的發展,增加個體與社會空間相互滲透的可能性。”[59]這些論著涉及網絡文學的空間,但并未直接關涉空間敘事層面,可見網絡文學的空間敘事研究還具有較大探索空間,這也與國內網絡文學相關的學術研究遠滯后于產業發展的現狀不無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與中青年學者對于空間敘事的散點式關注形成對照的,是年輕學者對于網絡文學空間敘事的密集關注,多篇碩士學位論文涉及網絡文學的空間敘事,有的就直接以空間敘事作為切入點展開研究。肖綿的《空間轉向與文學流變——以賽博空間的文學研究為例》,分析了文藝的“靈韻”與膜拜價值、文藝的“祛魅”與展示價值、文藝的“復魅”與操控價值的理論思辨,表達了對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化反思[60]。李薇的《網絡小說敘事空間研究》,把網絡小說的敘事空間分為故事空間和話語空間。在網絡小說的故事空間層面,拋開空間本身的多角度和多層次性,根據時間和空間彼此依存的關系,從時間的角度將網絡小說的故事空間分為現實空間、歷史空間和未來空間[61]。段曉云的《網絡仙俠小說文學空間研究》提出仙俠小說的空間分為三個層面:網絡仙俠小說中文本所塑造的文學想象世界、想象空間之下所表征出來的現實象征空間、網絡仙俠小說的產生空間與閱讀消費空間[62]。胡珍平的《想象與真實:網絡玄幻小說〈詭秘之主〉的空間敘事研究》借鑒國內外的空間敘事理論,對《詭秘之主》的空間敘事進行了詳細解析[63]。蔣陽的《場域視角下創意人群-空間互動研究:基于中國網絡作家村的實證》以網絡作家村的空間為切入點,從線上空間與線下空間兩方面展示了網絡作家的社會空間、生存心態和空間實踐情況,以及場所空間的構建歷程、運行機制和空間作用[64]。農詩慧的《貓膩小說架空世界的建構》認為,貓膩的多部小說“采用多重空間場所轉換敘事,借空間要素表征人物形象序列、推動情節發展,弱化了傳統小說時間要素功用”[65]。謝敏的《中國新媒介文藝時空觀研究》認為,新媒介文藝內部出現了時空轉向,在時間上表現為線性時間被打破,空間上超脫文本空間走向了更加廣闊的技術空間、虛擬空間[66]。
六、網絡文學空間敘事相關研究發展趨向
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伴隨著數字化生存的無孔不入和虛擬現實的日益增強,空間與時間在此起彼伏之間演變為壓縮的“時空體”“時空結”,故事的場景越來越被定位于無限漫長的時間跨度或極其細微的時空變化之間。“穿越”“重生”“無限流”“時間循環”等表述在網絡文學/網絡文藝中的大行其道,使得傳統小說中時間的決定性坐標意義被日益淡化,“架空”“X 次元”“異大陸”等天馬行空的想象被信手鋪衍為日常景觀,蛻變為家常話語。這一切,表現的正是數字社區原生居民的互聯網生存體驗。
空間敘事作為伴隨著工業革命浪潮而興起的研究方法,同時作為本土化程度較高的文藝理論體系,最能體現網絡文學鮮明的“空間轉向”特征。可以說,空間敘事在網文創作和評價領域都具有獨一無二的價值意義。空間敘事理論在網絡文學研究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既應運而生,又乘勢而起,生逢其時又極為緊迫,值得學界高度關注。
然而,當下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對網絡小說空間敘事的研究,都還比較匱乏。表現為兩個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方向的關注不足。已有的成果關注到了網絡文學的虛擬空間、虛擬生存體驗,但大多聚焦于虛擬生存現象與本質問題的探討,并未涉及空間敘事層面。整個學界尚缺少運用空間敘事相關理論對網絡文學展開深入全面的研究。二是論述的力度、深度不足。網文是“青年寫,青年讀”的文藝典范,是年輕一代自我表達的精神樂土。新人不斷涌現,類型時時推陳出新。雖然網絡文學的研究仍然以中青年學者為主體,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網絡文學研究的“空間轉向”,年輕一代顯然走在了研究的前列。當下關涉空間敘事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碩士學位論文,思考廣度和深度雖還不夠成熟,但不乏可圈可點之處。雖然年輕人囿于學歷和閱歷,大多論著集中于網絡小說空間敘事的敘事模式、創作特點、審美意蘊、文學價值、個案分析等,討論文本內部的空間呈現、讀者的心理空間等層面,在空間建構方面,還缺乏較為系統、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在理論的創新上更缺少推進。但這種對于網絡文學創作新動態敏銳的把握能力,恐怕也是這些碩士研究生的導師們要向“后喻文化”學習的地方。
當下網絡文學“空間轉向”的研究現狀與發展趨向,基本契合其“青年”屬性,表明網生青年一代不僅在網絡文學閱讀和批評上,而且在理論研究的層面,都有望依仗其數字社區“原生居民”得天獨厚的身份優勢以及與生俱來的敏銳網感,做出遠超前人的重大成就。更重要的是,這一趨向昭示著無限可能的未來。被譽為“世界四大文化奇跡”之一的網絡文學,作為最具有創新精神、生命活力與中國特色的當代文學范式,如果能夠立足于本土化的文藝理論,全面開拓,深度挖掘,有望極大地推進“空間轉向”的進程以及敘事學理論的特色化與本土化,成為朝向實現中國文藝批評理論創新偉大歷史使命的又一次全面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