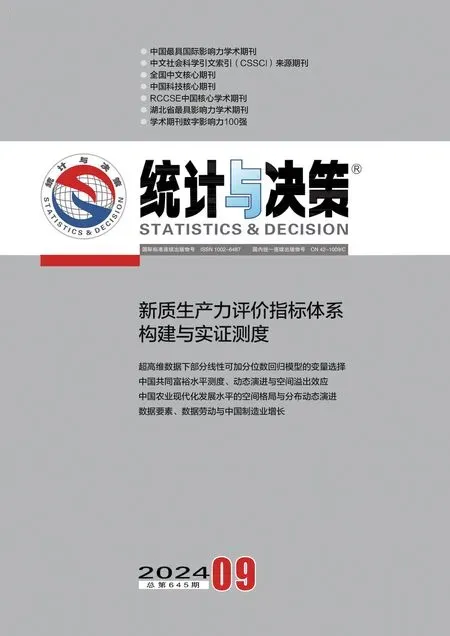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測度及時空演變研究
張思檬,吳東立
(沈陽農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沈陽 110000)
0 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1]。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當前,農業產業雙重脫嵌、農村優質資源流出、農民大量離鄉務工等現象頻發,區域間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問題日益嚴重[2]。目前學術界對共同富裕的研究面向城鄉中的所有群體,而較少對農村地區進行專門探討。已有研究主要從實證層面檢驗其影響因素,并多以收入差距等代表性指標衡量農村共同富裕水平,為破解農村共同富裕困局提供了經驗借鑒[3,4],但仍有拓展空間。第一,共同富裕評價內容有待厘清。現有研究更聚焦于“富裕度”,尤其是物質富裕。這不僅忽視了精神富裕,而且忽視了對“共同度”的衡量。共同富裕不僅要實現人民收入增長,還要讓改革發展成果公平地惠及不同群體[5]。第二,需更加系統、動態地考察共同富裕的演變,把握其時空演變趨勢等規律。第三,要解決數據的空間依賴性導致估計結果有偏的問題,就要觀察不同區域間發展態勢的空間集聚和分異特征,為解決區域間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現象提供思路。
基于此,本文以農村居民為研究對象,從“富裕”和“共享”兩大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值法測算共同富裕水平;利用核密度估計、空間可視化等方法量化分析其時空演化特征,并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分解差異來源;最后,基于地理學空間視角,揭示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空間非均衡性,采用收斂模型衡量其在時空演化中的穩健性。
1 研究設計
1.1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內涵
我國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一個重要維度,對其內涵的理解,既要包含共同富裕的一般要義,也要結合農村現狀融入獨特性[6,7]。因此,農村居民共同富裕也要包括“富裕”和“共享”兩個維度。隨著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農民物質生活基本富足,并開始產生精神文化上的追求。“富裕”仍是一般要義中的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共享”建立在“富裕”基礎上,是共享發展成果和美好生活。由于城鄉在產業發展、居住環境、公共保障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因此闡釋“共享”要基于農村的要素稟賦[8]。具體來說,產業興旺是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產業繁榮才能帶動農民致富,而產業發展離不開基礎設施。完備的基礎設施能夠保障要素流動,消除信息鴻溝,有助于農村與市場建立聯系。因此,要先確保基礎設施建設才能為農村居民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先行資本”。此外,公共服務是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2020年我國消除了絕對貧困,但部分脫貧村仍有“返貧”風險。因此,提供低保等公共服務,以社會保障兜底方式防止返貧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核心要素。最后,生態宜居是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撐。保護生態環境既能改善康養環境、提高生活幸福感,也能通過優美的生態吸引產業投資,在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的同時實現農民共同富裕。
1.2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引下,遵循《中國共同富裕研究報告(2022)》等政策導向,依據科學性、系統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則,本文從“富裕”和“共享”兩個方面,構建了包含5 個二級指標和24 個三級指標的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本文采用熵值法計算指標權重,并測度2012—2021年我國30個省份的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
1.3 非參數核密度估計
核密度估計是通過連續的密度曲線描述隨機變量的分布形態,對模型依賴度較低,具有穩健性[9]。隨機變量X的密度函數f(x)在點x的概率密度公式見式(1)。本文選擇高斯核函數來研究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動態演進趨勢,其表達式見式(2)。
其中,N代表樣本觀測值數量。Xi表示獨立同分布的觀測值,Xˉ為均值,? 代表帶寬。
1.4 Dagum基尼系數
將Dagum基尼系數分解為三個部分,分別是區域內差異貢獻(Gw)、區域間差異凈值貢獻(Gnb)和超變密度(Gt)[10]。式(3)為總基尼系數計算公式。本文將30 個省份按照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區域劃分。區域內差異貢獻(Gw)、區域間差異凈值貢獻(Gnb)和超變密度(Gt)的計算公式見式(4)、式(6)、式(7)。式(5)和式(8)分別表示j地區的基尼系數Gjj,以及j、? 地區之間的基尼系數Gj?。
1.5 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可得性,本文采用2012—2021 年我國30個省份(不含西藏和港澳臺)的平衡面板數據進行研究。本文主要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等,個別缺失數據經查詢相關省份的統計年鑒補全。
1.6 基本事實特征
圖1 展示了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2012—2021 年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變化趨勢。從時序特征來看,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保持波動增長態勢。從全國層面來看,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均值由2012 年的0.3094 上升至2021年的0.3927。從區域層面來看,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均值的變化趨勢與全國基本一致。考察期內,東部地區始終高于全國整體和中西部地區平均水平,由2012 年的0.4219 提高至2021 年的0.4976,漲幅為17.94%。中部地區在樣本期初期、中期的波動性較大,其變動態勢可分為三個階段,2012—2015 年保持“減增減”的“W”型走勢,2016—2018 年平穩增長,2018—2021 年在小幅下降后回升。西部地區農民共同富裕的改善程度最為顯著,均值由0.2197 增長至0.3215,漲幅達到46.34%。近年來,隨著我國農業支持政策的推進,西部地區獲得了更多的政策扶持,并作用于產業繁榮、農民增收、環境治理等方面,2017—2021年的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呈“U”型變化趨勢,表現出一定回落跡象,仍存在下行壓力。

圖1 2012—2021年全國及三大地區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
2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動態分布演進特征
2.1 核密度估計結果分析
下頁圖2為2012年、2015年、2018年和2021年的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核密度估計結果。從分布位置來看,核密度曲線的中心位置不斷右移,說明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隨時間推移持續增長。波峰高度大致呈先緩慢下降后快速回升的變化過程,表明地區間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離散程度在樣本期初期有所擴大,而中后期又趨于收斂;波峰寬度具有縮小趨勢,表明絕對差異有所下降。此外,核密度曲線具有明顯的右拖尾特征,但分布延展性呈逐步縮短趨勢,這意味著落后區域逐步向全國平均水平靠攏。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起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顯著上升,這與我國政府持續加大強農惠農政策的力度密不可分。2018 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產業發展、人居環境、治理模式等[11]。從波峰個數來看,2012—2018 年始終表現為“主峰+側峰”,說明在此期間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梯度效應,存在極化現象。但側峰的態勢在2018—2021 年由陡變緩,表明在考察期后段多極分化的現象有所好轉。

圖2 2012—2021年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核密度估計結果
2.2 時空演進特征分析
為更直觀地觀察時空演進特征,本文利用ArcGIS 軟件對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進行了可視化表達。考察期間,我國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演進大致可分為4個階段,因此繪制了2012年、2015年、2018年和2021年的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空間分布圖(見圖3)。由于自然斷點法在不同時段對目標變量的劃分標準不同,難以縱向比較,因此本文借鑒莫惠斌和王少劍(2021)[12]的做法,按照五分位數劃分為低(0~0.2424)、較低(0.2425~0.2736)、中等(0.2737~0.3302)、較 高(0.3303~0.4864)、高(0.4865~0.6787)五個等級。
由圖3可以看出,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等級向上躍升的省份數量逐漸增多。在樣本期初期呈“東高西低”發展態勢,高水平地區集中在東部地區的北京、上海、山東、江蘇和浙江。相比之下,青海、甘肅、寧夏、陜西等西部地區省份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偏低。2012—2015 年,發生等級躍遷的省份較多,其中內蒙古、四川、安徽由較低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重慶、湖南由較低邁入較高水平等級;湖北由中等水平邁入較高水平。但在此期間“中部塌陷”現象較為突出,較低水平的山西、河南、江西等中部地區省份被水平高的北京、天津、福建、廣東等省份環繞。2015—2018年,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躍升最為明顯。其中,陜西、青海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得到改善;河北、江西、山西邁入中等水平;內蒙古、四川躍升進入較高水平等級。2018—2021 年,西部地區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改善程度較為明顯,新疆、甘肅等省份的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有所提高。總體上,考察期內“東高西低”發展態勢有所改善,且“中部塌陷”現象得到緩解。另外,區域內差異不斷縮小,這與上文核密度估計的結果基本一致。
3 共同富裕區域差異及來源
3.1 區域空間差異及來源測算結果
本文利用Dagum 基尼系數及其分解方法揭示空間差異大小及其來源,結果見表2、表3。

表2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空間差異

表3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空間差異來源
3.2 全國及區域內差異分析
總體基尼系數均值為0.2062,表明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分布存在空間非均衡性。總體差異呈波動下降趨勢(見圖4),由2012 年的0.2195 下降至2021 年的0.1737,下降幅度為20.87%。而三大地區區域內基尼系數的演進不盡相同。東部地區基尼系數的演進過程與全國相近,樣本期初期,東部地區區域內空間差異性最大。但經多年發展,其基尼系數下降至與中部地區相近的水平。盡管基尼系數總體降幅達21.40%,但截至2021 年該地區基尼系數仍然最高。中部地區區域內基尼系數經歷先上升后波動下降的過程。該地區在2012 年的區域內基尼系數為0.1095,是三大地區區域內共同富裕水平空間非均衡性最小的地區。但其在2012—2015年持續上升至0.1539,隨后波動下降至2021 年的0.1363,空間非均衡性有擴大趨勢。西部地區的基尼系數自2013 年起持續走低,由2013年的0.1426 下降至2021 年的0.0674,降幅達52.73%。西部地區空間非均衡性的改善程度最為明顯。

圖4 全國及各地區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基尼系數演變趨勢
3.3 區域間差異分析
圖5 刻畫了區域間差異的演進過程。其中,東-西之間的差異最為顯著,均值達0.3012。時序特征顯示,二者間的空間非均衡性呈先發散后收斂態勢。東-中之間呈波動下降態勢,年均遞減率為0.23%,說明空間非均衡性有收斂態勢。最后,中-西之間的差異最小,均值僅為0.1570。自2017年開始,區域間差異普遍呈縮小趨勢。這可能與“十三五”規劃確立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有關。在此期間,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效果顯著,實現了農民收入翻番,并極大地改善了農村人居環境及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

圖5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區域間差異演變趨勢
3.4 差異來源及貢獻分析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空間差異來源貢獻的演變過程如下頁圖6所示。區域內差異、區域間差異以及超變密度的均值分別為0.0538、0.1349 和0.0222,貢獻率為25.53%、63.85%和10.63%。區域間差異構成了總體差異最重要的來源。由此可知,推動農村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是要關注并改善區域間發展落差。考察期內,區域內差異和超變密度值基本平穩。區域內差異在0.0500上下波動,超變密度基本環繞于0.0200附近。

圖6 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空間差異來源貢獻
4 收斂性分析
據前文分析可知,全國整體及不同區域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演進仍存在空間非均衡性。為進一步探究空間非均衡性在未來的演變中是趨于發散還是收斂,采用絕對β收斂模型分析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收斂性特征,計算公式見式(9)。其中,Vit和Vi0分別表示t時期和基期i省份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α和β為待估參數,?it為隨機誤差項。若β的估計值為負,則表明存在共同收斂趨勢。
根據Hausman 檢驗結果,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同時控制地區和時間固定效應。表4報告了檢驗結果。模型(1)至模型(4)估計結果均為負,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具體來說,全國層面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的發展態勢支持絕對β收斂機制,說明落后地區正以較快速度追趕先進地區。東、中、西地區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2811、-0.4944、-0.5474,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區域內空間差異性將隨時間推移而逐漸消失。收斂速度的排序依次為西部地區>中部地區>東部地區。總體上,各省份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將呈現趨同化演進趨勢。

表4 絕對β 收斂檢驗結果
5 結論
共同富裕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階段性目標,關鍵在于農村能否形成可持續的內生動力。在理解共同富裕一般涵義基礎上,本文圍繞我國農村現實狀況,闡釋了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內涵。并且從“富裕”和“共享”兩個維度構建了評價指標體系,利用我國2012—2021 年30 個省份的數據測度了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在此基礎上,利用核密度估計、空間可視化等方法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地區農民共同富裕水平的基本事實、動態演進特征、區域差異、收斂性特征進行分析。研究結論如下:(1)從動態演進特征來看,農村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考察期內,區域間差異逐漸縮小,但空間非均衡性仍然存在。(2)從差異程度及來源來看,全國整體及東西部地區的基尼系數均表現為波動下降趨勢,其中,西部地區降幅最大。區域間差異是造成空間差異最主要的來源。(3)從收斂特征來看,全國范圍內農村居民共同富裕的發展將呈現趨同化演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