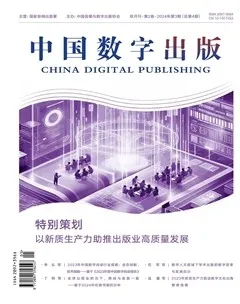數(shù)字人文視域下學術出版的數(shù)字變革與發(fā)展啟示
范軍 鐘準健
摘 要 數(shù)字人文是將數(shù)字化技術與傳統(tǒng)人文研究相結合的新型跨學科研究方式。它與學術出版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二者的發(fā)展目標具有一致性,并表現(xiàn)出相互促進的顯在關系。從數(shù)字人文看學術出版,數(shù)字人文的工具、平臺與理念加速了學術出版的三重變革:學術工具由輔助型向探索型轉變、學術出版平臺由獨立型向關系型轉化、學術傳播理念由集體向公眾改觀。在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融合發(fā)展中,面臨出版?zhèn)惱頎幾h、開放協(xié)同不足、技術應用困難、商業(yè)模式單一等瓶頸。基于數(shù)字人文給學術出版帶來的機遇與挑戰(zhàn),應正確審視人、出版與技術三位一體的關系、完善協(xié)同開放機制、加強出版隊伍建設、探索持續(xù)性商業(yè)模式,更好地實現(xiàn)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深度融合和創(chuàng)新發(fā)展。
關鍵詞 數(shù)字人文;學術出版;數(shù)字出版;融合發(fā)展
數(shù)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一般指向基于數(shù)字技術手段開展人文學科研究的研究方法論和交叉前沿領域,其概念前身為20世紀60年代所興起的“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作為舶來品的數(shù)字人文,至今仍處在快速發(fā)展的過程中,其內涵與范圍不斷地被定義、爭論與重構,因而當前國內外學界對于數(shù)字人文尚未形成統(tǒng)一定義。Gladney H M[1]認為數(shù)字人文是一種開放的、全球化、跨歷史、跨媒體的獲取知識或定義意義的研究方法。王曉光等[2]將數(shù)字人文視為數(shù)字化環(huán)境與數(shù)字化進程中對科研現(xiàn)存問題的回應與追問。哈佛大學中國史教授包弼德[3]認為,數(shù)字人文不僅是工具,還是在知識進步的過程中引起范式和理論變革的方法和技術體系。總的來說,當前學界對數(shù)字人文的定義存在方法說、領域說、活動說、實踐說等多種觀點[4]。我們認為,數(shù)字人文的核心內涵在于依托計算機、大數(shù)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shù)字技術與工具,將“計算”的量化優(yōu)勢與“人文”的質性研究相結合,在學術實踐中具有方法論、交叉學科、新型學術模式和組織形式等特質。
數(shù)字人文憑借其學術包容性和數(shù)字技術潛力,得以不斷延展研究邊界和擴大技術應用場景。與此同時,蔡迎春[5]指出,相比國外數(shù)字人文跨學科、多元化的蓬勃發(fā)展態(tài)勢,我國數(shù)字人文的研究范圍較為局限,研究成果集中于圖情領域,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理論和實踐成果仍有待深化。近年來,我國出版學界雖然也在逐漸關注數(shù)字人文議題,但相關研究成果較少,大多數(shù)出版機構也尚未以實際行動推進數(shù)字人文服務。在數(shù)字出版成為國家重要戰(zhàn)略的當下,學術出版作為連接數(shù)字人文內容編輯、價值評估以及成果傳播的重要范疇,數(shù)字人文研究為其帶來諸多理論與實踐層面的借鑒價值,學術出版的數(shù)字變革也將對數(shù)字人文產生重要影響。為此,本文以數(shù)字人文為視角,詮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闡述數(shù)字人文加速學術出版的數(shù)字變革實踐與發(fā)展前景,分析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在融合發(fā)展中所面臨的瓶頸與應對策略,以期為學術出版的數(shù)字化轉型提供啟示。
1 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
數(shù)字化語境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存在緊密的內在邏輯關聯(lián),這源于兩者使命的契合與內涵的交叉。從理論本身來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在實現(xiàn)知識創(chuàng)新與傳播的發(fā)展目標上具有一致性。從實踐過程來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具有顯在的互促關系,前者為后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視野,后者則為前者創(chuàng)造了重要的發(fā)展環(huán)境。
1.1 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發(fā)展目標的一致性
進入數(shù)字時代以來,以移動互聯(lián)、大數(shù)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為代表的數(shù)字技術層出不窮,數(shù)字技術既重塑了社會生態(tài),也賦能了學術研究的數(shù)字化轉型。數(shù)字人文是在此背景下所興起的交叉研究領域,數(shù)字人文通過數(shù)字化文獻資料、引入先進計算分析技術、構建數(shù)據大模型和研制可視化工具來促進與更新人文知識的表達、交流與評價,力圖推動印刷知識生產體系向數(shù)字知識生產體系進行轉變。與此同時,數(shù)字技術也不斷融入與重塑出版業(yè)態(tài),傳統(tǒng)學術出版的組織模式和流程環(huán)節(jié)不斷升級優(yōu)化,朝著數(shù)字學術出版的方向蓬勃發(fā)展。不過,無論數(shù)字人文與數(shù)字出版在發(fā)展過程中的技術樣態(tài)如何迭代,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本質仍未發(fā)生異變。因為數(shù)字人文利用數(shù)字技術與方法研究人文學科的最終目的是實現(xiàn)知識創(chuàng)新與服務,而學術出版的使命同樣是促進知識表達、輔助知識發(fā)現(xiàn)、進行知識傳播與實現(xiàn)科學交流,二者同樣依托數(shù)字技術的發(fā)展,追求人類知識的進步。最新的學科評議組也指出,數(shù)字人文與出版管理具有相同的學科使命和共同的理論基礎[6]。以古籍出版為例,近年來各出版機構著力推動數(shù)字古籍的出版和古籍數(shù)據庫的構建,與此同時,數(shù)字人文學者也對歷史檔案文獻進行了大量的數(shù)字創(chuàng)新出版工作。如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時光機項目[7]編制出了一本長達586頁的電子書,其以年份為軸,為中世紀以來的杜布羅尼克城市史建立了顆粒化與可視化的事件網、人物關系網和地圖網。以此來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二者在方法、內容與目標上都體現(xiàn)了交叉契合或者說一體兩面的特質。
1.2 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互促關系
從研究實踐來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之間有著顯在的互促關系,具體表現(xiàn)為兩方面。一方面,數(shù)字人文可為學術出版研究提供新技術與新方法。數(shù)字人文學者在跨學科實踐中,通過應用X射線斷層掃描檔案技術、手寫文字識別、索引驅動、分布式存儲、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數(shù)字孿生等先進技術與方法,幫助研究者、學術平臺和出版機構實現(xiàn)了知識關聯(lián)、文本分析與數(shù)據可視化的優(yōu)化,克服了傳統(tǒng)文獻數(shù)字化在數(shù)據收集、掃描識讀、內容關聯(lián)、分布存儲、開發(fā)利用等方面的不足。數(shù)字人文所帶來的技術與方法,引發(fā)了學術出版機構的關注與重視,進而豐富與更新了學術出版的問題域和理論庫,推進了學術出版機構在工具研發(fā)、方法創(chuàng)新、資源體系升級、優(yōu)質服務打造等方面的新發(fā)展。另一方面,學術出版的數(shù)字化有助于為數(shù)字人文創(chuàng)造良好的發(fā)展環(huán)境。數(shù)字人文的一大要求是要通過數(shù)字出版物對數(shù)據分析及結果進行多媒體展示[8],目前數(shù)字人文的發(fā)展正受制于項目協(xié)作、同行評審、成果出版等方面的問題,這要求以滿足學術需求為核心的學術出版需要對數(shù)字人文的內容生產、科學評價、知識產權、開放獲取等環(huán)節(jié)提供專門的數(shù)字出版服務,從而為新興的數(shù)字人文創(chuàng)造更加有利的發(fā)展環(huán)境。近年來,國外的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布朗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等高校出版機構已經著手為數(shù)字人文項目提供詳盡的出版服務,并推出了Enchanting the Desert、The Chinese Deathscape等多部受學術界與出版界好評的數(shù)字著作,而國內的出版機構尚少開展這方面的業(yè)務,這表明面向數(shù)字人文的學術出版仍有廣闊的開拓空間。
2 數(shù)字人文加速學術出版數(shù)字變革的三重維度
數(shù)字人文隨著技術的迭代不斷改寫自己的邊界和功能,數(shù)字人文研究從最初的“技術服務于人”,逐步走向采用數(shù)字工具、數(shù)字技術與數(shù)字媒介來塑造、改變知識的生產和傳播[9]。立足學術出版的微觀層面,數(shù)字人文全方位嵌入學術出版的各要素環(huán)節(jié),使學術出版的知識服務表現(xiàn)出跨學科工作、跨機構協(xié)同、知識生產智能化、人文數(shù)據開放公益化等新特點,推動學術工具由輔助型向探索型進行轉變,學術出版平臺由獨立型向關聯(lián)型發(fā)生轉化,學術傳播理念由集體向公眾產生改觀。
2.1 工具轉變:由輔助向探索的身份轉換
回顧數(shù)字人文的發(fā)展歷程,原先基于簡單計算分析的“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通過不斷將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云計算等先進數(shù)字技術應用于人文研究,使數(shù)字人文的研究邊界逐漸擴大至文化遺產、文學、歷史、藝術等范疇,從某種意義來說,數(shù)字技術的迭代為學術內容的發(fā)現(xiàn)、重組、生產等環(huán)節(jié)的創(chuàng)新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機,在此過程中,更是推動了數(shù)字工具在學術研究與學術出版中由輔助型向探索型的身份轉換。
數(shù)字人文要實現(xiàn)的是對海量文獻的充分掌握和便易分析。對人文研究者和出版編校者而言,面對數(shù)據的指數(shù)型發(fā)現(xiàn)與文獻的海量型獲取,數(shù)字人文技術與工具在內容創(chuàng)作端與出版發(fā)行端發(fā)揮著愈來愈重要的智能作用。一方面,在學術資料的收集與分析過程中,人文研究者可以通過詞頻統(tǒng)計的主題模型和自動文本摘要工具,從而快速提取海量文獻關鍵信息,實現(xiàn)對文獻的全面掌握,有助于出版知識服務的降本增效。另一方面,研究者和數(shù)字出版平臺可以基于數(shù)字人文研究所擅長的社會網絡分析模型、情感分析模型、語言風格分析模型以及地理歷史信息系統(tǒng)等工具,綜合運用于文學、歷史學、文化遺產學等數(shù)據庫的建設中,以高交互、開放式的方式呈現(xiàn)文本中隱藏的關系語境和再現(xiàn)歷史時空動態(tài)變化,啟發(fā)本學科和相關學科的研究者擴大問題域與提出新結論。相較于過往研究者所主導的旨在提高知識生產效率的科研助手型工具,近年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Ai Agent應用受到廣泛關注,它在數(shù)字人文研究中顯現(xiàn)出了智能探索的潛力,例如Hua W等[10]基于人工智能與模擬仿真技術,通過深入理解人類歷史上的戰(zhàn)爭沖突,為如何預防未來的國際沖突提供了模擬分析工具。這表明數(shù)字人文所提供的學術工具已經不再局限于編寫、標引、翻譯等被動輔助功能,而是漸漸地開始模擬復雜的人類社會行為,進而逐步向自主設計、規(guī)劃執(zhí)行的主動探索角色身份進行轉換。這一變革將導致知識生產的主體發(fā)生深刻變化,并對未來的學術出版生態(tài)造成重要影響。
2.2 平臺重塑:由獨立型向關聯(lián)型的轉化
利用數(shù)字平臺是出版機構提高知識生產與傳播效率的重要方式,作為一種獨特的出版服務形態(tài),數(shù)字出版平臺能夠在技術提供者、作者、讀者、編輯等主體之間建立起互動關系[11]。學術出版機構普遍具有自建數(shù)字平臺的主體自覺,但由于技術標準和同業(yè)競爭等原因,各類孤立的數(shù)據庫產生了海量但重復的數(shù)據,又因缺少有效的信息共享,使得文獻資源浪費嚴重,給信息的高效獲取與利用帶來了不便。因此,目前各類數(shù)字平臺建設的首要難點便是克服內容分散、“數(shù)據孤島”的不利局面,從而實現(xiàn)更高層次的知識服務[12]。近年來,國家陸續(xù)頒布了《出版業(yè)“十四五”時期發(fā)展規(guī)劃》[13]《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fā)展的實施意見》[14]等政策文件,明確提出要強化大數(shù)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qū)塊鏈等技術應用,創(chuàng)新驅動出版深度融合發(fā)展[13-14]。
在此背景下,數(shù)字人文的相關研究有助于打破知識的靜態(tài)與孤立,實現(xiàn)知識動態(tài)關聯(lián)[15]。以國外的免費開源網站Scalar為例,其為眾多分散的數(shù)字人文項目團隊、數(shù)字技術公司、圖書檔案館與出版機構創(chuàng)設了一個協(xié)同創(chuàng)作與出版平臺,方便用戶基于語義網創(chuàng)建原生數(shù)字成果與多媒體在線出版物,其所表現(xiàn)的跨機構協(xié)作特性,為學術出版提供了良好的知識協(xié)作生產服務范例。多模態(tài)文本互聯(lián)當前已成為數(shù)字人文項目的數(shù)據組建手段,多模態(tài)文本互聯(lián)是指通過文本挖掘、社會網絡分析、數(shù)據可視化、機器學習、數(shù)字地圖等技術與方法,以超鏈接的方式實現(xiàn)海量圖片、文檔、地圖及聲音文件的數(shù)據互聯(lián)[16]。以數(shù)字人文項目“羅馬重生”為例,其基于3D建模技術和VR技術,集合了歷史圖像、手稿、書籍等文本與檔案,實現(xiàn)了歷史時空脈絡的動態(tài)可視化,同時具備圖書索引和工具查找的功能,打造了一個結合教學、研究與出版的互聯(lián)型平臺。在數(shù)字人文的觀照下,學術出版平臺由獨立型向關聯(lián)型進行轉化的趨勢,有助于實現(xiàn)知識資源的數(shù)字化、結構化、關聯(lián)化與可視化,從而為學術出版平臺提升自身研究的準確性與科學性創(chuàng)造了路徑,并使出版業(yè)與其他知識行業(yè)的邊界融合成為可能。
2.3 傳播改觀:由集體向公眾的理念變革
考究出版(Publishing)的本意,即“公之于眾”,更確切地說,是將一切有價值的、有組織的、系統(tǒng)化的信息傳遞給公眾[17]。擴大研究成果的推廣和傳播,承擔文化傳承和推廣的任務,是未來數(shù)字人文研究的重要文化使命。學術出版與數(shù)字人文同樣承擔著服務公眾的愿景,或者說,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最重要的發(fā)展前景,不在于使用數(shù)字工具或這些工具帶來的新方法提出新的問題,而在于為公眾重塑知識的生產、表達、分享與討論。
伴隨數(shù)字化進程的推進,人們對于專業(yè)知識的開放性與去中心化的需求日趨強盛,社會大眾漸漸參與進學術資源的組織構建中來,如果說開放獲取(Open Access)學術出版模式的出現(xiàn)是學術知識對公眾開放的先聲,那么數(shù)字人文日趨成熟的數(shù)據眾包系統(tǒng)則預示了公眾參與學術知識生產的趨勢。以倫敦大學學院的邊沁手稿轉錄項目[18]、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的數(shù)字報紙項目[19]、上海圖書館的盛宣懷檔案抄錄項目[20]以及中華書局的“中華經典古籍庫”[21]為代表的數(shù)據眾包模式提高了公眾對數(shù)字人文學術數(shù)據建設及資源組織的參與度,讓公眾得以參與學術出版建設的前端鏈條,打破了傳統(tǒng)人文平臺的單向性和封閉性,使得許多在傳統(tǒng)出版時代不可能參與到社會知識生產體系的普羅大眾成為學術知識的貢獻者,從而極大地豐富了學術知識生產的源泉。這種強調面向公眾的知識生產活動對學術出版機構來說具有重要參考意義,因為這證明了為廣泛的受眾建立在線可參與性項目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以旨在深入映射現(xiàn)代東亞歷史的《身體與結構2.0》[22]這部在線書籍為例,其憑借多視角設計、可視化敘事、非線性瀏覽、交互式互動等內容特性,讀者可以在此書中進行自由探索與數(shù)據補充,從而較好地滿足了作者與公眾之間溝通的意圖。這一出版模式值得以古籍資源的活化應用與多感官數(shù)字化創(chuàng)意呈現(xiàn)為代表的數(shù)字出版借鑒:學術研究成果不再局限于期刊或者文章,而是以多模態(tài)、個性化、交互性的出版產品形式進行體現(xiàn),進而最大限度彰顯其社會價值。
3 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融合發(fā)展的瓶頸
就目前來看,數(shù)字人文對學術出版尚未形成全局性影響。數(shù)字人文雖然為學術出版的發(fā)展提供了機遇和條件,但也挑戰(zhàn)了其原有的出版運作方式和行業(yè)發(fā)展理念,進而引發(fā)一系列的討論爭議,映射了特定的發(fā)展困境。結合海內外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融合發(fā)展的相關實踐經驗,從而歸納出當前所存在的出版?zhèn)惱頎幾h、協(xié)同開放不足、技術應用困難、商業(yè)模式受限等四方面的發(fā)展瓶頸。
3.1 出版?zhèn)惱頎幾h
倫理探討在國外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中始終是前沿熱門議題[24]。目前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融合發(fā)展,存在較多涉及出版?zhèn)惱砑胺蔂幾h的問題。在學術寫作環(huán)節(jié),國外眾多學術出版人與作者就人工智能是否能獨立擔任作者身份這一爭議進行了深入探討[25]。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由于算法與工具中含有歧視與偏見,若不加以謹慎使用與審查,可能會放大學術研究中的偏見[25]。由此來看,以人工智能和算法工具為基礎的數(shù)字人文,不可避免地會在成果出版階段遭到同類爭議。在同行評議環(huán)節(jié),將依賴數(shù)據和算法進行運作的數(shù)字人文工具引入同行評審,同樣難免引起出版學界的質疑,因為學術成果的檢測是編輯和出版人的責任,倘若交給智能機器代以執(zhí)行,則是對編輯責任與價值的削減,也反映了隨著數(shù)字化、智能化技術與工具融入學術出版中,出版責任主體價值生態(tài)失衡問題[26]。在學術成果傳播與共享中,數(shù)字人文提倡學者和公眾對已發(fā)表的原始作品進行開放性編輯與補充,這雖然有助于完善原始研究,但其所引發(fā)的版本知識產權不清晰的問題也有待重視與解決。
在數(shù)字出版平臺的建設中,隱私問題同樣不可忽視。讀者在數(shù)字人文創(chuàng)作、眾包和出版平臺中所進行的注冊、收集、訪問、記錄、存儲、使用、共享等活動,如果平臺的技術使用不規(guī)范或數(shù)據管理不完善,極有可能導致諸如密碼泄漏、位置跟蹤、會話竊取、行為窺探等隱私侵權問題。特別是當前平臺與用戶的數(shù)字權利的認定與運用還未形成行業(yè)規(guī)范,如何保護用戶的知情、訪問、使用、更正、反對、刪除、建議、投訴、數(shù)據轉移等權利,對未來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互構過程形成了重要挑戰(zhàn)。而由于技術黑箱的遮蔽,學術數(shù)字出版平臺所掌握的私權力和新技術,難以被及時有效地監(jiān)管,因而可能會被應用于從事一些不良甚至違法行為,造成不良的社會影響,比如利用人工智能生成虛假的學術數(shù)據等。面對日益發(fā)達的數(shù)字技術,我們試圖在學術研究與出版中保持某種平衡。一方面,我們不希望學術研究與出版太工具化,因為這涉及人在技術主導環(huán)境下所懷揣的主體性隱憂;另一方面,我們也會擔心自身不夠工具化,因為我們亟須新工具所帶來的視野拓展、效率提升和成果迭代。因此,學術出版?zhèn)惱硪?guī)范與數(shù)字人文技術未來將經歷一段相互博弈與不斷妥協(xié)的過程。
3.2 協(xié)同開放不足
就當前國內外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實踐來看,協(xié)同開放雖然已成為顯著的趨勢,同時也是制約二者融合發(fā)展的掣肘,原因有以下兩方面。其一,跨機構協(xié)同開放不足會導致數(shù)據錯誤和版權糾紛。當下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進行科研創(chuàng)作或智能審校時,難免會存在數(shù)據錯誤或虛假的問題,使知識生產的可信度大打折扣,不得不引入人工復檢,而這與智能輔助的初衷相去較遠。這中間自然有技術不成熟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底層技術邏輯與中層知識庫的脫節(jié),即技術的數(shù)據需求與數(shù)據庫、出版平臺之間的版權開放度不相匹配。因為知識庫之間缺乏多元數(shù)據的關聯(lián)與共享,使得數(shù)據的清洗與檢測不充分,進而誘發(fā)了文本檢索、引用、分析等一系列數(shù)據錯誤,長久往復,更會造成數(shù)據庫內部的循環(huán)錯誤。盡管對數(shù)據版權的開放獲取呼聲甚高,但是文化安全、版權保護、數(shù)據隱私、市場準入等問題仍是數(shù)據開放共享的重要阻礙,這些數(shù)據版權糾紛在一些跨機構和跨國項目合作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例如在數(shù)字人文項目“威尼斯時光機”的跨機構合作過程中,一些涉及機密性和館藏特性的檔案或圖書難以被公開出版使用,同時,機構協(xié)同合作所形成的數(shù)據產權最后歸誰所有、誰有權使用、由誰來負責監(jiān)管等一系列問題也引起了激烈爭議,以至于最后成為該項目停止運行的重要原因。
其二,跨學科協(xié)同不足會導致研究進展緩慢、成果出版受阻。一方面,數(shù)字人文研究的對象既需要計算海量的數(shù)據,也需要人文專業(yè)的辨析,這使數(shù)字人文項目需要開展廣泛的跨學科合作。而我國許多數(shù)字人文項目在策劃、籌建和實施過程中經常會忽視對人文學者真實需求的考量,缺乏與人文學者的合作與溝通[27],加之人文學者難免會在數(shù)據模型應用與驗證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種種原因導致數(shù)字人文研究成果在出版后的適用性、利用率、滿意度及可持續(xù)性上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另一方面,因數(shù)字人文本身的跨專業(yè)、多媒體呈現(xiàn)、項目長期運作的特性影響,以傳統(tǒng)學術出版的理念來評估數(shù)字人文學術成果存在不兼容的問題,所以在對學術成果的評估上,目前學術出版還未對數(shù)字人文項目達成規(guī)范統(tǒng)一的同行評審標準。故而,未來仍需要在數(shù)字技術層、人文研究層與出版編輯層開展更廣泛的跨學科協(xié)同,不斷升級同行評審制度,提升數(shù)字人文成果出版的學術可信度。
3.3 技術應用困難
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都依托技術的發(fā)展與應用,這導致目前所遇到的技術應用困難問題直接影響了二者的融合發(fā)展實踐,具體來看,表現(xiàn)在以下3個方面。①技術應用不夠成熟。數(shù)字人文研究成果的出版與傳播需要出版機構進行相應的技術轉型,而就我國的情況來看,我國數(shù)字人文研究尚缺乏先進的數(shù)字工具,數(shù)字技術應用相對滯后,一定程度上無法滿足人文學者的需要[28]。學術生產端尚且如此,遑論學術出版的數(shù)字人文服務,因技術的制約,導致數(shù)字人文目前常見的項目體驗與手機等移動設備并不兼容,出版機構難以獨自實現(xiàn)數(shù)字人文成果出版的需求,故而杜克大學出版社與作者尼古拉斯·米爾佐夫不得不借助Scalar平臺來聯(lián)合編輯與出版他們關于阿爾及利亞革命史的在線多媒體書籍[29]。②技術迭代與業(yè)態(tài)發(fā)展脫節(jié)。數(shù)字技術迭代過快,容易使研究時效跟不上傳播技術時效,進而導致技術的應用失去持續(xù)性。近年來,伴隨數(shù)字出版的一系列戰(zhàn)略相繼提出,“數(shù)字出版”“融合出版”等實施計劃還未達預期,新的浪潮又已到來,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版等可能性又被納入討論。這雖然是技術迭代中客觀存在且難以解決的問題,但也不得不使大部分出版企業(yè)需要審慎考慮數(shù)字人文在市場應用中的項目風險和回報預期。③技能掌握難度大。數(shù)字時代的出版工作者必須面對文獻介質多樣化和內容海量化的現(xiàn)實,尤其是在開展數(shù)字人文的項目運行與成果展現(xiàn)活動時,更加要求出版從業(yè)人員需要同時掌握計算機編程、數(shù)學分析、項目管理等數(shù)字技能,才有可能策劃、編輯與出版更好的數(shù)字人文產品,但由于語言不同、編碼經驗缺乏、跨學科學習成本過高等原因,通過自學來熟練掌握數(shù)字人文技術的方式仍較為困難。
3.4 商業(yè)模式單一
就目前來看,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相融合的市場開拓與項目盈利仍處于研究摸索階段,故而學術出版機構介入與經營數(shù)字人文領域的商業(yè)模式較為簡單,大體可分為兩種:①提供輔助性的出版服務。如埃默里大學出版社、布朗大學出版社、弗吉尼亞大學出版社等出版機構,這些出版社更多地依靠Scalar、Omeka等平臺為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提供協(xié)助書籍出版的服務,原因在于自身出版力量較為局限,難以獨立開展這方面的業(yè)務。倘若出版企業(yè)的資金與技術較為雄厚,則可以通過共建數(shù)據庫的方式來盈利,如中文在線每年通過資助一定資金來保障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項目的持續(xù)發(fā)展,以此建立合作關系,并幫助CBDB開發(fā)與維護商業(yè)版的在線查詢系統(tǒng)來獲取收益回報。②自營數(shù)字圖書出版業(yè)務。以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為例,其旨在將數(shù)字人文帶入數(shù)字圖書出版的領域,至今已用7年的時間出版了10余部數(shù)字圖書,但是這個數(shù)字人文項目7年來仍是主要依靠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的資助,盡管斯坦福大學出版社試圖擴展在訂閱、作者付費等其他方面的收入來源,但按目前來看,出版社圍繞數(shù)字人文項目的商業(yè)模式仍然比較單一,而且盈利效果不佳。
不過,學術出版在數(shù)字人文領域所產生的盈利困難問題,并非只是出版一端的原因,數(shù)字人文項目本身的不穩(wěn)定性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因數(shù)字人文的組織架構松散、項目運行時間較短、高度跨學科等特性,在項目的可持續(xù)性運作上具有較大的組織和資金風險。因此,面對尚未成熟的數(shù)字人文項目,商業(yè)風險是客觀存在且未知的,所以目前多數(shù)企業(yè)嘗試進行商業(yè)合作的想法還比較保守,導致數(shù)字人文的資金注入渠道受限。故而大多數(shù)數(shù)字人文項目仍然是依靠國家或私人基金的資助來進行開展,如活躍在歐洲各地的時光機(Local Time Machine)項目多年來主要是受歐盟和當?shù)卣鸬馁澲诺靡员3诌\作。而一些民間的數(shù)字人文項目,如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Chinese Text Project)更是靠用戶自愿捐款和數(shù)以萬計的志愿者服務來維系。
4 思考與展望
陳寅恪曾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30]”數(shù)字人文為學術出版提供了新尺度、新方法與新機遇,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數(shù)字人文和學術出版的深度融合既是數(shù)字出版的攻堅目標,亦是創(chuàng)新路徑。學術出版工作者要在“人文的數(shù)字化”和“數(shù)字的人文化”之間尋求平衡點,將數(shù)字人文研究工具、方法、思維模式與學術出版理念和實踐相結合,作為推動當下數(shù)字出版研究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重要舉措。
首先,要正確認識人、出版與技術之間的關系,發(fā)展數(shù)字技術的同時要堅守人文價值內核。回顧出版的技術史,技術的發(fā)展雖然削弱了人對出版活動的影響力,但出版是一個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機器和技術為中心的過程,所以人始終是出版文化價值的真正創(chuàng)造者。在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融合過程中,如果僅專注于數(shù)據模型的構建,則容易忽略傳統(tǒng)人文分析豐富的主觀經驗,如果過度依賴于計算機輔助,則會導致人文深度的消失。因此,學術出版從業(yè)者既要把握數(shù)字人文賦能學術出版的發(fā)展機遇,也要堅守人文價值內核,促使學術出版秉持的思想傳播與文化傳承等核心理念嵌入平臺搭建的全過程,包括數(shù)據模型的建設、用戶界面的設計和傳播環(huán)境的營造等方面。只有將技術與人文并重,理智看待數(shù)字人文熱,方能實現(xiàn)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的可持續(xù)融合發(fā)展。
其次,建立完善的開放協(xié)同機制。在數(shù)字互聯(lián)的當下,原始數(shù)據的開放獲取與自由流通不僅可以加速科研的速度,也是消除人類知識流動障礙和知識鴻溝的必要選擇[31]。這要求學術出版行業(yè)要建立完善的開放協(xié)同機制,在政府與協(xié)會的支持下,通過設立相關的數(shù)字人文出版基金,助力打造良好的學術網絡基礎設施和網絡平臺。一個良好的學術網絡基礎設施的存在,能使眾多獨立數(shù)據庫、技術工具和出版平臺的有機連接成為可能,有助于減少學術資源浪費,提升使用效率和工作靈活度。出版機構需要全程參與學術網絡基礎設施的構建與完善過程,在多方對話、協(xié)作中降低學科協(xié)同壁壘,在數(shù)據庫建設、數(shù)據關聯(lián)發(fā)布、數(shù)據治理等方面制定并發(fā)布相關標準規(guī)范,促進數(shù)字人文知識共建、生產、共享、傳播等流程的優(yōu)化。同時,政府部門要不斷完善學術出版監(jiān)管體系,及時修訂和出臺數(shù)字出版相關管理辦法,強化數(shù)字版權保護,從外部層面確保開放協(xié)同機制的有效運行。
再者,加強出版隊伍建設。在數(shù)字人文的推動下,圖書館一度被認為是過去積累知識的被動儲存庫,當前卻在創(chuàng)造和傳播學術方面發(fā)揮著積極而顯著的作用[16]。這對學術出版的業(yè)務拓展與人才建設來說具有重要啟示,相關出版機構要把握數(shù)字人文的發(fā)展機遇,依實際情況設置數(shù)字人文部門,強化政、企、學、研之間的合作。近年來,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都設立了數(shù)字人文研究中心,故而高校出版社在科研教育、生產技術、數(shù)據挖掘、知識服務等方面的合作上具有先天優(yōu)勢,對于人才培養(yǎng)有積極作用。與此同時,要重點為出版機構的相關人員提供計算機編程等硬技能和項目管理等軟技能的培訓,提升從業(yè)者的業(yè)務能力,并將人才培養(yǎng)落實在員工招聘與績效考核等環(huán)節(jié),使出版從業(yè)人員成為既深諳數(shù)字人文,也具備編輯出版技能的綜合型人才,進而為出版機構參與數(shù)字人文項目提供人才保障。
最后,探索可持續(xù)性商業(yè)模式。具體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進行創(chuàng)新:①目前數(shù)字人文項目側重于技術開發(fā)和平臺搭建,在成果出版環(huán)節(jié)上顯得乏力。對此,出版機構應立足自身在編輯設計、同行評審、版權注冊、發(fā)行營銷等方面的優(yōu)勢,滿足數(shù)字人文學者不斷變化的出版需求,并為傳統(tǒng)人文學者提供個性化、低門檻的數(shù)字學術服務,策劃和出版更多數(shù)字人文精品,持續(xù)激發(fā)市場活力。②放眼未來,數(shù)據將成為一種重要的資產。學術出版機構要充分挖掘自身的圖書、檔案、期刊和用戶行為等數(shù)據資源,并進行資源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由數(shù)字人文服務提供者轉變?yōu)閿?shù)字人文內容生產者,通過自主創(chuàng)新、聯(lián)合研發(fā)等路徑,參與數(shù)字人文項目的標準制定與開發(fā)運營,形成核心商業(yè)競爭力。③當前多元的數(shù)字人文項目表現(xiàn)出了它在文化遺產、教育事業(yè)、創(chuàng)意產業(yè)、智能旅游、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應用潛力,學術出版機構應積極參與各類地方數(shù)字人文項目,設計如多模態(tài)書籍、非線性數(shù)字地圖、知識交互平臺等具有可視化呈現(xiàn)、互動化傳播、沉浸化體驗的數(shù)字出版產品,服務地方的教學機構、博物館、文化館、藝術館、圖書館等主體,在多方合作共贏中實現(xiàn)學術出版多維賦能社會。
目前,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研究的融合發(fā)展還處于前沿探索階段,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變革與困境共生。在當下及未來,我們需要深入推進數(shù)字人文與學術出版之間的理論探討與融合實踐,持續(xù)激發(fā)其在內容生產服務、知識傳播共享、數(shù)字出版業(yè)態(tài)重塑等方面的巨大潛力。
(責任編輯:翟艷榮)
參考文獻
[1] GLADNEY H M.Long-term digital preservation:a digital humanities topic?[J].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2012: 201-217.
[2] 李巧明,王曉光.跨學科視角下數(shù)字人文研究中心的組織與運作[J].數(shù)字圖書館論壇,2013(3):
26-31.
[3] 包弼德,夏翠娟,王宏甦.數(shù)字人文與中國研究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J].圖書館雜志,2018,37(11):
18-25.
[4] 王麗華,劉煒.助力與借力:數(shù)字人文與新文科建設[J].南京社會科學,2021(7):130-138.
[5] 蔡迎春.中美數(shù)字人文研究“差異性”的冷思考[J].圖書館建設,2022(6):100-111.
[6] 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yè)簡介及其學位基本要求[EB/OL].[2024-01-23].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7] 時光機組織.杜布羅尼克時光機項目[EB/OL].[2024-01-23].https://www.timemachine.eu/timemachines/ dubrovnik/.
[8] 包弼德,夏翠娟,王宏甦.數(shù)字人文與中國研究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J].圖書館雜志,2018,37(11):
18-25.
[9] 張耀銘.數(shù)字人文的研究與評價[J].社會科學文摘,2022(2):5-7.
[10] HUA W,F(xiàn)AN L,LI L,et al.War and peace(waragent):Large language model-based multi-agent simulation of world wars[J].Arxiv preprint arxiv:2311.17227,
2023.
[11] 劉廣東,陳丹.2022年數(shù)字出版領域創(chuàng)新研究主題述評[J].數(shù)字出版研究,2023,2(1):25-33.
[12] 沈悅,孫露銘,林子洋.歐洲學術出版業(yè)智能化轉型探索與啟示[J].中國編輯,2024(1):85-92.
[13] 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新聞出版署關于印發(fā)《出版業(yè)“十四五”時期發(fā)展規(guī)劃》的通知[EB/OL].[2024-01-17].https://www.nppa.gov.cn/xxfb/tzgs/202112/t20211230_666304.html.
[14] 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宣傳部印發(fā)《關于推動出版深度融合發(fā)展的實施意見》的通知[EB/OL].[2024-01-17].https://www.nppa.gov.cn/xxfb/tzgs/202204/t20220424_666332.html.
[15] 王麗華,劉煒,劉圣嬰.數(shù)字人文的理論化趨勢前瞻[J].中國圖書館學報,2020,46(3):17-23.
[16] 艾琳·加德納,羅納德·G·馬斯托.數(shù)字人文導論[M].閆欣怡,馬雪靜,王歡,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2.
[17] 方卿,王一鳴.論出版的知識服務屬性與出版轉型路徑[J].出版科學,2020,28(1):22-29.
[18] 英國國家檔案館.邊沁手稿轉錄項目[EB/OL].[2024-01-25].https://blogs.ucl.ac.uk/transcribe-bentham/.
[19] 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數(shù)字報紙項目[EB/OL].[2024-01-25].http://www.nla.gov.au/content/newspaper-digitisation-program.
[20] 上海圖書館.盛宣懷檔案抄錄項目[EB/OL].[2024-01-25].http://zb.library.sh.cn/index.jhtml.
[21] 張稚丹.“數(shù)字人文”成為出版新話題[N].人民日報海外版,2021-07-22(7).
[22] DABVID AMBARS,KATE MCDONALD.[EB/OL].[2024-01-26].https://bodiesandstructures.org/bodies-and-structures-2/index.
[23] 陳靜.復數(shù)的數(shù)字人文: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數(shù)字人文[J].中國比較文學,2019(4):14-28.
[24] LUND B D,NAHEEM K T.Can ChatGPT be an author? A stud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uthorship policies in top academic journals[J].Learned Publishing,2023.
[25] CHECCO A,BRACCIALE L,LORETI P,et al.AI-assisted peer review[J].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2021,8(1):1-11.
[26] 范軍,陳川.AI出版: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出版行業(yè)的融合創(chuàng)新[J].中國編輯,2019(5):64-71.
[27] 張軒慧,趙宇翔,劉煒,等.數(shù)字人文眾包抄錄平臺用戶體驗優(yōu)化的行動研究:基于社會技術系統(tǒng)理論[J].中國圖書館學報,2020,46(5):94-113.
[28] 蔡迎春.中美數(shù)字人文研究“差異性”的冷思考[J].圖書館建設,2022(6):100-111.
[29] Duke University,Mirzoeff,Nicholas.“‘We Are All Children of Algeria:Visuality and Countervisuality 1954-2011.”[EB/OL].[2024-01-26].http://scalar.usc.edu/nehvectors/mirzoeff/index.
[30] 陳寅恪.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1] 蘇磊,韓婧,張廣萌,等.聚焦面向數(shù)字學術的數(shù)據出版[J].科技與出版,2019(4):5.
The Academic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erspective Enlightenment for Change and Development
Jun Fan1,2Zhunjian Zhong2
Wuhan Business School,Wuhan 430056,China;2.School of Liberal Arts,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Digital humanities is a new type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that combines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humanities research. It has a close internal logical correlation with academic publishing, and the two development goals are consistent, and it shows the obvious relationship of mutual promo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the tools, platforms and concepts of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accelerated the triple changes of academic pub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tools from auxiliary to exploratory,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platform from independent to relational,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 concept from collective to the public. I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it are faced with bottlenecks such as publishing ethics disputes, lack of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difficul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single business model. Based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al humanities to academic publishing, we should correctly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publishing and technology, improve the collaborative opening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shing team, and explore the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so as to better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Academic publishing; Digital publish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