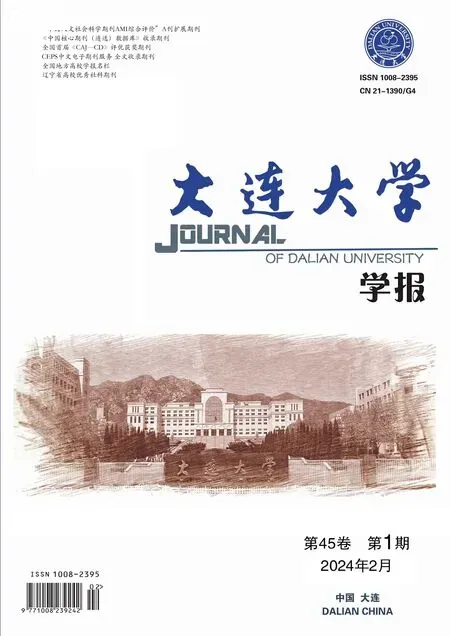國內學界關于美國印度洋政策研究的文獻綜述
李俊霖
(1.大連大學 歷史學院,遼寧 大連 1166222;2.大連大學 教育部環印度洋島國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622)
自大航海時代起,印度洋一直是連接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通衢。該區域內分布著曼德海峽、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重要水道,加之臨近全球最大的石油產地——中東,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國角逐的競技場。20世紀末以來,中國作為印度洋貿易通道的利益攸關方,始終關注著該區域的地緣政治動向,特別是對于旨在建立區域“單極秩序”的美國印度洋政策,更是格外留意。
一、研究的整體狀況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國內①本文所論及的“國內”僅指中國大陸,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學界關于美國印度洋政策的研究,包括冷戰以來美國政府與印度洋沿岸各國雙邊、多邊關系的演變,以及從“印度洋”(Indian Ocean)到“印度洋——太平洋”(即Indo-Pacific,下文統稱為“印太”)這一概念變遷背后美國印度洋政策調整的動機、表現和影響。
國內學界有關以上兩個問題的研究始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②相關研究成果檢索時間截至2023年4月20日。已產出的研究專著有李曉妮的《美國對巴基斯坦政策研究》(2010)、張威的《1971年南亞危機與美巴關系》(2015)、蘭江和馮韌的《“911”事件后美印巴關系研究》(2015)、王曉文的《美國印度洋戰略的歷史演進研究》(2017)和《第三者視角——印太大國互動研究》(2021)、李向陽的《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18——“印太”理念能否成為特朗普亞洲政策的基石?》(2018)、韋宗友的《美國印太安全布局研究》(2021)以及許以民的《冷戰時期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2021)共8部,學術論文110篇以上③以上統計結果來源于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中國知網。。
從研究成果的時間分布上看,1990至1999年,發表論文4篇;2000至2009年,發表論文10篇;2010至2019年,發表46篇,出版專著5部;2020年至今,發表論文51篇,出版專著2部,總體上呈現出明顯的遞增趨勢。從研究成果的內容上看,相關研究均與美國政府圍繞“印度洋——太平洋”區域的政策規劃及實踐高度相關,所涉及的研究領域以國際關系學為主,經濟學、情報學、軍事學和歷史學輔之。對照相應的時代背景可知,國內學界關于美國印度洋政策變遷研究的重視程度,與2010年前后國際地緣格局的變化有著密切關聯。在小布什政府任期內(2001至2009年),盡管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總體呈現出一種“合作”與“競爭”并存的“復雜”狀態,但總體而言,各國仍能以某種形式的“伙伴”關系相處。到了奧巴馬政府時期(2009至2017年),隨著美國愈發頻繁地動用其綜合國力優勢,干預經濟全球化進程,插手區域地緣博弈,致使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日益趨向動蕩。此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任內(2017年至今)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對抗性進一步加強[1]。為應對多元化的挑戰,美國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調整和強化區域政策,以穩固其既有優勢,印度洋政策就是該方針的具象化,而這直接促成了國內學界對相關議題關注度的提升。
二、冷戰以來美國對印度洋沿岸各國政策的演變
自1946年英國前首相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后,“冷戰”幾乎主宰了20世紀下半葉全球地緣格局的走勢。為了與蘇聯爭奪政治和意識形態勢力范圍,美國政府將觸角伸向七大洲和四大洋的各個角落。在印度洋方向,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馬爾代夫為代表的印度洋島國以及索馬里等非洲國家,是美國政府相關政策的主要目標對象①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及伊朗雖然在地理上亦位于印度洋及其毗連海區沿岸,但在地緣政治上屬于中東板塊,故此在梳理美國印度洋政策的演進時未將其納入考察范疇。。
(一)美國與印度關系相關研究
印度次大陸是印度洋區域內面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緣板塊,也是美國印度洋政策的焦點所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國政府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印度,全稱為“印度共和國”,于1947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鑒于曾被英帝國主義殖民的慘痛經歷,在整個冷戰時期,印度始終與作為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的蘇聯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關系。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冷戰時期的美印關系設置了上限。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阻礙美印關系發展的“意識形態障礙”也消失了,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印關系迅速由“冷”轉“熱”。
關于冷戰結束初期(20世紀90年代)的美印關系,杜幼康認為,美國對于改善雙邊關系的意愿要弱于印度,這源于南亞在前者全球地緣政治布局中的作用下降[2]。甘愛冬和張世均則認為,即便在“后冷戰時代”,印度對于美國而言仍具有穩定南亞局勢,維持歐亞大陸均勢,以及提供廣闊的消費市場等多重價值[3]。換言之,“后冷戰時代”美印關系的基礎是現實利益層面的共識。例如,張家棟和魏涵就指出,“后冷戰時代”的美印關系是一種介于普通國家和同盟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是基于現實利益層面的彼此需要,而不是全球性、戰略性、同盟性的伙伴[4]。張力、吳兆禮、蘭江和馮韌通過分析“9·11”事件后美國在強化與巴基斯坦的反恐合作之余,繼續拉近與印度關系的舉動,進一步印證了美國對印度政策的現實主義屬性[5-7]。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作為美國構建其“伙伴”體系的重要抓手,也適用于其對印度政策。例如,張貴洪和萬雪芬考察了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政府借助共同的“民主價值觀”拉近與印度關系的舉措,及其背后利用印度制衡中國的意圖[8-9]。
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綜合國力和影響力日益提高的中國,美國自奧巴馬政府開始,逐步將其對外工作重心轉向亞太,這為美印關系的進一步強化提供了契機。牛震和張根海分析了美國重新認識到印度作為區域性大國,可以在平衡西太平洋區域地緣關系方面發揮作用的始末,以及其為提升雙邊關系做出的努力[10-11]。然而,印度身為領土面積居世界第7位,人口數量超14億的世界性大國,在立國之初就將獨立自主作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信條。這也就意味著印度無法徹底成為美國的政策棋子。針對該問題,蔣愷、孫晉忠、馬孆等梳理了“后冷戰時代”制約美印關系發展的諸項沖突因素。譬如,在構建冷戰后的國際秩序的問題上,印度更希望形成多極化的國際秩序,以便其實現成為“有聲有色大國”的夢想;而美國則希望構建和鞏固基于自身利益的單極世界。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美國力求在印巴兩國間保持某種平衡,不愿意全面支持印度的領土主張。在印度洋話語權的問題上,印度始終堅持印度版“門羅主義”,將印度洋視為其天然勢力范圍,此舉與美國掌控全球航運節點的既定方針產生沖突。除此之外,在印度與俄羅斯關系、印度民間的排美情緒、核不擴散等問題上,美國與印度之間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12-16]。到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優先”成為其調整和重塑美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對此,孫現樸、唐小松和徐夢盈等梳理了特朗普時代美國對印政策的兩面性,即一方面提升反恐、防務和經濟領域的合作,另一方面收緊印度人赴美工作簽證發放,取消針對印度的“普惠制”,并加大對印度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扶持力度,以期達到借由軟實力輸出促使印度政府做出有利于美國的決策的效果[17-19]。
軍事合作往往是檢驗國與國之間互信程度的試金石,在美印關系中同樣如此。余翔和王棟對于美國與印度之間軍事合作的演進歷程進行了階段性梳理,即20世紀90年代的試探性合作,“9·11”事件后美印之間逐步建立起的涉及各軍種、多層次、例行性的軍事演習體系,以及2014年以來圍繞遏制中國展開的美印軍事合作再升級[20]。而這一變化反映出美印關系穩步升溫的發展態勢。
(二)美國與巴基斯坦關系相關研究
巴基斯坦作為南亞地緣板塊中綜合國力僅次于印度的地區性強國,其自冷戰時代起就是美國“伙伴”體系中的重要成員。同美國對印度的外交政策類似,美國對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也建立在現實利益的基礎上。冷戰初期,恰逢英國為代表的傳統殖民勢力從南亞地區撤離,作為資本主義世界新“盟主”的美國開始嘗試填補這一地區的“權力真空”以防備蘇聯影響力的滲透。此外,借助巴基斯坦作為南亞、中亞之間交通要沖的地理位置以及宗教和民族構成方面的特點①伊斯蘭教信徒在巴基斯坦總人口中所占比重超過95%,普什圖族為巴基斯坦國內的第三大族群,亦為阿富汗國內的第一大族群。向中亞地區投射影響力,也是促使美國著力發展與巴基斯坦關系的重要驅動力。
與印度相同,巴基斯坦也是從原英屬印度中獨立建國的,其建國后能在短時間內迅速與美國建立起較為緊密的“伙伴關系”,與印蘇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其背后社會主義陣營自中亞南下印度洋的態勢緊密相關。尤建設認為,在冷戰序幕緩緩拉開的時代背景下,美國政府將巴基斯坦視作其“中東防御”計劃中的一環,以及防御蘇聯在亞洲方向擴張的屏障[21]。張樹明和董韶華通過分析美國政府處理“普什圖尼斯坦”爭端的態度,揭示其借助巴基斯坦參與中亞地緣政治的方式和策略,即通過平衡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的關系,以有限和非正式的形式輻射影響力,其核心是提升巴、阿兩國間的經濟和政治互信,同時為美國在中亞地區塑造良好形象,而以上措施的最終目的是削弱蘇聯在中亞地區的擴張勢頭[22-23]。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后,巴基斯坦在美國制衡和削弱蘇聯的計劃中扮演的角色愈發重要。對此,許以民和孫立祥認為,在整個里根政府時代,巴基斯坦都是美國利用阿富汗實施削弱蘇聯的重要基地和中轉站[24]。
冷戰結束后,對于美國而言,巴基斯坦作為防御蘇聯在南亞擴張前沿陣地的價值不復存在了。如藍建學、王英良和鄧紅英所言,此時美國南亞政策的焦點逐漸由“扶持巴基斯坦、平衡印巴”變成“壓巴扶印、抑制中國”[25-27]。
進入21世紀后,南亞仍舊是美國向中亞地區施加影響力的跳板。依照杜幼康的觀點,布什執政時期的美國政府打算將中亞和南亞方向的力量和資源部署加以整合,而此時其假想敵已由蘇聯變為了中國[28]。
關于美國與巴基斯坦之間“伙伴”關系的定位,劉紅良、安高樂和梁東興等認為,美巴聯盟是較為典型的“準盟友”關系,二者的利益訴求既高度重合又并非完全一致,在實踐中表現為合作與分歧并存的復合型關系[29-31]。2011年,“9·11”事件的主謀,“基地”組織首領本·拉登被美國海軍陸戰隊擊斃,標志著美國政府耗時近10年的反恐戰爭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此事給美國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關系造成了不小影響。潘遠強、李斌和張力等指出,在“后本·拉登時代”,美國仍舊保持著與巴基斯坦之間的反恐合作,繼續對后者提供援助,但與此同時也時常指責后者執行反恐政策不得力,并以此為由向其施壓[32-34]。到了特朗普政府時期,由于印度可以為美國實施對華政策提供更多幫助,美巴關系進一步趨冷,美印關系更加熱絡。
軍事合作是觀察美國與巴基斯坦之間外交關系的重要維度。蘭江和毛德金以1954至1965年美國對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為切入點,論述了美國與巴基斯坦軍事合作的方式、規模以及演變趨勢[35]。在此基礎上,蘭江分析了巴基斯坦軍隊在美巴關系中扮演的角色,即一方面在反恐和對抗蘇聯方面與美國保持緊密合作,促進美巴關系發展,另一方面在核不擴散、印巴軍事對抗和巴基斯坦國內政治民主化等問題上持與美國政府相左立場,成為阻礙美巴關系發展的因素[36]。趙長峰、譚向豪和張威認為,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受到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巴基斯坦的地緣環境、區域及國際局勢的影響[37-38]。
除此之外,李曉妮和許以民分別對冷戰以來美國政府對巴基斯坦的外交和援助政策進行了系統梳理[39-40]。
(三)美國與其他印度洋沿岸及島嶼國家關系相關研究
相較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美國政府對其他印度洋沿岸及島嶼國家的關注度較低,與之相關的外交政策也大多圍繞遏制蘇聯擴張與應對“中國威脅”,以及控制具有戰略價值的交通節點。
高亮、李濤和崔佳宇探討了冷戰以來美國對尼泊爾外交政策的演變,如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放棄了自冷戰以來對尼泊爾國內左翼政治力量的敵視態度,積極謀求強化與尼泊爾政府之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以求將尼泊爾拉入其“伙伴圈子”;到了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加大了對尼泊爾國內親美政治勢力的扶持力度,以期能夠起到牽制中國的作用[41-43]。樓春豪、徐琴和王娟娟分析了冷戰以來美國政府對孟加拉國的外交政策,并指出其目的是制衡中國,其實現途徑是干預孟加拉國國內的選舉,以及強化美國與孟加拉國之間的經貿和安全合作[44-45]。
盧紅飚、孫現樸和崔戈等分析了冷戰以來美國對索馬里、肯尼亞、斯里蘭卡以及馬爾代夫的政策,由于以上四國地理位置臨近印度洋貿易線,因此美國旨在通過對四國施加控制,以保持其對印度洋海運動脈的掌控,進而維護其治下的國際秩序,而實施手段則無外乎輸出美式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提供經濟援助,強化安全防務合作等。但在實施過程中,上述意圖也會因為對象國內部復雜的社會矛盾和美國政府的舉措失當而難以達到預期效果[46-50]。
三、從“印度洋”到“印太”背后的地緣概念變遷與政策實踐
“印太”概念的問世反映出美國印度洋政策的一次重要升級。李金峰、蔡澤斌和李德木對“印太”一詞作為地緣政治概念的產生歷程進行了梳理,早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地緣政治學者卡爾·豪斯霍夫 (Karl Haushofer)就提出了“印太空間”(Indo-Pacific Space) 的概念,至21世紀初,經澳大利亞政界和國際關系學界重新詮釋,“印太”作為一個地緣政治概念正式登上國際政治舞臺,2010年前后,日本、印度和美國也先后接納了這個概念[51-52]。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解釋“印太戰略”的話,趙明昊的概括可謂精當,即由美國主導,“構建多層次的盟伴體系,打造融合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等多種力量的復合陣營”[53]。
地理意義上的印太地區應包括印度洋和太平洋及其沿岸的所有國家,但在地緣政治的語境下,所謂“印太”是指從西太平洋到西印度洋的廣闊海域及其毗鄰的沿海國家,即從東經140°到東經60°、南接南印度洋、北抵沿海國家的廣闊區域。
楊慧和劉昌明梳理了美國智庫眼中的“印太戰略”概念所經歷的由地理概念到區域概念再到政策概念的轉變,其背后反映了美國政策界對于來自“中國的挑戰”的認知在不斷更新[54]。
(一)美國印太戰略起源、發展和演變的相關研究
美國印太戰略始自奧巴馬政府時代,是美國調整和重構全球格局的組成部分。韋宗友和仇朝兵指出,經歷過2008年金融危機的美國意識到了中國正在成為其全球領導地位的威脅,遂將關注重心轉向亞太方向,并通過強化與印度的外交關系以求在印太地區建立新的有利于美國的地緣態勢平衡,進而在全球范圍內維護美國的價值觀和利益[55-56]。
除了印度之外,日本和澳大利亞也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參與者和關鍵節點。王守都從國際政治語言學的視角出發,分析了美、日、印、澳四國對印太戰略認知的分歧和差異[57]。
夏立平、陳邦瑜和韋紅等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闡述了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以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為核心的“同盟體系”的目的,即鞏固其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58-62]。
徐金金和張許許梳理了特朗普時代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價值觀層面的“對等原則”“法治”與“航行自由”;區域安全層面的“反對核訛詐和恐怖主義”以及“將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經濟安全領域的“自由貿易”等。而想要達成上述目標,美日同盟、美印關系、美日印澳四國關系是不可或缺的三大支柱[63-64]。陳積敏、夏立平和鐘琦等對特朗普時代美國印太戰略面臨的阻礙因素進行了梳理,其主要有“美國第一”理念導致的聯盟內在動力不足、團隊不完整和成員國兩邊下注,美國與其印太地區盟友在能力和地位上不平等,印度與美國的政策計劃不完全一致,美國政府投入的資源和目標不相稱等[65-67]。
胡娟、吳昊和張景全等對拜登執政后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內容和目的進行了分析,指出拜登團隊在推動印太同盟“北約化”,即強化北約與印太同盟國家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軍事和防務關系。具體舉措包括,實施前沿外交、前沿軍事部署以及推進“印太經濟框架”等[68-71]。吳士存、趙祺和羅圣榮就拜登政府印太戰略中的“小多邊主義”策略進行了分析,其核心是強化“印太”盟友間的合作,包括經濟層面的基礎設施建設,供應鏈重構和技術研發整合,以及軍事層面的合作部署和技術、信息共享,其底層邏輯則是“權力至上”和“利益至上”[72-73]。
王鵬權、趙菩和李巍等對于特朗普政府至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印太戰略的調整與變化進行了研究。二者之間的共性在于注重維護美國的優先利益與主導地位,以及印太戰略對中國的牽制作用。二者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對印太地區政策的定位方面,特朗普政府強調“自由開放”,拜登政府強調“安全繁榮”;在對華關系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強調“全面戰略競爭”,拜登政府強調“競爭性共存”。總體而言,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相較于特朗普政府更側重于回歸多邊主義,通過制度升級、創新,構建“封鎖”中國的秩序;注重外交,通過強化科技、供應鏈、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合作,夯實印太戰略的經濟基礎,不再片面強調“美國優先”,轉向投資伙伴關系[74-77]。
此外,李向陽對于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實施效果進行了評析和前景展望[78]。王曉文對美國政府的印度洋政策進行了系統的歷史性梳理[79-80]。
(二)美國印太戰略下的印太同盟的相關研究
盟友體系是美國政府踐行印太戰略的重要抓手。林民旺、宋偉和樊高月等對美日印澳四國機制的誕生和演變進行了分析,指出創造該機制的目的在于從“政治”“軍事”“經濟”“技術”等角度遏制中國的發展,在事實上促成所謂的“新冷戰”。而影響四國機制發展、演化的動機可以分為一般性動機和特殊背景兩類,前者主要是參與國內在的現實利益訴求,后者則包含新冠疫情和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沖擊等外部刺激[81-85]。肖軍分析了奧巴馬政府至拜登政府時期美國處理與印太盟友關系的政策,指出特朗普繼承了奧巴馬在印太地區保持領導權和控制力,同時鞏固與澳大利亞、印度以及日本等盟友關系的做法,并且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更加注重安全秩序的構建。拜登政府的印太盟友政策大體繼承了前兩任的既有成果,略有微調,更強調伙伴關系的構建、維系和運用[86]。基于近年來美國印太戰略的變與不變,謝曉光和杜洞光總結出了印太同盟的五大特征,即“威脅制衡、集群效應、議程多元、節點防御與區域聯動”[87]。
盡管美國政府在維系印太同盟方面投入了許多心力,但仍難以掩蓋同盟國家之間存在的分歧。孟慶龍、邢瑞利和唐小松等分析了印太戰略背景下,美印關系取得的突破以及存在的障礙,指出美國和印度之間的“同盟”關系之所以能夠成立,是源于經濟和地緣政治利益層面的共同點。但作為兩個在外交方面獨立自主的大國,美國和印度均無法接受成為別國的棋子,這也就決定了兩國在印太同盟框架下的關系始終在“盟友”與“伙伴”間徘徊[88-91]。
除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這三個核心盟友外,美國的印太盟友體系中還包括其在東南亞的傳統“追隨者”。張恒彬、韋宗友和劉若楠探討了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國政府與其東南亞傳統盟友間的關系[92-94]。其中,并非所有東南亞國家都積極配合美國政府旨在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例如,聶文娟探討了菲律賓選擇在美國主導的印太同盟中自我“邊緣化”的動機和舉措[95]。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地理意義上的印太區域內成員,東非沿海各國卻沒有被納入美國政府的印太戰略。趙晨光認為,這恰恰凸顯了“印太”作為地緣政治概念的戰略屬性、安全屬性以及封閉的“聯盟”屬性,映射出美國政府希望透過構建和具象化這一概念,掌握該地區政治主導權的意圖[96]。
(三)美國印太戰略下的“經濟聯盟”的相關研究
經濟合作既是美國政府拉攏印太盟友的手段,也是踐行印太戰略的具體舉措。蘇可楨、沈偉和楊飛等對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簡稱“IPEF”)進行了剖析,認為其延續了“小多邊主義”的理念,核心是經濟領域去全球化,或者更直白地說,是圍繞美國及其盟友重新構建“去中國化”的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其本質上是一份以“美國優先”為導向的印太地區經濟整合方案。而為了凸顯這一方案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的“正義性”,拜登政府還為其披上了“聯通經濟”“韌性經濟”“清潔經濟”“公平經濟”的外衣[97-102]。梁東興、陳仕平和毛維準等研究了美國政府在印太地區的基建和數字經濟計劃,前者是為了遏制中國利用現有的制造業優勢拓展經濟圈,后者是為了拖慢中國在新經濟領域的趕超步伐[103-106]。
能源合作是美國政府實施印太戰略的重要抓手。仇朝兵梳理了美國印太戰略中涉及的能源合作問題,即“能源安全、能源貿易與投資、能源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市場建設與能源市場一體化、能源技術研發合作與能源技術援助等”,并對印太聯盟圍繞上述問題展開的合作進行了評析[107]。唐新華對美國政府在印太地區爭奪新能源技術和市場話語權的部署進行了研究,指出美國政府的策略是一方面在新能源研發和產能方面下注,另一方面積極參與碳交易機制構建并炒作與之相關的安全議題,希望在能源領域與中國展開競賽和博弈[108]。
(四)美國印太戰略下的“軍事同盟”的相關研究
軍事合作是美國印太戰略和印太同盟的核心內容。韋宗友對美國政府在印太地區的總體安全布局進行了系統梳理和闡釋[109]。由于印度是美國印太盟友中獨立性和自主傾向最強的,因此美國與印度之間的軍事合作成了檢驗印太聯盟穩定性的“試金石”。楊震和王森探討了印太戰略框架下美國與印度之間的海上軍事合作,具體合作形式包括裝備技術合作、軍事演習和雙邊軍事論壇等[110]。為了使印度在印太同盟中發揮更大作用,美國還積極推動其與日本、澳大利亞之間的軍事合作。王曉文就對美國政府強化印太盟友間軍事合作緊密度的舉措,以及其在印太地區建立軍事霸權的意圖進行了研究[111]。王業超和宋德星對美國和印度之間的網絡安全合作進行了梳理和評析[112]。
為了能夠更好地感知和掌控印太地區的安全局勢,美國政府近年來一直在加強該地區的軍事部署。曹筱陽對于奧巴馬政府在印太地區的海上軍事部署及其影響進行了梳理和評析[113]。樓春豪和王寵著重分析了美國政府強化印太海域情報感知能力的諸般舉措及其實效[114]。李益斌和李浩洋基于聯盟理論研究了美國主導下的印太聯盟內部的情報合作情況[115]。張茗對于印太聯盟在太空安全領域的策略進行了研究,認為其具有軍事化、武器化傾向,且聯盟內部相互倚重,共同針對中國這一“假想敵”[116]。
按照韋宗友和趙青海的觀點,盡管美國盡力構建其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安全同盟體系,仍要面對以下的四重困境:1.全球戰略與地區承諾之間的張力;2.軍事預算縮水與戰略空間拓展之間的悖論;3.地區盟國及安全伙伴與美國在戰略目標及威脅認定上的分歧;4.對華關系中合作與制衡之間的選擇困難[117-118]。
四、評析與展望
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了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①該倡議與同年9月提出的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合稱為“一帶一路”倡議。。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其中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119]可見,“印太”概念下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及沿岸國家,對于21世紀的中國國家安全和利益至關重要。這也解釋了,為何國內學界近幾年對美國印度洋政策的關注度持續升溫。
總體來看,國內學界關于美國印度洋政策的研究成果,不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均值得稱道,但也仍存在一些有待改進的問題。首先,現有研究選題普遍較為宏觀,這直接導致了不少論文在結構、方法甚至內容上出現同質化現象。其次,研究視角過于集中于外交、經濟和軍事等傳統國際關系學的研究領域,而對文化、心理以及社會思潮等影響美國印度洋政策制定和實施效果的“軟”性因素關注不夠。
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進一步提升和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擴大,印太地區作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和價值必然迎來進一步提升。這意味著美國印度洋政策也必然隨之迭代升級,并給國內相關學者帶來新的研究素材、視角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