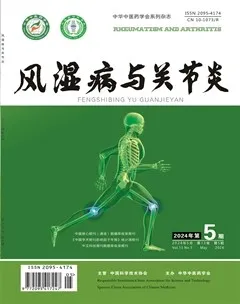劉英教授基于瘀血論治系統性硬化癥經驗探析
鄒國強 劉英 王夢潔
【摘 要】 系統性硬化癥是一種機制尚不明確的難治性結締組織病。山東名中醫劉英教授認為,“瘀血”為本病核心病機,貫穿疾病始終,當從瘀論治。臨床治療以活血化瘀為核心,注重從健脾益氣、養肝調情、調和營衛三方面入手以助化瘀血,并針對其皮膚病變靈活運用黃芪和積雪草,標本兼治,為系統性硬化癥治療提供新思路與新方案。
【關鍵詞】 系統性硬化癥;瘀血;活血化瘀;名醫經驗;劉英
劉英教授是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繼承人,山東名中醫,山東省優秀中醫臨床人才學科帶頭人,中華中醫藥學會風濕病專業委員會常務委員。
系統性硬化癥(systemic sclerosis,SSc)是以彌漫性皮膚增厚和纖維化為特征、嚴重時可累及臟腑的一種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本病進展隱匿,病程較長,早期易被忽略[1]。發病年齡多在30~50歲,以女性多見。本病可導致周身皮膚緊繃發亮和色素沉著,尤其面頸部受累呈現“面具臉”,引起容貌改變易使患者情緒焦慮,嚴重影響患者日常生活。目前,西醫治療本病主要運用抗纖維化、擴血管、免疫抑制3類藥物,效果不佳、不良反應大、費用昂貴,給患者帶來沉重負擔。根據臨床觀察和大量患者反饋發現,中醫治療本病優勢明顯且潛力巨大,為SSc的治療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法。劉英教授對SSc的治療有深入研究,她認為瘀血為本病核心病機,治療從中醫整體觀念出發,以活血化瘀為核心,同時兼顧健脾益氣、養肝調情、調和營衛以助化瘀血,配合經驗用藥黃芪和積雪草快速改善皮膚纖維化,臨床效果顯著。現將劉英教授治療SSc經驗總結如下,以期對臨床有所幫助。
1 病因病機
SSc屬中醫學“皮痹”“痹證”范疇,中醫學無SSc病名,對“皮痹”早有記載,皮痹以局限性或彌漫性膚冷肢麻、水腫,甚者肌膚僵硬、萎縮為主要表現[2]。外邪侵襲是痹證形成的首要因素,外邪入里,正虛不盛,邪阻脈道,氣血運行滯澀,肌膚失養,皮損硬化。《素問·五臟生成篇》云:“血凝于膚者為痹。”現代研究證實,微循環系統病變是SSc發病中心環節,SSc患者血管內皮細胞受損、通透性改變、紅細胞聚集、血液黏度升高引起微循環中血液流態改變[3]。符合中醫對“瘀血”的認識。范永升[4]將SSc的病機概括為虛、寒、瘀,治療以溫陽散寒、通絡祛瘀為主。周翠英[5]認為,SSc病機為先天稟賦不足、外邪侵襲、氣血津液運行失常,治療上注重活血化瘀。張志禮[6]認為,SSc病機為脾腎陽虛、氣血凝滯,治療以健脾益腎、活血化瘀為主。熊繼柏[7]認為,SSc病機為經絡阻隔、氣血不通,治療以活血通絡為主。由此可見,各大醫家在“瘀血”為本病的病機上達成共識。
劉英教授認為,瘀血是本病發生、發展的關鍵,也是治療的難點。多數醫家臨床上單純使用活血化瘀藥治療,見瘀化瘀,瘀血難以根除,相反使正氣耗散疾病加重,成為本病治療的棘手之處。劉英教授針對瘀血的治療極具創新性,在使用活血化瘀藥物的同時多方面考慮,注重整體調護,總結為正氣虧虛、情志抑郁、衛郁營滯3個方面,臨床收效頗豐。疾病發生皆是因人體正氣不足,無力抗邪。《素問·評熱病論篇》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劉英教授發現,本病患者多有遭受風寒邪氣經歷或后天調攝不當使正氣過度損耗。《圣濟總錄·婦人血風門》云:“氣憑血運,血依氣行。”氣與血相互促進,相互依存,兩者密不可分。正氣虧耗,血行無力。正虛是血瘀的重要原因,血瘀是正虛的臨床表現。《丹溪心法·六郁》云:“氣血沖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諸病生焉。”SSc病程長,易造成患者容貌改變,尤其年輕女性易出現焦慮抑郁等不良情緒。長期如此致使肝失疏泄,一身氣機運行不暢,病情惡化,所以治療上應考慮患者情志因素。風寒濕邪氣侵襲,擾亂營衛之氣運行,致使衛郁營滯。《傷寒論·平脈法》云:“營衛不通,血凝不流。”營衛失調導致氣血津液運行受阻,加重瘀血。可見,營衛之氣和瘀血之間的相關性。
2 治療特點
劉英教授治療SSc以活血化瘀為入手點,同時兼顧健脾益氣、養肝調情、調和營衛,臨床效果顯著。
2.1 活血化瘀為核心以攻逐瘀血 瘀血是SSc發生及遷延難愈的核心因素,是本病轉歸的中心環節。《類證治裁·痹證》有云:“久痹不愈,必有濕痰敗血瘀滯經絡。”瘀血日久不除,瘀而化熱,傷津耗氣,病情愈重。本病臨床表現與瘀血程度密切相關,重點突出在皮膚方面。欲治本病首選活血化瘀藥以逐瘀血、暢氣機。
劉英教授在活血化瘀藥選擇上具有獨到之處。皮膚增厚變硬、色澤變深、肌膚甲錯,當首選桃仁、紅花、牛膝、雞血藤4味基礎化瘀藥。桃仁活血化瘀潤燥;紅花活血止痛;牛膝入血分,通血脈,引瘀血下行;雞血藤行血補血,既化生陰血又可活血通絡[8]。4味藥相伍活血養血,化瘀潤燥。現代藥理研究表明,桃仁、紅花在改善血小板聚集和血液流變學異常方面具有明顯作用[9]。雞血藤被譽為“血中圣藥”,入肝腎經,行血散瘀,性質和緩。《飲片新參》中雞血藤具有祛瘀血、生新血、流利經脈之功。皮膚頑厚如皮革不能提捏者,劉英教授常配伍夏枯草。《本草求真》曰:“夏枯草辛苦微寒,詎知氣雖寒而味則辛,凡結得辛則散,其氣雖寒猶溫,故云能以補血也,是以一切熱郁肝經等證,得此治無不效,以其得藉解散之功耳。”夏枯草雖不屬活血化瘀類藥,但對于瘀血所致的頑癥確有明顯作用。張志禮[10]針對皮膚觸之質硬、色素沉著或脫失配伍夏枯草15 g以活血軟堅散結。但因其寒涼之性,體質虛弱者慎用。劉英教授常用夏枯草9~12 g與半夏、海藻相伍,共奏養血化痰破堅之功。現代藥理研究認為,夏枯草具有良好的抗炎和免疫調節作用[11]。皮膚顏色紫暗無光澤,毛發脫落,常規藥物力量不足難逐瘀血,劉英教授配伍三棱、莪術。三棱為“血中氣藥”,莪術為“氣中血藥”,兩者各具特色,具有行氣破血、消積止痛之功,為治療頑固瘀血常用藥對[12]。靈活運用蜈蚣、地龍、土鱉蟲等蟲類藥。蟲類藥具有走竄之性,與植物藥相配動靜結合彼此制約,加強化瘀力度而不傷正。劉英教授臨床善配伍蜈蚣,《醫學衷中參西錄》曰:“蜈蚣,走竄之力最速,內而臟腑,外而經絡,凡氣血凝聚之處皆能開之。”其具有鎮痛、抗炎、抗凝、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13],對于頑固瘀血具有獨特療效。屠文震[14]認為,蟲類藥為血肉有情之品,通達經絡之力強于草本植物。但蟲類藥藥效峻猛易傷脾胃之氣,臨床使用需固護脾胃。
2.2 健脾益氣以扶正祛瘀 劉英教授將健脾益氣作為治療SSc的基礎。《靈樞·百病始生》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正氣虧耗,邪氣趁虛而入,阻滯經絡氣機致使病情加重。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普濟方·方脈總論》所云:“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扶助正氣以疏通經絡,鼓動氣血津液運行使之環周無休,以達益氣行滯通痹之效。此外,使用活血化瘀藥配伍益氣補氣之品以防正氣虧耗,及時扶助正氣有助于增強機體抗邪能力并促進自我恢復。
劉英教授補氣善從脾胃入手。《素問·太陰陽明論篇》亦云:“脾病……今脾病不能為胃行津液,四肢不得稟水谷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則無氣以生,故不用焉。”脾胃居于中焦,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健運,氣血化生充足。SSc患者多有乏力、畏寒、食欲不振、便溏等脾胃虛弱之象,常用人參、白術健脾益氣。白術燥濕健脾與人參相配伍益氣補脾之力更著,取四君子湯之義。病情較重者再入黃芪,補中氣,固表氣。再配入足陽明胃、足太陰脾之引經藥升麻,升提陷下之中氣,臨床常用量為6 g,共奏益氣健脾行血之力。
2.3 養肝調情以解郁祛瘀 近年來,SSc患者神經系統受累備受關注。在345例SSc患者精神狀態研究中發現,焦慮抑郁在SSc患者中發生率明顯高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15]。本病患者常年焦慮抑郁易出現肝郁脾虛。肝主疏泄,調暢氣血津液運行輸布。肝氣郁結,瘀血加重。肝氣犯脾,脾失健運,精氣化生無源,五臟俱虛,惡性循環,疾病遷延難愈甚則加重;治療當從“肝”入手以疏肝解郁,養血健脾。《素問·六節藏象論篇》曰:“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為陽中之少陽,通于春氣……凡十一藏取決于膽也。”肝失疏泄則百病生,諸病治療勿忘疏肝。《醫貫·郁病論》曰:“予一方治其木郁,而諸郁皆因其愈,一方曰何?逍遙散是也。”
劉英教授以此為鑒,臨床運用柴胡疏肝解郁使肝氣得以調達;芍藥性酸苦,柔肝緩急;當歸養血活血。三藥同用,補肝體助肝用。配伍百合、玫瑰花調暢情志。《神農本草經》中記載百合性甘味寒,歸心、肺經,具有養陰清肺、清心安神之效。現代藥理學研究發現,百合具有豐富的藥理活性,對抑郁焦慮有顯著療效[16]。肝郁得疏,脾弱得復,情志暢達,則一身氣機順暢利于疾病的轉歸。
2.4 調和營衛以和營祛瘀 痹證多因外邪侵襲,擾亂營衛之氣致使衛郁營滯。《素問·痹論篇》云:“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澀,經絡時疏,故不通。”劉英教授在治療上常佐用風藥以調和營衛助氣血運行。風藥具有祛風除濕、活血化瘀、調和營衛之功。《圣濟總錄·皮痹》云:“治皮痹肌肉不仁,心胸氣促,項背硬強,天麻散方。”其組成為天麻、防風、麻黃、細辛等,體現出運用風藥治療SSc的理論依據。
劉英教授善用風藥麻黃調暢營衛之氣。部分醫家認為,麻黃為發汗峻劑,易傷津耗液損其正氣,應當禁用。其實不然,劉英教授反其道而行之。《神農本草經百種錄》言:麻黃,輕揚上達,無氣無味,乃氣味之最清者,能透出皮膚毛孔之外,又能深入積痰凝血之中,具有通清竅、通營衛、通三焦、通陽氣、通瘀痹、消癥瘕、通氣機之功用[17]。劉英教授運用麻黃開腠里使邪從表出,通營衛使氣血津液運行全身,通陽氣助余藥發揮藥性直達病所。但臨床使用需謹慎,忌大量使用,常用3~6 g。SSc患者正氣不足,以防發汗太過耗傷正氣,配酸甘之五味子收斂固澀。兩者相伍,散收相合而不削麻黃功用,臨床以3 g為宜。
2.5 靈活運用黃芪、積雪草 金代李杲所著《內外傷辨惑論》中“當歸補血湯”重用黃芪以補肺脾之氣,以此作為生血之源,為補氣生血之代表方。劉英教授治療SSc高度重視黃芪的使用。黃芪性微溫味甘,具有補氣升陽、固表止汗、利水消腫、生津養血、行滯通痹之功,居補氣藥首位,常與四君子湯同用以補氣健脾,助氣血化生,運化水濕。黃芪在本病中的作用不僅局限于補氣生血這一方面,而且在軟化皮膚方面效果甚佳。李存亮[18]認為,黃芪能增強細胞代謝,提高人體免疫力。針對硬皮病皮膚纖維化所擬定的“軟皮湯”,亦重視黃芪的使用[19]。《長沙藥解》云:黃芪“善達皮腠,專通肌表”。用藥劑量是否得當,直接影響藥效發揮。歷代醫家對于黃芪的使用常超過藥典規定劑量[20]。劉英教授對于黃芪用量的掌控具有獨到之處。對于皮膚硬化不明顯或皮膚腫脹者可用20 ~30 g;皮膚硬化較重,不能提捏可加至40 g;但對于皮膚細紋消失,毛發脫落,皮下組織鈣化較嚴重的患者,劉英教授根據患者身體情況逐漸加大黃芪的使用劑量,臨床最大可用至120 g,效果顯著。劉英教授認為,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炎癥反應,表現為紅細胞沉降率(ESR)加快,C反應蛋白升高。炎癥即為“熱毒”,應適當配伍清熱解毒類藥物。積雪草具有清熱利濕、解毒消腫的作用,常配伍30~40 g,順應張鳴鶴清熱解毒法治療風濕病的思維理論[21]。現代藥理研究發現,積雪草提取物積雪草苷具有抗纖維化、抗炎、抑制瘢痕增生、修復皮膚損傷的作用,除此之外具有一定抗抑郁作用[22],用于治療SSc可謂一舉多得。劉英教授常將黃芪、積雪草合用,以此減輕皮膚癥狀,提高患者生活質量。
3 臨證加減
SSc病情復雜,患者臨床表現各異,劉英教授在治療中將活血化瘀貫穿始終,她將疾病分為水腫期、硬化期、萎縮期。并在中醫辨證論治基礎上,根據各期特點及其兼證靈活加減相應藥物。
初期皮膚紅腫,觸之發熱。熱毒較盛者,加貫眾、土茯苓、蒲公英、金銀花、板藍根、白花蛇舌草等清熱解毒利濕。皮膚水腫無痛有緊繃感者,加車前子、豬苓利水滲濕。皮膚潰破疼痛明顯者,加乳香、沒藥活血止痛、消腫生肌。硬化期以血瘀為主,治療以益氣活血為要。后期兼有氣陰兩虛者,加太子參、黨參、麥冬等滋陰益氣。SSc日久不愈易累及肺臟出現肺間質病變,臨床癥狀以咳嗽、胸悶、氣急為主要表現,劉英教授常使用桔梗、瓜蔞、炒苦杏仁宣發肺氣“提壺揭蓋”;若兼有痰濕者,可加芥子、貝母、僵蠶、半夏、郁金、天花粉;伴有關節疼痛者,加藤類藥如忍冬藤、紅藤、大血藤以通利關節。
4 病案舉例
患者,女,45歲,2022年6月29日初診。以自覺雙臂及面部皮膚緊繃感,雙手遇冷刺激后變色并伴有刺痛加重3個月余為主訴。患者4年前因雨天道路積水步行回家,3 d后自感渾身發冷繼而出現指端腫脹疼痛,呈臘腸樣,面部皮膚出現無痛性非凹陷型水腫,在當地醫院就診,確診為SSc。口服羥氯喹0.2 g,每日2次;甲潑尼龍8 mg,每日1次,癥狀稍有緩解。近3個月加重,至今未進一步治療。刻下見:雙手指端皮膚蒼白疼痛,遇冷或情緒刺激后加重,雙臂及面部皮膚硬化嚴重,毛發脫落,皮膚甲錯,不能提捏并伴有緊繃感,呈“面具臉”,自覺吞咽困難,精神狀態較差,急躁易怒,無咳嗽,無口干,眼干,頸部僵硬不適,全身無關節疼痛,無口腔潰瘍,無皮疹,時有惡寒,平日乏力,活動后加重,納眠可,二便調,舌紫暗,苔薄白,脈沉弦細。輔助檢查:ESR 53 mm·h-1,ANA譜Scl-70(++)、抗核抗體1∶1000(+),血常規、血生化、抗環瓜氨酸肽抗體、補體C3、補體C4均為陰性。西醫診斷:系統性硬化癥。中醫診斷:皮痹,肝郁氣滯血瘀證。治法:益氣活血,疏肝解郁。方藥:雞血藤30 g、桃仁15 g、紅花15 g、當歸12 g、炙甘草6 g、茯苓15 g、人參6 g、白術12 g、升麻6 g、柴胡15 g、炒白芍15 g、川芎12 g、黃芪50 g、積雪草30 g、麻黃3 g、羌活9 g。
14劑,水煎服,每日1劑,早、晚2次溫服。西藥予甲潑尼龍4 mg,每日1次,口服;嗎替麥考酚酯0.25 mg,每日1次,口服。
2022年7月14日二診,患者自訴雷諾現象較前減輕,雙臂皮膚緩解,但面部皮膚仍有緊繃感,且皮膚甲錯,吞咽困難稍減輕,服藥期間情緒穩定,自感乏力減輕,可進行簡單日常活動,惡寒好轉,舌暗,苔薄白,脈沉細。予初診方去桃仁、紅花,加三棱12 g、莪術12 g、蜈蚣1條。西藥繼服。
2022年8月15日三診,患者皮膚癥狀均較前改善,緊繃感消失,可適度提捏,吞咽困難好轉,其他諸癥均好轉,舌暗,苔薄白,脈緩。復查血常規、血生化均為陰性,ESR 26 mm·h-1。上方去蜈蚣,黃芪減至30 g,三棱、莪術減至9 g。西藥停嗎替麥考酚酯,甲潑尼龍4 mg、2 mg交替服用。
2022年11月20日四診,查血常規、血生化均無異常,ESR19 mm·h-1,病情穩定,皮膚硬化好轉,雷諾現象好轉,患者自述可正常生活。此后中藥在三診方基礎上加減后繼服。停甲潑尼龍。
按語:本例患者4年前有受涼史,正氣過度虧耗,風寒濕外邪入里,阻滯經絡,瘀血漸成。早期出現手指腫脹,面部皮膚非凹陷性水腫。單純西藥難治其本,致使瘀血漸成,正氣難以抗邪,疾病加重。初診時根據刻下癥狀結合輔助檢查,西醫診斷為SSc,中醫診斷為皮痹。根據患者肌膚甲錯,急躁易怒,乏力且活動后加重,舌紫暗,脈沉弦細,辨證為肝郁氣虛血瘀證。劉英教授組方上以活血化瘀為核心,方中配伍雞血藤、桃仁、紅花,三藥活血化瘀而不傷正,使瘀血除,經絡通,氣血津液暢行全身,肌膚得以充養;柴胡疏肝解郁;白芍養血斂陰,當歸補血活血,兩者配伍養血活血之力更著;加活血行氣之川芎,補血而不滯血,茯苓健脾寧心;陳皮理氣健運。共奏疏肝解郁、養血健脾之功以解郁祛瘀。加人參、白術益氣健脾,扶正固本取四君子湯之義扶正祛瘀。再入黃芪50 g補氣生血,改善皮膚狀態;與清熱利濕、解毒消腫之積雪草相配,共奏軟化皮膚之力,為劉英教授治療皮膚硬化常用藥對。配伍風藥麻黃解表宣肺,調和營衛,使邪從表走,肺氣得宣,營衛調和,氣血運行順暢。二診時諸癥雖有明顯好轉,但瘀象仍然較重,可見常規活血化瘀藥力量不足。將桃仁、紅花易為三棱、莪術以破血逐瘀,加蜈蚣1條,增強其走竄之性,動靜結合,加大化瘀力度。三診時患者癥狀明顯好轉。
5 結 語
隨著臨床上SSc患者逐漸增多,單純西藥治療效果差且不良反應大,中醫藥治療確有療效。劉英教授在活血化瘀的基礎上,兼顧健脾益氣、養肝調情、調和營衛3個方面助化瘀血,堅持活血化瘀貫穿疾病治療始終。在中醫辨證論治,四診合參的基礎上,針對不同兼證合理配伍藥物。堅持一人一套治療方案,將中醫優勢最大化。希望運用中醫思維體系為本病治療提供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 白雨,王紅.硬皮病的中西醫外治療法研究進展[J].中國醫藥科學,2023,13(7):63-66.
[2] 李滿意,劉紅艷,陳傳榜,等.皮痹的證治[J].風濕病與關節炎,2020,9(8):59-63.
[3] 王瑞潔,姜文琦,張潤田,等.從《黃帝內經》痹證理論探討硬皮病的病機與治療[J].世界中醫藥,2023,18(2):224-228.
[4] 吳德鴻,李正富,范永升.范永升教授治療硬皮病經驗[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5,30(6):1990-1992.
[5] 張超,李大可.周翠英教授治療硬皮病經驗[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8,7(6):46-48,56.
[6] 劉欣蔚,徐佳,王萍.張志禮治療硬皮病臨證經驗[J].中華中醫藥雜志,2022,37(3):1521-1523.
[7] 文維農,姚欣艷,劉侃,等.國醫大師熊繼柏運用補陽還五湯合得效方治療硬皮病經驗[J].中醫藥臨床雜志,2021,33(6):1040-1043
[8] 朱梓波,吳夢麗,劉振雄,等.禤國維“溫通”法治療系統性硬皮病經驗[J].陜西中醫,2021,42(11):1598-1600.
[9] 李巧紅.桃仁紅花煎抗血小板聚集及改善血液流變實驗研究[J].亞太傳統醫藥,2016,12(9):14-15.
[10] 蔡念寧.張志禮治療硬皮病經驗[J].中醫雜志,2002,52(9):657-658.
[11] 汪曉河,馬明華,張婧婷,等.中藥夏枯草藥用概況[J].中國現代應用藥學,2019,36(5):625-632.
[12] 黃禮闖,趙夢亭,桑夏楠,等.三棱-莪術藥對化學成分及藥理作用研究進展[J].中華中醫藥雜志,2021,36(11):6612-6616.
[13] 熊英瓊,程紹民,劉端勇,等.全蝎蜈蚣在痹病治療中的應用思路[J].遼寧中醫雜志,2011,38(4):793-795.
[14] 王蕾,屠文震.屠文震從瘀論治系統性硬化癥的理論與經驗[J/OL].遼寧中醫雜志.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1.1128.R.20230406.0921.004.html.
[15] JEWETT LR,RAZYKOV I,HUDSON M,et al.Prevalence of current,12-month and lifetime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mong patients with systemic sclerosis[J].Rheumatolo(Oxford),2013,52(4):669-675.
[16] 張穎,陳宇霞,陳朝,等.百合抗抑郁的應用和研究現狀[J].醫學綜述,2016,22(17):3438-3440.
[17] 張曉樂,程發峰,李婷,等.基于通法理論探析仲景麻黃應用[J].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22,45(12):1230-1235.
[18] 李存亮.淺談黃芪的特殊功效[J].內蒙古中醫藥,2005,24(S1):33-34.
[19] 張曉岑,段行武.中醫治療硬皮病最新研究進展[J].中國中西醫結合皮膚性病學雜志,2016,15(3):191-193.
[20] 曲圣元,崔炳南,楊佼.大劑量黃芪在皮膚科的應用[J].中醫學報,2022,37(8):1606-1610.
[21] 曹培晨,付新利.張鳴鶴教授清熱解毒法論治類風濕關節炎[J].吉林中醫藥,2022,42(11):1269-1272.
[22] 秦慧真,林思,鄧玲玉,等.積雪草苷的藥理作用及機制研究進展[J].中國藥房,2021,32(21):2683-2688.
收稿日期:2023-11-01;修回日期:2023-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