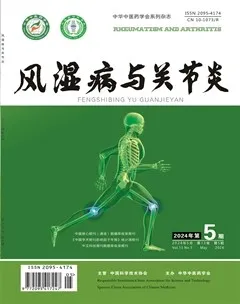基于“腎虛、痰濕、血瘀”的現代生物學基礎探討強直性脊柱炎中醫病機的科學內涵
王思遠 阮藝濤 陳進春 邱明山
【摘 要】 強直性脊柱炎的中醫病機關鍵是腎氣虧虛,痰濕、血瘀為主要的致病因素。通過將現代生物學與中醫病因病機相聯系,得出導致強直性脊柱炎發病的腎虛、痰濕、血瘀的微觀辨證特征,是涉及干細胞生成、水液代謝、血脂代謝、炎癥反應、免疫調節及血液流變學改變等多個病理變化的復雜過程,適用于中醫多靶點、多系統的整體研究。將現代生物學與中醫病因病機相聯系,有助于認識疾病發生、發展機制,從多個方面闡明中醫病機的科學內涵,為強直性脊柱炎的臨床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關鍵詞】 強直性脊柱炎;腎虛;痰濕;血瘀;病因病機;微觀辨證;現代生物學
強直性脊柱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是以骶髂關節和脊柱慢性炎癥為特征的風濕病,可造成關節軟骨、骨質等組織結構和功能損傷導致生活質量下降[1]。AS起病緩慢,其患病率約為0.08%~0.35%,發病年齡15~35歲,男女患病比例為3∶1~4∶1。風濕病的基本病因病機多為“虛邪瘀”[2],國醫大師朱良春[3]認為,AS多以腎督虧虛為本,邪氣不去,痰濁瘀血留滯為標,痰瘀互結,纏綿不愈,久之骨髓空虛,背部傴僂,筋骨拘迫,甚至癱瘓在床。臨床上常將AS主證分為腎虛督寒證、陰虛督虧證,兼證分為寒濕證、濕熱證、痰瘀證[4]。故本文著眼于“腎虛、痰濕、血瘀”的現代生物學基礎探討AS的中醫病機,以期為AS的辨證論治提供科學的理論基礎。
1 AS“腎虛”的中醫病機理論
中醫學并無AS病名的記載,根據其發病及臨床表現,歷代醫家對本病的中醫命名有痹證→歷節→竹節風→尪痹→大僂、僂痹[5]。現代醫家焦樹德[6]將其命名為“大僂”,也是目前被普遍認可的中醫病名。《黃帝內經》云:“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又云:“骨痹不已,復感于邪,內舍于腎,是為腎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說明正氣不足,陽氣虧虛為主要內因,加之感受寒邪,內外合邪發為疾病。《脈經》云:“督之為病,脊強而厥。”督脈主要分布于人體后正中線上,為陽脈之總督,腰為腎之府,腎經貫脊屬腎絡膀胱,若腎虛寒濕侵入機體,腎氣不足,督脈失養,故發為頸項強直,脊強反折,腰背不能俯仰,并借其循行之利,進而出現雙目干澀,枕部疼痛,髖、膝、踝、足跟部位疼痛等關節外表現。中醫學認為,肝主筋、腎藏骨,其虛者應責之肝腎不足,若局部冷痛或腫痛,亦可因寒濕、濕熱或腎陽不足所致,若疼痛固定日久,久病成絡,其血瘀證亦兼而發之。《壽世保元》曰:“男子以氣為本,女子以血為本。”男子以腎為先天,以精氣為本,張錫純指出:“腎虛者,其督脈必虛,是以腰痛。”故AS發病傾向于男性。腎藏精,為先天之本,對于大僂的病機,多數醫家將其歸為先天稟賦不足加之后天失養,肝腎虧虛,腎陽虛衰,邪氣侵襲,正不勝邪,筋骨失養,則發為大僂。焦樹德[6]認為,腎督陽虛為內因,寒邪入侵為外因,寒邪內生,陽氣不化,乃成大僂。閻小萍[7]繼承焦樹德的臨床經驗,提出AS為腎督正氣不足,風寒濕熱諸邪侵入腎督所致。沈丕安[8]創新性地提出AS病機為本虛標實,腎虛為本,風寒濕熱痰瘀毒七邪為標。AS發病主要在于腎元虧虛,而復感于邪,腎元虧虛乃發病之本。
1.1 AS“腎虛”中醫病機的現代生物學基礎
1.1.1 腎精的西醫學本質 馬迎民等[9]將腎精或干細胞的動態演變和主要功能進行研究,發現干細胞具有先天之精的特性,干細胞屬于一類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潛能的未分化或低分化細胞,其中自我更新主要是蛋白質的更新,以及分裂產生新細胞和舊細胞的凋亡。染色體DNA序列包含著個體發育產生的遺傳信息和其他各種生命現象。有學者發現,“腎藏精”的生物功能可以激活內源性干細胞及發揮微環境的調和狀態,同時調控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的動態平衡[10]。相關研究表明,腎為先天之本,且與遺傳密切相關,這與表觀遺傳學機制體現的動態觀和整體觀有異曲同工之妙[11]。腎主骨生髓,隨著人們對維生素D的深入認識,諸多學者發現維生素D的內分泌調控系統與“腎藏精”的現代功能高度吻合[12]。腎臟可分泌促紅細胞生成素(EPO),增加造血原料,同時EPO也可促進成骨分化,減少骨吸收,對骨組織的形成具有正性作用。這也與“腎生骨髓”理論不謀而合,此外骨髓是人體的中樞免疫器官,T淋巴細胞和B淋巴細胞都是源自骨髓的多能干細胞,因此中醫的“腎精”與免疫細胞的來源相關[13]。中醫“腎藏精”理論與現代生物學有機結合,可以從干細胞、微環境、遺傳學等多方面揭示從腎論治的科學內涵。
1.1.2 AS“腎虛”理論與現代生物學研究 當機體出現“腎虛”的證候特征時,干細胞、基因、維生素D和EPO等被認為是腎精生物學基礎的物質將發生改變。“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正氣具有抵御外邪、維持自身生理穩定的能力,這與西醫學免疫系統的三大功能防御、自穩、監視相吻合,正氣的產生從本質上來說源于先天腎氣,同時需要后天的補養,腎氣的虛衰影響正氣的虧虛,在HLA-B27和某些特定的遺傳背景(腎元虧虛)下,機體對某些病原體及抗原成分(邪氣)的清除能力下降,從而誘發機體產生過度免疫反應,造成關節、脊柱、附著點等部位的炎癥性改變。近年來,表觀遺傳學在AS的研究中越來越受到關注,AS相關基因組位點的異常表觀遺傳修飾,如DNA甲基化、組蛋白修飾、microRNA等。AS的嚴重程度、臨床表現和治療效果也存在著性別差異,男性患病率較高,這可能與遺傳、免疫和生活方式的差異(如吸煙、飲食)有關。HE等[14]通過氣相色譜-質譜揭示AS的性別特征,男性代謝組比女性更容易受到AS影響。BERNABEU等[15]研究常見復雜性狀和疾病遺傳病因的性別差異,觀察到AS的性別差異和高度遺傳性是一個全基因組的顯著基因型,其主要與骨骼肌組織中MHC Ⅰ類多肽相關序列A基因的性別差異表達相關,性別與AS發病風險相互作用。梁偉東等[16]研究發現,腎虛督寒型AS的病理機制可能與能量代謝、脂類代謝、氨基酸代謝、胃腸道菌群和免疫紊亂等代謝異常相關。孫文婷[17]研究發現,補腎強督法可以調控Wnt通路關鍵蛋白DKK-1的表達。AS患者脊柱的病理變化以成骨改變和溶骨性骨破壞為主要特征,間充質干細胞、成骨細胞和破骨細胞等骨細胞與T細胞、B細胞等免疫細胞相互作用,共同介導AS的發病[18]。張磊等[19]發現,AS患者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維生素D缺乏,在疾病早期會出現骨量減少或骨質疏松,進而導致微循環改變。維生素D在免疫反應失調和骨骼重塑改變中都有作用,其代謝受損可能是AS發病的原因。有研究者在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中,尤其是在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上找到大量與腎虛相關的活性成分及相互作用的依據[20]。可以推測出DNA甲基化、維生素D及HPA軸的改變可能導致AS出現免疫失衡及炎癥細胞因子的分泌,最終使機體出現一系列腎虛證的表現。
2 AS“痰濕、血瘀”的中醫病機理論
有研究表明,AS患者痰濕體質比例較高[21],究其原因是患者腎氣虧虛,腎陽不足,氣血津液運化失常而致痰濁、瘀血內生,阻滯筋骨,壅滯督脈,不通則痛,則出現各脊柱節段及腰背部的疼痛、僵硬及活動受限,即所謂“至虛之處,便是容邪之所”。風寒濕邪日久留滯筋骨關節,阻滯血脈,津澀血凝,故為痰瘀,若積聚日久,五臟虧損,疾病膠著不化,纏綿難愈,而成頑痹,則肢體拘攣,脊背彎曲,日久脊柱融合強直畸形、功能障礙。正如《類證治裁·痹論》云:“久而不痊,必有濕痰敗血瘀滯經絡。”AS起病緩慢而隱匿,早期癥狀多是慢性下腰痛,常感覺在臀部或骶髂區深部的鈍痛,靜息時疼痛加重,輕度活動后緩解,這與中醫學中濕邪重濁黏滯類似。濕為陰邪,易阻滯氣機,損傷陽氣,故腎督陽氣失于溫煦,運行受阻,則循行部位經脈肌肉僵滯疼痛。外邪侵襲,水濕運行不暢,濕聚成痰;或濕邪久滯不去,化熱傷津,耗傷陰液,煉液成痰。痰濕阻滯經絡,氣血運行不暢,痰濁、瘀血內生,痹阻經絡,膠著于經髓骨骱,導致韌帶鈣化,關節活動度降低,甚至強直變形。而致痰濕的病邪最易損傷脾臟,脾多夾濕,內外濕邪夾雜,故出現厭食、倦怠或乏力等表現。故腎氣虧虛為發病之本,痰、瘀之邪是主要的致病因素也是病理產物,貫穿疾病始終。
2.1 AS“痰濕、血瘀”中醫病機的現代生物學
研究
2.1.1 “痰濕、血瘀”的西醫學本質 近年來研究表明,痰濕的病理學特點主要與水液代謝、血脂代謝、物質能量代謝、炎癥反應和免疫調節等異常有關,與現代生物學中的氨基酸、葡萄糖、脂類化合物的代謝水平和基因組學密切相關,蛋白質、糖、脂質等代謝產物可作為診斷痰濕證的客觀指標[22]。痰濕體質人群處于慢性低度炎癥狀態,表現為炎癥細胞因子產生異常和炎癥信號通路被激活[23]。痰濕證血脂水平和炎癥細胞因子如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細胞介素(IL)-6、IL-1β、單核細胞趨化蛋白-1的表達水平顯著升高[24],這表明痰濕與免疫紊亂有關,細胞因子網絡紊亂是痰濕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有學者指出,痰濕證患者免疫細胞異常,其中T淋巴細胞亞群CD3、CD4、CD4/CD8比值均降低,CD8升高,提示痰濕證患者T細胞免疫功能降低[25]。AS患者血清中IL-17和IL-23水平較高,小關節中存在IL-17+細胞,發病多與IL-17和IL-23軸的紊亂以及調節CD4+或CD8+ T淋巴細胞活化和分化的基因異常有關,多數免疫細胞和細胞因子參與了AS的發病機制[26]。
高血脂為痰濕的病理物質,血漿脂質即為“微觀之痰”,高血脂所化生的“痰”,必然引起血液黏稠度增高,血漿流動性下降,血管內皮細胞損傷,凝血功能亢進,這是由痰致瘀的重要病理基礎。此外,血瘀證患者微循環障礙,血液流變學改變,血液淤滯,造成組織缺血缺氧,引起細胞脂膜代謝失衡,脂肪堆積。從微觀層面論述了“痰、瘀”的病理變化,同時說明了瘀血加重痰濕的演變過程。研究表明,細胞色素P450 2C11、環氧化物水解酶1、補體因子B、激肽原1、纖維蛋白原γ、纖維蛋白原α和纖維蛋白原β可作為血瘀證的標志性蛋白[27]。炎性因子如C反應蛋白、IL-6、TNF-α、黏附分子均與血瘀證密切相關,炎癥反應在血瘀證的發生、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28]。血瘀與炎癥反應、血管內皮功能紊亂、微循環障礙、血液流變學改變及凝血功能等存在相關性。
2.1.2 AS“痰濕、血瘀”理論與現代生物學 濕邪致病主要病位在脾,脾失健運,機體會產生腹部脹滿,大便次數增加,糞便稀溏等癥狀,腸道蠕動增加,刺激腸道微生物群中的雙歧桿菌產生醋酸及乳酸,導致腸道菌群結構和功能紊亂,失調的腸道菌群也可能通過參與免疫反應,而致內濕發病,這是痰濕致病的相關病理因素[29]。在代謝組學研究方面,AS患者處于腸道微生態失調狀態,相比炎癥性腸病更為明顯[30]。BERLINBERG等[31]依據色氨酸及其代謝物在免疫功能中的作用,發現吲哚-3-乙酸酯是腸道微生物組潛在影響AS發展的一種機制。ZHOU等[32]證明賴氨酸、脯氨酸、丙氨酸、絲氨酸與臨床指標(如BASDAI、ASDAS和BASFI)之間存在相關性;且嚴重活動性患者血清中乙酸鹽、乳酸和苯丙氨酸水平升高,甘油磷酸膽堿、谷氨酰胺、肌酸、甲硫氨酸和肌酸酐水平降低。YU等[33]采用液相色譜-串聯質譜分析發現,參與抗原加工和呈遞(HSP3AB90、HSP1AA90和HSPA1)、血小板活化(包括ITPR6、MYLK和STIM1)和白細胞跨內皮遷移(包括MYL10A、MYL12和ROCK9)的關鍵蛋白揭示了AS患者的免疫調節異常。這些蛋白質可用作AS診斷和治療靶點的候選標志物。許多與血液相關的過程可能導致慢性炎癥性疾病的血栓前傾向,這與白細胞相互作用和促炎細胞因子的形成密切相關,其中包括血小板含量增加、低水平血小板活化、血管內皮細胞激活和凝血活性增加[34]。
在中醫證候研究方面,馬琳[35]發現,寒濕痹阻型和瘀血痹阻型AS患者血清IL-23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趙鐵等[36]發現,AS濕熱證患者血清中溶血甘油磷脂酰膽堿、甘油磷脂酰膽堿、甘油磷脂酰乙醇胺、甘油三酯等諸多脂質組分顯著降低,表明氧化應激及脂質代謝異常可能與AS濕熱證的實質密切相關。王苗苗等[37]發現,AS寒濕痹阻證發病及病理變化與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弗林蛋白酶、血管內皮鈣黏蛋白、激肽原1、血管緊張素原等蛋白相關。孫志嶺等[38]研究發現,濕熱痹阻證的病理過程可能與Fibulin-1、二肽基肽酶1、激肽原1、IL-17F突變型、甘露糖結合蛋白C等差異表達蛋白相關,濕熱痹阻證總體表現傾向于炎癥免疫的增強、細胞增殖以及補體活化通路的參與。目前對于AS患者痰濕證或血瘀證的客觀化指標研究較多,但對于痰濕證或血瘀證體質的微觀辨證及現代生物學研究偏少,今后還需要大量循證醫學證據。
3 小結與展望
AS的病機多虛實夾雜,腎元虧虛為發病之本,痰濕、血瘀之實邪為主要的致病因素。腎虛、痰濕及血瘀導致AS發病是一個涉及干細胞生成、水液代謝、血脂代謝、炎癥反應、免疫調節及血液流變學改變等多個病理變化的復雜過程,故適用于中醫多靶點、多系統的整體研究。從當前的研究來看,組學技術結合中醫證型的研究偏少且深度不夠,難以與生物學中的靶點一一對應,尚不能揭示中醫“證”的本質。但將現代生物學與中醫病因病機相聯系,有助于認識疾病發生、發展機制,從多個方面闡明中醫病機的科學內涵,并從整體水平評估中醫本質的客觀化,為AS的臨床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參考文獻
[1] BRAUN J,SIEPER J.Ankylosing spondylitis[J].Lancet,2007,369(9570):1379-1390.
[2] 婁玉鈐,婁高峰,婁多峰,等.基于“虛邪瘀”理論的風濕病學科體系建立及相關研究[J].風濕病與關節炎,2012,1(1):10-15.
[3] 蔣恬,朱婉華.國醫大師朱良春“益腎蠲痹法”治療強直性脊柱炎經驗[J].北京中醫藥,2022,41(8):844-846.
[4] 徐然,紀偉.強直性脊柱炎中醫證型的優化及臨床指標相關性研究[J].風濕病與關節炎,2023,12(2):18-22.
[5] 李彥,孟祥震.強直性脊柱炎的中醫溯源考析[J].浙江中醫雜志,2021,56(4):297-299.
[6] 焦樹德.“大僂”芻議[J].中國中醫藥信息雜志,2000,7(6):1-3.
[7] 楊永生,劉瓊,王紅梅,等.閻小萍教授基于治未病理論從腎督虧虛論治強直性脊柱炎的經驗[J].風濕病與關節炎,2021,10(8):43-46.
[8] 徐靜雯,何文姬,胡燕琪,等.名老中醫沈丕安補腎壯督法辨治強直性脊柱炎經驗[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20,29(7):736-739.
[9] 馬迎民,徐德成,范吉平.中醫“腎精化生元氣和臟腑之氣”的現代醫學機制[J].中醫雜志,2016,57(12):1000-1004.
[10] 鄭洪新,王擁軍,李佳,等.“腎藏精”與干細胞及其微環境及NEI網絡動態平衡關系[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2,27(9):2267-2270.
[11] 王重一,鄧洋洋,高巳東,等.試論腎藏精主骨為先天之本與表觀遺傳學的關系[J].中國中醫藥現代遠程教育,2023,21(7):56-58.
[12] 管連城,張孟之,王宗陵,等.基于維生素D缺乏與腎虛證的相關性探討補腎抗衰老機理[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9,25(6):766-768,837.
[13] 陳立,王小琴.促紅細胞生成素為腎藏精理論主要物質基礎之一[J].中華中醫藥學刊,2017,35(3):537-540.
[14] HE Z,WANG M,LI H,et al.GC-MS-based fecal metabolomics reveals gender-attributed fecal signatures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J].Sci Rep,2019,9(1):3872-3880.
[15] BERNABEU E,RAWLIK K,CANELA-XANDRI O,et al.
Reply to:Genotype by sex interactions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J].Nat Genet,2023,55(1):17-18.
[16] 梁偉東,彭劍虹,尹曉霞,等.基于代謝組學分析腎虛督寒型強直性脊柱炎代謝網絡特點[J].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2021,38(6):1124-1132.
[17] 孫文婷.補腎強督方通過lncRNA H19/miR-22/Wnt通路干預人骨髓間充質干細胞成骨機制的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21.
[18] LIU L,YUAN Y,ZHANG S,et al.Osteoimmunological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ankylosing spondy-
litis[J].J Cell Physiol,2021,236(9):6090-6100.
[19] 張磊,高照猛,于春艷,等.維生素D與強直性脊柱炎患者甲襞微循環形態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骨質疏松雜志,2020,26(1):64-69.
[20] 壽旗揚,張利棕,蔡月琴,等.Lewis大鼠腎陽虛體質及其HPA軸功能失衡[J].中國比較醫學雜志,2015,25(9):8-13,38.
[21] 錢佳麗,余毅,毛盈穎,等.強直性脊柱炎家系流行病學調查和中醫體質分析[J].中華中醫藥雜志,2017,32(12):5599-5602.
[22] 任爽,劉妍彤,張杰.痰濕現代醫學本質述析[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21,27(9):1515-1518.
[23] 鄭璐玉.痰濕體質人群炎癥相關機制研究[D].北京:北京中醫藥大學,2013.
[24] 喻松仁,張一文,華詩培,等.基于脂肪細胞自噬探討溫膽湯干預肥胖痰濕證炎癥狀態的作用機制[J].中華中醫藥學刊,2022,40(1):14-18,259.
[25] 王斌,嚴燦.濕阻證患者免疫調節功能改變的臨床研究[J].新中醫,2005,37(8):15-16.
[26] ZHU W,HE X,CHENG K,et al.Ankylosing spondyli-tis:etiology,pathogenesis,and treatments[J].Bone Res,2019,7(1):22-37.
[27] 胡廣,李瑛,楊會珍,等.基于蛋白質組學探討慢性血瘀證大鼠的發病機理[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22,28(11):1796-1801.
[28] 馬曉娟,殷惠軍,陳可冀.血瘀證與炎癥相關性的研究進展[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07,27(7):669-672.
[29] 聞向暉,劉秋萍,余怡然,等.內濕致病與腸道菌群失調的關系[J].中醫雜志,2018,59(16):1377-1379.
[30] WEN C,ZHENG Z,SHAO T,et al.Quantitative metagenomics reveals unique gut microbiome biomarkers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J].Genome Biol,2017,18(1):142-154.
[31] BERLINBERG A J,REGNER E H,STAHLY A,et al.
Multi omics analysis of intestinal tissue in ankylosing spondylitis identifies alterations in the tryptophan metabolism pathway[J].Front Immunol,2021,12(1):587119-587131.
[32] ZHOU Y,ZHANG X,CHEN R,et al.Serum amino acid metabolic profiles of ankylosing spondylitis by targeted metabolomics analysis[J].Clin Rheumatol,2020,39(8):2325-2336.
[33] YU Z,HONG X,ZHANG X,et al.Global proteomic analyses reveals abnormal immune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new onset ankylosing spondylitis[J].Front Immunol,2022,13(1):838891-838899.
[34] BEINSBERGER J,HEEMSKERK JW,COSEMANS J M.Chronic arthrit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altered blood parameters give rise to a prothrombotic prope-
nsity[J].Semin Arthritis Rheum,2014,44(3):345-352.
[35] 馬琳.強直性脊柱炎患者炎癥和骨代謝細胞因子的表達及其與中醫證型的相關性研究[D].石家莊:河北醫科大學,2012.
[36] 趙鐵,殷婷婷,張英澤,等.基于代謝組學的強直性脊柱炎和痛風性關節炎濕熱證共性特征研究[J].中醫雜志,2013,54(7):592-596.
[37] 王苗苗,王玲,王富強,等.強直性脊柱炎寒濕痹阻證血清蛋白質組學研究[J].中國中醫骨傷科雜志,2015,23(12):9-11.
[38] 孫志嶺,徐驍,王玲,等.強直性脊柱炎濕熱痹阻證血清差異蛋白組學研究[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15,31(5):412-415.
收稿日期:2023-11-12;修回日期:2023-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