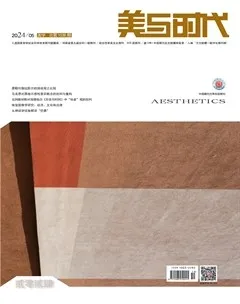新力量導演的創作分化及風格探析


摘? 要:新力量導演作為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的主力軍,面對多元文化圈層與龐大的電影市場,在電影工業美學的支撐下,愈加顯現出對電影工業與電影美學的駕輕就熟。青年導演的接續涌現與創作的不斷成熟,使得這一群體近年來在風格探索上漸呈分化之勢。無論是堅持市場化導向與類型化探索的商業片導演的市場性創作,還是兼顧現實關照與商業訴求的文藝片導演的社會性創作,抑或是傳遞自我生命體驗與詩意的藝術片導演的地域性創作,都在從集體性表達漸趨向個人風格探索過渡。
關鍵詞:新力量導演;創作;分化;風格
“代際導演”作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電影史論范式,未經官方認證卻能夠長時間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參照。從第一代導演的拓荒,到第六代導演的各自探索,反映了電影在中國不斷成熟的發展歷程。而作為“接棒”的一代,新力量導演又成為當下中國電影研究的重要對象。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全面小康社會的逐步建成,電影產業在經濟驅動下得到了勃發。在21世紀的互聯網語境下,新的消費社會與多元文化圈層不斷形成,電影越來越成為觀眾精神文化消費的重要選擇,而作為創作主體的導演則從高校學院派漸漸轉變為身份多元的群體。
《“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提出:展望2035年,我國將建成電影強國,中國電影實現高質量發展……以國產影片為主導的電影市場規模全球領先,電影產業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完善,培養造就一批世界知名的電影藝術家,中國電影在世界電影格局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大幅提升[1]。新力量導演作為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的主力軍,無論是多樣性的創作特點,還是現實性的主題傳遞,亦或是超越性的審美選擇,無疑都成功地開創了國產電影的新層次。但緣于官方的命名與扶持,依然缺乏題材類型多樣、表現手法新奇的電影,其作品難以在世界電影格局中具有廣泛影響力,同時高票房幻象之下是IP濫用、粉絲強撐的創作疲沓現實。由此觀之,新力量導演的內部分化不論是在創作實踐方面還是在美學價值層面都十分值得深入研究。
一、新力量導演群體的崛起與趨變
指涉含混的中國電影新力量這一概念,在新力量導演的創作實踐中慢慢明朗起來。自2014年國家廣電總局推介后,新力量導演在規模上慢慢容納新人而逐漸發展壯大,在多維創作中走向風格的成熟。在中國電影工業體系不斷完善的背景之下,新力量導演群體內部的美學風格在新的電影工業美學的生成中以及新的電影創作觀念的更新下,漸呈分化之勢。
(一)概念的生發與溯源
“新力量導演”這一說法首次出現在《當代電影》期刊2013年第8期的“本期焦點”版塊,由于當年多部由新人導演的青春、都市題材的電影火爆出圈,并通過票房與口碑的持續發酵而引起觀眾與學界關注。隨后,由電影局主導的“2014中國電影新力量推介盛典”推介出陳思誠、李芳芳、肖央、韓寒、郭敬明、郭帆、鄧超、田羽生、路陽等青年導演,“新力量導演”被國家媒體“命名”[2]。此后,廣電總局連續多年舉辦“新力量導演論壇”,不斷加大了對青年導演的扶持與培養力度。隨后便不斷涌現出如畢贛、文牧野、忻玉坤等有才華的新人導演,群體實力發展壯大,于是“新力量、新世代”等關于這一導演群體的命名頻頻出現于各種研究文章中。
2018年,在長春舉辦的第四屆“中國電影新力量論壇”,使業界與研究界對這一群體達成統一認知。他們將新力量導演群體及其創作置于中國電影產業化的進程中,研究范圍也覆蓋到整個中國電影產業鏈。但這批新人始終處于被官方命名卻無法通過群體性崛起而“正名”的窘境,由觀眾、導演、編劇、制片等多種角色與身份組成的電影新力量,構成了當下中國電影市場創作與消費主體。
(二)群體的辨析與厘定
顏純鈞認為,中國電影新力量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后,參與者從導演擴散到編劇、演員、出品人、制片人、監制、學者等電影界人士[3],使由官方所主導、媒體所命名的中國電影新力量成為一個概念含混的群體。王一川則更傾向于從宏觀層面進行概括,對“中國電影新力量”作出另一種解釋,即中國電影發展中的諸多“新興元素”的集合體也較有影響力。各學者對中國電影新力量或是新力量導演的定義不同,但都承認其作為新世紀以來的新生代創作主體所具有的特殊指涉意義。
新力量導演并非傳統意義上的代際劃分群體,他們與前輩們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師承關系,也沒有幾近同層的自然生理年齡和共同的生命體驗[4],但他們在互聯網語境下依托中國電影工業的成熟與完善,使電影趨向成為現代藝術、現代商業、現代工業相互融合的藝術產品。他們在創作中融入自我表達與生命體驗,關注當下社會現實,用影像來書寫人情與人性,用鏡頭來描摹社會與情感。而這一群體內部在近年尤其是在后疫情時代以來出現分化,在電影創作中隱去了集體性特征,著力探索新穎形式來呈現個人與觀眾共通的審美觀念和情感訴求,從而不斷形成各自的風格。
(三)創作分化與風格偏向的成因
新力量導演群體大多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才首執導筒,成為新人導演。他們幾乎是輕松瀟灑、游刃有余地在票房和口碑等多方面實現多贏,能夠處理好市場要求同個人風格表達等方面的矛盾,游走于電影工業與美學的二元對立之中[5]。但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電影工業體系的完善以及電影創作觀念的更新,這批青年導演在多年的創作實踐中愈發成熟而形成內部的分化之勢,在獲得商業投資后便朝著視聽的極致呈現、社會現實的赤裸批判與生命經驗的感性傳達等美學探索各自偏向。
1.電影工業美學在全面小康社會建設中不斷完善。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建成全面小康社會為國家及社會的整體奮斗目標,而文化產業得到大發展則是其中的重要一環。中國經濟實力的逐年增長,作為文化產業的電影發展也勢頭正盛。伴隨著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中國電影產業化進程加速,電影工業體系日趨完善,“中國式大片”再次以震撼視聽激發大眾共鳴。追求極致視聽呈現、多元類型融合以及商業性與藝術性均衡的電影工業美學,也在導演們不斷的創作實踐中與觀眾和市場相勾連,形成當下中國電影創作的內在肌理與美學支撐。所以,電影新力量的大眾化、娛樂化傾向,與小康社會建設和幸福指數提高的時代總體特征是具有同步性的[6]。
2.電影創作觀念在互聯網語境下不斷更迭。從早期單一的的影視改編到繁雜多樣的跨媒介敘事,這一變化成為當下電影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新力量導演成長并創作于互聯網時代,在這一背景下,通過電影與網絡文學、漫畫、游戲等其它具有粉絲基礎的媒介進行聯動融合,能夠較為容易獲得市場與受眾關注,仙俠玄幻、恐怖懸疑、浪漫喜劇等題材的電影愈加契合當下主要觀影人群的審美取向。而這種架空的題材、戲劇化的風格、游戲性的敘事以及奇觀性的視聽呈現,都體現了電影工業美學下跨媒介敘事的優勢。主要觀影人群從一二線城市向中小城市的青年聚集后,新力量導演群體的電影創作觀念、價值取向、審美趣味等方面也在實踐中做出了相應改變。
3.電影發行放映方式在后疫情時代漸趨流媒體化。2018年后經濟下行遭遇影視寒冬,2020年后的電影產業在疫情反復中元氣大傷,影院關門、影業停工常態化出現。與此同時,大眾的消費心理、消費能力與電影產業的制作、發行、放映、營銷方式等都在后疫情時代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如2020年春節檔,由徐崢導演的《囧媽》以“院轉網”的發行模式打破了當下主流的電影公映窗口期與付費模式,此后許多院線電影也由于疫情反復而轉為國內各大線上流媒體平臺發行。從傳統影院觀影到流媒體平臺觀看,內容時長并未改變,但觀影方式卻從公共空間轉向私人領域,觀影行為也從強制性轉變為隨意性,這意味著從攝制到發行放映,電影的主創人員必須對“小屏碎片化”、流媒體化的播映方式做一番考量。
二、新力量導演群體的創作分化
在消費主義盛行、商業氣氛濃重的當下中國電影市場,可以看到各種題材類型的電影活躍于銀幕與觀眾視野,這既豐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傳遞了導演的個人感知。在這之中,既有得力于資本的商業片導演關注受眾喜好進行的市場性創作,也有能夠均衡電影的商業性與藝術性的文藝片導演關照社會現實進行的社會性創作,還有不斷探索新表達的藝術片導演在熟悉的家鄉進行的地域性創作,這些創作都極大地豐富了觀眾的觀影需求。
(一)關注受眾的市場性創作
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之下,電影從攝制到放映這一完整閉環受制于市場與觀眾反饋,于是新力量導演的創作很快便進入產業化與市場化的模式。近年在市場化的推動下,中國電影的工業體系、產業模式不斷升級,類型化實踐不斷推陳出新,新力量導演迎合受眾的市場性創作在電影工業體系下初具雛型。而對市場的精準錨定以及對觀眾的深入了解,也使得商業片導演有意向美國好萊塢模式以及香港模式等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學習,以期獲得最大程度的投入產出比。
在市場性創作中,當下大熱的新主流電影與類型糅合的商業電影成功獲取大量市場份額,甚至不斷刷新中國影史票房記錄。2017年,吳京導演的《戰狼2》對世界局勢之下中國國家形象的準確構建,對孤膽英雄形象的生動刻畫,再度點燃了國人的民族熱血。2020年,管虎導演的《八佰》用IMAX影像還原并盛贊了塵封在歷史里的英雄挽歌,塑造的英雄群像無比悲壯。長于戰爭刻畫與家國敘事的新主流電影,正是融商業性于主旋律之中,通過震撼的視覺奇觀吸引眼球,將觀眾喚詢為具有家國意識的主體,取代了曾經空洞枯燥的直白宣教。而安排在諸如春節檔、國慶檔甚至是“五一”檔等節慶日檔期上映的商業片,也更能夠緊緊抓住受眾需求。2021年4月30日上映的《你的婚禮》,豆瓣評分為4.6,卻憑借許光漢與章若楠的“明星效應”撬動7.89億票房,甚至成為該檔期首映日票房冠軍,消費文化語境之下的兩極反轉不禁令人咋舌。而這些都是以受眾為導向進行市場性創作而帶來的一體兩面,不得不令人反思。
(二)關注現實的社會性創作
中國的現實主義電影創作在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是一脈相承的,從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運動中涌現的影史經典如《狂流》《神女》,到今時今日備受國民追捧的現實主義力作《白日焰火》《我不是藥神》,均延續了中國影人關注社會現實、賦予時代烙印的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無論是社會問題意識的表達,還是犯罪、懸疑、黑色幽默等多元類型的融通,抑或是對個人生命價值的找尋、對荒誕生活與復雜人性的反思,新力量導演的社會性創作無疑都是成功的。他們借鑒好萊塢類型片的生產樣式,又在其中打上帶有個人風格的作者標簽,在秉持現實主義美學原則的同時,兼顧資本的商業要求與個人的風格表達。
新力量導演的社會性創作,使商業化、娛樂化的消費主義追求同藝術化、私人化的作者風格表達之間形成微妙均衡。曾國祥導演的校園霸凌題材影片《少年的你》,以校園、男女生戀愛的青春片類型融合了沉痛的霸凌現實,喚起大眾的同情與關注。易烊千璽與周冬雨的聯袂出色演繹貢獻了影片許多的淚點與笑點,壓抑隱忍的霸凌現實牽動著每一位學生、家長的心,使得影片在觀賞性中更有極強的社會現實性。校園霸凌事件的層出不窮,是多方責任缺位而導致的,在電影上映后國家相關部門便出臺了更為細致的相關法案條例,并不斷完善相關法規來保護未成年人的成長。
(三)關注邊緣的地域性創作
地域性電影創作是近年來不可小覷的創作態勢,各個地域的人文景觀在虛構與記錄、荒誕與現實的交疊中勃發。其中以畢贛、饒曉志為代表的“貴州新浪潮”、以萬瑪才旦和松太加為代表的“藏地新浪潮”、以顧曉剛為代表的“杭州新浪潮”、以大鵬、耿軍為代表的“新東北電影”等構成了當下區域電影的另類呈現。而這些來自我國四個不同方位的區域電影創作,也為當下的中國電影建構了一層獨特的地域想象與文化身份認同。無論是特定的影像呈現方式與拍攝手法,還是獨特的地域文化符號與標識景觀,都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影像作為物質載體所具有的紀錄與傳達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新力量導演對地域、邊緣的表現,以及對成長光景、生命體驗的哲思。在高速發展、復雜多變的當代中國電影藝術圖譜中,地域電影創作以現實主義的取向和浪漫主義的手法構造了獨一無二的奇觀。
在《路邊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畢贛用浪漫迷離的臺詞和駁雜潮濕的田野構筑起魔幻與現實、工業與美學之間的貴州鄉土與記憶。在《殺死一只羊》和《氣球》中,萬瑪才旦以民族寓言呈現藏地人民虔誠的信仰,通過迷途人物的自我救贖來實現對生命意義的找尋。在《春江水暖》舒緩的長鏡頭中,參與導演的家鄉敘事,感受富春江畔普通人家家長里短的瑣碎與鐘靈毓秀的江南氣息;在融合了傳統山水畫和詩歌意象的鏡頭中,體味城市與時代的世俗風氣和社會樣貌,感知普通人的精神氣質和人生觀念。
三、新力量導演群體的的風格偏向
2014年以來,大量商業資本涌入中國電影市場,打破了傳統電影產業的舊格局,因而新力量導演群體順勢借力在其創作中進行各自的美學探索,形成了中國電影創作的重要現象。互聯網語境下新力量導演的電影風格探索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市場化導向下嘗試多元類型融合;二是在批判社會現實的前提下兼顧個人表達與市場調性;三是以詩化形式在導演個人生命體驗中尋求人類共通的情感。
(一)市場化導向與類型化探索的商業片導演
“盡皆過火,盡是癲狂”[7],曾是20世紀的西方影評人對香港功夫片的怨言,但后來成為評價香港電影類型化、本土化品格最為妥貼的表述。類型化的香港電影可以看作是東方美學韻味與西方現代特性的結合典范,曾吸引無數人為之著迷,也包括在“錄像廳美學”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新力量導演。他們之所以能取得商業票房上的巨大成功,正在于將香港電影的類型化經驗同自身成長過程中的生命體驗相結合,成功借鑒香港電影模式進行獨特的在地化實踐。無論是電影本身的類型化、制作運營的產業化還是消費市場的大眾化,都是以市場和觀眾作為導向,并在這一前提下不斷探索與拓展。如黑色幽默喜劇片、懸疑喜劇片與綜藝電影等新的電影類型,都能夠在講好故事的同時,加入喜劇、愛情、動作、懸疑等類型電影元素,以保證影片的上座率。
陳思誠導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憑借對市場的精準把控和對觀眾的清晰認知屢屢成為爆款電影。從第一部的8.23億,到第二部的33.98億,再到第三部的45.24億,陳思誠憑借“唐探宇宙”不斷刷新票房記錄。陳思誠將懸疑與喜劇的類型元素融合,將東方與西方的多元文化融合,同時在銀幕上展現美國、日本等不同國家的地域景觀以拓展觀眾的視野想象,成為春節檔闔家觀影首選。徐崢的《愛情神話》以輕松浪漫的喜劇氛圍鋪陳出時尚又接地氣的海派畫卷,在2021年末成為票房黑馬。影片以戲劇化的人物關系表現兩男三女在情愛矩陣里互相周旋,讓觀眾在摩登都市的弄堂里感受平靜的生活與浪漫的愛情。在傳統的愛情片類型中鋪陳劇情,同時又以生活的意外和巧合營造笑料與喜劇氛圍,兩種類型結合恰到好處。影片中著力刻畫的李小姐、老白、老烏等自由奔放的都市青年男女形象細膩獨到,他們正是在對愛情的尋覓與追求中體悟到當下的生活與人生。傳統的愛情、青春、懸疑等類型片在新力量導演的巧妙構思下,達成樂趣與意義的共生,這便是商業片導演的成功之處。
(二)兼顧現實關照與商業訴求的文藝片導演
當下游走在電影工業與電影美學二元之中的文藝片導演,既受到市場與大眾認可,又得到學者與電影節青睞,既能夠承擔起關照社會現實的責任,又能夠充分在影片中寄寓自我。這類“體制內的作者”導演將類型包裹下的藝術片展現得更為貼切,從而喚起觀眾的心底共鳴,并找到了藝術性和商業性的平衡點,使其既能在商業上獲得回報,又能忠于個人風格表達。2021年由路陽執導的《刺殺小說家》改編自東北籍作家雙雪濤的同名小說,影片通過“赤發鬼”臉部支離破碎的面具與廢料來暗喻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衰落與頹唐,交叉敘事所呈現的小說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交織更同影片之外的現實形成互文。魔幻題材再加上CGI技術對人物造像的加持,迅速引起觀影狂潮,在2021年的春節檔最終獲得10.35億票房。
要說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入和對邊緣人群生活的關照,刁亦男不可避而不談。無論是早期拿下金熊獎的《白日焰火》,還是近年備受關注的《南方車站的聚會》,都圍繞著人性與毀滅兩個關鍵議題來展開故事。導演在影片中深掘具有毀滅性力量的暴力、欲望如何激發人性的惡,并通過影像表層所展現的暴力,串聯起文本之中的轉型期社會現實,傳遞對人性的深層思考。而這兩部影片一直延續著刁亦男黑色電影的風格,混亂幽暗的夜巷、彷徨于小城鎮的邊緣人物,連帶著層層懸念嵌入復雜的敘事模式,這些都昭示著導演刁亦男所獨有的個人風格標簽。與此同時,影片將生活化的紀實性與藝術化的表現性統一,在劇情設置、場景安排、明星選用等方面下足功夫,從而能在獨樹一幟的風格下取得不錯的票房與口碑。
(三)傳遞自我生命體驗與詩意的藝術片導演
新力量導演群體中,對于偏重中小成本藝術電影創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導演來說,電影節成為藝術電影的主要生存方式[8]。“藝術電影作為‘電影機構的獨特分支,已然具備其獨特的生成路徑、形式力量和觀看誘惑,作為一種不可替代的電影實踐和文化生產模式,它積聚了一種可以召喚全球化語境中分散于各地的特殊觀眾群的能量,能夠縫合不同區域的縫隙市場,建構‘藝術電影愛好者的全球化的想象共同體”[9]。因而新力量群體中的藝術片導演們走在電影藝術探索的前沿,關注邊緣亦或是關注自我,用影像來書寫生命經歷,表達人情與人性,描摹感性層面的社會與現實,從而尋找到人類共通的情感寄托與價值觀念。這類藝術片所具有的極強藝術性幾乎決定了其無法在大眾化的電影市場中拔得頭籌,因而只能通過其另類的美學呈現、形式探索在電影節或者電影展上大放異彩。
藝術片導演手持中小成本的投資成為獨立創作者,以保證創作過程中始終具有的主導性,使影片具有一定的商業價值但并不迎合商業口味。他們能夠在市場、自我與體制之間達成微妙均衡,通過放棄宏大的政治和歷史敘事來致力于對電影形式和電影本體的深掘。后起的新力量藝術片導演在創作中呈現出一種詩意復歸的趨勢,透過黑白畫面、手持攝影、長鏡頭等電影技法來強調個人情感的呈現,展現社會圖景的同時又忠于作者個人的視域與生命體驗。畢贛導演的《路邊野餐》在雜亂無序的鄉野和時間的晃動中昂然著詩意,更在魔幻與現實、個人與家鄉間構筑起貴州的獨特地域景觀。而顧曉剛導演的《春江水暖》則通過極具古典美學韻味的橫移長鏡頭鋪展開富春江畔平凡人家的家長里短,緩慢靜觀的美學風格正契合了數千年來中國人堅毅隱忍的精神氣質。
四、結語
中國新力量導演從群體性崛起到駕輕就熟走向創作的分化與風格的偏向,在電影制作、類型生產、營銷模式等方面無疑推動了中國電影的產業化進程。影視寒冬的不確定性盈郁,加上后疫情時代下禁足與隔離的陰霾仍未散去,新力量導演以其創作將中國電影帶入一種更為多元、靈活的格局。盡管“娛樂至死”地過度營銷、片面追求快感的爽片仍然存在,在國際電影格局中沒有話語權的窘境依舊需要面對,但從共名到分化,新力量導演憑借各自的創作贏得了票房與口碑。他們正以傲人之姿續寫中國電影的神話,使中國電影更加有實力、更加有底氣,實現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的轉變。
參考文獻:
[1]國家電影局.“十四五”中國電影發展規劃[N].中國電影報,2021-11-17(02).
[2]陳旭光.“新力量”導演與第六代導演比較論——兼及“新力量”導演走向世界的思考[J].電影藝術,2019(3):63-69.
[3]顏純鈞.“新世代”導演:關于命名、身份和創作[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3):87-91.
[4]曹池慧.從“代際導演”到“新力量導演”的轉變看中國電影的嬗變[J].電影文學,2020(1):71-74.
[5]陳旭光.新時代 新力量 新美學——當下“新力量”導演群體及其“工業美學”建構[J].當代電影,2018(1):30-38.
[6]尹鴻.建構小康社會的電影文化——中國電影的新生代與新力量[J].當代電影,2015(11):9-14.
[7]波德威爾.香港電影的秘密[M].何慧玲,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8]李卉,陳旭光.新力量導演的“電影節生存”與藝術電影的多元樣貌——中國新力量導演系列研究之一[J].長江文藝評論,2020(4):14-20.
[9]范倍.作為一種文化生產的藝術電影:畢贛現象及其內蘊問題[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9(4):56-60.
作者簡介:李健,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戲劇與影視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