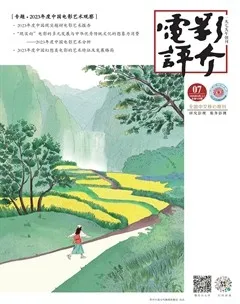《飛馳人生》系列電影: “中”式賽車電影的奇觀塑造與深邃內涵
石田宇 孟威


【摘 要】 2024年春節檔上映的《飛馳人生2》是韓寒執導的第五部電影,相較于《飛馳人生》對賽車競技的細致描摹,《飛馳人生2》通過全面升級的奇觀畫面,詮釋了“速度何以激情”的獨特魅力。電影以視覺奇觀的瞬時性、爆發性與主題的深邃性相互映襯,建構起中國賽車文化的影像敘事,讓觀眾看到了一個充滿熱血和激情的賽車世界。作為一名職業賽車手,韓寒以速度奇觀塑造的震撼畫面和場面奇觀營造的情感升華,對賽車運動進行深情致敬。文章將從影片的奇觀化塑造和敘事深度兩個方面,剖析《飛馳人生》系列對競技運動的深層次展現。
【關鍵詞】 《飛馳人生》; 賽車文化; 韓寒; 奇觀;
繼《阿郎的故事》(中國香港,1989)、《頭文字D》(中國香港/日本,2005)等影片開創國產賽車電影的先河后,韓寒執導的《飛馳人生》系列電影(中國大陸,2019/2024),以速度奇觀塑造震撼的視覺畫面,以場面奇觀推動沖突層層升級,將國產賽車電影推向一個新的高度。韓寒將自己作為賽車手的感受融入電影制作中,《飛馳人生》采用“競技+喜劇”的方式,呈現幽默而生動的賽車世界,其中雙雄對決的激烈場面,飛馳、漂移等精彩瞬間和幻影超車情節,都彰顯了競技運動的魅力。《飛馳人生2》在前作的基礎上,對競技場面進行全面升級,比賽時間更長、主題內涵更深、視覺效果更驚艷,其中賽車對撞實拍、高燃特效轉場和超現實的雙車并軌畫面,是國產賽車電影速度奇觀與場面奇觀的盛宴。從文本層面來看,兩部電影都采用典型的“建置—對抗—結局”三幕式結構,一方面通過追夢成功的大團圓結局,應和春節檔的節慶屬性,另一方面揭示商業法則對賽車競技的侵蝕。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融合,使影片既有文藝電影的細膩和深沉,又有商業片的娛樂性和觀賞性,突顯出創作者內容與形式并重、內斂與鋒芒同頻的創作理念。
一、數字特效對“中”式賽車奇觀的塑造
學者周憲在《論奇觀電影與視覺文化》一文中提出“奇觀電影的崛起和流行表明電影是由一個從話語中心范式向圖像中心范式的轉變。”[1]并根據視覺吸引力的側重不同,將奇觀電影分為動作奇觀、身體奇觀、速度奇觀、場面奇觀四種類型。如果把這種觀點與法國哲學家讓·鮑德里亞的類像理論結合起來,就可以從理性層面把握奇觀電影的快感文化特性。類像理論是深入剖析真實與模擬之間關系的學說,類像是指隨著科技的發展,尤其是數字技術的普及,人們越來越生活在一個由模擬和復制構成的“仿真”世界中。這些模擬和復制的圖像、聲音和文本,不僅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而且對人們的認知方式和文化體驗產生了深遠影響。類像理論最先出現在讓·波德里亞的代表作《象征交換與死亡》中,作者認為“人們建構的各種巨大仿象從自然法則的世界走向力量和張力的世界,今天又走向結構和二項對立的世界。”[2]隨后作者又在《消費社會》一書深化了該理論,認為類像不單純地再現和反映現實,更是文化工業的產物,而文化工業在大規模生產消費品的同時,也在生產適應該工業的消費者,而消費者的個性化差異,“無論怎么進行自我區分,實際上都是向某種范例趨同。”[3]類像理論在奇觀電影中的表現尤為顯著,奇觀電影是以創造視覺場面為第一要務的電影類型,它通過高強度的節奏、渲染氛圍的聲音和短平快的剪輯手段,塑造一個充滿沉浸感的虛擬世界。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數字特效、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等技術手段,使奇觀電影中的類像越來越逼真,與現實越來越難以區分,這不僅增強了奇觀景象的表現形式,也提升了人們觀看電影的沉浸體驗。
賽車電影是類像理論在影視領域的具體體現,該類電影以速度作為影片的核心,使用汽車這一載體創造令人驚嘆的速度奇觀。電影中的賽車、車手、賽道、自然景觀等元素,都是對現實賽車運動的模擬再現,然后通過藝術化的手法,將現實場景進行夸張、變形和重構,從而創造一種超越現實的視覺奇觀。與其他奇觀類型不同的是,賽車電影對速度、激情與技術有著極致的追求,以視覺沖擊力和視覺快感來滿足觀眾的觀影需求。《飛馳人生》系列是近年來我國賽車類型片的優秀之作,作品不僅豐富了中國賽車文化的層次性,還描摹了賽車手馳騁疆場的不屈精神,通過速度奇觀與場面奇觀的融合,構建一個充滿熱血的賽車世界。
兩部電影的故事情節相似,講述的是賽車手張馳率領車隊奔赴巴音布魯克參加拉力賽的故事。從執導處女作《后會無期》開始,韓寒執導的每部電影都有或多或少的賽車元素,隨著賽車元素的濃度增加,視聽效果也越來越奇觀化。以雙雄對決場面為例,《飛馳人生》90多分鐘的電影時長大部分時間都在講述一代車神從隕落到崛起的心路歷程,最后的20分鐘才正式進入賽事比拼。險峻的巴音大峽谷考驗的不僅是駕駛的水平,更是駕駛的藝術。因此除了速度上的你追我趕,創作者還將重點放在對賽車引擎、懸掛系統、剎車、輪胎等性能方面的展現。
“在當代觀眾不斷提出視覺需求的大環境下,傳統敘事電影那種娓娓道來的敘事模式已不再符合時代潮流,順應時代的‘快看和‘看快構成了速度奇觀電影的典型形態。”[4]《飛馳人生》系列順應當下快節奏、強刺激的觀影需求,相較于第一部的信念呈現,《飛馳人生2》以穿越機搭載高速攝影機、實拍與虛擬合體和短平快的剪輯等三種手段打造了一場視覺盛宴。例如片中的賽車翻滾對撞,是我國大銀幕首次呈現真實的賽車對撞場面,在正式開拍之前,創作組將兩輛賽車進行賽級改裝,每臺車的造價高達百萬級,為了獲得逼真效果,即使在看不見的發動機和避震區域,創作組依然采用符合賽車配置的裝備。對撞場面以穿越機搭載高速攝影機,同時輔以多角度攝影機全程高速跟拍,賽車的四面八方布有十四到十五個機位,確保每一個瞬間都能夠被捕捉。
從對撞實驗中心向巴音布魯克轉場的畫面,是全片最難的特效鏡頭,視效團隊將特效和剪輯工作前置,制作了近80個預演版本,2378幀變身場景由80臺渲染機不間斷工作,保證單幀渲染6小時,力求給觀眾帶來高燃酷炫的視覺快感。影片還對雙雄對決場景進行全面升級,張馳第一部的對手是技術與配置一流的林臻東,第二部的對手已經不是單純的某個團隊或者個人,而是曾經輸掉比賽,并在恐懼中沉淪的自己。對此,電影設置了燃情的雙車并軌場景,極限狀態中的賽車,竟然重走了5年前的行車軌跡,新舊兩臺賽車跨越時空完成合體。這場超現實的涅槃畫面,制作團隊花費五個月的時間定稿,共設計了70多個版本,其中的難點在于幻影車的虛實度,最終確定由沙子組成幻影,讓兩個時空的張馳在漫天晚霞中合二為一。《飛馳人生2》精心設計的賽車場景和震撼人心的數字特效,打造了熱血沸騰的視覺觀感,而賽車手挑戰自我、追求極致的奮斗過程,又讓這種視覺觀感由表及里地上升為精神激勵。
二、真實與虛擬結合下的空間延展
“‘場面作為影視藝術最為基本的單位,影片中的敘事和技巧都要在場面中進行展開。”[5]以美國賽車電影《速度與激情》為例,電影中的競速場面總是以暴力元素貫徹始終,人物行動和故事情節首先服務于畫面,戲劇沖突隨著競技者暴力行為的層層升級,飆車場面造成強大破壞力,荷爾蒙十足的格斗場景,單兵作戰到團隊作戰的協作升維,構成專屬于該影片的場面奇觀。與之不同的是,中國賽車電影的場面奇觀塑造更加注重真實感和細膩度,除了高精度建模和渲染技術創造逼真的動態效果,雪山、草原、湖泊等自然景觀也為電影提供了豐富的視覺素材,是電影情感表達和主題深化的重要工具,真實環境與虛擬技術相結合,拓展了電影敘事的空間維度,使得作品能夠深入地探討和表達主題思想。
首先,《飛馳人生》系列電影重點展現天山賽道地理位置的特殊性,電影虛構的巴音布魯克拉力賽,其地理形態由巴音布魯克草原、天山峽谷賽道、獨山子大峽谷等三個地方組成,高原雪山的點滴冰融匯成彎曲悠緩的開都河,而歷代車手和領航員的奮爭,則匯成這座拉力賽最高級別的山峰。巴音布魯克賽道設置在3500米海拔、1500米落差的險峻位置,全程109公里,共計1462個彎道,最窄的路面僅容1輛車通過,九曲十八彎的嶺盤山路、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砂石滿布的復雜地形,對車手的體力、忍耐力和專注力都是巨大的考驗。尤其是巴音布魯克的魔鬼路段,一邊是高山之巔,一邊是懸崖峭壁,稍有不慎就會萬劫不復。影像之內,鏡頭低空捕捉賽車的高速轉彎,隨后迅速上搖閃現壯闊的萬里高山,險峻的賽道不斷有意外發生,賽車從幾百米山崖垂直向下翻滾,直沖懸崖而去,路邊腐爛的動物肢體、支離破碎的金屬零件和渾身血漬的參賽隊員,讓本就緊張的比賽驚心動魄。厲小海在駕校訓練時,隊員們就不斷地抱怨模擬賽道設置過窄,開得不痛快,張馳一臉沉重地強調“因為外面的那不是路,是懸崖”。
在影像之外,創作團隊跨越1600多公里進行實地拍攝,80輛賽級車輛參與,光漂移彎道的素材積累就高達萬條,旋翼直升機與地面拍攝裝備同頻配合,力求無死角地捕捉賽車的飛馳細節,比賽中飛馳、漂移、超車等精彩瞬間,與賽車手們的專注表情和緊張動作,都被一一呈現。為了還原真實的拉力賽現場,創作團隊還著重展現賽車和賽道的種種細節,其中改裝賽車的馬力直接對標世錦賽,并量身定制飛躍跳臺,全速行駛的賽車輪胎跟地面摩擦造成的拉煙奇觀綿延不盡,真實環境與虛擬技術結合,塑造震撼人心的場面奇觀,讓觀眾感受到賽車競技的速度與激情。
其次,在聽覺層面,《飛馳人生》系列電影還有精心的音效設計,如賽車的轟鳴聲、剎車聲、風聲與高速運動的畫面,共同創造了極具空間感的場面奇觀。“透視一詞所指的常常是影像的空間感或深度感,然而,我們可以使用聲音透視一詞來表示聲音所特有的表現物理空間的屬性。”[6]兩部電影一共出現四次賽車改裝場景,每次都是在時間和預算極度緊張的情況下進行,每一次都預示著低谷狀態后的崛起,因此,各種機械零件的拆卸與組裝,電焊火花的飛濺閃爍,發動機的高速轟鳴,與激昂的背景音樂交織在一起,營造了廣闊的物理空間感,宣告著人與車的浴火重生,高亢的聲調還凸顯了團隊成員的奮斗激情,讓觀眾感知到人物心理層面的情緒轉變。《飛馳人生2》的冰雹風雪情節是一場以聽覺因素為主導、以視覺因素為輔助的場面奇觀,創作組使用了噸級的物理冰雹量,還原風雪冰雹與賽車碰撞的逼真情境,賽車和賽道被白茫茫的冰雹覆蓋,向遠望去黑云壓境、雷聲翻滾,近處冰雹如鋼珠一樣砸向車面,車窗的破碎聲、系統故障報警、發動機震喘,種種聲音交雜在一起,營造了絕望和嚴峻的敘事氛圍。視效與聲效的雙倍加成,真實與虛擬的交互融合,拓展了電影敘事的空間維度,也展現了賽車手們在極端條件下的堅韌和勇氣。
三、現實主題與奇觀敘事的融合突圍
(一)浪漫與現實并重的奇觀敘事
汽車文化與賽車電影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不同國家的賽車文化,因歷史背景、地域特色、工業發展等因素的不同,呈現豐富多樣的特點。例如基于本土賽車運動發展起來的法國賽車電影,就蘊含著深厚的歷史底蘊。法國是一個擁有近百年賽車歷史的國家,其賽車運動不僅是一項體育活動,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和文化現象;美國賽車電影比較崇尚個人英雄主義的塑造,形式上通常與犯罪元素結合,通過各種險境下的速度奇觀,賽車女郎和賽車手的身體奇觀,彰顯競爭激烈、對抗直接的賽車精神。相比之下,國產賽車電影因起步較晚,在數量上略顯匱乏,近年來,國產賽車電影的發展總體上呈現由少到多、由粗到精的趨勢。賽車在早期電影中多以體育類、警匪類電影的附屬元素出現,并沒有形成建立在本土汽車工業基礎上的賽車文化。進入21世紀后,賽車運動和賽車電影開始嶄露頭角,2005年由劉偉強和麥兆輝聯合執導的電影《頭文字D》以街頭賽車為主題,通過緊張刺激的賽事場面和個性化的人物塑造,吸引了大量年輕觀眾的關注,雖然電影對賽車場景的氣勢渲染相對不足,但對后期賽車電影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隨后,《賽車傳奇》(羅義民/韓之夏,2011)、《車手》(鄭保瑞,2012)等影片在賽車元素的基礎上,不斷嘗試新的敘事方式和視覺風格,不同程度上推動了我國賽車電影的發展。
職業賽車手出身的韓寒,是少有的執著于賽車運動的創作者,并對賽車文化有著獨到見解和深厚情懷。從初執導筒至今,韓寒的五部電影都與賽車有著緊密的聯系。這種執著從《后會無期》(2014)中開車去尋找詩和遠方,到《乘風破浪》(2017)里主人公獲得拉力賽冠軍等諸般榮耀,再到《飛馳人生》系列風馳電掣的速度奇觀,每部電影都融匯著創作者對賽車運動的感悟。韓寒電影彌漫著追求自由、尋找自我的人文情懷,這種情懷從《后會無期》開始,一直延續到專注于賽車競技的《飛馳人生》系列。其中《飛馳人生》是一部喜劇元素與賽車元素并重的作品,一代車王因非法飆車被禁賽五年,只能經營炒飯大排檔維持生活,在沒錢沒車沒隊友,甚至駕照都要重新考取的窘境下不忘初心,駕駛破碎的賽車沖向大海,夕陽漫照在海面,挑戰人類極限的追夢人享受速度的魅力,晚霞映照的赤子之心與張馳“不想輸”的勝利者姿態互為映襯,韓寒在結尾處用煽情的鏡頭語言塑造了張馳無懼生死的追夢人形象。
如果《飛馳人生》的慘勝結局充滿著浪漫主義色彩,那么2024年春節檔上映的《飛馳人生2》,則讓飛揚不羈的賽車電影長出了現實根基。相較于第一部的浪漫追夢,第二部中的主人公處處都是“廉頗老矣”的悲涼,五年的時間,科技的迅猛發展留給駐足者的希望愈發渺茫,混動車全面碾壓燃油車的時代,曾經難以突破的賽時記錄以分鐘為單位,不斷被后來者刷新。車王的英雄遲暮不僅是身體機能的下降,更是內燃機時代草臺班子對戰新時代混動王者的潰敗,相較于技術上的突破,最難打破的還有心境不復從前的悲哀,可以說影片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講述一代車王的無奈。影片的故事情節融入了諸多現實問題,多層次的表現方式,使《飛馳人生2》不僅是一部輕松愉快的喜劇片,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現實主義作品。
(二)主題的節慶屬性和深邃內涵
作為以賽車為主題的電影,《飛馳人生》在視覺效果方面表現出色,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電影過度依賴喜劇元素,導致劇情轉折稍顯生硬,往往前一個畫面還在煽情之中,后一個畫面馬上用反轉的方式對其解構,情感表達也過于直接,缺乏足夠的細膩感和深度感。《飛馳人生2》較好地規避了這些問題,影片整體節奏非常工整,創作者采用典型的“建置—對抗—結局”三幕式結構。第一幕融入適當的喜劇元素,通過背景介紹展現主人公的初始狀態:五年過去了,曾經的一代車王如今是“巴音布魯克之恥”“黑心駕校教練”,經濟來源主要靠駕校課時費,經營慘淡的駕校因輕軌動工需要提前拆遷。辛地機械的召喚喚起張馳的賽車初心,現實窘境又再一次給其迎頭痛擊,贊助資金半路夭折,賽車對撞意外頻出,名利場的金錢博弈步步緊逼,各種限制和不公讓辛地車隊一再妥協。電影第二幕正式鋪陳情緒,因為光刻車隊和組委會的聯合打壓,辛地車隊的頹廢情緒觸底反彈,此時主人公的人物弧光從“我接受了”釋然到“我還是喜歡賽車”的追夢火苗,再到“不留一絲遺憾”的熊熊火焰,被完整地勾勒出來,然后通過一個特效轉場進入巴音布魯克賽場,開啟競速比拼的第三幕。在準備并不充分的比賽中,張馳是最后一屆巴音布魯克比賽的最后一名參賽者,此時站在冠軍之巔的目的被暫時擱置在第二位,雙車合軌賦予了他英雄般的覺醒和勇氣,開向終點的一剎那,他抓住了“僅出現那么一兩次的機會”戰勝恐懼,繼十年前折桂后再次奪冠。
眾所周知,勵志電影如果僅依靠激情和熱血,讓主人公成為人生贏家,會有脫離現實之嫌,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方式顯然無法滿足觀眾對主題深度的追求,比起乏善可陳的心靈雞湯,觀眾更希望看到的是創作者對問題的深入剖析。《飛馳人生2》不僅繼承了前作的精神內核,在主題深度、人物塑造等方面有所突破,創作者還一邊以“兩代車王齊奪冠”的大團圓結局,應和春節檔的節慶屬性,一邊以資源高位對資源低位的碾壓,揭露殘酷又真實的商業法則,使電影既有理想主義的力量,又有現實主義的深邃。
首先,在熱鬧的春節檔,電影秉承“熱愛可抵歲月漫長”的情感基調,去沖淡主人公中年不得志的沮喪,5年前的巴音布魯克比賽,由于剎車制動過晚沖出跑道,張馳全身多處骨折,余生無法再開賽車,那場本該屬于他的奪冠賽,因作弊嫌疑淪為全行業的笑柄,擊垮他的不僅是身體的傷痛,還有不斷質疑自我的消極情緒。即便如此,影片依然強調著努力奮斗與執著追求的重要性,新人厲小海的加入,是兩代車王的精神互動,前輩為后輩樹立精神榜樣,后輩為前輩尋找追夢初心,“不想贏,只是想輸的漂亮點”是代系傳承下共享的價值理念。電影勵志敘事所傳遞的價值觀和人生觀,能夠給觀眾帶來正面的心理暗示,觀眾會不自覺地將自己的人生經歷與電影情節相聯系,從而產生強烈的共情效應,應和春節檔團圓、和諧的節慶屬性。
其次,商業法則對賽車運動的侵蝕是電影的另一深刻主題,汽車拉力賽的門檻比其他競技項目的門檻要高很多,其差距不僅體現在技術方面,還有強大的資金需求。《飛馳人生》絕大部分篇幅都在講述張馳團隊找資金、拉贊助的過程,賽前車毀人傷,也是因為富二代林臻東的慷慨解囊,張馳才有資格站在拉力賽的起跑線上。這種經濟窘境一直延續到《飛馳人生2》,落魄的張馳靠著駕校“刷”臉勉強度日,七拼八湊搭建的草臺班子,因為預算問題聚了散、散了聚,幾經周折才勉強跑進巴音布魯克賽場。賽車運動不單是個人技術的比拼,更是車手背后俱樂部之間的財力比拼,而俱樂部的實力又和雄厚的資本掛鉤。林臻東接受賽前采訪時說,他擁有最好的裝備和強大的后勤保障,個人的技能訓練也毫不遜色,成為巴音布魯克之王是天經地義的。《飛馳人生2》中光刻車隊對辛地車隊的碾壓也是全方位的,此時賽車運動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競技比賽,機會與實力也不是時刻成正比關系,而是摻雜了諸多現實因素。規則本身就對資源高位者充滿寬容,資源低位者只能是被安排、被服從,辛地機械車隊堅守競賽公平的防線,在賽事組委會和頂流車隊眼中顯得如此幼稚,就像那枚失而復得的鉛封,既無法追回當年的成績,也挽回不了因對方作弊帶來的損失,只換來一句諷刺性十足的“深表歉意”。《飛馳人生2》的升級有技術層面的增強,還有深邃的主題內涵、飽滿的人物塑造和強大的情緒感染力,為原本工整的敘事節奏錦上添花,這樣的表達方式顯然比淺層次的熱血追夢更加深刻,也是對賽車運動本質的精神堅守。
結語
《飛馳人生》系列電影是韓寒對賽車運動的深情致敬,也是記錄中國賽車運動的影像志。相較于第一部的浪漫追夢,《飛馳人生2》塑造影像奇觀的同時沒有止步于奇觀,而是以浪漫與現實并重的方式增強文本的深廣度,多層次挖掘“中”式賽車文化的豐厚內涵。主創團隊對電影的工業化制作流程進行全面升級,視效技術的創新應用、千人團隊的通力協作,不僅提升了影片的藝術表現力,還延展了電影的空間維度,大規模的人力資源整合和高效協作,是電影工業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將國產賽車題材影片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內容與形式并重、內斂與鋒芒同頻的創作理念,為未來賽車類型片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也是國產賽車類型片工業化進程的標桿。
【作者簡介】? 石田宇,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傳媒學院視聽學院講師;
孟 威,男,山西太原人,山西傳媒學院視聽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影視攝影技術和藝術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3年度山西省文化、旅游、創意產業發展調查研究專項課題“山西影視劇制作創新發展思路的調查研究”(編號:SXSKWC202306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