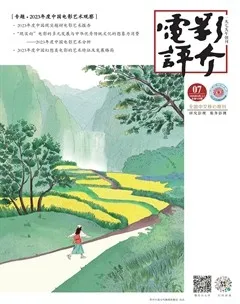從《你好,李煥英》到《熱辣滾燙》: 接受美學理論視域下的“作品”動態建構
關志英 甄永亮



【摘 要】 不同于《你好,李煥英》的一路高歌猛進、票房與口碑雙贏,由賈玲執導的第二部電影《熱辣滾燙》從籌備到前期宣發,再到正式上映,都存在爭議。導演創造電影,市場對電影作出反饋,這種“創作者-創作對象-接受者”的經典傳播模式讓靜態“文本”建構為動態“作品”,創作者與不同時期的創作對象形成映照關系,對觀眾產生情感教育和娛樂身心的作用,同時接受者對創作者與創作對象產生的評議又對其進行二次塑造。
【關鍵詞】 《熱辣滾燙》; 《你好,李煥英》; 接受美學; “作品”
接受美學理論肇始于20世紀60年代,德國文藝理論家姚斯發表《文學史作為文學理論的挑戰》,被看作是接受美學的宣言;隨后,伊瑟爾的《文本的召喚結構》更是讓接受美學理論名聲大噪,二者構成了接受美學的綱領性文獻。正如姚斯所說“一個作品,即使印成書,讀者沒有閱讀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1]。同樣,一部電影,即便拍攝完成,如若沒有觀眾欣賞,未曾得到市場檢驗,那么也只是半成品。
從接受視角看影像創造能夠將電影原始文本的靜態含義動態化,使之在與市場、創作者互動的過程中建構更為復雜多樣的意義體系。德國理論學家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曾提出:“接受乃是創造涵義的過程,它發掘出本文字里行間的種種意蘊。”[2]《你好,李煥英》(賈玲,2021)和《熱辣滾燙》(賈玲,2024)的上映和傳播,不僅讓這兩部劇本在被觀眾接受的過程中建構出區別于“文本”本身的劇情含義、互文意蘊、人物回響,更讓作為創作者的賈玲成為“作品”中的重要一環。創作者、文本和接受者一起循環生產,構成了動態的“作品”體系。
一、電影“作者”與虛構人物的互動
法國新浪潮電影運動代表弗朗索瓦·特呂弗在1954年發表的《法國電影的某種傾向》一文中首次使用了“作者電影”的概念,電影“作者論”由此誕生,其核心在于突出導演在作品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導演強烈的個人風格,使其創作的一系列作品擁有主體性,即一種非客觀的生命特質。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這樣定義電影的“作者”:“導演監管文字、聲音、視覺所有這些電影的基本元素,現在都要以電影‘作者,而不是編劇或文本作者等來衡量。”[3]迄今為止,中國導演賈玲有兩部電影上映,皆成績不俗。2021年的《你好,李煥英》在中國內地狂攬票房54.13億元,中國電影票房總榜排名第三,隨后在全球上映,知名度進一步打開;今年的《熱辣滾燙》初上映便登頂2024年春節檔,雖然后續跌至第三,但票房依舊破34億元,總票房仍居榜首。①作為一名喜劇演員,賈玲轉行導演后執導的兩部電影都成績斐然,這背后的商業邏輯、營銷策略和執導理念的配合都值得探究。作為電影“作者”的賈玲將自己視作傳播的一環,她將現實里真實的自我表象特質與觀眾期待的形象折疊,繼而打造出一個媒介展示的“賈玲”形象,以兩部電影為錨,對媒介形象“賈玲”進行加強或是顛覆,從而讓觀眾以為的電影“作者”影像虛構人物互動,產生真假交纏的夢幻感與迷離感。
(一)媒介展示的“賈玲”形象
現代傳播學理論認為,大眾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不向受眾反復傳遞信息以及各類觀點,深刻地影響受眾對某一事物或者某一形象的認知、態度和行為的變化,可以說,現代受眾的認知結構是在大眾傳媒所展示的“媒體現實”的基礎上形成的。[4]“媒體現實”是一種被制造出來的表象真實,人們通過現代技術和傳播媒介展現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物,這個人物在媒介中參與游戲、嬉笑怒罵、分享情感,她自己與觀眾都在這一過程中加深對這一媒介形象的認知。但需要注意的是,真正完全真實的自我人格永遠無法通過媒介傳播,因此“媒介現實”更接近于一種自欺欺人的存在。媒介所展示的“賈玲”形象恰巧是“媒介現實”構筑成功的一個案例。
賈玲,1982年出生于湖北襄陽,最初為相聲演員,在2003年獲《全國相聲小品邀請賽》相聲一等獎,由此嶄露頭角。緊接著,她參與各個劇場的演出,在舞臺上表演相聲、小品等,慢慢登上各大地方衛視春晚和央視春晚,后又在各類喜劇電影中客串,繼而涉足綜藝圈,成為綜藝節目《王牌對王牌》的固定嘉賓。縱觀賈玲的成長路徑,從出道到巔峰,她其實一直以喜劇形象面對觀眾。尤其是在小品《喜樂街》中,賈玲的形象定位是節目幽默搞笑的主要由頭。[5]這種幽默的喜劇形象經過她近20年的舞臺呈現,已經逐漸成為一種被時間錘煉的“媒介現實”,觀眾對媒介“賈玲”的認知在這一過程中緩慢固化。
媒介“賈玲”形象的喜劇特質來源于兩方面,一是她的外形,二是她的性格。眾所周知,娛樂圈是高顏值人群集聚的地方,賈玲本身五官清秀,長相甜美,有辨識度,但體重的增加讓她脫離當下主流審美,發胖的身材讓她和女明星形成鮮明對比,具有搞笑的形象特質。這種“肥胖=搞笑”的標簽背后其實蘊含著一種發人深省的底層邏輯——符合主流審美標準的外形會讓人自動產生仰望、喜歡、嫉妒、羨慕等正負摻雜的情緒,這種媒介形象可遠觀而不可褻玩、是清高遙遠的,所以很多演員有時會刻意減少自己在戲劇之外的出鏡次數,將真實的自我留給生活,將角色留給大眾,如此才能更順利地在戲劇中塑造不同的虛擬角色;脫離主流審美標準而又無傷大雅的外形則會減少攻擊性,給普通人群以一種特殊的安全感,賈玲就符合這一限定條件,她的兩個梨渦給人以親切感,肥胖的身材掩蓋了五官的明亮,但卻更給觀眾一種平易近人的感受。另一方面,性格要素也是其喜劇特質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在小品中還是在電影里,賈玲都展現出真實爽快的性格特征,不同于娛樂圈大部分人所背負的偶像包袱,賈玲展現給觀眾的更多是主動扮丑搞怪的形象。自尊心是人性天然具備的東西,不能否認真實的賈玲可能也有好面子的一面,但在媒介中,她所呈現出來的性格是拒絕矯揉造作的,尤其是在各類綜藝節目中,相聲演員出身的她更擅長捧哏接梗,也更了解怎么擊中人們的笑點。
觀眾、媒介和演員自己一同塑造出的媒介“賈玲”,為作者“賈玲”奠定了基礎,既積累了一定觀眾緣,又以媒介“賈玲”為底色與影像虛構人物互為指涉,從而讓作品在創造過程和市場接受過程中煥發出不同色彩。
(二)電影指涉中的女兒與自我
目前,賈玲執導的兩部電影雖然主題迥然不同,但其中都有對母親和女兒形象的構造,更有對母女關系的深思。她的第一部電影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改編,在電影制作之前已經作為小品劇本進行了多場演出,因此具有良好的改編基礎,而且因為來自導演個人情感經歷,所以才能將樸素的情緒展現得格外出色。私人化表達和大眾媒介工具的結合,讓真實情感和電影藝術在創新中同頻共振。從這種意義上而言,《你好,李煥英》其實是作者“賈玲”與影像人物賈曉玲的一次正式邂逅,媒介現實和虛擬藝術重疊,“賈玲”作為女兒與死去的母親的情感在觀眾的視野中變得更為真實動人。
在攝影機之外的2021年,作者“賈玲”以女兒賈曉玲的身份進入影像,這是賈玲給自己的青春執導的一場夢:影片開場,她借賈曉玲的視角再次進入一場時光流轉的夢境,在這個彩色電視剛剛面世的20世紀80年代,黑白色的、關于死亡和離別的現實沾染上了鮮艷的色彩;影片結尾,女兒賈曉玲回到母親李煥英48歲、昏迷在醫院里這一年,一件針線密織的衣物讓她恍然驚醒,那個夢境中的少女李煥英身體里住著的依舊是48歲李煥英的靈魂,于是另一場夢境顯現,即母親李煥英在彌留之際為女兒織造的一場相逢之夢。從這三場夢的整體結構來看,賈玲將作為電影作者的自己和影片藝術中的女兒進行疊合,最終又以母親對女兒的愛來進行反轉,從而倒扣女兒對母親的愛。情感的雙向流動讓這場看似荒誕的穿越從夢境回歸現實。
如果說《你好,李煥英》是作者“賈玲”與女兒賈曉玲的互文,是給作為女兒的自己的一場救贖,那么《熱辣滾燙》則是作者“賈玲”摒棄家庭身份標簽“女兒”,強調人格與自我的一場藝術指涉。從《熱辣滾燙》的英文名便可見一斑,“YOLO”,根據牛津詞典的解釋,其為“You Only Live Once”的縮寫,翻譯為中文即是“人生只有一次”的意思。人生一次,于是要拼搏,為什么而拼搏?很多人為生計、為兒女、為權利、為欲望……在這部影片中,拼搏的目標是重塑自我,是讓生而為人的自我認真的、熱辣滾燙的鮮活一次。
故事前半段,杜樂瑩整日無所事事,日常三餐甚至需要母親端到床上,體重嚴重超標,遭到妹妹嫌棄鄙夷,男朋友和閨蜜的聯合背叛更是讓她對生活和人性失去信心。這個時候的杜樂瑩只是一具“行尸走肉”,導演用很多鏡頭細節來彰顯其自我的缺席,例如她對父母年老狀態的漠視、有氣無力的聲音、眼神的黯淡無光……轉折出現在離家這一行為的產生,當她走出便利店,耀眼陽光直射,多日未曾出門的樂瑩下意識瑟縮,從此時開始,在客觀條件層面,自我擁有了改變的機會,因此舒適圈被突破。
需要注意的是,這時的主人公在主觀意識層面仍然消極,她的出走僅僅是因為想讓潛意識里的逃避人格繼續躲藏,而不是想要主動融入社會。主觀能動性的產生是在一立一破的過程中實現的。這個過程里,兩個配角的表演十分出彩,他們的變化促成主人公重塑自我的能動性。健身教練因業績對樂瑩釋放友好信號,兩人曖昧拉扯,在鍛煉和拳擊比賽中加深情感,最后更衣室里健身教練的單方面侮辱撕碎了樂瑩對愛情的幻想;遠房表妹在雨天撫慰了樂瑩失落的情緒,卻在聚光燈照射下擊破了樂瑩對人性的最后一絲善意揣測。對這兩個人物進行細致分析可以發現,他們是一類人,甚至與主人公的交往過程都如出一轍——從帶著目的和人建立聯系,到目的達成露出真實面目。從立到破的關系往來,導致主人公在風雨交加的夜晚產生自盡想法,身體的肥胖讓她逃過一劫。在這里,導演通過從夜晚到白天的光線變化、南北朝向的窗戶劇烈晃動和空蕩的房間來暗示悲劇的發生,鏡頭一轉,主人公在大雨瓢潑里的躺姿讓觀眾同情,卻又因自盡未遂甚至未傷分毫的既定事實而感到滑稽。重塑自我的想法在這一漫長的夜晚里生成,后續的減重、訓練、比賽都是“作者”賈玲和人物樂瑩一同完成的情節,真實和藝術形成閉環,自我重新在場。
《熱辣滾燙》的主題是“自我”的實現,這雖然與《你好,李煥英》以親情為主題不同,但可以發現,兩部電影都是從導演親身經歷出發,將媒介“賈玲”首先前置于觀眾實現,然后“作者”賈玲利用前置的媒介形象打造藝術形象,將三者結合,從而在市場中形成漣漪點點的圈層擴大效果,激活觀眾的習慣性認知結構和現有認知體系。
二、從“文本”到“作品”的突圍
接受美學理論認為藝術創作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只有創作者的參與顯然是不夠的,外部世界、創作對象以及接受者都需要和創作者共同發生作用、互為牽引力,如此才能真正讓具有不確定性的“文本”蛻化為意涵豐富的“作品”。康斯坦茨學派代表人物伊瑟爾更是直接區分了“文本”與“作品”:經由讀者閱讀闡釋之后,或者說在與讀者結合之后,“文本”才變成“作品”[6]。賈玲的兩部電影從創造之初的劇本,到演員演繹,再到網絡營銷,直至最后上映,評價褒貶不一,整個生產銷售鏈條實際上就是故事從“文本”到“作品”的突圍過程。
自在是指事物的客觀存在狀態,它的對立面尚未展開,所以這種狀態更接近于一本閉合的書,在未被讀者打開之前,一切都是不確定的。結構完整、情節圓融的不確定性“文本”擁有很多塊空白意義領域,需要作者和讀者共同挖掘。“作品”的最終生成需要雙重反饋——一方面是接受者對其做出多樣評價或表現各種反應,召喚自在“文本”的空白成分;另一方面是不確定性的“文本”要及時回召接受者。
《你好,李煥英》在上映之前其實已經具備了一定開放性——同名小品的多場演出讓劇本在一定范圍內得到傳播,等到制作方將其改編時,“文本”的空白部分才被真正填滿。大部分觀眾在電影上映之前,只對賈玲這個導演有一定了解,且是對其先前的身份(喜劇演員)接受度更高,不可否認,這些觀眾里有小部分人是賈玲的粉絲,他們構成了堅定的觀影基礎,而剩余的人們則是帶著好奇和對“文本”本身的期待與猜測走進影院。需要注意的是,在電影上映之前,賈玲對母親的講述在各種場合中被提及,毋庸置疑,這是營銷的一種手段,但也確實飽含女兒對母親的懷念,所以才能有很多觀眾對這種營銷不反感,甚至積極買賬。
目前來看,這部影片豆瓣評分7.7,中規中矩,但票房領先。雖然有濫用穿越梗的嫌疑,但勝在劇情飽滿、細節處理恰當、情感表達真摯,結尾的反轉更是擊中觀眾淚點。很大一部分觀眾都會因為賈玲和母親李煥英的成長故事而給出較為正面的評價,觀眾對自己的母親或者女兒的情感通過這部電影得到釋放,文本以故事中的人物情感為主體框架,意義空白部分則由無數觀眾對親情的牽掛建構。
《熱辣滾燙》改編自日本電影《百元之戀》(武正晴,2014),在女主人公的形象轉變前后的塑造手法、拳擊誘因、情節架構等方面借鑒頗多。日版電影以小成本博得大收益和高評價,這自然也是中國制片方想要達到的效果,但改編一直以來都是把雙刃劍,它能夠讓創作者更明晰市場動向,但也可能因為珠玉在前的對比而陷入瓦礫困境。客觀來說,《熱辣滾燙》其實對原有“文本”展開了本土化改編:原版色調灰暗,缺乏喜劇元素,主人公離家后到百元超市打工,杜樂瑩則是去了餐飲店;與男主相識的細節設置也頗具喜劇色彩;中版增加了閨蜜的搞笑情節,刪除了主人公被強暴的情節;也將原版里與健身教練重歸于好的情節改為女主勇敢獨立面對新生活……從主題改變和整體風格轉變來說,《熱辣滾燙》實際是更適合春節檔的一部勵志溫情“文本”。影片在上映之初,市場反響較好,但上映幾天后,卻有一些爭議,很多觀眾認為電影對賈玲減重一百斤的營銷過多,女性主義宣傳勢頭太過,繼而將這種對“作者”本人的反感情緒引向“作品”本身。于是“文本”中的意義空白不僅被觀眾的正面評價所建構,也會被負面評價所建構,在市場的接受過程中,“文本”的不確定性逐漸定型,其中蘊含的鮮明自我主題反倒成為一個爭議。
此外,《熱辣滾燙》的褒貶不一還影響了《你好,李煥英》的豆瓣評分,使其從2021年的8.3分降為7.7分,這顯然是接受者對“作者”和“作品”的一種有效的負面召喚。德國文學理論家伊瑟爾認為,文學作品具有兩極,我們可以稱之為藝術極和審美極:藝術極是作品的本文,審美極是由讀者完成的對本文的實現。[7]每一部文學作品的核心,是發生在作品的結構與作品的接受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種文本召喚結構會對作品產生影響力,只要“文本”在市場上流通,只要有接受者一直對其進行關注并展開評議,那么“作品”的生成就永遠只是個偽命題。這從《熱辣滾燙》上映以來人們對賈玲以及《你好,李煥英》評價風向的轉變可以看出。
三、情感激發與娛樂渲染
“作者電影”與以商業電影為代表的“他者化”電影間的對立,還代表著對電影功能與價值的不同認識——電影應當是啟蒙的還是從眾的?前者是“作者電影”的目標,后者是商業電影的手段。[8]早期,電影“作者論”常用于文藝片的拍攝,這與“作者論”的發起者出身與文學流派有較大相關性,但隨著電影文學的發展,許多有效理論也會被商業片使用,用以增加作品的深度和市場粘性。賈玲的兩部作品在考慮“作者論”基礎上,接受市場檢驗,具備商業電影的娛樂功能,又兼具情感激發的功能。
(一)大眾文化的盲目生產
現代工業社會的龐大生產規模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讓基本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之后,人類開始尋求精神文化層面的產品,大眾文化便是在這種環境下應運而生。因此,從本質上來說,大眾文化是以大眾媒介為生產傳播工具,依照商品市場規律運作的,使市民產生愉悅感的抽象性文化產品。既然其中有市場參與,那么大眾文化一定具有盲目性和從眾性,于是就產生了問題——一些文化生產者因為利益導向而生產出大量同質化產品,單調、膚淺、庸俗的產品使觀眾在短時間內沉迷,又迅速失去興趣、陷入審美疲勞。
近年來,中國經濟態勢發展良好,人們的基本物質需要得到滿足,于是有更多時間探索高級需求,需求催生供給,大量自媒體短視頻、電影、電視劇投入生產,雖然豐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但難免有一些文化產品只具有愉悅感官的簡單作用,缺乏對人類精神提升和人文關懷的探求。《你好,李煥英》和《熱辣滾燙》兩部電影無疑是較為優秀的大眾文化。J.R.弗斯則將文化語境定義為“說話者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文化”[9]。賈玲作品的成功有一定的文化語境,它們是市場經濟運作的結果,但也凝聚了創作者的情感體驗和在小品表演里的經驗。不可否認,這兩部作品的娛樂功能大于情感渲染功能,但仍舊對中國電影人研究商業電影的寓教于樂特征有一定助益。
(二)創作者的有意把控
《你好,李煥英》和《熱辣滾燙》沒有完全追逐娛樂性而放棄情感激發,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創作者的有益把控。賈玲曾經在節目中談到過當導演的初衷,她說自己不是為了當導演才去拍電影,是為了拍李煥英才去當導演。她將自己表演喜劇的工作經驗融入電影拍攝中,讓作品回歸普通人的世界,并添加幽默調料,表達真摯情感。一部好的作品,既要有生活氣息,能夠吸引觀眾,如此不至于曲高和寡,又要主題鮮明、情感充沛。
《你好,李煥英》中有很多精心設計的喜劇包袱,例如賈曉玲拿回的通知書、穿越回過去時的狼狽模樣、爭奪電視機時的妙語連珠、假裝盲人欺騙售貨員、一家三口在山坡上的對話……這一系列的細節設計都不是脫離日常生活的空洞情節,而是將幽默元素和生活場景相結合,無傷大雅的“抖包袱”讓觀眾在密集的笑點里感受到溫情。影片前半段以喜劇元素為主,但卻在搞怪滑稽的場景中暗暗埋下伏筆,例如,運動場上年輕李煥英看向賈曉玲的繾綣眼神和李煥英為賈曉玲縫補的破衣服,最終在李煥英的視角中,這一切得到合理解釋——她剛穿越時的場景也令人發笑,一句“你咋變得這么年輕了”,讓劇中人物疑惑,讓觀眾在大笑的同時理解了前面劇情的不合理之處。賈玲以這部電影表達自己對母親的思念,也讓銀幕前的觀眾在笑淚中激發了對母親的復雜情感。
《熱辣滾燙》與《你好,李煥英》如出一轍,都是披著喜劇外殼講述溫情的故事。不同的是,這個故事里的杜樂瑩成為真正的主角,相比賈曉玲性格的大膽,這個角色從最初的頹廢到后來的堅定,更有張力。
結語
從喜劇表演者到電影導演,賈玲憑借僅有的兩部電影占據可觀的市場份額,這種意想不到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于她從小銀幕到大銀幕近二十年的辛苦經營。在她的視野中,接受者和創作者的關系至關重要,因此,她極為重視對自我形象品牌的營銷。媒介形象“賈玲”與作者“賈玲”為其首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的主人公增強了現實底色,在第二部電影《熱辣滾燙》中,導演反其道而行之,以虛構主人公來顛覆既有的媒介形象,造成反差效果,雖然市場反響與預期有差異,但依舊對影片熱度的保持大有裨益。這種將市場視為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的理念,對于拓展中國電影人的拍攝視野具有積極影響。
①參見:貓眼票房專業版.[EB/OL].(2024-03-15)[2024-03-15].https://piaofang.maoyan.com/mdb/search?key=%E7%83%AD%E8%BE%A3%E6%BB%9A%E7%83%AB.
【作者簡介】? 關志英,女,新疆伊寧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講師;
甄永亮,男,河北石家莊人,河北民族師范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IP形象設計、品牌設計、文化創意設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