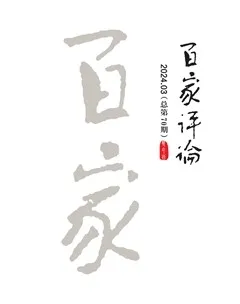操縱藝術:影片《滿江紅》之民間與官場的“對話”之道
趙潞梅
內容提要:影片《滿江紅》的形態建構與題材運用,要實現的是一種“六經注我”式的藝術表達,它極具戲謔性地呈現了高層權貴的操縱邏輯與底層草根借助權力秩序展開逆向操縱的“對話”模式。影片最終完成了對位于秩序兩端的兩股力量展開有效溝通的艱難搭建,同時也抵達了一個《滿江紅》詞作得以流傳開來的藝術世界。影片傳達的戲外之音也許是,《滿江紅》的官場生態可能存在于任何時代,對抗可能發生于社會秩序的任一環節,重要的是,延續不斷的對抗和“對話”訴求是歷史前行中的潛在步伐。
關鍵詞:《滿江紅》 權力秩序 操縱邏輯 南宋 對話
電影《滿江紅》a的藝術完成度總體上不錯,觀眾的情緒始終追尋著劇情的節奏,不過,當“精忠報國”這一元素赫然出場后,由于這一文化符碼的歷史意義過于強大,顯得影片植入情懷的成分過猛,破壞了原創劇情的藝術自洽性與代入感,即雙方力量在權力游戲規則內展開殺與反殺、舍命與保命、暗殺與自殺、救與自救等層面上的尖銳較量。同時,影片結尾部分在肆意支配人物角色后又任其回歸歷史軌跡的圓場設計也使影片結構產生了撕裂,導致劇中人跳出自己的生存現場對當事人展開了超歷史性的道德審視b,并擾亂了人物植根于權力場的行動邏輯,比如化身孤膽英雄的孫均身手不凡的武俠氣質、比如孫均與手下兩位護衛的江湖式出走。
好在,影片在“精忠報國”出現后的美學“變道”,又歪打正著地推動了新的藝術走向——被攔截的密信與遺言(詞)在最終的制衡中實現了各自的溝通功能,只不過二者的價值指向不同。縱觀全片的藝術構架,其實整體上呈現了一種民間力量突破權力高壓進行意愿表達的抗爭訴求——張大一伙以自己的知情權換取宰相的知情權,盡管這種溝通只能建立在弱者殉身暴力的自我布局下。下面依循貫穿影片始終的操縱邏輯的脈動,從權力秩序、身份認同、價值訴求三個維度,并通過分析人物的內在張力與外在關聯,來透視《滿江紅》的藝術世界。
一、高與低:權力秩序內的操縱與逆向操縱
《滿江紅》的精彩在于它以宅院這一微縮的社會形態,于限定的時間內(黎明前一個時辰)呈現了權力運作與生成的細節,并將官場頂層冠冕堂皇、血腥陰暗的暴力生態曝光。事實上,這也是包括底層小人物所承受和適應了的封建王朝上層建筑的“主旋律”。影片里,宰相下榻的宅院籠罩于嚴密的武力布控下,其整套權力機制所指向的唯一效力焦點就是宰相本人,至于宰相是秦檜還是李檜,其實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宅院的運轉機制會按照唯一的施令者的意圖進行。
影片一開始,突如其來的暗殺事件像一股急流,沖擊著宅院內的秩序法則。戒備森嚴的宅邸卻發生了人命案,留宿宅院的兩名使者之一——禮儀官被殺,更嚴重的是其隨身攜帶的密件被竊,電影也由此帶領觀眾打開了反觀宅院內權力秩序的嚴密性與松動性的上帝之眼。院落之內,宰相以下的每個大小人物都是一個可以被取代或舍棄的工具,然而竟有捉摸不透的小角色試圖撬開這嚴絲合縫的權力鏈環,逼得宰相不得不見機行事以查明真相。刺殺事件發生后,撲面而來的就是這座權力大廈的暴力應激機制,在安保漏洞與追兇破案的雙重壓力下,親兵營副統領孫均宰殺眼前的嫌疑士兵就像隨手折斷一根根草芥,并且以荒誕的抽簽形式來決定要折斷哪些“草芥”,可以說,這種表演式的殺戮就是這座宅院的手段和效率,暴力也是支撐這座宅院的權力秩序的構成性力量。
一根與副統領有血緣牽連的“草芥”——效用兵張大,抓住離死前被對方審問的機會,以透露其了解被害人的相關信息為由頭,為自己贏得一線生機,并以此為籌碼獲得了面見宰相的機會。接著借助對現場取證而來的所謂信囊的一番演繹,張大被宰相賦予一個時辰的生命時限和查案權限,同時還被附加了一塊可以通行全院的令牌。張大以提供宰相關注的要害信息——信,獲得了一個時辰跑腿辦事的喘息機會。這與其說是張大的口才發揮了作用,不如說是宅院內的秩序鏈出現風波后,宰相想打聽到信息,就是宰相這種想聽的心理,為后續兩三個小時的事態演變打開了豁口。作為主宰者被人掣肘,宰相只能給出一個時辰的空間松動來靜觀事態演變,而影片伴隨張大一行人爭分奪秒走場時的戲曲配樂,則暗示了被牢牢掌控命運的小人物在出場與退場之間的掙扎。
傍身令牌,張大擁有了在宅院內自由行走的權力,人們也得以一窺院內的空間布局。事實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在權力操控體系內規定的活動范圍,如若突破界限,必須經過合法賦權。如果說在現代都市嚴密的門禁體系內,身著工服的保潔人員在各樓層間忙忙碌碌卻不被“看見”,那宰相宅院里容易被忽略不計的人物就是諸如更夫之類的“邊角廢料”,大概人們已經習慣將這類人當作日常背景了。就像發生在醫院里的劫匪喬裝保潔人員進行隱身的橋段,宰相宅院里的防范弱點也容易在這些盲區被突破。也許沒有人比更夫更熟悉一宅之內的地理面貌與日常動態,加之職業身份帶來的行動便利,影片設定更夫為暗殺事件的“第一棒”無疑具有其嚴密性和巧妙性。在歌姬瑤琴指出更夫有問題后,更夫丁三旺不僅承認自己利用打更之便創造時間差刺殺了禮儀官,而且做假證嫁禍王統領,直至出逃失敗并設局引孫均出手射殺。這里,更夫作為被審案犯出場后,依然繼續作案,既借副統領的刀殺了正統領,又以自己多重案犯被殺滅口的嫌疑點拖孫均入局。當時人們只目睹了小小更夫死到臨頭的囂張和慘烈,卻看不出他以自己的性命為誘餌來操縱目標人物的謀劃。同時,也是從更夫死于宅院大門外這一幕開始,觀眾方知門外依然是宰相麾下嚴陣以待的重重禁軍,可以說,宰相在宅院內外的統治權不容撼動。
更夫劉喜殞命,隨著案情線索的拓展,影片向人們呈現了宅院權力場的另一重附屬空間——下院。在這個孫統領不屑步入的下人們生活起居的院子內,觀眾一方面發現了人間煙火般的普通人的溫情和色彩,另一方面也發現了無辜的“草芥”張大原來是攪動宅院局勢的核心人物。張大和更夫、新出場的車夫都是刺殺事件的行動組成員,“劊子手”孫均不過是他們要拿下的一個棋子,而宰相面對的隱蔽對手也是宅院內這組聯手的小人物,尤其被他們截獲的密信是標記宰相政治污點的把柄。
這組依次出場的行動小組的力量雖然較之宰相的勢力弱小單薄,但他們籌謀已久,并懂得整體布局和借力打力,尤其是借助官場的游戲規則來展開遞進式反殺,即借助隱秘的權勢變化來展開逆向操縱。更夫丁三旺利用正、副統領之間的嫌隙借刀殺人,馬夫劉喜重新分析局勢后,以拋出密信為籌碼,決意離開下院到上院與最強對手——宰相府總管何立交手,最終訴求是借助密信激化宰相小陣營的矛盾。果不其然,密信出場后,整個宅院內的權力面貌急遽復雜化,高層行動組的查案進度幾近僵滯,影片重心也從小人物刺殺行動中的互相成全、接力推進轉移到上層人物之間的各懷鬼胎、相互算計。
更夫招供后,案情重心已不再是追查嫌犯,而是主審成員之間如何化解后顧之憂的問題,尤其是如何面對宅院一把手的政治“忌諱”這一官場難題。宰相的底線不能觸碰,副總管武義淳亮出御賜金牌后,宅院秩序之上疊加了皇權牽制,使得局勢走向更加復雜。因而,無論是何立藏信、孫均偷信、全體人員不敢看信,還是四人飲茶時的攤牌較量,都是官場高層日常面對的生死考驗。影片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描繪出了官場轄制的細節,張大他們就是抓住了這一官場操縱的要害,才能夠招招反制宰相的心腹要員。當統領、總管以他們生命個體的專業本色面對案情時便能夠頭腦清醒、決斷明快,一旦牽涉勢力陣營和官場規則,便淪為了權力結構的人質,首先要想方設法明哲保身。他們就像賈雨村在亂判葫蘆案中扮演的荒誕角色,“表面上是喜劇,內里則是一個士人沒有自由、沒有靈魂主體性的深刻悲劇”c,這也是孫均為何奉命查案卻極力回避案情敏感點的荒誕緣由。
《滿江紅》偏重于喜劇色彩,但喜劇比悲劇更殘酷,它粗暴地向人們揭示了一個無意義的掙扎空間。影片在拆封密信環節,全方位呈現了劇中幾位人物自然而然的滑稽相,身為草根的張大也天衣無縫地配合著高層權貴幾經歷練的官場默契。“拍電影是為了給人們一些東西,把他們送到一個別的地方,不管你是把他們送到直覺的世界還是智力的世界”d,此時的密謀現場沒有英雄的維度,沒有正義的品質,沒有王者的哀傷,只有鏡頭聚焦下的活命藝術,與這樣的官場人格相呼應的“藝術將會是智慧的笑聲”e,影片這里一本正經的戲謔也是它對現實世界的權力異化所盡的審視職責。
除了自上而下的權力秩序,空間布局在中國文化中也與權力邏輯和操縱美學密切相關。無論是建筑物中軸線的方位坐標,還是當下現實名利場中對“C位”的講究,都是權威與能量在日常生活中的審美輻射。在影片《滿江紅》的宅院內,除了與上院相對照的下院外,更有與所有人形成空間區隔的宰相樓。從電影中下屬人員幾次隆重地凈身上樓面見宰相的繁復程序,可以看到,掌管千軍萬馬的宰相幾乎杜絕任何人的靠近,這種高高在上的防范手段和地位象征為他本人營造出一種駕馭全局的神秘感。宰相不輕易接近任何人,也不信任任何人,重要的是,人們對這種不信任與非人性化的操縱完全適應。這也意味著居高臨下的宰相在這個權力空間內為所欲為的任意性和荒誕性,而下屬的不敢造次與投其所好就成為他們必然的生存路數,這也使得宰相在很多時候尋求真相卻難以接近真相。
影片以宅院的微縮結構作為透視權力場的一則寓言,讓人們看到底層力量在權力秩序內尋找切入點和權力跳板接近權力核心的可能性和風險性,尤其是消除雙方的物理間距以實現現場對話所面對的挑戰性。在以絕對服從權力秩序為行動依據、以職級升遷為行動指向的體系內,不必說社會各階層之間難以溝通,即便上下級之間、主仆之間的相處之道也高深莫測,這與《左傳·莊公十年》中曹劌向魯莊公論戰于軍前,《莊子·天道》中輪扁斫輪于齊桓公堂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中許行求田于滕文公門內等場景所描述的人際關系——君民之間、肉食者與草根之間溝通對話的暢通性截然不同,影片中的權力秩序和空間隔離表明社會各階層之間對話的渠道已經蕩然無存,剩余只是不擇手段的防范。然而,再清晰的權力構架也有模糊其邊界的力量,在嚴密的權力場中卻交織著人倫親情,執法者與嫌疑人之間的舅甥關系,就是影片喜劇性與反轉性的基點。尤其是孫均作為暗殺與追殺兩股力量的交叉點,雙方都在利用又都在爭取他,宰相用升遷職位來操縱他,張大用斷其后路的手段來操縱他。
張大的計劃并不具有貫穿始終的連貫性,“某種意義上,張大的計劃是角色行為相互對照辯證法作用的結果,而非張大設計的結果”f,但是他利用政治把柄和游戲規則來牽制對方的操縱邏輯是一以貫之的。這種以卵擊石的操縱和較量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下下策,因為在宰相的勢力范圍內,但凡與其意圖相異者,即便是持有金牌如副總管武義淳都免不了一死,何況他人乎?影片的可取之處在于它沒有泛泛而談匹夫對天下興亡的職責,而是具體呈現匹夫如何在壓制他們的嚴密秩序下邁出了膽敢與宰相“洽談”的一步。他們處心積慮地以暗殺手段接近宰相,亮出密信卻始終遮掩信件內容以創造對話機會,因為“對話結束之時,也是一切終結之日”g。
事實上,推動影片案情進展的內在張力是張大與宰相之間互換籌碼的對話訴求,在各自獲取信息和真相的道路上,“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h。只不過,“這種‘對話不是原來在語言范疇里的‘對話了,它們既可以是彼此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也可以是一種理解、解釋、重寫、重建”i,效用兵與宰相之間的對話是一種跨越社會勢位的暴力性溝通模式,背后體現的也是存在于社會文化結構內民間與官方之間價值錯位后的沖突性爆發。這種極富張力的逆向交鋒,有點像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里“以下犯上”的藝術構思。嘉靖皇帝一時意氣,為失勢的嚴嵩打抱不平,之后有口皆碑的“六必居”醬菜無人再敢問津,海瑞卻賦予了“六必居”j站得住腳的另一重闡釋內涵,以激活社會文化結構內被專制秩序阻斷了的對話機制。專制權威嚴酷而不容冒犯,人們對卷入是非的人事避之不及,唯獨海瑞以筆來進行正面回擊,而張大則以謀略來進行暗自較量。
二、內與外:敵我分界與權力制衡下的身份撕裂
對權力機制的動態呈現是影片最具藝術捕捉力的層面,如上文分析,這種操縱邏輯可以成為任何一個時代權力異化的縮影,它是詩與想象的領地,并不僅僅聚焦于產生《滿江紅》這一詞作的社會。而且,操縱總是高對低、強對弱的權力實施,即便如上文探討的逆向操縱,也是對同一套權力操控邏輯的巧妙利用,尤其離不開宰相的權力場。《滿江紅》中小人物與大人物的“對話”搭建只是一種靠制造意外介入權力規則后的僥幸實現,與現代哲學中,尤其哈貝馬斯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所呼喚的理性與平等的對話模式并不是一回事。此外,當影片的寓言架構落地,宰相宅院的操縱權力場安放于南宋初期家國興亡的處境后,便將這套官場生態推向了更具體的歷史時空,疊加了人們國仇家恨的價值判定與文化撕裂后,也將影片的人物和話題置入了更具立體性的存在界面與時空切面,尤其是靖康之變前后的民族對決與金、宋皇室之間的操縱與制約這一大背景。
前岳家軍成員張大是宰相府刺殺金人事件的驅動者,這一行動除了要掌握權臣秦檜的通金把柄外,背后更大的推動力就是對民族大義的捍衛與擔當。面對國仇家恨與民族恥辱,尤其是家園遭受金人踐踏屠戮的南宋百姓,無法接受南宋朝廷一味稱臣納貢的討好卑怯,更無法接受南宋軍隊面對金人的癱瘓軟弱。曾經的青樓女子以歌姬身份自作主張加入心上人的刺殺計劃,親人被金人殺戮就是她尋找機會刺殺求和派主帥秦檜的本能反應,在目睹了宰相宅院內的兇險狠毒不亞于金人后,更加堅定了她的刺殺決心。影片《滿江紅》不但呈現了這一時期百姓和將領面對朝廷無所作為的壓抑和絕望,也從微觀層面描繪出南宋告饒求和的主導態勢下存在的更為多元的歷史豐富性。
當金廷傳譯在禁軍前叫囂——“宰相的令管得了金人嗎?宋人的令管得了金人嗎?”,當孫統領與禁軍將士面對其挑釁束手無策時,張大卻手起刀落斬了對方,并當場奚落孫統領的窩囊。由于南宋朝廷的和議立場,破壞和議就是破壞國事,宰相麾下的將士無人敢輕舉妄動,這使得占有和議掌控權的金人在各方面都碾壓了淪為下風的南宋臣民,包括南宋的法令。影片中,金庭傳譯挑釁被殺的這一場面極具張力,一方面為體現張大敢作敢為的岳家軍本色做鋪墊,另一方面更具沖擊性的效果是金人這句質問形成了對中國傳統皇權專制的質疑和解構,致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一封建王朝的絕對敘事在這個宋金議和的局勢下失效了。結合歷史背景,南宋初年的朝政國運疊加了皇室內部的權力爭奪,宋高宗趙構對待金人的立場、對北伐的態度背后夾雜著自己對皇位的考量,在位者的私心與權欲也造成了岳飛被殺、南宋初期宋人屢屢遭受金人拿捏欺凌的命運。在戰場與朝政的對決和斡旋之外,南宋君主一度被金人以皇家人質操縱制衡,朝廷的窘態尚且如此,更不必說百姓的處境。
在宋金對峙的動蕩局勢下,影片呈現了多組對立的二元要素,比如漢文與金文、漢幣與金幣、替身與真身、墨與血,甚至岳飛與秦檜等,電影用這些多元并置的文化細節來切近當時復雜多面的歷史狀況。即便秦檜一行浩浩蕩蕩氣勢十足,金庭禮儀官和傳譯官兩人就讓宅院上下壓力重重,宋人與金人之間敵我對立的身份敏感性存在于任何場合。敵我分界的張力外,同時還存在有文化的溝通與排斥問題,而且文化元素會隨著雙方境遇的改變體現出溝通與屏蔽的雙重功能。如電影里一直強調密信使用的語言問題,由于金文與漢文的語種差異,信件的內容解碼被借故一再延宕;又由于金人和漢人銀子火印的標記差異,更夫以銀子大做文章,給王統領扣上了通金罪,由民族的敵對上升到了文化元素的敵對。不過正如人們指出影片不少環節存在邏輯漏洞一樣,導演張藝謀想表現“小人物在困局中的掙扎”k,但是也有將文化元素道具化或夸大化之嫌,比如將銀子設計為通金證據就缺乏說服力,民族矛盾是事實,但宋金的地緣關系與錯綜復雜的文化交往,就像會有宋人識得金文一樣,貨幣的流通未必像敵我陣營一樣有清晰的界限。
正是宋、金之間的敵對與敏感關系,使秦檜的通金證據——密信在影片中發揮了四兩撥千斤的威力。面對南宋的屈辱與劫難,人們對岳飛的含冤去世大有一種“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遺恨。因而,岳家軍有生力量的使命不只是無政府主義式的刺殺,更是要讓南宋上下不要丟掉岳飛的抵抗精神與民族信念。因而,即便在秦檜當道的局勢下,南宋的社會空氣中并非沒有彌漫著拒絕妥協的抗金精神。正是源于這種堅實的抵抗土壤,才有影片最后,孫均接替張大以岳飛遺言激活人們心中壓抑著的信念和豪情。孫均以命相搏換來《滿江紅》詞作的重新問世后,也意味著在現實的高壓之下一點點撕開歷史的真相,影片的敘事也指向了一個不再拘泥于當下的未來。未來如何,與每一代人對自己時代的真相打撈、記憶拯救密切相關,因為“忘卻集體的經驗和記憶,也就等于謀殺一個民族的精神生命”l。因而,當孫均釋然地宣告,秦檜殺不掉誦讀過《滿江紅》的幾千禁軍,篤定這首詞消失不了之后,也在兌現“有些事比生死更重要”的信念后,終于擺脫了其一度要褪去的民族“走狗”的身份撕裂。同時,《滿江紅》作為文化的流傳物,也獲得了它與后人對話的生命力,生生不息地流淌在人們的精神血液中,就像影片里桃丫頭在玩耍時的本能默念一樣。
在全軍復誦岳飛遺言時,秦檜本人被迫聆聽《滿江紅》,之后又暫時卸掉一貫的偽裝,與自己一手提拔的新任總管孫均進行了一番設身處地的溝通對話。幾年的籌劃,張大他們利用名節制衡宰相,最終的收獲就是用一隊人的生命掙得了一次底層與頂層的談判,并從歷史的暗影里打撈起岳飛被淹沒掉的遺言,完成了一次信念與現實的抗爭。因而,可以說,影片最后的全軍復誦也是誦讀給慣于滅口消聲的位高權重者聽的,他們需要去“聽”而不僅僅去“令”。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也許黎民百姓希望做的事情大概是像《詩經》的國風時代一樣,能夠大聲說出自己的心聲,如果這種想法已經有人表達出來了,那就要捍衛這種聲音的力量。
三、陰與陽:個體的社會角色與內在生命地圖建構
在家國層面與權力秩序之外,每個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個體也在追求與世界的深度關聯,也在發揮自我生命的最大潛能,可以說,對個體精神追求和生命真相的刻畫也是影片具有超越性的地方。《滿江紅》的色調是黑白相間的,而且整體上體現為灰色。可以說,夜色中的光與影猶如每個人精神世界的圓周結構——陰陽參半。影片中的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心事,每位角色都有不同面向的盤算和欲念,無論社會地位如何,《滿江紅》匯聚的是一群被社會歷練后的智者之間的對決。地位越高,勢力越大的人顧慮也越多,因而不能簡單地認為大人物也怕死就更無恥,影片在風頭變化中挖掘角色的完整人格也是其精髓之所在。權力場中的云詭波譎與個人的手段志向共同造就了這些人物高深莫測的性情,《滿江紅》從世俗的低姿態出發充分尊重了官場的復雜性和人性的豐富面,呈現了人物滑稽卻真實的理性與本能之間的掙扎。
從喜劇的立意來看,影片中的官場派勢和人物手段徹底打破了人們對官場形象的慣常認知,正如電影的陰陽構圖與明暗色差,影片在案情推進中逐漸解構宅院內正與邪、真與假、情與仇、敵與我等情勢的界限,最后只保留了文化的底座作為歷史的價值立場。在局勢的操縱與反向操縱的交鋒中,影片中的大人物沒有被符號化,小人物也沒有成為道德的化身,反而他們身上的靈活性、多面性更有藝術穿透力。同時,影片呈現了位高權重者的私心與算計,也呈現了底層張大和車夫的承受極限,在骨肉親情、至愛親人面前,岳家軍成員也會屈服認命。這點也說明了普通人接受的生存現狀未必是稱心如意的人間天地,歷史的過往也未必是當事人心滿意足的歲月變遷,而是攜帶著軟肋后的無奈和屈從,因而張大等人逆大勢而行的魄力才顯得愈加可貴。
在亂離的時代,不受呵護的每個人都攜帶著時局的刺痛和掙扎的勇氣,即便是影片中最純粹鮮亮的三人,妖嬈嫵媚的舞姬瑤琴與柳燕和青梅兩個跟班兒,也有著她們瞞天過海的執著。但是瑤琴并不是單純的柔弱女子,她敢于打入宰相宅院“圖謀不軌”,可以說她們一行三人自從踏進大門后,就選擇了飛蛾撲火的命運。不像柳燕和青梅如待宰羔羊般卑微無力,秦檜身邊的兩名年青侍女藍玉和綠珠冰雪聰明、身手不凡,擁有近身守候宰相的特權,然而兩人卻是只能默默執行指令的啞巴,這是權力場對人身擁有絕對掌控權的體現,也是多疑狡詐的秦檜為自己私人定制的防身工具,二人的宿命就好比宰相最后踹自己腳下那僵死的替身時所言:“你也配(做回了自己)?”。
影片中的每位大人物都擁有特殊的物件標識自己的特權,總管何立有一把鑲有紅藍寶石的詭刃,而且以玩弄人命來達到逼供目的是他的慣常手段,同時也說明他是憑借自身的手腕才躋身為秦檜身邊的骨干。副總管武義淳攜帶一塊御賜金牌,在宰相府里是一個有背景的人物。孫均的臉上烙著自己戰場上幾經歷練留下的傷疤,手上的砍刀也能瞬間殺人于無形,他的兩次職位升遷也體現出他將作為新一代宰相府紅人的潛質。
小人物沒有任何特權卻膽敢興風作浪,他們的戰略就在于操縱邏輯下的義無反顧,不到生命最后一刻絕不放棄每一次出擊。大智若愚的張大擁有高明的偽裝技巧和高超的操縱本領,他在初次面見秦檜時的油嘴滑舌,在審理舞姬時的流氓做派,在審理更夫時的煞有介事,直至和車夫接頭后人們才認識到這個偽裝者身上的使命,可以說,他在一個時辰內的百般變通也是影片對這個角色立體性的不斷敞開。張大被逼手刃車夫后,在巷子里幾近崩潰時還不忘用言語點撥孫均,煽動其對何立的反感。當再次與瑤琴相見后,電影進一步揭開了這個粗中有細的小混混的人生另一面——他是瑤琴重情重義的丈夫,可知他在為案情奔波的一個時辰里所背負的心酸和焦灼。最后岳家軍的身份曝光,更是給他在岳飛被殺后的四年里的等待和謀劃安放了一個堅實的信念基座。不過,岳家軍的地下身份從邏輯上講沒有問題,從電影語言的設計和藝術呈現上就顯得過猶不及,因為張大的篤定完全可以是內在的,以他的變通性和成熟度無須在脊背上留著一個標記來標注底色。總之,張大身份的一步步疊加也伴隨著他的潛力的一層層拆解,但他以自己強大的生命力至死不渝地推動著計劃向前推進,直至在墻上默寫出整封密信的內容時,他的形象已經可以和在墻上寫下一百零一字遺言的岳飛的形象化合,當斃命于宰相面前時,他以整個生命與現實展開對話的腳步才徹底停歇。
張大在夜色中行走,身子位于巷子里有光的部分,但他不得已一路布下對目標人物的圈套時,內心也免不了凄涼和撕裂。張大懂算計善操縱,他是正義使者,但也墮入了無間道的深淵,這一點在丁三旺和劉喜身上也一樣。他們都在信念的推動下,過著陰陽參半的人生,不僅是身份的偽裝,更有以暴制暴的血腥和傷及無辜的酸楚,比如被他們累及的在影片一開始就被孫均斬殺的無知的“草芥”們。更夫丁三旺作為案發現場的直接嫌疑,他從執行行動的那一刻便走上絕路,當張大告訴車夫丁三旺死得慘烈時,不敢想象的是接下來車夫死得更慘烈。車夫有自己的骨肉牽絆和隱忍慈愛,無論是祖傳的玉鐲子,還是活潑的桃丫頭,都是他人生僅有的珍寶,然而這些早已被何立拿捏于手掌心。但是,無論是丁三旺還是劉喜,他們都以自己慘烈的死,或主動牽連或作為人肉道具,依次為孫均脫離秦檜陣營疊加籌碼,尤其是孫均作為一個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人,也在劉喜之死一事上反感何立以殺人進行實驗的下作。
惡人未必兇神惡煞,大總管何立一身青衣一把扇子,儒雅的面相風采背后卻是笑談間草菅人命的嗜血本性。他在嬉笑怒罵中奪人性命,卻玩弄賭博式逼供帶來的快感,似乎別人身死刀下,是由于自己的命運不佳。劉喜暴露后,何立明知真相卻借機看戲,更何況在劉喜暴露前他就已經成了一位伺機捕獲的獵人。武淳義身為副總管卻被人輕視,隨身帶刀又屢次護刀不力,然而這位高階混混卻是皇帝的眼線,這就像那只御賜的“變得像烏鴉的軍鴿”一樣,雖然不具有實際威懾力,卻表明君臣之間利用和纏斗的復雜性,這也是秦檜自身面臨的官場考驗。秦檜貴為宰相,多疑卻是他的處世哲學,甚至不惜代價開發了替身。然而,啟用替身也會造成自我屏蔽后的信息空白,以至于秦檜目睹了替身以自己的名義、職位自我發揮的大戲。雖然不屑但宰相不得不承認,在歷史的波瀾壯闊里,那些被大能量主導的小人物,也有自己對現實和自我人生的主見。
在南宋對金媾和的復雜背景下,大多數官場中的個體無法做到在政治立場上黑白分明,更多的人是如孫均一樣處于“時時刻刻想反,時時刻刻又不想反”的灰色區間。在游戲規則面前,“事物的力量等于事物的道理”m,實干家張大明白只有靈活度足夠高能力足夠強的人才能不斷獲得打入高層的入場券,才能在權力秩序中獲得足夠大的能量去辦成更大的事情。張大也深知他們的前赴后繼充其量不過是小打小鬧,只能對宰相的行動造成干擾,然而更重要的則是扭轉和喚醒一名官員的民族氣節。正是一批又一批捍衛正義的人們的不懈努力,人間正道才得以繼往開來,才能造就秦檜在歷史中被永遠唾棄,岳飛在歷史中不斷地重新出場。孫均最終完成了接力賽的最后一棒,直接與對提拔自己如兒戲的宰相過招,甘愿為了追求一種比生死更重要的東西傾盡所有。總之,孫均一夜之間達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頂峰,最終卻離開了這個權力場。道不同不相謀,有別于求和派的社會力量帶著自己的信念選擇在官場之外流亡,影片也用人物走出宅院的敘事朝向為《滿江紅》的藝術世界打開了新的想象空間。
結語
《滿江紅》是一則官場寓言,民間的草根力量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以獻身權力規則的謀略、決絕來換取與主流權勢對話的能量,最終不但讓位高權重者聽到了他們的呼聲,也使這種呼聲獲得了超越歷史的生命力。這種小人物為了民族大義而抗爭社會強權的信念就如一首詩中所言,“要做到當你離開世界,不僅你是好的,而且留下一個好世界”n。為了人間正道,心懷大義的人們以自己的拼力一搏來標注那個時代的血性,也用行動爆發出了對社會主導力量的一種微弱的反撥,即便如飛蛾撲火,影片《滿江紅》中的一眾義士不愧為那個壓抑的時代讓人活得更像人的人,后人也不會忘記他們對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的期望。
注釋:
a《滿江紅》于2013年1月22日上映,片長159分鐘,導演張藝謀。
b孫均作為局內人,在官場錯綜復雜的局勢中被張大步步策反,焉知秦檜日后不會有更多變數?在南宋初年就敢于宣判當權者秦檜的結局,不能不說是夾帶了劇外觀眾的歷史視角。
c劉再復:《永遠的紅樓夢》,見《〈紅樓夢〉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頁。
d[英]達紐西亞·斯多克編:《基耶斯洛夫斯基談基耶斯洛夫斯基》,施麗華、王立非譯,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頁。
e[美]喬治·斯坦納:《文學與以后的歷史》,見[美]喬治·斯坦納《語言與沉默:論語言、文學與非人道》,李小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頁。
f丁亞平:《〈滿江紅〉:一部“意識影片”的辯證法》,《電影藝術》2023年第2期。
g[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43、344頁。
h[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白春仁、顧亞鈴譯,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43、344頁。
i楊矗:《對話詩學》,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頁。
j劇中嘉靖對“六必居”的解釋是:“六合一統,天下一心”,初衷本是為了糾正拜高踩低的社會風氣,但無奈被政治形勢扭曲;海瑞對“六必居”的闡釋為:六必居,六必者——產地必真,時令必合,瓜菜必鮮,甜醬必醇,盛器必潔,水泉必香。海瑞以尊重醬菜工藝的原則來矯正政治非議對市場秩序造成的壓力,他敢于對風險話題另辟解釋路徑,其實是以知識層面的多元闡釋來打破話語霸權的一種對話實踐。
k張藝謀、曹巖:《〈滿江紅〉:在類型雜糅中實現創作突圍——張藝謀訪談》,《電影藝術》2023年第2期。
l張隆溪:《記憶、歷史、文學》,見張隆溪《文學·歷史·思想:中西比較研究》,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62頁。
m[法]余蓮:《勢——中國的效力觀》,卓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頁。
n[德]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當你離開世界》,見布萊希特《致后代——布萊希特詩選》,黃燦然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2年版,第171頁。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后人類思潮”與文學理論新議題研究》(18YJC751068)]
(作者單位:太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