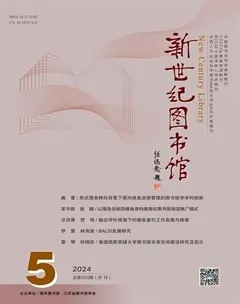形式服務轉向背景下面向信息資源管理的圖書館學學科創(chuàng)新
唐雷
摘 要 “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名稱調整為“信息資源管理”,在此背景下圖書館學的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要主動面向信息時代帶給圖書館傳統(tǒng)服務內容空殼化的挑戰(zhàn)與機遇。數字化信息化正在“掏空”圖書館傳統(tǒng)內容服務,圖書館面臨生存危機,為此,形式化突圍成為圖書館學新的研究對象和命題。圖書館形式化服務需要建立在圖書館的儀式感之上,重塑儀式感是圖書館安身立命的重要實踐,也是學科創(chuàng)新的機遇。
關鍵詞 信息資源管理;圖書館服務;服務形式轉向;儀式感;圖書館學;學科創(chuàng)新
分類號 G256.1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4.05.001
Subject Innov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toward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mal Services
Tang Lei
Abstract The name of the first level disciplin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 Management” has been adjusted to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is context, academic research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should actively fac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traditional service content of libraries, which is becoming shell like. The challenge is that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are hollowing out traditional content services in libraries, and libraries are facing a survival crisis. Therefore, formal breakthroughs have become a new research object and proposition in library science. Formal services in libraries need to be based on a sense of ritual, which is an important asset for librarie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an opportunity for disciplinary innova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Library services. Transformation of service form. Sense of ceremony.Library seience. Disciplime innavation.
2022年9月14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頒布了《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yè)目錄(2022年)》(以下簡稱《學科目錄》),將“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名稱調整為“信息資源管理”,該目錄雖然在2021年12月已提前發(fā)布過相關“吹風”信息,但是在落地后依然引起圖情檔界廣泛議論。眾多學者抱有觀望懷疑的態(tài)度,信息資源管理是怎樣的一級學科,它會對既往的二級學科發(fā)展帶來什么樣的沖擊?傳統(tǒng)圖書館也有這樣的疑慮,當前一級學科名稱語義不明,造成圖書館學的發(fā)展路徑不清晰,以及圖書館實踐的邊界不清楚,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應該怎樣發(fā)展?可以說,這既是圖書館面臨的時代危機,也是信息時代給圖書館學提出的新課題。
1 圖書館危機為圖書館學帶來的挑戰(zhàn)
圖書館學是以圖書館為主要研究對象,關于圖書館事業(yè)的規(guī)律總結和理論概括。因此需要根據圖書館事業(yè)的發(fā)展而改變圖書館學的研究對象、主題、范式、人才培養(yǎng)等,才能保證在學科體系改革中不會迷失方向。在圖書館服務形式的轉向正在發(fā)生的過程中,不能對學科的研究內容視而不見。近年來,頻頻見諸報端的圖書館自習室化、真人圖書館、火車圖書館、地鐵圖書館、患者圖書館、飛行圖書館、移動圖書館、自助圖書館、尋偶圖書館、聲音圖書館已呈現出轉向征兆。這個轉向意義重大,必須引起圖書館學人的足夠重視。“有的學者害怕打破當前的研究態(tài)勢和平衡,既擔心學科更名破壞原有的研究基礎,又擔心更名后不知做什么、怎么做,患得患失,迷茫失措”[1]。作為圖書館學人,應該正視圖書館的生存形勢的重大變化。如何正視并應對它,考驗著圖書館學學者的智慧。
如火如荼的信息技術革命加快了人類文明發(fā)展,影響波及圖書館領域。快餐文化造成需求變化,數字技術帶來功能轉移,數字化正在“掏空”圖書館傳統(tǒng)服務內容。圖書館規(guī)模越來越宏大,館藏越來越豐富,服務越來越精細,富麗堂皇的建筑里,雖然擺放著舒適的沙發(fā),售賣著香濃的咖啡,提供著大開放的借閱體驗,可是讀者到館不讀館藏,自修在圖書館成為常態(tài)。在圖書館形式不斷膨脹的過程中,以館藏滿足閱讀需求的服務內容卻落空了。
傳統(tǒng)圖書館的藏書、借書、讀書功能依托的是宏量的紙質圖書,以及讀者到館實現服務。數字化時代不再強制讀者親臨圖書館現場,也不再憑紙而讀,而是直接獲取“比特”。數字技術的去中心、去物質,彌散化、形式化,正從多方面解構圖書館的現代性。網絡就是一個巨大的圖書館,無需進入圖書館實體,足不出戶就可以獲取需要的知識信息,這在傳統(tǒng)圖書館時代是不可想象的。那時的圖書館是知識中心,讀者視館藏若珍寶,圖書館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居于無可動搖的中心地位。后現代圖書館作為內容中心的地位搖搖欲墜,數字技術正在不斷“掏空”圖書館的服務內容,正使圖書館服務從大內容到微內容,再到無內容、空殼化。圖書館服務的空殼化,囿于圖書館藏書借書讀書活動的急劇弱化,圖書館功能需求的轉移或喪失,傳統(tǒng)業(yè)務內容的空心化。
服務的“空”內容讓圖書館的生存面臨挑戰(zhàn),部分學者開始了圖書館危機研究。1965年互聯網開山領袖之一J·C·R·Licklider的《未來的圖書館》問世,該書指出:隨著新技術的推廣普及,圖書已不再是理想的信息貯存物,當人們拒絕接受圖書是一種有效的信息傳播機制時,他也會拒絕圖書館[2]。1978年美國圖書情報學家F·W·Lancaster 的《走向無紙信息系統(tǒng)》一書出版,該書首次提出了“無紙情報系統(tǒng)”的概念,大膽預測電子資源將代替紙質讀物進入人們的閱讀生活。“隨著電子資源的日益重要和紙資源的日益減少,隨著計算機終端在辦公室和家庭日漸普及……圖書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3]。1982年他的又一著作《電子時代的圖書館與圖書管理員》發(fā)行,該書對新的情報系統(tǒng)下圖書館及管理員的未來圖景進行展望,進一步確定其預測,認為“在下一個二十年(1980—2000),現在的圖書館可能完全消失”[4]。這種預測性的研究發(fā)生在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現代信息技術迅速發(fā)展并逐漸普及的背景下,預測新技術變革對傳統(tǒng)圖書館事業(yè)正在造成和即將帶來的沖擊,對新技術背景下圖書館紙質館藏及業(yè)務的現狀和未來均持一種悲觀態(tài)度,其觀點被定性為“圖書館消亡論”或“危機論”。
半個世紀過去,人們發(fā)現圖書館不僅沒有消亡,反而通過不斷吸納新技術,完善業(yè)務模式,大有與新技術共舞走向新生之勢。正當“圖書館消亡論”引發(fā)的轟動效應漸趨衰減之時,2011年1月2日,美國《高等教育紀元》雜志刊發(fā)了Alfred大學用戶培訓館員T·Sullivan的《2050年學術圖書館尸檢報告》[5],再次在圖書館學界掀起波瀾。該報告指出,學術圖書館將會死亡,其作為大學心臟的作用也將會被世界遺忘。
圖書館面臨的時代危機是圖書館紙質資源的閑置,基于紙質資源的傳統(tǒng)管理與服務模式過時。但是,紙質業(yè)務的危機必然意味著圖書館的危機嗎,圖書館的危機必然意味著人類文明傳承與傳播的危機嗎?究竟該站在怎樣的立場才能看清楚由信息技術革命帶給圖書館的這場變局,這也是圖書館學面對的新問題。
2 信息時代給圖情檔學科研究帶來的新變化
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圖書、情報、檔案這些與信息有著天然聯系的學科看到了崛起的契機,以對標信息作為研究對象成為更名“信息資源管理”的時代要求。
1983年第一次編制《學科目錄》時圖情檔分屬文學、理學、歷史學門類之下,1990年《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yǎng)研究生的學科、專業(yè)目錄》在管理學門類下設1205圖書館、情報與檔案一級學科,首次將圖情檔聯姻,統(tǒng)轄三個二級學科:120501圖書館學、120502情報學、120503檔案學,這意味著原圖情檔專業(yè)開始向多學科融合方向發(fā)展邁進。
然而,“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建制為一級學科,是對二級學科的機械羅列,在學科專業(yè)目錄中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特殊存在,起不到挖掘下級學科共同內涵的統(tǒng)領作用,同時又對研究對象的外延進行了圖書館、情報所、檔案館的場所限制。由此造成“圖情檔學科長期在各個學科門類中寄居流離,社會認知度不高,考生報考意愿低,總體辦學規(guī)模小,在各辦學院校中的話語權普遍不強,甚至出現因專業(yè)教育與社會實踐脫節(jié),圖書館不愿招圖書館學畢業(yè)生的怪相”[6]。在這樣的狀態(tài)下,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之下的本科招生淪落到以調劑為主,甚至有考上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的考生也因此沖淡了讀北大的喜悅。雖然《學科目錄》是針對研究生的招生培養(yǎng),但對本科招生導向作用顯著。
為了更好地體現一級學科在信息時代的學科屬性,圖情檔學科其實早在1992年原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宣布“情報”改“信息”不久就有“轉型”的意識。1997版一級學科名稱微調為“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后,北京大學便將圖書館學情報學系改名信息管理系,此后三年十多所高校將系名改為信息管理系,比如2001年武漢大學將原圖書情報學院更名為“信息管理學院”[7]。可以說,高校院系改名信息管理是一級學科調整的推手。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以學校名義向國務院學位辦提交了近萬言的將研究生學科專業(yè)目錄中“圖書館、情報與檔案管理”一級學科和本科專業(yè)目錄中“圖書檔案學”一級學科,統(tǒng)一更名為“信息資源管理”的調整建議書[8],其后學者們進行了數年學科更名的討論和努力。
2011版再去標點,簡稱為“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并放權學位培養(yǎng)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一級學科更名,作為信息資源管理的基礎二級學科圖書館學的地位不可能不動搖。從四、五版《學科目錄》之下不再列出二級學科和圖書館學,由招生單位自主設置可見一斑。2018修訂版保留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為學術學位,加設“1255圖書情報專業(yè)學位”。2022版1205一級學科更名為信息資源管理,可授予碩博士學術學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1255僅授圖書情報碩士專業(yè)學位。可以說,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這個頂層設計在于要求學界能進一步把握業(yè)界在信息時代的轉型趨勢。
3 圖書館服務形式轉向為圖書館學帶來的機遇
“內容與形式二元范疇在古羅馬時代出現……將‘內容與‘形式放在同一層面”[9]。黑格爾等哲學家認為內容和形式是一對辯證范疇,內容是事物一切內在要素的總和,形式是這些內在要素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具體到圖書館,傳統(tǒng)內容是藏書、借書、還書的功能服務,形式是行使這些功能的結構和組織方式。信息化造成圖書館服務內容空心化的現實,藏借還書服務內容的日漸式微威脅到了圖書館的生存和價值,發(fā)掘形式化服務是業(yè)界近些年應對這種情況而進行的一系列實踐和突圍。當前,多數學者能夠接受的觀點是數字化進一步拓展和延伸了傳統(tǒng)圖書館的功能,推進傳統(tǒng)圖書館與數字圖書館融合,為用戶提供智能化、泛在化的服務。那么,相對服務內容的關注,筆者為什么特別強調圖書館服務形式化轉向?是為了請學界注意新形勢下服務重點不再以館藏紙質資源為主要服務內容,而是注重服務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各種形式翻新已成為圖書館界引人注目的新現象。圖書館因應數字化、信息化的創(chuàng)新形式,將成為圖書館學無法忽視的研究課題,而研究課題的創(chuàng)新才能帶來圖書館學的創(chuàng)新。
3.1 加強圖書館空間改造研究
圖書館紙書借閱下滑造成藏書功能空間閑置和其他功能空間需求緊張,這引發(fā)了一波長達二十余年,至今方興未艾的圖書館空間改造運動。“信息共享空間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美國興起的一種新的學習模式”,2005年吳建中發(fā)表《開放存取環(huán)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間》,首次向國內介紹了圖書館“空間”概念[10]。“2015 年到2017 年是圖書館空間再造發(fā)展的激增期,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發(fā)展迅猛,研究的學者不斷增加,研究不斷深入”[11]。21世紀以來,圖書館新館、分館建設熱火朝天,在藏書之外建立了大量的讀者活動空間,這些空間較之藏書主功能呈弱功能化,成為功能不確定的剩余空間。“創(chuàng)客空間、咖啡吧、影視欣賞室、教師備課室、錄播室、晨讀室、照相室均有”,“開放了攝影間、預演間、書法間、棋藝間等新功能區(qū)”[12]。空間形式一言以蔽之:“集文化交流空間、學術空間、社交空間、休閑閱讀空間、體驗空間于一體”[13]。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寬泛,空間改造還要分區(qū)分眾,于是“擴充了兒童、盲人、教師等特種區(qū)域,對讀者空間根據讀者類型進一步加以細分”[14],精準讀者服務。
各種功能空間的分區(qū)探索,其共同特征都是不再像傳統(tǒng)圖書館的固定空間那樣承擔固定的借閱主功能,而是由可變空間承擔弱化的剩余功能。這些實踐被敏銳的學者觀察和反映在圖書館學研究中,有人開始質疑空間改造和空間服務偏離了圖書館的主業(yè)務,是圖書館的自殺式拯救,會最終傷害圖書館事業(yè)和自戧圖書館學。試問守住空無一人的書庫,就能使圖書館高枕無憂嗎?當紙書成為獲取信息最慢最不方便的途徑時,當實體借閱下滑趨勢不可遏止時,圖書館就不能不做出改變,同樣圖書館學的研究重心也不得不隨之而變。
3.2 加強圖書館網絡信息服務研究
一級學科更名強調信息資源管理,是符合圖書館是知識圣殿這一功能的,知識是由信息構成的,是經過積淀被認可傳承的信息。紙本圖書被視為知識的集合,在掃描轉化為電子圖書之后成為方便獲取的信息。無論是紙質資源還是數字資源,人與資源之間的對接關系可以概括為:人尋找資源;資源吸引人。傳統(tǒng)圖書館以前者為主要服務內容,數字圖書館則憑借后者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對相同資源感興趣的人聚攏到一起,談論它,使用它,分享它,就形成了資源社群。圖書館要做的是以資源為媒,搭建人與人之間的局域網。讀者與讀者組成閱讀社群,社群與社群組成閱讀共同體,個體在共同體中獲得歸屬感,既可以用自己的閱讀貢獻于共同體,又能夠從共同體中獲得滋養(yǎng),在閱讀中實現社交。高校圖書館可以搭建館讀群,來連接圖書館與讀者、讀者與讀者,形成校園閱讀共同體,使讀者產生泛在的歸屬感;還可以搭建館院群,學科館員嵌入院系服務,讓教師需要的教學參考書、科研檢索等服務隨時在線,讓學生需要的學習參考書、文獻檢索技能培訓服務適時出現,不僅有成熟的參考咨詢服務,還會有閱讀筆記、心得評論等隱性知識留痕下來,成為具有本地特色的留痕數據庫,貢獻創(chuàng)新服務。條件成熟后,還可以利用VR、AR、MR技術打造虛擬圖書館,讀者就有望置身元宇宙圖書館了。這些網絡服務是圍繞資源進行的,只有服務形式被不斷推陳出新才能更好地服務于讀者。
3.3 加強圖書館閱讀推廣研究
圖書館網絡服務包括部分閱讀服務,但閱讀推廣是圖書館的核心任務,需要集中觀察。近幾年的閱讀推廣很大程度上也是形式服務,而不只是內容服務。國家及政府層面自2012年開始不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倡導全民閱讀,2016年出臺的《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三個五年規(guī)劃綱要》將全民閱讀工程列為十三五時期文化重大工程之一[15]。閱讀不再是自然需求,而需要推廣,推廣形式就成為圖書館的創(chuàng)新點。
本文作者所在的魯東大學東區(qū)圖書館自2013年至今一直與學生社團璜山讀書社合作舉辦“徜徉璜山,同讀經典”的閱讀推廣。形式力求多樣。筆者為讀者作《傳奇女子楊絳先生》、《追逐路遙感受人生》講座;擔綱“捧讀莫迪亞諾”“跟隨三毛”沙龍主講;舉辦莫言、劉同作品分享會;動員歌德閱讀機下載,撰寫“揣本電子書回家過年”招貼;同讀《看見》,作文示范評論;發(fā)布疫情畢業(yè)季捐書倡議。自制作者作品介紹海報、讀書心得留言簿、文學評論校報推薦比賽、館讀面對面現場交流、書中名言書法大賽、送繪本進幼兒園……在各種形式的閱讀推廣活動中,館員變身設計師、教師、精神療愈師、編審、評議工作者……
公共圖書館招募閱讀推廣人[16],舉辦短視頻推廣[17]、讀者薦購[18]、家庭閱讀指導[19]、閱讀療愈、主播推廣、AI推廣、文創(chuàng)推廣、手作推廣等活動屢見報道,這些閱讀推廣的重點已經不是靜靜地讀書和讀書內容,而是怎樣設計吸引讀者讀書的形式。
4 一級學科更名背景下的圖書館學學科創(chuàng)新
讀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促讀,甚至閱讀本身已經成為圖書館組織活動的一個“賣點”,服務的形式轉向同時帶來了人員管理、資源建設、標準規(guī)范、信息技術等變革。數字信息唾手可得,造成藏書空間功能上的剩余,剩余空間被改造,挪作其他空間,組織各種看似與圖書館無關的業(yè)務,引發(fā)了圖書館人的集體憂慮。在學科目錄最新一輪調整出爐之前,圖書館學界專家學人已經多次爭鳴探討,涉及方方面面,其聚焦的核心是未來圖書館學的出路問題與人才培養(yǎng)方向問題。
4.1 正確對待學與術,從內部與外部建制上進行學科創(chuàng)新
《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yè)目錄》是國家進行學位授權審核與學科專業(yè)管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yǎng)工作的基本依據。名變了實就要變,才能名實相符,積極推動更名的初景利倡導:“需要學界業(yè)界加大對作為一級學科的‘信息資源管理的概念與內涵、意義與價值、范疇與邊界、方法與技術、學科與理論、應用與成效、規(guī)劃與未來的認知與研究,推動一級學科從名稱(名)到內容(實)的根本性轉變。”[20]定制學科目錄是學科建制的初始階段,變更目錄意味著信息資源管理統(tǒng)轄下的圖書館學新的學科階段開始起步。學科建制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內部建制,另一個是外部建制。內部建制設置相應的教學任務,組織學科研究和培養(yǎng)學科人才。外部建制主要指相應學科的社會組織,承擔社會分工、管理、內部交流機制等。這兩者分別是對內在觀念和外在社會的雙重探討,內部觀念建制是源泉和根本,而外部建制是學科范式外在社會形式的延伸,更是促進學科內在建制成熟的條件。“學”與“術”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學”的目的是為了“用”,而運用實際上會更好地反哺“學”。外部建制上,圖書館界進行了大量的形式化“術”的探索,圖書館學應將之納入專業(yè)術語、理論體系的范式研究,促進學科內部建制的成熟。學科是知識建制,學科知識編制在溯源固本的基礎上,還要大力發(fā)展學科外延,模糊知識的邊界,廣泛開展對其他學科基礎知識的通識教育。這就要求在課程編制上要突出作為信息資源管理學科的多元屬性,巧用舊資源,圖書館學涉及被實踐檢驗的信息,情報學涉及當下的信息,檔案學涉及歷史的信息,與其他二級學科,如信息資源管理、信息分析、出版管理等,共同支撐著一級學科。學問分支的建設目的要適應現實的變化,重新對學問分類,體現信息資源管理的學科思想。既要注意二級學科之間的信息共融,又要保持學科獨立,在守住邊界和開拓疆域之間尋找平衡。為何要調整學科目錄,就是要聚焦學科力量,搭建學科隊伍,進行學科創(chuàng)新。
4.2 強化圖書館形式服務研究是圖書館學的一個創(chuàng)新路徑
半個多世紀的圖書館危機研究并沒有唱衰圖書館,相反芬蘭花費9800萬歐元建設赫爾辛基圖書館,出手如此闊綽不過是讓市民進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圖書館設計的前期調研就是滿足市民愿望,可以在館里免費學習各種技藝,也可以不看書、不學習。同樣斥巨資打造的上海圖書館東館是國內單體建筑面積最大的圖書館,以22個主題空間成為市民的“書房、客廳、工作室”。網紅打卡地天津濱海新區(qū)圖書館入門大廳的書山上畫滿了假書,不能取閱,卻給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儀式感。是的,儀式感,正因為圖書館是裝載知識的圣城,進城是來朝圣知識的,一如德布林筆下的煙囪工感到“圖書館里的書久而久之一定會對四周的墻壁產生影響”,懵懂闖入了象征知識的儀式性世界,“不讀書而讀書”,從而成長為“一位態(tài)度嚴肅、深思熟慮的人”[21]。不讀而讀,不只是弗里德爾,每個人進入充滿知識的圖書館,看電影并不像在電影院,喝咖啡也不似在咖啡廳,空氣中恍惚擠滿了圣哲先賢給我們留下的書香真理。千年圖書館積淀了這份揮之不去的儀式感,弗里德爾從中獲取的是一種環(huán)境熏染的收益,這份收益并非來自于圖書館的內容服務,而是圖書館的象征性儀式與讀者交感思維交互感應的結果。它提醒我們——圖書館的象征性儀式是一筆重要的發(fā)展資源,交感思維作為一種普遍的人類思維,其中蘊藏著用戶對圖書館形式的豐富需求,把圖書館的形式研究置于儀式感之上是圖書館學的嶄新思路。圖書館學的形式研究關注的是圖書館服務的結構和組織方式,圖書館形式研究之所以能夠建立于儀式感之上,在于無論什么樣的服務形式都是發(fā)生在圖書館這個具有儀式感的平臺上,保證了圖書館服務形式的邊界、合法性與感染力。
4.3 著眼專業(yè)性和挑戰(zhàn)性,創(chuàng)新圖書館學人才培養(yǎng)
信息資源管理研究有更多的學科交叉基因,需要多學科支持,人才培養(yǎng)既要打通學科壁壘,又要突出學科特點,守正創(chuàng)新。圖書館人才包括學術和實踐兩類人才。譬如,高校圖書館學科館員是外聯院系的實踐人才,既要有圖書館學知識,又要有對接專業(yè)的學科知識,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正是圖書館學人才培養(yǎng)的重點。圖書館學本科教育遇冷,有著更加清晰職業(yè)規(guī)劃的碩博士教育卻是熱狀態(tài),是因為有更多發(fā)展可能的本科生看不到圖書館的職業(yè)前景,當藏書借書遇冷,甚至圖書分編外包,仍然培養(yǎng)大量的分類編目人員,圖書館如何容納得下,職業(yè)的前途在哪里?信息平臺、學術集市、信息眾籌眾包等服務的專業(yè)性和挑戰(zhàn)性抬高了圖書館學的技術門檻和學習成本,這樣的圖書館學人才培養(yǎng)會從過程中規(guī)避圖書館不要圖書館學畢業(yè)生從事圖書館工作的錯誤。學術人才的培養(yǎng)不妨著眼于物理圖書館與形式圖書館的關系、信息技術時代圖書館與人類的關系等命題的探討,這樣既有形而下也有形而上的思考。
5 結語
圖書館變成自修室,不是圖書館的主動改變,而是被動改變的結果。這未必是壞事,為何讀者選擇圖書館作為自修室,因為圖書館的儀式感。紙書遇冷,圖書館卻是巨資打造的熱狀態(tài),基于儀式感的形式化轉向拯救了圖書館。建造圖書館呈現熱狀態(tài),研究圖書館的圖書館學卻處于冷狀態(tài),我們拿什么來拯救圖書館學?
“隨著豐裕社會的來臨,越來越多的剩余物在被‘去功用化或‘抑功用化處理,從而轉化為表意的形式”[22],這句話也可以用來闡釋圖書館或被迫或主動的轉型處境。所謂圖書館的危機其實是圖書館的轉型,如何轉型化解危機,需要我們洞悉這場危機的本質,進而提出有效的干預措施。從伊尼斯媒介偏倚[23]的視角審視當代圖書館正在面臨的這場變革,會發(fā)現圖書館的功能正在由偏倚時間的文化傳承向偏倚空間的信息散播位移(有些圖書館改叫圖書信息館),圖書館作為文化機構的偏倚時間的媒介屬性與作為信息組織的偏倚空間的媒介屬性之間正處于一種失衡狀態(tài)。化解圖書館危機的根本辦法是重構圖書館的功能與屬性,協調圖書館文化屬性與信息屬性之間的沖突,恢復其在偏倚時間的文化傳承與偏倚空間的信息散播之間的平衡狀態(tài),加強圖書館的儀式化服務為這個矯正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操作空間,也為圖書館學在新語境下的開疆拓土找到了邊界和支撐點。
*本文系教育部研究規(guī)劃基金資助項目“面向空間改造的圖書館空間失效研究”(項目編號:23YJA870008)研究成果。
劉瓊,劉桂鋒,盧章平,等.開放與進取:“圖情檔”一級學科更名為“信息資源管理”[J].圖書館論壇,2022(6): 20-27.
LICKLUDER J C R. Libraries of the Future[M] .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 .
LANCASTER F W.通向無紙情報系統(tǒng)[M].莊子逸,等,譯.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8.
F·W·蘭開斯特.電子時代的圖書館和圖書館員[M].
鄭登理,陳珍成,譯.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 1985.
SULLIVAN,BRIAN T. Academic Library Autopsy
Report[EB/OL].[2018-07-02].http: //chronicle.com/article/Academic-Library-Autopsy/125767/.
王喜明,楊新明.“圖情檔”一級學科更名的歷史回顧與未來展望[J].圖書館論壇, 2022(6): 11-19.
曹建勛.圖情檔一級學科改名的慎思[J].數字圖書館論壇, 2022(10): 1-2.
馮惠玲.以信息資源管理的名義再繪學科藍圖[J].信息資源管理學報, 2022(10): 4-10.
趙憲章.形式概念的濫觴與本義[J].文學評論,1993(6): 323-34.
吳建中. 開放存取環(huán)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間[J]. 國家圖書館學刊, 2005(3): 7-10.
凌征強,盧橋.圖書館空間再造研究綜述[J].圖書館,2018(10): 55-59.
劉霞.從年度數據報告看我國“一流大學”圖
書館的服務現狀與趨勢[J].大學圖書館學報, 2020(3): 89-96.
史艷芬,徐詠華,劉玉. 圖書館空間布局與功能維度的戰(zhàn)略規(guī)劃研究:以同濟大學圖書館為例[J].圖書情報工作, 2017(6):61-66.
霍瑞娟,張文亮,敦楚男.我國公共圖書館空
間類型及其演化特征分析[J].圖書館建設, 2018
(4): 96-103.
陳幼華.論閱讀推廣的概念類型與范疇界定[J].圖書館雜志, 2017(4): 19-24,18.
楊飛,李武, 羅笑婷.圖書館閱讀推廣人工作技能和滿意度自我評價研究[J].圖書館雜志, 2022(8):70-77.
賈娟.圖書館短視頻閱讀推廣發(fā)展策略研究:以2014—2021年“金牌閱讀推廣人”抖音短視頻為例[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2022(11): 75-82.
徐曉,陳琳,葉春波.高校圖書館“書店式”
閱讀推廣創(chuàng)新服務模式探析:以上海大學圖書
館讀者薦購書店為例[J].圖書館雜志,2022(11):
1-10.
盧婭,張麗.浦東“0~3歲嬰幼兒家庭閱讀指
導包”項目:“聚焦家庭”服務模式的實踐與探索[J].圖書館雜志,2022,41(6):88-95.
初景利,黃水清.從“圖書情報與檔案管理”到“信息資源管理”:一級學科更名的解析與思考[J].圖書情報工作, 2022(14):3-9.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圖書館[M].李健鳴,譯.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0.
林春田. 轉向意義域 重建稀缺性:豐裕社會下美的濫用與藝術的險途[J].浙江學刊, 2021(2): 173-182.
哈羅德·伊尼斯. 傳播的偏向[M].何道寬,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