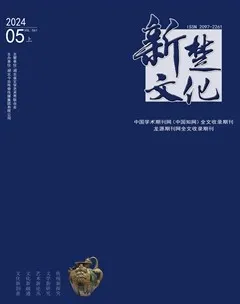共同體意識視域下的文學(xué)書寫與情感表達
【摘要】詩歌作為主情的文學(xué)樣式,一方面承載著書寫者生命情感的流露和歷史體悟,另一方面也彰顯著書寫個體和所處群體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時所共有的價值選擇和認知判斷。作為特殊場域下的情感載體,《天山牧歌》不僅深刻凝結(jié)了歷史記憶與文學(xué)創(chuàng)作、社會生活和國家意識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而且成了新疆地區(qū)民族認同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本文通過對《天山牧歌》的深入剖析,探究了其書在文學(xué)書寫和情感表達層面的價值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同時考察了其書對促進新疆地區(qū)民族融合和多民族文化交流,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的作用與價值。
【關(guān)鍵詞】共同體意識;文學(xué)書寫;情感表達;天山牧歌
【中圖分類號】I227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7-2261(2024)13-0026-03
【DOI】10.20133/j.cnki.CN42-1932/G1.2024.13.008
【基金項目】本文系和田地區(qū)科技局 2021 年立項課題“和田地區(qū)的政治抒情詩研究”(項目編號:202125)研究成果。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理論”①中認為,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是“透過共同的想象,尤其是經(jīng)由某種敘述、表演與再現(xiàn)形式,將日常事件通過報紙和小說傳播,強化大家在每日共同生活的意象,將彼此共通的經(jīng)驗聚在一起,形成同質(zhì)化的社群”[1]。這一觀點無疑強調(diào)了文學(xué)書寫在民族國家共同體意識建構(gòu)中的作用。詩歌作為文學(xué)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一方面承載著書寫者生命情感的流露和歷史體悟,另一方面也彰顯著書寫個體和所處群體面對歷史和現(xiàn)實時所共有的價值選擇和認知判斷。而在現(xiàn)在國家認同建構(gòu)的動態(tài)過程中,通過詩歌文學(xué)來復(fù)刻“記憶之場”②并喚醒集體記憶,進而賦能國家認同,已成為共同體意識教育特別是民族團結(jié)教育的重要方式。
作為邊疆抒情詩的代表,《天山牧歌》[2]是詩人聞捷于20世紀50年代初創(chuàng)作的詩作集合,主要收錄了包括《吐魯番情歌》《哈薩克牧人夜送“千里駒”》在內(nèi)的共計四個組詩、九首牧歌和一首敘事詩,是中國當代第一部反映新疆少數(shù)民族生活和情感的詩集,也被認為是“我國建國十七年詩壇上最具特色的詩集之一”[3]。詩人用見證人的身份和視角,以新穎的富有民歌風(fēng)味的格調(diào),充滿激情地歌唱了解放初期新疆地區(qū)哈薩克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新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4]。在當下學(xué)界的研究中,從文學(xué)的視角出發(fā)動向探討《天山牧歌》本身文學(xué)價值的研究不在少數(shù),但從共同體意識角度來進行闡釋的卻不多見③。基于此,本文擬從國家意識建構(gòu)的視角,嘗試解構(gòu)《天山牧歌》的文學(xué)和情感特點,并論述其在當下共同體意識建構(gòu)中的作用和影響。
一、基于歷史記憶的文學(xué)書寫
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理論”中對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看法一樣,歷史記憶“不是一個既存的物理性實存,而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構(gòu)建”[5]。《天山牧歌》是作者根據(jù)自身生活經(jīng)歷和歷史見證,通過詩歌的形式,以獨特的藝術(shù)語言展現(xiàn)了新時代的風(fēng)貌,傳達了對新時期中國少數(shù)民族勞動人民的贊美,因而也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歷史背景。詩歌抓住1949年初期這一特定歷史階段,通過對民族歷史的回顧、對民族英雄的歌頌、對民族信仰的描繪,強化了詩歌的民族性和歷史性。詩歌是主情的文學(xué)樣式,抒情已成為中國詩歌的傳統(tǒng),聞捷的詩歌卻將抒情與敘事巧妙地結(jié)合在一起,敘事的對象和抒情的內(nèi)容相互依托,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抒情方式[4]。
(一)創(chuàng)新的情感表達和抒情技巧
情感是人類內(nèi)心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天山牧歌》作為邊疆抒情詩的代表,展示了作者迥異于其它抒情詩的獨特的情感傳遞和情感表達的方式與技巧。作者一改傳統(tǒng)直抒情懷的方法,選擇一些動人的生活片段,把敘事、抒情、繪景融為一體,創(chuàng)造了詩情畫意盎然、情景契合無間的藝術(shù)境界:一是大量使用比喻、象征等修辭手法,描寫新疆地區(qū)1949年后各族人民的新生活,使得詩歌充滿了獨特的邊疆風(fēng)情。如《蘋果樹下》和《種瓜姑娘》,成功地將愛情與勞動相結(jié)合,用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元素描繪了新疆各族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的生活變遷。二是在表現(xiàn)手法上,善于選取動人的生活片段和簡潔的景物描寫,把敘事、抒情、繪景融為一體,鑄成一種詩情畫意交融的藝術(shù)境界。還借鑒了少數(shù)民族的口頭詩歌和歌曲的特點,如重復(fù)、對仗、排比等,這使得詩歌在形式上更加豐富和多樣。這種創(chuàng)新的表達方式和抒情技巧,使得詩歌既具有高度的藝術(shù)價值,也使詩歌更加生動和具有感染力。
(二)豐富的藝術(shù)體驗與自然美感
在《天山牧歌》中,作者積極運用富于地域色彩和自然情趣的畫面,注重色彩感和構(gòu)圖感,給人以視覺感。如《遠眺》中對博斯騰湖的描述:湖面上掠過雁群,白天鵝飛上藍天,散布在湖濱的帳篷,飄起淡藍的炊煙……[2]9此外,詩作中還廣泛吸收了新疆獨特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情感語言,如草原、湖泊、山溝、牧場、果園等畫面秀美、色彩明麗自然風(fēng)光,以及打獵、賽馬、宴客、婚禮、舞會等風(fēng)情濃郁、令人神往的人文景觀,構(gòu)成了獨特藝術(shù)風(fēng)格。“《天山牧歌》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學(xué)特征,就是在描寫少數(shù)民族愛情生活時富于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濃郁的少數(shù)民族色彩。無論是天山南北迷人的自然風(fēng)光,還是新疆各少數(shù)民族的風(fēng)俗民情,在詩中都有充分的詩意呈現(xiàn),帶給讀者一種別樣的審美體驗。”[6]
(三)兼具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敘事
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結(jié)合是抒情敘事的一個突出風(fēng)格。在《天山牧歌》的文學(xué)價值中,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結(jié)合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例如,作者用《古老的歌》中老牧人的悲慘歌唱,與《哈蘭村的使者》中三位維吾爾族少年的成長經(jīng)歷相互映射,通過精湛的藝術(shù)手法,將兩個時代的對立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作者通過細致地刻畫新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和家庭生活中流露出的幸福、歡喜的民族自然情感,來積極歌唱社會主義新中國為新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帶來的幸福生活新時代,同時表現(xiàn)了對舊社會壓迫剝削的反對和對新時代民族團結(jié)、共同繁榮的贊許。?
二、國家意識建構(gòu)下的情感表達
情感的存在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無限的空間,也決定了一件文學(xué)作品的價值。作為邊疆抒情詩的代表,《天山牧歌》除詠頌愛情外,更重要的是對祖國的熱愛和歌唱。作者“通過歷史重構(gòu)和現(xiàn)實書寫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國家認同,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展示了各族人民對于新中國民族政策的認同,以及對國家強盛的渴望”[7]。從國家認同建構(gòu)的角度看,《天山牧歌》所展現(xiàn)出的建構(gòu)要素包括對勞動價值的肯定、對忠于祖國的贊頌和對共有歷史的謳歌。
(一)對勞動價值的肯定
《天山牧歌》中處處體現(xiàn)著對勞動的贊美和肯定,甚至將是否熱愛勞動詩作為衡量愛情的標準。詩作中對勞動價值的肯定表現(xiàn)為:勞動產(chǎn)生愛情,愛情在勞動中發(fā)展,伴隨勞動季節(jié)、環(huán)節(jié)的更迭愛情隨之加深。勞動果實成熟、愛情也隨之成熟[3]。《葡萄成熟了》歌詠了勞動的畫面:“馬奶子葡萄成熟了,墜在碧綠的枝葉間,小伙子們從田里回來了,姑娘們還勞作在葡萄園。”[2]28即便是牧人們坐在一起討論自己的志愿時,依舊描繪了生產(chǎn)的場景——牧場上奔跑割草機、部落里開設(shè)獸醫(yī)院、湖邊站起乳肉廠、河上跨過水電站[2]17。可以說,《天山牧歌》中所涉及的勞動中的人們,不管是哪個民族,都屬于勞動人民,這也正是作者所深情歌頌的。
(二)對忠于祖國的贊頌
《天山牧歌》中還大量描述了各民族人民對祖國的熱愛與忠誠。詩作《告訴我》中敘述了守疆戰(zhàn)士的愛情:“此刻,我正在漫天風(fēng)雪里,監(jiān)視著每一棵樹,每一座山崗…我過去怎樣現(xiàn)在還是怎樣,我永遠地忠實于你,像永遠忠實于祖國一樣。”[2]36-37在《夜談》中,翻了身的窮苦蒙古族牧人“比了一個簡單手勢,我聽到他心底的聲音,蒙古人有了祖國,蒙古人永遠跟著毛澤東”[2]22。在這些詩作中,無論是面對愛情,還是面對困難,抑或是面對來犯的敵人,主人公的心理活動都無一例外表達的是對新中國的無限忠誠和熱愛。“在這些詩作中,‘祖國并沒有作過多特意的解釋,但無疑,它不僅對應(yīng)著新疆天山南北,對應(yīng)著各民族人民的祖居之地,也對應(yīng)著幅員遼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8]
(三)對共有歷史記憶的謳歌
包含共同價值觀和追求目標的歷史記憶有助于促進民族融合。在詩作《古老的歌》中,老牧人用歌聲講述了新疆地區(qū)1949年前生活在草原上的牧人悲慘的命運際遇:老藝人彈起他的二弦琴,唱出了一支悲涼歌……多少勇敢強悍的牧人,群起反抗草原上的暴君,一腔熱血染紅了無名野花,或者被關(guān)進罪惡的鐵柵欄[2]75-76。
對比之下,《夜談》則敘述了生活在新疆地區(qū)的蒙古族同胞的解放史和得救史:他生在“中華民國”元年,只有收稅官記得他是“國民”,在那漫長的三十八年,他嘗盡了人間的苦痛……他挑亮了小桌上那盞燈,燈光照亮了整個帳篷,三十八年過去了,窮苦的牧人翻了身[2]20-21。革命歷史的共同記憶,將不同民族的革命者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讓同處于社會下層的勞動者之間不再有民族的界限,有的只是共同的革命記憶,而這些共同的集體記憶則構(gòu)成了民族融合和國家認同的基礎(chǔ)。
三、《天山牧歌》的價值意蘊
具有歷史記憶的文學(xué)書寫和具有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情感表達,使得《天山牧歌》不僅是文學(xué)作品,更是具有強烈社會功能和歷史意義的文化現(xiàn)象。“歷史記憶似乎看起來體現(xiàn)著一種聚焦于過去的時間體驗?zāi)J剑嬲木劢裹c是現(xiàn)在。”[9]盡管《天山牧歌》是詩人聞捷創(chuàng)作于20世紀50年代的邊疆抒情詩集,但它依然是我們今天維護民族團結(jié)、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文化交流所必要的因素。
(一)引導(dǎo)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
《天山牧歌》中廣泛刻畫了進行社會主義勞動的場景。如詩作《吐魯番情歌》中的“淡紅的果子壓彎綠枝,秋天是一個成熟季節(jié)”[2]25不僅展現(xiàn)了大自然的美景,更隱喻了人們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的勞動成果。而《哈薩克牧人夜送“千里駒”》則進一步展示了新時代下,新疆各族人民如何齊心協(xié)力,為社會主義建設(shè)貢獻自己的力量。詩中描述的“千里駒”不僅是哈薩克牧人的驕傲,也代表了新疆廣大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
(二)增進民族團結(jié)與融合
民族特色的引入有助于增強文化認同感。通過《哈薩克牧人夜送“千里駒”》,作者成功地將新疆地區(qū)的民族交融景象以詩歌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讓讀者能夠更加直觀和深入地感受到民族團結(jié)下的新疆社會生活的祥和與溫暖。作者通過展示哈薩克牧人在寒夜中送馬的情景“老牧人右手貼在前胸,謝過大家的深厚情誼……李永緊握哈薩克老人的手,連聲說熱合買提”[2]137-138,強調(diào)了新疆各民族之間深厚的友誼和相互支持的精神。而詩中的“千里駒”象征著各民族間的友誼和合作,詩人用這樣的形象比喻,突出了民族團結(jié)的重要性。通過細膩的筆觸,展示了各民族在社會主義建設(shè)中的共同參與和努力,強調(diào)了團結(jié)互助的重要性,強化了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jié)的主題。
(三)促進文化交流與傳承
《天山牧歌》以其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絲綢之路文化傳承和發(fā)揚的重要載體。詩作中,作者巧妙地將絲綢之路的壯麗畫卷和各種文化元素融合,生動展示了絲綢之路的歷史魅力和文化豐富性。例如,在《哈薩克牧人夜送“千里駒”》中,詩人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哈薩克牧人的生活場景和內(nèi)心情感,展示了哈薩克族的傳統(tǒng)文化和生活方式。這不僅為讀者展示了新疆哈薩克族的獨特文化,也有助于促進各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通過詩歌的形式,作者成功地將新疆的地域文化傳遞給了更廣泛的讀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新疆地區(qū)多元文化的傳播和發(fā)展。
四、結(jié)論
綜上所述,作為邊疆抒情詩的《天山牧歌》,不僅清晰地描繪了1949年初期新疆地區(qū)的自然景觀和民族風(fēng)情,更是深刻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shè)和民族團結(jié)進步的歷史畫卷。從文學(xué)書寫上看,詩人通過細膩的筆觸和鮮明的民族特色,集中展示了新疆地區(qū)各族人民在新時代中的生活變化和精神風(fēng)貌。從情感表達上看,作者熱情謳歌了新疆地區(qū)少數(shù)民族同胞對勞動、對愛情、對祖國的熱愛和認同。從價值功能上說,《天山牧歌》深刻地體現(xiàn)了詩歌在引導(dǎo)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方向、增強民族團結(jié)和社會和諧、促進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傳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說,《天山牧歌》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情感表達,開創(chuàng)了一種富有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文學(xué)抒情詩新形式,不僅豐富了抒情詩的表達方式和內(nèi)容,也為促進邊疆地區(qū)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注釋:
①“想象的共同體理論”由美國著名民族主義和國際關(guān)系學(xué)專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根據(jù)安德森的定義,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zhì)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quán)的共同體”。但“想象”不意味著“虛構(gòu)”和“捏造”,而是指向集體認同的“認知”層面,這種想象是“形成任何群體認同所不可或缺的認知過程”。參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記憶之場”概念由法國學(xué)者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提出,其認為記憶不僅塑造了個體經(jīng)驗,而且構(gòu)建了我們的社會、歷史與文化。記憶之場作為一種具有開放性和共享性的空間,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社會可以通過交流和分享記憶而相互影響。相關(guān)論述參見皮埃爾·諾拉《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艷紅等譯,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7年6月版。
③以筆者所見,現(xiàn)有研究多從愛情觀、民族觀或勞動觀的角度審視詩集所表現(xiàn)出的文學(xué)價值,代表成果有侯鳳超:論《天山牧歌》中的勞動愛情觀,時曙暉《論聞捷政治抒情詩的民族特色——以<天山牧歌>為例》,以及姚洪偉《政治化語境中的愛情詩寫作——論聞捷的<天山牧歌>》等。研究成果中涉及認同建構(gòu)的僅有方維保的“天山牧歌”與聞捷的國族價值觀構(gòu)建。
參考文獻: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M].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6.
[2]聞捷.天山牧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3]侯鳳超.論《天山牧歌》中的勞動愛情觀[J].文學(xué)教育,2018(04):35-37.
[4]時曙暉.論聞捷政治抒情詩的民族特色——以《天山牧歌》為例[J].天中學(xué)刊,2013,28(05):49-51.
[5]趙瓊.國家認同建構(gòu)中的歷史記憶問題——以對共有祖先的追述為視角[J].中國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4(03):86-93+159-160.
[6]姚洪偉.政治化語境中的愛情詩寫作——論聞捷的《天山牧歌》[D].重慶:西南大學(xué),2009.
[7]趙永輝.個體情感·民族記憶·國家認同:聞捷詩歌新疆體驗的三重書寫[J].新疆藝術(shù),2023(02):31-37.
[8]方維保.“天山牧歌”與聞捷的國族價值觀構(gòu)建[C].2014年中國西部文學(xué)與地域文化國際高端論壇論文選,2014:103-109.
[9]郭學(xué)松,方千華,楊海晨,等.作為象征載體的身體運動:鄉(xiāng)土社會儀式中的歷史記憶與認同[J].上海體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16,40(06):45-50+57.
作者簡介:
劉聚,男,研究生,和田師范專科學(xué)校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