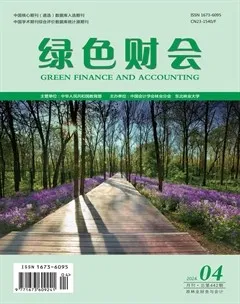交叉持股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及智能分析*
張文珂
摘要:交叉持股企業的協同一致性很可能引發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以交叉持股企業為研究對象,根據環境信息披露理論,研究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機制。基于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方法對交叉持股企業高管人員行為進行監測預警、挖掘群體關系。
關鍵詞:交叉持股;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
中圖分類號:F830
一、引言
據CSMAR數據庫統計,2001—2021年間,上市公司發生12809件違規事件,其中涉及信息披露違規事件有8347件,占比達2/3。究其原因,信息披露違規存在“同群效應”[1]和“傳染效應”[2-4]。隨著股權多元化、高管聯結、交叉持股和關聯交易成為資本市場普遍現象,人力、資本和信息在企業間加速流動,企業行為越來越具有協同一致性。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于海量數據的高效加工、挖掘、分析和利用,有助于梳理錯綜復雜的聯結關系。綜合運用可視化工具和定量研究法,對信息披露違規行為傳染風險進行研究,能夠幫助企業和監管機構實現智慧治理。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的新《證券法》強調,要對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從源頭治理,增加了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相關主體的連帶責任。而錯綜復雜的交叉持股結構更易增加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的風險。
我國交叉持股企業數量較多。2015年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指出,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交叉持股有助于企業實現股權多元化、共同發展,可以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但是,這種企業具有股權結構不清晰、行為協同、經濟利益糾葛等問題,交叉持股企業的協同一致性很可能引發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企業管理層人員在不同公司之間進行交叉任職,管理人員之間頻繁接觸和溝通,增加了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概率。交叉持股、企業制度、結構比例都可能是影響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因素,這對交叉持股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深入分析交叉持股對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的影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具有重要意義。
二、交叉持股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內在機理
1.交叉持股企業增加了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①經營策略。交叉持股會導致市場產品同質化,破壞了信息多樣性,且企業混同用工,會增大信息泄露的風險,削弱行業競爭[5],導致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增加[6]。②外部關系。交叉持股企業間存在溢出效應,研發投資聯動[7]導致企業知識技術轉移[8],從而影響并購價格[9]。③公司治理。交叉持股企業的產權結構對內部治理存在負效應,會影響混合所有制企業最優的國有產權比重[10],容易產生“雙刃劍效應”[11],誘發公司內部控制問題[12],導致信息違規披露[13]。交叉持股打破了企業原有的產權結構、經營體制和治理機制,增加了信息披露違法違規的傳染風險。
2.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負面影響。①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具有不確定性和波動性,其負面影響是集中研究領域。例如: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會降低投資水平和企業成長性[14]、抬高融資成本[15]、影響經濟資源配置。②隨著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測評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性突顯出來。國內外學術界已經提出了一些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測評方法,根據研究問題的側重點不同,可以對信息風險指標進行分解,分析不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造成的經濟后果,以避免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16]。
3.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具有傳染性。①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負面影響并不局限于企業內部[17],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能夠進行傳遞和轉移。已有研究發現,財務重述能夠放大同行企業的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當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通過擴散與傳播渠道傳遞出去,會為其他企業的信息披露造成影響,甚至會出現虛假陳述,這就是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傳染。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主要在同行企業[18]和集團內部這些關聯企業之間傳遞。當虛假陳述、財務重述或操縱性應計等操作帶來的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導致同行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顯著升高甚至引發虛假陳述時,就證明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具有傳染性。②對其他公司或利益相關者行為產生的影響,也是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重要表現。存在競爭關系的同行企業為獲取競爭優勢,往往對虛假信息做出不當反應,導致同行企業進行錯誤的資源配置。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會改變投資者對競爭企業未來收益的預期。例如,虛假陳述被揭露時,同行企業股價也受到波及,造成競爭對手的異常損失,且影響的程度取決于企業之間的關聯性或共同特征[19]。
三、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研究方法
1.對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進行測評,為后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做準備。在借鑒現有文獻基礎上,根據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研究的需要,確定樣本、數據和變量的選擇標準。對應計模型進行修正,使之滿足傳染分析的需要;借助統計軟件分析樣本數據,得到企業傳染測評指標;將傳染企業和接受企業的特征指標加入有序Logit模型,對傳染情況進行分類評級。利用離散Hopfield、Elman、Jordan深度神經網絡,構建虛假陳述、財務重述和操縱性應計的傳染評價模型。
2.分析傳染接受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變化過程和機理,以進一步研究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擴散機理。從行業競爭壓力、外在信息環境、信息不對稱等視角,剖析企業接受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內部和外在動機。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對象的設定并不局限于關聯特征較強的企業,可以將范圍進一步擴展到一般企業。在實證分析中,采用傾向評分匹配模型、面板數據模型分析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影響。傾向評分匹配(PSM)、面板數據模型能一定程度克服變量的內生性問題。傾向評分匹配的第一階段是建立企業虛假陳述或財務重述的預測評分模型,第二階段是建立虛假陳述或財務重述對其他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影響效應模型。在前述實證分析的基礎上,需要進一步采用面板數據分析模型,驗證當行業內存在虛假陳述或財務重述等行為時,其他企業的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是否會受到影響。
3.以交叉持股企業為研究對象,基于信號反饋原理對交叉持股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發生機制進行研究。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是風險在不同企業之間傳遞擴散的過程,類似于“虛假信息—產權關聯—虛假信息”的傳遞過程。對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分析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本身,需要綜合分析與交叉持股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相關的因素,如環境和文化因素。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在其作用結果和表現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將交叉持股背景下的社會關系、企業社會責任、行業和區域環境特征的一致性、生產業務的關聯性等納入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環境因素中,將企業倫理、從眾心理、人員流動、行為規范等人文信息納入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文化因素中。基于此,研究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影響路徑和作用,分析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與潛在影響對象之間的關聯關系,采用分層動態潛在因素模型對相關理論設想加以驗證。
四、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智能分析
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具有難以確定性和動態性的特點。基于回歸分析法進行的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研究具有局限性,例如,Logit回歸模型、分層動態潛在因素模型等,在分析隱含關系、非結構化或非線性問題上,存在評價不全面和適用條件苛刻等問題,無法有效地評價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傳染情況。因此,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對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進行測評。人工智能技術具有更強的數據形態挖掘能力,在處理未知的復雜模型、偵測舞弊行為以及風險管理等方面比傳統統計方法更有效,與判別分析、Logit回歸等方法相比,具有預測精度高、誤分類代價低的特點。目前人工智能的應用主要集中在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影響因素上,重點對虛假陳述行為進行預測和甄別,尚未涉及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分析。用人工智能技術分析交叉持股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傳染機制,可以避開傳統統計模型苛刻的假設條件,通過機器學習智能地模擬出傳染的仿真結果,進而系統全面地分析企業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傳染情況。
綜上可知,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行為會會對市場、企業和利益相關者產生嚴重影響,近年來,政府監管機構加大了對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管控,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的傳染使得管控工作更加復雜化。本文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挖掘各類相關數據,以交叉持股企業為研究對象,預測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擴散的軌跡和傳播趨勢,為企業提供規避信息披露違法違規風險傳染的策略,以期增強企業信息披露質量,以促進企業健康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陸蓉,常維. 近墨者黑: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同群效應”[J].金融研究,2018(8): 172-189.
[2]劉麗華,徐艷萍,饒品貴,等. 一損俱損:違規事件在企業集團內的傳染效應研究[J]. 金融研究,2019(6): 113-131.
[3]趙艷秉,李青原.企業財務重述在集團內部傳染效應的實證研究[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6(5): 72-80.
[4]徐艷萍,王琨. 審計師聯結與財務報表重述的傳染效應研究[J].審計研究,2015(4): 97-104,112.
[5]Shelegia S, Spiegel Y. Bertrand competition when firms hold passive ownership stakes in one another[J]. Economics Letters,2012,114 (1): 136-138.
[6]Faccio M M,Marchica T R M. Large shareholder deiversification and corporate risk-Taking[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1, 24 (11): 3601-3641.
[7]López L, Vives X. Overlapping ownership, R&D spillovers, and antitrust polic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127 (5): 2394-2437.
[8]Ghosh A,Morita H. Knowledge transfer and partial equity ownership[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17,48(4):1044-1067.
[9]Hansen R G,Jr. Lott J R. ?Externalities and corporate objectives in a world with diversified shareholder/Consumers[J].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1996,31 (1): 43-68.
[10]張偉,于良春.混合所有制企業最優產權結構的選擇[J]. 中國工業經濟, 2017(4): 34-53.
[11]冉明東. 論企業交叉持股的“雙刃劍效應”:基于公司治理框架的案例研究[J]. 會計研究, 2011(5): 78-85.
[12]智寶月,畢穎. 公司交叉持股及其法律規制[J].管理世界, 2009(9): 176-177.
[13]儲一昀,王偉志.我國第一起交互持股案例引發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5): 173-186.
[14]Kedia S, Philippon T.The economics of fraudulent accounting[J].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 (6): 2169-2199.
[15]Kravet T,Shevlin T. Accounting restatements and information risk[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0,15 (2): 264-294.
[16]Cohen D A.Does information risk really matter? a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8,15 (2): 69-90.
[17]Henry E.A, Leone J. Measur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in Capital Markets Research: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ethodologies to Measure Disclosure Tone[J]. Accounting Review,2016,91 (1): 153-178.
[17]Goldman E, Peyer U I. Stefanescu.financial misrepresentation and its impact on rivals[J]. Financial Management,2012, 41 (4): 915-945.
[18]Akhigbe A,Madura J. Industry signals relayed by corporate earnings restatements[J]. Financial Review,2008,43 (4): 569-589.
[19]Gleason C A, Jenkins N T, Johnson W B. The contagion effects of accounting restatements[J]. Accounting Review,2008,83 (1): 83-110.
責任編輯:田國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