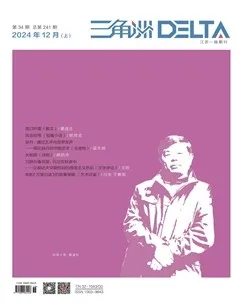李長之對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道路的設計與構想
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文化語境中實現復興,如何突破西方文論入侵下的“失語困境”,李長之在《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對中國文化復興之路的宏觀建設為我們提供了可供探索的思路。李長之通過對“五四”的重構、中國文化建設的策略和思想的提出凝望未來文化發展的世界洪流。本文將從時代背景出發,闡釋和發掘李長之對中國真正文藝復興道路的設計,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蘇和當代的文化建設提供參考。
重構“五四”
——李長之文藝復興道路設計的起點
《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寫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火紛飛、民族危機深重,面對西方文化的強烈沖擊和“西體中用”的社會現狀,李長之深感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決心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發展探尋理論支撐和實踐路徑。在書的自序中,李長之闡述了自己的創作初衷,“在那百廢待舉之際,文化的建設豈是可以忽略的?在我們這不能執干以衛社稷的人,似乎至少應該對文化建設的問題貢獻一點意見”。
因此,李長之的文化觀念正是建立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入反思和重構的基礎之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20世紀初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一場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其歷史地位舉足輕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直至新中國成立的幾十年間,學者們紛紛從各自獨特的視角對其性質進行了深刻的探討。其中,典型的代表是蔡元培、胡適等學者倡導的“文藝復興說”。胡適先生曾明確指出:“‘五四’乃是一個文藝復興運動。”這一論斷深刻揭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文化領域的創新性和重要性。海外學者周策縱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關于這場運動,自由主義者或獨立派認為,或許至少是從文化方面來看,‘五四運動是一場中國的文藝復興’。”而李長之卻對這種說法質疑,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啟蒙論”,他明確地呼喊:“未來的中國文化是一個真正的文藝復興。”首先,在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定性問題上,他不贊成用文藝復興來稱呼,而認為其在定義上更接近于西方的啟蒙運動。李長之在胡適的觀點上實現了超越,進一步指出,“‘五四’是一個移植的文化運動。”雖然有一定的文化成就,但其本源大都來自對西方文化改頭換面的重新包裝。這種成績就像花瓶里的花,雖然鮮艷美麗,但卻是從別家的花園里攀折來的,沒有本民族的土壤和氣候,有的只是對于傳統文化的大肆破壞和對于西方文化的機械移植。他們所提倡的民主與科學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結晶,取得的最大成績也是自然科學的成績,在此期間步入國際論壇的學者也大多來自科學領域,而非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領域。“文藝復興的實質在于一個古代文化的再生。”但對五四運動來說,打倒孔家店,將傳統文化視為封建糟粕而加上封條的事件比比皆是,只是引進西方的先進思想更加符合啟蒙運動在一切人生問題和思想問題上要求明白清楚的一種精神運動的定義,陳獨秀對于傳統文化的猛烈攻擊、胡適對于新生活的提倡,以及顧頡剛對于古典的懷疑,這些都是啟蒙的色彩。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應該稱之為啟蒙運動,而非文藝復興運動。李長之從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新解讀和闡釋出發,力求超越“五四”的精神內核,致力于引入西方卓越的文化資源。在全面理解并把握西方思想精髓的基礎上,他再次審視中國的文化傳統,深入探尋其中蘊含的內生力量,并以此為基石,構建起關于中國文藝復興的文化理想。
中國本位
——李長之文藝復興道路設計的基點
開出自己本民族的花,需要從中國文化本身尋找根基,因此,李長之文藝復興道路設計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就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李長之通過對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進行重新解讀,提出了實現其文化理想的兩大基本途徑:一是弘揚儒家文化中的剛性精神,以培養崇高的道德品格;二是發揚審美精神,通過美育來塑造新時代的文明個體。儒家精神博大精深,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都有其滲透灌溉的地方。而儒家的核心精神來說,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光芒萬丈的,自然是孔子。李長之把孔子當作未來文化建設的范本,他在《中國傳統文化之認識上:儒家之根本精神》一文中寫道:“孔子是把中華民族所有的優長結晶為一個光芒四射的星體而照耀千秋的人。”李長之在傳統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中提出了關于儒家文化剛性的一面,他認為:“其實孔子的真價值,卻毋寧在他那剛強,熱烈,勤奮,極端積極的性格。”而這種張揚剛烈的性格特征,才是儒家美學的真精神。五四是“清淺的理智主義”,從而導致整個民族的文化“少光、少熱、清淺、單薄”,缺少深厚強盛的生命力,而儒家反功利輕小我的精神,恰是滌清時代浮躁之氣,改變精神病態的解藥。儒家剛性而蓄藏的精神,使我們成為最愛和平而又最英勇不撓的民族,要完成中國的真正的文藝復興,栽出自己土壤里的花,必須以儒家的根本精神為根基。
儒家的根本精神如何融合進現代社會,如何以新的方式闡釋于我們的血脈中蘇醒?李長之提出了美育的觀點,讓傳統文化重新流動于我們的血脈之中,其關鍵在于美育。蔡元培在推動現代中國美育發展方面貢獻卓越,為了紀念蔡元培先生的逝世,李長之撰寫了紀念文章《釋美育并論及中國美育之今昔及其未來》,文中表達了對蔡元培的深切懷念。受到蔡元培的影響,李長之也深刻認識到文化建設與美育的緊密聯系。他指出,中國古代美育之所以卓越,“是因為那時有極健康,極正確,極博大精深的美育概念,而教育的建設又那么完備之故”。這種美育傳統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李長之進一步指出,中國古代之所以能夠培育出健全的人格,其背后正是源于古代美育思想的完善與健全。因此,李長之呼吁要重新塑造現代民族品格,需要喚醒古代健全的美學。在李長之的視角中,他堅信唯有堅守反功利的精神,方能真正將集體和大局利益置于首位;而強調理想主義,則是實現民族復興理想的必由之路,因此面對時代的功利主義彌漫,李長之急迫呼喊:“救水莫若火,所以我們急而提倡原始儒家的反功利精神!”李長之認為,美學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反功利。中國傳統文化里不僅有美的義理,更有美育精神的豐富內涵。在《審美教育之本質》一文中,李長之深入探討了教育的核心意義,他認為教育的精髓在于“使人類全體或分子在精神上擴大而充實,其效力系永久而并非一時者”。從這個視角出發,教育的本質與美的教化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美育并非僅僅是教育體系中的一個分支,而是其中最為關鍵、最為核心的一環,甚至可以說是最貼近教育本質的唯一形式。相較于知識教育的片面性、道德教育的抽象性,以及技能教育的局限性,審美教育能夠從內在出發,實現精神上的富足與生活的充實,從而塑造出更為全面、更為豐富的新個體與新人類。
世界大同
——李長之文藝復興道路設計的終點
李長之從對“五四”的重構開始,提出了中國本位的文化思想,并由此生發出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應當是以本民族的文化為根基,以古代美育精神為材料,通過現代教育手段重新構建中國的傳統文化復興之路,而這條道路的終點,也是李長之對于未來世界的文化發展的卓越見識——即我們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為未來的文化事業留遺產。
為此,李長之區分了“國防文化”和“文化國防”的概念,他認為,“國防文化”是“只在證明本國人是最優秀的人類的,只在證明某些地方是原屬于本國的”,而我們要談的文化國防,則是“由文化觀點而看到文化價值,而想到必須采取的許多保衛手段和方法”,我們保衛一個文化,并非僅僅因為它來自本民族,而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內涵和價值。歷經五千年歷史沉淀的中國文化,其獨特價值舉世矚目,理應在全球舞臺上占據更為顯著的地位。然而,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并非僅僅局限于對傳統的挖掘,更需與現代文化相互融合,實現進一步的拓展與弘揚。這種復興的過程,需要我們積極地將傳統文化融入現代語境,參與國際交流,以展現其獨特的魅力和價值。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鑄就并非僅僅囿于地理,而是真正的心理上的永久的“文化長城”。李長之以其卓越的眼界,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經看到了當今世界終將走向全球化的必然性,“我不相信將來有任何一國可以統一世界。只是萬一仍有人抱這種迷夢卻只會增加人類的痛苦”。人類的生存權利是平等的,中國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分子,中國公民是社會公民的一分子,中國傳統文化里的大同思想和和平心態將通過真正的文藝復興留存于世界長河。
李長之的文化觀念和實踐方法為中國文化的建設注入了豐富的精神內涵,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李振聲在慶應大學進修時,特意深入閱讀了李長之的《迎中國的文藝復興》,并深感震撼,他表示:“讀完之后,我覺得我們前幾年盛極一時的文化討論思潮,其對‘五四’的理解,對中西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沒有超過李長之的研究范圍……迄今為止,對李長之的生疏,不能不說仍是中國思想學術史中的一種缺失。”李長之先生對中國文藝復興的設計在今天依然是我們學習的方向。為了克服“五四”時期的片面與淺薄,我們應當從文化傳統內部尋找文化的內生力,并在全面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礎上求新求變,以彌補“五四”新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裂痕,并最終超越“五四”,將中國傳統文化真正置于世界的大背景中,打破當代文論的失語困境,推動“新世界新文化新中國”的文化運動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的發展。正如李長之所預見的那樣:“在不久的將來,我相信文化的交流必將更繁密。西方的文明——科學與民主,更為我們所欣賞;我們的文明——和平大同理想,也將洋溢于歐洲各國。”
作者簡介:
紀真真,1997年生,女,河南周口人,碩士,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202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學。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