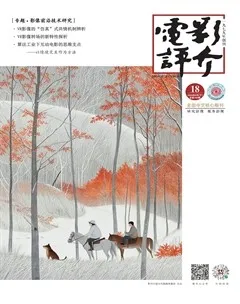VR影像的“仿真”式共情機制辨析
【摘 要】 VR影像這一“數字符碼”是否已然成為有效的“移情機器”,關鍵在于其與觀眾交互時,引發觀眾共情的機制如何觸發、有何特征?VR影像除了視聽沉浸外,還表現出“身體轉向”,觀眾被充分調動起觸覺、動覺參與觀影,形成不同于傳統影像引發受眾共情的機制,觸發路徑表現為“身體-情緒-認知-共情”。本文通過對《集裝箱》(南非,2021)、《生還911:瓦礫下的27小時》(美國,2022)、《夏威夷末日》(美國/法國/英國,2022)等文本的媒介特征、敘事經驗與受眾感知維度的考量,發現該共情機制的生成邏輯存在產生阻斷的潛在因素。VR影像可視為數字技術創造的“仿真”世界,其共情也體現出“仿真式”的特征:快感式、想象性、身心不一性、消費游玩式。在未來,相信VR影像引起受眾的情感共情將會具有更加真實、真切、真誠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VR影像; 共情; 仿真; 沉浸; 交互
一些VR影像的追捧者揚言“VR難民紀錄片創造了‘終極移情機器’(the ultimate empathy machine),在數字世界里與人民同在”[1]。那么,VR影像這一“數字符碼”是否已然成為有效的“移情機器”;受眾通過穿戴VR影像設備具身性地經歷戰爭、疾病與苦難,是否能夠設身處地地感知、理解他者的情緒與情感?基于虛擬現實產業發展仍處于上升階段的現實語境,該言論所觸及的理論議題、創作現象顯然值得辨析——VR影像引發受眾共情的機制如何觸發、有何特征?
與傳統影像主要作用于觀眾的視聽感官不同,VR影像重在調動受眾的觸覺、動覺等身體感官,意在為受眾打造一個具身沉浸的擬像世界,受眾的體驗更偏向于“游玩”,而非“觀看”。由此,VR影像引發受眾共情的機制的觸發路徑與傳統影像相比較,便會有所不同。本文以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XR單元的部分影像——《集裝箱》(南非,2021)、《生還911:瓦礫下的27小時》(美國,2022)、《夏威夷末日》(美國/法國/英國,2022)為討論案例,從受眾的游玩體驗、身體感知,與預設的敘事經驗等角度分析VR影像引發受眾情感共情的生成邏輯以及該機制產生阻斷的潛在因素,并嘗試總結該共情機制的特征。
一、VR影像共情機制的觸發路徑
共情體驗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由感官到認知的、由低級到高級的情感認知體驗。“共情”這一概念較早見于美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來源于德國哲學家羅伯特·費舍爾(Robert Vischer)在《論視覺的形式感情》一文中提到的德文詞匯“Einfühlung”,有感覺、感情進入(feeling into)的意思,指觀眾對于藝術作品的積極參與,是身體與欣賞對象之間相互交流的體驗。[2]他強調在觀看/欣賞活動中,需要調動人的知覺神經與運動神經同時起作用,并將“人格”融入所看的事物中,與之交互,才可以形成共情。這里的“人格”即是指主體的理性認知。社會心理學家喬治·H·米德(George H.Mead)也重視人在社會環境中自我認知的能力,強調個人對他人觀點的采擇能力,將共情與“觀點采擇”聯動分析。[3]可見,共情體驗先是主體受到身體的、感官的刺激或吸引,再通過主體的理性認知參與,體會到客體的觀點/現實處境/內心狀態。而在這個過程中,認知具有喚醒、引導情感的作用。
所以,影像引發受眾的共情情感是否真實、有效,關鍵就在于受眾能動的“認知”參與。認知心理學家沙克特和辛格提出情感的雙因素理論(two-factor theory)[4],生理喚醒激起情感,而認知引導了情感,認為人的生理反應和認知(知覺、記憶和分析)共同引發了情感,即情感有兩個組成成分:生理喚醒和認知標簽。[5]前者傾向于某種“即時觸發的”身體反應、感官刺激下的本能情緒,可以視為一種生理感受,是共情機制的產生前提——共情力(empathy);后者是理性和感性綜合權衡下的認知操作,強調個體主動地、能動地參與理解,從而產生共情機制的本質——共情情感(empathic emotion)。所以,影像的有效共情機制需要觀眾由“反應式”的共情力轉向為“認知性”的共情情感,二者缺一不可。換句話說,觀眾由影像的感官刺激所引起的生理感受,與現實中的本能情感沒有什么區別,只有當觀眾進入影像故事中——體會人物情感、填補敘事邏輯,才能算得上與影像實現了深層次的共情,進而有可能影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而人們常說的“共鳴”與“共情”概念也有細微差別,共鳴強調的是觀眾受到影像的情緒感染、意識形態詢喚,觀眾與影像之間的關系更偏向于被動地“應答”。相較而言,共情則是受眾主動認知地“參與”影像。
傳統影像作用于觀眾的視聽感官,更大可能地保留觀眾沉思,生成共情機制的“情緒-認知-共情”的觸發路徑。一般來說,傳統主流影像的語法結構、視聽邏輯都致力于將觀眾縫合進故事世界中,調動觀眾的情緒認同與認知解碼。雖然柏拉圖認為這種洞穴式的“幻影”助長了“低層次的熱情”(lower passions),拉遠了與現實世界的關系,但不可否認的是,觀眾本身強大的思考能動性也可以強化影像的現實意義。就像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認為“在視覺世界里,間離效果更明顯,反思總是可能的”[6],傳統影像的視覺吸引力會更大可能地保留觀眾獨立的沉思。傳統影像讓觀眾在受到視聽刺激的同時,能夠認知參與影像敘事,進而有可能形成共情情感。無論是作者電影通過“思考”指向個人魅力,還是真實電影通過“在場”浮現真實,它們都擅長用藝術手段調動觀眾的認知參與,進而和文本達成某種情感和價值認同。
VR影像除了視聽沉浸外,還表現出“身體轉向”,觀眾被充分調動起觸覺、動覺參與觀影。在VR影像中,具身性、交互性的體驗不僅增加了受眾探索文本的可能性,而且沖擊著受眾傳統的觀看習慣,其觀看機制更傾向于游戲藝術的參與邏輯,受眾的“觀看”不如稱之為“游玩”。VR影像雖不如游戲藝術那般依賴于界面語言、身體語言的強操作,但“身體介入式”參與足以將其區分于傳統影像的觀看。“身體”介入后,才能調動“感知體”的全方位,進而滿足受眾當下要求較高的“體驗式消費”訴求。[7]
VR影像正探尋出共情機制的“身體-情緒-認知-共情”的觸發路徑。理想情況下,在VR影像的“游玩”過程中,影像(裝置)首先作用于觀眾的身體感官(尤其是觸覺),“放大”刺激觀眾的本能情緒,進而讓觀眾沉浸式地認識、分析文本,與文本形成共情情感。所以,它的邏輯是觀眾“由身而感”地認知參與,理解情感,辨析文本與現實的想象關系。
二、VR影像共情機制的生成及存在的阻斷因素
美國科學家格里戈里·比迪亞(Burdea,G,Coiffet,P)概括出虛擬現實技術的“3i”特性:Immersion(沉浸);Interaction(交互);Iimagination(想象)。[8]從引發受眾共情的視角看,VR影像強調受眾沉浸式、交互式的參與,以期達到認知維度的(想象性)共情情感。“沉浸”與“交互”凸顯的都是受眾的身體介入,即VR影像是麥克盧漢所提及的熱媒介的重要表征,其調動受眾的多重感官,如視覺、聽覺、觸覺、身體動覺等,是一種“由身而感”的身體媒介生成邏輯。這正對應了梅洛·龐蒂“被具體看待的作為我之所是的主體最終與這個身體和這個世界不可分離”[9]的哲學思考,重視身體的知覺體驗。
由此可見,觀眾的“身體介入”是VR影像“由身而感”共情機制的重要前提。大部分虛擬現實影像,都需借助觸感直觀性、身體的空間直覺、身體動覺等綜合知覺來協同,實現身體的情動體驗。[10]雖然從共情機制觸發的正向邏輯看,“身體介入”仿佛使其變得更為簡易、直接,但基于VR影像的觀看效果、敘事經驗與受眾的身體感知維度而言,該共情機制的生成也有被阻斷的可能。
(一)“幽靈感”的游離與錯位
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提出觀眾在觀影過程中奇妙的幽靈體驗,“人們在電影中既相信、又不相信,兩種完全矛盾的信任效果在觀影中相互疊加,且無法彼此覆蓋”[11]。VR影像即是再現了受眾體驗的“幽靈感”。VR影像需要受眾穿戴裝置設備“圈”入“銀幕圖景”中,受技術條件限制,理想化的“三維+360度+交互操作”效果尚未廣泛實現,所以受眾在體驗時可能會出現感知的游離與錯位。
首先是受眾“游玩”時視點和位置的流動感、飄蕩感,會使其反思自身的“存在”——是玩家還是影像事件的經歷者,從而難以有現實性的情感參與。VR影像的玩家如“幽靈”般存在于數字奇觀的影像世界中。一方面,玩家所處的視點“并不固著于某個特定主體的視線”[12],只能隨著身體與頭部轉動,在固定空間固定視點位置中選擇視線。如《夏威夷末日》中玩家的視點局限于攝影機預設的空間場景,雖然可以像玩游戲時移動鼠標那樣變換視線方向,但是變換的自主性并不如游戲那般自由。即使玩家是影像中角色的交流對象,視線的“非自主性”也難以再現現實生活中的親近感、交流感。《生還911:瓦礫下的27小時》試圖強化玩家與影像之間的聯系,玩家被設置為主人公吉內爾的談話對象,但影像單一“展映”式的弱交互(類似于場景圖片的切換)卻難以讓玩家沉浸聯動;另一方面,玩家在空間中的“步伐”動線由攝影機的預設路線決定,以此生成一種幽靈“游走”的飄蕩感,其新異于日常觀影經驗,還會有中斷沉浸體驗的可能性,共情感受更易脫離。如《集裝箱》中玩家沒有自己的實體形象,所處位置被固定在視線只有180度的集裝箱空間中,只能跟隨影像中的角色行動或環境展示而變換位置。玩家這種在垂直、水平方向的自由游動,仿佛是密閉空間中飄蕩的“幽靈”。對于玩家來說,與影像之間的情感生成更多的讓步于對空間游蕩的獵奇心理。此外,影像中的雜亂環境和角色身體突然出現在玩家的“面前”,近距離的接觸刺激并不會具有現實生活中的沉浸感,而是一種超現實的、跳脫的,甚至是不適的怪異感,這容易阻斷影像引起玩家共情的生成機制。畢竟,身體與化身的聯動結構,成為VR影像機制生成深潛體驗的關鍵路徑。[13]
其次,VR影像為了適配觀看屬性、觀看裝置,在空間景觀及轉場技巧等方面還不夠成熟,使其具有某種數字技術特性的“劣質感”。此“劣質感”不是指常規意義上“劣質影像”(Poor Image)[14]的低清模糊、雜亂卡頓,而是指在VR影像中存在某種數字景觀的“超現實感”以及空間場景過渡的“稚嫩感”。如《集裝箱》中玩家轉動視點超過180度便會得到設備的字幕提醒,且不同場景空間的切換技巧包含硬切、疊化、遮黑轉場等,這種在電影藝術中早已輕車熟路的基礎性轉場技巧,在VR影像的觀看過程中會顯得比較突兀和不自然,甚至會讓受眾產生眩暈感。生理的不適與介意,會阻礙他們沉浸體會影像中奴隸的慘苦遭遇。在《生還911:瓦礫下的27小時》中,隨著吉內爾的自述,這一歷史事件在受眾面前緩緩展開,其形式卻是圖片組合敘事(圖片上會有部分動態處理),影像的敘事沉浸感全靠吉內爾的口述,在此,圖片的“展映”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劣質影像”。固然,VR影像的底層邏輯是通過數字技術的“超現實”(再現歷史事件、重現故事細節)營造玩家的高沉浸感,以此達到受眾的共情指認,但“劣質感”的數字景觀及空間切換效果容易使玩家從影像世界中跳脫出來,并產生一定的生理不適感。
于此,受眾感知的視點,空間景觀視角下的觀看/游玩體驗并未完全走向VR影像預設的“情感預聚焦”[15],受眾的共情體驗容易被阻斷。
(二)“掌控式”的思考“存在”
VR影像生產與運作邏輯的背后實則是消費主義文化邏輯,體現出后現代注重感官消費、奇觀消費、快感消費的文化癥候,傾向于帶給受眾一種“掌控式”的游玩體驗。時下,AI作畫、算法影像創作等數字技術手段給傳統行業帶來審美與實踐等多方面的革新,VR影像同樣基于沉浸式交互體驗的核心技術消費看點沖擊著傳統影像的生產邏輯。
VR影像具有“影”與“游”的雙重媒介特性,“在敘事組接上都具是‘前框架性’的,即框架都是搭建好,再進行敘事”[16]。在預設好的影像世界中,吸引受眾深層參與的是對文本多義性的主體解讀。在電影藝術的接受中,觀眾在漆黑的影院中觀看,與文本保持著一種適度的“間離感”,使得觀眾有較大的思考空間對文本進行多維層面的填補、闡釋。而在VR影像中,玩家穿戴裝置設備“進入”影像世界,其“新異體驗”會影響到“沉思解讀”。另外,VR影像由于文本容量限制、沉浸敘事與交互操作之爭等問題,在文本敘事上較之電影往往更加直白,所以玩家對影像文本的解讀較為單一、直接,與文本之間的情緒、認知聯系不如電影藝術那般深入。
受眾的“掌控式”游玩體驗影響著VR影像共情機制的生成。如鮑德里亞所論述的:“技術媒介之所以會體現出‘惡’的性質,是因為人們變得毫無隱私和秘密可言,甚至連主體性和人身安全都隨之消失了。”[17]VR影像的“超現實”游玩體驗存在這種擔憂。第一,玩家的全知視角在“前框架性”的預設敘事中感知到某種“幽靈”掌控感。這與傳統影像中觀眾的全知視角有所差異,因為VR影像會給受眾更加“具身性”的感知體驗。例如《生還911:瓦礫下的27小時》中玩家通過吉內爾的講述見證“9·11”事件發生的前后經過,眾多照片、影像在玩家面前專屬展現,玩家再以“幽靈感”的視點、“步伐”全方位體驗,難免會生成一種對影像世界的游玩掌控感;第二,VR影像強調玩家的交互體驗。例如在《錫德拉灣上空之云》等VR影像作品中,受眾可以調動整個身體在影像世界中“游走”。當行動、感知、欲望等人的概念被技術“操作化”,玩家在VR影像世界中就會以游戲的可掌控感戰勝現實原則;第三,VR影像的受眾處于游戲中的“玩家”中心地位,玩家操控、掌控著影像裝置。例如《夏威夷末日》中的場景空間多是三維的建模景觀,在富于變化的線條、像素場景中,觀眾處于影像預設邏輯的中心位置,如同游戲藝術中的玩家那樣去不斷探索新的場景/關卡。
當VR影像中的受眾取得和游戲玩家一般的“掌控式”游玩體驗時,受眾與影像之間的情感和認知邏輯將會更加個體化、復雜化。
(三)“即時性”的消解沉思
前文所述,傳統影像通過觀看的“間離感”維系著觀眾的沉思狀態,無論在故事中是以自我的視角,自我地帶入角色體驗,還是以他者的視角,他者的身份體驗,觀眾都具有獨立思考的空間,相較而言,VR影像則容易中斷受眾的沉思狀態。鮑德里亞曾以嗅覺的“幻覺”,指出“身體機器可以分泌出某些物質的幻覺——而人們只知道精神能夠分泌出精神的幻覺。這就說明人們在生理上也會受身體的欺騙”[18],身體的觸覺同樣具有情感上的“欺騙”。當玩家穿戴設備體驗“VR影像游戲”時,奇觀消費、快感消費的生理體驗,易凌駕于受眾共情情感所需要的認知能力之上。即VR影像引起受眾感官上的即時感受,只是調動了觀眾本能的共情力。共情情感則源自內心觸動、價值認同,是一種主體自覺、能動的認知狀態。
觸覺、動覺等對受眾沉思狀態的消解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穿戴設備的外在因素,在VR影像的“游玩”過程中,較長時間的戴顯示器、耳機,握手柄等會使部分受眾感到不適,不時地進行調節、控制,從而中斷沉思狀態;二是VR“游玩”的內在因素,VR影像世界的“未知”需要受眾參與解碼,如同玩家玩游戲時探索世界地圖那樣。所以,這種具身性的探索體驗將受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場景空間的變化、人物姿態的細節等等,獵奇心理使受眾服務于影像本身,不斷地去探索影像世界,而非影像服務于受眾的沉思。例如《夏威夷末日》營造了受眾的沉浸觀看狀態,但受眾的“沉浸”也不盡等同于情感的“參與”,受眾轉動身體和頭部觀看奇觀影像的景觀,控制手柄進入下一章節,“面前”突然出現的人與物,都有可能打破受眾的沉思狀態。
三、VR影像的“仿真式”共情機制特征
“由身而感”觸發路徑所帶來的共情具有怎樣的實效價值與現實意義,即“數字符碼”能否成為具有革新意義的“移情機器”的關鍵,在于該共情作用機制的特性如何。
(一)符碼預設的VR“仿真”影像
鮑德里亞創造性地提出具有后現代主義特質的擬像理論,在數字仿真世界中符碼居于統治地位。“在符碼時代,現實不再是原初物及其關系結構意義上的現實,而是經過符碼中介出現的模擬物,物與物之間的系列關系,使物與其指涉的現實關系消失了。”[19]VR影像便是數字技術打造的“超現實”的仿真世界,其指攝對象是影像對現實的模擬、想象再現,既比現實生活“高級”,又體現出虛無、透明的“空無”影像符號特征。技術創造的真實終歸稱之為“仿真”,而非真實,“人們越是接近這個理想的清晰度,這種無用的優點越是使幻覺能力失去”[20]。VR影像與現實之間的指攝關系依靠受眾的想象連接,它過于“完美”地再現現實,現實對受眾的吸引力被這種游玩體驗、奇觀消費所奪去,使VR影像成為純粹的擬像——消滅了真實。受眾在這預設過的、經過對現實記憶或現存影像的雙重模擬過后的仿真世界中,消費著想象力與專注力,從認知上進入這種消費主義符號商品中,這種VR影像所引發受眾的共情情感可能從本質上便是“仿真”的,體現出后現代的某些傾向。就像大多數觀眾會對于VR影像的沉浸感所制造出來的恐怖體驗感到新奇,這也是觀眾選擇觀看VR的消費初衷,正如桑塔格所描述的那樣,觀眾所經驗的是一種虛偽的共情。[21]
VR影像具有類似夢境、記憶的超現實傾向,受眾在此游玩體驗中消解了沉思,沉迷于想象。VR影像具有記憶的“危險”性,即“會以回溯的方式給事物賦予它本來沒有的意義。它會以回溯的方式抹去眾多事件的內在幻想,抹去形成事件獨特性的幻想”[22]。這種基于記憶再現現實的功能卻往往會走向超越現實、創造現實,“超越”也許會帶給受眾震撼的沉浸體驗,但“創造”永遠無法再現真實的感受和經驗,即人之所以為人的心理感知狀態。例如受眾在《集裝箱》中沉浸式消費奇觀,但如何用數字技術重現奴隸面臨死亡時的恐懼、絕望和不甘,其是否能將受眾從消費商品的游玩邏輯中轉換為體悟現實、建立共情的價值機制,答案似乎并不樂觀。
(二)“仿真”世界的“仿真式”共情
在符碼預設下的VR“仿真”世界中,受眾產生的共情體驗也具有“仿真式”特征,具體表現為快感式、想象性、身心不一性、消費游玩式。
一是快感式。當下是消費快感的時代,體現出重感官、快反饋的后現代主義文化癥候,VR影像便重視直觀、即時的心理和情感反應。受眾被“圈”入預設的超現實影像中,以“游玩”的中心位置參與角色行動、時空轉換及敘事進展,進而在生理、心理上得到既自主又被動的即時反應,生成與影像人物、文本及延伸意義之間的情感聯系。其本質是基于仿真影像創造的“游玩”體驗。
二是想象性。VR影像是可感知的、非“遠觀”的數字化景觀,需要受眾調動想象力自主認可與建構影像世界,從而充分參與到影像裝置中。當受眾主動性、想象性地認同影像時,會進入“自我想象式”或“他者體驗式”的移情狀態,但是,無論是“自我代入溝通”,還是“體悟他者體驗”,都帶有某種“偽善/虛假”的“濾鏡”——一邊消費奇觀,一邊旁觀共情。
三是身心不一性。身體具有與精神同樣的欺騙性,在VR影像中受眾的身體是非實體的、虛擬的,其顛覆了日常經驗中對真實與情感的察覺與鑒別能力。當VR裝置機器刺激著受眾的生理感官,身體會做出不經由思考的自然應激反應,這事實上與認知體系是分離的。如在《集裝箱》中,當惡劣生存環境中的黑人奴隸裸露著殘忍身體創傷突然近距離(并且越來越近)的出現在受眾的“面前”,受眾所感知到的首先是生理的應激反應——可能是悲憫、不忍直視……即使在影像結束后,這些具有刺激性的畫面仍是腦海里的關鍵記憶點,那么,受眾是否能夠由此認知到對奴隸真正平等意義上的同情與悲憫,以及生發出現實價值的情感力量,還是只停留在“生理上的共情”。于此,VR影像身心不一性的共情作用特征體現為身體與心理處于分離、不同步甚至是不匹配(身體超越心理)的姿態。
四是消費游玩式。VR影像是強調沉浸感、交互性的數字影像裝置,其消費游玩式的共情特征是注重受眾的消費體驗、掌控游玩。如前文提到,VR影像裝置帶給受眾的審美感受比起稱之為“觀看”,更像是“游玩”。在游戲中,玩家往往通過操作相關設備深度參與影像中,在選擇的游戲玩家身上找尋主體性,從而與游戲角色共進退。而在同樣注重受眾參與的VR影像中,受眾也具有較強的自主性,可以選擇性地認同影像角色、文本理念,那么這種“共感”是圍繞受眾為核心的,體現出消費主義文化癥候。即依靠“沉浸感=參與性”等價公式的VR影像所真正展現的影像奇觀,實際試圖喚起的并非某種“VR拯救××”的西方人道主義關懷,而是數字時代觀眾對于虛擬現實奇觀的消費欲望。[23]
結語
在后審美時代,審美與快感被混淆,快感甚至取代美感,似乎回到重視身體體驗、消解主體思考的“低級”階段。如當下短視頻對受眾的“吸引力”,“其是一種無意識的、欲望化的情動,是處在混亂無序變化過程中的自然的身體感受,沒有也來不及被整合為具有主體意識或社會表征意義的相對穩定的情緒”[24]。VR影像興起的本質同樣具有某種奇觀體驗的吸引與數字消費的驅動,所以,VR影像成為“終極移情機器”的關鍵,就在于能否引起受眾真實的共情情感,真正地觸動他們,進而有可能影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行為選擇。隨著VR影像創作技術的不斷發展,相信其引起的受眾情感共情將會具有更加真實、真切、真誠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Robert Hassan.Digitality,Virtual Reality and the \"Empathy Machine\"[ J ].Digital Journalism,2019:2.
[2]Derek Matravers,\"Empathy in the Aesthetic Tradition\",in Heidi Maibom,ed.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mpathy[M].London:Routledge,2017:78.
[3]周夢菲.社會認知理論視野下的讀寫教學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23.
[4]Schachter,S.,amp;Singer,J.E.Cognitive,Social and Physi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Emotional State[ J ].Psychological Review,1962:373.
[5]張菁.基于“雙因素”和“雙通道理論”的電影認知情感研究探索[ J ].當代電影,2022(01):149-155.
[6][法]讓·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M].車槿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83.
[7]張明浩.感知美學與感知電影:技術時代下重思電影“感知”之本性[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2(11):15-28.
[8]Burdea,G,Coiffet,P.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M].New York:John Wiley amp; Sons,Inc,1994:4-5.
[9][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512.
[10]張洪亮.觸感對虛擬現實影像美學的重構[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3(01):37-45.
[11]李洋.雅克·德里達與幽靈電影哲學[ J ].電影藝術,2020(03):3-10.
[12][斯洛文尼亞]斯拉沃熱·齊澤克.無身體的器官:論德勒茲及其推論[M].吳靜,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285.
[13]杜梁,聶偉.VR影像機制:“隱形”系統、幻覺“深潛”與腦機引擎[ J ].當代電影,2023(03):144-151.
[14]張凈雨.從斷裂到延展:逃逸與被征用的劣質影像[ J ].當代電影,2021(12):151-156.
[15]諾埃爾·卡羅爾,黎萌.電影、情感與類型[ J ].電影藝術,2015(02):115-121.
[16]張明浩,郭培振.論影游融合的“媒介共通性”基礎、敘事融合策略與想象力消費滿足[ J ].東南傳播,2022(02):5-9.
[17]黃泓積.走向更新的“象征交換”邏輯一一略論鮑德里亞的“超真實”概念及其誕生背后的理論脈絡[EB/OL].(2015-10-15)[2024-05-15].https://www.cafamuseum.org/exhibit/newsdetail/2267.
[18][22][法]讓·鮑德里亞.斷片集:冷記憶3[M].張新木,陳旻樂,李露露,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19-20,45.
[19]仰海峰.后生產時代、符號的造反與激進批判理論——鮑德里亞《象征交換與死亡》解讀[ J ].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4(02):12-18.
[20][法]讓·鮑德里亞.完美的罪行[M].王為民,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33.
[21]陳亦水.VR改變了當代電影“女性被看”的視覺機制嗎[N].中國婦女報,2019-05-28(6).
[23]陳亦水.柏拉圖之穴:關于虛擬現實(VR)影像藝術的媒介文化研究[ J ].電影評介,2020(16):4-9.
[24]李寧.情動的危機:流媒體時代短視頻平臺的觀影體驗[ J ].當代電影,2023(04):85-90.
【作者簡介】" 周 涌,男,四川仁壽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北京市四個一批人才,主要從事影視創作及理論研究;
郭培振,男,山東菏澤人,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碩士生。
【基金項目】" 本文系北京市宣傳文化系統高層次人才培養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戲劇與影視學理論構建研究”(編號:SGYP20230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