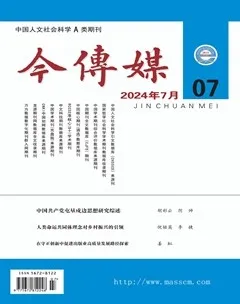淺析網絡新聞報道中女性形象的建構
摘 要:大眾媒介借助互聯網技術實現了新聞報道方式轉型,越來越多的女性身影出現在大眾媒介中。本文以部分微博賬號近一年的新聞報道內容為研究對象,采用構造周抽樣法,抽取部分樣本來研究新聞報道內容對女性形象構建情況,發現其中發布的女性相關報道多以負面為主,正面相對較少,且未全面地向受眾展現當代女性形象。與此同時,分析總結了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并對女性形象媒介呈現的未來之路進行了探討與歸納,旨在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關鍵詞:女性形象;網絡新聞報道;形象建構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24)07-0116-04
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傳播媒介更新迭代迅速,網絡媒體憑借信息豐富多彩、交互方便快捷等特點,吸引了廣泛關注,成為除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以外的“第四媒體”,全方位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網絡時代的去中心化讓女性更多地參與到公共話題空間,女性話題逐漸成為大眾媒介關注的焦點內容。同時,當今的國際社會普遍重視對女性權利的尊重和保護,甚至將一個國家對女性的尊重作為對該國文明程度判斷的標尺[1],因此,對女性形象進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法國女性主義研究者西蒙娜·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指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而成的”[2]。在互聯網時代,網絡新聞媒體在女性媒介形象塑造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部分網絡新聞并沒有全面客觀地報道女性形象。基于此,本文運用文本分析法,對部分微博賬號2023年1月至12月期間的新聞報道內容進行分析,由于樣本量過大,采用構造周抽樣法抽取部分樣本進行研究,總結網絡新聞報道中塑造的女性媒介形象概況、影響因素,探討女性形象媒介呈現的未來之路。
一、網絡新聞報道中塑造的女性形象
“形象”的概念內涵很豐富,不同領域的學者對其解釋也不同。在傳播學領域,人是形象認知的主體,“形象”被認為是一種認知信息。范玉明在《基于建構視角的媒介意象研究》中指出:“媒介形象就是媒介化的形象,是客觀存在的人或物通過大眾傳播媒介的建構,從而呈現出的符號化的認知信息。媒介形象是建構的產物,它是從社會現實中派生出來的,但并非單純的現實投射出來的。”[3]“女性媒介形象”是通過大眾媒介構建與呈現的女性群體形象,既帶有一部分真實的女性群體特征,又包含著大眾媒介的主觀認知,反映了社會公眾對于女性形象的態度。
本文在部分微博賬號中以“女”或“女性”為關鍵詞進行搜索,并對搜索內容采用構造周抽樣法。2023年全年共365天,即52個星期零1天,所以按52周的總體基數計算,從中選取為期4周共計28天的樣本,再經過篩選剔除無關樣本。
通過對有效樣本進行分析,本文發現這些賬號中構建的女性形象以正面為主,多數報道內容展現了女性在不同領域的個人成就、貢獻和優良品行等。例如,《女博主在國外受種族歧視霸氣反擊》《向乘客哽咽喊話的女乘務員被提拔》《張桂梅曾流著淚把失學女孩找回學校》《17歲黃雨婷登上福布斯!成為今年最年輕上榜者》等,這類報道展現了女性辛勤工作、無私奉獻、勇于奮斗的形象。網絡媒介塑造出的女性正面形象相較于傳統媒體來說更加多樣。總的來看,正面的女性報道涉及的領域逐漸廣泛,但是也存在所塑造的正面女性形象相對片面的問題。
負面報道數相對較少,多以弱勢形象報道女性,沒有完整客觀地塑造女性形象。例如,將女司機描繪成“事故幾率大”“應變能力差”的形象,使人們錯誤地形成了“女性是馬路殺手”的認知;在女性受到傷害的報道中,將女性刻畫成“弱者”形象,突出女性受害者的身份而缺少對施害者的批判;在女性違法犯罪的報道中,將女性塑造成“沖動無知”的形象,將犯罪原因歸結于她們的不理性,未深挖其中真正的原因。這些報道所建構的女性形象較為主觀片面,造成了女性形象被污名化。
蓋伊·塔克曼認為:“大眾媒體會將女性置于一種被責難、被瑣碎化,甚至在傳播過程中不被媒介呈現的情形下。”[4]目前,部分網絡新聞媒體對女性被害、不文明行為的報道比較多,這使得少數女性群體的消極事件在受眾眼前大量出現、比例增加,雖然能迎合一些受眾的心理,卻導致女性群體被污名化、標簽化。
二、影響網絡新聞報道對女性形象塑造的因素
(一)男權社會的根深蒂固
社會性別一詞最早由蓋爾·盧賓提出,該學者將社會性別定義為“一種由社會加強”的兩性區分,“是性別的社會關系產物”,這一觀點使社會性別成為女權主義學術和理論的核心概念[5]。學者戴維·波普諾將“性(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區別開來,認為“sex”指男女生理上的差異,而“gender”用來區分男女在心理特征上的差異[6]。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女性的行為受到種種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得到提升,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但是,社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依舊存在。
此外,網絡新聞媒體與受眾的社會性別意識也有待提升,例如,部分媒體與受眾存在“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的思想。網絡新聞媒體受到傳統的父權文化影響,基于男性視角來報道與女性相關的新聞;受眾通常會贊頌女性對家庭的犧牲與隱忍,將女性的形象局限在了家庭之中,這便是受眾性別意識的典型偏差之一。女性的形象不僅僅只體現為賢妻良母,更應該體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如今,許多優秀女性在社會發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如女飛行員、女科學家等,但部分網絡新聞媒體卻沒有客觀全面地展現她們的形象。
(二)注意力經濟的推波助瀾
邁克爾·戈德海伯在《注意力購買者》一文中提出了“注意力經濟”的概念———“人們關注一個主題、一件事、一種行為和多種信息的持久尺度。”可以理解為注意力成為稀缺資源,獲得注意力便成了一種重要的財富。由于我國大部分網絡新聞媒體并不具備采訪權,只能轉載新聞,因此在商業化的發展進程中,它們為了謀求利益,在點擊率、瀏覽量、下載量等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競爭,這便出現了標題黨、炒作、蹭流量等現象;部分網絡新聞媒體也熱衷于報道滿足受眾好奇心理與感官需求的內容。例如,利用帶有夸大與獵奇效果的字眼來激發受眾興趣,從而獲得閱讀量、點擊量。
女性形象在媒體中被呈現的機會,并不僅僅源于媒體的責任感,更多是媒體自身滿足利益需求和迎合受眾的客觀需要[7]。因此,在消費主義與注意力經濟的影響下,部分網絡新聞媒體為了受到大眾青睞,對女性群體備加關注,甚至在新聞報道中加入與“性”“傷害”有關的內容,這種做法忽視了作為新聞傳播者本應承擔的責任,導致女性形象被標簽化,不利于塑造真實的女性形象。
(三)媒體“把關人”的功能弱化
盧因在《群體生活渠道》一文中指出,在群體傳播的過程中,存在一些“門區(Gate)”的渠道,信息的流動就是在這些渠道中進行的。這些渠道都有一些“看門人”即“把關人”,只有符合群體規范和把關人價值觀的信息才能進入到傳播渠道中[8]。從心理學角度來看,有兩個方面影響著把關人:第一,人的認知結構;第二,動機,包括價值判斷的選擇、需求以及要克服的干擾和障礙[9]。
傳統的把關流程也隨著網絡新聞的發展而改變。傳統媒體在采訪、寫作、編輯、審查和傳播信息方面有嚴格和標準化的程序,而網絡中的信息量過于龐大、內容豐富,把關人難以在有限的時間內篩選出真實可靠的信息。目前,大部分網絡新聞媒體都采用“智能+人工審核”的審核機制流程,即智能系統去除掉內容中含有違法違規的內容后,再由人工審核進一步篩選。相較于傳統把關流程,這樣的審核機制容易導致網絡中虛假信息泛濫。此外,網絡新聞報道的內容大多來源于對傳統媒體報道的篩選、轉載等,為獲取點擊量,它們往往會通過標題吸引受眾眼球或進行敘事煽情,導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較為混雜,甚至出現了歪曲的現象。
例如,《健康時報》針對“病媛”事件發布了文章《“佛媛”之后再現“病媛”: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妝》,隨后,澎湃新聞、環球時報等諸多知名網絡媒體和政務平臺在沒有核實新聞真實性的情況下,盲目跟風轉發這篇文章,加入了聲討“病媛”的行列。然而,事件卻發生了反轉,這篇報道與事實嚴重不符,損害了當事人的名譽。這一現象反映了部分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思考不充分的工作態度,對新聞的真實性不加佐證就直接報道,甚至是跟風報道,且報道內容中還存在不合理標簽的情況,這些都是對當事人的過度消費,更是新聞媒體對自身公信力的不重視。
三、網絡新聞報道中女性形象的重構
(一)推進性別意識教育,增強女性自我意識
兩性關系是最重要、最普遍的社會關系之一,男女平等發展是社會和諧的重要特征,也是社會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10]。因此,政府部門要向社會宣傳正確的性別觀念,加強全社會的性別意識教育,完善健全婦女權益保障的相關措施。媒體工作者要轉變自己的性別觀念,在報道標題、內容中引導受眾樹立正確的性別觀念,多展現女性積極正面、豐富多樣的形象。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的獨立意識不斷增強,女性自身也要改變傳統觀念,提高對性別平等意識重要性的認知,勇敢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二)增加女性相關議題,豐富女性媒介形象
縱觀各網絡新聞中對女性議題的報道可以發現,大多數塑造出的女性形象以正面為主,且主要集中在對高知女性的報道中。因此,應增加與女性相關的報道數量,拓寬報道的領域,展現不同女性形象,從而激勵更多女性群體,體現女性對社會的價值。同時,網絡新聞媒體要為女性提供表達自我與發聲的渠道,鼓勵女性勇敢地向大眾展現自己的能力與優勢,積極地為自己、為其他女性發聲,擁有更多的媒介話語權。
(三)強化網絡媒體責任,加強內容把關篩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提升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新聞媒體是我國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工作應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隨著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信息傳播環境和結構發生了較大改變,大眾傳媒所承擔的責任越來越重,它不僅影響著大眾的價值觀,更影響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因此,在性別價值觀上,網絡新聞媒體要引導受眾樹立男女平等的價值觀。新聞的本源是事實,媒體工作者要堅持真實性和客觀性原則,時刻擔負起責任,全面提高職業素養,同時增強把關意識,積極做好“把關人”,減少迎合商業市場與受眾的花邊新聞、口水新聞,減少女性新聞報道內容中的敏感詞匯,避免產生刻板印象,提高新聞質量與專業性。此外,還要對女性形象進行全面塑造,增加女性的正面形象報道數量,提高新聞報道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和公信力。
四、結 語
網絡媒介是人們獲取新聞的主要渠道之一。近年來,網絡新聞中對女性正面形象的報道不斷增長,但仍存在帶有性別歧視的信息,甚至夾雜著媒體的主觀看法,導致女性形象被“標簽化”“污名化”。為了重塑女性形象,網絡新聞媒體應積極糾正這種異化現象,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樹立正確的性別意識;在新聞生產的過程中,強調客觀敘述,杜絕性別歧視,完善與優化女性相關新聞報道的內容質量;增加女性相關議題,賦予女性更大的話語空間,讓更多人聽到更多女性的聲音,維護女性利益,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燁輝.基于女性形象傳播的國家形象塑造思考[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4,36(12):146-147.
[2]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Ⅱ[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8.
[3] 范玉明.基于建構視角的媒介形象研究[J].新聞知識,2018(11):20-24.
[4] 曹晉.抗爭途徑:婦女與另類媒介[A].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傳播與中國·復旦論壇”(2011)———交往與溝通:變遷中的城市論文集[C].上海: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2011:12.
[5] 金一虹.社會性別理論:新視角?新思維方式與新的分析范式———《社會性別研究選譯》評介[J].婦女研究論叢,1999(1):58-60.
[6] 戴維·波普諾.我們身處的世界:波普諾社會學[M].李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383.
[7] 羅漢,鄒月華.媒介?話語與性別:虐童報道中女性形象研究———以“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為例[J].新聞愛好者,2020(10):89-91.
[8] 范佳明.網絡傳播對把關人理論的顛覆與重組[J].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3):118-119.
[9] 麥奎爾.大眾傳播模式論[M].祝建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135.
[10] 劉淑娟.男女平等社會性別視角解讀[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1(5):222-224.
[責任編輯:李慕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