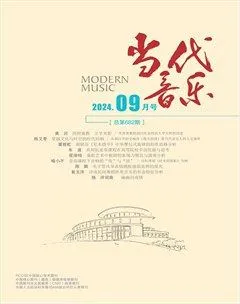流域文化空間視野下瀘州河川劇芻議
[摘 要] 流域文化空間是近年來民族音樂研究的熱點視野,屬于長江上游支流的沱江,其流域孕育了四川盆地的眾多優秀民族文化,其中,瀘州河川劇便在此生根發芽。本文以瀘州河川劇為研究對象,將沱江流域文化空間作為觀察場域,從流域音樂人類學的整體性、關系性、開放性和動態性視角出發,探究瀘州河川劇自身發展及劇種主體、參與者主體間的互動關系,并以流域文化空間為依托研究瀘州河川劇的發展策略。
[關鍵詞] 瀘州河川劇;整體性;關系性;動態性;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 J607"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2233(2024)09-0089-04
“流域”“聚落”“走廊”,已成為近年來人類學研究的視野熱點。我國是一個流域眾多的國家,黃河、長江、珠江等江河流域是我國各族人民賴以生存的沃土,并在華夏土地上產生了大量的精神食糧。民族音樂學家將視野投放到流域空間,旨在剖析自然場域中的文化屬性,多維立體地呈現當地音樂文化,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流域音樂人類學——“流域音樂人類學是在吸收流域人類學研究理念的基礎上,取其整體性、動態性、關系性和開放性視角,對流域內所有水系的音樂文化事項進行立體式研究,其主旨在于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方法來探究流域音樂文化的多元敘事,揭示流域音樂文化的整體全貌。”[1]
其中,西南地區山河交錯,盆地、高原和山地集聚于此,是人類學田野考察的重要實踐場域。沱江是長江上游支流,是四川盆地區域文化發展的重要河道之一。而瀘州作為沱江沿岸的文化重鎮,地處川、渝、滇、貴四省通衢,且為沱江長江交匯處,交通便利、物產富饒,歷來是川東南經濟、文化中心。沱江對瀘州的發展影響深厚[2]。四川東部河流眾多,瀘州河川劇也得益于發達的水路而流傳到河道相連的各個地區[3]。本文以流域空間為觀察場域,從流域音樂人類學整體性、關系性、動態性、開放性的學科視角出發,分析瀘州河川劇劇種及區域主體間的互動關系,并以流域文化空間為依托研究其發展策略。
一、瀘州河川劇藝術整體性敘事
四川的川劇藝術以河道來命名流派,按地域劃分,分為西壩、資陽河、川北河、下川東四大流派,瀘州地區傳承的川劇被稱為瀘州河川劇,瀘州河川劇屬資陽河流派分支。地域上,瀘州、資陽同屬沱江沿江城市。沱江發源于川西北九頂山南麓,流經成都東側、簡陽、資陽、自貢、內江,至瀘州匯入長江主干,全長712公里,上游從源頭至金堂縣的河段稱綿遠河,金堂至瀘州匯入段方稱沱江。流域內有青白江、湔江、釜溪河、瀨溪河、陽化河、九曲河等多條重要支流,流域內部聚集了多個重要工業城市,也是成都平原腹地重要的蔗、棉農產區。
(一)歷時性研究
古代河運網絡四通八達,文化也隨河運游走在各個城鎮之間。關于瀘州河川劇藝術的起源,有學者認為:“以瀘州河為代表的資陽河川劇藝術是川劇的起源,川劇中的高腔是川劇聲腔的最初形態,川劇高腔源自弋陽,其遠祖為弋陽腔,近源則為流行于明末安徽地區的徽池雅調。”[4]歷史上多次“湖廣填四川”移民潮,使得客家、荊楚的音樂元素,也隨著川江流域深入到四川盆地腹地。瀘州河川劇較其他流派,保留著更深厚的傳統高腔。據當地非遺工作者介紹,瀘州河川劇藝術孕育于元雜劇,流行于雍正二年(1724年),瀘州戲曲藝人赴成都演出,在當地收徒并傳播,成立了川劇歷史上最早的戲班——慶華班,并借此開啟了西壩川劇流派的藝術之路。
水對西南流域的族群互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這決定了以西南山間河流為中心的族群廊道的方向性和整體性[5]。川劇早期的傳播方向由瀘州北上,途經自貢、資陽等進入成都平原腹地,沱江流域的河流走向對其文化傳播路徑產生了極大影響。資陽河流派也因流域的聯結聚合,區域藝術風格趨于統一,流域內部族群文化認同通過河道川劇藝術與自然文化屬性的緊密關系,形成互動紐帶,同時也促進了區域文化主體間的協同發展。
(二)共時性研究
共時性與歷時性的概念相對,主要針對當下的音樂活態資源開展研究,從空間的維度對具體音樂事象進行解讀。胡曉東認為:“川江流域音樂文化的共時性整體研究,在凸顯流域作為線性文化景觀的前提下,關注流域內具體音樂事象和文化主體在不同空間語境中所展現出的多元一體格局和互文性結構關系,全方位拓展川江流域音樂文化的整體性研究。”[6]
瀘州河川劇藝術的共時性研究,旨在探析在沱江流域空間中,作為觀察對象的瀘州河川劇與當地其他具體音樂事象的共生互融關系。民族音樂中,民歌是基礎,戲曲、民間舞蹈、民族樂器、說唱都與之有著重要聯系。瀘州地區民間音樂體裁眾多,代表的有中河調清音揚琴、永寧河船工號子、福寶石工號子、瀘縣嘉明花號、玄灘薅秧歌(薅草鑼鼓)等。幫、打、唱是川劇高腔的主要表現手段,其中幫腔通常采用領腔與和腔配合的形式,瀘州河川劇善用幫腔,這在整個川劇流派都是獨具一格的。劇情進行當中,常采用借眾幫聲的方式渲染氛圍,這與玄灘薅草鑼鼓、永寧河號子一領眾和的表演方式非常相似。此外,在相似的打戲舞蹈中也能找到民間曲藝之間互相借鑒的影子,如瀘州河川劇和瀘縣百和蓮槍的耍槍打戲的融合。
二、瀘州河川劇藝術關系性敘事
瀘州河川劇藝術關系性的探究,注重劇種本身與具體的社會主體、社會場域的直接雙向互動,從“關系”的范疇看待劇種在所處場域中的定位和意義。在民族音樂學的研究過程中,對音樂事象的研究不僅需要關注音樂本身,更要關注與音樂產生關系的音樂主體——人、音樂發生的場域——具體的自然及社會環境等除音樂以外、音樂事象以內的事物。在具體音樂事象研究中,“音—人—地”的關系是研究者不可忽視的范疇。人地關系的研究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中心課題,主要探討各種人文現象的分布、變化、擴散、人類社會活動的空間結構及人類活動所創作的人文事象規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音樂地理學也為民族音樂學的學術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7]。
瀘州河川劇和流域的關系,是以人為媒介的,人在其中所處的角色不同,思考的視角不同,發揮的作用便不同。在這其中,表演者(會館、劇團人員)—觀眾(消費者)、表演者(執行者)—領導者(決策者)兩對主體關系占主要方面。
(一)表演者(會館、劇團人員)—觀眾(消費者)
一方面,表演者作為輸出方,其自身的專業水平和藝術追求決定著表演角色最終的呈現效果,也影響著一部作品整體的完成質量。而觀眾作為藝術作品的接收方,他們所樂見的作品又是由自身的喜好和經驗決定的。通常情況下,觀眾的接受程度相較于表演者自身,更能決定一部作品的成敗和后續的演出收益。這種接受主體和表演主體同等重要甚至超過表演主體重要性的例子,在當下民間音樂的發展中并不少見,這也是民間音樂商業化之后,主體權力轉移的必然結果。因此,沱江沿岸會館劇團里的瀘州河川劇表演者需要顧及迎來送往的商客的文化背景。
(二)表演者(執行者)—領導者(決策者)
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音樂的載體和傳播方式也在不斷地更新迭代,瀘州河劇種本身的革新力度與現今音樂傳播快速發展之間的不平衡,加劇了瀘州河川劇的發展困境,需要強有力的抓手將有關民間力量匯聚。在瀘州河川劇的現代傳承和傳播中,國家權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劇種的專項扶持和人才的專項培養,減輕了民間劇團單一前進的困難,瀘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習所根據現有場地和師資力量,建立瀘州市非遺藝術免費培訓基地,集中開設瀘州河川劇精品傳習班,并聯合全省中小學、高等院校招收瀘州河川劇表演人才[8]。這在無形之中推動了瀘州河川劇的發展。
瀘州河川劇的社會功能是其與瀘州人民相精神聯系的體現。文化藝術是一種外顯的精神世界,我們總能從每個民族、地區的藝術產物窺探到該民族、地區的精神風貌、人文傳統。所以,瀘州河川劇從民間藝術的層面體現了自身的社會風貌呈現功能,它將瀘州人民的似火熱情、干練又安逸的慵懶感用變臉、吐火、耍槍爬繩等技巧藝術地呈現出來。同時,瀘州河川劇也有教育傳承功能,如《三跑山》《白蛇傳》的劇情,用藝術的表現手法講述人生道理。
三、瀘州河川劇藝術動態性敘事
流域是地理概念中的相對靜止的一片土地,而河流則是這片土地上流動的血脈。沱江作為進入四川盆地的水上通道之一,連接了自東而來、自西而去的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旅人,也為不同流域間的音樂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能。沱江流域銜接了西南絲綢之路、茶馬古道的區域交通,其音樂文化在繼承當地傳統文化的同時,也不斷受到外域、外族文化的影響。而瀘州河川劇藝術的發展動力就是源于沱江流域的動態性敘事特征。
此外,大規模的族群遷移也是瀘州河川劇藝術多元性的重要原因,如歷史上著名的明朝洪武大移民“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為當地注入了許多異鄉血脈和藝術種子。瀘州合江縣的《張氏族譜》中有一首始遷祖留下的《留別遺后詩》,其中提到:“自統湖麻祖籍居,紅巾趕散各東西;先到巴渝開大業,后到綦陽置田溪。”瀘州市的《創修羅氏特凌支譜》稱:“祥勝,字勝二,先業儒,元致和末徙湖廣麻城,孺人麻城仙居鄉人也。至元、正間兵亂,攜家屬至松溉,時荒林茂草,茫茫而已,始就荒居,以避亂焉。”[9]歷史上的幾次移民潮,促進了西南地區的民族多樣性發展,使西南四省與湖廣、江西等地的人民交往更加密切,在催生航運事業發展、貨物交流頻繁的同時,也極大地促進了精神文化的交流傳播。人們在瀘州沱江沿岸的碼頭、河港周圍建立會館,如瀘州合江的萬壽宮、瀘州龍馬潭小市從前建的會館茶館,是供各個省份地區的人們思鄉懷舊,滿足商客的鄉土情懷的重要場所。
音樂體裁動態性敘事有兩個方面的呈現:音樂涵化和濡化。音樂涵化是指不同區域或族群的音樂文化因長期交往、交流而引發的相互影響與交融的結果。濡化則是同一文化內部的傳播過程,是文化內部主體自我的傳承方式,也是建立族群文化認同的過程。瀘州河川劇在其發展過程中,吸收四川清音“哈哈腔”、玄灘薅秧歌表演形式、川江號子音樂風格,在作品中融合當地多種音樂形式,豐富了自身的音樂多樣性和表現性。
四、瀘州河川劇藝術開放性敘事
西南地區的聚落整體呈現出大分散、小聚居的聚落樣態。有學者形容道:“西南范圍內的聚落,就像散落在山間河谷中的珍珠,散發著歷史與文化的熠熠光輝。然而,單顆的珍珠無論多么完美,其價值都非常有限,只有將一粒粒珍珠按照一定的方式穿連起來,才能成為手鏈和項鏈,形成整體和諧的美感,發揮其最大的價值。而這條關鍵的線,就是靜靜流經村落的河流以及由河流形成的廊道。”[10]
民族文化生態系統是開放的,具體表現為民族之間文化上的相互交融和族際間的文化溝通[11]。從漢代唱跳開始,到隋唐瀘州戲曲雛形的建立,元雜劇內容和演出形式的加入,再到清朝川劇第一個戲班成立,瀘州河川劇能經受幾百年的演變卻依然頑強,與其不斷推陳出新、革故鼎新的戲曲品質有關。當地表演者在保留瀘州河川劇固有特色的同時,積極吸納異質音樂文化精髓,以“拿來主義”精神,融合新的元素。同時,流域空間的開放性也為瀘州河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外族、外域音樂,流域內部聚落間的風俗共融互取,也加深了瀘州河川劇的歷史積淀。如四川地區盛行的“燈戲”,瀘縣牛灘的“馬兒燈”、瀘州古藺縣“花燈”等,都為瀘州河川劇的藝術延展力提供了更多借鑒的可能。
族群的開放性,是瀘州河川劇保持藝術多元性的第二層外因。在沱江流域,漢族、彝族、回族、藏族等多民族和平共處,民族文化間的交流加深了各民族精神文明的歷史厚度,少數民族的民族風尚、風俗被表演者用漢文化的表現形式藝術地呈現出來,如瀘州河川劇的經典絕技——吐獠牙,就受到了少數民族祭祀所用鬼怪形象的啟發。作為沱江流域的經典,瀘州河川劇藝術吸收各家所長,促進了當地人民對自身文化的認同感,同時加深對民族的族群認同、區域文化認同,凝聚了本土人民的文化向心力。
五、瀘州河川劇發展困境及策略
(一)瀘州河川劇發展困境
隨著現代多元音樂風尚的流行,主流音樂審美更替,瀘州河川劇面臨著無人可傳,無戲可表的尷尬境地。曾經的瀘州民間音樂核心地位正逐漸邊緣化,正統的瀘州河川劇流派急需開辟新的發展路徑。當前瀘州河川劇面臨的困境有:
1.表演組織者減少。劇團數量急劇下降,現今可查詢到的發展瀘州河川劇的專業組織僅瀘州非遺傳習所一家,民營劇團幾近凋零。
2.專業表演者減少。如今還活躍在表演一線的表演者大多為高齡老人,總體的表演質量下降,表演者出現斷代危機,急需年輕血液加入。
3.表演內容的隨意性。非遺活動開展之前,民間劇團保存曲目譜集的能力不佳,導致曲目保存不完整,影響實際表演操作,在實際表演中,便會有臨時刪減段落,隨意拼湊戲份的情況發生,進而影響總體觀感。
4.受眾反饋效果對劇種的影響減小。時代更替,觀看戲劇表演的觀眾也在變化,老戲迷因年齡、身體健康狀況等逐漸減少,新戲迷在戲劇審美方面與演出者的差異性,都會影響劇目演出頻次。而新興傳播手段的發展,則是改變人們觀戲方式的主要原因。
5.劇種理論及演出文本資料沒有得到重視。現階段的瀘州河川劇已流失百余個劇目文本,一些經典的表演劇目也欠缺音視頻資料(或已流失),且缺乏專門從事瀘州河川劇的音樂創作、理論研究的人才。
(二)瀘州河川劇發展策略
1.還原川劇歷史定位,建立流域發展網絡
以瀘州河川劇為代表的資陽河川劇流派,一直被視為川劇正朔,它較完整地保留了川劇最原本的表演樣態,原始的川劇高腔至今存在于瀘州河川劇的表演中。因此,還原瀘州河流派的歷史定位,樹立當代劇種表演者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從劇種文化本身引導參與者積極建設,有一定現實意義。同時,以沱江流域空間為自然基礎,在相同或相似的社會文化場域中建立區域發展網絡,聯合流派內部各文化聚落,打造沱江河道川劇品牌,有助于增強川劇流派本身的文化建設。
2.融合本有民間音樂,突出劇種個性元素
突出瀘州河川劇“吐獠牙、打叉、斗笠功、倒彪椅子”等劇種絕技的宣傳,復排經典劇目如《火燒濮陽》《九龍嶼》《白蛇傳》,有意識地建立劇種文化標志,使這些文化符號在觀眾心中產生“聯覺”效應,增強參與者本身及普通觀眾對瀘州河川劇形象的認同觀念;融合本有民間音樂特色,如潮河鐵水花龍舞、牛灘馬兒燈、玄灘薅草鑼鼓、古藺花燈等,以及永寧河號子等河道藝術體裁,吸收其中的經典作品曲調,如玄灘薅草歌“涼風吹來心有潮”等曲調,可以豐富瀘州河表演內容及藝術形式,促進劇種整體多元發展。
3.保存作品原味風格,推進劇種藝術革新
有學者認為:“川劇的曲牌眾多,但從旋律特點上看,許多曲牌僅僅是一兩腔、一兩音之差,大同小異者甚多。”[12]與之相同,瀘州河川劇作品數量多,曲牌種類更有兩百多種,但經典曲牌占比較小。從瀘州河川劇曲牌基本曲調的板式入手,增強唱腔的板式變化,整合部分區別甚微的曲牌,有助于增強曲牌的經典性和代表性。
瀘州河川劇的唱腔,以高腔、胡琴腔為代表,其中高腔又占有絕對突出的地位。瀘州河川劇唱腔的發展,可以在保留高腔傳統的基礎上,增加輔助唱腔,為拓展瀘州河川劇聲腔多樣性創造更多的可能。川劇聲腔發展中,有過融合多種唱腔的方式,比如現代川劇《塵埃落定》,在延續川劇高腔傳統的同時,融入了藏族民間音樂“鍋莊”和大合唱為輔助唱腔[13]。這對瀘州河川劇在此路徑上的發展有借鑒意義。
伴奏方面,瀘州河川劇的打擊樂伴奏(鑼鼓伴奏)是其突出優勢之一。表演時,唱句之間常常僅用鑼鼓聲連接,因此,是否加入更多的旋律伴奏也成為瀘州河川劇戲改的重要話題。筆者認為,在復排傳統劇目時,保留鑼鼓伴奏的優勢,創新性地加入合適的旋律伴奏,可以增加劇目本身的音樂表現力。在創作現代瀘州河川劇作品時,嘗試加入管弦樂、人聲音響等西方、現代的伴奏形式,亦可在瀘州河川劇伴奏音樂的創新發展上作出重要嘗試。
4.借助非遺傳承保護,培養新時代人才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保護是民族文化繞不開的一環,瀘州河川劇藝術在非遺保護政策的扶持下,已入選四川省非遺名錄。專項政策、資金的扶持,成功挽救危機中的瀘州河川劇。瀘州河川劇可以借此契機,加大對年輕傳承人的培養,在瀘州中小學設立戲曲藝術第二課堂,發掘、培養人才,與高校建立瀘州河表演人才對口通道,為劇種的表演、創作、理論研究提供專業的人才支撐。
5.扶持劇團演出,開辟新傳媒傳播路徑
從線下線上多方面拓寬劇種宣傳渠道。扶持、重組整合民營社團,為民間團體演出創作提供資金幫扶、表演平臺。以民營劇團為中心,建立各級劇種聚落,打造劇團品牌。借助新媒體發展,開通瀘州河川劇宣傳網站、線上公眾號、視頻號,用AI制作、VR全景等方式開辟更多線上觀劇渠道。拓展瀘州河川劇周邊業務,提高曝光度,讓更多人了解并喜歡上瀘州河川劇。
結" "語
以沱江流域為文化生成空間的瀘州河川劇流派,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和傳播條件。通過整合流域內的音樂發展資源,調動沱江沿岸各文化河道,建立流域內流派發展共同體,打造區域藝術品牌,是瀘州河為代表的資陽河流派發展的整體性空間優勢所在。瀘州河川劇關系性范疇的兩對主體,是瀘州河川劇能否長遠發展的動力性因素。正面發揮表演者與決策者、表演者與觀眾的關系紐帶作用,才能更好地利用外部參與者扶持自身。積極融入當地、外域民間音樂、民間雜技,調動劇種本身的動態性和開放性作用;在保存劇種原有特色的同時,從唱腔、曲牌、伴奏等方面推動瀘州河川劇藝術革新,促進瀘州河川劇的創新多元發展;借助非遺政策和新興傳媒力量,擴大瀘州河川劇流派的影響力。瀘州河川劇的傳承與發展,離不開當代文化建設者的共同努力,有了社會各界的共同扶持,瀘州河川劇藝術定能常青不敗。
參考文獻:
[1] 胡曉東,謝佳麗.流域音樂人類學鉤撢:以川江流域為例[J].音樂研究,2022(04):89-100.
[2] 銀進康.“瀘州河”民營職業劇團及創作特征——以龍潭劇社為例[J].四川戲劇,2012(06):13-15.
[3] 彭煦,包靖.瀘州河川劇傳承與發展的自我救贖[J].四川戲劇,2018(09):85-87.
[4] 鄔丹.瀘州河川劇藝術特色淺析[J].中國戲劇,2018(09):60-61.
[5] 王劍.聚落、廊道、立面:西南區域研究的流域人類學視野[J].社會科學戰線,2016(10):270-274.
[6] 同[1].
[7] 吳惠敏.音樂與地理之關系的個案分析[J].音樂創作,2013(08):119-121.
[8] 同[3].
[9] 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5卷·明時期)[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148.
[10] 同[5].
[11] 鄧先瑞.長江流域民族文化生態及其主要特征[J].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06):10.
[12] 馮光鈺.川劇高腔音樂改革芻議[J].音樂研究,1982(01):107-115.
[13] 吳民,陳莉萍.一次成功的藝術探索——論現代川劇《塵埃落定》的創新與突破[J].新疆藝術學院學報,2014,12(04):76-80.
(責任編輯:劉露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