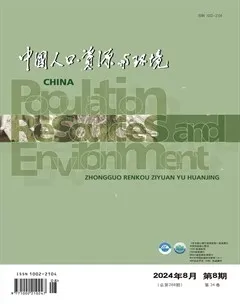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時空格局與分布動態演進













關鍵詞 生態足跡;生態韌性;空間相關性;核密度估計;Markov鏈分析;黃河流域
中圖分類號 X321;F1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4)08-0136-12 DOI:10. 12062/cpre. 20240318
黃河安瀾,天下大穰。黃河流域作為中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然而,由于黃河流域生態系統先天脆弱引致的各類災害[1],加之長期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帶來的生態失序[2],致使旱澇災害、土壤侵蝕、水土流失、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頻發,流域生態系統遭受著無法避免的擾動與沖擊,區域生態安全與可持續性面臨著嚴峻挑戰。面對經濟社會發展對生態資源的過度攫取,黃河流域生態系統亟須提升韌性水平,進而消解與吸納這類外界干擾。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國務院于2021年10月發布的《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和生態環境部等4部委于2022年6月聯合發布的《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均明確指出,要防范和化解生態安全風險,提高黃河流域自然生態環境的適應力和恢復能力。黨的二十大報告同樣強調,要推進生態優先發展,提升生態系統穩定性。由此可見,如何提升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增強生態系統對外界擾動的消解與吸納能力,已成為新時代全面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進程中一項亟待解決的重要議題。因此,全面揭示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時空格局與分布動態演進特征,對于制定科學合理的生態環境保護規劃與政策,確保生態系統環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文獻綜述
韌性概念最早由Holling[3]引入到自然生態學領域,并形成“工程韌性”概念,其是指系統遭受外部沖擊后恢復到原有狀態的能力。在此基礎上,Alberti等[4]從人類生態學視角出發,將生態韌性定義為生態系統在應對長期壓力時,能夠迅速恢復到初始狀態并保障區域生態安全的能力。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從韌性強度與韌性限度兩方面界定生態韌性內涵[5]。其中,韌性強度是指生態系統在外部風險影響下的預防、響應及恢復力程度,而韌性限度是指生態系統能夠承受外部干擾而不喪失功能的范圍,取決于區域生態系統對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消耗資源的包容程度與適應能力[6-7]。
生態韌性水平測度是生態韌性研究的關鍵,測度方法可分為綜合指標體系法和生態足跡法兩類。①綜合指標體系法,即通過構建生態韌性綜合指標體系,從不同維度指標計算綜合評價值的方法,常用于測度生態韌性強度。現有研究采用人口密度、GDP、綠化覆蓋率、污水處理率、降水量、NDVI等指標構建了抵抗-響應-創新、規模-密度-形態、抵抗力-適應力-恢復力、潛力-連通度-恢復力等生態韌性綜合指標體系,并采用耦合協調模型、熵權TOPSIS法、社會網絡分析等方法測度生態韌性[8-11]。如王松茂等[8]從“抵抗-響應-創新”視角測算山東半島城市群生態韌性水平,認為該地區生態韌性水平具有“高值散落、低值集聚”的空間非均衡分布特征,總體呈波動式增加。修春亮等[9]通過構建“規模-密度-形態”三維評價體系測度大連市生態韌性水平,發現大連市生態韌性水平整體呈下降趨勢。陶潔怡等[10]從“抵抗力-適應力-恢復力”角度測算長三角地區生態韌性水平,并指出該地區生態韌性水平整體呈波動上升趨勢。王文慧等[11]采用“潛力-連通度-恢復力”三維體系測度鄱陽湖生態韌性水平,認為鄱陽湖水陸交錯帶生態韌性水平與區域生態系統本底緊密相關,整體有所增加。②生態足跡法,即通過計算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兩項指標的差值或比值來表征生態韌性水平,多用于衡量生態韌性限度。如王少劍等[2]采用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比值測度珠三角地區生態韌性水平,以此反映生態系統資源的生態安全壓力水平,研究發現該區域生態韌性水平呈下降趨勢。史丹等[12]采用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差額(即生態盈余)來反映地區生態韌性,并指出由于社會經濟活動對生態系統資源過度索取,致使中國生態環境面臨較大的生態壓力。程莉等[13]選取27種生態資源賬戶,采用當量因子法修正傳統生態足跡模型,測度長江經濟帶鄉村生態韌性水平。
上述研究對本研究具有重要啟示,但仍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間:①生態韌性測度方法有待改進。現有研究主要采用綜合指標體系法測度生態韌性水平,側重分析城市生態系統抵御風險與恢復建設的能力,較為缺乏從生態資源供需變化視角的測度方法。雖然部分學者嘗試采用傳統生態足跡模型解決這一問題,但囿于傳統生態足跡模型中均衡因子、產量因子與全球平均生產力等指標會隨時間和地區不同而發生較大波動,導致測算結果不穩定性增加。②評價對象有待擴展。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省、市、縣等區域[8-9]或珠三角[2]、長三角[6,10]、長江經濟帶[13]等地區,缺少對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及其時序發展態勢的研究。③研究范式有待豐富。以往研究側重于對生態韌性測度結果的簡單概括,對于生態韌性時空格局及分布動態演進特征的研究相對較少。鑒于此,本研究基于能值生態足跡模型,從流域區段、省域、城市群、市域等多級空間尺度對2007—2021年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進行測度,并結合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核密度估計與Markov鏈分析等方法研究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時空格局與分布動態演進特征。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 1 研究方法
2. 1. 1 基于能值生態足跡的生態韌性測度模型
(1)能值生態足跡。為克服傳統生態足跡模型的核算缺陷,本研究根據Odum[14]提出的能值生態足跡模型,通過統一的能值標準將生態環境系統中不同類型、不同質量、不同量綱與不可比較的各類資源轉換為具有可比性的太陽能值形式,以此客觀反映黃河流域生態系統資源供需的實際情況。參考楊燦等[15]的研究思路,將生物性資源與能源類資源賬戶分別按生產性生態足跡與消費性生態足跡進行核算。根據黃河流域各類資源的實際生產情況,選取6類42項能值生態足跡指標,其中,生物資源生產性項目包括農產品、林產品、畜產品與水產品4類33項指標,能源消費項目包括化石能源與電力2類9項指標。由于部分城市分品種能源消費量數據缺失,故采用各城市生產總值占所在省份生產總值的比重乘以所在省份分品種能源消費總量計算得到。參考現有研究[14-19],能值生態足跡賬戶各類產品的能量折算系數與能值轉換率見表1。能值生態足跡計算公式如下:
(2)能值生態承載力。能值生態承載力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可更新資源[15],本研究計算了太陽能、雨水勢能、雨水化學能、風能、徑流勢能、徑流化學能與地球旋轉能等7種可更新資源。由于太陽能、雨水勢能、雨水化學能、風能、徑流勢能與徑流化學能具有相同性質的能量,為避免重復計算,選取這6種可更新資源中最大的一類能值與地球旋轉能值之和作為可更新資源的太陽能值,并扣除12%的生態容量[14-19],計算公式如下:
2. 1. 2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旨在揭示空間事物的相似集聚和分異特征,包括全局自相關與局部自相關[20]。全局自相關用于描述事物在整個區域的空間關聯及分異程度,常用全局莫蘭指數衡量。若值為正,說明研究區域生態韌性水平呈空間正相關;若值為負,說明呈空間負相關。局部自相關旨在描述某一區域與鄰近單元之間的空間關聯特征,常用局部莫蘭指數判別。若值為正,說明相似屬性值的城市存在“高-高”或“低-低”聚集;若值為負,說明非相似屬性值的城市存在“高-低”或“低-高”聚集。
2. 1. 4Markov鏈分析Markov鏈分析
方法能夠將不同時期的黃河流域生態韌性進行數據離散化處理[15]。本研究采用四分位點將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由高到低劃分為低水平、較低水平、較高水平和高水平4類,并通過測算生態韌性4種類型的概率分布與轉移情況,將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演進過程近似為Markov過程。由于傳統Markov鏈分析未能考慮空間因素的作用,進一步采用空間Markov鏈分析方法研究鄰近地區生態韌性水平是否對本地區生態韌性水平產生影響,以此揭示不同時期的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動態演進情況[22]。本研究將生態韌性在相鄰類型中發生變動的現象定義為正向(或負向)轉移,如由中高水平轉移至高水平為正向轉移;同時,將生態韌性跨類型變動的現象定義為正向(或負向)跨越式轉移,如由低水平轉移至高水平為正向跨越式轉移。
2. 2 數據來源
考慮到黃河流域地區間內在關聯性與行政單元的完整性,研究區域包括黃河自然流經地區與深受黃河流域影響的社會經濟關聯區域[23]。以2007—2021 年為研究區間,最終選取黃河流域90個城市(指地級市、州和盟)作為數據樣本,并將其劃分為黃河流域上、中、下游3大區段與7個沿黃城市群,見表3和表4。各城市2007—2021年的自然地理資源數據、生物資源生產數據、能源資源消費數據與社會經濟數據主要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農業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漁業統計年鑒》《中國林業和草原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中國氣象年鑒》和各城市統計年鑒等,對于缺失數據采用插補法進行填補;降水量數據來自各省水資源公報與中國氣象數據網;能量折算系數、太陽能值轉換率及能值分析與計算方法主要參考Odum[14]、楊燦等[15]、王奕淇等[16]、黃黃等[17]、藍盛芳等[18]的研究,以及《農業技術手冊》[19]的研究成果。
3 結果與分析
3. 1 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時空演變特征分析
3. 1. 1 不同空間尺度下的時序特征分析
如圖1(a)所示,研究期內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整體呈波動下降趨勢,均值由2007年的0. 23下降至2021年的0. 16,年均降幅為2. 57%,說明黃河流域面臨的環境資源承載壓力不斷增大,抵御和應對外部不確定風險的能力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在2019年后趨于平緩并有好轉態勢,說明隨著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各地區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將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放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位置,通過實施各項生態環境保護戰略與政策,不斷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力度與環境治理強度,促使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得以改善,生態韌性水平逐步提高。
變異系數能夠反映樣本期內各地區生態韌性水平的分異程度。可以發現,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的變異系數始終大于1,整體呈先增加后減少的變化趨勢,說明樣本期內黃河流域地區間生態韌性水平存在明顯的非均衡性特征。鑒于此,本研究進一步從流域區段、省域、城市群和市域等空間尺度深入分析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差異化問題。
(1)基于流域區段差異的分析。由圖1(a)可知,黃河流域各區段生態韌性水平均值由高到低分別為上游地區gt;黃河整體gt;中游地區gt;下游地區,說明相較于上游地區而言,中、下游地區生態韌性水平較低。究其原因,上游地區生態環境本底較好,區域內生態系統資源能夠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且生態環境受外界因素威脅時的抵抗能力與恢復能力較強。而中、下游地區多處于工業化與城鎮化高速發展階段,人口集聚、城市規模與產業布局密度不斷擴大,加劇了區域生態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加之污染排放與資源過度消耗引發的生態赤字問題,致使中、下游地區生態系統自適應能力與抗風險能力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中、下游地區生態韌性自2019年有所增加,說明中、下游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大,地區生態保護與修復成效日益顯現。
(2)基于省域差異的分析。省域尺度生態韌性的時間演變趨勢見圖1(b)。可以發現,生態韌性水平整體呈“西部—中部—東部”省份逐漸遞減的分布特征。其中:四川和青海生態環境本底較好,對生態資源的索取程度相對較低,具有較高的生態韌性水平,其生態韌性水平遠高于其他省份;甘肅、陜西和內蒙古生態韌性水平處于中等水平,均值分別為0. 25、0. 22和0. 19,且大于黃河流域整體水平;而寧夏、山西、河南和山東生態韌性始終處于較低水平,均值分別為0. 08、0. 08、0. 07和0. 05,遠低于黃河流域整體水平。原因在于,寧夏自然條件惡劣、生態脆弱性較高,致使生態韌性水平較低,特別是“苦瘠甲天下”的寧夏南部地區荒漠面積大且水土流失問題嚴重,進一步加劇了區域整體生態系統承載壓力;山西作為全國能源重化工基地,依賴于煤炭等傳統能源,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一系列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問題,致使地區生態系統自適應能力與恢復能力較低;河南、山東作為人口大省與經濟發展較快區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大量的生態產品與能源產品需求,致使生態環境承載壓力逐年擴大,生態韌性水平較低。
(3)基于城市群差異的分析。城市群尺度生態韌性的時間演變趨勢見圖1(c)。由圖1(c)可知,黃河流域7個城市群生態韌性整體呈波動下降趨勢,城市群間差異較大。其中:蘭西城市群生態韌性水平顯著領先,均值為0. 37,遠超黃河流域整體水平;關中平原城市群次之,均值達到0. 15;而中原經濟區、寧夏沿黃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和山東半島城市群的均值均小于0. 10,山東半島城市群的生態韌性均值最低,僅為0. 05。說明這些城市群生態環境承載壓力不斷加大,生態系統自適應能力與恢復能力相對較弱,且山東半島城市群生態韌性薄弱的問題尤為突出。
(4)基于市域差異的分析。從市域尺度生態韌性的時間演變趨勢來看,各城市生態韌性水平存在明顯差異(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此處省略市域尺度生態韌性時間演變趨勢圖,可向作者索取)。根據黃河流域整體均值進行劃分,高生態韌性水平城市共25個,占比為27. 78%,低生態韌性水平城市共65個,占比為72. 22%。這意味著黃河流域市域尺度的生態韌性水平較低,流域內生態系統安全與環境承載壓力較大。
3. 1. 2 空間演變特征分析
采用自然斷裂分類法將生態韌性水平從低到高劃分為低度韌性(0≤ER≤0. 149)、較低韌性(0. 149lt;ER≤0. 349)、較高韌性(0. 349lt;ER≤0. 600)與高度韌性(0. 600lt;ER≤1),將能值生態盈虧從低到高劃分為高生態赤字(ED≤-0. 191億hm2)、中等生態赤字(-0. 191億hm2lt;ED≤-0. 137億hm2)、低生態赤字(-0. 137億hm2lt;ED≤0)、低生態盈余(0lt;ED≤0. 015億hm2)、中等生態盈余(0. 015億hm2lt;ED≤0. 067 億hm2)和高生態盈余(EDgt;0. 067 億hm2),空間分布結果見表5和表6。由表5可知,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4類生態韌性區域交錯分布,整體呈“西高東低”的分布格局。其中:高度韌性區域以塊狀形式集中分布在阿拉善、阿壩、玉樹、果洛、甘南等生態本底資源豐裕的上游地區;較高韌性區域主要分布在甘肅與陜西南部;較低韌性區域穿插分布在高度韌性與低度韌性區域之間;低度韌性區域以大面積連片形式分布在中下游地區,且多以經濟發達、資源消耗程度高或生態本底較差的城市為主。
從表6可以看出,生態韌性分布與生態盈虧分布具有一致性,高生態韌性區域由于自然本底較好且生態資源消耗較低,具有較高的生態盈余,而低韌性區域由于生態資源消耗遠超生態承載力閾值,故為生態虧損區域。值得注意的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生態赤字惡化趨勢有所緩和,生態赤字情況有所扭轉,這是由于各地區推動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與生產生活方式的綠色低碳發展,降低了生態足跡,使得生態赤字問題有所改善。
生態韌性類型轉移趨勢如圖2所示。可以發現,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等級結構始終以“金字塔”型為主,塔尖逐漸變窄,塔底逐漸變寬。其中:低度韌性城市數量持續增加且區域分布最廣,整體呈“由東向西、由北向南”逐步擴張態勢;較低韌性與較高韌性城市數量持續減少,區域范圍不斷縮減,且大多轉變為低度韌性區域;高度韌性城市數量較為穩定,且區域分布范圍基本保持不變。
《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規劃》明確指出,到2035年,黃河流域生態安全格局基本構建,生態環境全面改善。為研判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未來發展趨勢,參考茹少峰等[20]的研究思路,進一步采用CA?Markov模型對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未來發展趨勢進行模擬預測(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此處省略CA?Markov模型預測步驟和模擬預測結果,可向作者索取)。結果表明,2028年和2035年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分布格局整體保持相對穩定狀態,呈“西高東低”的分布態勢,低度韌性城市數量最多,區域范圍由中心向外圍小幅擴散,而高度韌性城市數量最少,區域范圍由外圍向中心略微收縮。具體來看:高度韌性區以塊狀形式分布在阿拉善、阿壩、玉樹、果洛、甘南等區域;較高韌性區分布在隴南、漢中與安康;較低韌性區分布較為廣泛,呈條狀聚集與零散分布相結合的分布特征;低度韌性區集中分布在黃河中下游地區,且以省會城市和經濟發達區域為主。
3. 2 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空間關聯分析
3. 2. 1 全局自相關分析
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全局自相關結果如圖3所示。
由圖3可以看出,樣本期內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全局莫蘭指數均為正值,波動區間為[0. 528,0. 687]。經檢驗,各年份全局莫蘭指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Z 值均為正且高于1. 96。這表明黃河流域各地區生態韌性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即地區生態韌性高值趨向與高值聚集,低值趨向與低值聚集。因此,提升黃河流域生態韌性需要積極打破地理空間的局限,持續推動各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協同發展,實現黃河流域生態環境共建共治共享。
3. 2. 2局部自相關分析
采用2007—2021年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測度結果計算局部莫蘭指數,并通過局部莫蘭散點圖分析生態韌性的空間集聚特征(圖4)。可以發現,樣本點主要集中分布在第一、三象限,呈現出明顯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狀態,表明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較高(低)的城市被較高(低)的城市包圍,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馬太效應愈發明顯。此外,位于第一象限的點主要是西部生態本底較好的城市,而位于第三象限的點主要為中東部城市,進一步證實黃河流域“西部高、中東部低”的生態韌性分布格局。
3. 3 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分布動態演進
3. 3. 1 生態韌性分布的時間動態演進分析
黃河流域整體生態韌性的核密度估計結果與密度等高線分別如圖5(a)和圖5(b)所示。具體來看:①在分布位置上,黃河流域整體生態韌性水平的核密度曲線呈小幅左移態勢,說明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②在分布形態上,樣本期內核密度曲線波峰高度出現“高-低”交替波動態勢,且在樣本期末表現為主峰高度下降、曲線寬度擴大的發展趨勢,說明黃河流域地區間生態韌性水平的絕對差異和分異趨勢均有所擴大。③在分布延展性上,曲線存在右拖尾延展拓寬,說明區域內存在部分城市生態韌性水平顯著高于其他城市的現象,且與區域整體生態韌性平均水平的差距有所擴大。④在極化現象上,曲線均由一個主峰和多個側峰構成,說明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存在多極分化現象,空間非均衡問題亟待解決。綜上可知,黃河流域整體生態韌性水平有所降低,多極化現象明顯,且區域差異明顯擴大,說明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尚未形成高效穩定發展態勢,仍然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由圖5(c)可知,樣本期內黃河上游地區生態韌性核密度曲線主峰經歷了“左移—右移”持續交替的變化趨勢,整體表現為左移且幅度較小,波峰高度波動式上升,波峰寬度收窄,右拖尾收斂,具有明顯的雙峰特征,說明上游地區生態韌性水平有所下降,兩極化趨勢較為明顯,且城市間絕對差異有所減少。由圖5(d)可知,黃河中游地區生態韌性的核密度曲線主峰整體向右略微移動,峰值上升且曲線寬度變窄,右拖尾收斂,波峰數量保持不變,由1個主峰與1個側峰構成,說明黃河中游地區生態韌性水平略微上升,兩極分化特征較為明顯,且絕對差異不斷增加。結合圖5(e)可知,樣本期內黃河下游地區生態韌性的核密度曲線主峰經歷了“右移—左移”的動態變化,并于期末表現為右移態勢,波峰高度經歷了“低—高—低”的變化過程,波峰寬度表現為“寬—窄—寬”的動態分布,右拖尾現象明顯且隨時間推移有所擴大,波峰數量從多峰向雙峰轉變,說明黃河下游地區生態韌性水平有所增長,多極化現象有所緩解,由多極化向兩極化轉變,地區間差異有所擴大。由此可見,黃河流域不同區段的生態韌性分布動態及演進趨勢存在明顯區別,上游地區絕對差異縮小,而中、下游地區絕對差異擴大。因此,未來應重視黃河流域不同區段生態韌性的非均衡發展特征,有針對性地推進黃河各區段生態韌性能力建設,以此來縮小地區間差距。
3. 3. 2生態韌性狀態轉移的時間特征分析
本研究按照四分位點將90個城市生態韌性水平劃分為低水平、較低水平、較高水平和高水平4類,將時間跨度分別設定為1年、2年和3年,得到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傳統Markov轉移概率結果(表7)。可以發現:①在不同時間跨度下的轉移概率矩陣中,主對角線上的數值均高于非對角線上的數值,且主對角線兩端值較中間值略高。這表明在不考慮空間因素的前提下,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具有穩定性,存在“俱樂部趨同”現象。②隨著時間跨度增加,主對角線上的概率逐步降低,說明黃河流域各城市生態韌性保持原有水平的概率呈下降趨勢,流動性漸趨增強。③不同時間跨度下均不存在生態韌性跨越式發展。以時間跨度1年為例,由低水平地區向上跨越式轉移至中高水平與高水平地區的概率均為0,且隨著時間跨度增加,概率保持為0。由此表明提升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短期內無法實現跨越式發展。
3. 3. 3 生態韌性分布的空間動態演進分析
基于鄰接空間權重矩陣,采用空間Markov鏈分析方法研究不同城市生態韌性動態演進中空間因素的作用。卡方檢驗能夠對空間因素的影響進行驗證。經檢驗,時間跨度為1年、2年和3年的Q 值分別為148. 88、151. 09和176. 80,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空間因素對黃河流域各地區生態韌性的轉移具有顯著影響,即某一地區生態韌性的動態轉移會受到鄰近地區的影響。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空間Markov轉移概率結果見表8。可以發現:①不同時間跨度下,主對角線的概率均大于非對角線的概率,且隨著時間跨度增加,主對角線的概率均略微下降,說明考慮空間因素時,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具有穩定性大的特點。②不同時間跨度下,主對角線上低水平與高水平地區的概率普遍高于較低水平與較高水平地區,說明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分布存在“低水平陷阱”與“高水平壟斷”并存現象,空間俱樂部趨同現象并未得到控制與緩解。③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空間溢出效應明顯,且鄰域生態韌性水平對周邊城市向上轉移與向下轉移的概率是非對稱的。一方面,與生態韌性低水平城市相鄰時,無論本地具有何種生態韌性水平,其發生向下轉移的概率遠高于傳統Markov概率矩陣中對應的數值,且概率隨時間跨度增加而提高。例如,與低水平城市相鄰,當時間跨度分別為1年、2年和3年時,較低水平城市向下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 258、0. 357和0. 423,大于傳統Markov鏈情況下的0. 139、0. 196和0. 247。可見,低水平城市對周邊城市生態韌性的發展產生一定消極作用,且低水平城市難以跳出“低水平固化陷阱”,進而形成低水平區域趨同的態勢。另一方面,與生態韌性高水平城市相鄰時,當本地為較低水平與較高水平時,其向上轉移的概率明顯高于傳統Markov概率矩陣中對應的數值。例如,與高水平城市相鄰,當時間跨度分別為1年、2年和3年時,較低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 185、0. 160和0. 155,較高水平城市向上轉移的概率分別為0. 112、0. 121和0. 128,均大于傳統Markov鏈情況下的概率。這說明在高水平鄰域的影響下,生態韌性較低水平與較高水平城市會受到輻射帶動作用,進而提高向上轉移的概率,形成高水平區域趨同現象。④城市初始生態韌性水平對未來生態韌性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即使與高生態韌性城市相鄰,低水平或較低水平城市向高水平城市跨越式轉移的概率也為0,且隨時間跨度延長至2、3年時,概率仍為0。這說明在考慮空間因素的情況下,各城市生態韌性仍然無法實現跨越式發展。因此,應持續推進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實現區域生態韌性的良性發展。
4 結論與討論
4. 1 結論與啟示
基于能值生態足跡模型,本研究測度多級空間尺度的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刻畫并分析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時空格局及分布動態演進特征,主要結論如下。
(1)時間序列上,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整體呈波動下降趨勢,不同空間尺度下生態韌性的時序變化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各區段生態韌性水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為上游地區gt;黃河整體gt;中游地區gt;下游地區;省域生態韌性水平呈“西部—中部—東部”省份逐漸遞減的分異特征;城市群生態韌性水平整體呈波動下降趨勢,蘭西城市群生態韌性水平顯著領先,山東半島城市群的生態韌性水平最低;市域生態韌性水平存在明顯區別,以低生態韌性水平城市為主。
(2)空間格局上,黃河流域生態韌性水平整體呈“西高東低”的分布格局,西部地區生態韌性高于中東部地區,生態韌性分布與生態盈虧分布具有一致性,生態韌性等級結構始終以“金字塔”型為主。CA?Markov模型預測結果表明,2028年和2035年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空間分布整體保持相對穩定狀態,呈“西高東低”的分布態勢。
(3)空間關聯分析表明,黃河流域各地區生態韌性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相鄰區域相互影響,呈現“高-高”和“低-低”集聚狀態,“馬太效應”愈發明顯。
(4)核密度估計表明,黃河流域整體生態韌性水平降低,多極化現象明顯,不同區段的時間動態演進特征存在明顯區別,上游地區絕對差異縮小,而中、下游地區絕對差異擴大。
(5)Markov鏈分析表明,黃河流域生態韌性具有穩定性,存在“低水平陷阱”與“高水平壟斷”并存的俱樂部趨同特征,且隨著時間跨度增加,流動性漸趨增強,但均不存在生態韌性跨越式發展。考慮空間因素影響時,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空間溢出效應明顯,且鄰域生態韌性水平對周邊城市向上與向下轉移的概率是非對稱的,若與生態韌性高水平城市相鄰,則會提高向上轉移的概率,反之亦然。
上述結論蘊含的政策啟示包括:第一,堅持“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戰略思路,在經濟社會保質保量發展基礎上,系統推進黃河流域生態環境保護與綠色低碳發展,完善生態環境保護與生態環境監管機制。第二,結合不同區域特點,實施差別化生態恢復政策與生態系統協同保護修復工作。上游地區應持續優化生態資源承載能力以鞏固生態系統安全,中游地區應加強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力度以降低生態系統承載壓力,下游地區應重點開展生態環境綜合整治以強化國土空間保護利用。第三,高度重視區域生態韌性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積極開展區域間生態韌性協同聯動機制與跨區域開放合作機制,強化生態保護機制、政策與項目協同聯動,充分釋放生態韌性高值城市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緩解生態韌性空間俱樂部趨同現象,實現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空間共建共治共享。
4. 2 討論
流域作為相對完整的生態空間,是探索綠色發展路徑的有效單元,深入探究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時空格局及其分布動態演進特征,對于推進國土空間綜合整治與流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受限于流域系統本身的復雜性,本研究在流域生態韌性量化與綜合評價方面的探索仍存在一定不足尚待提升:①本研究從生態資源供需變化視角出發,將能值生態足跡模型有機嵌入研究框架,為改進生態韌性量化方法貢獻新思路,但量化方法的兼容性與研究結論的現實性仍需深入研究。未來應采用跨學科知識進一步厘清流域生態韌性的內涵,并結合各地區自然條件、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完善生態韌性核算框架。②生態韌性具有動態性與復雜性,本研究力圖揭示其時空格局及分布動態演進特征,但缺乏對其內在驅動因素的分析,未來應進一步深入分析并挖掘黃河流域生態韌性的內在驅動因素。③囿于數據限制,特別是部分城市數據的不完整,使得生態韌性定量分析過程仍存在不可避免的誤差。未來應結合生態環境大數據、環境監測數據和實地調研等多源數據,并采用人工智能與遙感技術融合方式,提高生態韌性量化研究的時效性與解釋力。
(責任編輯:田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