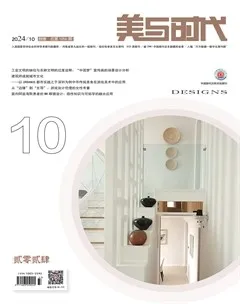數字時代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塑造與審美價值探賾
摘" 要:文化形象塑造是中國進入新時代所面臨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需要。隨著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微動漫已成為中國民族文化形象傳播的有效載體。彝族古訓文化形象也在中國式文化創新語境中嬗變為以微動漫形象為代表的數字化民族符碼形象。本研究以云南省楚雄州發布的《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為案例,梳理了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孕育背景和誕生過程。深入分析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民族、地域、古訓形象的構建方式和文化表征,在綜合前述的基礎上探討了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的審美價值。
關鍵詞:數字技術;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微動漫形象;審美價值
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要“塑造更多為世界所認知的中華文化形象,努力展示一個生動立體的中國”[1]。在數字時代的潮流下,微動漫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表達方式,正逐漸成為民族文化傳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彝族古訓文化形象作為中國民族文化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承載著豐富的歷史淵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在數字技術發展契機與中國式文化創新語境的雙重加持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孕育而生。《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系列作品實現了彝族古訓形象的數字化轉型,這正是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重要體現,同時也為中國民族文化形象的創作與傳播提供了新思路。
一、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孕育與誕生
在比較文學研究中,“形象”是指“對一個文化現實的描述。通過這種描述,塑造這個形象的個人或群體,顯示或表達出他們樂于置身其中的那個社會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或虛構的空間。”按照法國比較文學家巴柔之言,“形象”乃是“社會集體想象物的一種特殊表現形態:對他者的描述”[2]。換言之,形象作為想象主體的表意實踐,深植于特定歷史語境與意識形態之中。文化形象的塑造涉及文化元素在形成、表述與傳播中的復雜互動,這一過程不僅反映了文化內部的自我對話,也體現了文化與社會集體的廣泛交流。最終,文化形象凝聚為“社會集體想象物”,高度概括了地區的精神風貌、文化品位、民族性格及價值觀念,成為社會文化認同與尊重的重要載體。彝族古訓文化形象深植于彝族歷史文化之中,是對彝族民族智慧、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具體表達與傳承。進入新時代,中國式文化創新語境與數字技術發展為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提供了契機,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就此應運而生。
(一)新語境:彝族古訓文化形象的現代性轉化
口耳相傳是彝族古訓文化的重要傳播方式。在過去,彝族人民主要通過長輩對晚輩的教導、族群聚會的講述等方式來傳承古訓文化。這種傳播方式雖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使得彝族古訓文化更具生動性和真實性。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彝族人民能夠深刻領會古訓的精髓,并將其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此外,彝族民間文學文本也是彝族古訓文化傳承與傳播的重要方式之一。彝族古訓一方面來自以《梅葛》《查姆》《阿細的先基》《勒俄特依》四大創世史詩為代表的彝族民間文學經典,另一方面則來自彝族相關文化研究學者所編纂的學術專著,如1981年由四川民委彝文工作組編纂整理的《彝族格言》等,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彝族傳統古訓遺產,為彝族古訓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較為完備的歷史資料。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在“口傳”與民間文學文本中逐漸形成。隨著中國進入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我們提倡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3]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塑造迎來了新的歷史語境,中國式文化創新為彝族古訓文化提供了媒介形象塑造的新機遇。為深入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黨的十九大精神,楚雄州紀委監委等機構積極行動,精心策劃并推出了“中國彝族彝鄉文化微動漫作品”,旨在進一步推進“中國彝鄉·滇中翡翠·紅火楚雄”的建設與發展。彝族古訓文化得以借助現代媒介技術,以全新的形象呈現在公眾面前。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在現代性轉化的過程中,對其中的文化元素進行了深入的提煉與重塑,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審美需求和文化語境。這包括對彝族古訓文化中的故事、人物形象、符號等進行再創作,使彝族古訓文化形象在現代社會中煥發新的生命力。同時,彝族古訓文化形象的現代性轉化并非一蹴而就的過程。這既是一個創新的過程,也是一個傳承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彝族古訓文化形象保持了其獨特性和民族性,又呈現出新時代內涵與現代性表達。
(二)新契機: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生成
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彝族古訓文化形象的媒介化演繹帶來了新契機,彝族古訓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在數字化進程中找到了新的表達方式——微動漫形象。這一創新形式不僅為彝族古訓文化賦予了新的生命力,更為其與現代文化的融合開辟了新的道路。彝族古訓文化,蘊含著深厚的民族智慧和獨特的審美觀念。然而,其傳統的文本與口傳形象,在傳播和傳承方式上往往受限于地域和媒介的局限。而如今,數字技術的崛起打破了這一局限,使得彝族古訓文化能夠以更加生動、直觀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2018年至2020年,楚雄州在“挖掘彝族古訓,傳承民族文化,弘揚時代精神,倡導化風成俗”的指引下,聯合中共楚雄州紀委監委、組織部、宣傳部等多方力量,攜手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彝族與周邊民族研究專業委員會、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及《人民日報》媒體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了《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系列作品,共計三季。這些作品汲取了《梅葛》《查姆》《彝族畢摩經典譯注》《彝族諺語》等彝族經典著作的精髓,通過生動的彝族人物形象和真實的彝族生產生活場景,深入闡釋了彝族古訓的內涵。每季作品均包括季、篇目、訓語、故事、釋義五個部分,遵循彝族十月太陽歷的年節規制和數理概念,歷時三年完成,每年推出一季,每季共十二篇,總計三十六篇。作品在“清風楚雄”微信公眾號、Bilibili、抖音、微博以及各級融媒體平臺播出,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就此誕生。該作品將彝族古訓文化的精髓與現代動漫藝術相結合,通過獨特的視覺效果和敘事方式,將彝族文化的魅力展現得淋漓盡致。彝族古訓文化形象不僅繼承了彝族古訓文化的精髓,更在現代審美觀念的引領下,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和嘗試。它們以更加生動、活潑的方式展現了彝族文化的獨特魅力,使得更多受眾能夠了解和接受傳統古訓文化。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誕生,也體現了彝族文化與當代社會的對話與融合。這種形象的塑造不僅涉及彝族自我認知與表達,還呈現了與他者的多元互動關系,它們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將彝族文化融入當代社會的各個領域,為彝族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內涵。
二、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建構
微動漫是微動畫與微漫畫的合稱,具有“微制作”“微時長”“微平臺”“微操作”等特點,是一種在融媒體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全新的動漫形態。微動漫與民族文化形象建構具有深刻聯系。微動漫所采用的數字技術、傳播手段,以及微動漫中的文化內涵和價值觀念綜合體現出中國民族文化的發展水平、文化底蘊和整體形象。在“微”成為時代發展潮流的今天,微動漫在民族文化形象建構中的重要性迅速升維。《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第三季作品正是通過36篇故事,從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建構出了一個更鮮活、更立體、更豐富多元的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這種媒介形象便是創作者與受眾在多元互動中對于彝族古訓文化的“社會集體想象”。然而這種想象并非絕對的主觀臆想,而是以彝族古訓文化符號為物質載體,對彝族人物、事物、景物等的具象化描述,其中包含著社會集體的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審美心理等。具體而言,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可看作是社會集體在客觀基礎上對其民族、地域、古訓文化等的總體認知與評價。這種認知與評價以微動漫為媒介,通過圖像這一中介呈現出來。民族形象、地域形象以及古訓形象構成了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的整體形象,其背后的文化表征也在形象建構的過程中彌散開來。
(一)民族形象:彝族“本真”與現實“仿真”
媒介在民族形象的形成過程中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微動漫作為一種新興的媒介形式,能夠以更加生動的方式展現民族形象的魅力。《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系列作品中的彝族形象,是以彝族微動漫人物形象為主導,彝族景觀、局部場景或某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象征符號為補充的媒介形象組合,是彝族生產生活歷史印記的具象化呈現,同時也是當代彝族精神風貌的具體體現。例如,在第一季的創業篇中,作者選取了《彝族格言》中“人勤莊稼好,人懶地生草”這一訓語,講述了一段創業故事:“很久以前,一戶彝族人家有三兄弟,母親早故,父親含辛茹苦養大哥仨個,父親憐惜溺愛過甚,養成了哥仨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的習性。重病不治即將離世的老父憂心自己死后兒子生活無著,便跟兒子們說在自家地里埋了一罐金子,想以此激勵兒子勞動創業。之后,父親去世,兒子們為挖出金子慢慢習慣了勞作,獲得了豐收,終于明白了父親的用意,從此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本篇再現了彝族人民勤勞耕作的生活生產場景,展現出彝族延續至今艱苦創業的優良美德。其民族形象建構主要從人物行為邏輯以及其他文化符號中體現,呈現出帶有歷史與生活印記的彝族“本真”和現實“仿真”。彝族微動漫人物的行動邏輯是以訓語“人勤莊稼好,人懶地生草”為出發點展開的,在全知敘事視角下,彝族父輩們的智慧和對家庭的期許表露無遺。在提到“兒子們從此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時,女性形象則作為家庭幸福美滿的標志物展現出來,不僅體現了彝族社會對女性的尊重和關愛,也呈現出彝族人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這種對女性形象的刻畫,是對彝族精神風貌的一種“仿真”,是社會集體對彝族形象的主觀再現。
(二)地域形象:異域符像的陌生化景觀
馬克斯·舍勒于1924年在其著作《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中首次引入了“知識社會學”的概念,這一里程碑式的創新不僅標志著知識社會學的誕生,更為后續地域形象建構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思想源泉。伯格等美國社會學家認為,“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對象是現實的社會建構”,“日常生活現實包含一些‘類型化圖式’,我們在互動中通過這些圖式理解他人、對待他人”[4]。地域作為現實的存在,是一種“實在”元素或者“實在世界”[5],是由“各個參與者之間通過話語或其他行為的互動建構起來的,這是一個主體間分享的意義世界”[6]。因此,地域形象是一種虛擬的客觀實在,媒介促使其“類型化圖式”生成,所展現的地域環境不是直觀“鏡像”,而是社會集體選擇、加工和生產化的結果,受眾對地域的感知通常是由媒介所營造出的“擬態環境”而形成的。《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系列作品中的地域形象,即一種以彝族異域符碼圖像為主要元素拼貼形成的陌生化景觀,極具后現代民族主義特色。《元陽縣志》載:“彝族多居住在山川壯麗、資源豐富的山區,村寨依山傍水,四周梯田層層,村后有山可供放牧,村前有田可供耕種,多數村寨都有一條水溝從中流過。”[7]在其微動漫中,山、水、索瑪花等自然環境元素貫穿始終,為彝族地域生態提供客觀依據,瓦房、土掌房、閃片房、茅草房等彝族民居,加之彝族圖騰、服飾等自由拼貼共同構成了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地域形象的“類型化圖式”,這種圖式因其獨特的異域符像,在大眾傳播過程中,會使受眾產生一種神秘、未知的陌生化體驗,受眾憑借這一認知圖式感知社會集體打造出的彝族地域“擬態環境”。
(三)古訓形象:從“詩性”到“知性”的嬗變
“古訓”一詞,最早可溯源于《詩·大雅·烝民》中的“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其中“式”即規范、標準之意。大意為古代流傳下來的、可以作為準則的話就是標準。從古至今,彝族古訓經歷了由“口承”到“文學書寫”再到“視聽傳播”形態的三次變革,彝族古訓在不同時期呈現出不同的媒介形象。在“口承”與“文學書寫”階段,彝族古訓通常以“詩的形式”傳承,呈現出“詩史合一”如《梅葛》《查姆》《阿細的先基》《勒俄特依》等,以及“以詩論詩”的具體形態,如畢摩典籍和古典詩文論《彝族詩文論》《彝語詩律論》等。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8]彝族古訓遺產有著亞里士多德所揭示的詩學本質,“詩性”是“口承”與“文學書寫”階段彝族古訓形象的精神內涵,其媒介形象呈現出朦朧性與多義性等特質,凝結著彝族創世神話、民族語言、思維等的原始狀態,展現出彝族先輩們的才智與性情。進入新時代,文化創新與數字技術的發展為彝族古訓視聽傳播提供了契機,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就此誕生。《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系列作品三季共36篇,每一篇都是對古訓釋義的故事化演繹,微觀化與個體化敘事是其典型特征,如第三季循規篇,訓語為“牛羊不循道,虎豹會跟隨。人類不守規,禍事會降臨。”出自《彝族格言》。講述了哀牢山彝家兩兄弟,阿憨與阿聰為迎娶阿果,與黑豹搏斗的故事,最終居心叵測的阿聰自食惡果,勤勞善良的阿憨過上了幸福美滿的生活。這種微觀化與個體化敘事是對古訓“詩性”的一種解構,呈現出更多的是一種“知性”,知性強調的是探索和客觀,從客觀事實與實踐出發,探索真理。具體而言,在微動漫中古訓形象為一個神秘卷軸,開卷以彝漢雙語字幕的形式呈現,其媒介形象顯現出一種直觀性,一種以審美教育為目的的“知性”。
三、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的審美價值
中國彝族古訓文化作為彝族人民智慧的結晶,承載著豐富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在當今時代,中國彝族古訓文化正面臨著新的傳承與表達方式。其中,微動漫作為一種新興的媒介形式,以其獨特的視覺魅力和互動體驗,為中國彝族古訓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系列作品在審美價值層面呈現出彝族文化與“二次元”符號審美交融的特征,滿足了新時代彝族古訓功能外延的現實需求。
(一)彝族文化與“二次元”符號的審美交融
“二次元”一詞,最早源于日本,原意為“二維空間”,后來多指日本漫畫、動畫、電子游戲這三種文化形式所創造的虛擬空間[9]。隨著二次元文化的本土化以及中國青年亞文化環境因素的融入,借助二次元文化符號傳承與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中國式文化創新的重要實踐路徑之一。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審美價值首先體現在彝族文化與“二次元”符號的審美交融上。在微動漫這一新興的媒介形式中,彝族古訓文化被賦予了全新的生命力和表現力,展現出一種既古老又時尚、既傳統又現代的美學魅力。創作者們巧妙地運用他們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將彝族的傳統元素與現代動漫設計相結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二次元”風格。彝族的傳統服飾,以其獨特的色彩和圖案,成為動漫角色服飾設計的重要靈感來源。同時,彝族的圖騰和建筑元素也被巧妙地融入動漫的場景設計中,使得整個作品充滿了濃厚的彝族風情。在彝族動漫角色的塑造上,創作者們通過夸張、幽默的手法,展現了彝族人民豐富的情感世界和獨特的文化特色。角色的臉譜化表情,如憤怒的火苗、夸張的笑容等,不僅增強了角色的個性化和辨識度,也使得觀眾更容易產生共鳴和情感聯系。這種彝族文化與“二次元”符號的審美交融,不僅讓彝族古訓文化在視覺上更加新穎、獨特,也更容易吸引年輕群體的關注。通過動漫這種生動有趣的形式,彝族古訓中的智慧和哲理得以輕松傳遞給觀眾,使得觀眾在娛樂的同時也能夠獲得啟示和教益。這種審美交融體現了彝族文化與現代審美趨勢的有機結合,展示了中國彝族文化在新時代背景下的創新與發展。同時,也為現代微動漫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靈感,推動了微動漫產業的多元化和個性化發展。因此,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審美價值不僅在于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表現形式,更在于其傳承和弘揚彝族文化、推動動漫產業創新發展的重要作用。
(二)新時代彝族古訓功能外延的現實需求
在中國式文化創新語境中,彝族古訓功能外延的探討不僅是對傳統智慧的深入挖掘,更是對當代社會現實需求的積極回應。彝族古訓,作為彝族文化的精髓,其深邃的哲理和獨特的文化魅力在新時代背景下呈現出更為豐富的功能和價值。從歷時性的角度審視,彝族古訓經歷了“口承”與“文學書寫”階段,其功能主要表現為道德約束與行為教化,以及啟發民智、以史為鑒。然而,在“視聽傳播”的新階段,彝族古訓的功能得以進一步外延,尤其是其審美教育功能得到了顯著地增強。具體而言,彝族古訓中強調的公正、廉潔、勤奮等價值觀,與當代社會廉政文化建設的理念相契合。在新時代背景下,將彝族古訓與廉政文化建設相結合,通過微動漫這一創新的視聽表達形式,將彝族古訓中的廉政理念傳遞給廣大干部群眾,不僅有助于推動廉政文化的普及和深入發展,還能增強干部群眾的廉潔自律意識,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此外,彝族古訓功能外延的現實需求還體現在文化傳承與弘揚、社會道德建設、民族團結與進步以及教育意義與實際應用等方面。在新時代背景下,彝族古訓的傳承與弘揚不僅是對傳統文化的尊重與繼承,更是對當代社會精神文明的豐富與提升。通過加強對彝族古訓的研究與傳播,可以推動彝族文化的創新發展,促進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彝族古訓所蘊含的道德智慧和倫理原則,對于當代社會的道德構建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啟示,其深遠的價值不容忽視。通過學習和踐行彝族古訓中的道德理念,可以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推動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總之,新時代彝族古訓功能外延的現實需求是多方面的,需要我們從多個角度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通過挖掘和傳承彝族古訓的豐富內涵,可以推動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為當代社會的精神文明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
四、結語
本文以《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為案例,深入探討了數字時代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塑造及其審美價值。通過微動漫這一數字化藝術形式,彝族古訓文化得以生動、直觀地展現,實現了民族文化形象的數字化轉型。這一創新不僅豐富了彝族古訓文化的傳播渠道,也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分析、梳理了中國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中民族、地域和古訓形象建構及其背后的文化表征,凸顯了彝族古訓文化的獨特性和地域性。同時,微動漫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其獨特的形象塑造方式為彝族古訓文化提供了全新的審美體驗,展現了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展望未來,應繼續深化對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的相關研究,同時積極探尋數字技術在民族文化傳承與創新中的新應用,力求在數字化時代背景下為民族文化的繁榮與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實現文化多樣性的維護與提升。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 展示中國文藝新氣象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N].人民日報,2021-12-15(001).
[2]達尼埃爾-巴柔.形象[M].孟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156.
[3]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貫通[EB/OL].[2023-1-13].http://theory.people.com.cn/GB/n1/2023/0113/c40531-32605692.html.
[4]王秀艷.地域形象媒介建構與東北刻板印象的歷時傳播[J].社會科學戰線,2021(2):267-273.
[5]許茨.社會實在問題[M].霍桂恒,索昕,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308.
[6]江根源:虛擬社區中的現實建構——概念、范式與相關路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42.
[7]云南省元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元陽縣志[M].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0:636.
[8]亞里士多德.詩學[M].羅念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9.
[9]林品.青年亞文化與官方意識形態的“雙向破壁”——“二次元民族主義”的興起[J].探索與爭鳴,2016(2):69-72.
作者簡介:王佳樂,成都大學廣播電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視藝術傳播。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現代設計與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度項目“數字時代彝族古訓文化微動漫形象設計與接受度研究”(MD23C001)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