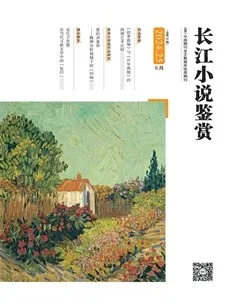《莫羅博士島》之哥特主題探析
[摘要]《莫羅博士島》是英國科幻小說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在1896年創作的一部科幻小說,其作品沿襲18至19世紀英國科幻小說中的哥特傳統,并在此基礎上深入探討與反思科學倫理問題。小說中充滿哥特式恐怖怪異的氛圍,通過神秘瘋狂的哥特式人物、對比強烈的哥特式景觀以及恐怖刺激的哥特式情節構建作品獨特的精神場域。在這里,人類由對經典哥特環境的恐懼轉向對未知科學力量的恐懼。同時,受當時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的影響,作品延續瑪麗·雪萊作品中提出的“弗蘭肯斯坦”問題,體現出作者對現代科技理性下人類道德倫理的反思。在當今科技飛速發展的背景下,《莫羅博士島》中對科學倫理問題與人類主體地位危機的探討愈加具有研究價值和警示意義。
[關鍵詞]《莫羅博士島》" "哥特元素" "科學倫理" "科幻小說
[中圖分類號] I06" " " [文獻標識碼] A"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4)25-0035-05
一、引言
19世紀末,科技迅猛發展,給西方社會帶來了巨大能量。“弗蘭肯斯坦的故事——在實驗室里用人體器官塑造出一個怪物——不再屬于遙遠的幻想領域……”[1]當一些人在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充滿期盼時,另一些人卻在這種不斷變化中預見了夢魘,并通過最能表現這種恐懼的方式去構建自己所預見的某個未來。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在其作品《莫羅博士島》(The Island of Dr.Moreau,1896)中以哥特幻想的方式深入探討了這些問題,提煉出維多利亞時代民眾面對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時充滿恐懼與希望的矛盾心理。
哥特小說(The gothic)產生于18世紀的英國,是一種恐怖和鬼怪小說,多以中世紀古堡、墓地等遠離光明之地為故事背景,情節刺激緊張,涉及追逃、兇殺、鬼怪等哥特小說中常見的元素,營造了一種神秘恐怖、怪誕緊張的氛圍,給人以痛感和快感并存的審美體驗[2]。到了19世紀,英國哥特小說在科學技術發展等影響下,融入對未知科學力量的恐懼與思考,影響了一大批作家的創作。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便是將科學幻想與哥特恐怖有機熔為一爐的典型代表[3]。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Mr.Jekyll and Mr.Hyde)中對雙重身份的描寫繼承自一個很容易辨認的哥特傳統[4]。阿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在《高天的恐怖》中描寫了飛行員各種神秘恐怖的失蹤與死亡方式。同樣,威爾斯繼承并運用哥特敘事,在作品中構建了一個宏大的科幻宇宙。可以說,“哥特式小說作家采用的方法已經成為今天許多科幻小說作家和恐怖小說作家的方法”[5]。
目前國內對《莫羅博士島》的研究較少,在中國知網上以書名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自2000年至今,每年平均發表一篇相關研究文獻,研究多涉及人物形象、科幻文學、生態及種族等方面,而幾乎沒有對其作品中哥特元素的分析。本文將從英國哥特文學傳統和科幻小說的聯系出發,對《莫羅博士島》中的哥特元素進行解讀,發掘作品的獨特魅力。
二、《莫羅博士島》中的哥特元素
威爾斯繼承并發揚英國哥特傳統,其作品中對惡棍式人物的描寫及恐怖緊張氛圍的營造無不充滿哥特氣息。如《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中展現了人類退化后的陰森景象。《隱身人》(The Invisible Man)中描繪了格列芬的邪惡瘋狂。其中哥特色彩最濃厚的是《莫羅博士島》,作品對哥特式人物形象的刻畫、恐怖對立場景的描寫以及緊張刺激情節的安排,具有典型的哥特元素。
1.瘋狂怪異的哥特人物
暴君形象與鬼怪形象是英國經典哥特小說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之一[3]。到了19世紀,出現了瘋狂科學家和怪物異類這樣的原型人物。在《莫羅博士島》中,脫離道德倫理制約的瘋狂科學家形象與拼湊改造的怪物形象賦予作品鮮明的哥特氛圍。
1.1瘋狂科學家
暴君形象是英國哥特小說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但到了19世紀中后期,這類暴君形象逐漸與新出現的瘋狂科學家形象相融合,其最突出的特點是被科學所異化,陰森偏執、毫無人性。在《莫羅博士島》中,莫羅是最為典型的瘋狂科學家形象,其瘋狂殘酷體現在實驗的殘忍性與對獸人的嚴酷統治上。
莫羅本是一個頗有名氣的生物學家和外科醫生,但因殘忍的動物實驗而被倫敦學術界驅逐,來到荒島繼續實驗。在沒有道德倫理制約的荒島上,他對各種動物進行活體器官移植,將它們拼湊改造成人形,裝上喉頭,試圖使之成為新人。莫羅的這種實驗無疑非常殘忍,曾從他倫敦家里逃出來的狗“身上的皮給剝光了,而且肢體被截得殘缺不全”[6]。被實驗折磨的美洲獅的慘叫更是令普倫迪克和蒙哥馬利都難以忍受。
然而,莫羅的實驗并未止步于肉體拼湊和重塑,而是以造物主的身份在島上建立極權統治秩序。“在這里,古老的哥特主題——渴望統治出現了。”[4]他為這些獸人制定嚴苛的法律,并要求他們不斷重復這些律條。為了確保法的實施,莫羅以鞭笞、烙燙,甚至以在“痛苦屋”中進行活體解剖為手段,通過極度的痛苦威脅和控制獸人。
莫羅身上匯集了哥特暴君與瘋狂科學家的特質。他對重塑生物實驗的狂熱,對生命的漠視以及對獸人的殘暴,都將他與英國哥特傳統中的暴君形象聯結起來。他用自己的科學知識來滿足個人欲望,最終走向悲劇。
1.2獸人
在傳統哥特小說中,鬼怪并不作為主要角色登場,而是為小說中的人物活動營造怪異恐怖的環境。到了19世紀,哥特小說中的鬼怪形象逐漸被人造怪物所取代。《弗蘭肯斯坦》中的怪物是一個由人創造出來的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欲望要求的魔鬼形象[3]。這些人造怪物與瘋狂科學家相輔相成,共同建構了一個恐怖怪異的哥特異域。
在《莫羅博士島》中,獸人是莫羅進行科學實驗的產物。身體上,他們外形怪異,四肢不成比例,頭部前傾,脊背彎曲得很別扭,五官形狀奇怪,特別是眼睛,顏色不似常人[6]。所有獸人既保留了原有物種的基本特質,又與人類相似,他們都是莫羅從不同動物身上提取不同身體部位并重新拼湊組合而成,而非大自然的造物。精神上,獸人在莫羅的教化下短暫具有了人性,學會人語,像人一樣生活,由內到外與人無異。然而,這也使普倫迪克從第一次見到獸人起便覺得怪異恐怖。獸人與人的高度相似性動搖了普倫迪克作為人的自我認同,使他在回到文明社會后依舊無法擺脫夢魘,認為身邊的人都是被改造的獸人。
生物學在19世紀初便已誕生,“到1900年……動物體溫的秘密早已被破解,分析生命中各種能量關系的基礎也已奠定”[7]。莫羅的動物改造實驗正是基于生物學的發展,其恐怖實驗給社會各界帶來巨大恐慌,在這里,令人恐懼的不再是幽靈、鬼魂等傳統哥特元素,而是被莫羅等人濫用的科學研究成果。
2.對比極端的哥特景觀
琳達·拜爾-貝倫鮑姆(Linda Bayer-Berenbaum)在其作品《哥特想象:哥特文學與藝術的擴展》中指出:在哥特主義看來,社會及其語言所奉為真實的東西,只是現實的一小部分,還存在著未被認識的更大的現實,而哥特便是通過這種極端對比的方式表現更大的現實(reality),將對現實的擴展延伸至意識領域[1]。在《莫羅博士島》中,這種對比則主要表現在哥特式景觀上。琳達認為,哥特式景觀通常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即使是拋棄了這些陳詞濫調的現代哥特小說也保持著極端的對比。比如從古樸的城堡大門到精致而虛幻的蜘蛛網,從夜晚的寧靜到突如其來的尖叫……它們將現實放大,使人的感官處于兩種對比的狀態中,無法調整和適應,從而避免了感官的遲鈍[1]。在《莫羅博士島》中,這種哥特式景觀主要分為兩個部分。
2.1海上
第一部分是在海上,普倫迪克走出船艙后與一張黑色的臉龐打了個照面,那張臉完全畸形,一口奇怪的大白牙,雙眼四周充血。那奇特怪誕的臉龐使得普倫迪克感到恐懼。一天深夜,普倫迪克與蒙哥馬利在后甲板上聊天,在那微弱燈光下,蒙哥馬利的臉顯得奇怪又蒼白,還有那突然閃著淡淡綠光的眼,勾起了普倫迪克早已淡忘的童年時所經歷的恐懼。與此同時,大海本身也成為最大的哥特式景觀,平靜無波不過是深海的偽裝,上一刻是托著小船行駛的溫柔的手,下一刻便是吞噬生命的巨獸。
在這片無邊無際的大海上,在這個普通的小商船上,普倫迪克總是從平靜或寧靜的氣氛突然轉入某種恐懼中,這一切似乎預示著真正的冒險即將開始。
2.2島上
第二部分主要集中在貴族島。島上景色宜人,草木蔥綠,明亮的藍天與潺潺流動的小溪,一片寧靜,但下一刻,草叢中突然傳來的響動、那半人半獸的幻影及蕨草叢下兔子艷麗的尸體便打破了這份寧靜。普倫迪克受不了美洲獅被解剖時痛苦的哀號,出門探索整座島嶼,結果收獲的不是寧靜,而是恐怖的追逐。第二天醒來,普倫迪克在早晨的微風中感到身心愉悅,然而當他推開實驗室的大門時,卻看到椅子上綁著一個傷痕累累的人,以及莫羅那猙獰的臉和染血的手。莫羅第一次正式出現時,給人的印象是身材高大,額頭飽滿,五官鮮明,頭發灰白,后來,莫羅在與獸人的沖突中死亡,他臉朝下,一只手腕被割斷,銀白色的頭發浸在血泊中……
日常的船上景觀與突然出現的奇怪黑臉、半夜燈光下普倫迪克那突然變化的臉、美麗的風景與艷麗的兔子尸體、恐怖的黑暗與溫暖的燈光……作品中隨處可見這種哥特式景觀的對比,它們體現出現實生活的曲折多變,將書中的人物和讀者帶出已知世界,進入另一個更深的異世界——與世隔絕的貴族島。無論是身處其中的人物還是讀者都無暇在持續出現的極端之間調整狀態,普倫迪克便在這種極端景觀的不斷沖擊下看到了更大的現實,回到文明社會后再也無法正視遇到的其他人。
3.怪誕恐怖的哥特情節
哥特小說多描寫由于個人欲望或財產所引起的迫害、逃殺等緊張刺激的情節,涉及恐怖與怪誕,為小說奠定了恐怖駭人的整體基調[3]。就《莫羅博士島》而言,其哥特式情節主要分為緊張的追逃和神秘的懸念兩部分。這些情節為故事增添了神秘氣氛,沖擊著讀者的感官,給讀者帶來痛與美并存的審美體驗。
3.1緊張的追逃
第一次追逃是普倫迪克登島后對貴族島的第一次探索。美洲獅痛苦的嚎叫聲使普倫迪克感到煩躁不安,于是他走出門,在屋后的樹林中散步。就在普倫迪克沉浸在這難得的寧靜中時,他被溪邊飲水的怪人嚇了一跳,接著又被兔子的尸體弄得惶惑不安,小溪邊那張不屬于人類的臉使他感到恐懼,于是他想要逃離此地。天色漸暗,普倫迪克急忙往住所趕去,但一路上總有人暗暗尾隨,使他更加慌不擇路,甚至迷路。在這一路的追趕中,那腳步聲,黑夜里窸窸窣窣的聲音以及樹枝折斷的噼啪聲,都不禁讓人呼吸急促,瑟瑟發抖。這一緊張刺激的追逃,使得故事更加神秘,充滿戲劇性。
另一次追逃是在普倫迪克親眼看見莫羅博士對美洲獅的暴行之后,害怕自己也成為實驗品,于是想要逃走。在四周都是海的荒島上,瘋狂的科學家拿著武器,帶著獵犬和助手追捕普倫迪克,被活體解剖的痛苦以及獵犬的吠叫使普倫迪克害怕不已,他發現自己無處可去,也沒有防身的武器,恐懼折磨著他的身心,對生的渴望又使他拼命逃亡。這一情節涉及許多經典的哥特元素:追逃、緊張、恐懼以及死亡,讀者不禁會為普倫迪克接下來的命運擔憂。
作者運用哥特小說中經典的追逃情節,將未知科學力量所導致的恐怖呈現在讀者面前,使得讀者在恐懼緊張中思考現代科技所帶來的災難性的一面,擔憂這一切會成為現實。
3.2神秘的懸念
哥特小說作家常在作品中利用讀者對未知、懸念的好奇營造神秘氛圍,使情節緊張刺激,以引起讀者的探求欲與恐懼。
《莫羅博士島》在作品中設置了一系列懸念,但主要集中在獸人的身份上。第一個出現的獸人是船上奇怪的黑臉人。普倫迪克遇難后被一艘名叫“吐根號”的小商船所救,并結識了蒙哥馬利。在他第一次走出船艙時,突然與一個面部畸形怪異的黑臉人打了個照面,使他大吃一驚,加之蒙哥馬利對某些問題的支支吾吾,更使得普倫迪克心頭始終疑云重重。其后便是島上那些長相可怕的人。普倫迪克在島上多次見到這些奇怪的人,他們面目丑陋奇異、動作僵硬扭曲、行為怪異、語言生澀,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對這些人的身份產生好奇,同時也對這些奇怪的島民感到恐懼。
與此同時,普倫迪克上島后,其命運中潛伏著的危機,也始終牽動讀者的心。顯然,這是一座很奇怪的小島,其中恐怖怪異之事頻發,長相怪異的獸人時不時出現,使得讀者期待謎底揭曉的同時,為其捏一把汗,擔憂著他接下來的命運。威爾斯緊緊抓住人類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安排了一系列謎團,并在故事進行中伴隨著戲劇化的效果逐步展開,鋪陳故事,解開謎團,引發讀者對科學倫理的思考。
“當恐怖被引入小說時,需要很大程度的技巧和安排。”[8]《莫羅博士島》中刺激的追逃、神秘的懸念,使得故事一層一層鋪展開來,將主人公與讀者拉入高潮迭出、緊張恐怖的奇特歷險中。同時,哥特式情節與科學實驗研究的結合,引發的不再是人類對超自然未知力量的恐懼,而是對濫用科學力量所導致的災難性后果的恐懼。
三、哥特傳統下的“弗蘭肯斯坦”問題
文學是人學,文學作品以人為行為主體,其閱讀和寫作都是一個言語的交往與對話的過程,反映人的情感態度與價值判斷,體現文學作品與世界的關系。因此,文學作品不能僅是一種單純的精神形式,它還具有豐富的倫理內涵,承擔著道德教化的作用[9]。科幻文學主要描述人類面對科技變化時的反應,幫助預見不可避免或者很有可能發生的災難,使現世的人們能夠采取行動阻止災難的到來[10]。《弗蘭肯斯坦》以哥特的激情,描繪了人造人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莫羅博士島》也關注到了這個問題,作家運用哥特式的創作手法,表現出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科技力量的擔憂與恐懼,從科學倫理和人類主體地位的角度進行審視,具有強烈的道德警示意義。
1.瘋狂科學家的道德倫理悲劇
濃厚的哥特因素使得讀者能夠在極端的語境中反思科學理性和道德倫理問題,《莫羅博士島》通過對典型哥特人物、景觀與情節的描繪,引發讀者更深層次的思考和聯想。
作品中融入了大量哥特元素:瘋狂科學家與其創造物的沖突、暗夜中緊張刺激的追逃、接連不斷的死亡以及恐怖駭人的氣氛……在這典型的哥特氛圍下,不僅對科學家的道德進行了拷問,也使主人公與讀者對未知的科學力量及其所帶來的后果感到無比恐懼。“恐懼是一種對于痛苦或死亡的憂懼,因而它以一種類似于實際痛苦的方式發揮作用。”[11]在書中,這種痛苦和死亡的罪魁禍首來自科學家對科學知識無底線的濫用,“我們的技術越來越復雜,范圍越來越廣,力量也越來越大,風險也越來越大。我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哥特式恐懼的現實……”[1]這種哥特式恐懼將讀者拉入如何應用科技的反思當中,若是科學家不顧道德,如莫羅博士一般,被倫敦學術界驅逐后竟來到與世隔絕的荒島繼續進行恐怖實驗,那么將會給人類帶來難以預料的災難。威爾斯通過這種人為造成的恐怖,預言了生物實驗發展的可怕后果,并對科學家發出道德倫理上的警示。
實際上,威爾斯在《莫羅博士島》中預言的未來已經成為現實。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和日本進行的毒氣實驗、細菌實驗,都是由成果卓著的科學專家執行的。他們如同冷漠的機器,以活人為實驗對象,不顧其痛苦哀號,通過各種殘忍的實驗手段,發明出許多致命的毒氣和細菌武器,在戰場上殺人于無形,留給世人無盡的恐懼。《莫羅博士島》中的哥特式噩夢照進現實,提醒著世人遵守科學倫理道德的重要性。
2.人類主體地位的審視
17到18世紀,人類重新認識了世界,人是一種動物的觀點動搖了基督教傳統中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到了19世紀,關于人類的研究快速發展起來,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人們普遍認為人類也會或必定會很快成為科學研究的一個適當的對象[7]。不管答案是什么,人總是占據最中心的位置。
《弗蘭肯斯坦》中“人造人”的出現,對人類的主體地位發出了挑戰,引起讀者對人類主體問題的無限思考。當今社會,科技飛速發展,“人造人”不再只是文學作品中的哥特式人物,而成為現實的存在。在現代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的催生下,克隆人、仿生機器人等相繼出現,這些未知科學力量所創造的“人”破壞了人的整體性,其帶來的諸多倫理道德問題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探討。
威爾斯的《莫羅博士島》將科學幻想、哥特元素、現實問題以及深刻的思想結合起來,在探討人性與獸性的過程中,對人類主體地位發出挑戰。書中塑造了瘋狂科學家與怪物異形這兩類19世紀典型的哥特式人物形象,通過兩者的沖突,反映出人性與獸性之間復雜的關系,動搖了人的主體性。莫羅博士的瘋狂實驗首先是在生物學意義上使動物具有人的外形和身體,以及會發聲的喉頭。這種生物肉體屬性成為區分人與非人的一個決定性標準。然而,作品中獸人的身體從頭至尾并未發生較大改變,其行為模式卻發生了很大變化。莫羅利用現代催眠術將人的道德倫理嫁接到獸人的思想中,改變和扭曲了他們的獸性,使之具有人性。在前期,獸人還能遵守人類制定的道德和法律,但隨著時間流逝,他們的獸性逐漸戰勝人性,重新退回野獸的狀態。然而,作品中對人性的探討不止于此,書中展現了人類如野獸一般殘忍的獸性,如普倫迪克三人面對死亡危機,都選擇犧牲另一人以保全自己;莫羅對動物們進行殘忍的活體解剖,甚覺享受;獸人暴亂,普倫迪克等人毫不猶豫地射殺。《莫羅博士島》認為人與獸在本質上是相似的,甚至在道德和行為上否定了人與獸的本質區別,動搖了人類的自我認同,激發了人類對自身主體性的懷疑。
威爾斯將對科學倫理和人類主體地位的探討都放置在恐怖駭人的哥特傳統之下,通過哥特環境激發人類對未知科學力量的恐懼,進而反思現代科技理性下的倫理道德與人性問題,表現出作者對人類命運的擔憂與思考。
四、結語
2008年7月1日,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道,英國人工授精與胚胎管理局(HFEA)頒布一項決議,宣布生成人豬混合胚胎的醫學研究原則上可以開展[12]。無疑,《莫羅博士島》中預言的未來已經成為現實。威爾斯站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期,以獨特的英國哥特傳統主題為人類敲響科學倫理的警鐘,預言了無底線發展生物技術和基因工程的嚴重后果。首先,作家塑造了脫離道德倫理底線的瘋狂科學家及其人造怪物異形形象,描繪了沒有道德倫理約束的未知科學力量的可怕以及人獸之間駭人的相似性。其次,作家描寫了對比強烈的哥特式景觀,放大現實,將人類帶入科學影響下的未知世界,表現出人類在面對未知科學造物時的恐懼。再次,作品中融合了追逃、懸念等哥特情節元素,將人物與讀者拉入緊張恐怖的哥特環境中,更加突出了人在面對這種未知科學力量時的恐懼。最后,作家在繼續探討“弗蘭肯斯坦”問題的同時,審思人性與獸性,對人類主體地位發出挑戰。因此,《莫羅博士島》不僅具有前瞻性地預言了人獸實驗,還在探討科學倫理問題的同時體現出作者的人性關懷,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這部作品依然具有現實意義和警示價值!
參考文獻
[1] Bayer-Berenbaum L.Gothic Imagination:Expansion in Gothic Literature and Art[M].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1982.
[2] 陳榕.哥特小說[J].外國文學,2012(4).
[3] 李偉昉.黑色經典:英國哥特小說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4] Punter D.The Literature of Terror:A History of the Gothic Fiction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M].New York:Routledge,2013.
[5] 奧爾迪斯,溫格羅夫.億萬年大狂歡:西方科幻小說史[M].舒偉,孫法理,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
[6] 威爾斯.莫羅博士島[M].陳胤全,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7] 科爾曼.十九世紀的生物學和人學[M].嚴晴燕,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8] Summers M.The Gothic Quest:A History of the Gothic Novel[M].London:The Fortune Press,1969.
[9] 陳禮珍.俄國形式主義文學倫理學再評判[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21,32(1).
[10] 阿西莫夫.阿西莫夫論科幻小說[M].涂明求,等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
[11] 伯克.關于我們崇高與美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M].郭飛,譯.鄭州:大象出版社,2010.
[12] 金濤.半人半獸的怪物[J].科技潮,2008(8).
(責任編輯" 夏"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