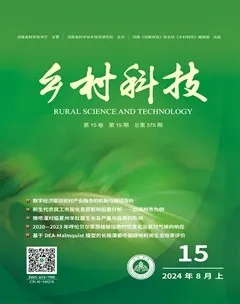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現實梗阻與優化路徑
摘 要: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關鍵。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有利于改善鄉村居民生產生活環境,是對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回應,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化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當前,人居環境整治面臨主體合力不強、支撐資源不足、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因此,各地應努力形成上下聯動、內外協作的共建共治格局,應強化協作以形成主體治理合力,應加強整合以提升資源支持力度,應健全機制以確保整治常態長效。
關鍵詞:農村人居環境;鄉村振興;生態宜居;美麗鄉村
中圖分類號:D42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7909(2024)15-38-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5.008
0 引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的一項重要工作 。 改善農村人居環境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點任務,關系農村居民根本福祉和美麗中國建設。在持續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作為中國農村環境治理的重要任務,進入全國性的公共政策議程[1]。自2018年起,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的實施,有效扭轉了農村長期以來臟亂差問題。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方案(202—2025年)》,對進一步加快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做出部署。當前,農村人居環境總體質量不高、管護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仍然存在,亟須解決。
1 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重要意義
1.1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以建設宜居村莊為導向,把農村垃圾處理、農村污水治理、農村村容村貌提升、農村“廁所革命”作為主攻方向,通過完善農村生活垃圾處理體系、推進農村生活污水處理、提升農村衛生設施建設與管理水平、優化村莊建設等舉措,使鄉村變得更加生態宜居。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也極大地改善了鄉村基礎設施條件,為招商引資、人才集聚提供了良好的支撐條件,也為鄉村發展觀光農業、創意農業、旅游農業等產業項目提供了機遇,不僅激活了農村經濟活力,還有助于帶動鄉村居民增收。與此同時,農村人居環境整治 ,還有利于增強鄉村組織力和凝聚力,促進組織振興、文化振興,提升鄉村基層治理效能[2]。進言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通過環境、設施、服務等的優化改善,可以對鄉村發展和振興產生直接或間接的促進作用。
1.2 人居環境整治是化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轉變為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發展之間的矛盾。宜居的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是 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人居環境深刻影響 農村居民的生活體驗。農村生活垃圾治理、農村生 活污水治理、農村村容村貌提升、農村廁所改造升級等人居環境整治舉措的實施,不僅改善了農村居住環境、提升了公共服務水平,也間接為人才回流、投資建設、產業發展提供了契機,對農村的產業發展、環境改善、文明建設、基層治理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這對于城鄉融合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區域差距。這些顯著作用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2 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現實梗阻
2.1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主體合力不強
2.1.1 基層政府行為存在偏差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要堅持以地方為主,強化地方黨委和政府責任,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構建政府、市場主體、村集體、村民等多方主體共建共管格局。但在實際中,基層政府對其他主體的動員力度不夠,市場主體、村民、社會力量未能充分參與其中。此外,一些地方缺乏長遠規劃,在措施擬定過程中,未能充分考慮不同村莊的差異性,存在“一刀切”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治效果。同時,一些地方在人居環境改造過程中存在重速輕質、搞“形象工程”等問題。
2.1.2 社會力量參與力度不夠
社會力量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體。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等力量的參與可以促進信息溝通、優化資源配置,也有利于引導村民參與整治行動 。 近年來 ,隨著整治行動的持續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取得初步成效,但也存在市場、社會組織參與程度不高,間接參與多、直接參與少等問題。一些市場主體、社會組織過于逐利,存在半路撤退現象,造成項目擱淺。同時,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多為規模較小的企業或者個體戶,其規模小、資源整合能力有限,促進作用并不明顯。
2.1.3 村級組織功能發揮不夠
村級組織是連接黨組織和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也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主體之一。但當前,村級組織領導能力弱化、執行力不強、創新力度不夠等問題,顯著影響了村級組織在人居環境整治中發揮作用,為整治工作增加了難度。一方面,村“兩委”干部年齡偏大,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政策理解不深、認識不足,主動參與意識不強。另一方 面,就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而言,若上級沒有嚴格的 政策落實時限、標準與制度要求等,村級組織可能 會采取選擇性應對方式進行處理,通過“運動式清場”,以覆蓋、遮擋或美化等方式應付檢查,由此也 帶來整治不徹底、不充分和難長效等頑瘴痼疾。
2.1.4 農民參與積極性不高
一方面,村民雖然較為認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政策,但這并未帶來農民個體行為的改變和集體行動的達成。政策執行中的標準化、清晰化、規范化與農民生活中的非標準化、模糊性等存在沖突,相關知識懸浮于農民認知之外[3]。進言之,對村民而言,以便捷性、實用性為特點的日常生活習慣與整齊、美觀的標準化要求難以融合。另一方面,有些村民認為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是政府的事,自己只需要被動參與就好,對村莊整治工作漠不關心。
2.2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資源支撐不足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一項長期的工程,涉及面寬、范圍廣。隨著整治工作的推進,資金投入不足、專業技術支撐不到位、專業管護隊伍缺乏等新問題不斷涌現。
2.2.1 財政資金投入不充足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資金主要來自政府財政支出及農村環保專項資金,社會資本投入的接續性較弱,環境治理設施的建設與運維存在較大的資金缺口。近年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是各級政府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任務,但由于各項工作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客觀上導致各級財政可用于投入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資金受到擠壓和制約。
2.2.2 專業技術支撐不到位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涉及村莊規劃、政策制定、基礎設施建設等多方面工作,工作的開展不僅需要資金投入,也需要專業技術及人才支撐。但當前出現了技術支撐不到位、專業技術人才缺乏等困境。人才培養有其周期和規律 ,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迫切性與專業人才的短缺性之間的矛盾變得不可調和,成為制約人居環境整治成效的重要因素。
2.2.3 專業管護隊伍缺乏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涉及較多基礎設施維護,這些設施需要定期保養、檢修,運行管護技術要求較高。農村居民居住相對分散 ,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小、數量多、較分散,基層政府難以為每處基礎設施配備專門技術人員、專業管護隊伍,這導致一些偏僻鄉村基礎設施維護、維修不及時,部分基礎設施后期管護存在短板。其中,也存在運維人員專業能力不足、缺乏必要的保養和維護技能等問題。同時,一些農村基礎設施雖由村干部負責管理,但由 于其不懂維護、維修技術,也導致了一些基礎設施長期缺乏必要的基礎維護。
2.3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缺乏長效機制
2.3.1 基礎設施利用率低
隨著“三年行動”“五年提升方案”的實施,各地陸續加大基礎設施投入力度,興建垃圾處理廠、污水處理站、鄉村大舞臺、圖書室、文化廣場等并配備健身器材。完善的基礎設施不僅有利于優化農村人居環境,更有助于豐富農村居民精神文化生活,但也出現了基礎設施使用率低甚至閑置的現象。一方面,有些地區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由于前期規劃缺乏必要論證,有些文化廣場、健身器材設置地距離村民居住區遠,村民很少使用。有些地區文化廣場長期閑置,最后成了村民打糧曬場的地方。另一方面,基礎設施管理不合理,維修不及時,損毀嚴重,影響村民使用。
2.3.2 缺乏長效管理機制
以垃圾處理為例。一些村民對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及操作方法缺乏了解,導致生活垃圾的分類回收和資源再利用率低。在一些地方,垃圾桶隨意堆放,垃圾不入桶現象也較為普遍。類似的污水處理、廁所改造以及村容村貌等相關工作,也都或多或少存在管理機制不健全、管理行動滯后等問題。
2.3.3 整治成效容易反彈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使村容村貌有了整體提升,改善了農村居民居住環境,但也可以看到,臟、亂、差現象仍然在整治過后會重新出現。一方面,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中,缺乏對項目實施全過程的監督,導致建設過程偷工減料,部分基礎設施項目不達標、不耐用。另一方面,村民長期以來的生活習慣難以改變,政府出資動用村公益崗,雇傭保潔公司對村內垃圾、殘垣斷壁、廢舊坑塘等進行集中清理。一些地方維持幾天后又恢復原來的樣子,垃圾亂倒污水亂排等問題仍然存在,導致前期整治成效大打折扣。
3 推進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優化路徑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是一個系統性工程,需要主體間的協作、強化資源整合與支持力度、完善制度建設以構建長效機制。進言之,上下各級政府、市場主體間的多維聯動及村莊場域內村集體能動性的發揮,共塑的資源供給與行動耦合合作網絡對未來人居環境的順利推進尤為重要[4]。
3.1 強化協作,形成主體治理合力
3.1.1 不斷調試政府行為
一方面,基層政府要轉變理念,強化動員合作,堅持以人為本,通過實地調查、多方協商、聽取專家建議等方式,提高決策科學性、合理性。另一方面,要采取措施,完善多元合作機制建設,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政策制定、項目實施、項目驗收等各環節充分傾聽市場、社會組織的意見建議,平等協商、共擔責任,提升治理效果,共同推動農村人居環境長效發展。同時,地方政府應重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制度規范的體系建構,樹牢“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理念,摒棄重城市生態環境治理、輕農村環境整治觀念,正視問題、聚焦重點、補齊短板,全方位推進整治工作[5]。
3.1.2 強化社會力量責任意識
一方面,可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如基礎設施建設補助、減免企業稅費等,鼓勵市場主體、社會組織更好地參與整治行動,吸引更多資金、技術雄厚的企業助力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另一方面,通過培訓,加大宣傳力度,激活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的社會責任感,調動其參與積極性。
3.1.3 充分發揮村級組織的引領作用
一方面,加大村干部培訓力度,全面提升基層干部文化素質及綜合素質。借助社會培訓力量舉辦鄉村綜合整治培訓班,將基層村“兩委”干部納入培訓計劃,分級分次開展培訓。鼓勵村干部學歷提升,提高村干部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建立村“兩委”年輕后備干部培育庫,培養年輕干部后備力量,改善村“兩委”干部年齡結構,為基層補充新鮮血液。
3.1.4 增強村民參與意識
充分利用村廣播喇叭、文化長廊、宣傳冊和宣傳頁等,結合微信、快手、抖音等網絡平臺,拓寬宣傳途徑,提高宣傳覆蓋面 。探索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政策融入村規民約,充分發揮村規民約的規制作用。同時,可靈活采取契約化機制,通過門前責任契約化、村民輪流契約化等形式明確權責邊界,由上級單位駐村干部、村民代表、黨員代表和村組干部等組成村級環境治理監督隊進行網格化管理監督,防止出現公共性空間環境治理“公地悲劇”現象[6]。
3.2 加強整合,加大資源支持力度
3.2.1 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
一方面,要進一步加大財政統籌力度,為整治工作提供資金保障 。 基層政府應確保上級下達的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資金專款專用,同時結合地方財政情況,量力而行,適當予以補充 。另一方面,基層政府可以通過以獎代補、以工代賑、先建后補等方式,提高資金利用效率,集中財力保障整治行動重點項目穩步推進,把有限的資金用在刀刃上。
3.2.2 拓寬社會投資融資渠道
一方面,廣泛吸引社會資本,構建多元化資金供給體系。地方政府可探索建立社會資本投入回報機制,在彌補整治資金缺口的同時,使社會資本也能夠獲得合理利益,實現社會資本投入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鼓勵村級組織投入。村級組織可因地制宜探索發展集體經濟,開發利用當地資源,發展鄉村旅游等產業,將經營所得用于當地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同時,可充分挖掘新鄉賢力量,為有志建設家鄉的新鄉賢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協助。
3.2.3 加強技術支持及人才培養
一方面,要創新生態數字治理監管機制。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建立信息化農村人居環境治理體系。通過數據分析精準監測污水排放量和垃圾產生量,實現全過程、全周期在線監管[7]。另一方面,加強與農村人居環境整治、鄉村產業發展相關的主體人才、支撐人才和管理型人才隊伍建設,打造先進農業科技人才隊伍。同時,要關注基層設施專業管護隊伍建設,合理配置基層專業人才,保障既有基層設施維護的可持續性。
3.3 健全機制,確保整治常態長效
3.3.1 建立科學長效管護機制
一方面,要明確項目管護主體、管護部門、管護人員,確定管護權限和管護職責。另一方面,根據地區實際,因地制宜選取適當的管護方式。對資金充裕的地區,在加強監管的同時,可采取第三方專業公司管護方式。對村集體經濟較好的地區,可考慮由村級運營管護,由村集體出資培養、聘用專業管護人才。
3.3.2 健全督導監督機制
一方面,加強協同監督。充分調動村級組織、企業主體、社會組織、村民等多方主體參與監管的積極性,加強合作、合理分工,提高監督效率。另一方面,加強督導檢查力度 。依托“督察臺賬”,對項目建設情況、村容村貌整治情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情況等進行全面督導檢查。
3.3.3 完善考核制度
一方面,科學制定考核體系。結合地方實際,制定差異化考核體系,分類考核,確保考核結果準確、有效。同時,有條件的地方可依托第三方機構,對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成效進行考評,診斷建設、運營、管護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時處理。另一方面,要優化考核指標。減少對會議記錄、工作臺賬等文字材料的檢查,注重對農村居民的滿意度調查,使基層整治重點體現農村居民的期盼與訴求。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地區情況存在差異,因而考核評估方式需要推進分類別、精準化、差異化考核,建立分級分類考核評價制度,綜合運用日常考核、年度考核、專項考核、綜合考核等多種方法,實行差別化與綜合性評價相結合的評價方式,拓寬考核的視野和范圍,立體化、多維度考核評價干部實績,增強考核工作的科學性、針對性、可操作性,引導各級干部全面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真正讓高質量發展要求深入人心、融入工作。
參考文獻:
[1]吳柳芳.農村人居環境治理的演進脈絡與實踐約制[J].學習與探索,2022(6):34-43.
[2]李裕瑞,曹麗哲,王鵬艷,等.論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與鄉村振興[J].自然資源學報,2022,37(1):96-109.
[3]李祖佩.人居環境整治中的農民主體性缺失:過程與機制[J].求索,2024(3):55-65.
[4]杜焱強,詹昕穎.農村人居環境何以實現異質性治理?:基于外部資源和內在動力的解釋[J].公共管理學報,2024,21(4):151-165,176.
[5]皮俊鋒,陳德敏.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實踐經驗、問題檢視與制度建構:以重慶市地方實踐為切入視角[J].中國行政管理,2020(10):153-155.
[6]陶自祥.差序整治:鄉村人居環境治理的地方化實踐[J].2023,49(4):98-106.
[7]毛佩瑾.農村人居環境長效管護機制的功能定位與構建路徑[J].東南學術,2024(5):149-159.
(欄目編輯:劉靜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