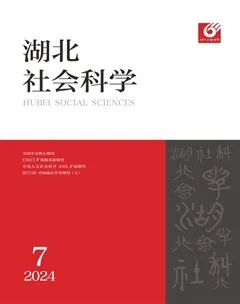落實新質生產力的關鍵:考察創新的三種途徑及其價值


摘要:科技創新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但對如何科學地掌握創新動態,準確地評價創新產出,并據以進行重點的政策扶持,在現實中卻殊為不易,學者也莫衷一是。對于此項不可回避,但又不易厘清的工作,本文從近年中外相關研究中,梳理出三種主要的創新度量途徑——資源投入、成果產出與體系特征——分析它們是否容易具體落實?能否指導國家科創政策的制定?基于此三類不同考察策略,建議以“產出維度”為指標基礎,補充以投入數量與體系特征,作為考察中國的科技創新發展與動態,幫助引導政府決策、落實政策督導的基礎,從而落實“新質生產力”發展,全面推進國家技術創新。
關鍵詞:創新度量;研發投入;專利;國家創新系統;新質生產力
中圖分類號:G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477(2024)07-0060-09
收稿日期:2024-04-02
作者簡介:陳博(1993—),男,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博士(浙江杭州,310058);耿曙(1965—),男,政治學博士,浙江大學文科百人計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浙江杭州,310058)。
一、引言
在2024年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也被列為本年度的首要任務。那么何謂“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1]由此來看,“新質生產力”雖是一個嶄新概念,其本質仍是強調創新發展,而這正是我國近年來發展理念與實踐的主線。既然創新在我國當下發展全局中居于如此核心的地位,眾多概念也嘗試從不同角度來對其進行闡釋和拓展,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測量創新?這是本研究關注的主要問題。
測量創新是一項基礎性和重要的工作,它是后續政策規劃的前提。自2018年以來,美國不斷加碼對中國的科技制裁,試圖限制中國在科技創新領域的發展。在此形勢之下,中國必須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為了更加高效地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合理、可靠地度量創新,唯有如此才能精準地評估我國創新實力與技術領先國家間的差距,在此基礎上分析現階段的不足,造成創新差距的原因,進而制定針對性的政策,快速有效突破技術發展的瓶頸,實現技術升級與迭代。為此,我們需要盡快選擇、制定適合我國的創新測量方案。
針對“創新測量”問題,創新研究領域的學者對此進行不斷持續的探索。縱覽這些相關成果,我們不難發現,測量創新的前提是清晰、具體地界定它的內涵。此項工作并不容易,因其既要全面涵蓋創新的抽象意義,又要尋覓可觀測的具體指標。經過近百年的探索,學者依次形成側重“投入”“產出”和“系統”三類考察創新的視角,也衍生出三種對應的測量方案。[2](p287-343)這些方案在學術研究和政策評估中廣為應用。[3](p10)然而這些方案各有哪些局限?應當如何克服這些局限,進而形成更加清晰可行的方案?這些都有待進一步考量,這也正是本文的寫作目的。因此,本文梳理了近年來創新測量領域的發展脈絡,介紹各個階段主要的創新測量方案,闡述諸項方案優勢與不足,在比較、綜合分析過程中選擇較為合適的度量方案,以便作為今后考察與規劃中國技術創新的參考。
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各節規劃如下。第二節簡介創新考察的困境,并概述現有度量方案,即如何從“投入”“產出”和“系統”三個層面來定義和度量創新。文章第三、四、五節依次具體介紹三種度量方式、各自常用指標,分析每種方式的優勢與局限。第六節綜合上述分析,主張未來度量創新應以產出層面,尤其是專利指標為主,同時就我國專利發展策略提出建議。
二、創新考察的困境與途徑
創新考察的首要困境在于其內涵太過廣泛與抽象,因而難以具體界定和度量。學者通常將“創新”定義為“將新知識應用于產業/商業部門”。[4](p66-71)然而知識本身就是無形之物,難以具體觀測衡量,而知識應用到產業/商業環節后,將會產生何種影響?這就更難追溯界定。因此,為了測量“創新”這一抽象概念,學者一般對策是借助某種更為具體且可觀測和可計量的概念來對其具象化,也即我們常說的“概念的操作化”。[5](p529-546)但如何具體進行操作化,又取決于學者如何認知和理解“創新”。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兩種創新認知途徑是從投入到產出的“線性過程模型”和包容各類創新要素的“體系結構模型”,[6](p317-350)基于兩種視角的差異,這才依次衍生出學界采用的三類主要創新度量策略。
起初,學者基于“投入—產出”的線性模型,將“創新”定義為“研發和應用新知識的活動”,通過統計其中資金和人力投入來嘗試度量創新。但投入未必創造產出,因此學者轉而將創新直接界定為“研發或應用新知識的產出”,并借專利(研發產出)和新產品收入(應用產出)等指標進行衡量。[7](p18-57)然而創新產出得以實現,通常有賴多年的持續投入,因此可能其嚴重滯后于創新發展,故難及時掌握創新能力的動態。
于是有學者放棄前述“線性過程”思路,轉向孕育創新的“體系特征”模型。根據多數學者的看法,這一體系中包含影響創新的諸多要素,例如研發部門和商業組織、組織間的網絡聯系、產權制度等,[8](p181-208)通過上述要素的綜合運作,最終創造出創新成果。[9](p3-22)因此,若能考察創新體系內部組成要素及其之間的互動模式,便可有效掌握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以此代理創新。然而,針對創新體制涉及哪些要素?整體體制如何考察度量?學者之間尚未取得共識,往往只能以“要素累加”——將體系各要素分解為具體指標,然后分別測度,并將所得加權合計——作為替代。但這種策略本質仍是分解的“指標測量”,而非整體的“體系考察”。
以上便是當前度量創新的主要策略及其發展與局限,筆者將其整理為表1,并在下文更為詳細地展開探討。
三、基于投入層面的創新度量及其局限
在創新研究興起伊始,學者通常將創新視作從研發到應用的“線性過程”,并將其界定為“生產和應用新知識的活動”,[10](p148-179)考察這些活動的主要方式,便是統計其中經費支出和人力投入,這也成為最早度量創新的方案,時至今日仍被廣泛應用。
(一)主要測量方案
這一方案如此受青睞,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歷史背景。在二戰和冷戰期間,美國等國家的研發投入與創新發展齊驅并進,因此許多官員和學者相信:創新投入自然能夠帶來技術產出。也因此,美國在二戰期間的聯邦研發經費增長了15倍,[11](p29-75)美國也借此高速增長的研發投入,迅速崛起成為頂尖科技強國,不但成功研制出原子彈,還在各個領域引領技術創新。在隨后的冷戰期間,各國進一步角逐于科技研發領域。以美國為例,其研發投入總量比當時所有其他經合組織國家(OECD)的總和還多。[11](p29-75)得益于如此巨額的研發投入,美國相繼推出計算機和互聯網等一系列革命性創新成果。有鑒于如此豐碩的創新成果,西方學者和官員都深信,國家應當大力投入研發,由此便可推動技術創新。這一信念終于在《科學:無盡的前沿》得到最系統的展示,并在日后不斷發展與強調。這一“投入引導”視角,不僅推動了政府資助研發的政策模式,也影響了后來的創新測量活動。
誠如前述,“投入就能帶來創新”的思想觀念,影響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1的技術創新測量以及后續OECD的測量。后者于1963年發布了著名的《弗拉斯卡蒂手冊》(Frascati Manual)。2該手冊為測量研發投入,確立了概念框架和數據收集方法,也首次確定了創新測量的國際標準。手冊中的測量指標沿用至今,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研發經費投入,其中最常用的是國內研發費用總額(GERD)及其占GDP的比重(即所謂“研發強度”)。在創新各環節,政府最容易進行支配的便是研發經費,因此格外重視這項指標。第二類指標也與此類似,但特別強調研發人員投入,主要包括研發人員數量與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后者衡量的是研發人員的工時投入,因此若相當比例的研發人員并非全職時,它的測量結果更為合理。[3](p10)
盡管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許多學者預設“創新發展取決于研發投入增長”,并據此將創新測量聚焦于研發投入。但早在20世紀60年代,有部分學者意識到,將研發成果應用于市場,才是實現創新的關鍵步驟。[12](p20)因此他們主張,研發成果應用活動的投入也應納入創新測量。[13](p275-306)學者們的努力進一步落實為《奧斯陸手冊》(Oslo Manual)。3該手冊仍由OECD發布,用于指導各種創新調查。根據該手冊,創新活動費用除了研發經費之外,還有購買知識的費用、購買機器等資本品的費用、新產品的規劃和設計等費用、營銷和培訓費用。上述所有費用共同組成“創新活動總費用”。[14](p80-85)不過,由于研發以外的其他創新活動費用通常缺乏完整數據,因此學者在測度創新投入時,仍以研發經費作為主要指標。
(二)測量方案的局限
研發經費等投入性指標,看似能夠反映國家和企業的創新努力,進而有助推斷其創新成果,但其測度過程可能面臨各種爭議。此處可以“研發經費”為例說明。首先,在收集研發經費數據時,概念界定環節就面臨爭議。具體而言,在現實經濟運行中,研發與非研發活動之間并無清晰界限,因此兩者很難清楚區分。例如教育、制度、基建等各種投資,看似不是直接的研發活動,卻為研發活動提供基礎,因而可能兼具研發功能。面臨如此模糊界限,研發定義也難界定分明。根據廣為接受的籠統定義,“研發”是“系統性地獲取和利用新知識”,[3](p1-10)但這卻無助判斷“哪些活動(費用)算是研發(經費)”。因此企業在上報研發經費時,經常會任意劃分。不同企業的劃分標準常常相去甚遠,所以研發經費的統計口徑非常混亂,所得數據也難以進行系統比較。
其次,研發經費數據還可能受到企業操縱。企業在研發指標上“灌水”,經常能獲得額外好處,例如政府的稅收減免、創投基金的資助,或是提升公司股價。企業受到這些好處激勵,便會設法拉高研發投入數據。然而,企業若是大量投入研發,通常會降低其凈利潤,研發失敗又是常事。因此,許多企業并無意愿投入研發,而是傾向選擇造假——研發數據一般只能由企業自行上報,而且相關部門難以查驗。在中國“高新技術企業”認定中,類似問題屢見不鮮。這些常見的數據造假,也讓研發經費難以反映創新投入的真實水平。
最后,也是最嚴重的問題,即便企業沒有虛報數據,研發經費也未必反映其創新發展。原因在于,研發活動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企業常常很難選準研發方向,導致投入難以順利轉化產出。而且,由于早期選定的研發方向通常會被延續下來,引導企業后續投入。因此,企業即便察覺路徑出錯,也可能繼續加碼下注,結果造成大量經費付諸東流。典型如韓國、新加坡等為了發展生物科技,前后豪擲數十億美元,結果卻以失敗告終。[15](p1-15)上述因研發方向出錯,導致投入失敗的現象,在國家資助的項目中通常更為普遍。在此類項目中,企業缺乏預算約束,投入無須精打細算,各種浪費更是屢見不鮮。[16](p103-114)總結而言,研發投入并不意味著創新產出。此一考察方案的前提,“投入就能帶來創新”,其實讓人存疑。
總結本節內容,早期創新研究學者似乎相信,創新投入能夠反映創新努力,進而預示創新產出,故而選用投入指標來度量創新。然而,學者的這種信念其實并不成立。首先,投入數據未必準確,因而也無法反映創新努力,況且這些投入大半可能失敗,所以未必帶來產出。如此一來,利用“前期投入”折射出來的“創新”,可能未必具有參考價值。于是學者們轉向直接從產出層面度量創新,這也正是下節將要探討的內容。
四、基于產出層面的創新度量及其局限
為了取代參考價值存疑的“投入”層面的度量,學者轉而將直接關注“創新產出”,并以此指導創新的度量。
(一)主要測量方案
根據“研發—應用”的線性創新模型,創新產出大致被界定為兩類,第一類是研發產出,其中最常用的指標是學術出版和發明專利。學術出版物承載著各門學科最新穎的知識和最前沿的發現,因此常被用來反映科學進展。然而,科學進展雖可反映大學研究產出,但后續的應用開發產出卻多半源自產業部門。為能測度產業領域的創新,經濟學家經常仰賴專利指標。部分經濟學家甚至將專利指標視為唯一能夠測量大規模發明的方式。[17](p227-241)這一觀念確立于雅各布·施莫克勒(Jacob Schmookler)的研究,他用專利數量代表發明水平,嘗試證明“技術發明主要由市場需求拉動”。[7](p179-188)
盡管學術出版物和專利均可用于考察研發產出,但這些產出未必都能應用于市場,因而不能算作嚴格的創新產出。所以有學者認為,還需要尋求更為直接準確的測量指標。學者們的努力催生出第二類創新產出指標,即“新產品”數量。[17](p1-25)新產品源自對專利等科研成果的開發與應用。不過這些成果的科技含量可能相差很大,這就導致新產品的創新程度也有極大差異。有些新產品能夠創造新的行業,而有些新產品只是對原有產品的輕微改進,常見如更改外觀設計等。為了減少產品創新程度帶來的統計偏差,學者們使用新產品的市場收益來幫助度量創新產出,其中涉及新產品的產值或銷售額等。[18](p3-29)例如,著名的“科學政策研究所”(SPRU)1曾借助新產品銷售額,總結歐盟創新產出的結構與模式。
雖然上述三項指標都被用來度量創新產出,但是相較之下,專利似乎更為合適,因其兼具“科技含量”和“市場價值”,更加契合“創新”含義。具體比較而言,學術出版作為基礎研究的成果,雖能體現科學進步,但要經過應用研究、實驗開發和商業化等漫長過程,才能應用于市場,落實創新。反過來看,新產品的經濟收益雖能反映科研成果的市場價值,但這種價值未必取決于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或許更依賴于企業的營利能力。[19](p285-305)舉例來說,榮冠可樂公司首次發明了無糖軟飲料,但最終憑此獲得巨額利潤的卻是行內頭部企業——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因此,綜合上述,學術論文作為指標太偏科研,新產品收益則太重市場,兩者各有偏頗。專利則恰好位于兩者之間,既是科技發明成果,又深具潛在商業價值,因而較為契合創新的核心定義,更適合用來測量創新產出績效。
此外,相比于其他指標,專利還具備明顯的數據方面優勢。首先,專利數據相當豐富,且便利獲取。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建立起專利制度,并且在互聯網上公開專利文件。中國自1985年起正式實施專利制度,并公布了所有的微觀專利數據。許多學者和機構將專利數據與企業和產業等數據匹配,創造出豐富的研究成果。[20](p69-76)其次,專利文件披露了翔實的細節,可供學者進行記錄、分析、追蹤,發展出更為具體細致的研究。例如有學者利用專利引用信息,分析創新價值,還有學者利用合作各方信息,呈現創新網絡關系。[21](p1-22)最后,專利數據不僅內容豐富,而且相對可靠。因為其他創新指標,例如研發投入、學術論文、新產品收益等,數據僅來源于學界或者產業等單一部門,不但標準無法統一,也難以事后系統檢驗;但專利數據則經過發明者、專利代理律師、政府專利機構等多個部門連番審查,在專門的專利部門進行登載,因此更為系統可靠。
(二)測量方案的局限
盡管“創新產出指標”常被用于衡量企業和國家的創新,但就筆者看來,這種衡量仍然有欠準確,其具體原因如下。首先,利用產出指標來衡量創新,通常會高估其真實的績效水平。原因在于,一項創新成果得以問世,不僅僅得益于最終推廣企業的努力,還需要其他組織的配合以及制度環境的支持。具體而言,一方面,創新成果往往凝聚著多個組織的貢獻。這些組織相互分享知識、合作開展研發,共同創造出發明成果。以近來頗受關注的半導體制造設備——光刻機為例,它的制造涉及化學工程、材料學、光學、軟件設計等多個領域的知識,它能問世也得益于上述各領域團隊的科技攻關。另一方面,專利發明活動需要受到制度保障。有效的知識產權制度能夠激勵研發,支持性的金融政策可為研發提供充足資金,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為合作研發保駕護航。換言之,眾多組織的投入以及各項制度的支持,共同孕育了創新成果,因此在考察與測量創新時,不能只關注最終發明者或銷售者,而排除忽視其他參與成員。
其次,具體的產出指標——例如專利——無法衡量許多重要但無形的創新。事實上,創新不僅僅存在于技術層面,還存在于組織層面。[22](p58)這些無形的組織創新既不能申請專利,也無法直接轉化為新產品和工藝,但卻極其關鍵——經常都是組織、制度的變革促進了知識和信息的流動,從而催生了大量技術創新。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莫過于硅谷。硅谷早期的創業者們開創了靈活開放的組織結構,這一結構聯通著大學、風險投資機構和公司,從而建立起“工程師—投資者—企業家”的合作網絡。這種產學網絡孕育出了半導體、計算機和互聯網等行業,使得硅谷成為全球創新勝地。[23](p7-10)硅谷的經驗似乎表明,組織創新能夠促進知識流動,從而激發系統性的技術創新。盡管組織創新是創新的重要維度,它卻無法由創新產出指標直接衡量。
最后,產出指標可能無法度量國家或企業近期的創新動態。原因在于,創新是一個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從基礎研究到論文產出、專利申請和市場應用,經常需要多年持續投入,才能取得客觀的成果。以最為典型的制藥產業為例,一項新的藥物需要經歷可行性分析、化學或生物分子分離、動物測試、臨床試驗、政府審批等多個階段,才有望上市,整個過程耗時頗久。有學者曾經統計美國18種創新藥的生產周期,結果發現,這些藥物從確定可行性到合成有效藥,平均花費17.3年,最長竟達54年之久。[24](p1-34)如此漫長的開發周期意味著,創新產出通常會嚴重滯后于科技投入與創新發展。因此,若要利用產出指標考察國家創新,較適合于考察美國和德國這種老牌科研領先國家,而不適合于考察中國和印度這種后起之秀。因為前者創新投入已然實現產出,后者的科創成果可能還處在孕育過程中。
綜上來看,創新產出盡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家的創新,但可能只是以往成績。然而,創新意味著拓展知識和產業前沿,因此相比于既往成績,最新動態顯然更受人們關注。為能測量創新動態,學者轉而將創新視作“體系”,它涵蓋了創新的重要特征,例如制度支持、組織互動。更重要的是,通過考察國家當下的創新潛力,它能預判其未來績效。體系視角如何實現這一功能,正是下節將要探討的內容。
五、基于體系層面的創新度量及其局限
為了彌補產出視角的局限,幫助考察新晉創新國家的績效,學者放棄“投入—產出”的線性模型,轉向借助“創新體系”(Innovation System)概念來指導創新測量。根據一般接受的定義,創新體系由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的要素(組織和制度)組成,這些要素彼此互動,共同影響創新的開發、擴散和使用。[25](p41-61)
(一)主要測量方案
學者們之所以利用“系統”視角來把握創新,是因為他們發現,創新通常無法由某一組織單獨完成。相反,創新成果得以問世,既得益于多個組織在研發、生產和銷售領域的合作,也有賴于財政政策、教育體系、專利制度等相互配合。這種觀點最早見于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對日本創新經驗的研究。在他看來,日本能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創新追趕,原因在于通過“逆向工程”,吸收和改進了別國的先進技術。這種方式涉及原料供應、零件加工和產品裝配等生產環節,因此需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緊密配合。此外,要完成這種技術前沿項目,還需人力財力支持。因此日本政府積極提供財政資助,發展高等教育,培養出大量工程師。上述“組織—制度”互動過程,便被弗里曼稱作“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26](p31-54)
以上分析說明,“國家創新系統”概念的提出,正有助于考察國家創新。后來學者拓展這一思路,比較不同國家(地區)的創新體系與績效,從而基本確證:不同組織與制度之間有效地協調互動,有助提升體系的創新產出。這一結論也為改進創新度量提供了思路——若能測量創新體系中的“要素互動”,便能反映國家創新的動態進展。憑借這種測量思路,學者們不僅能夠考察傳統創新強國,也能考察新興創新國家。[27](p64-73)
受到上述思路啟發,學者們設法度量“國家創新系統”。但由于要素互動不易測量,他們只得訴諸簡化方案:分別測量各項要素,然后將這些要素進行因子分析或加權合計。這種度量方式被稱作“創新(復合)指數法”或者“記分牌”,例如“歐洲創新記分牌2020”(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參見表2)[28](p8)和“全球創新指數2020”(Global Innovation Index,參見表3)。[29]上述做法的具體度量過程如下:首先,學者會主觀選定影響創新的重要因素,然后將選出的要素分解為更具體的指標,從而形成指標體系,如以“歐洲創新記分牌2020”為例(參見表2),其包含10項要素,每項要素包含2~3個指標。接著,學者依據指標體系,逐項收集數據。最后,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加權合計,所得數值用來反映一國創新。根據“歐洲創新記分牌2020”,中國當年得分95,被認為在創新領域表現出強勢作為(Strong Innovation)。
(二)測量方案的局限
上述測量策略雖然有助考察創新的實時發展,但其本身仍較初步。具體來看,首先,哪些要素對于實現創新必不可缺,因而應當包含在創新體系之中?學者對此少有共識。[8]( p181-208)因此,學界迄今尚未形成一致的“國家創新系統”的既定框架,可以幫助學者確認特定指標,并據以測量創新水平。結果學者們不得不憑借各自對創新的主觀認識,做出各有不同的度量選擇。也因此,不同學者主持的測量項目,要素和指標差別很大,例如上述“歐洲創新記分牌2020”選擇了10項要素(見表2),而“全球創新指數2020”則選擇了另外21項要素(見表3)。而且由于要素和指標存在差異,即便考察同一組對象,不同測量項目的結果也會不同。這一點非常類似于形形色色的大學排行榜:面臨多樣的要素和指標體系,會有不同的測量結果,各家排名頗有出入,社會與政府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認定。
其次,創新體系中的要素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發揮作用,也缺乏具體厘清。對于體系層面的互動特征,學者們對此認識有限,更不知如何度量。[30](p43-53)理論上講,要想度量各類創新要素的貢獻及其之間互動,學者們需要將這些要素作為“原因變量”,將創新作為“結果變量”,然后借助實證計量手段,識別出前者對后者的凈效應以及不同要素之間的交互效應。但在現實中,此類研究鳳毛麟角,遠不足以形成一致結論,用來指導創新的系統測量。因此,即便學者們已經意識到,創新要素及其之間互動至關重要,但無奈停留直觀認識,不知如何進行測量。
最后,當前體系考察中經常使用“要素累加”來代替測量“要素互動”,這不免有悖于考察“創新體系”的出發點。因為根據“體系”概念,不同要素之間互動形成系統的獨有特征,此類特征不能化約為個別要素的加總。舉例而言,根據創新體系的思路,即便某項要素非常強勢,但若沒有其他要素配合,也難充分發揮作用。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國家過分重視基礎研究,忽略科技成果轉化,那么這個國家的創新未必很好。但是在“要素累加”這種測量方式中,一項要素越強,創新體系最終得分越高,這代表其創新越好。這與該體系的最終創新可能存在落差。
綜上所述,“國家創新系統”概念為考察國家創新提供了洞見。基于這一概念來度量創新,看似可以綜合多項指標從而避免單一指標的局限,但由于這種方法缺乏明確的理論指導,因此在個別指標的選取和不同指標組合方面,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很難拿出讓人信服的測量結果。總之,就體系特征考察創新的做法,目前似乎尚不成熟。既然如此,應當如何度量創新,才能引導中國技術推進?下節結論部分,筆者就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六、結論與展望
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中央政府2024年度的首要任務,其關鍵是依靠創新驅動,這首先需要我們科學地測量我國當下的創新水平。本文聚焦“創新測量”這一議題,圍繞其演進線索,分析了創新投入、產出和系統三項測量方案的進展與局限。學者起初強調通過資金和人力投入來衡量創新,這種方式雖能反映出“努力”,卻無法呈現出“成果”。于是學者轉而直接考察創新產出,在產出指標中,專利既貼近創新概念,又具有數據優勢,因而最為合意;但其只有助評估“過往”的創新,而無法幫助指引“當下”的政策研擬。于是學者又倡導創新系統途徑——測量國家圍繞創新的“制度—組織”安排,以期考察、預判各國的創新。但也由于學者既無法確認度量的重點,也未能有效地測量制度安排與組織互動,體系層面的測量方案還不太成熟。基于上述各種途徑的進展與局限,筆者主張,當前度量創新,應以“產出途徑”為主,尤其側重使用專利指標。當然,為了確保測量結果穩健,最好輔以“投入”和“系統”途徑的考察。
上述各類測量途徑不僅為評估我國當下創新水平提供了參考,也為我們提升創新水平提供了思路。未來可以在創新投入、產出和系統三個方面綜合施策。在創新投入方面,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作用,從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需求出發,集中力量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尤其是重點研發具有先發優勢的關鍵技術和引領未來發展的基礎前沿技術,從而在國際上掌握創新和發展的主動權。在創新產出領域,一方面要提升產出質量,在前沿領域掌握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將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新產品與新工藝,從而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在創新系統方面,要加快完善支持創新的國家制度體系,既要發揮政府的政策協調作用,通過財稅金融、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等政策來引導和支持創新發展,又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不同所有制企業提供公平獲得創新資源和參與市場競爭的機會,從而建立優勝劣汰的創新競爭機制。通過上述各途徑的科學施策與綜合發力,有助我國盡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早日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J/OL].求是,2014,(11).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4-05/31/c_1130 154174.htm, 2024-05-31/2024-06-03.
[2]Griliches Z.Patent statistics as economic indicators:a survey[M]//Griliches Z. Ramp;D and Productivity: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3]OECD.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tivities:Proposed Standard Practice for Survey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Paris:OECD,1963.
[4]Schumpeter J A.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5]Adcock R, Collier D.Measurement Validity: A Shared Standard for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1,(3).
[6]Lundvall B A.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M].London:Pinter, 1992.
[7]Schmookler J.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8]Edquist C. Systems of Innovation: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M]//Fagerberg J, Mowery D, Nelson R.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Nelson R R, Rosenberg N.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national system[M]//Nelson R R.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Smith K. Measuring Innovation[M]//Fagerberg J,Mowery D C,Nelson R R.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nov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1]Mowery D C, Rosenberg N.The U.S.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M]//Nelson R R.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Mansfield E.Industri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conometric Analysis[M].New York: Norton, 1968.
[13]Kline S, Rosenberg N.An overview of innovation[M]//Rachel L.The Positive Sum Strategy:Harnessing Technology for Economic Growth. Washington, 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1986.
[14]高昌林.奧斯陸手冊:創新數據的采集和解釋指南[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
[15]Wong J.Bet on Biotech:Innovation and the Limits of Asias Developmental State[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1.
[16]陳瑋,耿曙.政府介入與發展階段:發展策略的新制度分析[J].政治學研究,2017,(6).
[17]Freeman C, Soete L.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3rd edition) [M].Cambridge MA:MIT Press,1997.
[18]Dziallas M, Blind K.Innovation indicators throughout the innovation process: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analysis[J].Technovation,2019,(80).
[19]Teece D.Profiting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1986,(6).
[20]梁細林.專利制度的社會適應性問題研究——以發明專利為主要視角[J].湖北社會科學,2014,(8).
[21]Jaffe A, Trajtenberg M.Patents, Citations, and Innovations:A Window on the Knowledge Economy[M]. Cambridge MA:The MIT press,2002.
[22]Edquist C, Johnson B.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Systems of Innovation[M]//Ediqust C. System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e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2005.
[23][美]安納利·薩克森寧.硅谷和128號公路地區的文化與競爭[M].曹蓬,楊宇光,等,譯.上海: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9.
[24]Cockburn I, Henderson R. 2000.Publicly funded science and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Innovation Policy amp; the Economy,2000,(1).
[25]Edquist C, Johnson B.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in systems of innovation[M]//Edquist C, Mckeley M. Systems of Innovation:Growth,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 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0.
[26]Freeman C.Technology Polic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Lessons from Japan[M].London:Pinter, 1987.
[27]熊鵬,張輝,張承龍.中韓科技創新體制比較分析——以半導體產業和公司為例[J].湖北社會科學, 2022,(9).
[28]European Union.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2020[R].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fice of European Union, 2020.
[29]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 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誰為創新出資?(摘要版)[R/OL].https://www.wipo.int/edocs/pubdocs/zh/wipo_pub _gii_2020.pdf. 2022-09-21/2024-03-21.
[30] [瑞典]克里斯蒂娜·查米納德,[丹麥]本特-艾克·倫德瓦爾,[丹麥]莎古芙塔·哈尼夫.國家創新體系概論[M].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譯.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
責任編輯"" 賈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