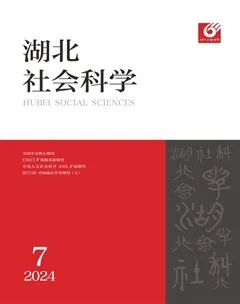書教論
摘要:“書”本指口述及口述史,有文字后兼指書寫及成文史,后世書寫便捷,口述史傳統斷絕,遂僅指書寫及成文史。五帝三代之書是詩書禮樂混雜、口述史成文史混雜的書。西周春秋之交,書寫工具成熟,周朝王官始用方策系統整理頒行記錄“先王陳跡”、體現“先王之道”的六經,五帝時代早中期古史則因為“不雅馴”而被剔除,于是《虞書》《夏書》《商書》《周書》遂專稱為《書》。戰國時代亦有泛指六經為《書》者。漢至清代經學教材雖有調整,但始終以四《書》合編的《尚書》為《書經》,其他不斷增加的海量史書均只用作課外參考書。五千多年的書教,形式一直是“先王陳跡”教育即歷史教育,本質則一直是“先王之道”教育即治國實踐和理論教育,旨在教化官員效法先王,治國富民,并按公認的準則獲取有限的私利。中國歷史記錄十分漫長而完整,且歷來要求“慎終追遠”,反對“數典忘祖”,原因固然復雜,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國歷史一直是后代官員的治國指南,故古人稱“六經皆史”,如今亦可稱“六史皆經”。
關鍵詞:《書》;《尚書》;口述史;成文史;國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477(2024)07-0161-08
收稿日期:2024-02-10
作者簡介:吳天明(1956—),男,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湖北武漢,430072)。
①周公召見天下諸侯的“明堂”,應該建在魯國汶陽之田上。由于春秋時齊國占領了汶陽之田,并一直妥善地保護了周公明堂,所以至戰國齊宣王時代,周公明堂尚存,齊宣王還就是否毀掉明堂征求過孟子的意見。
②史稱周公死后,伯禽將周公太廟與魯國朝堂分開,后成慣例。春秋時代學堂均單設,如《左傳》記載鄭國有鄉校、魯國有鄉學、周王朝有國學。由此推測,四堂分開,可能始于周初周公死后不久。
③春秋魯昭公時代,周天子國學停辦,孔子在孟孫氏資助下舉辦國學,遂為傳統,直至清末。
子夏嘗言:“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1](p2532)這句話總結了中國古代平民教育和君子教育兩大教育體系的基本特點。百工所“居”之“肆”,就是古代手工業者的生產場所、教學場所兼居所;百工所“成”之“事”,則為手工技藝的不斷精進和商業利益的不斷擴大。據中外科技史家和經濟史家研究,中國在明朝以前,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長期位居世界前列,即與百工教育關系密切。
百工學習有“肆”,君子學習有“堂”,就是《禮記·明堂位第十四》所記載的周公召見天下諸侯之類的“明堂”①,那是時任官員祭祖的廟堂、行政的朝堂、行禮的禮堂,也是候任官員學政的學堂。上述四堂很可能在周初開始逐步分開②,遂有專門的學堂。孔子設帳開創了古代民辦公助國學的傳統③,其教學場所亦稱學堂,孔子的學堂就僅僅是學堂。君子所學之“政”即國政,“政”即“正”,只要治國君子公道公平公正,平民百姓自然都會正,上下均正,國家大治,故《尚書·君陳》稱“爾惟風,下民惟草”,[1](p237)孔子亦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p2504)“政”即“文”,五帝1、夏、商、西周時期為詩書禮樂混雜、口述史成文史混雜的“文”;春秋時代始為文本化、分門別類的“文”,即《論語·學而》所謂“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文”,[1](p2458)也就是書面文獻,具體指記錄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歷史2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古代教化嗣君的王官,就是《尚書·舜典》記載的“教胄子”的夔之類的史官、樂官、卜官、禮官3等等;春秋晚期至清末,民辦公助國學學堂的教官,也有明顯的官府背景,與現代普通教師不同。君子通過學“文”所“致”的“道”,也就是九代先王治國富民、有限利己的大道。春秋君子或從歷史記錄的角度稱其為“先王陳跡”“周召之跡”,或從治國實踐和理論的角度稱其為“先王之道”“文武之道”。
在君子學習的治國經典中,《詩》《書》《禮》《樂》四經最為重要4。國學總論,詩教、禮教、樂教等分論,筆者此前已經專門討論,本文只討論書教問題。筆者在使用“書”“書教”這兩個概念時,考慮到五帝、夏、商、西周時代的國學教材還沒有完全文本化,故籠統稱其口述史、成文史混雜之書為“書”,稱其書教為“書教”;春秋時代國學教材均文本化并分門別類,故效法春秋君子,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為“《書》”,稱四《書》之教為“《書》教”;漢初孔安國奉旨將四《書》合編為《尚書》,漢代至今均特稱“《書》”,本文一仍舊貫,稱漢代至今的《尚書》教育為“《書》教”。另外,如果兼稱上述兩種史書,本文則稱“書”;兼稱上述兩種書教,本文稱“書教”,如本文題目所示。這樣表述雖然拗口,但不如此不嚴謹,尚祈讀者諒解。
一、“書”的概念史
研究中國古代的書教史,就要首先研究“書”的概念史,而要研究“書”的概念史,則要從研究“書”這個漢字開始。
繁體“書”字從“聿”,許慎云:“書,箸也。從聿,者聲。”[2](p210)認為“書”就是筆,也指用筆記錄,還指用筆記錄的歷史文獻。箸多為竹制,亦有木制者5。雙支之箸為筷子,《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紂為象箸。”[3](p509)稱商紂王用象牙制作筷子,生活奢侈。單只之箸,先人做筆用,朱自清《背影》有“舉箸提筆”一說,當屬方言存古。五帝時代在尚未干透的陶坯上刻字以記錄先王歷史,待陶坯干透并燒制為陶器,便成為罕見的陶文;夏商西周三代可能用青銅器、石器制作書寫工具,在青銅器和甲骨上刻寫文字,形成寶貴的金文和甲骨文。中國大約在西周春秋之交進入鐵器時代。鐵器遠比青銅器便宜6、鋒利、堅韌,可以廣泛應用于農業、手工業和軍事領域,由此得以迅速推廣,于是先人用鐵制工具預先大量加工制作箸和木板。需要發布政府文告時,便用箸蘸上天然染料,在“方”7即木板上書寫文字,將其掛于城闕之上,一般公示十天,期滿即存入國家檔案館,作為政府日后治理國家的政策法律依據1。春秋時代的王官們還用“箸”在簡牘、絲綢(許慎并稱“竹帛”,今日并稱“簡帛”)上系統記錄早先主要依靠口耳相傳的口述史和正在發生的當代史2,五帝夏、商、西周、春秋九代的傳世文獻六經,就由此而來。那么,根據許慎的上述解釋,“書”字的原始意義是筆,作名詞;先人用筆書寫記錄歷史,故“書”字又是動詞;亦指書寫記錄而成的歷史文獻,也是名詞,許慎稱:“箸于竹帛謂之書。”[2](p210)
許慎這個解釋很可能只包含了“書”字的一部分晚起之意,而并非“書”字的原始意義。
繁體“書”字為上下結構,上部為“聿”,下部為“曰”。《說文解字·聿部》曰:“聿,所以書也。”[2](p210)《說文解字·曰部》云:“曰,詞也。從口,象口氣出也。凡曰之屬皆從曰。”[2](p359)這就是說,“聿”是筆、用筆書寫、書寫之物(成文史)的意思,“曰”是口、口述、口述之物(口述史)的意思。也許在“書”字初創之時,社會上就同時存在口述和書寫兩種情況,時人所學的“書”,就有口述之書和書寫之書兩種。許慎僅僅以“箸”釋“書”,很可能只注意到了用筆書寫記錄文獻這個后起之意,而忽略了用口講述古史這個更加古老的含義,犯了以今釋古、以偏概全的錯誤。
根據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常識,幾乎所有民族早先都依靠口耳相傳的方式記錄歷史;有了文字以后,還會有很長一段同時依靠口述和書寫兩種方式記錄歷史的時間。口述史傳統斷絕,是部分民族很晚近的事情。所以從文化發生學上講,中國的“書”,應該大體經歷了如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五帝時代以前,先人完全依靠口述的方式來講述傳承各自氏族種群的歷史,那時的“書”其實就是口述和口述史。
第二階段,五帝、夏、商、西周時代,先人開始創造文字,但是或者文字還不成熟,或者書寫條件還不成熟,只得仍然以口述為主,以文字記錄為輔,同時采用這兩種方法傳承歷史。所以,如前所述,先人所造之“書”字,應該反映了五帝、夏、商、西周時代歷史傳承的基本特點:那時的“書”,既是筆,也是口;既是文字記錄,也是口述;既指文字記錄之成文歷史,也指口頭傳述之口述史。
第三階段,文字成熟、書寫條件也成熟的歷史時期,口述傳統逐步喪失,口述史基本上都被記錄整理為成文史。就中國的情況而論,春秋時代至今,應該屬于這一歷史階段。近些年,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部分媒體雖然開設了口述史的專欄,制作了一些口述史節目,但是普遍影響不大、受眾較少,最后不了了之。這主要是因為,現代社會書寫已經十分方便,口述史傳統已然喪失,世人早已習慣于閱讀成文史了。許慎對“書”字的解釋,只適用于第三個歷史階段。
上述對“書”的概念史的文字學解釋,并非僅僅是筆者的懸想臆測、向壁虛構,除了有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大量證據可以證明以外,還可以得到中國遠古傳世文獻的有力佐證。《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左史倚相趨過。(楚靈3)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1](p2064)由楚王所述可知,這些古史至少在春秋時代的楚國已經被記錄為成文史了,由于這些典籍自戰國時代至今已經只字無存,后人對楚王所說的古書有很多推測,但均不足為憑。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古書中至少有一部分比華夏列國的傳世六經要古老很多,早期必然是口述史,至晚在春秋時代,由于書寫工具逐步成熟,而被楚國王官記錄整理為分門別類的成文史,所以史官倚相才可能去熟讀這些古史。楚人在被周公逼迫南遷之前,原本是經濟文化非常發達的東夷之一。《左傳》的上述記載,如果放在這個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尤其可信。
最早的傳世文獻是記錄堯舜歷史的《虞書》,但根據近百年的考古成果,結合《荀子》關于五帝的說法,參考《宰我問五帝德》《五帝本紀》,堯舜只是考古學上的古國時代(約當歷史學上五帝時代晚期)的先王。五帝時代早中期尚有黃帝、顓頊、帝嚳三個時代。也就是說,中國遠古時代的口述史,除了《虞書》以外,還應有更加古老的“黃帝書”“顓頊書”“帝嚳書”之類。根據《五帝本紀》關于炎黃古史“不雅馴”1的說法,完全可以推知,黃帝、顓頊、帝嚳時代的古史,因為禮俗與堯、舜、夏、商、西周、春秋六代差距很大,讓后人難以理解,所以口耳相傳至國家開始用方策大量記錄已經口述千百年的“先王陳跡”時,周朝王官或者根本就沒有將其記錄為成文史,或者雖然將其記錄為成文史,但在最終編輯定型并頒行天下時,還是被剔除了“不雅馴”的內容,以致孔子、司馬遷也只能根據零零星星的口述史片段和非常有限的成文史片段來記錄五帝古史。根據《論語》《左傳》《戰國策》的記載,春秋戰國君子言必稱堯、舜、夏、商、西周、春秋六代,而不稱此前的時代,可能就是因為受到了周朝正統史學的影響。從較為晚近的《虞書》原本主要是口述史的情形來看,早先口耳相傳的“黃帝書”“顓頊書”“帝嚳書”之類,原本亦當為口述史,這些推測應符合歷史發展邏輯。
五帝歷史是“書”,夏、商、西周歷史自然也是“書”,同樣,周代華夏列國的史書也是“書”。不過,由于《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文本傳世已久,而《春秋》被列入六經晚至魯昭公時代2,所以《春秋》并沒有被納入《書》的體系之中,只成為與四《書》并列的一經。
總之,無論是從民族學與文化人類學上講,還是從訓詁學和歷史文獻學上講,“書”都當本指口述和口述史;出現文字并具備初步的書寫條件后,才能兼指文字書寫和成文史,古人造“書”字,就體現了這一歷史階段“書”的特點;文字成熟而且書寫條件也成熟,用文字記錄文獻、閱讀文獻成為讀書人的習慣,口述史傳統逐步喪失以后,“書”才能完全專指文字書寫和成文史,只有到了這個歷史階段,許慎對“書”字的解釋才是正確的。
二、“書教”發展史
人類可能在很早的時代,就開始世代傳承自己氏族部落的歷史。但本文所謂的“書”,并非泛指一般信息,而是特指五帝、夏、商、西周時代主要依靠口述,春秋時代用文字系統記載,周代君子反復言及的“先王陳跡”,即中國進入文明時代以后,歷代先王治國情況的歷史記錄;本文所指的“書教”,亦特指對官員(包括候任、時任、卸任官員)進行的以“先王陳跡”“先王之道”教育為主要內容的治國教育。因此“書”和“書教”均與階級、私有制和國家同源,與邦國文明3同源。從理論上講,只要借助考古資料找到邦國文明的起點,就有可能找到“書”和“書教”的源頭。那么,中國邦國文明的起點究竟在哪里呢?
考古學上的賈湖文化距今大約9000—7800年,那時氏族部落聚落的祭司酋長已開始用骨笛教化子嗣如何治理聚落。我們雖不知道其具體教學內容,但可推測應有聚落治理的歷史經驗教訓之類的內容,其教化子嗣的作品,應與后世黃帝時代的組詩組樂《大卷》《云門》類似。當時,階級、私有制和國家尚在發育之中,還沒有真正進入邦國文明時代,那時的“書”還不是本文所謂的治國之“書”,相關教育也還不是嚴格意義上治國之道教育的“書教”。
距今大約5500年的黃帝古城文明,不僅有出土文物可供研究,還有《大卷》《云門》以及傳世文獻《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等予以佐證,所以筆者將中國書教乃至整個國學教育活動、國學理論創造的起點,都初步確定在考古學上的黃帝古城時代,約當歷史學上的黃帝時代4,這應該不至于太保守或太孟浪。
從歷史發展邏輯上推論,黃帝時代以后,歷代先王依次登上歷史舞臺,“書教”教材自然會在“黃帝書”的基礎上,依次增加“顓頊書”“帝嚳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等等。但是由于五帝、夏、商、西周時代的國學教材以口述史為主、成文史為輔,且詩書禮樂混雜在一起,不可能有單獨的“書”和“書教”。
至春秋時代中期,文本化并分門別類的《詩》《書》1《禮》《樂》已經傳世。春秋時代晚期,大約在魯昭公時代,可能經過周朝史官統一協調審定2,華夏列國的史書均被分別納入各國的國學教材體系;《易》也成為與《詩》《書》《禮》《樂》并列的華夏列國國學通用教材。由此來看,《春秋》教實際上也是典型的新書教。可能因為早在《春秋》教確立之前,成文四《書》和四《書》之教就已經至少有上百年的歷史,《書》和《書》教的特定概念早已深入人心;還可能因為,四《書》記錄虞、夏、商、西周治國富民的陳跡,而《春秋》主要記錄列國貴族們“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1](p2504)的故事,其主旨明顯不同,故而周朝史官不把《春秋》納入《書》的體系,而將其單列為一經。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1](p1822)這一史料說明,魯僖公時代,開展國學教育和評價治國狀況,仍然只考慮《詩》《書》《禮》《樂》四教。到了春秋末期的魯昭公、定公、哀公時代,鄉學、家學3的課程設置,很可能已增加了《易》《春秋》,這樣四藝就變成六藝,四教就變成六教了: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1](p1609)4
到了戰國時代,根據《荀子·天論》“萬物之怪,《書》不說”5的記載,[4](p316)可知戰國君子既以四《書》為《書》,也泛泛以六經為《書》;既以四《書》之教為《書》教,也以六經之教為《書》教,只是當時諸子百家對六經之《書》均各有新的解讀而已,其解讀成果就是如今傳世的戰國諸子。
從漢代開始,隨著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的大發展,圖書出版逐步增多,故漢代學者不得不創造目錄學,以方便天下讀書人,并一直影響至今。6綜觀漢代至今的目錄學,不論圖書的具體分類怎么變,但有一點始終完全相同:體現當時中央政府主流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的圖書,一定就是當時中央政府確定的治國經典,就是當時國學候任官員的必修教材、各級政府時任官員的行政指南和所有卸任官員評價國政情況的基本依據。這類治國經典,一定是當時國家圖書目錄中的第一類圖書,而《書》教之《書》始終在第一類圖書中。
《漢書·藝文志》記載,漢朝皇家圖書分為六大類38種,第一大類為六藝,包括春秋晚期、戰國時期的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以及漢朝中央政府新增的《論語》《孝經》《小學》共9種,仍然稱為六藝,也就是漢朝中央政府認可的新六藝;第二大類為諸子10種;第三大類為詩賦5種;第四大類為兵書4種;第五大類為數術6種;第六大類為方技4種。[5](p1701-1784)按照上文所總結的目錄學規律,漢代候任官員治國之學經典教育的必修課教材,就是第一大類的9種教材,其中包括《書》,即孔安國將《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合編的《尚書》(《書經》),《尚書》教育就是漢代的《書》教。
《隋書·經籍志》采取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將漢代的六藝部改稱為經部。經部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書、小學10類。經部之外,另有史部13類、子部14類、集部3類。[6](p903-1104)經部之圖書才是國學學堂的必修課教材,其中的《尚書》才是《書》,《尚書》教育才是教化官員的《書》教。
《四庫全書》沿用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經部包括易、書、詩、禮、春秋、孝經、五經總義、四書、樂、小學10類。經部之外,另有史部15類、子部14類、集部5類。到了清代,中國文獻已經浩如煙海。如同上文總結的那樣,清代國學的治國經典教材,仍然包括在第一類即經部的10類圖書中,其《書》僅僅指《尚書》;清代的《書》教當然也只是《尚書》之教。
從漢代開始,特別是魏晉以后,中國的出版文化事業快速進步,生產出了浩如煙海的圖書。但是這些圖書并非僅僅服務于國學學子,而是服務于天下所有讀書人。國學只培養治國官員,其基本教育內容始終只包括兩類:一是識字讀書等一般的文化基礎知識教育,古代國學教育之所以包括小學在內,就是為了幫助學子閱讀古代文獻,而不是為了培養語言學家,把小學當學問做是后代的事情;二是治國之道教育,即讓學子從“先王陳跡”中領悟“先王之道”。治國官員無須什么都學、什么都懂,更不需要也不可能成為某個方面的專家,他們只需要扎實的文化基礎知識,能夠自主學習先王的治國典籍,知道如何效法先王治國富民、如何按照公認的準則獲取有限的私利即可。故先漢時代的四藝、六藝之教,漢代的新六藝之教,此后的經學教育,才是中國古代國學教育的基本內容,其中的《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及之后合編的《尚書》之教,才是春秋時代直到清代中國的《書》教。
在此需要探討的問題是,漢至清代產生了無數史書,為什么從春秋時代一直到清代的《書》教,始終未將其他史書教育納入呢?筆者認為,可能主要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其一,《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以前的古史,早在春秋時代就已被周代官方剔除,四《書》才是周代官方的正統史學。周代以降,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思想文化主要是周文化,所以即使是《大戴禮記·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也未納入《書》教體系,也未撼動周朝主流意識形態、主流思想文化的統治地位。最近三千年,官方和坊間經常稱中國思想文化為“周禮”“周公之禮”,多實行紅色崇拜等等,皆可佐證本文關于周朝官方以四《書》為“《書》”,以《書》教為“《書》教”的思想長期影響后世的初步判斷。
其二,周朝王官(史官、樂官、卜官、禮官等)將六經最終均確定為治國之經,將《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確定為“書經”,意在昭告天下,四《書》所記錄的“先王陳跡”,體現了“先王之道”。記錄春秋歷史的《春秋經》,其重點已不在講授先王如何治國富民,而在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p2503-2504)故周朝史官不再將其納入“書經”之中。后世史書、史料雖然增加千萬倍,史書形式亦豐富無數倍(例如新增起居注之類),但治理國家的“先王之道”仍然是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治國富民、適當獲取有限私利之道,后世帝王及其他史書在理論上并無新創造,所以后世帝王均未取得“先王”的政治地位,后世史書亦均未取得“書經”的政治地位和學術地位,故國學學堂的《書》教不再新增史書。總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治國君子的核心價值觀,而治國君子的核心價值觀,從來就只是治國富民、有限獲利而已,[7](p114-122)而《書》所體現的“先王之道”,就是帝王的治國之道,這一點在后世并未有根本改變。
其三,隨著經濟建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知識生產只會越來越豐富,圖書只會越來越多,這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即使古代國學學堂愿意將其他史書納入《書》教的范疇,受客觀條件限制(教師和學生窮極一生也無法一一研讀),恐怕也無法實現。
三、經史關系史
中華民族歷史記錄之漫長而完整,中國歷史教育之久遠且綿延不絕,在人類文明史上都是罕見的。這種現象引發了無數學者的關注,但似乎還未有人提出一種極具說服力的科學解釋。或認為這與中國文字發明、書寫工具成熟和中華民族成熟均很早有關,或認為這與中華文明綿延不絕、從未中斷有關。筆者以為,這些思考都有道理,但恐怕都未指明根本原因。
中國漫長的歷史和書教史涉及許多基礎理論問題,在學界的努力下,有些問題已經解決,本文不再贅述。例如書教的教官自然與詩教、樂教、禮教一樣,是歷代王官(包括公辦國學和民辦公助國學的教官),學生自然主要是歷代候任官員。春秋時代以前,學生主要是儲君,即《虞書》所謂的“胄子”;春秋至清代,由于貴族大增,士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大幅下降,必須讀書做官,于是卿大夫的余子即士(也稱儒士)也加入到學生群體中。1筆者在此只想討論三個基本問題:其一,關于“慎終追遠”;其二,關于“數典忘祖”;其三,關于中國歷史記錄(包括書教史)為何特別漫長而完整。這實際上是同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歷史記錄何以如此漫長而完整。這涉及中國經學史和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即經史關系問題。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p2458)這是曾子教化自己門徒的話,他的帳下弟子多是候任官員。曾子告訴弟子即未來的治國君子們,要謹慎地對待自己父母的死亡,還要追懷遠代的祖先,如果君子如此這般遵守古禮,那么就連平民百姓的道德都會歸于醇厚,國家也就很好治理了。父母死亡,兒女自然不會輕忽,但曾子要求治國君子要非常謹慎,這是何故?筆者認為,這與中國從商末周初一直實行到清末的宗法制關系密切。按照這一制度,一般只有嫡長子才是儲君宗子(后),其余嫡子和庶子都是余子(余夫、支子、別子);君父去世,宗子方為喪主,守喪期間,喪主宗子不可改變君父的任何政治安排,包括不可改變政策、不可任免官員;待喪期屆滿,宗子嗣位為新君以后,方可對君父生前的政治安排進行調整,這就是“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1](p2458)的意思。由于君父去世,守喪的宗子事實上已經大權在握,故曾子叮囑喪主宗子務必要“慎”,不能在君父尸骨未寒時,在喪禮期間就“改于父之道”。在宗法制度下,中國非常重視喪禮,因為喪禮最講喪服制度,而喪服制度最講嫡出、庶出,需要非常謹慎,不可有絲毫含糊。父母死亡時,諸子都要非常謹慎地按照宗法制度行事,不可有任何僭越禮制的行為,否則國家必然大亂。例如春秋初期魯國國君魯隱公,乃魯惠公之庶子,而惠公之嫡子為魯桓公。惠公去世,桓公年幼,故隱公姑且攝政,待桓公成年再還政于桓公,與周初周公攝政故事一樣。隱公在位期間,惠公嫡妻即桓公生母、隱公嫡母去世,年幼的桓公方為喪主,所以可以會見前來吊喪的列國諸侯和使臣,而隱公不是喪主,自然不可會見列國諸侯和使臣。這就是“慎終”的意思,“慎”就是要謹慎地遵守周公之禮,遵守宗法制度、喪服制度。隱公在位期間,惠公庶妾即隱公生母也去世,隱公亦不可以君夫人之禮安葬生母,這也是“慎終”的意思。“追遠”就是追懷、效仿遠代先王的治國之道,當然包括宗法制度、喪服制度,如此才能確保權力順利交接和國家安寧。如前文所述,君子如何行事,不僅深刻影響其他君子,還會深刻影響平民百姓,最終影響整體國家治理。顯然,曾子是在教導自己的弟子都要模范遵守周公之禮。而周公之禮究竟如何,《周書》和戰國時代失傳,但春秋時代尚在傳世的周公《周禮》[1](p1861)記錄得十分清楚。后世學者解讀曾子這番話,往往僅就字面意思而論,并未讀出曾子的深意和“先王陳跡”中蘊含的與喪禮有關的重要治國道理。
與“慎終追遠”相反的則是“數典忘祖”。《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晉國大夫籍談出使周朝,周景王責問晉侯為何不貢獻器物。籍談回答說,晉侯未受過周王室的賞賜,“何以獻器?”景王歷舉晉侯受賞的事實,責備籍談“數典而忘其祖”。[1](p2078)后用“數典忘祖”比喻忘本或對本國歷史的無知。春秋戰國時代經常結合其職業給人命名,例如《孟子》記載有一位圍棋高手名曰弈秋,“弈秋”是善于下圍棋的“秋”,“秋”是名,“弈”是職業。同樣,“籍談”是負責管理“籍”而名為“談”的人,“籍”本指典籍和國家重要文獻檔案,轉指管理典籍的職業。晉侯分封、周王賞賜,都是晉國的大事,周王朝和晉國的檔案自然都會記錄,而一個專門負責管理晉國重要檔案的官員,居然不知道周王多次賞賜晉侯的歷史故事,這就是周王責怪他“數典忘祖”的原因。
上述一正一反兩個故事,正好揭示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就是在世界所有國家中,中國的歷史記錄最漫長、最完整、最繁多;而且本朝不僅記錄本朝的歷史,還會記錄整理前朝的歷史;歷史學在中國一直是顯學,修史是官方重要的責任和權力;中國書教史亦同樣漫長。這又是為什么呢?魯迅先生曾說,中國史書只是帝王的家書,固然不錯,說具體一點,應該是記錄帝王家治理天下的史書。所有帝王,在治國富民之外,無不十分重視兩件事情:一是帝王剛剛登基,就開始營造自己的陵墓;二是極其重視歷史記錄和歷史教育,因此我們還可以說,中國的史書,都是各代先王留給儲君的治國教科書和課外參考書。這就是中國向來主張“慎終追遠”、反對“數典忘祖”,歷史記錄十分漫長而完整,書教一直綿延不絕的根本原因。
上述判斷,可以假借春秋傳世文獻予以佐證。春秋君子稱六經,無不稱為“先王陳跡”,亦無不稱為“先王之道”①,“先王陳跡”就是各種形式的史書,“先王之道”就是史書中蘊含的歷代先王治國富民并合理獲取有限私利的準則、規范、常道,周公《周禮》稱“則”,[1](p1861)孔子稱“道”“中庸”。史書就是“史”,治國之道就是“經”,春秋君子認識問題的側重點不同,判斷結果就不同,說法就不盡相同。所以,把“經”與“史”當作一回事,始于春秋君子。戰國《荀子》以為六經皆《書》,清代學者章學誠遂稱“六經皆史”,他們的觀點,其實都源自春秋君子。
參考文獻:
[1]十三經注疏[M].(清)阮元,校刻.北京:中華書局,1980.
[2](漢)許慎.說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3](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4](清)王先謙.荀子集解[M].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5](漢)班固,等.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6](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7]吳天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J].學術界,2024,(1).
責任編輯"" 孔德智
①亦稱“文武之道”,借文武代指所有先王,如《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參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5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