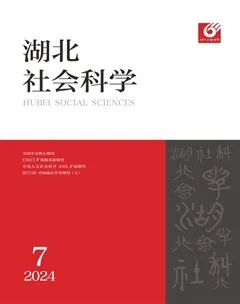商兵互動:武漢城市生成與發展的動力機制
摘要:由于獨特的地理區位,武漢在歷史上不僅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也是“導財運貨”“轉輸貿易”的區域乃至全國性商業中心。戰爭與商業的交互作用不僅塑造了武漢港城一體的空間格局和商兵并重的功能結構,而且使武漢城市氣質和文化精神呈現出敢為人先、勇于斗爭、堅忍不拔、開放包容、功利實用等鮮明的地域特色。
關鍵詞:武漢;戰爭;商業;互動
中圖分類號:K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477(2024)07-0169-08
收稿日期:2023-08-13
作者簡介:涂文學(1958—),男,江漢大學武漢研究院教授(湖北武漢,430056);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特約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9)。
武漢城市的歷史是商兵互動的歷史。因為獨特的區位優勢,武漢在歷史上不僅是軍事要塞,也是“轉輸貿易”的商業大碼頭,因此形成了復合多元的城市功能和獨樹一幟的文化風貌。
一
武漢居天元之位,處戰略要沖,久為兵家必爭之地。誠如康熙《湖廣武昌府志》所云:“鄂州東連吳會,西控夔巫,北枕三關,南引百粵,割寓內之半而為邊。自古兵交,于茲為劇。”[1](p268)縱觀武漢城市史,可以看到,中國歷史上的大規模戰爭,幾乎都與武漢有著或大或小的關系。軍事斗爭催生了這座城市,并深刻影響了城市物質本體形態空間格局。
武漢城市最早因軍事而興。商代盤龍城的軍事意義極為突出,盤龍城擁有內外兩重城垣,其墓葬中還有大量青銅武器,“說明了居住在這里的大小貴族都有自己的武裝,有著當時先進技術裝備的部隊。……有人推斷這里是商人南侵的一個軍事據點,城址是商人在南方建立的一個都邑”。[2](p8)所以李學勤指出,盤龍城“既是一個軍事重鎮,也是一個諸侯封國”。[3](p41-42)
武昌和漢陽作為政治軍事中心城市,無論是創制時期的夏口城、郤月城、魯山城,還是后來的郢州城、鄂州城、武昌城和漢陽城,無不具備郡縣城市城墻環衛、以安屯戍的一般特征。三國時期郤月城、魯山城、夏口城的修筑與戰爭直接相關。郤月城最早就是軍事據點,“城有屯城、治城之別。屯城,臨時屯城,臨時屯軍;治城,則永久治民者也。漢陽于后漢有郤月城,在縣北三里,為黃祖屯軍處”。[4](p43)“江水又東徑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筑,故曲陵縣也,后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吳遣董襲、凌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于此。”[5](p2895-2898)漢魏之際,郤月城既是軍事據點,又是行政中心,曾是沙羨縣、江夏郡治所。康熙《漢陽府志》謂:“獻帝末,沔口為重鎮。劉表使黃祖為江夏太守,表守郤月、沙羨二城,皆在沔口之左。”[6](p84)由于郤月城據有沔水入江口的重要位置,劉表、孫權和曹操都極為看重其戰略地位,孫權認為要守住夏口和武昌,進而西進攻取劉表盤踞的荊州,必須先攻克對岸的郤月城。甘寧曾向孫權建言:“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川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后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7](p1292-1293)曹操認為只有擁有郤月、夏口二城,才能進圖江東,完成統一霸業。因此,“魏江夏郡,西至京山縣東境,東至西陵縣西境與弋陽郡接界。南至漢陽郤月城”。[8](p229)從建安四年(199年)到建安十三年(208 年),孫氏政權與劉表為爭奪郤月城先后進行過三次戰爭,最終以孫權勝利、郤月城易主而告終。郤月城后又有魯山城,“魯山城本劉表子琦所筑,背山向沔。吳程普、蔡遺、陸渙、孫興、孫皎、孫奐、孫承、刁嘉為江夏太守,皆治此城。謂之沙羨,蓋當時漢陽屬沙羨縣也”。[8](p243)
黃武元年(222年),孫權在武昌(今鄂州)稱王即位。他深知夏口戰略地位重要,于是黃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7](p1129)“州城本夏口城,吳黃武二年,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9](p644)該城“依山負險,周回不過二、三里”,[10](p3031)朝臣建議“選名將以鎮戍之”。[7](p1403)南北朝時期的郢州城在原夏口城基礎上進行了改擴建。劉宋時期的郢城是內外兩重城垣的“母子城”,這可以在《梁書·范云傳》中找到佐證,其時一般百姓居外城而駐軍守內城:“父抗,為郢府參軍,云隨父在府。……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云為軍人所得。”[11](p229)555年,北齊占據郢城時,慕容儼曾修繕城雉,有學者認為,其修繕的很可能是內城,因為外城被戰爭破壞了。[12](p32)《湖廣圖經志書》記述得更為明確,夏口城和郢州城“周圍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為重城,設二門,東曰鄂州門,西曰碧瀾門,宋、齊、梁、陳皆因之”。[13](p15)唐代的鄂州城無論是規模還是城防設施都超越前代,鄂州刺史牛僧孺以陶磚代替夯土修筑了新的鄂州城垣。“僧孺至,計茆苫板筑之費,歲十余萬,即賦之以磚,以當苫筑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14](p4470)南宋前期,鄂州城墻多次加固,建炎年間還在黃鵠山頂修建了軍事城堡“萬人敵城”。南宋末年,為了應對蒙軍,重修鄂州城,景定四年(1263年)二月“乙亥,呂文德浚筑鄂州、常、澧城池訖事,詔獎之”。[15](p884)明代武昌城曾有二次大的增修擴建,一次是洪武四年(1371年),“江夏侯周德興因舊城增筑之。城周圍三千九十八丈……門曰大東、小東、新南、平湖、漢陽、望山、保安、竹簰、草埠,共九門”。[13](p15)一次是嘉靖年間,御史顧璘修繕武昌城,并對城門重新命名,其中草埠門改為武勝門,小東門改為忠孝門,大東門改為賓陽門,新南門改為中和門,竹簰門改為文昌門。
至于漢陽城,北宋時期曾數度被洪水沖毀,至南宋時已是無城之城。嘉定年間,漢陽知軍黃榦有感于漢陽無城可守的狀況,曾多次向宋廷申請筑城,[6](p541-542)但并未獲準。朱元璋平定湖廣后即在漢陽筑城,設二千戶所守御漢陽,“漢陽古城,其門有八:東曰迎春,南曰沙洲,西曰孝感,北曰漢廣,而東南為朝天,西北為漢南,東北為慶(賀)〔和〕,西北為下議。環城一千七十二丈”。[16](p67)嘉靖年間,漢陽城得到再次修繕,“嘉靖三年,致仕千戶朱鳳奏筑里城,奉旨,下工部尚書趙璜題覆得旨,時巡撫張公琮、巡按王公秀、參議王公棟、僉事林公燧、漢陽知府孔公鳳計估修筑”。[16](p67)明代統治者多次培修城池,與其對漢陽戰略地位重視有關。時人以為,漢陽墻高城固,不僅使漢陽可以免水患、御戰亂,而且可以拱衛武昌,使其不至于成為一座孤城:“楚自開國以來,武昌為會城,漢陽稱接壤,為右臂。無事則唇齒相依,有事則首尾相應。兩郡對峙在形勝,而設險在城池。”[16](p68)
漢口作為商業城市,長期并無城墻。但缺乏防衛體系的商業市鎮免不了戰火涂炭之苦。太平軍四戰漢口和捻軍兵鋒的迫近,促成了同治年間漢口筑城之舉。“同治三年,郡守鐘謙鈞、前令孫福梅暨紳士胡兆春等建議,就后湖一帶筑堡開濠,上至硚口起,下至沙包止。環漢鎮西北面,缺其東南臨江河處,計長一千九百九十二丈二尺,約十一里許。堡基則密布木樁,堡垣則全砌紅石,外浚深溝,內培堅土。辟堡門七,曰玉帶、便民、居仁、由義、大智、循禮、通濟。建炮臺十有五,其費皆商民籌捐,共銀二十余萬兩。于是漢口恃以為固,而賊不敢入矣。”[17](p138)陽夏分治后,張之洞成立漢鎮馬路工程局,意欲修筑大智門至玉帶門一帶馬路,即有拆城之議,1906年,僅僅存在40余年的漢口城墻被全部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后城馬路。“此路上起硚口,下迄歆生路,長約數里,創始于清光緒三十三年,從前為人跡罕到之處,近則輪軌交通,店鋪林立,幾令人不可思議矣。”[18](p201)
二
戰爭是武漢興起與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如果說武漢城市的興起和城市形態基本格局的形成是因應了軍事斗爭的需要,際會了戰爭的風云;那么武漢的成長與壯大,特別是宋明以后武漢的幾次勃興則主要是商業發展使然。也可以這樣認為,武漢早期的發展是“因武而昌”,中古以后,則是“因商而興”,商業貿易自此以后成為武漢顯著的城市功能。
早在東漢時期,武漢就如蔡邕《漢津賦》所說,“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是“導財運貨,懋遷有無”的商業碼頭。[19](p161)這種商業上的優勢隨著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愈益顯現。從唐代開始,鄂州、漢陽一方面承擔地方行政中心的職能;另一方面開始具備長江航運港埠和商埠的功能,并隨著歷史發展而不斷得以強化。唐代鄂州的港埠功能齊備、轉輸貿易發達,成為長江流域內與揚州、益州、荊州齊名的重要商港。沿江碼頭林立,江上舳艫相連,沿岸街市喧鬧,商賈云集,一派繁盛景象。李白曾多次駐足鄂州,對其繁盛之狀印象深刻,寫下了“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的詩句。[20](p574)漢陽的商業同樣可觀,甚至出現了夜市。詩人羅隱描述道:“漢陽渡口蘭為舟,漢陽城下多酒樓。當年不得盡一醉,別夢有時還重游。襟帶可憐吞楚塞,風煙只好狎江鷗。月明更想曾行處,吹笛橋邊木葉秋。”[21](p843)鄂州與漢陽不再只是軍事要塞或軍港,而且成為商旅輻輳的貿易港口,標志著武漢城市功能開始發生重大轉變。
如果說武漢地區的雙城在隋唐時期已呈現出區域商貿中心的特征,那么這一特征在兩宋時期得到進一步強化,使鄂州在長江中上游地區的政治經濟地位日益突出。這主要得益于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以及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完成。此外,紹興和議后江漢地區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以及長江航運的進一步開發,也促使武漢地區的商業獲得迅猛發展。漢陽“平時十萬戶,鴛瓦白1賈區。夜半車擊轂,差鱗銜舳艫。麥麻漫沃衍,家家足粳魚”。[21](p868)雖然不乏夸張之語,卻也道出了當時城市商業繁榮的盛況。“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阓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22](p141)“南市在城外,沿江數萬家,廛闬甚盛,列肆如櫛。酒壚樓欄尤壯麗,外郡未見其比。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且不問多少,一日可盡,其盛壯如此。”[23](p42)由此說來,鄂州已然扮演了南宋王朝全國市場中心的角色。
明清時期,武漢的整體面貌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延續了上千年的“雙城并峙”被“三鎮鼎立”的格局所取代,明代中葉因漢水改道形成的漢口鎮異軍突起,成為武漢城市發展的最大亮點。漢口憑借兩江交匯、九省通衢的自然稟賦,際會著社會變動的時代風云,一舉成為綰轂南北、溝通東西的集散中心與市場樞紐,在明中后期已躋身四大名鎮之列。清代前期,漢口商業貿易進一步發展,各地旅漢商賈紛紛結成以地域為紐帶的商幫,俗稱“幫口”,于是就有了湖南幫、寧波幫、安徽幫、四川幫、山陜幫等。各幫活動和議事的地方稱為會館或公所。清代中期,漢口的會館、公所多達200余處,可謂萬商云集、市廛櫛比。據統計,清代漢口市場上的商品共有18個大類,320余種。有清一代,漢口的商業行業以“八大行”見稱。“八大行”是指銀錢、典當、銅鉛、油燭、綢緞布匹、雜貨、藥材、紙張八個商業門類,它們的交易額占到當時漢口商貿總額的八成左右。漢口市場之大,不僅表現為商品的豐盈充沛,更表現為商品交易量的巨大。漕糧、淮鹽與竹木材是清代漢口市場上三項規模最大的貿易。此外,漢口也是華中最大的棉花市場和茶葉集散地,其棉花市場規模與蕪湖等地不相伯仲。在20世紀以前,漢口一直是俄國和英國最大的茶葉供應地。時人描述,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也是“云、貴、四川、湖南、廣西、陜西、河南、江西之貨”轉輸集散的中心。“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24](p193)所謂“天下四聚”就是當時中國的四個商業中心,漢口是其中之一,而且是長江上中游及中西部地區最大的商業中心。
1861年開埠以后,漢口市場進一步擴大,成為內地華洋互市的中心。19世紀末,這里形成了一個以土貨出口、洋貨分銷為特征的,規模巨大的國際市場,其影響可輻射湖北全省乃至整個中西部地區。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經漢口出口的棉花占全國輸出總值的40%,茶葉占全國輸出總值的60%;桐油出口在一般年份占全國輸出總值的40%,個別年份占全國輸出總值的60%—80%;牛羊皮、蛋品、腸衣、五倍子、生漆、豬鬃等土貨的年出口值均在300萬海關兩以上。1906年,江漢關統計的漢口港貨物進出口總值約占當年全國貿易總值的12.4%,僅次于上海。[25](p33-43,74-84,146-151)此時的漢口已發展成為內地最大的農副產品出口貿易中心,中西部地區的農副產品主要通過漢口輸往上海或外洋。其進出口貿易(直接貿易與間接貿易合計)長期位居全國通商口岸的前三甲,成為四大口岸或五大商埠之一,時人譽之為“東方芝加哥”。
從“東南巨鎮”到“天下四聚”再到“東方芝加哥”,這是武漢商業貿易發展的千年足跡,它表明:武漢“以商名世”并非始自近世,“因商而興”是中古以后武漢城市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
三
千百年來,武漢在戰爭亂象與商業繁榮間不斷交替轉化,平戰交替的歷史循環,商兵互動的功能與動力機制,深深影響了武漢的城市物質形態、文化品格與城市社會生態。
其一,由于武漢居中的地理位置和濱江的水運優勢,使其成為兵家和商家都看重的勢要之地,城市的一些重要地區往往既是軍事據點,又是商業市場,武漢因此建構起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體系。
郤月城和夏口城不僅是軍事堡壘和地方行政中心,也是重要的商業港口城市。城市功能分區一般是:城——“安屯戍地”,港——“導財運貨,懋遷有無”。如夏口城附近的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5](p2898-2899)王葆心曾以夏口、石陽和黃軍浦為例,對魏晉之際武漢城市的這種商兵兼用功能進行了詳細論述:
三國時,此地為兵爭之據要,夏口南北城名之移易,亦在是時。吾考《三國·吳志·陸遜傳》,知是時有石陽市。《遜傳》有云:“孫權北征,遜與諸葛瑾攻襄陽,瑾督舟師上進,潛遣軍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將軍周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后得闔。”據此,稱石陽市盛,可見當日是地商場之況。按石陽,即東晉之漢陽,為漢陽始置縣,在今黃陂地。然三國時便有是名。《魏志》稱黃初五年,孫權圍文聘于石陽即此。然則石陽今雖在黃陂,實則古漢舊地。其地既有城,又早見于三國時,是亦先有市鎮,而后有邑治,與今夏口同也。《元和郡縣志》稱,故城在縣西二十三里。《黃陂縣志》稱,在今縣北十五里,今名西城子。以圖考之,地去漢口甚近。于方位,在今鎮之東北。在季漢朝,地屬吳魏二國邊境。今鎮有黃陂街之名,沿縣名名之。彼此之石陽市,亦沿石陽城鎮名名之也。今之黃陂街,雖不必由石陽孳乳而來,然當時軍用要地,莫如夏口;商用要地,則石陽也。其時漢水入江故道,與今日有縱橫之殊。又聯湖潴,訥沱夏諸水,其地水勢回環,故東晉又改名曲陽,宋為曲陵,皆寫地勢與水勢盤曲,利于交通。故吳人在此用兵,必多具舟楫。即平時商人舟楫,亦便利可知。宜乎當日市場必建于此也。蓋石陽市,與今武昌內隔以漢水、瀟湘等湖,外又隔以大江,其勢與南岸之夏口、殆與今武漢相倚之勢同也。[26](p6)
這就是說,古代漢陽—石陽同武昌—夏口一樣既是商業市鎮,也是行政―軍事中心(石陽縣―曲陽縣―漢陽縣),無論是吳人用兵抑或商人經商都十分看好其濱江臨湖、舟楫便利的地理位置。而且是先有石陽市,后有石陽縣,縣之治邑是在市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王氏同時指出,魏晉時夏口—石陽這種商兵并用的城市功能格局,與近代武昌―漢陽(漢口)的政治―商業功能格局極其相似。至于魏晉武昌城外之黃軍浦,更是“商地與兵地相維”之地:“典午南來以后,市場應在今夏口,大江南岸,武昌文昌門外,鲇魚套口一帶。按《水經注》云:‘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軍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玩‘商舟所會’一語,知商船所屯,傍岸必有極劇之市場。而水勢又潴曲不流駛,可免風濤,利于系纜維舟者。今套口而水勢回旋,內有湖,旁有洲渚,當是其遺。且是時鸚鵡洲猶在大江中,表里皆便。據《宋書·沈攸之傳》及《通鑒》胡注,知當時有西渚可泊兵,有南堂可校射,是亦商地與兵地相維之證也。又《括地志》云:‘船官浦東對黃鵠山’,《讀史方輿紀要》云:‘船官浦在黃鵠東,自昔為泊舟之所,有船官司之,因名。’皆南北朝時,商埠之所在。”[26](p7)
與商兵并用城市功能相伴隨的是武漢港城一體的城市空間布局。夏口城和郤月城、魯山城的空間布局除了傳統郡縣城市的一般性特征外,還具有港城一體的濱江城市特色。郤月城南倚龜山、北扼漢水入江口,陸地是軍事城堡,水中是軍事港口。夏口軍港規模較郤月城有過之而無不及,據說赤壁之戰時這里屯扎的周瑜水軍多達數萬;夏口的軍港也不止一處,鸚鵡洲、南浦和黃軍浦皆是其重要軍港。夏口、郤月港城一體化的格局,顯示了武漢城市水陸并存并重的城市空間布局特色,陸上城樓巍峨,江畔帆檣十里。是為武漢尤其是漢口聞名海內外的船碼頭之濫觴。唐宋以降,港城一體空間格局得以延續,其港口―碼頭的商業功能增強而軍事作用式微。唐宋時期鄂州有“南市”:在鄂州西南江面與沿岸之間,即鸚鵡洲與鄂州江岸之間的狹長帶狀水域,形如一條內河,并延伸到巡司河河口一帶,江面港灣與江岸街市連為一體,具有港市合一的特點,又稱為“南浦”。它既是商船停泊之所,又是商品交易之地。唐時的鄂州,實際上存在水上和陸地兩個世界,“城周卅里……商侶便填,水陸居人三萬余戶”。[27](p10-14)元代初年,武昌港埠商旅云集,帆檣林立,“巉然壁立邊江城,黃州鄂州勢相爭”。[28](p266)明清時期,武昌作為湖廣會城,不僅是四級官衙薈萃之所,也是八方商旅駐足之地。城內的長街(今解放路)是武昌城商業精華之所在;城外,從漢陽門往南至鲇魚套一帶,江邊碼頭橫陳,帆檣林立,而鲇魚套至中和門一帶因毗鄰白沙洲和巡司河,更是繁榮的水陸商市。漢口自明代中后期成鎮后,沿漢江一帶,河中碼頭一字排開,岸上河街鱗次櫛比,“石填街道土填坡,八馬頭臨一帶河。瓦屋竹樓千萬戶,本鄉人少異鄉多”。[29](p132)除岸上生意外,水上貿易也十分興盛,“其外濱江,舳艫相引數十里,帆檣林立,舟中為市”。[30](p30-37)“19世紀中期,全中國的河運、海運中達到50噸位以上的帆船合計約有22000只,包括小船在內據推測有20萬只。據說每年出入漢口碼頭的共有1萬只船,但這似乎只是大船的數量。較為可信的數字則是:此地交易量最大的物資是鹽、茶、米,而從江蘇來的運鹽船一年有15000只,一年四季都在1500―2000只,一條船裝鹽166噸。據說,在漢口設置十多家代理店的被稱為‘運商’的食鹽批發商、貿易商每年雇傭1.1萬人充當船長及水手,因此,相當于每家商家約雇有18人。另外,眾所周知的是:每條船上有六七名船員,則每年就有165000船戶到漢口來。”[31](p119)“競流漢水趨江水,夾岸吳城對楚城。十里帆檣依市立,萬家燈火徹宵明。梁園思客偏多感,直北滄茫是帝京。”[18](p615)清人吳琪這首詩,便是明清時期漢口港城一體空間格局的形象寫照。
開埠后,現代交通的注入和國內外航線的廣泛開辟,使漢口成為一個繁忙的國際性商業港口城市。據江漢關統計,1882—1891年“十年里每年進入漢口港的船只23500艘,總噸位達1000000噸,運送旅客165000人”;[25](p22)“1890年進出漢口港的輪船和貨船總噸位是1226980噸,比1889年增加146009噸,1891年又增加了48690噸”。[25](p4)1912—1921年十年間,進出漢口的各國輪船達169229艘次,總噸位達63430999噸,平均每年的總噸位較之19世紀末增加了6倍。[25](p113)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進出本埠的船只數量和噸位基本保持穩定。1922年在江漢關注冊的船只有12802艘,總噸位7408838噸,1931年分別為11176艘和7448362噸。1928年是創紀錄的一年,出入港口的船只有14260艘,總噸位8869999噸”。[25](p151)與國內外航線廣泛開辟相伴隨的是一大批碼頭、倉庫、堆棧的興建。至20世紀30年代末期,漢口港口的碼頭形成了三分的格局:硚口至龍王廟漢江沿岸,為小輪船碼頭和木船碼頭;龍王廟至江漢關沿岸,為中國輪船公司興建的干線碼頭;江漢關以下江岸為外國輪船公司開辟的碼頭。全面抗戰前夕,漢口一帶的中外庫場堆棧總計達到146座,其總容量約20萬噸。[32](p561)碼頭、貨棧的修筑,不僅強化了漢口港城一體的城市格局,而且進一步提升了漢口城市功能。1892—1901年的海關十年報告說:“截至過去兩三年里,外國居民還只有290000平方碼的土地,而現在外國人實際借用或正在租借中的土地面積差不多有1428489平方碼。現代化的改造也逐步展開;電報已經開始運營,不久電燈也會得到廣泛使用。除日本租界外,外國人占據的河岸長1000多碼。京漢鐵路車站附近長達1235碼的堤防工程已經竣工,一些大的貨棧也已落成,一座遠洋輪船能停靠的碼頭正在擬議中。……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近幾年漢口是在以多么巨大的步伐向前邁進。這里不再是一般的通商口岸,它已發展成為帝國極為重要的商業都會。”[25](p32)
其二,商兵互動,治亂循環,還使武漢成為一座極富韌性的城市。每一次兵燹或天災過后,城市都能從廢墟中迅速恢復,使喧囂繁華的煙火氣重新彌漫在市井間。
明末戰亂,漢口盡成灰燼,但不到30年,漢口便于康熙年間再度崛起,成為“天下四聚”之一。當時,不少文人雅士游歷漢口,驚訝于該鎮醫治戰爭創傷的速度,留下了一些膾炙人口的詠嘆之作。如“漢口通江水勢斜,兵塵過后轉繁華”,[17](p273)“雄鎮曾聞夏口名,河山百戰未全更”,[17](p273)皆不惜以夸飾而細致的筆墨描繪漢口富庶紛繁的萬千世相。1810年,漢口曾發生過一次燒毀數萬家的大火災,但災后重建工作非常迅速且卓有成效。“漢口鎮,商賈居民湊雜,戶以十萬計。嘉慶十五年庚午春,大火延爇,殆數萬家。街市中截,彌望盡成焦土。然以貨物所集之區,不難重構。一月之內,室堵齊興,凡百販鬻,俱復其常。”[26](p18)辛亥陽夏之戰,馮國璋采火攻戰術,漢口除租界外皆成焦土。但武昌起義后僅僅三年,“到1914年,城市80%得到重建”。[25](p137)
武漢城市屢戰屢毀、屢毀屢建,乃是多種因素使然,筆者以為其中有兩大因素尤為重要。一是武漢獨特的交通樞紐地位和商業物流中心功能,促使市場經濟規律以一只看不見的手,快速推動著城市的重建與市場的恢復。1912年初“漢口城的廢墟仍在冒煙,貿易前景令人沮喪。盡管交通嚴重受阻,城區還在遭受蹂躪,但1912年的貿易總值居然創歷史紀錄,超過155000000兩,而1910年只有152000000兩。在如此動蕩多變的政治、經濟背景下取得這一成果是中國人民治愈力的一個很好說明,也是漢民族商業活力的一個例證。”[25](p107)同樣的情況在大革命高潮過后的1928年也出現過,漢口商業的驚人活力讓海關人士驚詫莫名:“上年本埠多故,商業凋敝,財政紊亂之余,今年尚如此優越,殊出意料之外。在最佳年份,該埠稅收不過550萬兩有奇,上年降至不及300萬兩,本年乃有510萬兩。貿易估值共有37,750萬兩。上年只有25,370萬兩。……中國商人慘淡經營,具有不折不撓之毅力也。”[33](p328)二是社會主體的多元參與,形成了推動城市重建和復興的合力,尤其是當政府和國家缺位時,民間與社會及時跟進,主動承擔起城市重建和經濟復蘇的社會責任。武昌起義后,湖北軍政府乃至南京國民政府都曾高度重視漢口重建問題,孫中山多次強調,“務使首義之區,變為模范之市,有厚望焉”。[34](p68-69)但由于官僚體制痼疾作祟和重建經費無著,由政府主導的漢口重建工程只修筑了幾條馬路,街道、市場和居民區的建設始終停留于紙面規劃。于是,漢口商務總會等漢口民間組織主動作為,修路建房。經過將近5年的建設,在西起歆生路(今江漢路)、北抵鐵路邊(今京漢大道)、東至大智門馬路(今大智路)、南到保華街和湖北路(今中山大道)的范圍內建起店鋪及住房數百棟之多。這些新建房屋大多為西式洋房,區內街道鋪以碎石,并鋪設了下水道,形成了整齊的馬路和成片的里弄,成為租界和特別區以外華界唯一整齊的住宅區,因此被時人譽為“模范區”。
其三,歷史上的戰火烽煙雖已散去,但金戈鐵馬的戰爭往事、豪杰迭起的軍事敘事構成武漢厚重的城市記憶,亦深刻影響了武漢的城市性格與文化風貌。
首先,敢于嘗試,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戰爭是一個充滿變數、復雜艱險的過程。長期戰爭環境的歷練,培養了武漢人處變不驚、鎮定自若、應急能力強、決斷水平高的獨特稟賦和堅毅品格。
其次,漢口非行政中心的地位和轉輸貿易的商業功能,孕育出了不同于傳統農業—宗法—儒學正統文化的新的商業—城市“亞文化”。與農業―儒學文化的重農輕商、重義賤利、崇儉黜奢相反,漢口商業—城市文化的重商傳統、逐利意識與奢靡習尚十分突出。“夫逐末者多,則泉刀易聚;逸獲者眾,則風俗易隤。富家大賈,擁巨資,享厚利,不知黜浮崇儉為天地惜物力,為地方端好尚,為子孫計久遠;驕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戶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羨慕,既而則效,以質樸為鄙陋,以奢侈為華美,習與性成,積重難返。”[35](自敘p1)美國漢學家羅威廉也注意到18世紀以來的漢口社會秩序與傳統城市大相徑庭:“在我們研究的時段里,盡管漢口是個形形色色、魚龍混雜的城市,但本地居民和往來客商在談起所謂‘漢口特性’時有著驚人的一致。漢口最引人注目的第一個特征就是極度的世俗化,其最典型的表現則是窮奢極欲,相互攀比以夸豪斗富。可以想見,這通常會遭到儒家文人們的譴責,他們指出:漢口的生活方式與儒家倡導的‘儉樸’精神背道而馳。”[36](p19)我們注意到,羅威廉用了“漢口特性”這個詞匯,并直指其特征是“極度的世俗化”。這似乎表明,前近代時期漢口社會文化所具有的某種范型意義,而且,“極度的世俗化”表明漢口的社會文化遠離傳統政治宗法文化而逼近近代市民文化。
再次,武漢(漢口)“轉輸貿易”的商業形態表現出商業—文化的高度流動性。這種流動性包括商品的流動性、人口—社會生活方式的流動性以及文化的流動性三個方面。第一,商品的快速流動帶來的商品本身涵蓋文化信息的匯集,特別是在近代文化本身作為一種商品的時候,商品的文化信息更重,漢口成為演示各種文化的大舞臺。第二,商人流動帶來的不同區域的異質文化經過漢口中轉又流動到其他區域,使武漢的碼頭不僅轉輸商品,也轉輸文化。第三,商品、人口和文化的流動,使武漢這個移民城市產生了異乎尋常的文化寬容性。這種文化寬容性,使得武漢市民帶有一種普遍的變革、趨新意識,如漢口市民民國初年追捧新劇(話劇):“國人心理崇尚新劇,前新民所排之《大香山》,社會趨之若鶩,而大舞臺之座殊覺冷淡。后大舞臺排《潘烈士投海》與《情天恨》等劇,武漢人士亦喜趨之,而新民之座不覺頓減,可見人心世道,好奇喜新,此其證也。”[17](p75)城市文化因此而呈現時尚浪漫的多彩風貌,并成為向內陸傳播近代西方文化的橋梁。
復次,商業與碼頭文化另一突出特征是鮮明的市場取向和強烈的競爭意識。“生意分行三百六,同行要比別行強。行兇打架天天有,霸道無如踩石坊。”[35](p115)商業社會的競爭,有的是產品質量的競爭,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良性競爭。如漢口的關帝廟街有一個創始于清同治年間的蘇恒泰紙傘,在與同業的激烈競爭中靠質量和技術的改進提高占據市場主流。到1911年,“蘇恒泰”與“葉開泰”“老九如”“牛同興”等齊名,成為漢口十大名牌之一。良性競爭之外,亦存在以惡性競爭“打碼頭”的情形,如湖南李氏商人先后開辦“正大”“華豐”綢布店,以降價促銷方式與老字號“謙祥益”爭奪漢口市場,最后血本無歸。商業競爭的殘酷性,毫不遜色于碼頭幫派勢力的武斗火拼。
最后,商業與碼頭文化的流動性和競爭性,與戰亂頻仍、動蕩不居的戰爭環境相互疊加影響,形成了武漢(漢口)市民的功利主義價值取向。武漢“山少水多,坎流之性有余,艮止之性不足,故地無團結之氣,人亦少團結之心,其不植私黨者道在此,其不能合群者道亦在此”。[18](p34)社會文化氛圍重商輕文、重利輕藝,商人、市民只注重商業利潤,而忽視教育文化,使得漢口商業繁盛、文化貧乏,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嚴重失衡;漢口商人對投資小、周期短、見效快的轉輸貿易和小本經營津津樂道,而對投資額大、見效周期長的近代工業投資則缺乏興趣。以至張之洞招商興辦工礦企業時,漢鎮商界應者寥寥。張之洞無奈發出“華商力微、識近,大都望而卻步”的喟嘆
由是觀之,“商”與“兵”的互動,無論對于武漢城市物質形態的生成,抑或對城市文化品質的打造,都產生或積極或消極、或正面或負面的多重影響,使得武漢城市文化呈現多元、繁復、駁雜的面相。武漢人既敢于斗爭,亦精于算計;既注重契約,亦追求功利;既敢為人先,亦缺乏遠見;既變革趨新,亦膚淺浮泛。然則正是這種“商”“兵”互動下形成的多元復雜的文化風貌卻使得武漢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尤其是在近代轉型變遷的歷程中始終占據著一席重要之地。尤其是推翻二千年君主專制,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辛亥革命,更是“商”“兵”互動的絕佳注腳。“商”所形成的有主見、敢參與、善競爭的城市性格特征以及參與意識、民主自治意識,“兵”所帶來的“敢為天下先”、處危不驚、應急能力強、敢于斗爭等等,都為資產階級革命厚植了爆發和勝利的豐沃土壤。
參考文獻:
[1]武漢市地方志辦公室.清康熙湖廣武昌府志校注[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
[2]陳賢一.武漢三千五百年前的古城:介紹商代盤龍城遺址(之一)[J].武漢春秋,1984,(2).
[3]李學勤.盤龍城與武漢市的歷史[M]//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武漢市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武漢城市之根:商代盤龍城與武漢城市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
[4]武漢市漢陽區地方志辦公室.新輯漢陽識略校注[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2.
[5](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疏[M].(清)楊守敬,熊會貞,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6]武漢市漢陽區地方志辦公室.康熙漢陽府志[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4.
[7](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8]潘新藻.湖北省建制沿革[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
[9](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M].賀次君,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清)顧炎武.顧炎武全集:10 肇域志(五)[M].譚其驤,王文楚,朱惠榮,等,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1](唐)姚思廉.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12]王素.南朝夏口地區社會經濟雜考[M]//中國唐史學會,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古代長江中游的經濟開發.武漢:武漢出版社,1988.
[13]〔嘉靖〕湖廣圖經志書[M].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
[14](后晉)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5](元)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7.
[16]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M].武漢:武漢出版社,2007.
[17]徐煥斗.漢口小志[M].張博鋒,尉侯凱,點校.武漢:武漢出版社,2019.
[18]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武漢圖書館.民國夏口縣志校注[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0.
[19](唐)歐陽詢.藝文類聚[M].汪紹英,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0](唐)李白.李太白全集[M].(清)王琦,注.北京:中華書局,1977.
[21]武漢市漢陽區檔案館(史志研究中心).同治漢陽縣志[M].武漢:武漢出版社,2019.
[22](宋)葉適.葉適集:第1冊[M].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1.
[23](宋)范成大,等.吳船錄(外三種)[M].顏曉軍,點校.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
[24](清)劉獻廷.廣陽雜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7.
[25][英]穆和德,等.近代武漢經濟與社會——海關十年報告(江漢關)(1882―1931)[M].李策,譯.香港: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1993.
[26]王葆心.續漢口叢談 再續漢口叢談[M].陳志平,張志云,余皓,等,點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27]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古文獻編輯委員會,英國國家圖書館,等.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第2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28](元)顧瑛.草堂雅集[M]//(清)永瑢,紀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29](清)范鍇.漢口叢談校釋(第2版)[M].江浦,等,校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0](清)章學誠.湖北通志檢存稿 湖北通志未定稿[M].郭康松,點校.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31][日]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M].布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2]皮明庥,歐陽植梁.武漢史稿[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
[33]江漢關年報、貿易報告(續1927—1946)[M]//曾兆祥.湖北近代經濟貿易史料選輯(1840—1949):第2輯.武漢:湖北省志貿易志編輯室,1984.
[3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M].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北京:中華書局,1982.
[35](清)葉調元.漢口竹枝詞校注[M].徐明庭,馬昌松,校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36][美]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M].魯西奇,羅杜芳,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
[37](清)張之洞.張之洞全集:3[M].趙德馨,主編.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責任編輯"" 孔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