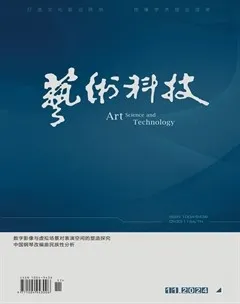德彪西音樂中的“水”
摘要:目的:文章旨在厘清德彪西的音樂作品與印象主義繪畫、象征主義文學之間的區別,揭示其中的音樂因素與非音樂因素的關系,進而更合理地理解其音樂作品的內涵。方法:文章聚焦于德彪西關于“水”的音樂,并選取相關作品進行分析,引入聯覺心理機制,梳理德彪西音樂中“水”與其他感官印象的關系、“水”的不同形態及同種形態間的異同。結果:德彪西有關“水”的各類音樂作品中既包含視覺印象,又包含象征意義。德彪西作品中獨特的音樂音響組織形式能與其音樂的“模糊”特質構成聯覺對應關系,然而是否能夠引申出“水”的畫面與意義,需要非音樂因素的引導。結論:文章研究發現,以聯覺反應為基礎理解德彪西音樂中的“水”的畫面感和象征意義,再結合標題、創作背景、故事情節等非音樂因素,才能更合理地推斷音樂的畫面與意義。
關鍵詞:德彪西;音樂;水;聯覺;印象;象征
中圖分類號:J6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4)11-00-03
0 引言
人們常以印象主義定義德彪西的音樂,“水”即典型例證之一,水的光影印證了它的“印象”屬性。也常有人以象征主義解讀其音樂中的水,水作為一種意象時,能從中歸納出“象征”屬性。但德彪西本人反感以印象主義解釋其音樂,“這些傻瓜稱之為‘印象主義’,不可能有比這個術語更不恰當的了,尤其是被藝術評論家所用”[1]11。同時,德彪西從未將自己的創作歸入象征主義的流派。本文對德彪西音樂中的“水”進行分析,揭示其中音樂因素與非音樂因素的關系,希望能為更合理地理解德彪西音樂中的“水”提供一些思路。
1 “水”中的視覺印象
一些研究致力于尋找德彪西音樂中類似印象主義繪畫的畫面感。以“水”為例,水變幻無常且能映射萬物光影,這與印象主義的精髓契合,但正因如此,人們容易過度分析音樂中的“水”如何表現色彩光影,所以重新思考其合理性十分必要。人類社會存在一種“普遍性的人類心理活動規律”[2]127——聯覺,“聯覺是音樂音響與其表現對象之間的中介環節”[2]127,音樂的高低、強弱等成為音樂理解共同性的基礎,如德彪西音樂具有模糊朦朧之感為人們所公認,這就是由聯覺導致。但“能夠與音樂具有聯覺對應關系的感性特征,常常不是確認一個對象的唯一感性標志或關鍵標志”[3],若要將聯覺機制引起的模糊朦朧之感進一步想象成一幅較為具象的畫面,則需依靠標題等非音樂因素。
引入聯覺的目的在于,德彪西特有的音樂音響組織形式與這種模糊構成聯覺對應關系,但究竟是“水”還是其他感官印象,取決于音樂之外的非音樂因素。標題是其中重要的一類,“值得指出的是,標題或解說對明確音樂與其表現對象之間的對應關系以及對哲理性內容的反思起著重要的理解定向作用”[4]。以下以德彪西具體的音樂作品為例進行分析。
《水中倒影》中的全音階是音樂具備模糊朦朧感的關鍵,由于全音階相鄰兩音間都是一個全音關系,調性游移不定;琶音也是音樂產生模糊感的重要原因,波浪形琶音與水波線條構成運動起伏上的聯覺對應關系;空五度和弦由于三音的缺失,也可帶來模糊的音響效果,與水中倒影的模糊能夠構成聯覺對應關系。此處對畫面的解讀能夠如此具體,得益于標題的限定,在“水中倒影”的規定下,波光、游魚等畫面是合理的推斷。然而,如果去掉標題,只保留來自音響形式的聯覺作用,是否還能如此想象?也許有人會聽出水波蕩漾,也有人會聽出月影朦朧。《月光》中也有大量短琶音或波浪音型,能夠使聽者產生相似的模糊聽覺感受,但此處究竟是水中月還是月下水?若不看標題,回答哪一種都不為過。可見,當標題限定為“月光”時,聽者便會不自覺地想象以月為中心的畫面,反之亦然。因此,標題這種非音樂因素具有明確具體印象的作用。
除視覺印象外,其他感官印象也能與音樂構成聯覺對應關系。《飄蕩在晚風中的聲音與香氣》中不斷起伏的音型即飄散四處的聲音和氣味,這依然是標題限定的結果。由此可知,德彪西音樂中任何一種縹緲之物似乎都可以成為合理的想象,至于它是月光、水波還是聲音、氣味,都須靠作曲家給出的非音樂因素來間接指明。
2 “水”中的象征意義
德彪西的不少作品都與象征主義詩歌相關,有大量研究者將其與象征主義文學相聯系。象征是指“一個客觀對象代替另外一個……也指用具體的意象(imagery)去表達抽象的思想感情”[5],據此,意象通常具有象征的作用。因此,當“水”從一幅畫變為一個意象時,人們試圖解釋它所蘊含的深意,加之德彪西與較多象征主義文人的交往,似乎也印證了如此解讀的可行性。但通過第一部分的論述可知,音樂音響產生的聯覺不能等同于某種具體意象并承擔象征作用,若要得出具有象征意義的結論,也需要非音樂因素的支撐。關于德彪西音樂中“水”的象征含義,《德彪西的巴黎:美好年代的鋼琴肖像》中有如下闡釋:“ (水)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完美容器。水似乎是許多記憶、影子和夢想的象征性容器。”[6]這種“介于兩者之間”正是在模糊之上延伸出的象征意義,可從以下兩個角度分析。
2.1 不同形態的“水”
德彪西音樂中的“水”有“雨”“水面”“霧”
“雪”“海”等多種不同形態。
《雨中花園》顯然是歡快活潑的夏季暴雨,體現在幾乎全曲一致的十六分音符或八分音符音型及結尾的驟停上,聯覺能夠讓聽者感受到動感與活力,而標題點明了雨。曲中引用《我們不再去森林》《睡吧,孩子睡吧》兩首法國童謠,約定俗成地給人以孩子天真爛漫的音樂理解,因而它們也作為一種非音樂因素,指引聽者對“雨”的形態及氛圍產生更具體的想象。但此處的“雨”是否具有“介于兩者之間”的象征意義,依據現有的信息,筆者認為不足以得出此結論。《水中倒影》的模糊感能夠讓人們聯想到展現平靜水面的印象主義繪畫,但似乎仍不足以稱之為一種象征。再以交響素描《大海》第一樂章《海上,從黎明到中午》為例,開頭部分就體現出聯覺,長笛透亮的音色及上下起伏的波動,讓人好像感覺到晨曦照得海面波光粼粼,高音的豎琴似是海面上跳動的陽光,小提琴組小音程的波動使人產生微波蕩漾的動感,大提琴在低音區的運動如同來自海底深處的暗流。同樣,如此解讀依舊不能忽略標題的作用。此處更多僅是對海的形象描繪,并無象征意義。《雪花飛舞》中,盡管兒童的屬性和飛舞的姿態反映出樂趣,雪花一直在十六分音符的重復中上下翻飛,但小調調性又讓持續的憂郁潛伏在不斷降雪的背景下,這可以理解為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象征。《霧》采用雙調性創作,高聲部以?C大調為主,低聲部以C大調為主,因此兩聲部之間常出現小二度對立,整體的調性模糊。然而,盡管和聲調性上相互矛盾,聽感上卻沒有強烈對抗的感覺,德彪西很擅長將對立融合,這正是“水”作為“介于兩者之間”的象征的表現。
《佩里亞斯與梅麗桑德》中的“泉水”主題也可作為一例進行分析。歌劇故事本身就具有顯著的象征主義風格,第二幕第一場的泉水主題由弦樂奏出,曲調在整部歌劇中顯得格外靈動而充滿朝氣,“泉水”在這里也因為情節被賦予了特殊的象征意義——“盲人泉”傳說能使失明者重見光明,可現實并非如此,希望與荒廢并存。這一場佩里亞斯和梅麗桑德在泉水邊談笑,當天是難得的好天氣,泉水主題的和諧優美正對應這層戲劇含義。然而,梅麗桑德與戈洛結婚的戒指掉進了泉水、盲人泉實則不能使人復明都預示著未來的不祥,泉水主題展示出的一片祥和只是“表”,象征暗示的不祥才是“實”,結合劇本文本使泉水主題具備雙重意義,其象征作用在情節的輔助下得以明確。
由此可見,德彪西音樂中形態各異的“水”并非都可以進一步解讀出象征意義,同樣要基于音響形式引起的聯覺反應以及相關的非音樂因素的引導才能展開。
2.2 同一形態的不同象征
第一類,雪的形態。《雪中足跡》中的雪完全不同于《雪花飛舞》中的雪,這里的雪更接近冰。“有理由揣測,最終導致德彪西于1918年3月25日去世的嚴重疾病的初期癥狀,早在他創作《前奏曲》時就顯示了,它喚起了《雪上足跡》中那種對死亡的音樂性預感”[1]9,這種象征意義可以對應于音響組織,全曲彌漫的孤獨絕望在一次次緩慢上行后又跌回原點,直到音樂終以D-G的連續下行結束,打破所有希望。
第二類,海的形態。歌劇《佩里亞斯與梅麗桑德》中的古老王國地處海邊,因此該故事中的海洋是極具象征意義的意象,大海與故事中的未知時空一樣代表著難以估計的神秘力量,情節和歌詞與音響形式構成聯覺對應關系,表現海的音樂也自然而然地被賦予更多含義。第三場,主人公來到海邊巖洞尋找戒指,以佩里亞斯的一段宣敘調來描述場景,“這里真黑,無法將洞口分辨清晰,到處黑漆漆的,天空沒有一顆星星”等,第二幕第二、第三場間的間奏曲也與這樣的描述完美相連。“憤怒的大管在低音區徘徊,大提琴則奏著顫音。然后雙簧管、英國管及單簧管以帶有鼻音的音色營造了風與海的哀聲”[7],音樂既在漸強漸弱中發展,又在整體上保持平靜。
鋼琴作品《水妖》、管弦樂作品《海妖》都與海的古老傳說有關。《水妖》的創作靈感源于拉克漢姆為兒童讀物所畫的插圖,原作品為弗里德里希創作的Undine。“Undine”是歐洲傳說中的水中精靈,也具有“介于兩者之間”的象征性,其同時是“邪惡”和“美麗”的縮影,這就明確了音樂的象征意義,使聽者在聯覺作用下進一步產生聯想。《水妖》開頭音里的二度關系以及第四小節突然出現的三全音象征水妖的形象以及悲劇的結局。《海妖》類似,其中無詞女聲合唱象征著誘惑者捕獲過往的水手,象征她們作為善與惡的集合體。
可見,德彪西音樂中的“水”有多種形態,每一種形態又會因為不同的非音樂因素表現出不同的形象特征,而象征的有無和程度必須以非音樂因素為依據。就影響象征的程度而言,通常故事(傳說、劇情或歌詞)相比于標題與音響組織形式的關聯更為緊密。
3 音樂之“水”以聯覺為先
上文實際上是從兩個方面對此問題進行論述。一方面,明確德彪西音樂中的“水”與其他“印象”間的界限,進而在“水”的范圍內區分其多種形態,可以發現同種形態也會因不同類型的非音樂因素各異。另一方面,從德彪西“水”之音樂和繪畫、文學的區別著手。德彪西音樂中的“水”與視覺印象存在區別,其音樂的模糊性除了視覺印象外,還可表現其他感官印象。德彪西之“水”與作為語言藝術的象征主義文學相區別,其有無象征及程度,須考量非音樂因素及其與音響組織形式的關聯程度。若夸大或首先考慮非音樂因素,則會落入以畫面描繪和意義解讀為初衷及目的的境地,因此明確音樂音響特征與作品中非音樂因素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特別是在鑒賞和分析德彪西的音樂時。
因此,對音樂作品的鑒賞應當將聆聽置于首位,因為直觀可感的聯覺反應來自音樂本體,而往往只有作品中的非音樂因素才能明確作品中具體的形象以及形象背后的象征意義。因此,在欣賞和理解德彪西音樂中的“水”時,也應以聯覺為先,進而適當地根據非音樂因素加以聯想。反之,如果不首先考慮音樂音響組織,而是從非音樂因素出發分析,則是本末倒置。
4 結語
德彪西有許多關于“水”的音樂作品,歷來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分析其畫面和象征意義。本文通過梳理德彪西音樂中的“水”與其他感官印象之間的關系、“水”的各種形態及同種形態間的異同,重新思考其與印象主義繪畫及象征主義文學之間的區別,認為對其畫面感和象征性的理解首先要建立在對音樂音響組織形式的聯覺反應基礎上,再結合作品中的標題、背景、情節等非音樂因素進行,才能更加合理地推斷畫面與意義,如此也能更好地鑒賞德彪西的音樂作品。
參考文獻:
[1] 麥可·斯特格曼,麥可爾·貝洛夫.德彪西前奏曲 第1集
中外文對照[M].李曦微,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11,9.
[2] 周海宏.音樂與其表現的世界:對音樂音響與其表現對象之間關系的心理學與美學研究[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04:127.
[3] 張前.音樂美學教程[M].上海: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133.
[4] 周海宏.同構聯覺:音樂音響與其表現對象之間轉換的基本環節[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0(2):59-64.
[5] 查爾斯·查德維克.象征主義[M].肖聿,譯.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1-2.
[6] 凱瑟琳·考茨基.德彪西的巴黎:美好年代的鋼琴肖像[M].馬里蘭州拉納姆:羅曼與利特菲爾德出版社,2017:169.
[7] 梅西安.節奏色彩和鳥類學的論著:德彪西的音樂[M].張惠玲,鄭中,譯.上海: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9:68.
作者簡介:康霽昀 (2000—),女,研究方向:西方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