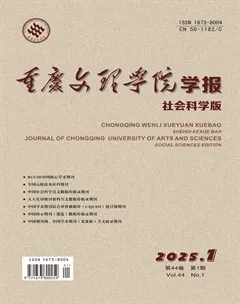李德裕平泉書寫與宋代平泉文學景觀的持續建構
【摘" "要】 晚唐名相李德裕創作了大量書寫私家園林平泉莊園的“平泉詩”,以花木、動物、奇石等景觀為中心,營造出一個五光十色、精彩紛呈的“物質世界”,體現出對物的迷戀和仕隱的苦惱,即李德裕不僅建造了現實的園林,還通過缺席的書寫構建了自己的精神空間。在宋代,平泉故事成為文學典故,宋人在看待平泉故事、書寫平泉故事時表現出多重面向,折射出北宋文化精神及士大夫審美觀念,從而使平泉文學景觀被持續建構為不朽的精神家園。
【關鍵詞】 李德裕;平泉莊園;平泉書寫;文學景觀
中圖分類號:I206"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8004(2025)01-0105-12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晚唐名相李德裕雅好山水,自稱有“林泉深癖”,不但構筑了平泉莊園,且寫詩描繪之,篇幅占其現存詩歌的半壁江山。李德裕通過這些詩賦予平泉空間以詩意,建構出平泉文學景觀,使其成為唐代園林文學的一個動人符號。
學界對李德裕的平泉莊園及其平泉書寫已有研究,如趙建梅總結了平泉詩的隱逸思歸情緒與幽邃、脫俗、孤峭的藝術特點[1];路成文、張麗莎認為平泉莊園構筑了李德裕的精神世界,他的“守園觀”隱含著對家族興盛的期冀與方外之名的追求[2];沈揚、鐘振振分析了李德裕的博物趣味對平泉山居營造的影響,認為李德裕在文本的世界中實現了對平泉山居的文化占有[3],以上為直接相關的研究成果。在關于李德裕研究領域,學界對其生平事跡、政治思想等有較多研究,但李德裕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作品尚未得到過多關注,且研究話題比較分散。羅燕萍[4]、唐誕[5]、唐文婧[6]、方海林[7]的碩士論文分別分析了李德裕的部分詩歌;肖瑞鋒認為劉禹錫與李德裕的唱和詩體現出政治風云的變幻和士人命運的播遷[8]。總體來看,李德裕的平泉書寫仍有研究空間。
有意味的是平泉文學景觀在宋代經歷了持續建構的過程。宋人將李德裕的生平、平泉別業的歷史以及醒酒石的故事聯系在一起,在時代洗禮、景觀變遷、宋代審美與宋人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合力影響下重寫平泉文學景觀,融入了宋代文化精神,這是此前的研究未能展開的。基于這一思考,本文梳理從李德裕到宋代對平泉文學景觀的建構過程,分析李德裕透過書寫表現其文化人格與精神追求、將其塑造為精神空間的具體狀態,以及宋代平泉文學景觀的形成與意義,以此揭示平泉文學景觀的全貌和宋代文人的審美傾向。
二、李德裕缺席的平泉書寫
唐人好園,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后》云:“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余邸。”[9]283洛陽私家園林極一時之盛。李德裕平生極好泉石,《平泉山居草木記》自言:“嘉樹芳草,性之所耽。” [10]684因此竭力“采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11]806,在長慶、寶歷年間營造了頗具規模的園林別墅平泉山莊①。《新唐書》本傳載“德裕性孤峭”[12],其平泉山莊“有虛檻,引泉水,縈回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周圍十余里,臺榭百余所,四方奇花異草與松石,靡不置其后”[13]616-617,景觀與物產盡天下之奇。李德裕一生仕宦漂泊,留駐平泉的時間并不多,僅在大和八年至開成五年(834-840年)間有過三次短期居住。但是,園中的美景與嘉物依然盤桓在他心中,是他心期終老之地,也留下了大量書寫平泉景物的詩篇,構成了最初的平泉文學景觀。
平泉山莊在李德裕身后很快就凋零了,急遽破敗的歷史可以從最得李德裕鐘愛的醒酒石的傳奇經歷中具體而微地表現出來。《舊五代史·李敬義傳》載:“洎巢、蔡之亂……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掘,樵人鬻賣,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保惜者。光化初,中使有監全義軍得此石,置于家園。敬義知之,泣渭全義曰:‘平泉別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違先旨。’因托全義請石于監軍。他日宴會,全義謂監軍曰:‘李員外泣告,言內侍得衛公醒酒石,其祖戒堪哀,內侍能回遺否?’監軍憤然厲聲曰:‘黃巢敗后,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有石哉!’全義始受黃巢偽命,以為詬己,大怒曰:‘吾今為唐臣,非巢賊也。’即署奏笞斃之。”[11]806-807世事無常,唐末天下大亂,東都洛陽亦遭軍閥肆虐,無數屋舍化為灰燼。李德裕曾告誡子孫善保平泉樹石:“吾百年后,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10]682竟一言成讖,果然,平泉的花木被偷掘變賣,最鐘愛的醒酒石也為人所奪。至五代時期,平泉林石蕩然無存,僅余遺跡。《唐語林》載:“怪石名品甚眾,各為洛城族有力者取去。有禮星石、獅子石,好事者傳玩之。”[13]617其命運令人唏噓。李德裕《離東都平泉有詩》末聯云:“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10]601對人對園,都是一個準確而凄涼的預言。
本文擬對李德裕平泉書寫的精神心理以及所營造的景觀世界進行進一步討論,尤以其缺席的書寫為重點。
(一)李德裕平泉詩的主題與內容
對物的迷戀和仕隱苦悶是李德裕平泉詩寫作的兩個基本主題。
1.物的迷戀
李德裕有足夠的財力、權勢支持滿足“林泉深癖”,又兼備詩人的慧眼和收藏家的熱忱,在仕宦漂泊時,以詩營造了一個五光十色、精彩紛呈的“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花木是著墨頗多的部分,詩中涉及紅桂樹、金松、柏、野竹、巖松、松栝、薜蘿、桑柘、鐘菰、藥苗、商山芝、首陽蕨、月桂、山桂、辛夷、寒梅、紫藤、芳蓀、海石楠、重臺芙蓉、紅芍藥、紫櫻桃、梨花、奇筱、女蘿、蕙草、蘭花、蘭苕、杏花、菊等植物。在《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中,有十一首以平泉莊園生長的花木為主題,或贊美其別樣的風貌,如“纖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金松》)[10]720,“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重臺芙蓉》)[10]729;或吟詠其鮮妍芬芳的色香,如“紫艷映渠鮮,輕香含露結”(《芳蓀》)[10]721;或以草木高貴的品性自喻,愿在物的芳華中寄寓人生境界,如“妍姿無點辱,芳意托幽深。愿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潯”(《紅桂樹》)[10]719-720。李德裕亦不吝以深情書寫山莊的動物,尤其鐘愛飛禽,舉凡鸂鶒、巢燕、雁、鶴、鳩、白鷺、彩鴛、鳧鵠等,皆自由靈動,與美景相映成趣。或如清沚上的一對鸂鶒“欲起搖荷蓋,閑飛濺水珠”(《鸂鶒》)[10]722,又如春雨中自在漫游的鳩鳥、白鷺、彩鴛,“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溪邊草更長。梳風白鷺起,拂水彩鴛翔”(《憶春雨》)[10]740。一對猿猴也會喚起詩人格外的感慨,他想象它們被人類捕獲,遠離故山的經歷:“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沖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二猿》)[10]730,見羈的猿猴也許令詩人聯想到落入塵網永被羈絆的自己。
奇石更是這個“物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平泉莊園坐擁商山石、似鹿石、巫山石、漏潭石、海嶠石、疊石、泰山石、羅浮石、釣石等各種奇石。讀者能夠在平泉詩中近距離觀賞它們,獲得類似的感官愉悅,如在水流沖刷下變得“鱗次冠煙霞,蟬聯疊波浪”的疊浪石(《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疊流石》)[10]729;上有綠蘚、紫苔,“仿佛獸潛行”的似鹿石,因石形逼似鹿,遠遠看去“乍似依巖桂,還疑食野蘋”(《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似鹿石》)[10]728。李德裕也追記奇石的來龍去脈,如“于溪人處求得”的釣石,自言“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返伊川,悠然慰衰疾”(《重憶山居六首·釣石》)[10]735,以為人生自適的慰藉;由“兗州從事所寄”的泰山石,“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重憶山居六首·泰山石》)[10]733-734,依然內蘊泰山的光輝,為詩人贊頌。奇石不僅帶來感官欣賞的愉悅和占有的滿足感,更是寄托人格和超脫審美情趣的載體,由此,李德裕筆下的石意象展露出一種象征性。《思平泉樹石雜詠一十首·海上石筍》云:“忽逢海嶠石,稍慰平生憶。何以似我心,亭亭孤且直。”[10]728孤迥特立的海嶠石與詩人產生心靈的連接,詩人從中得到深刻的慰藉,人格化的奇石就是李德裕在精神上的自我托付。《題奇石》又云:“蘊玉抱清輝,閑庭日瀟灑。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10]570《新唐書》本傳曰“德裕性孤峭”,懷抱清輝、孤高獨立的不只是一塊又一塊的奇石,更是在身不由己的政治動蕩中,詩人對自我命運的抒懷、自我形象的確立與塑造。
2.仕隱苦悶
李德裕的政治顯赫身份及與晚唐黨爭的密切關系,不能不影響到對其文學創作的認識和評價,平泉詩也不能例外。在平泉詩所描繪的幽美景觀中,恰恰蘊含著李德裕徘徊于江湖與廟堂之間的矛盾苦悶情懷。
平泉詩情的基調是李德裕的思歸之情——無論吟詠平泉山居的人、事、物、景,最終的落腳點都是歸隱。如“麇麚來澗底,鳧鵠遍川潯。誰念滄溟上,歸歟起嘆音”(《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10]743、“累榭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掇汀蘋”等等(《首夏清景想望山居》)[10]727,從思戀景色到渴望歸隱的表達不可勝舉。然而,莼鱸之思的頻繁出現不代表李德裕愿意舍棄現實,隱居江湖,縱情山水。他在《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中如此寫道:“乃知軒冕客,自與田園疏。歿世有遺恨,精誠有所如。嗟予寡時用,夙志在林閭。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鰷魚……”[10]696縱使田園佳景如許,李德裕與之仍有疏離之感,事實上,“軒冕客”與田園的對立貫穿在他一生創作的平泉詩中,這昭示了一個事實:即使李德裕在詩中無數次追慕野客與幽人,卻未有一刻忘卻其煊赫門第和顯貴的現實地位。他以山水嘉興為態度,試圖去調和乃至淡化仕宦之世俗色彩,然而,調和正意味著對立的存在。《唐語林》的記載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佐證:“李德裕自金陵追入朝,且欲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周游,不暇久留。”[13]616開成二年(837年)李德裕奉詔從金陵還朝,事關宰相任用,事態緊急。途經洛陽,他依然要在一夕之間秉燭夜游平泉,對平泉的熱愛與癡情確鑿無疑。然而,最終的“不暇久留”卻表明,在平泉與政治前途之間,李德裕心中的天平依然傾向著京城。
李德裕在平泉詩中所著力強調的與政治的區隔,正凸顯出與政治千絲萬縷的聯系。夢中的隱退終究難以實現,他在《退身論》中說:“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 禍機不測……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10]786將仕宦的延續看作避禍的方式。而那個高呼“我有愛山心,如饑復如渴”的詩人,終究沒能實現他的愿望。李德裕于開成五年至會昌六年(840—846年)任宰相,后又外放為汝南節度使(846年),最終貶死崖州(860年)②。不在洛陽的日子里,他一直追憶平泉,而平泉卻如海市蜃樓,終于可望而不可即。
(二)缺席的平泉書寫:李德裕精神世界的詩化建構
追憶,才是李德裕寫作平泉詩的真實狀態。現存的八十多首平泉詩中,近七十首都是李德裕不在場時的產物,因此,平泉詩少有對景觀面對面的摹寫,而更多是對莊園景觀的想象——未曾經眼的景觀也在想象中被賦予實體。
“平泉”是詩人透過詩歌建構的一個文學景觀,也正是“缺席”的平泉書寫造就了李德裕的精神世界。李德裕曾在《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中如此描述書寫平泉時的心情:“我有愛山心,如饑復如渴。出谷一年余,常疑十年別。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卮,冬思玩松雪……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10]701-702顯然李德裕本人也意識到頻繁追憶平泉景物的不尋常,因此作出自辯。他傾訴了身遠山林、卻于心中時刻縈繞的熱愛。如此深切的情懷令他“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仕途坎壈,未及歸隱,縱情山水似乎遙不可及,這促使李德裕創作出詩的平泉以為慰藉。
平泉詩中充溢著對莊園景觀的想象,深情包蘊其中。夏季,松、竹、泉、月共同造就清幽涼徹的境界:“密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夏晚有懷平泉林居》)[10]697“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翠岑當累榭,皓月入輕舟。”(《初夏有懷山居》)[10]709秋季,碧綠的原野令人舒爽,菊與蒿點綴出高潔的情操:“綠筱連嶺多,青莎近溪淺。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剪。”(《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10]699冬季,平泉化作冰雪世界,寂寞無人:“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薜蘿。竹梢低未舉,松蓋偃應多。山溜隨冰落,林麇帶霰過。”(《晨起見雪憶山居》)[10]737更有出離塵世的遐思。四季中,留下最多筆墨的是春,李德裕甚至從未見過春天的莊園,卻憑借詩意的想象勾畫了一幅幅清麗自然的春日園景,一償“未嘗春到故園”的遺憾[10]739。如《憶平泉雜詠》組詩所詠,思及“細雨入池塘”的柔婉(《憶春雨》)[10]740,“春晚紫藤開”的燦爛(《憶新藤》)[10]740,“林間布谷鳴”的催耕(《憶春耕》)[10]741,以及“雪開喧鳥至”的春暖(《憶初暖》)[10]738,主題同是春景,在刻畫時卻力求立體多面,或早或晚,或晴或雨,有近有遠,動靜結合,自然靈動,意象悠然。除卻四季景觀,園內造景也在詩句中被細細展示,瀑泉亭、西園、竹徑、花藥欄、釣臺、藥欄、流杯亭、雙碧潭等皆有專詩吟詠。平泉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鳥,乃至每一個角度,都被細心摘取,精心編織,逐一記錄,形成難以磨滅的文字印記,成為平泉景觀的直覺印象。
李德裕在詩歌中頻繁表達的追憶是一種自我敘事,其落腳點在于,將平泉看作僅屬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幫助自身摒棄塵世的紛擾,暫時忘卻政治的波詭云譎,在靜謐的隱居生活中尋獲自己的精神家園。這就是說,李德裕不但建造了現實的園林,還構建了一個獨屬于自己的文學化的精神空間。如果把現實平泉的構建稱為“在場”的書寫,精神平泉的構建就是“缺席”的書寫,李德裕的書寫主要是后者。在想象的平泉里,李德裕總是孤身一人,極少允許朋友、同僚、世間親緣的介入,所以這里沒有官場政治與家庭生活,可以放下些許塵世負擔,獲得自由和超越的境界。這造成了一個結果:平泉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夢空間,是李德裕的“桃花源”,即身在官場,心在平泉,就是平泉書寫中詩人缺席的意義,也是平泉書寫的主要價值。正是這一點引起了后人極大的興趣。
平泉的物質基礎也許轉瞬即逝,散落無蹤,但是平泉的文學景觀通過文字得以保存,又通過文字繼續流傳,在不斷的追憶與想象中成為人們歷史記憶的主要來源與基本形式,并進一步成為士大夫精神建構的范本與藍圖。
三、宋人建構平泉文學景觀的多個層面
平泉地處洛陽伊闕以西,即李德裕在《平泉山居誡子孫記》中提到的位于“龍門之西”的一條山溝。此溝峰巒環抱,林木蔥蘢,因有“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故稱平泉,平泉“涌不騰沸,淡然洌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鑒”,因泉溫較高,而山嵐清冷,二者相激而霧氣繚繞,使山林美如仙境。因此,平泉在唐代已備受眾多達官的青睞,多建有莊園別業,亦以“平泉”為名,即“自東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靈泉賦》)[10]688。可見,無論是指地理,還是莊園,“平泉”二字在唐代都曾是泛稱,它的專名化是隨著李德裕平泉詩的大量創作而悄然發生的。換言之,平泉文學景觀建構使“平泉”之名在物質與文化兩個層面為李德裕所獨有,成為整合了特定文化與文學審美內涵的專名,在李德裕和平泉山莊都消失后,仍然在不斷延續與發展。
在宋人筆下,就一般意義來說,“平泉”是稱譽園林之美的一個舊名雅稱,又可借以表達對閑適人生的向往之情。這是基于“平泉”的物質特征與園林屬性的偏于審美意義的化用。在更深的層面上,“平泉”是對李德裕政治人生的隱喻,因此是反思政治追求、出處進退和物欲人情的標靶。這是基于“平泉”的歸隱內涵與精神屬性具有更強的政治文化批判意味的建構。
(一)基于園林勝跡閑適情懷的“平泉”文學建構
如同唐人用典偏好“以漢喻唐”一樣,宋人亦好用唐典,這內蘊著對唐代歷史文化的強烈認同情感。平泉在宋代唯余遺跡,其風韻情致卻記錄于李德裕的文字,深契于宋人心中。凡書寫園林美景、草木勝跡,表達褒美之情時,“平泉”便是符合情境的最佳語典。紹興五年(1135年),張守和呂本中曾造訪名臣李綱的園亭,此時李綱以罪休官,暫回福州閑居,二人詩句多有褒揚安慰之意。張守《次韻李丞相園亭二首》其二云:“疏泉■石寄高懷,仙藥名花取意栽。履道醉吟齊步武,平泉景物付云來。”③前用“履道醉吟”四字稱道其詩酒風流,后用“平泉景物”四字贊美其園亭景致。呂本中《次韻李伯紀園亭》其一云:“可但海山勝綠野,頗知風物似平泉。”[14]用“綠野”和“平泉”二典,褒揚李綱園亭的“海山”與“風物”。趙翼曾指出“詩詞專用本家本人事”的用典慣例[15],張、呂二人用“平泉”入詩,既見其博雅,也契合李綱的姓氏、出身與地位,是很貼合人物與情境的做法,只是別無余意。除卻風光之美,宋人用“平泉”之典,也有取于李德裕對恬淡自然的鄉居生活、悠游自適境界的向往與追求。李彌遜《次韻葉觀文游賢沙鳳池安國之作》云:“登臨賴陶寫,可但思平泉。郊原問農事,柔桑起蠶眠。”④ “陶寫”即怡悅情性,消愁解悶之意,原出《世說新語·言語》,王羲之所云“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16]。此詩將“陶寫”與“平泉”并舉,意在借美景以開懷抱。另如虞儔《暇日邀王天任諸公游南坡天任有詩因次韻》云:“君家有西園,望我南山巔。觴詠繼曲水,花石希平泉。” ⑤白珽《湖居雜興八首》其四云:“相國平泉水竹居,吳山花石世間無。游人馬上休回首,一半春風在里湖。”[17]也都是以平泉草木之盛、花石之奇為依傍,抒發湖山嘉興以悅己悅人。
其實,以“平泉”為贊美園林之美及閑適生活的語典,乃宋人文化審美傾向之一隅。前揭“履道醉吟”和“綠野”都是宋詩常典,后者指唐憲宗宰相裴度晚年在洛陽集賢里所造別墅綠野堂,與“平泉”常常并用。關于綠野堂,《舊唐書·裴度傳》云:“自是,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于集賢里,筑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回環,極都城之勝概。又于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水貫其中,釃引脈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皆從之游。”[18]可見“綠野”極一時山川風物之盛,是洛城名士常相聚會賞樂之所。“平泉”與“綠野”不僅同為洛陽名園,在意義上也有高度的互補性,宜于捉對使用,以豐富詩旨。它們聯翩出現在宋人的壽詞及賀老詞中,營造令人身心舒暢的景觀氛圍,如“綠野舊游,平泉雅詠,霞舒煙卷朝昏”(張元干《望海潮·為富樞生朝壽》)[19]1097,“綠野風光,平泉草木,爭似梅山好”(姜特立《念奴嬌·庚申生朝》)[19]1606,“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為先生壽!”(辛棄疾《水龍吟·甲辰歲,壽韓南澗尚書》)[20],“未可卷懷袖手,續平泉莊記,綠野堂詩”(劉克莊《漢宮春·陳尚書生日》)[21]7185等。裴、李同為唐代名相,“平泉”與“綠野”是名臣退居之所,有對退隱生活的美好期待,又有極雅致精麗的美景,在壽詞中成對出現,可助興添雅,也形成了南宋祝壽風俗的一個顯著文化特征。當然,“平泉”與“綠野”的內蘊不止于此。因為平泉之怪石草木蕩然,命運令人唏噓;綠野堂曾薈萃天下風流,裴度晚年仍出任要職,歸老園亭的盟約終成一夢。所以,宋人用此二典,也有取其“不如意”的一面,抒發歲月如流、美景與功名易逝的感懷。如“平泉有墅空流水,綠野無人但繞垣”(晁沖之《傷心》)[22],“綠野移春花自老,平泉醒酒石空存”(王安中《安陽好》其六)[19]752等,一經渲染,頓覺人生空茫,滿懷傷憂。另如“蕭散香山與輞川,功名綠野及平泉”(汪藻《題張資政汝川圖九首》其九《甘陂莊》)⑥,“半畝園林數尺堂,凡花疏竹小池塘。平泉綠野休相笑,事業功名合自量”(周必大《南園筑小堂鄰里侯旸獻上梁文戲成小詩記實解嘲》)[23]等,又有對過度追求功名的否定,故以自適的態度解嘲。這是“平泉”典故的又一層用意。趙翼《甌北詩話》云:“詩寫性情,原不專恃數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則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詩者借彼之意,寫我之情,自然倍覺深厚。”[24]“平泉”“綠野”之典為宋人所關注,正是由其傳達詩情的深厚意蘊所決定的,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現。
(二)基于政治人生隱喻的“平泉”文學建構
宋人對“平泉”的深層建構,建立在對李德裕政治人生的認識之上。李德裕對平泉山莊的苦心經營,對平泉山川風物的酷嗜之情、追憶書寫與歸隱期待,以及累居高位卻貶死朱崖的政治遭際等,都是直接影響宋人感受與書寫“平泉”的基礎。無論是閱讀“平泉”,追憶“平泉”,或身臨“平泉”遺跡,從文字、想象和殘垣斷壁中得來的感受與認識,都會不期然地與其對歷史、政治、文化的認知與體悟相融合,與其人生的遭際感受和審美傾向相融合,借著諸多場景予以文字表達,傳達出歷史的滄桑、現實的迷茫與個體的感喟,必然內蘊時代文化精神與審美傾向的深刻痕跡,從而完成更深一層的平泉文學景觀建構。
首先,李德裕人生浮沉的遭遇與平泉山莊的興衰是“平泉”故事令人嘆惋的另一側面。這一跟隨在美景之后的慘淡世情與陵谷變遷,牽連著宋人的思緒情懷,他們將感慨系之,詩興滿懷,嘆惋曾經的繁盛與目下的荒寒。宋人寫詩,正是歐陽修所謂“讀《山居詩》,見文饒夢寐不忘于平泉,而終不得少償其志者,人事固多如此也”的詩意表達[9]298。他們借助平泉故事,傾訴懷抱,自澆塊壘。早在梅堯臣的感受里,曾經的名園就已是“廢宅長春草,故山存舊碑”的破敗景象(《依韻和刁經臣讀李衛公平泉山居詩碑有感》)[25],這如同一聲定音鼓,奠定了群聲齊奏的基調。司馬光親臨平泉,目見荒寒,賦詩紀游,就是隨后發出的一聲強音:“相國已何在?空山余故林。向時堪炙手,今日但傷心。陵谷尚未改,門闌不可尋。誰知荊棘地,鶴蓋舊成陰!”(《游李衛公平泉莊》)[26]將山莊與主人的命運同構,炙手可熱的相國早已湮滅,空山不見冠蓋勝跡,追求功業與奢華的意義何在?韓琦的“平泉幾易主,況乃刺史宅”(《題辛夷花》)[27]把這種感喟擴展推衍到更廣泛的人群。王灼的“平泉山居付夢想,石上刻字空照日”(《 李仲高石君堂》)⑦,陸游的“樂天十年履道宅,贊皇一夕平泉莊。公看富貴定何物,一笑乃復坐此妨”(《題閻郎中溧水東皋園亭》)[28],劉克莊的“平泉花木奇樟檜,辛苦栽培竟屬誰?”(《雜興四首·其四》)[21]1403云云,都是這一情緒的延展。他們分詠了一個共同的主題:富貴榮華如過眼云煙,功名仕途不過千秋大夢,滲透了世事無常的感慨。這種自白居易《傷宅》以來確立的抒情模式,被宋人移諸“平泉”故事,一抒亙古未易之世變情懷。
有意思的是,平泉故事可以用來憑吊與覺悟,也可以用來自警與贊頌。宋人在為新建園堂撰寫記文時,曾以李德裕的平泉遺恨為現實的對照,贊揚新成園林主人的盛德與清醒。理宗淳祐初,劉克莊為妻兄林公遇棄龍圖閣學士,歸隱林泉后所筑石塘撰《新筑石塘記》云:“昔李贊皇謂鬻平泉非吾子孫,以平泉一草一木遺人,非佳子孫。柳子厚謂上世藏書三千卷在善和宅,然贊皇自不能一夕安平泉,善和宅及子厚在已三易主。今林氏之尊老遠矣,而代有象賢,愈蕃而大。樵牧愛護其松楸,郡邑表章其宅里。予嘗訪其屋壁,舊藏則手澤如新,曾玄論著,篇帙多于祖禰,是豈非盛德之后,積善之家乎?”[21]3934贊賞其勇于進退善保遺澤的盛德。淳祐九年(1249年),趙葵堅辭右相兼樞密使,回到建于長沙錫山的莊園群山囿堂。此堂之名出自韓愈《南山詩》“茲維群山囿”句[29],理宗親書以寵之,而劉克莊受命撰《群山囿堂記》,此堂固然是“信開辟以來殊尤巨麗之觀也”,但劉克莊在文中著力表彰的是趙葵在圣眷正隆時急流勇退的自省意識:“蓋天下清絕之景,常屬之閑退之人。若夫仕至將相,安危佩于身,事物衡于慮,負夔禹之望,而抗巢許之志,未有能兼之者。”然公身居高位,毅然角巾東路,“惟退惟閑,斯堂之景遂為公有”,既得“合族交賓、論文樂飲”之趣,又“曷嘗一飯忘吾君”。在他看來,趙葵的選擇與“昔平泉竹石,僅獲一夕之享;綠野鐘鼓,不能蓋晚節浮沉之愧”[21]3853-3854,胸懷境界不啻有天壤之別。事實上,以劉氏與林、趙的交誼,這兩篇記文雖不能是純出于社交敷衍,但人情以安居為樂,而且當時歸隱也未必是終局。劉克莊在《群山囿堂記》里明白表示趙葵必有復起之日,而后來也確實如此。趙葵竟于八十一歲高齡卒于小孤山舟中,則“負夔禹之望,而抗巢許之志”的頌揚也無非止于當時,其實并不比李、裴的晚節更高尚。但李德裕的平泉遺恨給予后人的印象之深,卻由此可以想見。
劉克莊的書寫是旁觀者的意見,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北宋名相文彥博從自身道德追求出發,從為官修身之道批評前人李德裕,著墨更多,更可體現北宋士大夫秉持儒家思想的整體傾向。嘉祐三年(1058年),文彥博罷相,改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在洛陽避禍的日子里,常得閑暇,游覽勝跡,因此得以踏足平泉遺跡,所賦《游平泉作》詩一首,表達了當時紛紜的思緒感情:“一崦抱溪斜,前朝輔相家。遺基皆瓦礫,古木尚煙霞。夙昔東山墅,留連上殿車。雖云營退隱,未免逐豪夸。事往如飛鳥,林空噪暮鴉。池平無舊鳳,堤壞有殘沙。野叟猶能說,樵夫亦共嗟。至今巖石下,多長紫薇花。”末句自注:“平泉花木無孑遺,然巖谷間猶多紫薇花,是其遺種乎?”[30]259從眼前殘跡聯想到如煙的往事,一代英豪已是野叟樵夫嗟嘆的對象,唯有巖下怒放的紫薇呼應著舊時的豪奢。“雖云營退隱,未免逐豪夸”二句,仍是詩中警句,這是對李德裕的批評,也是對自己的提醒。罷相顯然是文彥博仕途的挫折,令其心有苦悶,但從此詩看,他并不頹廢放縱,仍有一腔自激自勵的志氣。所以,文彥博重溫了《平泉花木記》,寫下《又讀平泉花木記》三首,直截了當地批評了李德裕從政處世之道。其一云:“歷覽《平泉記》,文饒性苦奢。如何伊上墅,多是日南花。”本詩自注云:“當時文士詠平泉有‘日南太守獻名花’之譏。”其二云:“上黨夷兇日,太和歸國年。此時能勇退,應遂老平泉。”其三更是表意無隱,指斥意味更濃:“吾觀李太尉,所失在夸權。名遂不知退,膏明惟自煎。終身戀華組,何日到平泉。徒有思歸意,歌詩盈百篇。”[30]260-261顯然,文彥博的批評集中在“性苦奢”與“夸權”之上,尤其以戀權為害最大,因此導致“名遂不知退,膏明惟自煎”的嚴重后果,自陷危地,不得善終,縱有歌詩百篇表達思歸之情,其實是自貽笑柄而已。文彥博的批評有其思想根源,其《座右志》云:“士君子不達即已,茍達焉,可不益思慎其名檢乎?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夷險一致,終始不渝。”“又嘗患士之多上人而自大者,殊不能景行先哲,見賢思齊。”并推崇“藏器抱德,與時隱顯”的處事原則,認為君子當藏器隱睿、謹慎行事、謙卑自守,不可自得自滿,多事夸耀。他以唐朝宰相鄭余慶為政治楷模,稱之為“真君子之儒”,認為鄭氏“砥名礪行,謙卑自牧,踐歷臺省,以蹇諤聞。侃侃于公卿間,未嘗俯仰媚于一人,必以其道。祗事四朝,出入將相,逮于晚節,不渝素行,可謂以功名終始者矣”,可為效法的榜樣。他本人也歷任四朝,三度為相,在宦海浮沉中持重守節,忠厚惇大,盡畢生之力,成為一個“君子之儒”[30]572-573。《宋史》本傳評曰:“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沖御侮于千里之表矣。”[31]他對鄭余慶“祗事四朝……可謂以功名終始者矣”的向往,最終成為自己人生的注腳。由此觀之,文彥博批評李德裕在位時借權勢營造莊園,夸耀權勢;遇到困境時,不善保身,自取敗亡之道的態度,是非常自然的。如此追求,也正是宋代士大夫精神風貌與道德追求的一個典型縮影。
(三)基于物欲批判的“平泉”文學建構
宋人批評李德裕的又一個領域,是對其強烈物欲的譴責。在宋人眼中,這時的平泉反而成為埋葬李德裕苦心追求的泉林奇石的墓冢。其實,宋代社會的藝術與審美活動空前繁榮,宋人并非不熱愛花木泉石,所以這種批評自然有其深意。其關鍵在于,宋人把李德裕的“林泉深癖”視為一面鏡子,時刻以過猶不及的道理自我提醒對物欲的控制。這種態度與宋代的文化特質及士大夫思想意識密切相關——宋人在物欲問題上主要繼承了儒家的基本價值取向,強調“存理制欲”,對“欲”持限制性態度。在宋人的日常審美活動中,審美與物欲之間存在一種緊張的對立關系,在對平泉的批評中,這種關系被深刻揭示出來。
一代文宗歐陽修曾作《平泉草木集跋》,著力批評李德裕對物的迷戀:“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或至疲敝精神于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9]297歐陽修點出李德裕身處高位卻依然旺盛的“好奇貪得之心”,認為這使他精神疲憊,這種執著的占有欲已經近乎愚蠢了。事實上,南宋刊刻的《平泉草木記》后已有此跋文:“《平泉草木記》跋后印本尚有六七十字,深誚文饒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以取禍敗,語尤緊切,足為世戒。”[9]25可見歐陽修的意見已成為一定程度上的權威文本,形塑著宋人對李德裕的基本認識。從后來的創作實踐看,歐陽修的意見相當于給李德裕的“林泉深癖”的性質定了調,對李德裕人生遭際與貪婪遭禍的批評已成為宋代的主流意見。文同《書平泉草木記后二首》,其一云:“衛公當國日,力與天地均。平泉植草木,取盡四方春。海岳欲必得,亦能役鬼神。可笑身未冷,已聞屬他人。”其二云:“公豈不聰明,嗜好乃如此。若非以私餌,是物安至止。彼致者何人,定非端潔士。草木固為塵,丑名終未已。”⑧在文同看來,平泉草木的聚集是李德裕以權力為“私餌”“取盡四方春”的結果,否則天下奇物何以能匯聚于平泉,而助其滿足物欲的人被定義為“定非端潔士”。結果,隨著李德裕的失勢,奇物業已為有力者奪去,唯余丑名而已。顯然,對物的迷戀是導致李德裕失敗的重要原因,而天下奇物隨著權力的轉移又進入下一輪回!可見文同對物之迷戀的政治道德譴責躍然紙上。汪藻的《盡心堂為張丞相題》亦云:“向來卜筑營草木,汲汲可笑平泉愚。”[32]這是對李氏之“愚”的另一種表述;而姜特立僅是為直廬砌一道臺階,也會有“為語平泉公,經營毋太廣”的告誡(《直舍作小砌》)[33]12,再讀到《平泉草木記》,仍未免生出“平泉草木頻移主,西洛園池幾換人。但把風花觀世界,莫將金石認吾身”(《因觀贊皇平泉草木記有感》)[33]135的勸勉與譏刺內涵仍然落實在所謂“愚”上。事實上,所謂“經營毋太廣”,以及“可笑平泉愚”,就是宋人批評李德裕物欲迷戀的典型話語。
這種批評意識仍深契在宋代的精神文化之中。我們知道,“物的審美”是北宋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命題,“關系到如何理解士大夫物質生活與精神層面的相互影響與塑造”[34]。士大夫對待物的態度具有辯證屬性,他們一方面為物的感性之美所動,樂意欣賞,乃至占有物質,另一方面視“美的誘惑”如虎狼[35]171,秉持著“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尺度,以此與儒家思想相調和。比如,賞石本是宋代的時代風尚,大批嗜石的文人和禪僧道士相互觀賞、贈送怪石,甚至形成了一個“人文旨趣較濃的怪石愛好者的圈子”[36]。但是,溺于物的態度頗為宋人不取,他們對“美的誘惑”持有意識地抵抗、自責和警惕態度。如以怪石為平生愛好之物的蘇軾,他與仇池石的故事天下盡知,但他仍試圖以自己的方式調和人與物的關系。《雪浪石二首》其二云:“洛陽泉石今誰主?莫學癡人李與牛。”[37]以李德裕和牛僧孺式的占有欲自戒和戒人。蘇軾認為,要破此貪欲困局,須放棄對物的占有心,要做到“定心無一物”,即“不摻雜占有欲的占有”的狀態[35]172。他在《寶繪堂記》里又說:“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于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38]即人一旦為占有心主宰,怪石就失去了審美意義,若是對物不存占有之心,則此局可解。換言之,既要滿足對“物的審美”,又要避免對物投入過度的情感,即在審美追求與感官體驗方面保持適度的中庸立場。蘇軾以“寓意”的態度,消解“留意”的執念,為“人”與“物”塑造了一種新的關系,達到“游于物之外”的審美境界。他所持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之觀點深刻影響后人處理人與物關系的基本態度。
迨至南宋,葉夢得對李德裕之事大發議論,他批評了李德裕對物的占有欲,認為李德裕告誡子孫善保“平泉一樹一石”,是對物的過分追求,這也導致孫輩向監軍求取醒酒石、最終造成悲劇性的結果。在他看來,“一石亦何足言”,也就是說,一塊石頭實在是太微小,并不值得人們為之所奴役,“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后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對于人與物之間關系的難題,葉夢得一方面承認自己也有“自不能解”的好石之癖,曾“借錢買石,得石祛病,抱石而眠”;一方面認為自己沒有“文饒之病”,凡是自己收藏的石頭,只要客人喜歡,都“聽其自取以去”。他說:“嘗戲謂兒童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39]164-165可見,“不為物所累”之觀念,成為調和宋人的收藏愛好與物癖道德問題的一把鑰匙,宋人試圖在有限的范圍內滿足自己的收藏愛好與審美愉悅,同時巧妙化解道德層面的難題。
元明清人對平泉的接受與宋人可謂一脈相承,有大量文學作品書寫、引用、再創造平泉。元代的宋沂用平泉草木之典為致仕者助興添雅:“平泉山木芳華里,終日垂紳擁玉魚。”(《奉餞御史中丞汪公大司徒致仕歸隴右》)[40]清代的查慎行以平泉草木贊美園亭美景:“何似贊皇行樂地,手栽花木記平泉。”(《重過相國明公園亭四首·其一》)[41]隨著文人畫的繁盛,這一書寫方式也體現在題畫詩中,如廖道南《題鄒黃山畫》云:“時人不解神仙宅,卻道平泉李相莊。”⑨翁方綱《張荔亭溪山選勝圖》曰:“夢游問奇載酒處,一水一石懷平泉。”⑩斗轉星移,平泉故事依舊引發后人的興廢之感:“君不見金谷繁華斗一時,綠珠墜樓竟何益。又不見平泉醒酒石可憑,須臾轉入他人宅。”(《石梅行和鄭給舍作》){11},“金谷名園委蔓草,平泉荊棘無人掃。榮華瞬息可奈何,空令過者傷懷抱。”(《題安仁余氏留余堂》)[42]363-364李德裕與平泉的故事也一度被后人重寫,他們帶著悵然之情再度重溫這位晚唐名相的一生。朝鮮李朝哲學家樸世堂追記云:“一石如今更勿言,平泉終不屬孱孫。人生勤苦都無益,末葉誰能念本根。”“敢望子孫能保守,唯求身死葬其間。墓前萬古峨峨石,不阻后人來借看。”“由他不得不由他,遺語雖勤恨謾多。死后此身猶未料,其余萬事奈渠何。”(《偶記李衛公平泉石事有感三首》){12}對李德裕平生遭際的嘆惋之情,與宋人別無二致。在異代不斷的追憶與書寫之中,平泉故事被不斷接受與續寫。
四、結語
李德裕的平泉書寫是用文字建構景觀并占有景觀的一個實例,他以“詩性擁有”的方式在平泉打下了自己的印跡{13}。這使我們體會到書寫的力量——李德裕與平泉莊園因文本而不朽。因其不朽,故而永存,成為歷史記憶,從而在宋人及后人的不斷想象與書寫中持續發展。正如阿萊達·阿斯曼所言:“文化文本具有一種能力,使作品所負載的能量不會消失殆盡,而是隨著不斷閱讀而傳播并存儲在記憶之中,跨越歷史的鴻溝結合在一起。”[43]平泉之名,就是在文化與歷史記憶參與下,被賦予與寄托了多種價值和意象,成為一種書寫歷史、建構文化、敘述故事的路徑。
在文學史上,如平泉文學景觀的持續建構的例子不少,曹操的銅雀臺、石崇的金谷園、武昌的黃鶴樓、裴度的綠野堂、白居易的履道坊宅園等,都以其特有的故事和文化意蘊,不斷獲得書寫的機會,發展成燦爛的文學風景,成為寶貴的文化遺產。這種建構是一種文化生成機制,也是一種傳播機制,以不同的表達方式在“不同的文化符號中為文學的人學本質保駕護航”[44]121。《水滸傳》第一百零八回,盧俊義與朱武攻取城池,燕青預感不祥,伐木以備后路時,書中寫道:“統領眾將兵馬,離了大寨,由平泉橋經過。那平泉中多奇異的石子,乃唐朝李德裕舊莊。”[45]平泉的倏然閃現表明這份文化記憶已經延伸到更加遙遠的空間{14}。
注釋:
①" " "康駢《劇談錄》卷下“李相國宅”條云:“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間,無物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威勢之使人也。”據《太平廣記》卷四百五補。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271頁。
②" " "參傅璇琮著《李德裕年譜》,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37頁。
③" " "張守《毗陵集》卷十六,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④" " "李彌遜《筠谿集》卷十二,清乾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⑤" " "虞儔《尊白堂集》卷一,清乾隆翰林院鈔本。
⑥" " "汪藻《浮溪集》卷三十二,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⑦" " "王灼《頤堂集》卷三,宋乾道八年王撫干宅刻本。
⑧" " "文同《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明萬歷三十八年吳郡吳一標刊崇禎間虞山毛晉重訂本。
⑨" " "陳邦彥《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卷十五,清康熙四十六年內府刻本。
⑩" "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三十九,清刻本。
{11}" " "佘翔《薜荔園詩集》卷四,清鈔本。
{12}" " "樸世堂《西溪先生集》卷二,茂朱赤裳山史庫所藏朝鮮總督府寄贈本。
{13}" " "沈揚、鐘振振評曰:“李德裕在文本世界中繼續維系著對平泉山居的占有,以山居景觀為對象的詠物詩,詮釋著他不朽林泉的幻夢。”(《李德裕平泉詩的博物學考察》,《中華文化論壇》2021年第1期,第128-136頁)。
{14}" " 關于“文化記憶”的含義,參阿斯特利特·埃爾著,馮亞琳譯《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參考文獻:
[1]" "趙建梅.試論李德裕的平泉詩[J].文學遺產,2005(5):141-144.
[2]" "路成文,張麗莎.平泉,別業與李德裕的精神世界——兼談李德裕的“守園觀”[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6):71-79+178-179.
[3]" "沈揚,鐘振振.李德裕平泉詩的博物學考察[J].中華文化論壇,2021(1):128-136.
[4]" "羅燕萍.李德裕及其詩文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04.
[5]" "唐誕.李德裕詩文研究[D].漳州:漳州師范學院,2012.
[6]" "唐文婧.李德裕及其詩歌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9.
[7]" "方海林.李德裕的文學創作及其與文壇關系[D].蕪湖:安徽師范大學,2006.
[8]" "肖瑞峰.論劉禹錫與李德裕的唱和詩[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92-98.
[9]" "曾棗莊,劉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10] 傅璇琮,周建國.李德裕文集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2018.
[11] 薛居正.舊五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
[12]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5342.
[13] 王讜.唐語林校證[M].周勛初,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
[14] 韓酉山.呂本中詩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7:1064.
[15] 趙翼.陔余叢考[M].欒保群,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63:475.
[16] 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M].北京:中華書局,1984:68.
[17] 全元詩[M].楊鐮,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161.
[18] 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4432.
[19] 全宋詞[M].唐圭璋,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20] 辛更儒.辛棄疾集編年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5:829.
[21] 辛更儒.劉克莊集箋校[M].北京:中華書局,2011.
[22] 宋詩鈔補[M]//宋詩鈔.吳之振,呂留良,吳自牧,選.管庭芬,蔣光煦,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1061.
[23] 宋詩鈔初集[M]//宋詩鈔.吳之振,呂留良,吳自牧,選.管庭芬,蔣光煦,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1635.
[24] 江守義,李成玉.甌北詩話校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456.
[25] 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198.
[26] 李之亮.司馬溫公集編年箋注[M].成都:巴蜀書社,2009:299.
[27] 全芳備祖[M].陳景沂,編.祝穆,訂正.程杰,王三毛,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415.
[28]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
[29] 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M].郝潤華,丁俊麗,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12:201.
[30] 申利.文彥博集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
[31] 脫脫.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264.
[32] 汪藻.浮溪集[M]//四庫輯本別集拾遺.欒貴明,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85.
[33] 姜特立.姜特立集[M].錢之江,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34] 姚華.蘇軾詩歌的“仇池石”意象探析[J].文學遺產,2016(3):155-165.
[35] 艾朗諾.美的焦慮:北宋士大夫的審美思想與追求[M]. 杜斐然,劉鵬,潘玉濤,等譯.郭勉愈,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6] 周裕鍇.蘇軾的嗜石興味與宋代文人的審美觀念[J].社會科學研究,2005(1):169-176.
[37] 蘇軾.蘇軾詩集校注[M]//蘇軾全集校注.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4248.
[38] 蘇軾.蘇軾文集校注[M]//蘇軾全集校注.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1122.
[39] 葉夢得.巖下放言[M]//全宋筆記.徐時儀,整理.鄭州:大象出版社,2019.
[40] 顧瑛.草堂雅集[M].楊鐮,張頤青,祁學明,等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8:652.
[41] 查慎行.敬業堂詩集[M].范道濟,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7:612.
[42] 劉基.劉伯溫集[M].林家驪,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43] 文化記憶理論讀本[M].阿斯特利特·埃爾,主編.馮亞琳,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137.
[44] 王春艷,加曉昕.巴山文學與其他藝術融合的文化符號化探究[J].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23(4):121-125.
[45] 王利器.水滸全傳校注[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3544.
責任編輯:楊" "釗;校對:吳" "強
Li Deyu’s Pingquan Writing and the Continuous Construction of the Pingquan Literary Landscape in the Song Dynasty
LIU Peiqi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207, China)
Abstract: Li Deyu, a famous minister of the late Tang Dynasty,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Pingquan Poems” depicting the private garden Pingquan Manor, focusing on the landscapes of flowers, trees, animals, and strange stones, creating a colorful and wonderful “material world”, reflecting his obsession with objects and the distress of being a civil servant and a recluse. In conclusion, Li Deyu not only built a realistic garden, but also constructed his own spiritual space through absent writing. In Song Dynasty, the story of Pingquan was condensed as a literary allusion, and the people of Song Dynasty showed multiple aspects when looking at and writing the story of Pingquan, reflecting the cultural spiri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scholars, so that the literary landscape of Pingquan was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as an immortal spiritual homeland.
Key words: Li Deyu; Pingquan manor; Pingquan writing; literary landscape